- +1
數字社會|關于數字社會學的目標和目的的反思
本文經作者許可譯自Tom Redshaw, “What Is Digital Society? Reflections on the Aims and Purpose of Digital Sociology”, Sociology, 00(0) 1-7. 湯姆·雷德肖是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社會學博士,索爾福德大學衛生與社會學院講師。這是一篇書評論文,評的是:
瑪麗·吉科(Mary Chayko):《超連接》(Superconnected), London: SAGE, 2018。中譯本見黃雅蘭譯,清華大學2019年版。
茱蒂·威吉曼(Judy Wajcman)和奈吉爾·多德(Nigel Dodd)編:《速度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Spe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費奧納·阿特伍德(Feona Attwood), 《性媒介》(Sex Media), Cambridge: Polity, 2017。
2019年是萬維網(World Wide Web)的30歲生日。蒂姆·伯納斯-李的這一重要創新把互聯網從主要用于軍事和研究目的的、相對較小的計算機網絡變成了今天的全球傳播基礎設施。這場技術革命形成了一種新型社會的物質基礎。如今,整整一代人都是在網絡社會、信息社會或——用最近在社會科學中流行起來的術語來說——數字社會中長大的。這種社會的特征是,信息以史無前例的速度通過全球網絡流動。專門致力于理解“數字社會”、“數字文化”或“數字媒介與社會”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新課程也應運而生。新的研究領域猛增并發展為像“數字社會學”和“數字人文”那樣的學科。相應地,我們看到,試圖界定這種社會學研究新模式的關鍵主題、方法和邊界的教科書也層出不窮(例見Lupton, 2014; Marres, 2017; Selwyn, 2019)。雖然這些文本成功地實現了上述目標,但它們往往沒有顧及一個社會科學新領域的形成必然會引出的、更廣泛的理論問題。社會科學的核心是研究現代性,即自工業資本主義出現以來日益席卷世界各人群的生產力和理性化進程。這種新型的“數字社會”和那些進程的關系如何?如今,人類活動在很大程度上通過越來越多的設備來記錄和連接這個事實是不是表明了一種技術-社會發展的新邏輯?還是說,這只是社會的進一步理性化?今天信息的高速生產和交換是否引出了新的社會關系?還是說,一直以來,生產的加速都是資本主義的核心要義?如果數字社會學要在描述性的案例研究之外提供更多的東西、要發展出理解技術與社會新發展不斷積累的影響和軌跡的解釋框架的話,那么,這些問題就是至關重要的。這里評論的這幾個文本也做到了這點。它們都識別出數字社會的主要特征并提出關于這些特征對社會進步來說的更廣泛含義的理論。這些文本中的每一個都記錄了當代技術-社會關系的一些特別驚人的方面的歷史發展。阿特伍德的《性媒介》展示了通過更廣泛的理性化進程(如管制和法化)來理解性與親密關系的日益技術中介化和在這個語境中出現的各種實踐的有效性。威吉曼和多德在《速度社會學》中也對當代生活最特別的特征之一——加速——進行了類似的分析。他們詳述了何以加速一直處在現代性的中心,而不是把它拿來和先前的社會關系對照。不過,最能定義數字社會的特征在于,如今,新的設備在很大程度上把世界各地的人群都連接了起來。吉科的作品《超連接》主要關注的就是這個,它也馬上成為了數字社會學的一個關鍵文本。《超連接》是百科全書式的數字社會指南。這個社會的特征,是和先前時代不一樣的各種新形式的“技術-社會生活”。但吉科提供了一個其他探討數字社會學的書沒有提供的東西,她邀請讀者主動參與塑造這個新社會。她測繪了可供人們在其中集合和表達自我的新空間和人們可能面對的各種障礙。結果是一部描繪數字社會的匯編。這是本書評第一部分的焦點,這一部分具體考察了吉科和阿特伍德是怎樣定義數字社會的。從根本上說,我認為,這雖然是一種豐富而有用的對數字社會特征的總結,但它并沒有涉及更廣泛的歷史力量。本書評的第二部分是通過對威吉曼和多德編輯的文集的重要見解加以引申,來提出這個問題:數字社會是否構成與現代性的決裂?然后,我將在結論部分思考這三個文本對新興的數字社會學領域來說的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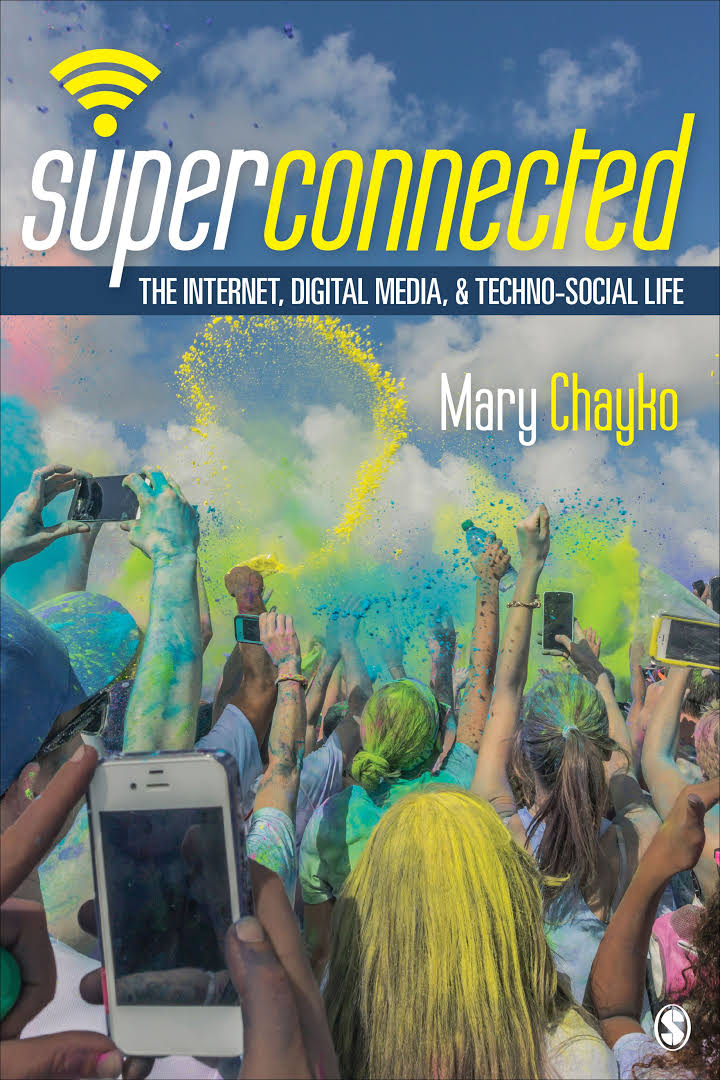
《超連接》
數字社會的特征是什么?
吉科稱,“關于未來的技術社會,也許,人們可以做出的最有可能成真的預測,和不斷加強的監視有關”(p. 205)。大數據的經濟必要性(economic imperatives)正在推動在形式上日益復雜、微妙和無處不在的數據挖掘的發展。隨著這些技術在社會中擴散,“退出”變得越來越不可行,因為參與社會的重要途徑——從基本的衛生保健到親密關系——也越來越多地以各種記錄我們的活動和日常交流的設備為中介。這個過程的具體體現,就是越來越多的設備,它們構成了所謂的“物聯網”和“智慧城市”,把我們環境中的各種平凡事物和數據分析的網絡關聯起來,并在過程中使我們的日常生活變得越發地“超連接”。這種新的“技術-社會”安排是數字社會的背景,形形色色的社會議題也必須放到這個背景下來理解。
吉科的功勞,在于介紹了很多如今每天都會在公共話語中凸顯的社會議題。從危及民主正常運作的“假新聞”到線上“回音室”,到在以數字為中介的賭博和消費中無處不在的各種新形式的“癮”,《超連接》全面概述了組成數字社會的各種議題。它也因此而對數字社會學這個新興領域做出重要——也許是迄今為止最全面的——貢獻,并為對這個領域感興趣的本科生提供了一個極其有用的起點。吉科的作品也成功地揭開了這些新的社會互動領域的神秘面紗,挑戰了主流新聞報道提出的一些更加夸張的主張。其中一個特別相關的領域,涉及新形式的親密關系。吉科用她自己的一手數據來探索以數字為中介的親密關系和新形式的騷擾,比如說“網絡論戰”(flaming,意在威脅的負面、嚴苛評論);和“引戰”(trolling,執著地用這樣的語言來把討論帶偏)。吉科強調這些行為對公共權威提出的挑戰,同時也強調總體而言人們在關系中對數字媒介的使用趨向于積極而非消極。
拆穿圍繞親密關系語境中對數字媒介的使用出現的嘩眾取寵的神話也是阿特伍德的《性媒介》的主要目標。阿特伍德把這些神話放進更加廣闊的父權制和道德恐慌的語境中去考慮,并用這個歷史來討論在網上擴散的具體實踐。她最有洞察力的例子之一是“性短信(sexting)”,即通過手機來發送裸照或半裸照的行為。阿特伍德回憶了一些令人震驚的、引起道德恐慌的故事,包括私下發給伴侶的照片被傳到網上后被逼到自殺的年輕女孩的故事。阿特伍德指出,研究表明多數性短信屬于穩定關系的一部分。然后,她說:
從證據來看,顯然,問題的原因不在于收發照片,而在于騷擾和霸凌,在于成年人和各種機構未能保護涉事的青少年,在于人們把事情怪到那些自己的照片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被傳播出去的女孩頭上。(p. 54)
書中多次重復這種敏銳的推理,比如說,她指出,研究表明,青少年的性活躍率實際上是在下降的,這就反駁了所謂的“性化”過程說,這種說法認為,青少年會因為接觸某些形式的媒介而更加快速地“性化”。通過以這樣的方式質疑常規敘事,用經驗證據來破除關于各種新實踐的神話,吉科和阿特伍德都提供了可以促進政策討論的作品。這兩位作者都強調了現有的媒體和公共機構在塑造數字社會上必須起到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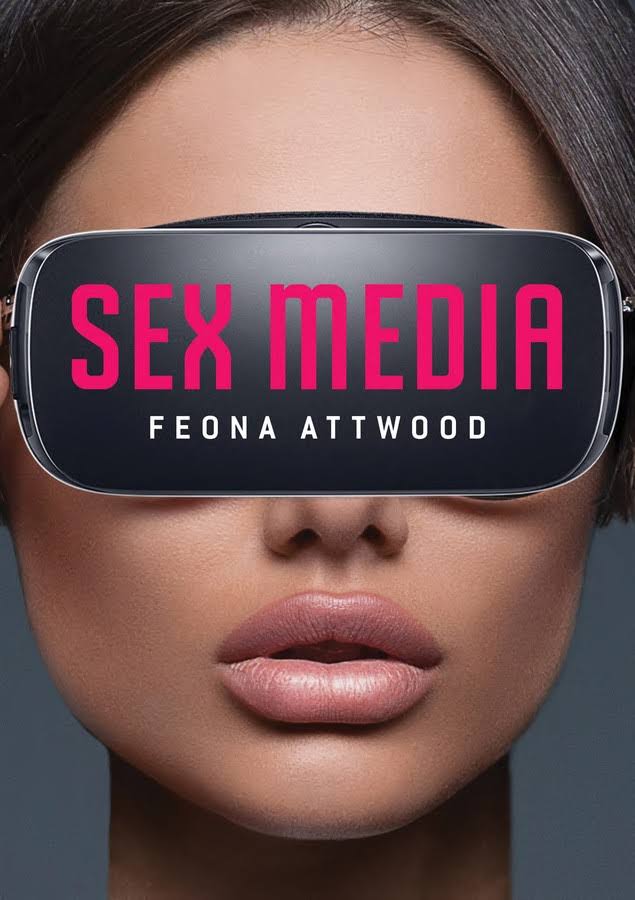
《性媒介》
阿特伍德是從福柯的“法化”(juridification)角度來討論的:顯眼的話語和監視技藝起到了以各種方式來管制性的作用。隨之而來的推論是,我們可以在各種地方形式的創造性表演中找到對各種壓迫形式(如父權制)的抵抗。吉科也在《超連接》中花了很多時間來敦促讀者“聯網、創造、混搭、行動”,號召個體創造性地挪用他們遇到的設備和程序,以建設他們想要生活的那種數字社會。在這兩種情況下,資本主義都是房間里的大象。雖然吉科觸及了諸如日益加強的監視此類的重要趨勢,阿特伍德也提出了關于話語力量的理論,但是,引導對技術的生產和使用的經濟必要性卻沒有得到充分的討論。
在吉科那里,這削弱了她贊美新形式能動性、邀請讀者更加積極地塑造技術發展的總體論證。當然,在一個史無前例的不平等和環境崩潰的年代,這種對技術民主化的呼吁至關重要。但這樣的計劃肯定需要將技術政治化,用更加進步的優先考慮來挑戰和取代或至少用新的監管框架來限制引導生產的經濟必要性。在缺少這樣的批判的情況下,吉科對行動的呼吁主要針對的依然只是地方層面的小規模挪用和政治消費,她眼中的數字社會也只是一個稍微活躍一點兒的公共領域而已。如此,這兩個文本——和大部分一般意義上的數字社會學一樣——都和現代性銜接得過于緊密了。生產力和廣泛的理性化過程——它們依然以如此之多的方式定義著社會關系——依然沒有受到質疑。
現代性與“數字”
就像之前說到的那樣,數字社會的特征,是信息以史無前例的速度通過全球網絡流動。對很多有很大影響力的學者來說,這構成了與現代性的決裂。眾所周知,曼紐爾·卡斯特爾(Manuel Castells 1996)宣稱這場技術革命可以和那些開創了“現代”的革命相提并論,最近像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 2011)那樣的暢銷書作家對像“第三次工業革命”和“后資本主義”那樣的術語的宣揚也響應了這種觀點。在此之前,像讓-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Fran?ois Lyotard 1984)那樣的哲學家就已經論證過,電子媒介正在侵蝕維系“現代性”的知識基礎,并因此而標志著一次與現代性的、歷史性的決裂。可這種說法在多大程度上是真的?信息生產、傳播和交換的史無前例的速度是否真的標志著一種新的社會關系系統的出現?
格奧爾格·齊美爾已經在他的作品中觀察到,定義現代性的一個特征,是連接和速度的邏輯。這個新邏輯的體現,就是錢。威吉曼和多德在他們為《速度社會學》撰寫的首章中考察了齊美爾的作品,通過關于齊美爾作品的討論強調了,金錢的流通是怎樣通過把人和更廣泛的商品和服務網絡關聯起來,提高經濟生活的速度并從而改變新興城市中心人們體驗時間的方式,使共同體迅速擴大的。如今,日益流動的文化中彌漫著一種不穩定和加速的感覺,雖然這大大有利于商業、語言、法律和科學——齊美爾把這些領域統稱為“客觀的文化”——的發展,但它同時也犧牲了“主觀的文化”,“個體的精神的、理想的生活”。齊美爾的話在我們的時代聽起來也無比真實:“城市給我們的感官過載”讓我們的大部分經驗失去了意義,因為“運動變成了絕對”(p. 16)。[1]在這里,威吉曼和多德引入瓦爾特·本雅明來解釋時間的意義是怎樣被“清空”的——因為時間被簡化為一個令人目眩的、旨在實現不明確目標的持續創新過程。即便我們依然不清楚我們在朝什么進步,那種以進步之名要求我們不斷加快生活節奏以變得更加高效、更有生產力的觀念依然沒有受到質疑。使這種對時間的感知變得更加有害的是它的“同質性”;它不只框定了我們當下的環境,還通過把歷史的主體放進一個線性進步的連續序列,重塑了整個人類的歷史。在威吉曼和多德看來,定義“現代”的,正是這種特殊的、充斥著一種獨特時間感——覺得時間是連續的、順序的、加速的——的對進步的構想,因此,我們需要研究這種構想本身,需要一種“速度社會學”。
這個框架使我們可以理解新形式的抵抗和解放。威吉曼和多德還把本雅明的“辯證意象”當作挑戰人們對時間的理解、喚醒他們、使他們意識到還可以用新的方式來詮釋歷史和進步的美學手段來討論。在這里,我們可以把一些像閑逛(flaneurie)——19世紀流行的,在城市里漫步遐思的行為——那樣的特殊實踐理解為對加速邏輯的抗議。雖然文集中沒有提到保爾·拉法格,但這個分析還是讓人想起他的經典論文《懶惰的權利》(1883),而在第二章中,當哈特穆特·羅薩著手解決拉法格論文的核心難題的時候,這個遺漏就顯得更加地讓人奇怪了。羅薩問,為什么各種節省時間的設備最終卻增加了對我們的時間的要求?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羅薩提出了本書第一個“晚期現代”的速度理論。
對羅薩來說,我們的閑暇時間(也就是我們可以為了一些活動本身而從事這些活動的具體時刻)消失的原因在于新技術對我們的時間的“合理要求(legitimate claims)”不斷加碼的趨勢。羅薩解釋說,“在電話(更不用說互聯網了)出現之前,一旦我們回家就不可能與朋友聊天了——因此,雙方也就都不會有這方面的合理預期”(p. 28)。雖然一方面,新的通信設備為我們節省了時間,但另一方面,它們也大大提高了對我們的時間的預期和要求。反過來,在我們為適應這些新要求而掙扎的同時,這反過來又對節省時間的設備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此,在羅薩看來,一種“加速的邏輯”定義了現代性。一個社會“在系統地要求自身的結構再生產增長、創新和加速的情況下”就是現代的。羅薩把這稱作“動態穩定的模式”。不過,和拉法格不一樣,羅薩并不把這歸咎為資本主義再生產的要求。相反,羅薩強調動態穩定的文化和物質根源,他的立場更接近于韋伯而不是馬克思。因此,“加速社會學”起到了框架的作用,在這個框架下,我們可以理解何以加速是當代社會中衡量進步的一大指標。
在唐納德·麥肯錫(Donald MacKenzie)貢獻的文章,即文集的第四章,關于高頻交易(HFT)的案例研究中,速度作為一個組織原則的物質表現得到了最清晰的說明。在這里,我們看到了在計算機以超出人類個體行動者能力的頻率參與自動交易過程的時候把速度委托給算法的必要性。麥肯錫詳細說明了對速度的要求是怎樣被置于對可靠的要求之上的,這種設計上的權衡強調了這些網絡在很大程度上是社會建構的。計算上的創新為速度提供的新的可能性進一步激勵了加速,這是一個共同生產(co-production)的過程,其結果是在金融資本主義的網絡中,速度作為指導原則進一步擴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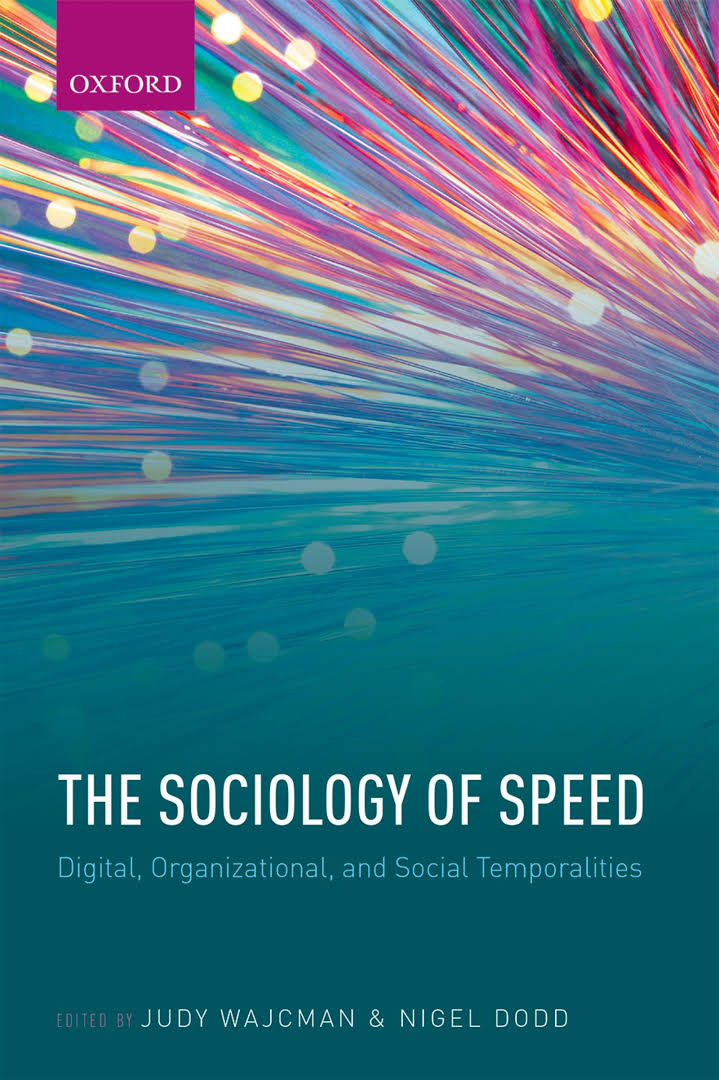
《速度社會學》
在包括公共部門在內的各種機構語境中,速度也變成了一種“存在的絕對”。保羅·杜·蓋伊(Paul Du Gay)在第六章中追蹤了這點。他對當代管理和組織話語的分析揭露了何以在破壞性創新、表現和交付的文化中,審慎的考慮——官僚制的存在理由——被放到了一邊。關于托尼·布萊爾政府在伊拉克戰爭前的決策過程的討論敏銳地說明了這點。在更廣泛的私營部門,我們也看到速度被拔高為衡量成就的關鍵指標。在第七章,梅麗莎·格雷格(Melissa Gregg)把這個過程的起源追溯到工作場所中的“科學管理”的出現。她令人信服地論證了,各種技術創新尤其自我追蹤技術的發展表明,泰勒主義已經轉變為一種更加普遍也更加微妙的規訓權力。這個論證的一個非常有趣的方面在于,它也為冥想和“正念”的流行提供了一種令人信服的解釋:因為人們想要逃避對生產力的永無止境的追求。這些見解也對《速度社會學》——這部文集提出了一種詮釋數字社會的總體合理性的新進路——中呈現的對當代技術-社會關系的更廣泛的理論理解做出了貢獻。就像這里概述的這樣,這種進路的好處很清楚,它對我們對數字社會的理解——不是把它理解為與以現代性為特征的社會關系的根本決裂,而是把它理解為起源于那些關系的各種力的結果——做出了巨大貢獻。
為數字社會學而做的一些反思
像吉科的《超連接》那樣的作品通過大量需要分析的新實踐,提出了支持作為一個社會科學新領域的數字社會學的論證。被理解為一個新興的、以互聯網為中介的互動領域的數字社會顯然需要學術研究。而且,就像我們每天都在見證的那樣,處在民主社會核心的關鍵機構也還在掙扎著應對日益增長的數字化。像《超連接》和《性媒介》那樣的文本至少證明了扎實的、能夠為政策討論提供信息的數字社會學的必要性。比如說,當成千上萬人在私有平臺上分享錯誤信息的時候,說到底,該由誰來負責呢?線上匿名狀態提供的自由和問責的必要性之間的界線又在哪里?像這樣的問題是迫切的,通過嚴格、無偏見的學術研究來回應這些問題至關重要。但是,除此之外數字社會學還必須提供更多的東西。
數字技術發展并在社會中擴散的極快速度意味著,數字社會學不能是一門反應式的學科。雖然地方的案例研究也能提供影響政策的深刻見解,但在不批判地介入驅動生產的邏輯和必要性的情況下,數字社會學只會被監視資本主義的操作者牽著鼻子走。[2]這樣的批判介入應該是兩方面的,它不但涉及更廣泛的、關于支撐數字化的合理性和生產力的理論思考,也涉及對技術民主化的呼吁。吉科的著作因為提供了后者而在數字社會學中脫穎而出,但它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前者。反過來,威吉曼和多德的文集為詮釋滲透當代技術-社會關系的邏輯提供了一個創新的框架。然而甚至在聯系勞動或環境的狀況來討論這個邏輯的破壞性后果的時候,在很大程度上來說,書中的作者們也沒有提出一個關于抵抗的理論。在這方面,薩斯基雅·薩森為文集撰寫的文章,也就是《速度社會學》的第五章是一個例外。
薩森的章節在推進《速度社會學》的總體目標上可能是效率最低的,但它提出了一個鼓舞人心的行動號召,這個號召提醒了我們數字社會學可以實現什么。薩森把批判和具體的、務實的考慮——比如說,“滿足低工資工人和低收入街區的應用程序的不足”——結合起來,并認識到何以物質基礎設施能夠使“靜止的地方活動人士”網絡之間的直接交流成為可能。《速度社會學》追問的是當代技術-社會關系底層邏輯,而薩森的章節則作為對進步路線的干預、問題化以及重新調整方向的努力在其中脫穎而出。如果數字社會學不甘心只充當監視資本主義的基礎設施,那么它就必須遵循這一進路。
注釋:
[1] 關于當代的類似情況,參見吉科《超連接》的第九章《全天候超連接的利弊得失》。
[2] 也即,日常互動通過數字設備的持續商品化(Zuboff, 2019)。
參考文獻:
Castells M (1996) The Network Society.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Lafargue P (1883) The right to be lazy. In: Lafargue P (2011) The Right to Be Lazy: Essays by Paul Lafargue. Edinburgh: AK Press.
Lupton D (2014) Digital Soci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Lyotard F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rres N (2017) Digital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cy Press.
Rifkin J (2011)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Selwyn N (2019) What Is Digital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Zuboff S (2019)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London: Profile Books.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