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張呈忠評《荊公新學研究》|內圣外王的思想體系及其歷史命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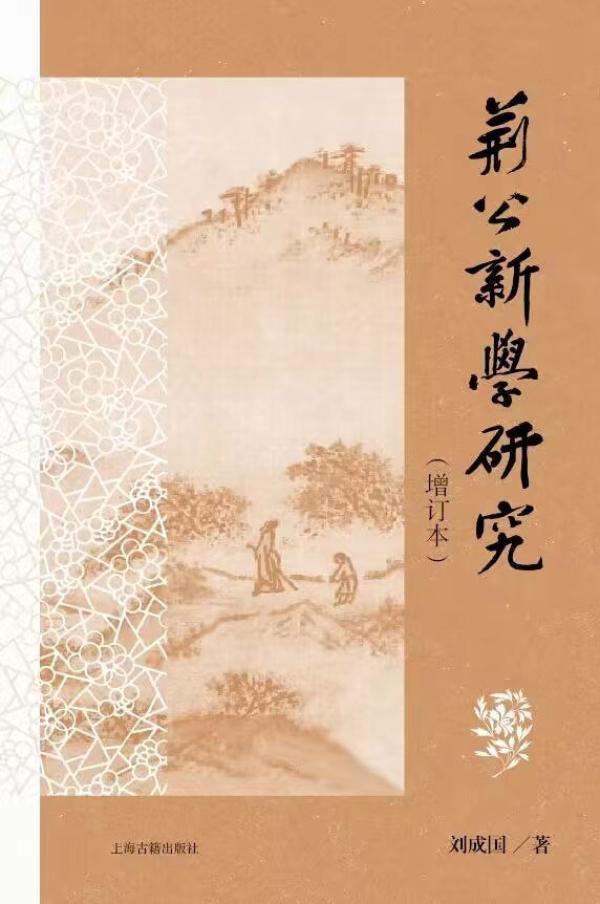
《荊公新學研究(增訂本)》,劉成國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629頁,180.00元
二十一世紀以來,王安石學術思想研究成為宋代文史領域之顯學,相關論著的出版呈井噴之勢,從過去一個相對不太受關注的課題到如今已然蔚為大觀,其中劉成國教授貢獻頗多。最近幾年劉成國教授以一己之力完成了編纂《王安石年譜長編》和整理《王安石文集》兩大工程,去年又向學界推出了分量不輕的專著《荊公新學研究(增訂本)》。
此增訂本以首版于2006年的《荊公新學研究》一書為基礎,名為增訂,實為新著。舊著二十六萬字,增訂本有五十三萬字,這不僅僅是字數的增加,兩相對照,幾乎每頁甚至每段都有改動。在這個學術論著“走量”的時代,著者竟刪去了舊作中的整整一章(共六章),其原因是認為此章“與本書主題不甚密切,且自覺難以在學界已有的研究外另出新意”,可見著者對待文字之嚴格態度。新舊兩版對比閱讀,可以清楚地看到劉成國教授是一步一個腳印地將“少作”充實為一部集成之作。
該書首兩章論述了王安石的學術歷程與思想發展,以時間為序,將思想學術的演變貫穿其中,實為內容詳實的學術傳記,再現了王安石的學術生命史。其后《新學門人與著述考》一章羅列了王安石門人近六十人、王安石著述四十余種、新學學者著述一百余種,展現了新學學派的整體面貌。不過,令人稍感遺憾的是門人與其著作分列兩節,先后次序上并不對應,且新學學者的范圍大于荊公門人,非荊公門人的新學學者僅列其著作而未論述其生平。接下來第四章對荊公新學的學術建構與理論特色則重在義理辨析,在批判地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基礎上系統地闡述了新學理論。最后兩章是對荊公新學的盛衰、荊公新學對宋代學術思想史的影響的分析,既有橫向比較,又有縱向觀察,綜合呈現了新學史的全貌。該書用力之勤、史料之豐與持論之慎,都令人印象深刻。如論王安石所編纂的《四家詩選》,前人僅根據一兩條史料推測其成書在王安石罷相之后,而該書先以《永樂大典》所載華鎮《題杜工部詩后》一文將其成書時間鎖定在元豐年間,再以王鞏《聞見近錄》中所載王安石與黃庭堅之間的問答,明乎《四家詩選》的編纂乃因陳繹的問詢,進而通過考證陳繹在元豐五、六年間知江寧府的行實將其編纂時間和背景過程都具體展現出來了,將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大大推進。
該書的著述形式與具體觀點皆平和而質樸,既少有新概念、新提法,也鮮見新理論、新方法,可謂是不務新奇之論而又不乏新穎之見。如論王安石與周敦頤的關系,對這一著名公案,著者綜合分析了相關史料,最后給出了較為穩妥的見解:“所謂王安石向周敦頤懷刺求學,出自南宋理學弟子的渲染編造,意欲借此提升后者的學術地位。倘若由此否認王、周之間曾有交往,也屬矯枉過正,似無必要。此外,或許令理學家尷尬的是,周敦頤在熙寧變法期間頗受重用。”(46頁)這一論斷可以說是一詠三嘆,一定程度上還原了復雜的多面的歷史。對荊公門人與著作采用了非常傳統的考據方式一一羅列,這種方式使得著作與人物的重要程度被扁平化了,若不仔細品讀,可能會漏掉一些重要線索。比如,相比于舊版,增訂本明確將蔡京增列為荊公門人之一,并在《(嘉靖)建寧府志》所載楊訓與蔡京同學于王安石這一記載的基礎上又補充了一條證據,即劉弇《龍云集》所載《上蔡內翰元長書》,其中說道:“竊伏蔡公下風之日舊矣。道完德粹,根柢六經,斷以義命之學,則得之王荊公。”蔡京也是講求道德性命之學,曾在《王安石傳》中盛贊王安石對道德性命之理的發明之功(參看拙文《蔡京為〈安石傳〉考》,《閩臺文化研究》2017年第三期)。以往的一些研究刻意否認蔡京與王安石的承繼關系,僅承認蔡卞是荊公門人,其實是因為對蔡京有著根深蒂固的偏見,只將他視作一個不學有術的政客。徽宗朝蔡京改革的規模并不亞于熙寧新政,蔡京之術是否有“新學”的背景?從荊公門人的角度來觀察北宋晚期政治,是否將蔡京列入其中,以蔡京地位之重要性,可以說有著根本的不同。由此可見荊公后學的研究仍有較大的空間。
據著者《增訂本后記》自述:
就內容而言,此次增訂,最大的不同體現于義理的分析。二十年前,總感覺與研究對象之間,似乎隔了一層。很多結論游移在不同的文獻、論述之間,拿捏不準,似是而非。比如,對于新學思想和歷史地位的整體判斷,原書即參考余英時先生《朱熹的歷史世界》中的觀點,將宋代理學視為典型的內圣外王之學、儒學復興的巔峰,而新學則是理學發展中的一個被超越的環節。增訂本從整體上改變了原先的認知和論述,認為新學和理學一方面呈現出北宋儒學復興思潮中的若干共同特色——例如皆屬解經新范式;另一方面,它們分別代表了宋代儒學中制度與德性兩個不同的建構方向。(628頁)
這段話對于我們理解整本書的立場、方法與思路十分有幫助。
增訂本將二十世紀以來荊公新學的研究取向分為三類:唯物主義的剖析、理學的參照和宋學的視野。在“理學的參照”中特別分析了余英時的《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朱熹的歷史世界》雖主要討論理學,但是將宋代思想史的演進實際上劃分為前王安石時代、王安石時代、后王安石時代,對王安石重要性的強調,推動了學界對于王安石學術的重視。但是,余英時是將王安石置于朱熹的歷史世界之中,如著者所說:“此書隱含著的先入為主的敘事意圖,以及判教式的目的論證——理學是宋代儒學演變的最高階段,卻往往被忽略。這種研究取徑,基本按照對理學發展的貢獻多少,來評判新學的思想價值。”(第3頁)理學家批評王安石的道德性命學說源自佛老,這是新學的錯誤之源,故他們致力于建立純正的儒家心性學說。而理學家的這種批判得到了余英時的認同,他認為王安石的內圣之學源自佛教——這就涉及了王安石思想的起點問題,也是本書反思新學研究中理學敘事模式的切入點。

王安石
荊公新學研究的難點,正在于如何講清楚王安石的思想體系。作為一種能夠占據統治地位近百年的思想學說,體系完備是其首要特征。增訂本在討論荊公新學的學術建構與理論特色時通過重敘道統、建構本體、辨析人性、學以至圣、制度之源、義理解經六個環環相扣的部分,完整地揭示了新學的學說體系,是全書中最為用力的一章。著者特別重視對王安石思想中道家成分的挖掘,認為“王安石綰合內圣與外王的思想資源,主要來自道家,而非禪宗”(18頁),由此批判了余英時認為荊公新學形成過程中主要是假借佛教的觀點。通讀此章可以發現,王安石受老莊思想影響,首先表現在對“道”的認識上,《莊子·天下篇》中悲嘆百家往而不返,道術將為天下裂,王安石也認為孟子而下圣人之大體就分裂為八九,諸子百家各自得道,但都不見道之大全,故王安石主張恢復“道之大全”,對百家之書乃至各種小說無所不讀并有所去取,惟理之求,對西域之佛書也能發現其與儒家之經典相合之處(278頁)。其次,王安石的宇宙論本體論深受《老子》影響,他在《老子注》中集中闡述了“道”為宇宙之本原的觀念,但扭轉了道家哲學中重“無”輕“有”的傾向,特別強調“有”的優先性,從而論證了制度創建與變革的必要性(291頁)。胡適在討論法家思想時曾經盛贊王安石對老子無為主義的批評,認為王安石在《老子論》說老子“知無之為車用,無之為天下用,然不知其所以為用也。故無之所以為車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為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于車,廢禮樂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為用也,則亦近于愚矣”很有道理,“法家雖信‘無為’的好處,但他們以為必須先有‘法’然后可以無為”(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275頁)。其中的邏輯頗有相通之處。再者,王安石的制度觀深受《莊子》影響,在盧國龍、梁燾等學者對王安石《九變而賞罰可言》一文深入解讀的基礎上,著者指出王安石將道家理論引入儒家政治實踐,整合天道、仁義、刑名,對本屬于道家、法家的概念賦予了儒家的內涵,從而建構起“儒家政治憲綱”(340頁,這一說法見于梁燾《王安石政治哲學發微》一文而為著者引用)。最后,從經典的角度來看,《老子》《莊子》兩部著作在新學體系中的重要性,并不亞于五經,因此毫不奇怪王安石及其門人均有注解《老》《莊》的著作(349頁)。以上幾點,充分證明了王安石思想中道家成分之重。
那么,受老莊思想影響如此之大的王安石是道家嗎?倘若是,雖然和余英時的觀點有區別,但仍舊是如道學家所說王學并非純正的儒學。著者明確否定了這一觀點,認為道家話語、思想只是王安石加以利用的思想資源,王安石思想中的佛教因素、法家因素也是同樣的性質,荊公新學的學術取向就是“以儒為主,整合百家”(272頁)。
荊公新學以發明“道德性命之理”為其宋學上的大貢獻,也是他在宋代最受理學家攻擊之處,從理學發展史的角度來看,新學在這一方面顯得很不成熟。該書也認為王安石沒能“為儒學開辟出一條嶄新的個體德性修養之路”(332頁),“心性領域中洛學卻遠勝新學”(548頁)。如果順此思路,就自然會陷入理學支配下的思維模式——王安石內圣之學不足而理學超越了新學。走出理學的思維模式,關鍵在于問題意識與思維方式的轉變。著者指出,新學是制度儒學,理學是德性儒學,兩者本來的取向就存在根本不同。對荊公新學的思想體系正是在這一儒學取向二分法的基本框架之下展開討論。由于南宋以后理學的勝利,“新學關于天道、人性、圣賢人格等諸多論述,本來以制度為指向,卻被強行納入理學以成德為目標的話語模式中比較”(457頁)。簡言之,本書的研究取徑是從宋學視野之下考察新學,并在制度與德性兩方面比較新學與理學。著者認為,在制度變革方面,理學毫無建樹,甚至輕視經世之學,而新學才是真正的內圣外王之學。與道學試圖在內圣的基礎上建立外王不同,作為制度儒學的新學是既追尋其超越的天道根據,又尋求內在的人性基礎,以推動社會政治的變革實踐為目標。也就是說,王安石對于人性的探索服務于制度變革的整體目標。就連王安石的圣人觀(即理想人格)都頗具改革家的本色:僅有個體道德的完善不足以成為圣人,圣人必須因時救弊,“他心目中的孔子,之所以賢于堯舜,乃因時勢之變而集歷代法度之大成”(327頁)。順此思路,稱荊公新學為“外王內圣之學”是否會更為準確?
從本體論、人性論、圣人觀再到制度觀,王安石的新學理論體系得以完整呈現。雖然個別地方的闡述仍不夠通透,所引用的“儒家政治憲綱”一詞略顯生硬,但著者對王安石思想體系的解讀基本上是成功的。從中可以看出,王學能夠成為官學不是偶然的,它能夠為當時的知識世界、思想世界提供相當充分的解釋能力和切實的指向作用,王安石本人有能夠被當時的讀書人普遍認可能昌明圣人之道而繼承道統的資質。就“內圣”層面而言,王安石的人性論與理學家強調內在本性之善的主動性、自發性呈現有著根本性差別。在王安石看來,人性中雖有善端,卻不能自發地顯現,必須借助于外在的制度環境。著者反復強調,在王安石的思想中,“制度對于人性的成就,不可或缺”(這句話在書中出現兩次,318頁和344頁)。制度與天道、人性三者的關系是:制度既是天道在政事中的體現,又具備人性的內在根源。制度之于人性有雙重作用:它一方面順應人性中的某些趨向,另一方面又約束、鑄就人性,使得人性的善端得以成就、惡端得以抑制。由此可以得出結論:用制度來造就人(人才),正是王安石的改革著力點。所謂制度造就人才,對于王安石來說,關鍵就是經術造士、統一思想。在王安石的歷史世界里,三代就是“一道德而同風俗”的時代,三代以下則是眾說紛紜、邪說橫行的時代。為了回向理想的三代,同時也是為了解決政爭之中議論紛紛的問題,身為宰相的王安石在落實新法的同時進行了科舉教科書《三經新義》與《字說》的編纂以及相應的科舉學校制度的改革,對新法的經學闡釋也是新義的核心內容,可以說內圣外王之學由此形態完備。最終,荊公新學由一家之學變成了欽定官學,成功成為了大宋王朝的官方意識形態。
然而荊公新學的歷史命運令人感慨。作為一個學術流派的新學,盡管從學者眾,但是第二代傳人已經遠不能與荊公的學術氣象相提并論,再往后的傳人更是寂寂無聞,幾乎可以說是二世而亡的短命學術,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以經術造士為指向的科舉改革與人才培養機制,制度設計是按照王安石的思路進行的,較為徹底地得到了落實,但是結果并不如意,新學異化為求取功名的工具和束縛思想的牢籠,甚至就在新學如日中天的時候,“懷揣真誠的學術理想、以追求儒學真諦為目標的一些士人,如劉勉之,毅然放棄新學轉習程學”(455頁)。這些普通士人的選擇決定了新學的學術生命。
否定新學的首先是歷史本身——北宋王朝的滅亡。南宋以后的新學亡國說不絕于耳,不過從學理上講,荊公新學雖然遭到了嚴厲抨擊,但并沒有真正徹底地被否定。理學對新學的否定,是從內的方向,認為王學的本質問題是內圣不足。從根本上講這仍然是“用玄學打敗玄學”。當然在政爭與學爭的背景下,王安石的反對者所采取的也不乏技術手段,如從王安石早年文章的字里行間作出王安石有異志、有不臣之心的指控。這自然是無稽之談,不過相對于新學的官方形態《三經新義》中對于君臣之分的強調(360頁),早年的王安石在士人出處之道上確實顯得更加自由奔放,但要說他有異志那完全是欲加之罪。其實新學官學化的過程也是學問從開放走向封閉的過程,王安石追求“道之大全”的學術精神、無所不讀的學問熱情、對外來學說盡力吸收的開放氣象,在王安石自認為與被認為掌握了“道之大全”之后就已經蕩然無存,其他學說皆被視為俗學,其最甚者莫過于徽宗朝出臺了絕滅史學的國策。新學異化的思想源頭,還是應該追溯到這個“道之大全”——理一元論。
在新學盛衰的過程中,作為一個學派的蜀學與理學、新學鼎足而三。其中蘇軾對王安石的批判無疑是最具有現代意義的:“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蘇軾《答張文潛縣丞書》),“王氏之學,正如脫槧,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飾而成器耳”(蘇軾《送人序》)。蘇軾對王安石的批評,堪稱“孤勇”:“只有蘇軾,敢于逆潮流而上特立獨行,對一元化的儒家政教模式表現出敏銳的警省和深刻的批判。”(477頁)但是蘇軾本人也未能否認理一元論,只是認為“一不可執”,世人無法掌握。這種自由思想的萌芽在理學與新學爭衡的背景下顯得極其微弱,特別是朱熹所說的“若荊公之學是,使人人同己俱入于是,何不可之有?”(《朱子語類》)在“天下只有一個理”的普遍認知之下更容易獲得認同,只是隨著時勢轉移,官學由荊公之學變成了程朱之學,經典由《三經新義》變成了《四書集注》。
關于蘇軾蜀學的儒學位置,著者并未給出明確觀點,僅稱其為“文學”,也指出其龐雜的特點。不過,認為蜀學龐雜,恰恰是理學家特別是朱熹的經典看法,“朱熹對于蜀學的批評,嚴格來說只能代表理學作為一個思想流派的獨特觀點,或者說只能代表理學對于所謂一以貫之之道的獨特理解”(盧國龍:《宋儒微言:多元政治哲學的批判與重建》,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504頁)。蜀學本身有其內在的思想邏輯,這種思想邏輯不同于新學,也不同于理學。那么,制度儒學與德行儒學是否能涵蓋宋代儒學的全貌?早在民國時期蕭公權在其名作《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中便提出:“理學與功利思想為宋代政論之兩大主流。此外尚有反對功利而不屬理學范圍之守舊思想,以及另辟宗風意近‘縱橫’之蜀學,凡此皆支流別派,雖未足代表時代精神,而亦具重要之意義。”(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417頁)可見蜀學之定位,在功利與理學之外,亦在制度儒學與德行儒學之外。而即便在制度儒學內部,南宋的葉適、陳亮等人與王安石所講求的制度,仍然有著根本性的差異。從宋學的視野出發,在荊公新學之外,制度儒學仍有不同的面向,這是值得注意的。
最后談一下本書最重要的一個關鍵詞:內圣外王。它究竟是荊公新學所高懸的目標與理想境界,還是說王安石已經做到了“內圣外王”?在北宋晚期新學鼎盛之時,這一問題不成問題,王安石被認為是已然實現“內圣外王,無乎不備”(《故荊國公王安石配饗孔子廟廷詔(崇寧三年六月九日)》),但到了南宋,在理學家那里,這兩者都很成問題,因為王安石沒有做到“內圣”所以無法實現“外王”。是否“內圣”很難有客觀標準,但“外王”確實是可以有所界定的。余英時先生雖然高度肯定理學是“內圣外王之學”,但主要論述的還是理學家要“內圣外王”,想“得君行道”,特別是在已經“內圣”的基礎上還抱有“外王”的理想,但是具體如何外王,能不能實現外王,得君之后如何行道,所行是否真正符合道,都是懸而未決的問題。反觀新學,雖然不能如南宋理學家那樣一口咬定是王學導致了北宋王朝的滅亡,但是無可否認的是,新學關乎宋朝之國運,新學定于一尊對北宋晚期士風有著絕對的消極影響,造成“彌望皆黃茅白葦”般的人才荒蕪,絕不可等閑視之。荊公新學作為制度儒學,很難說是成功的,如果一開始就將其設定為內圣外王之學,是否有拔高之嫌?當然,如何評判王安石之功過是非,乃是王安石研究中最為惱人的問題。盡管如此,要準確評判荊公新學與新法,仍需直面王安石所身處的現實世界。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