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盲目”的愛:失明41年,尋找“第四條出路”丨鏡相
鏡相欄目首發獨家非虛構作品,如需轉載,請至“湃客工坊”微信后臺聯系
作者丨楊海濱
編輯丨柳逸

圖源:婁燁電影《推拿》
“所有盲人的職業,就我的經歷來說,只有三條路能走,一是上按摩學校,畢業后當按摩師,也是最好的出路;二是在民間跟著懂易經的師傅學八卦,之后蹲路邊算卦,是低級的出路,這兩者的前提條件是家庭經濟要好,能拿出數年學費才行。第三條路就是因為家庭經濟條件限制,出不起學費,他沒有任何方面的一技之長,也就只能窩在家吃喝等死。而這樣的盲人占整個盲人群體的百分之六七十。”
這是豐望在2024年2月23日焦作市民主南路他所在的“中醫推拿”店對我說的話。在我還沒來得及向他提問前,他首先定義了盲人的職業范圍。我正思忖怎么接話時,又聽到他反問:“在今天的社會,像我這個年齡段的正常人是如何生存的?”
我明白像他這樣天生失明的盲人,都伴隨著天生的敏感,我怕隨意的一句不妥的話傷害到他,便在大腦里飛速選擇著合適的詞匯。我稍許的遲疑果真被他敏銳察覺出來,他安慰似的又說:“我經歷的事多了,你把我當個平常人就好,沒必要顧慮什么話會傷害我,我抗打擊能力很強,這也是我們盲人在社會上生存的最基本的技能。”我心里又一驚,小心翼翼地說:“不僅是你這年齡段的人,而是所有人都在奮力掙扎。”說話時我一直看著他的表情,見他雙眼快速眨動,似思考著什么。我繼續說:“我說掙扎這個詞,本意就是熱愛,熱愛就是不停地掙扎。試想一下,如果連掙扎都沒了,那不完全失去對生活的熱愛了嗎?”
他點頭說:“這說法有道理!”然后用語速急促的北京腔調說:“盲人肯定比正常人付出數倍的掙扎才能勉強地活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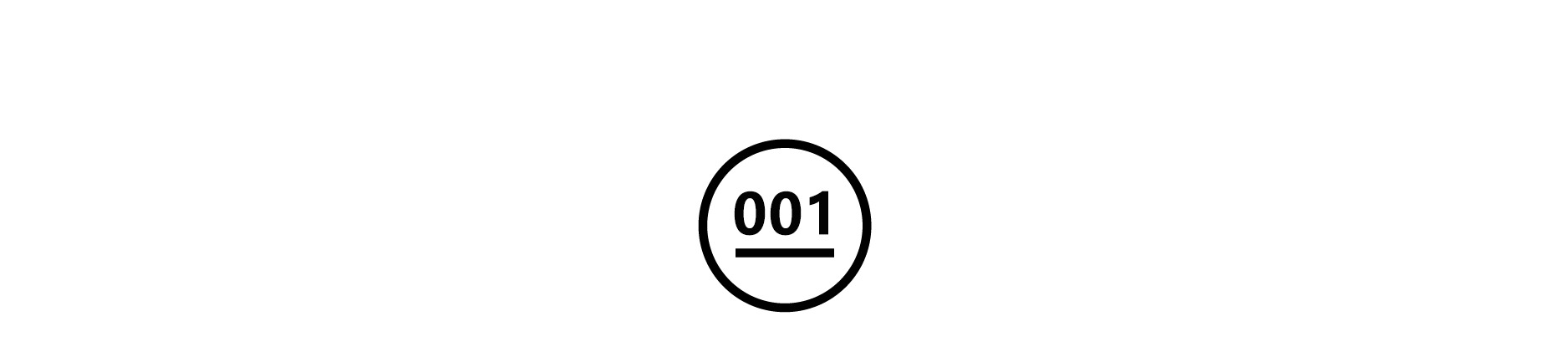
“盲人為什么不能上學呢?”
豐望出生于1982年12月的修武縣郇封村,父母都是沒上過一天學的純農民,一直希望豐家能有個傳宗接代的人——在已有兩個妞的情況下超生了豐望。但沒想到盼來的兒子卻是個先天性盲人,之后,他們對豐望的哺養方式幾乎是自生自滅。到他該上小學的年齡時,也沒人想起他能不能上學,平時的生活由比他大十一歲的大姐負責。大姐去上學時,他便由父親帶到一個磚瓦窯的坯場上,讓他自己跟自己玩,父親去背磚,天黑才帶他回家。因他不熟悉環境,常跌倒在一邊的溝壑或泥潭,臉上的傷痕和渾身的泥水成為他這個時期的記憶。

主人公豐望,在河南焦作一家推拿店給顧客推拿(受訪者供圖)
有天,正當他與小朋友玩得高興時,伙伴們忽然被他們的父母叫走,把他一人孤零零地留在那,后來才知道,人家父母怕他這個瞎子沒輕沒重,給他們的孩子造成傷害。還有天下午,鄰居倆小孩來找他,這可是他童年里小朋友僅有兩次主動找他的一次玩耍,結果也只玩了一會,就爬在小凳子上寫作業。豐望聽著文具盒和翻書聲,一種失落油然而生。自己為什么不能上學呢?從此孤獨成了他童年永恒的狀態。
豐望的大姐從小去哪都帶上他,仿佛他是她身體的延伸部分。盡管家庭經濟條件差,手里有了零錢就給他買能買得起的食物,一般小孩吃厭了的方便面,就是他生日最美味的蛋糕。所以他對大姐的感情甚至勝過和母親的感情,有什么心里話就對大姐一人說。大姐成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人。
在他12歲這年,大姐在廣播里聽到焦作特殊教育學校招生的消息,立即告訴了父親。豐望兒時就被小伙伴的翻書聲吸引過,早有上學的念頭,但也知道自己拖累了家庭,家里數年來被村委會評為貧困戶,以政府每月發的幾百元救濟款過活。父親覺得他這樣的盲人上學沒什么用,能吃上飯不餓死比去上學更重要,一直拒絕他去上學。恰好這時,已二十來歲的大姐某次外出打工掙了數百塊錢,她拿著這錢交給父親,說:“如果不送豐望上學,將來他就是一個文盲加瞎子,一輩子只好窩在家吃喝等死,如果現在送他去上學,學個一技之長,再讓他去討生活也許還有出路……”這話驅散了父親原本的猶豫,豐望的命運因大姐的話得到改變。
父親咬著牙拿出家里的錢,加上大女兒的錢,湊齊了豐望的學費。他被送到焦作特殊教育學校。他在學校用四年學完小學課程,初中只讀一年就畢業了,接下來面臨的就是高考。對于盲人來說,高考的面很窄,他也只能考專收盲人的河南省針灸推拿學校,結果以較優異的成績被錄取。他再次被父親和大姐送到洛陽這所學校讀大學。
可在入學的第一年發生的一件事,讓他崩潰,甚至想退學。這個學校除了盲人學生外,還有健全的學生。有天有個健全學生把煙頭彈到他的保暖瓶里,他在喝水時喝出煙味,就把這個瓶里的開水倒到另一瓶里,可那個惡作劇學生,又悄悄把尿尿到他的保暖瓶,他在無意中喝到了,雖然憤怒,可不知道是誰干的,沒有證據,就忍下沒報告校方。不久后的某天,他再次喝到尿到他保暖瓶里的尿,忍無可忍,報告了老師,老師也很憤怒,要揪出這個沒有道德的壞學生,由于沒有證據查不出是誰干的,而且這個學校以教技術為主,對學生道德甚是無視,過了好長時間也沒有下文。他知道這是個不能破的案件,也就不了了之。在盲人的成長過程中,承受這樣的羞辱是常見的代價。
從此他基本不再用保暖瓶,而是托大姐買了一只容量很大的塑料水杯,隨時帶在身邊,這習慣一直保持數十年,直到今天仍然是這樣喝水。

再見姐姐,親愛的姐姐
大學期間,豐望格外認真地學習推拿技術,同時還進修中醫理論,學習養生,終于熬到畢業季。
學校和全國各地的推拿店都簽有實習合同,每年畢業季前,北京東城某家推拿店的老板就來洛陽,挑選幾名最優秀的學生到北京實習。豐望名列其中。他也想趁機實現自己的抱負,回報家庭一路來的支持。
豐望到了北京的店里才知道,在他們之前,老板已在北京推拿學校招了六人,每當有客人來總是先安排北京的學生上,甚至北京的學生輪到第二圈了,也沒他們上場的機會。他們接待不上客人,就提不了成,而他們的工資都是按推拿次數提成的。這樣的現實讓豐望有了被欺騙的感覺。
洛陽的同學圍著他商量咋處理。也許他生來就是個有智慧的人,在學校也這樣,同學有拿不定主意的事都會找他商量。他說:“我們要聯合起來給老板提意見,既然都是實習生,那就要公正,所有人都要排隊,輪到誰誰上,否則我們就要求回洛陽,拒絕實習。”他領著五個同學找老板提意見。起初老板并沒在意,直到七天后豐望和同學要離開北京時,他才引起重視。老板怕他們回去讓他名譽受損,向他們道歉說忽視管理了……
在接下來的一年里,豐望盡可能把自己在學校所學的技術施展出來,沒事就給北京盲人出版社打電話買業務相關的書籍,進修并提高理論水平,還給客人講養生之道。
沒想到的是,他們與老板因伙食問題再次爆發了沖突。老板覺得這些外來者在他這干活掙錢,有碗飯吃就不錯了,并不顧及他們的要求。
通過這兩件事,豐望明白了這個社會并不會因為你看不見、是個盲人,就同情、寬容你,你必須要和正常人一樣生活和工作,盡管他自小就明白這道理,但在踏入社會之初,還是遭受了超出想象的殘酷。
在北京,只要遇到不順心的事,他就會在晚上給大姐打電話訴說。這天他也照常把這事跟大姐說了。不料幾天后,大姐出乎意料地出現在他面前。
他想都沒想她為什么舍得花幾百塊錢專門來北京看他,以為她是擔心自己的生活。大姐對他說,“這個社會可不像大姐那樣心疼你,你在保護好自己的安全之外,還要勤快,把推拿技術再提高一截,讓自己變成店里的招牌,才能更好地發展。”
他“嗯嗯”地答應著,然后告訴大姐:“等我實習結束后,想考鄭州或是北京的大學,學心理學專業,當心理咨詢師,那樣就能掙到更多的錢。”
大姐說:“那就靠你的奮斗了,大姐可能再也幫不上你的忙了。”
大姐的口氣充滿了傷感,他雖然聽出來了,也沒在意,然后她就回了河南。沒想到這一別竟成了永別。
當豐望再次收到父親打來的電話時,他才得知,大姐回焦作后,喝農藥死去了。大姐為他今后的生活不知道哭過多少次,也為自己幫不上豐望而自責,她自己的生活也出現問題,一切讓她更加絕望。
得知這一消息時,豐望正給一位客人推拿,頓覺天雷轟頂,不顧形象也不顧客人反應,蹲在地上大哭起來:“你怎么這么傻,你讓我替你死呀,你為什么自己去死?我是個沒用的人……”
他在那時覺得,原本堅實的大地突陷沼澤,他深陷其中,快要窒息死了。至親離世的痛苦,時刻襲擊著他的頭腦,讓他無法集中精力。他決定不再實習。2002年6月5日下午,豐望坐上火車,回到修武郇封村那個用土坯壘起的、簡陋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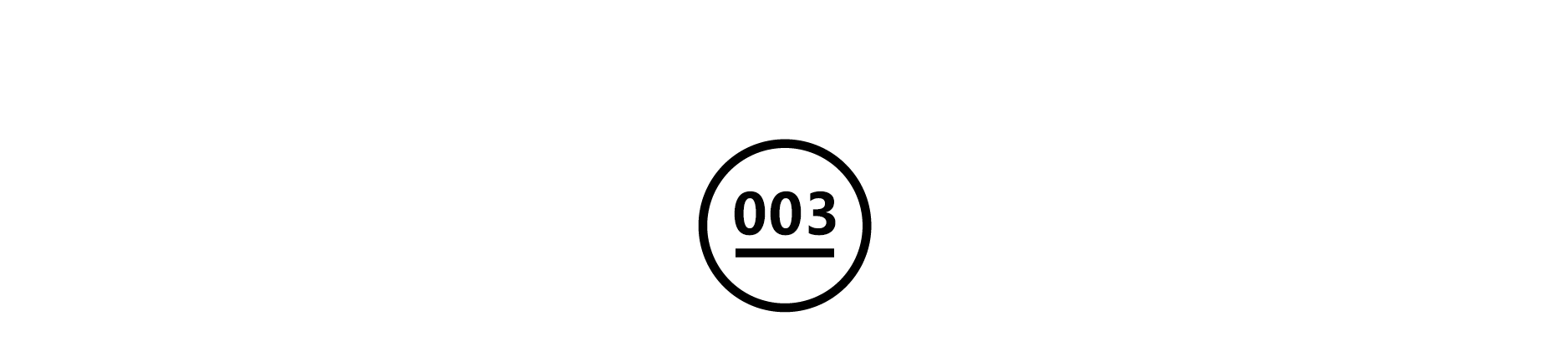
再出發
豐望回到老家后,憂郁得像臘月里陰沉的天氣,這樣的心緒延續了一年。他曾經考大學當心理師的計劃,因為大姐的去世碎了一地。他常能聽到老父親的唉聲嘆氣,盡管他不說什么難聽的話,但豐望也明白,父親也年近八十,自己不能再啃他的老。他這才從渾渾噩噩中清醒過來,決定到焦作闖蕩一下,改變一下陰沉的氣象。
他和同學們在微信上一直保持著聯系。盲人們用的微信軟件是觸屏式的,在買手機時會花數百元下載這套軟件,手指頭就是盲人的眼睛。那天,他聽說他在焦作的小學老師目前正在焦作市內開一家大型推拿店。他便給老師打了個電話,還沒等開口,老師就大聲說,“我正四處打聽你呢,你藏到哪去了?一年也不見你,我這正需要你這樣的專業人才,明天就來上班!”
2002年十月,豐望一個人拄著盲杖從郇封村搭班車到了焦作,當他穿上白大褂開始為客人推拿時,終于感到自己從陰沉的天氣中走進了有陽光的社會,也算在社會上站下腳了。他格外珍惜這份工作,對待每個客人都盡心盡責,一般推拿半小時的他都會延長五六分鐘,以博得客人好感,并在推拿過程中分享他在前一天聽到的最新的保健知識。客人很喜歡他的這種服務態度,許多人辦了數千元的長期卡,就是沖著他的手藝和態度。
這樣一干就是八年。他也從一個盲人學生成長為推拿師,甚至在入崗第四年拿到了推拿師的資質證書,工資也逐漸升到了他所期望的數字。
終于,他在職業上有些順風順水了,但與初戀的女友卻出了問題。女友原是他在洛陽推拿學校的同學,畢業后一直在南方某市做按摩,2000年春天,豐望邀她回焦作一起工作。可戀愛中的卿卿我我到了漫長、艱難、瑣碎的生活中,很快就化為泡影。
豐望在感情中的強勢,和他在成長中受大姐、母親、姑姑們的寵愛有關。他認為別人對他的照顧都是應該的,不自覺就有了唯我獨尊的大男子主義意識,把女友當成了大姐,對她指手畫腳。
失戀讓他像失去大姐一樣痛苦,他這才意識到自己要打一輩子光棍了,這才是他最焦慮的。為轉移注意力,他給北京盲人出版社打電話買盲文書。由于他這些年常打電話買書,出版社的人都知道他。巴金、高爾基,加上多年前買的《紅樓夢》《西游記》,他一本一本地看,或是聽《靜靜的頓河》等有聲書。半年后,他終于悟出一個道理,生活就是要奮斗,愛情就是要奉獻,即便在社會上拼搏得遍體鱗傷,也要為愛人、為家庭挺身而出,而不是像以往那樣只懂索取。
他想起大姐在北京對自己說過的話,說他業務上還需要再提高,以往幾年里他雖積累了一些中醫理論,但還需要加強對西醫的學習。于是他又買了盲文版的《內科學》《病理學》《藥理學》等基礎書,和《生物力學》《微生物與寄生蟲》等專著自學。
一年后,豐望感覺自己在理論上有了積累,心里也有了底氣,便重新回到焦作,準備自己開一家推拿店創業。這時距失戀已過去一年。

“盲目”的愛
2018年初,豐望和同學們在焦作合伙開起了推拿店。但由于門店選址的問題,有段時間推拿生意很不好。于是,他便在QQ上搞起副業:教不會操作電腦的盲人如何上網。因盲人的空間感較差,常常不知道鼠標在哪,用的也都是組合鍵,豐望給他們講具體的操作細節。
這天,有一位女生顧客在網上問了他許多問題,他倆聊得很投機。“幾天后,我有了一種半天不聊就失魂落魄的感覺,就直接向她要了微信號。她很大方地給了我。”她叫阿蓮,湖北荊州人,原本有正常視力,可1987年,她從武漢船舶學院畢業那年,患上了‘一過性’失明癥。起初是左眼失明,后來是右眼,然后是雙眼失明。這是一種不可逆轉的眼病,2014年,阿蓮完全失明。
豐望大膽地向阿蓮表明,自己有想跟她交男女朋友的意思。沒想到,她答應了。“看來她也是在尋找男友。我倆屬于網戀,網絡成了我倆花前月下的地方。我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和她聊天。”她讓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就像皸裂的大地飽飲暴雨的甘露。豐望第一次明白了愛情的滋味。

阿蓮未失明前的照片(受訪者供圖)
“有天我在微信里隨口說,我要去荊州看她。她肯定知道我說這話的意思是想表達感情,鄭州至荊州這么遠,沒人護送怎么可能成行,當即她就將了我一軍,她說可以呀,那你就一個人來吧。然后又強調了一遍,那你就一個人來吧!當時我特別驚訝,哪有這么大方的女生?”豐望不明白她是開玩笑還是真誠邀請,反倒一時沒了主張,隨后幾天,他想了又想,她兩次說讓他一個人來,肯定是想考驗他有無遠行的能力,于是決定,去荊州看望她。
2018年8月,那時正是豫北最炎熱的季節。豐望沒告訴阿蓮他的計劃,自己偷買了鄭州東至荊州的高鐵票。在買票的同時,他向鄭州東站打電話預約申請了重點旅客乘坐高鐵的幫助服務,“他們派人按我到鄭州的時間和地點來接我,還開玩笑說,你視力不好,走這么遠的路,還要帶著大包小包,去相親啊?我想,一個人的幸福肯定能被別人看出來,就告訴他們,還真是相親。”豐望在祝福聲中被送上去荊州的高鐵。
“這個社會有很多善良的人,一路上,有人見我需要幫助都會伸手。坐公交車也很順利。幾經輾轉就到了阿蓮家附近。”他打開導航,用盲杖摸索著前進。當他準確無誤地來到她家門口,預備舉手敲門時,卻被內心涌出的激動沖得一哆嗦,不自覺放下手,平息情緒。他想著見到阿蓮的第一句話該怎么說,想好后又舉手,可還是沒敲。“我發現自己的喘息過快,做了幾次深呼吸才去敲門。”
是阿蓮開的門。當豐望說“我來看你來了”這句話時,他雖看不到她驚訝的表情,但從她的喘息聲中能知道,她很意外。阿蓮花了點時間才確定,豐望就站在她面前,故作鎮靜地說“你真的一個人來了!”同時,伸手摸了一下他的肩膀。豐望明白,她這是在摸他的身高。阿蓮這才把驚訝換成一種平靜,說“你到底還是來了!快進屋!”
進了屋,她又摸了摸豐望的臉,“我這才確信了她在微信上說的,她是全盲”。
豐望把帶來的焦作土特產一一拿出來,她馬上給正在上班的哥嫂打電話,說焦作的豐望到家了。豐望早在微信上聽她說過,她父母已去世,她跟著她哥生活。她哥嫂回來后見他一個人,迷惑地問“你一個人來的?”口氣充滿了不信任,又強調了一句“沒人送你來嗎?”豐望淡淡地說,“多年來我就是一個人走南闖北的啊,這不是很正常的事!”
當晚,他住進離她家一公里的連鎖酒店,第二天早上在附近小吃店吃了早餐,又多買一份,給阿蓮帶過去,在陌生的環境里,他都是用盲仗摸索道路。他倆聊到中午,豐望邀阿蓮外出到飯店吃飯,卻被她拒絕。像她這樣后天失明的盲人沒有空間感,不像豐望這樣的天生盲人,有平衡感。連續三年,阿蓮竟然沒出過一次家門。平時吃飯都是靠哥哥,或是親戚們幫忙做飯。
“我見她這樣自閉,反復給她講,一定要融進社會、不能被生活淘汰這類鼓勵的話。還說,你看我,到哪都可以自由行走,你要不相信,就和我一塊下去感受一下,看看我在你家前面的街道上是怎樣行走的。她這才第一次跟我到了街上。我們去一家飯店吃炒粉。我能感覺出她的興奮。”
后來五天里的每日三餐,都由豐望去街上買回,再送給阿蓮,然后坐在她家聊天。第六天一早,豐望要返回焦作了,這也是向她哥展現自己有無遠行能力的好機會。哥哥主動幫他買了客車票,看著豐望上車,當天就回到了焦作。

圖源:婁燁電影《推拿》
在他離開阿蓮那天,她用無意的口氣刻意說,她想離開這個家。這話讓他明白她在家里的處境。到焦作后,豐望立即在微信里商量起接她來焦作的事宜,同時開始找房子。
豐望的二姐聽說此事,陪他又去了一趟荊州,請阿蓮的親戚們吃了頓飯,正式確定豐望和阿蓮的關系。“她哥把我和我二姐的身份證拍了照片,我知道他們怕我詐騙,然后他陪阿蓮來到焦作,看了我租的房子和我的推拿店,才放心離去。”
兩人同居后,每天早上7點前,豐望吃過早餐,帶著阿蓮去店里上班。一個月后,豐望嘗試讓阿蓮自己摸索著一個人走。但有天正好下雨,阿蓮站在十字路口將近一小時,不知去向,發著呆,當豐望找到她時,她失聲痛哭。晚上趁豐望做飯時,她獨自在樓下的院里徘徊許久,差點不辭而別坐火車回荊州。她為不能很快融入嶄新的生活而發愁。
“她后來說,她覺得我為了她來焦作,費了那么多的心思,她要是真走了怕我不能承受。心想既然如此,那就結婚吧!”
2019年12月25號,阿蓮和豐望在焦作民政局領了結婚證。

豐望在河南焦作一家推拿店給顧客推拿(受訪者供圖)

豐望在河南焦作一家推拿店給顧客推拿(受訪者供圖)
豐望在給我講述他的故事時,一直坐得筆直,挺著上身一動不動,我看他很累,就說:“你把身體調適到你覺得舒服的姿勢坐著,不用這么正式。”他卻說:“這樣的禮儀還是必須有的,我是個很注重禮儀的人。”他這話讓我想起介紹我來找他的李玉萍對他的評論:“許多盲人由于看不見,穿戴也就不講究,自然就邋遢,不是他們不想注意衛生,而是看不見沒法講衛生。但豐望卻是例外,愛干凈,皮鞋每天早上都要刷一次,穿的衣服從來都是整整齊齊、干干凈凈。關鍵是他還娶了個老婆,這和他有文化、懂業務、素質較高也有關。”
豐望自己開的推拿店一年多就關門了,經營和管理是個難題,他不會經營,也覺得不會的東西硬做是自找苦吃,索性找到如今的老板李總,焦作的推拿圈很小,李總早就知道他,就讓他來自己店里干活了。這不,一干就是四五年。
阿蓮走的卻是盲人的“第三條路”——在家待著。她如今生活在豐望的老家郇封,豐望每月回郇封看她。
我問豐望:“你今后有什么打算?”他說:“盲人沒今后,不知道今后的打算。有句老話叫隨遇而安。”
這時一位顧客走進店里,點名要他推拿,他說這是他的老顧客,不敢懈怠,馬上停止對我的講述,進入工作狀態。我站在一邊看著他工作。這時已是晚上近十點,街道上的燈光早已亮了起來。
(除豐望外,文中人物皆為化名。文中圖片皆獲豐望授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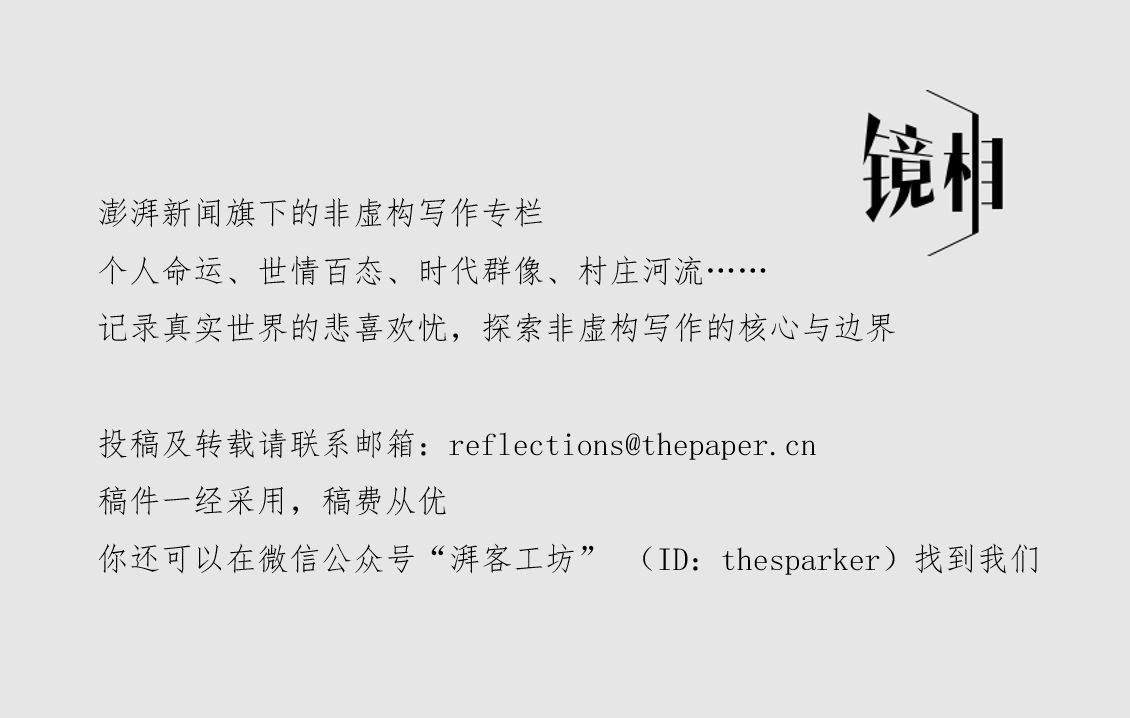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