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巴塔耶:精神分析與“惡”的解構
巴塔耶不僅是精神分析理論的閱讀者,更是精神分析臨床實踐的體驗者和超越者。他與精神分析之間的聯姻不僅僅通過他第一任妻子西爾維亞·巴塔耶和拉康的關系達成;經由他自身的虛構寫作,他在拉康提出“圣狀”[1]概念的幾十年之前——法國精神病學界仍是弗洛伊德的時代——就創造了前-拉康意義的文學增補,使自身獲得在文學界命名的主權性。我在閱讀和翻譯《文學與惡》的過程中回溯性地看到,閹割(la castration)[2]作為一道卡夫卡意義上的“法門”,隔絕出無意識領域和意識領域、童年的王國和成人的活動世界。薩德和薩德式的倒錯幻想在這本書中被搬上舞臺,而在無意識的機制中,這不過是兒童多態情欲[3]的夸張隱現。
國家圖書館的借閱記錄[4]便可佐證他作為弗洛伊德閱讀者的身份,早在1920年,他就看了《精神分析入門》。1927年,他閱讀了《圖騰與禁忌》:在這本書中,弗洛伊德提出的假設是,在神經癥那里被壓抑的機制(亂倫的欲望,或者是對“正確”生殖活動的無視)在“原始人”那里則是光天化日發生的,而巴塔耶討論的對禁忌的僭越無疑是在回歸這種原始性或動物性;而弗洛伊德對“神圣”“禁忌”等概念的雙重性挖掘在巴塔耶那里也可以瞥見[5]。巴塔耶很有可能也看過《群眾心理學和自我的分析》,這篇文章中提及的“無意識”[6]這一術語,“意識自我的審查和排除機制”幫助他構思了《法西斯主義的心理學結構》(1933)的寫作。

巴塔耶
除此之外,弗洛伊德關于性欲、驅力和夢的學說等對于巴塔耶來說并不陌生。巴塔耶曾待過的超現實主義團體Contre-Attaque里,弗洛伊德的影子也隨處可見:“教皇”布勒東作為曾經受訓的年輕精神科住院醫生,一直潛心研究弗洛伊德,他也見過弗洛伊德本人。比起臨床的診斷目的,他更在意自動主義(automatisme)在文字聯想和寫作上的運用。然而,無論弗洛伊德的影響能不能被準確追蹤,都無法遮蔽巴塔耶原創性的光芒。在《天空之藍》中,我們可以看到無意識最重要的素材——夢境的顯化:關于一場革命的墻畫被他描述為龐貝的死尸,鬧事者像被掩埋了一樣懸置在房間中。這一場景的描寫無疑是在影射欲望的壓抑(refoulement),尤其是當我們聯想到弗洛伊德關于詹森《格拉迪瓦》的評述,即浮雕和壓抑機制的美學類比(analogie):浮雕上的少女格拉迪瓦在主角漢諾德的幻想中被龐貝城傾斜下的火山灰掩埋;而漢諾德童年時期的欲望則也像這樣遭到掩埋。
巴塔耶體驗精神分析臨床的經歷也值得展開來講。在巴塔耶出生的時候,他的父親Joseph-Aristide已經感染了梅毒,接近失明、四肢癱瘓。在《眼睛的故事》中,他寫道:“我的神經性梅毒的父親在懷上我的時候就已經失明了,在我出生后不久,他就因惡疾而被禁錮在扶手椅上。”[7]1915年,他早已失智的父親去世。巴塔耶曾確信他父親亂倫式地撫摸過它,甚至強迫過他進行性行為,但這段歷史并未得到確鑿的證實。或許在巴塔耶的眼中看來,對父親的感情總是混雜著這種淫穢的愛恨交織。如果說,這些個人史并不足以讓我們推斷出“父之名”的脫落(forclusion du Nom-du-Père),因為這樣顯得有些倉促和冒進,但這一歷史的難以過活(invivable)確實足以讓一個人進入精神分析——不止是談論他的痛苦遭遇,更是談論他的享樂。
1925年,巴塔耶通過朋友認識了曾在圣-安娜工作過的精神病醫生Adrien Borel。有意思的是,Borel的名字與巴塔耶光顧的“妓院”和他生活的“爛攤子”(這兩個詞在法語里都是bordel)只差了一個字母d,而這個字母的發音正是dé,在法語中表示去除、剝除的前綴。也正是Borel在這一年給他展示了最著名的被凌遲的犯人照片。之后,在《內在體驗》(1943)中,他描述了受酷刑折磨之人傳遞給觀看者的共融(communion)式狂喜(extase):“頭發豎起,面目猙獰,面容憔悴,血跡斑斑,像妖女一樣美麗”[8]。在最后一本書《愛神之淚》(1961)中,他也重新展現了這些相片和對這一享樂的沉迷:“我從未停止對這種痛苦形象的癡迷,既心醉神迷又難以忍受”[9]。通過精神分析,巴塔耶串聯起來了他這一癡迷的連續性,他聯想到自己沉浸在患梅毒和性無能的父親的痛苦和死亡中的快感[10]。從這一意義上而言,Borel的介入促成了巴塔耶寫作的開始,又扣上了他寫作的結尾。
1926年夏天到1927年,他與Adrien Borel正式進入簡短又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精神分析。在和Madeleine Chapsal的訪談中,他這樣總結他的這段體驗:
我做過一段時間的精神分析,可能不是很正統,因為只持續了一年。雖然時間有點短,但最終它讓我從一個完全病態的人變成了一個相對可以生存的人[…]我寫的第一本書是在分析之后才能寫出來的,是的,從精神分析中走出來之后。我想我可以說,只有當我以這種方式獲得解放時,我才能夠寫作。[11]
從“難以過活”到“可以生存”(viable),并不是說物理現實中的創傷被清算干凈,而是說,在心理現實中,驅力以另一種方式激活。它不再只憧憬自己實在的機能性死亡,而是把死亡以符號的方式演繹在虛構之中,把死亡視為黑格爾主奴辯證法的賭注,引入他者,自此生與死的二元悖論得以在矛盾中延續。Borel的治療方式并非是弗洛伊德派那樣,找到創傷的源頭并給予解釋,而是和巴塔耶交流如何以其他的方式配置享樂——這種交流甚至是非-語詞的,直擊感官的。在這個意義上,Borel的操作是前-拉康式的:其治療的目的不是為了讓癥狀消失,而是為了讓癥狀有潛能地成為創造的線索,讓主體找到一個位置,站穩在世界中。
這些精神分析的理論和體驗材料,都將成為巴塔耶創作的養料。因此,在當下,我們重新引入這一角度再去看《文學與惡》,更是在塑造一種把他的生命歷程納入虛構中的解構式閱讀。雅克·德里達在其1975—1976的研討班《生死》(La vie la mort)中提出這樣解構弗洛伊德《超越快樂原則》的方式:他把biographique(傳記性的)一詞拆分成bio-graphique[12](生命-圖示)。而因為死亡又混雜在生命中,因此又可以寫作bio-thanato-graphique(生命-死亡-圖示)。他認為,弗洛伊德的自傳(autobiographie)和書寫場景如影隨形。弗洛伊德對其外孫Ernest著名的Fort/Da場景(也就是線圈游戲)的描述嵌套了他對自身死于重病的恐懼和對他者(hétéro)——女兒之死的哀悼,其實也是他自身哀悼、謀殺式和嫉妒式的認同(identification)網絡[13]:“(歷史)的遺產和嫉妒不僅構建了Fort/Da,而且將Fort/Da構建為自我-生命-死亡-他異圖示的書寫場景”。精神分析的理論作品、弗洛伊德的生死傳記和精神分析史上死亡驅力概念的演變就這樣通過“類比”(analogie),幾重嵌套在了一起。
書寫場景是否是遮蔽死亡之焦慮的面具呢?當我們借助德里達的這一思路,從巴塔耶的自我-生命-死亡-他異圖示出發,便可以揭開他書寫場景的種種嵌套、穿越《文學與惡》的幻象。但我們不妨從證明這一解讀巴塔耶角度的必要性開始。《眼睛的故事》的書寫場景中,巴塔耶戴上了Lord Auch的面具,而他的父親形象被掩蓋得只剩下了失明了的、只剩眼白的眼睛,淪為放蕩者的玩具。巴塔耶的傳記作者Michel Surya寫道:“在面具下,只有眼睛是可見的。但在面具下,一張盲人的臉還能看到什么呢?除了兩只死了的眼睛荒誕地出現在為它們開的縫隙里,什么也看不見。巴塔耶為自己的名字和父親的面孔戴上了假名的面具,從中可見的只是死物。在這種情況下,面具產生了一種悖論的效果,即遮蓋了活物,而裸露了死物”[14]。而我想補充的是,巴塔耶用虛構的活人名字置換了死人,并不代表他徹底遺棄了死物。他異性死物的不可名狀推動了虛構的生產,并一直存在于他的自我-生命-死亡-他異書寫圖示當中,使得碎片式的寫作可以成為一種未達成死亡狀態、沒有上帝律法而彌散擴張的生命。
現在,我們可以正當地提出《文學與惡》書寫中的三重類比關系,觀看巴塔耶如何把死亡、動物性和惡蒙上面紗展露其赤裸,如何把自我-他者-生死置換成文學史上永遠鮮活的人物和人性:(1)巴塔耶自身的éros和Thanatos與文學人物的情欲生死類比。(2)童年和原始社會心理的類比。(3)無意識之惡、意識之善(bien)與耗費之惡、勞作之善的類比。當然,這三重類比并非毫無交集的并行關系,而是環套鑲嵌在《文學之惡》的書寫場景中。
首先,巴塔耶在書寫,巴塔耶在書寫卡夫卡、波德萊爾、薩德……的書寫。如果說,卡夫卡的父親“代表著權威,他只關心有效行動的價值”,且我們已知巴塔耶真實的生父(le père réel)的一些信息,那么巴塔耶認為的符號性父親(le père symbolique)是什么呢?行動的世界、介入的世界、功用性的世界。巴塔耶在《卡夫卡》這一章中,選擇了共產主義立場來扮演這一符號性父親,因為“它是典型的行動,它是改變世界的行動”,這一行動顯然需要主體負擔起責任。面對父親,卡夫卡“讓自己仍然是那個不負責任的孩童”,而巴塔耶在和杜拉斯的訪談中,則承認:“我缺乏那些覺得要對世界負責的人所有的使命感。從某種程度上說,在政治上,我要求擁有作為瘋子的免責權……我不是那么瘋,但從任何意義上講,我都不會對這個世界負責。”[15]怎么能要求一個如此焦慮,離完全的瘋癲就差一步之遙的人負責呢?然而,當巴塔耶選擇為《文學與惡》中一系列文章署名,而非像其他虛構作品中一樣戴著筆名的面具出場時,便悖論性地選擇承擔責任,承擔作家的責任。如果說行動讓文學處于從屬地位,抗爭的出路便是擁有以自我賜死為代價的主權性:不為有用、效率、目的而寫作,也不為規范化的責任感而寫作,相反,是為反道德而寫作,為耗費寫作,為無目的的惡而寫作。
因此,在評述波德萊爾時,巴塔耶也認為,“在他身上占據上風的是拒絕工作,從而拒絕滿足;他維持在他之上的義務的超越性,只是為了強調拒絕的價值,以及更有力地體驗到不滿的生活的焦慮吸引力”。這一取向便是在對未來的關注(與有用性和道德并置)和當下(與消耗和感官享受并置)的關注之間做的選擇。主體在做選擇時,總會獲得和失去一些東西。選擇工作,意味著可以累積生存的需要,滿足生命的存續,但同時必須要承擔“成人”關注未來之首要性的責任;而拒絕承擔責任,就如同巴塔耶在他生命中想擁有像瘋子的免責權一樣,得經受無法滿足的持續性焦慮,走向存續的反面——毀滅性的死亡驅力。但把死亡置于主權式的選擇之中,便可以取消生命在等待死亡的過程中所等待的利益,因此得以擺脫詩歌、文學對作家的外在要求,遵從內心的私密要求。上帝或各種意義的“父親”的死允許了巴塔耶不期待“父”所許諾的效用性利益,使他成為自身的主權者,成為自身唯一的責任人。必須經由這樣的否定性操作,接受死亡的內嵌,“死刑判決”[16]的立刻到來,死亡在當下享樂時的懸置,巴塔耶才能悖論性地完成書寫文學之惡的責任。
從這一意義出發,巴塔耶、威廉·布萊克和詹姆斯·喬伊斯在“無名老爹”(Nobodaddy)這一新造詞上匯合了。這一詞由無名之輩(nobody)和爹地(daddy)組合而成。而Nobodaddy取自布萊克閱讀的圣經中一個人物的名字變形:Abaddon,在希伯來語中指的是毀滅。通過倒置和變形,這個詞又可以變成Nobadad。因此,Nobodaddy在布萊克的語境中,代表著不受經典意義上的上帝眷顧的,雜亂無章、幽暗模糊、具有毀滅性力量的原型形象,同時,又是看不見、摸不著,躲在云里享受原樂的嫉妒之父。巴塔耶借用布萊克的這一詞時,涉及到的形象更像是上帝所代表的律法消失后的“無頭人”(acéphale)。上帝死后,更糟糕的是欲望的消失,主體以前欲望著上帝的欲望,善引導著欲望,而后,主體要去欲望超出上帝欲望之外的東西,便要承擔巨大的焦慮,因為上帝不再為任何想要擺脫外在要求的欲望負責。巴塔耶和他評論的這些文學人物進行這樣主權式跨越時,不會有任何律法為它們的行動背書,不再有僭越這一欲望存在的合理性。在悲劇性的死亡之上,又疊加了一層喜劇性的歡笑,仿佛孩童在沒有父母的房間玩耍時面對破壞性爛攤子的無用(inutile)歡笑。“無名老爹”代表的正是這種荒唐的不司其職,上帝的拋棄。在《文學與惡》中,巴塔耶引用了“幻視者”布萊克的這首詩歌來表達這樣“不合時宜的自由”:
當克洛普施托克向英格蘭發起挑戰時,
威廉·布萊克驕傲地站立起來;
因為那上面的無名老爹,
放屁、打嗝、咳嗽;
然后,他大聲地咒罵,震動了大地,
疾呼英國人布萊克。
布萊克在蘭貝斯的白楊樹下,
正在解手。
然后他從位置上站起來
自轉三次,轉了三圈。
看到這一幕,月亮面色緋紅,
星星扔下酒杯,撒腿就跑[17]……
巴塔耶的世界便是這樣無父無頭的世界,更是一個沒有父法兜底的自由世界。這樣的自由永遠有著悖論性,它攜帶著摸不著邊界的恐慌,因為主體僭越上帝的欲望后,便要承擔無章法世界的到來,類似末世論的恐懼。正如詹姆斯·喬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寫道:“至于這些是罪惡還是美德,無名老爹會在末日降臨時告訴我們”。這意味著由“父”承擔的價值判斷的失靈。這三個人對這一詞的使用并非偶然,亞歷山大·科耶夫寫道:“所有的神秘主義都在這個詞里:Nobodaddy”。[18] 毫無疑問,這里對應著拉康所說的“父之名的脫落”(forclusion du Nom-du-Père)——這一概念指的是,沒有一塊地方,可以使得主體能在其中找到象征性的定位,來回答和命名“父”的顯現。因此,“父”在無意義的實在界回歸,以妄想、幻覺等的形式出現。
這樣的法外之地在現實中的對應物無疑是童年和原始社會。在《圖騰與禁忌》中,弗洛伊德試圖勾勒起這樣的聯系:無意識機制和社會文明組織形式之間的聯系,以及野蠻人、原始人的心理和人類心理發展階段的聯系。簡單來說,他提出了個人與集體進程之間的類比,將主體的驅力與文明的發展相提并論。他假設這些活在所有機制和組織之外的前-原始人展現了文明發展的第一階段,即所有的性驅力都毫無約束、不以繁殖為目標的階段。與之平行的,是兒童性驅力的倒錯特征——只追求部分性的快樂滿足。弗洛伊德為他的立論過程插入了父姓“圖騰”來解釋:即便在原始人那里也遵守著亂倫禁忌。而巴塔耶則徹底來到“父姓”之前的時代,也就是他在描述《呼嘯山莊》所說的“童年的王國”。他著重描寫這一被成人的算計所禁止的世界,也就是神圣的領域。在巴塔耶的筆下,它是天真、無邪和對當下享受的關注,是走向善的對立面,“童年的‘沖動活動’類似于神圣的迷醉,它完全處在當下。在兒童教育中,對當下瞬間的偏愛定義了普遍的惡。”凱瑟琳和希斯克利夫共同違犯了這個世界的理性規則,回歸童年時共謀的日子和野性的沖動,擁有律法之外的野性幸福,因此他們最終要接受彼此的獻祭。這種主權式選擇始終和巴塔耶成為“文學家”的選擇是同構的。
熱內作為生性頑劣的少年犯,不也一直固著在童年的王國里嗎?不也演繹了“成為作家”(devenir-écrivain)“從無到有”的過程嗎?首先,我們將建立熱內的生性頑劣與巴塔耶的關鍵概念“耗費”的關系。回到《超越快樂原則》的線圈游戲場景中,觀察者弗洛伊德作為“父”在場,他先入為主地認為,小孩子玩線軸應該是把線軸當車一樣拖來拖去,而他卻拽著線繩把線軸扔了出去。也就是說,精神分析之父認為,小孩子玩汽車、火車才是真正的游戲,而非摔東西、扔玩具。然而,事實上,孩子會毫不留情地在大人眼皮底下摔壞他們的玩具,他們會把玩具贈送給公園里剛認識的玩伴,他們會要求得到和哥哥或妹妹一樣的玩具,并在得到它的當下立刻把它扔到儲物柜深處。這便是兒童的玩樂——它像夸富宴(potlatch)一樣,具有奢侈、贈送和浪費的性質[19],是資本主義規則難以想象的場面。而孩子這樣做,是為了對抗大他者這一大人世界的符號秩序。在公園中當著其他家長的面因為抗議父母而大叫,為了就是“失去”(perdre),失去“父”強調的秩序,失去效率,同時讓大他者也失去臉面。孩童正是在這一肆意玩鬧的空間中獲得主權性。熱內和他筆下的人物便是這樣的“野孩子”。在他眼里為了利益而偷盜,滿足生活的需求,這樣的惡就成為了積累而非耗費,而因謀殺而被判死刑,則走向了耗費的最高程度:自我毀滅。巴塔耶這樣評論:
熱內只能在惡中成為主權者,主權本身也許就是惡,這一惡因為受到懲罰而更加確定是惡。但偷盜遠沒有殺人能得到的聲望多,坐牢和送上斷頭臺相比也是如此。罪的真正主權是屬于那些被處決的殺人犯的。熱內努力用想象力和看似武斷的方式贊頌王權,在監獄里,他不顧關禁閉的懲罰,大聲喊叫:“我在鐵騎上高貴地生活……,我進入他人的生活就像一位西班牙的最高貴族進入塞維利亞大教堂一樣”,他的虛張聲勢脆弱但又意味深遠。如果處處都充滿死亡,如果罪犯造成了死亡又等待著接受死亡,他的憂傷便會讓位給他認為是完滿的主權性。
對律法和禁忌的僭越讓無名之輩(nobody)一躍成為王室后代,擁有貴族的榮耀,過街老鼠成為目光的焦點,如同“名流”一樣以盛名存世。這樣的“成名”以自身的死亡為代價,它蔑視了生命存在的有限性,因為它像安提戈涅的行動一樣,打破了成文“父法”的界限,通過埋葬兄弟的舉動,在尚未死去的時候就被父法的世界除名,來到神圣律法的地域。毀滅自身的存續,但在此基礎上,犯罪主角的非人性讓她發出刺眼的光芒,使她獨異的主體性能夠被創造出來,并延續下去,這便是熱內給少年犯戴上璀璨皇冠的真正意味。如同巴塔耶評價的那樣,這種存在之美是“是由對延續的漠視、甚至是由死亡的誘惑所造就的”。可以補充的是,對延續的漠視其實是對人法時間局限的漠視,而通過耗費之惡、毀滅之惡,熱內和巴塔耶完成了主體被拋在沒有符號秩序的荒漠之后,無中生有的創造。正如拉康在《研討班七:精神分析的倫理學》中所說:“毀滅的意志。重新開始的意志。他異之物的意志,只要一切都可以在能指的功能基礎上提出質疑。[……]在這一點上弗洛伊德思想的要求其實是合理的,因為它要求相關的東西被表述為破壞驅力,正因為它懷疑所有的存在之物。但它也是一種從無到有的意志,一種重新開始的意志。”[20]不要忘記,拉康正是從本書的主人公之一薩德那里學來的毀滅沖動——真正的犯罪不僅是殺死身體,更是對自然交換秩序的毀壞。巴塔耶和莫里斯·布朗肖則看到,在巴士底監獄中,薩德把一切存在者的局限性、所有的創造物都驅逐出去,達到了徹底的毀滅。宇宙的孤寂和想象的浩瀚存在于四壁空無一物的牢房中,感官的滿足無法通過肉身實現,于是欲望無盡的創造、薩德式的理性思辨都得以自由滋長。
當我們回顧《文學與惡》中那些“成為作家”的道路時,會發現在“文學何為?”這一問題上,巴塔耶的立場和薩特的介入式寫作分道揚鑣。在這本書中,巴塔耶提到薩特譴責這樣的消費社會,而期待以蘇聯為范式的生產社會。巴塔耶承認耗費本就該被譴責,然后呢?他追求丑聞式的寫作,及其能傳遞的交流:一旦這樣的惡噴射向讀者,讀者立刻就沾染了神圣之物(即不可觸碰的禁忌之物)的骯臟。無論他的反應如何,都證明了這一傳染方式的命定性,即人們無處可逃。布朗肖評價巴塔耶《愛華妲夫人》的這句話很好地總結了這點:“這本書正是以這種方式抓住了我們,因為它不可能讓我們毫發無損,這是一本真正丑聞性的書,如果丑聞的本質就是人們無法抵御它,而且人們越是抵御丑聞,就越會將自己暴露在丑聞中”[21]。
我們最終會來到普魯斯特,以及他通過書寫承載起的東西——同巴塔耶做的一樣,不是別的,正是死亡本身。書寫欲望(Vouloir-écrire)和書寫之間的關系正如(死亡)驅力與(寫作)活動的關系一樣不言自明。羅蘭·巴特這樣評論馬塞爾的“成為作家”之路:“對于普魯斯特而言,寫作也意味著死亡可以用于某事,書寫書寫的欲望(écrire le Vouloir-écrire)說明了這點,即可以利用死亡,即書寫欲望和書寫可以用來拯救、征服死亡;不是他自己的死亡,即便他在與之抗爭,而是那些他曾愛過之人的死亡,通過寫作、通過使他們永存、通過將他們從非-記憶中樹立起來,他為他們做見證”[22]。正是由死亡的黑暗造就出的對比,生之幸福才令人渴望,因此,巴塔耶說普魯斯特比薩德更加狡猾,“他讓惡習保留了其令人憎恨的色彩,和德性的譴責”。保留惡的可譴責性,我們也偷偷為自己保留了幸福的可被欲求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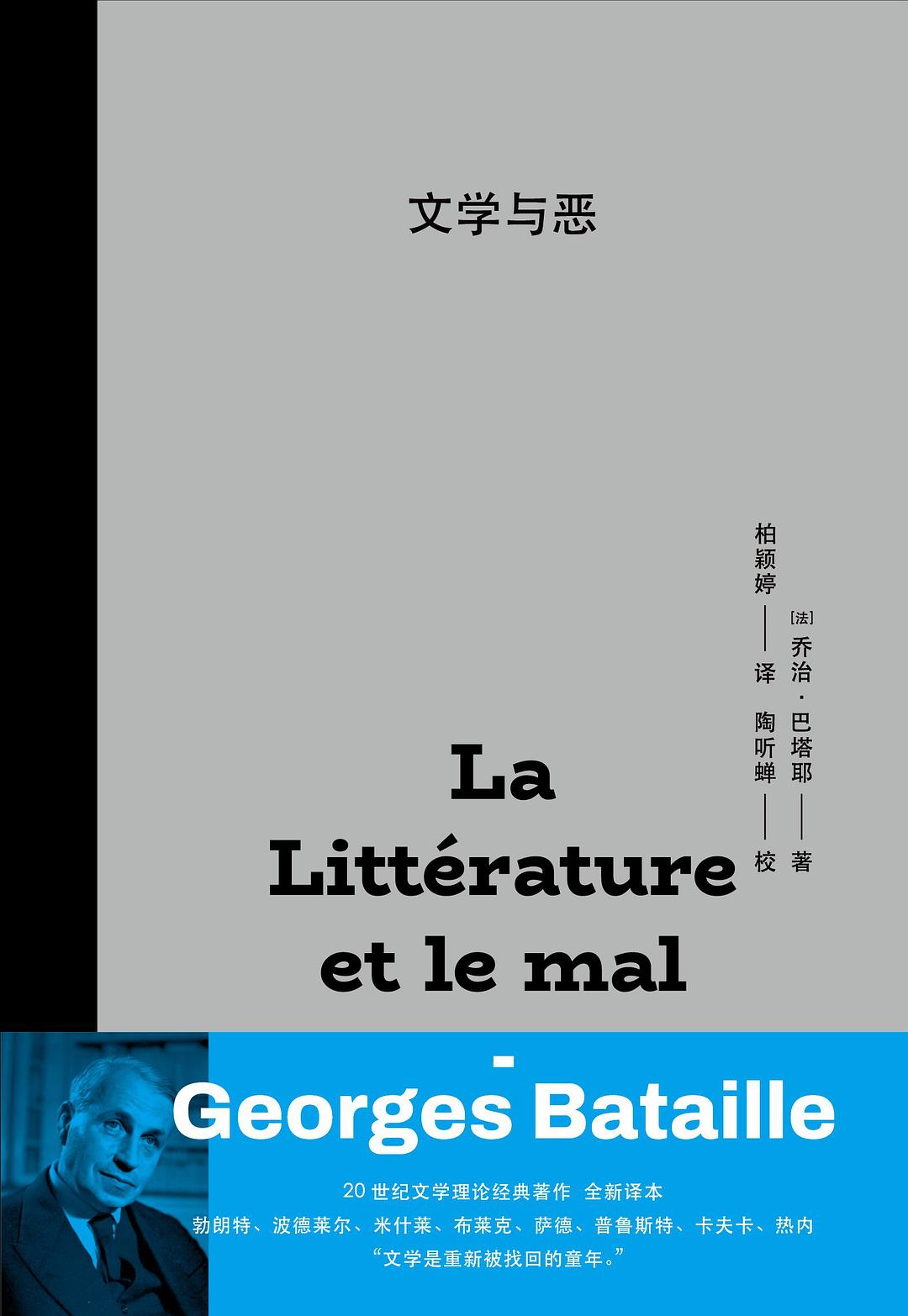
《文學與惡》;[法] 喬治·巴塔耶;譯者:柏穎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
注釋:
[1] 圣狀(sinthome)是癥狀(sympt?me)的一種古老的書寫方式,拉康在1975—1976年的研討班上使用這一術語來指寫作對于作家詹姆斯·喬伊斯的特殊作用。弗洛伊德曾認為癥狀也是一種痊愈的嘗試(tentative de guérison),而在拉康派精神分析看來,這一概念現在用來指主體用來站穩腳跟、串聯三界(想象界、符號界、實在界)的特殊方式,或是指主體與語言的特殊關系。
[2] 在拉康看來,閹割指的是兒童放棄與母親的融合狀態,從想象性關系過渡到符號性關系(學會語詞化他者的缺席、進入社會聯系)的過程。
[3] 當談及兒童性欲時,弗洛伊德認為兒童因其探索身體時驅力的局部性,具有多樣態性倒錯的傾向。
[4] Georges Bataille, ?uvres Complètes, tome XII, Paris, Gallimard, 1988, p.554 et 565.
[5] 羅杰·凱洛瓦在《人與神圣》(L’homme et le sacré)中也幾次提到人面對神圣之物時的矛盾情感:神圣之物既是有益的又是邪惡的,既會激發欲望又會激發恐懼。
[6] Georges Bataille, ?uvres Complètes, tome I, Paris, Gallimard, 1970, p.344.
[7] Georges Bataille, Histoire de l’?il, ?uvres Complètes, tome I, op.cit., p.75. 巴塔耶把“懷孕”這一詞賦予給父親,而并不在意父親的實際生理功能。
[8] Georges Bataille, 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uvres complètes, tome V, Paris, Gallimard, 1973, p. 139.
[9] Georges Bataille, Les Larmes d’Eros, ?uvres Complètes, tome X, Paris, Gallimard, 1987, p. 627.
[10] Michel Bousseyroux, ? La psychanalyse de Georges Bataille ?, dans L’inconscio letterario, n°6, dicembre 2018, p. 324.
[11] ? Entretien avec Madeleine Chapsal ?, parue le 23 mars 1961 dans L’Express, n°510, p.35. 筆者按:巴塔耶在精神分析結束的后一年1928年,用筆名Lord Auch寫了《眼睛的故事》。
[12] Bio(s)這一前綴源自古希臘語 β?ο?,表示生命。而graphique源于γραφικ??,表示書寫的動作。
[13] Jacques Derrida, La vie la mort. Séminaire (1975-1976), édition établie par Pascale-Anne Brault et Peggy Kamuf,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19, p.139. ? Et le legs et la jalousie ne construisent pas seulement le fort/da mais le fort/da comme scène d'écriture auto-bio-thanato-étéro-graphique ?.
[14] Michel Surya, Georges Bataille. La mort à l’?uvre, Paris, Gallimard, 1992/2012, p.113.
[15] Georges Bataille, ? entretien avec Marguerite Duras ?, France-observateur du 12 décembre 1957.
[16] 《死刑判決》為莫里斯·布朗肖的書名,法語標題L’arrêt de mort又可以被譯為“死亡的暫停”。
[17] ? Poèmes mélangés ?, dans William Blake, Poetry and Prose, p.103.
[18] Cité par Michel Surya, Georges Bataille. La mort à l’?uvre, op.cit., p.350.
[19] Marcel Mauss, ? Essai sur le don. Forme et raison de l’échange dans les sociétés archa?ques ?, dans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Paris, PUF, 1950, p. 239.
[20] Jacques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VII, L’éthique de la psychanalyse, Paris, Seuil, 1986, p.152.
[21] Maurice Blanchot, Le livre à venir, Paris, Folio essais, 1986, p.262.
[22] Roland Barthes, La preparation du roma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et 1979-1980),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15, p.37.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