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雜話”里的“暗功夫”丨高明勇調研筆記

高明勇 | 政邦智庫理事長
有不少朋友問我,你的“調研筆記”有新聞要素,有現場觀感,有閱讀體會,有行走隨想,有文學語句,有系統思考……這與傳統的文體類別都有明顯區別,算是什么文體?
很多時候來不及細說,我都簡單回答算是“雜話”。但這并非應付敷衍,確實是有出處的。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中以“雜話”的形式比較自由地表達了他對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特點的看法。
2022年,我在清華大學參加“墨點半日談”學術研討時,偶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呂文浩先生,他長期研究費孝通先生等社會學家。期間我們談到“雜話”這種形式,他認為“雜話”不像專業期刊論文那么規范和嚴謹,有話則長,無話則短,可以不等作者思考成熟和表述完整,即時地向讀者傳遞出其對相關問題的思考。但這種方式的不足是引證和表述都不甚完整和規范,給讀者留下了很多可供繼續思索的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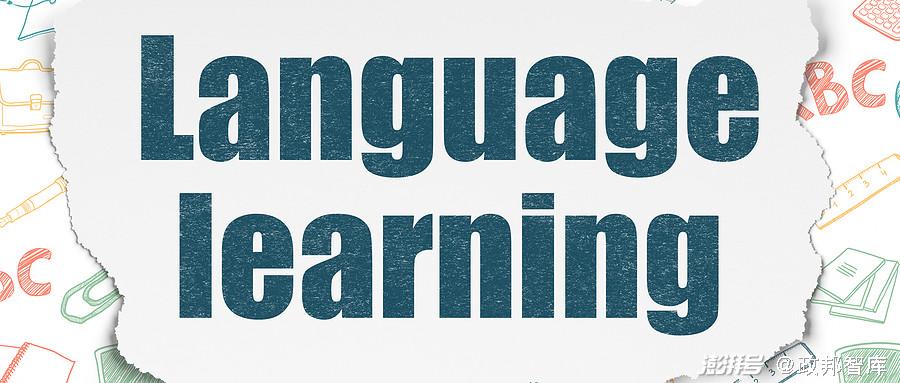
規范的說法,“雜話”也可以算作是“雜文”,我之所以采用“雜話”,而不是“雜文”,一方面,“雜文”這個概念因為使用廣泛,已經形成了固化的印象,容易限制在這一特別文體下的想象力與延展性,另一方面,“雜話”這個說法,因為費孝通先生的使用與闡釋,也有了社會學意義的內涵。“調查研究”,本身也是社會學研究的重要方式。
當然,“雜文”也好,“雜話”也罷,文本形式的背后是“雜學”。記得20年前,讀周作人的《我的雜學》,甚為嘆服。周作人一生閱書無數,古今中外皆有涉獵,其一生所學的思想路徑,都可在其“雜學”中追根溯源,他以中土、西洋、東洋為界,包括從中土的八股、散文、小說、筆記、佛經等,到西洋的神話學、人類學、生物學、醫學、性心理學、妖術史等,還有日本的民俗學、浮世繪、川柳、俗曲與玩具等,如數家珍。
也因此,他更看重行文的“見識與趣味”:“要在文詞可觀之外再加思想寬大,見識明達,趣味淵雅,懂得人情物理,對于人生與自然能巨細都談,蟲魚之微小,謠俗之瑣屑,與生死大事同樣的看待,卻又當作家常話的說給大家聽,庶乎其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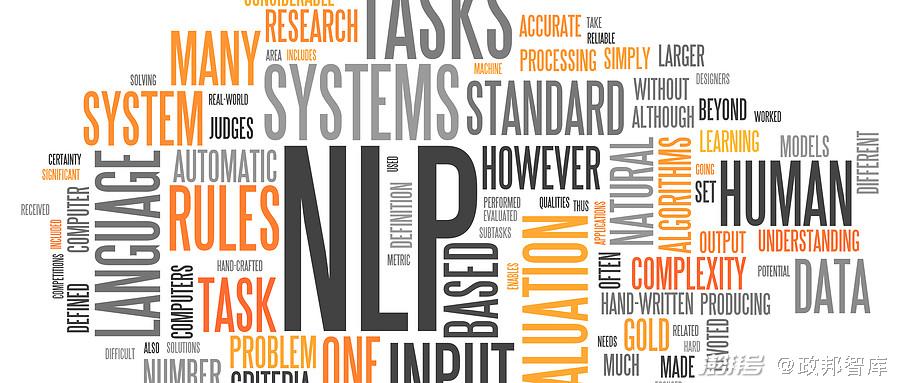
無獨有偶,魯迅亦如此。陳平原先生說,魯迅、周作人之所以成為現代中國散文最主要的兩種體式——“雜感”與“小品”的代表,除了政治理想與思維方式的差異外,還與其尋找的“內應”不同有關。
“雜感”與“雜學”,本質上是一脈的。學者孫郁認為魯迅的背后,是他的“暗功夫”。所謂“暗功夫”,即詞語背后的存在,它不顯現,但在無形里存在著,而且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詞語厚度的有無。暗功夫是摸不到的,是虛的存在,但爆發起來,卻有大的內力。(《魯迅的暗功夫》,孫郁)據統計,除了文學之外,金石學、考古學、科學史、文字學、哲學、美學、民俗學、心理學、歷史學的著作都有,這構成魯迅知識譜系的全面。魯迅的藏書被完整保留下來,有14000多冊。
最近,我與作家梁衡先生對談,談到他的作品《數理化通俗演義》,他認為就像是典型的三邊地帶,“三邊地帶打天下”,一個是文學,一個是科學,一個是教育。科學家不會寫,作家也寫不了,老師同樣也寫不了,反而是我這個經常采訪學校的記者,能寫這個東西,因為我又接觸科學家,又進行文學創作。梁衡先生也自稱“雜家”。
說到“雜家”,其實歷史上是有的,他們沒有明確的學派歸屬,兼采各家,匯合雜糅,獨立為派,被稱之為“雜家”。有觀點認為,從學術史的角度看,“雜家”融貫諸家學術,又批評諸家學術。不過有意思的一點是,關于雜家是否成一個學派,學術界也有爭議,梁啟超先生認為“既謂之雜,則已不復能成家。”
最近二三十年的知識界,“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李澤厚語),在這種時代背景與演變趨勢向下,“雜家”是否算一個學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真正的創造,則需要“雜家化”。
無論“雜話”“雜文”“雜感”,還是“雜學”“雜家”“雜家化”,關鍵是能雜而不亂,雜而能通,雜而務實,博學于文,以雜為專,專以求精。
基于“雜家化”思考撰寫的“調研筆記”,根子上說,還是延續了中國的文章傳統。
就像周作人在《我的雜學》中所言,一個人做文章,要時刻注意,這是給自己的子女去看去做的,這樣寫出來的無論平和或激烈,那才夠得上算誠實,說話負責任。(完)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