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對談|汪民安、姜宇輝、楊全強、尉光吉:理論在今天衰落了嗎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知識界出現了一股研究后現代和后結構主義的學術潮流。作為這一潮流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的當代法國理論開始占據主導地位。羅蘭·巴特、福柯、德里達、拉康、德勒茲、鮑德里亞等人的主要著作正是從這個時期開始被系統地譯介到國內,并不可逆轉地改變了中國的知識生態。
汪民安可以說完整地見證了這股潮流,并且是其重要參與者之一,他在世紀之交開始編輯輯刊《生產》,并完成了《誰是羅蘭·巴特》《福柯的界線》兩部著作。這兩部作品分別生動而準確地展現了羅蘭·巴特、福柯的思想歷程,二十多年里,兩本書都反復再版。
去年9月,南京大學出版社·守望者推出了《誰是羅蘭·巴特》《福柯的界線》的修訂版。除此之外,南京大學出版社·守望者近幾年還陸續出版了汪民安的其他著作:《現代性》《身體、空間與后現代性》《論愛欲》。這些理論著作極具風格性,它們既清晰生動又積極回應當下生活,在短期內都多次重印,廣受歡迎。
日前,在南京先鋒書店五臺山總店,汪民安攜手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姜宇輝、出版人楊全強、南京大學藝術學院特任副研究員尉光吉,與讀者分享了福柯等法國哲學家的迷人思想、理論的書寫性和功用性,以及哲學對當下生活回應的可能性。以下是本次對談的文字整理稿。

對談現場
楊全強:汪老師跟法國理論的淵源非常深,我想問一下你與法國理論,尤其是與你前兩本書的主角羅蘭·巴特和福柯,緣分始于何處?他們一開始是哪些東西吸引了你,讓你想更深入地去了解、去寫作,能不能跟讀者分享一下?
汪民安: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我讀研究生的時候,作為中文系的學生要看很多小說,那個時候我讀了大量的現代主義文學。當時非常流行卡夫卡、貝克特、喬伊斯這些現代主義作家,看的時候覺得非常有意思,它們非常吸引我,但是我當時也很難理解這些作品。我就去圖書館找各種相關的書和雜志——那個時候我們讀書主要靠圖書館。我讀過很多雜志,印象很深的是一本雜志是《當代電影》,那里面有很多介紹西方理論的譯文,它主要是從電影理論的角度來介紹拉康、阿爾都塞、德里達這些人的。實際上,電影研究和文學一樣,都是從這些法國理論中獲得啟發的。我就是在90年代初讀到關于德里達和福柯的介紹文章的。我印象很深的是第一次看到“解構”這個詞的時候,就莫名地興奮,我不太知道這個詞的意思,但是有一種被擊中的感覺。簡單的地說,我讀這些理論書,開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去理解那些現代主義小說,想讓理論來解釋小說,但讀了這些理論書之后,我發現我對這些理論更感興趣。我在那個時候很認真地讀了三聯書店出版的羅蘭·巴特的《符號學原理》,本雅明的《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尼采的《悲劇的誕生》等書,我那個時候不可能完全讀懂這些書,但越是這樣,它們對我越有吸引力——當時,沒有人指導我讀這些書,我覺得這純粹是一個身體上的吸引,慢慢地我的興趣就轉到理論的方向上了。當然,我對小說的興趣也貫穿了我的學生時代。只是最近一二十年沒怎么讀小說了。
楊全強:我們今天討論的核心是法國理論,姜宇輝老師翻譯過法國理論中的經典作品《千高原》,他自己的寫作實際上也是深受法國哲學的影響,姜老師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對法國理論的學習認識和感受。其實這些理論也是汪老師的研究重點,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眼中的汪老師的學術形象。
姜宇輝:我心目之中做得好的學問就應該有思想,同時應該有生命,我覺得汪老師剛才說身體有點低了,咱們應該把思想跟生命結合在一起,光身體的話可能還不夠。這么多年他一直都在不斷地去推進,從他開始寫書,出了《誰是羅蘭·巴特》《福柯的界線》,一直到后面寫《現代性》《身體、空間與后現代性》,前兩年出版了《論愛欲》。他每年都在堅持寫1-2本書,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說明他的生命意識一直都在那,這也是我心目中做學問的最純粹的一種境界。
我在大學的時候接觸了很多歐陸的理論,我也是跟汪老師一樣,從文學來入手。我當時是先鋒文學的狂熱粉絲,每天到圖書館就看《鐘山》,看蘇童、馬原他們的小說,當時這種文學的現代性對我來說有強烈的啟示,所以哲學一開始對我來說,就不是單純的思辨或者演繹,單純的寫論文或者學術的機器,相反它對我來說就是一種寫作,把生命變成文字,然后用文字來激蕩思想,我對它是有一種深刻的共鳴的,所以我也一直想從寫作的角度去打磨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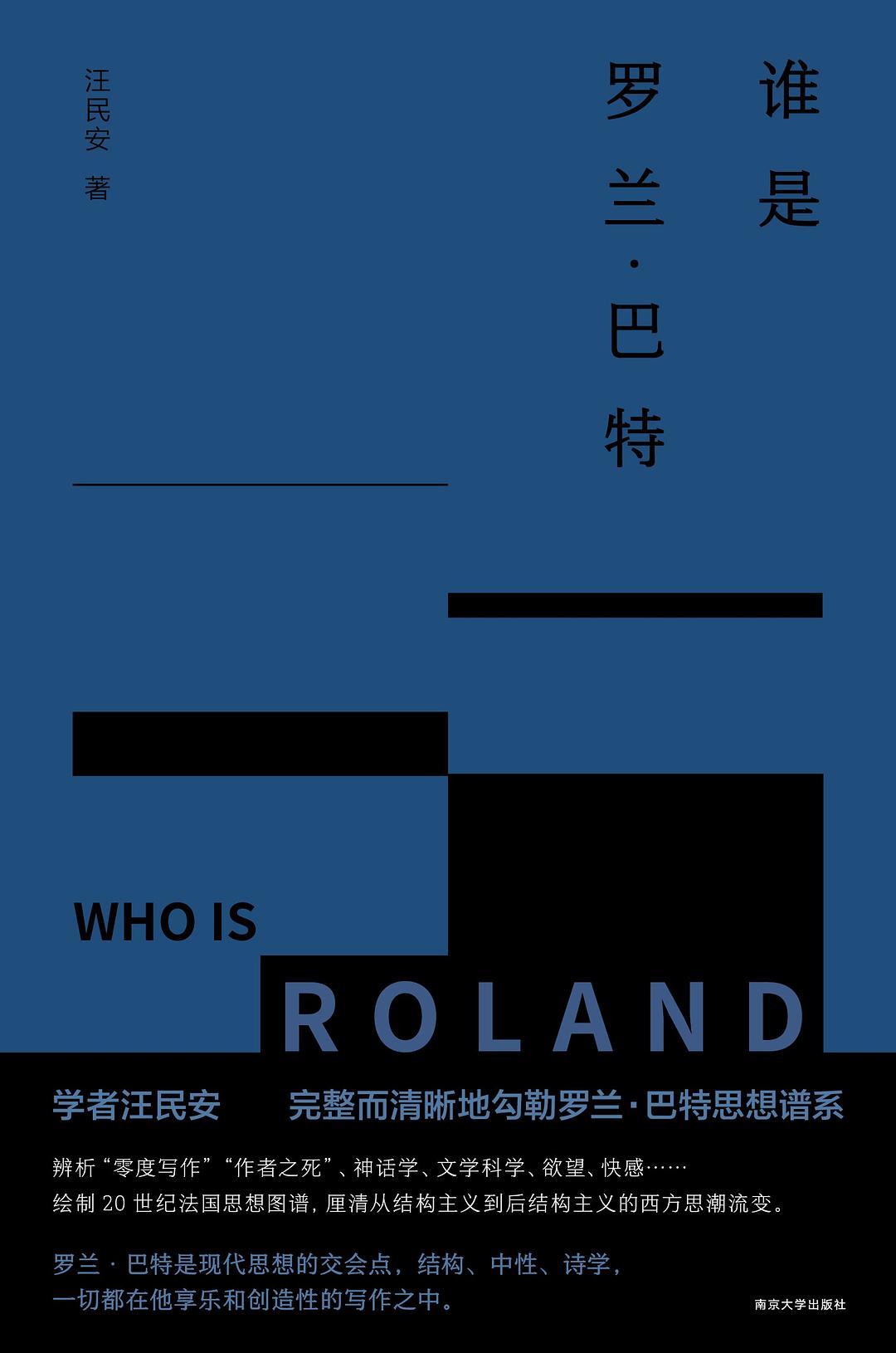
楊全強:尉老師跟汪老師也頗有淵源,他的博士導師吳瓊是汪老師特別好的朋友。我大概十幾年前就知道尉老師譯理論特別厲害,后來也有了合作,他也是我非常欽佩的一個年輕的學者、寫作者。尉老師能不能從你的視角說一說對汪老師的印象?
尉光吉:我接觸法國理論的時間在2005年以后,但我很早就看過汪老師的書,第一本買的是《誰是羅蘭·巴特》。我在接觸了歐陸的各種理論思想之后,最喜歡的就是法國理論。你可以在法國理論中看到一種文學性,這也是我們能從汪老師的文章中看到的。汪老師更多是在寫作的層面上吸引我,他的文章不是我們在期刊上看到的那種死板的論文。像汪老師后面寫的《身體、空間與后現代性》這樣的書,也是跟我們中國當代文化研究的一些非常具體的實踐有關的。讀汪老師的作品就像在讀散文,但是它里面又有一種思想的魅力,可以讓人一直讀下去。后來我才知道這也是法國理論當中的一種寫作態度。
楊全強:我們今天是對法國理論非常密切的分享,在整個西方哲學史上,六七十年代的法國哲學,或者說法國后現代理論是一個高峰,雖然我們統稱這一時期的理論是法國理論或者后現代理論,但實際上每位思想家的寫作方式、寫作領域,對世界觀察切入的角度都不太一樣。在這些思想家當中,最重要或者說影響最大的就是福柯。汪老師除了寫了《福柯的界線》這本書之外,前些年還拍過一個福柯的紀錄片,在北京放映過很多次,廣受歡迎。我想問一下汪老師,你對福柯特別贊賞、特別著迷是為什么?你愿意把福柯身上的哪些方面推薦給今天年輕的朋友們?
汪民安:我差不多在30年前接觸到福柯,到現在還經常讀。他大概是我讀得最多的一個作者。或許每一個讀者都有一兩個終身作者吧。我只要讀他,就能夠從他的書中吸取力量和智慧。福柯對我來說大概就是這么一個作者。至于福柯的哪些方面讓我著迷,我只能說,在不同時期讀他的時候,他都會對我產生不同的吸引力。我年輕的時候和現在讀他的感覺當然會有差異。我只是說說最近幾年的一個強烈體會。
那就是,我們今天遭遇的事件,福柯在他的書中都談到了——盡管他是對歷史的考察。這是我這幾年感受最深的地方,也是我最佩服的地方。也就是說,他去世了四十年,但他的關切點好像是此刻的現在。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比如說流行病,福柯在不同的書中都講到了這個問題,歐洲歷史上對待流行病的不同方式——你會覺得跟今天的非常接近。還有戰爭的問題,今天的戰爭非常接近福柯所說的生命政治導致的死亡形式和戰爭形式。還有你會覺得《規訓與懲罰》真的是一部偉大的預言性著作。盡管那本書是寫的17、18世紀的歷史,但今天才徹底實現了福柯所說的全景敞視主義。此外,他最后一本法蘭西學院的講稿《說真話的勇氣》,講的是犬儒學派,我也是最近幾年才讀到的,對我來說,那本書散發著強烈的鼓勵力量。
楊全強:那姜老師呢?姜老師其實也是國內重要的做法國理論的學者,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喜歡的法國理論家?
姜宇輝:我雖然研究德勒茲,但是其實我心目之中最喜歡的是福柯。一個最直觀的原因,當然說起來比較膚淺,我覺得福柯比德勒茲帥的不是一點。我是從碩士期間就開始讀德勒茲,博士論文也寫的是他。但這些年我越來越覺得福柯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法國理論家,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福柯特別強調“體驗”/“經驗”這個概念,最早從他的《古典時代瘋狂史》,他要研究的就是瘋狂的體驗,一直到《知識考古學》,他還是在講這個東西,所以我這些年也開始關注“體驗”這個問題。因為“體驗”跟“主體性”是非常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我這些年都想重新在數字時代去找到主體性,包括“主體性”跟“真理”,這兩個福柯晚期的核心概念也是我非常關注的。我覺得在今天這樣一個所有的東西都可以通過人工智能合成的時代,真理這個問題變得尤為重要,我們總要去捍衛它,然后通過捍衛真理去捍衛我們自己的主體,人的自由、人的地位。這些年我更關心的是這些問題,而這些問題是福柯給我帶來更直接、更強烈的啟示。
還有最后我想補充一點,在福柯的哲學里面,“僭越”“邊界”是非常重要的。有一個關于福柯的事件,福柯有一次在馬路上被車撞了,他倒在馬路的中央奄奄一息,他沒有報警,沒有叫救護車,就感受著自己瀕臨死亡那個時刻,他說那是他人生里面最快樂的一個瞬間。所以他的勇氣實際上是把生命推到一個極限,去挑戰那些危險僭越的東西,這可能是福柯的勇氣很重要的一個來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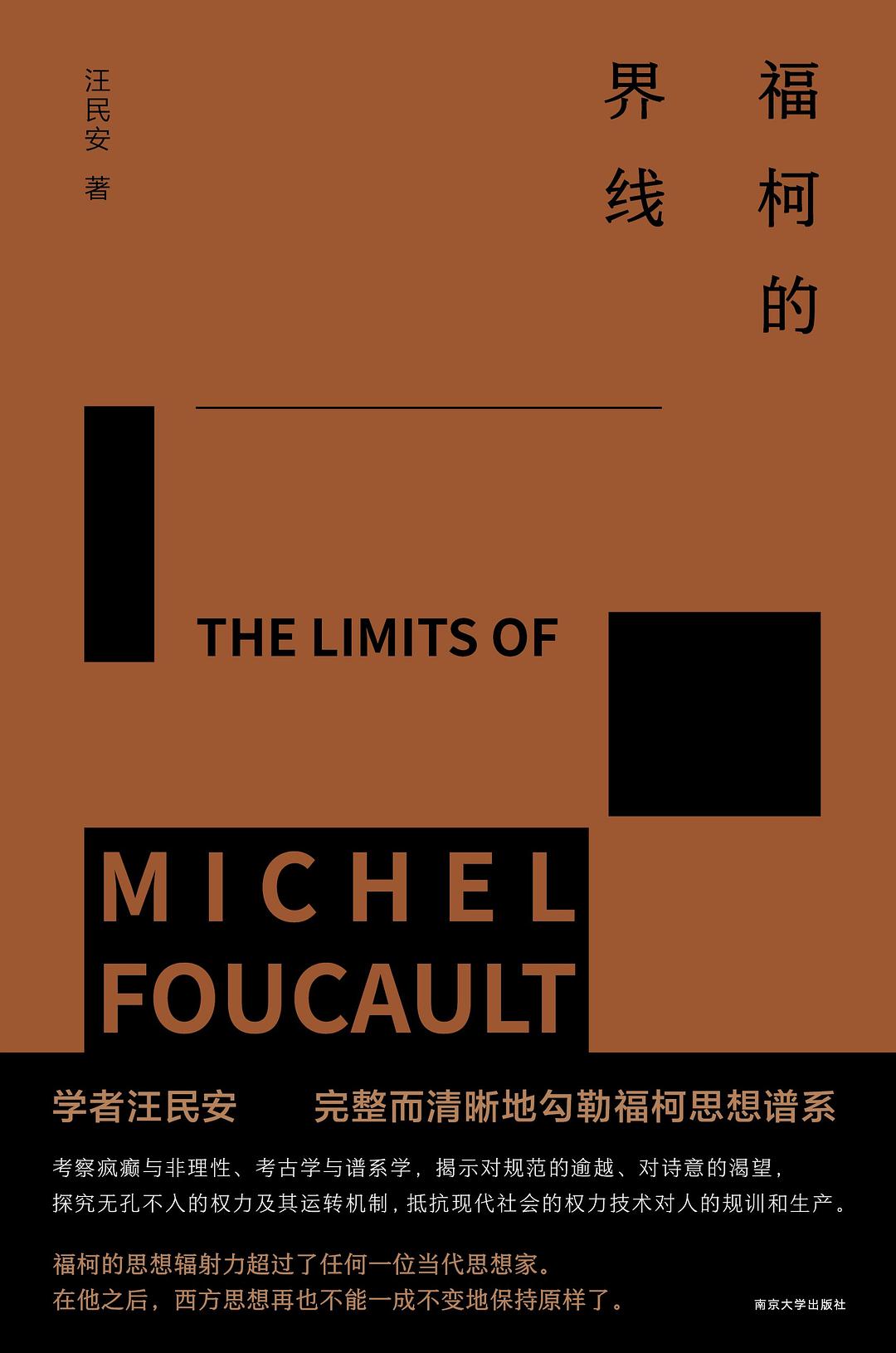
楊全強:我記得十幾年前一個學術會議,當時汪老師在會上有一句話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說你可以把理論看作一種藝術。在六七十年代理論的巔峰期過去后,現在好像進入了一個衰退期,想問問各位老師,這些理論在今天的學界是一個什么樣的地位,或者說大家對當年的那些理論現在大概是什么樣的態度?
汪民安:對于我們剛剛說到的這些思想,被美國人稱為“法國理論”。所以“法國理論”現在是一個比較固定的詞語了,我們知道“法國理論”的另一個名稱是“當代法國哲學”,但是人們為什么稱之為理論而不是哲學呢?我覺得理論跟傳統意義上的哲學大概是有幾點不太一樣。一般來說,哲學,尤其是德國古典哲學,討論的都是相對抽象的,概念化的問題。但是從60年代的法國這一輩人開始,哲學討論的對象變得更具體了,他們把傳統的哲學跟其他的學科進行結合。比如說精神分析,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文學和藝術這些學科跟傳統的哲學結合在一起,所以它有一種跨學科的色彩,突破了傳統哲學那種固定的、抽象的范疇和概念,這樣的目的是更關心社會問題,更關心一些具體的、當下的問題,它有很強的現實感。這樣的理論就跟傳統的抽象的思辨哲學區分開來,這是法國理論的特征。
至于有人說理論在今天衰落了,我不這么認為。任何時候理論都不可能衰退,只要人們在從事某種思考,都需要一種理論的深入。沒有理論的思考不過是一些淺顯的回憶。人類之所以是人類,就是因為他是沉思的動物。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上的任何一個階段,都有偉大的哲學家和理論家。只不過是他們的理論或者哲學內容不一樣。半個世紀前由法國人開創的主導性的理論潮流肯定會有消退的一天——事實上,它們已經在被消化,被改造,也在發展——但是,理論本身不會消退,總是有改造過和發展過的理論源源不斷地涌現。今天看上去理論沒有以前那么熱,但這是正常的,理論本身只是少數人的事情。
姜宇輝:我讀書的時候跟現在相比,現代理論如果說有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當時理論能夠成為熱點,成為社會的潮流。一個原因是當時西方哲學譯介比較少,引進一本書可能要等半年的時間,出版的書也很少,所以一旦有一本重要的哲學著作被翻譯過來,它一下子就會成為一個熱點,受到整個學界的關注和討論。但是現在出版業太繁榮了,每年出版的理論書數不勝數,每天可能都有新的譯著出現,一本書根本產生不了對整個社會的宏觀的影響力,這是一個明顯的變化。
還有一個原因,今天的理論實在是太過工具化了,它實際上就是學校里大家用來寫論文或者評職稱的工具,我看一本書不是因為它真的有那么重要,所以理論的社會影響力,包括對人生的影響力都下降了。今天大家談理論可能就是談理論,就是文本上的東西拿過來引用而已。
汪民安:你講的是一個事實,但這恐怕還不是理論所獨有的。我覺得人文學科都在衰退。在80年代,如果新華書店預告明天要賣外國文學名著,當天晚上就有人去門口排隊,這是現在的年輕人沒法想象的,那個時候整個社會對文化和知識如饑似渴。薩特的《存在與虛無》出了中文版,這本書其實是很難讀的,但是它也能夠印幾十萬冊成為暢銷書。那個時候只要是名著都是暢銷書,所以,不僅僅是理論在今天衰落了,整個人文學科都在衰落。
尉光吉:今天的理論書受眾都是非常有限的,一本比較專業的理論書差不多就賣四五千冊,基本上是針對高校或者比較專業的讀者,再也不會有普通讀者也充滿熱情去買一本這樣的情況了。就算在這些受眾中,也有很多人不會去買書了,就像我們剛剛說的法國理論,它已經被經典化了,思想家的觀點、代表作品教材里都幫你總結好了,所以你都不用去看原著。比如福柯,他變為了一個符號,雖然現在每年仍然在出新的福柯作品,但大家對這些書的需求跟二十年前肯定是不一樣的。
目前國內理論研究的現狀,就翻譯跟引進來說,還是遠遠不夠的。一些思想家像福柯、德勒茲,大部分的作品已經被引進了,但另一些我們也非常熟悉的思想家,比如拉康、德里達的作品,翻譯得又非常少。但是目前我們的理論書的確也在不停地出版,甚至都看不過來,這是一個非常矛盾的現狀。
讀者提問:各位老師,我是一個大四的學生,很喜歡做學術研究,我的研究方向和姜老師非常接近,也是對數字時代的理論的關注。我的問題是,我們現在對理論的運用是不是已經泛濫了?不知道這個詞是不是合適,我平時在寫論文或者學習老師們的文章的時候發現,大家都陷入了一個怪圈,會臆造一些理論,但是可能我們對這些理論的掌握并不深刻,甚至都不算了解,就是為了引用而引用。我覺得理論根本沒有衰退,它反而泛濫了,深刻地鉆入了我們生活的每一個地方,任何角落里面都會出現理論,我們到底有沒有真正讀懂這些理論,或者是把它當作我們的一種精神延續下去,這都是我現在思考的一些問題。
汪民安:你提到的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也是很多學生會問的問題,就是到底我們對理論的運用是否正確?我們是否真正地理解了這些理論?我覺得我們可以從福柯對尼采的使用中獲得啟發。福柯是尼采的信徒,但是他說過,尼采講了什么,尼采的真實意圖是什么,我們能不能搞清楚這些,其實并不重要,或者說,并不是太有意義。有意義的是如何去運用尼采。運用尼采并不意味著我一定要回復到尼采的原意。相反,我可以創造性去運用尼采,我可以把他的某句話發展為自己的東西。德勒茲對此講道,尼采射了一支箭,福柯把它撿起來射向另一個方向。
也就是說,一個好的作者也許不是要努力地回到原作的意義——事實上,原作或者理論的意義有時候是很難把握的。這就是理論為什么晦澀的原因,如果它非常清晰的話,理論著作就不可能以那樣的形式出現。在這個意義上,你不要想你對理論的使用對不對,如果說你對于海德格爾,對于德勒茲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理解,哪怕你的理解并不是他們的原意,這也沒關系。只要你從他的理論當中得到刺激和啟發,然后去闡釋你自己的東西,這同樣是有意義的。
讀者提問:汪老師您好,我想回應一下今天的主題,您寫過很多有關現代性和當代性的著作,都是試圖用法國理論去剖析我們的現代性生活。我想請教您,像我們這樣的年輕人,生活在這樣一個充滿了結構和符號的社會中,我們應該如何用哲學來回應或者說去解答我們當下生活的問題?
汪民安:哲學是很晚才開始回應當下生活的。按照福柯的說法,這實際上應該是從康德開始的,在康德之前的哲學是不回應現在的。康德有一篇文章叫《什么是啟蒙》。康德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就在討論他所在的那個時代,啟蒙時代。哲學在這之前,基本上不討論哲學家所在的時代。這篇文章這樣一個主旨,對福柯有很大影響,所以福柯說他的哲學就是有關現在的本體論,他的哲學就是討論現在的。但是你看福柯的書,全部都是講歷史,從古希臘、羅馬,講到文藝復興,再講到17世紀,直至20世紀,它看起來都是歷史著作,所以很多人說福柯是歷史學家。但是福柯講歷史是為了講現在,講現在的我們是怎么從歷史中過來的,他的關注點是現在。也就是說,他回應現在是通過歷史的方式。
我覺得本雅明對現在的回應也采取了一種非常有意思的方式。本雅明的主要著作都在講他此刻遭遇到的現代性。但他怎么來講現代呢?他借用的“浪蕩子”的形象,一個旁觀者的形象,這個浪蕩子置身于時代中,但也脫離時代,他是時代的旁觀者,也就是說,他在人群中,但不被人群裹挾。這個思考形象非常有意思,一個理論作者對時代的回應,也許首先就是要跟這個時代拉開距離來分析和觀察這個時代。
姜宇輝:汪老師剛才談到本雅明,我最近也一直在看本雅明,本雅明所說的“漫游者”或“浪蕩子”,他們漫游在這個世界里面,其實不是為這個世界辯護,也并不僅僅是旁觀,相反,他們要看到這個世界荒誕的地方,不自洽的地方,偶然的東西,斷裂的東西。這個世界在我們面前是縫合起來的,看起來是一致的、完美的,光有各種各樣的理論為這個世界辯護,告訴我們這個世界是正義的,這個世界是有希望的,這個沒有意義。本雅明的“浪蕩子”,他們看到的是這個世界自相矛盾的地方,黑暗的地方,他們看到的東西跟你不一樣。你看事物是戴著有色眼鏡的,因為你已經有固定的框架、成見,但真正的哲學就是要刺痛所有支撐你生活的,信仰也好,常識也好,傳統也好,讓這些土崩瓦解。它是一個否定的東西,自己否定自己,甚至要經歷一個自我死亡、自我殺戮的過程。哲學的快樂不是來源于迎合這個時代,而是找到真實的生命的意義。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