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小說、歷史與小說的歷史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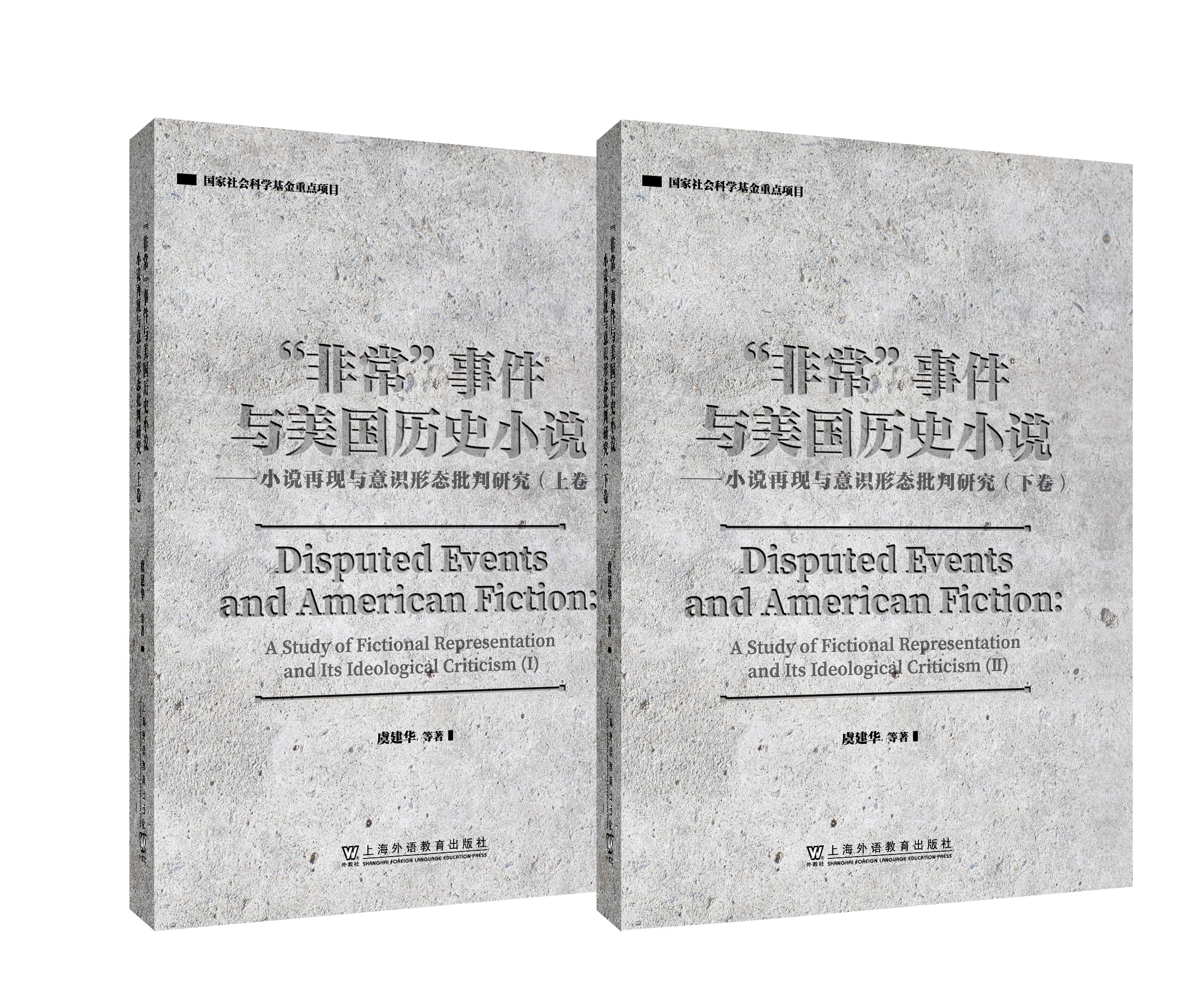
《“非常”事件與美國歷史小說——小說再現與意識形態批判研究》,虞建華 等著,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
不管是口承的還是書寫的,人類早期文化中對過去記錄和敘述的經典作品,都以“詩史合一”為特征,最典型的是“史詩”。中國早期歷史著作《春秋》和《史記》也一直被視作文學經典,“師范億載,規模萬古”。最早的小說脫胎于歷史。自古以來,文學與歷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學記載歷史,歷史賦予文學以主題和內涵。當代著名美國作家埃德加·勞倫斯·多克托羅仍然強調史、詩兩者的關聯,說:“歷史是一種我們生存于其中的小說,小說是一種或然歷史,或者也許可稱之為超歷史,這個歷史的書寫材料遠比歷史學家所能涉及的更加廣博浩大,更加豐富多彩。”
但這樣的說法已經帶上了比喻的色彩,“詩”和“史”兩種敘事畢竟在近代分道揚鑣了。在19世紀史學家的踐行之下,歷史研究逐漸演變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打起“科學”和“客觀”的大旗,以此為其安身立命之本,而小說則強調其“藝術性”和“想象創造”的虛構特權。兩者互相排斥、橫眉冷對、彼此輕慢,成為一組二元對立。多年來,歷史話語似乎占據了高點:歷史是真實的,小說是編造的;歷史基于嚴肅、科學的考證和記載,提供真理性的認知,而小說出自想象虛構,供人娛樂消遣。小說和歷史的傳統分野一度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不容置疑,不容混淆。
“歷史上的曹操和小說中的曹操,是兩個人,一個是歷史人物,一個是藝術形象,歷史人物是客觀存在的,而藝術形象是作家和讀者的長期創造。今天,一個成熟的讀者的頭腦中,《三國演義》中的曹操絕不會等同于《三國志》中的曹操。”這是今天所謂的“舊歷史主義”的認識觀,具有典型性。“舊歷史主義”的說法原先并不存在,隨著新歷史主義的產生,傳統的歷史認識觀被賦予了與之相對應的名稱。新歷史主義要強調的是,《三國志》中的曹操也不等同于真實的曹操。那么真實的曹操呢?真實的曹操死了,史書作者、小說作者和讀者誰也不認識、不了解他。《三國演義》和《三國志》的作者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他們都是按照各自能獲得的前人留存的書寫材料來建構曹操這個人物形象的,而建構的過程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自己的知識局限,不可避免地融進了自己的理解、認識、性情、喜好、偏見和想象,也不可避免地在某種程度上受到當時意識形態的影響和制約。新歷史主義更強調歷史與小說兩者的共性,而不是差異。這個共性就是歷史和小說共享的語言敘事特性。
其實,從“詩”“史”分離開始,不少歷史學家就意識到歷史書寫中想象和虛構成分難以避免,而這決定了以書寫方式維持的歷史知識本身的不確定性。現代史學理論開始把“敘事”視為史學之根本。當然,敘事也是文學的基底,這樣,兩者間就有了廣闊的交集。以海登·懷特的《元歷史》的出版為標記,一種與傳統歷史觀完全不同的后現代“新歷史”認識逐漸被學術界接受,確定了史學家建構歷史的方式是詩性的。分久必合,歷史和文學走近靠攏,“史”與“詩”的兩分法不再被廣泛認同。海登·懷特指出:“歷史事件首先是真正發生過的,或是據信真正發生過的,但已不再可能被直接感知的事件。鑒于這種情況,為了將其作為思辨的對象來進行建構,它們必須被敘述,即用某種自然或技術語言來加以敘述。因此,后來對于事件所進行的分析或解釋,無論這種分析或解釋是思辨科學性的還是敘述性的,都總是對預先已被敘述了的事件的分析和解釋。這種敘述是語言凝聚、替換、象征和某種貫穿著文本產生過程的二次修正的產物。”
新歷史主義強調,我們在討論“歷史”的時候,涉及的其實只是由記憶和語言組成的“知識論”的歷史,而非“本體論”的歷史,這樣的推導呼應了意大利歷史學家貝奈戴托·克羅齊的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在《政治無意識》一書中呼應了懷特的新歷史觀。他指出,歷史“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們,我們對歷史和現實本身的接觸必然要通過它的事先文本化,即對它在政治無意識中的敘事化”。歷史書寫和文學書寫都是語言再現,都是文本化的重構,兩類書寫者都運用文學書寫特有的文字手段、語言藝術和敘事策略來建構某種狀況,表達某種觀念。也就是說,新歷史主義“承認歷史學家不可能客觀地、科學地復原過去,而只能從現在的視野中構造過去”。傳統的“舊歷史”觀由此受到挑戰和顛覆,歷史與小說因其敘事模式大同小異而變得界限模糊。這樣,歷史與小說的共同特征被凸顯,距離被拉近,兩者之間的互文解讀不僅可能,而且也變得富有意義。
小說通過虛構再現歷史,但“虛構”不是“虛假”的等同概念。小說虛構往往可以凸顯真相的多元性。因此,小說再現的歷史不應該被看作對歷史的戲弄或篡改,而是對歷史的重新陳述。歷史小說家以自己的方式呈現事件,重構語境,讓文學話語與歷史話語形成對話或碰撞。這種文學性的歷史再現,可以豐富或修正歷史敘事,也可以使之瓦解。在歷史宏大敘事和小說家們以真實事件為藍本的文學文本之間進行比較性的解讀,我們可以看到真理的多面,從而逼近事情的真相。被稱作“新歷史主義”的后現代史學觀在認識上具有顛覆性,但如林瑛指出,“其目的并非全然否定一個不可知的大寫的歷史,而是給予小寫的復數歷史以合法的地位,從而深化關于歷史性質與本質的反思與認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美國文學中以歷史事件為素材創作的小說,是作家們參與歷史建構的努力,而對這些歷史小說的解析,有助于我們揭示歷史沿襲過程中美國文化生態的構成要素和發展變化,也可以為我們思考、解讀似曾相識的當下政治和社會情境提供借鑒。
在英國文藝理論家特里·伊格爾頓看來,“歷史是文學的終極能指,也是文學的終極所指。因為只有給表意實踐提供物質母體的真實社會形態才可能是表意實踐的根源和目標”。當代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呈現出歷史轉向,涵容了更多的文化政治關懷,走向空間性和對話性的歷史。在這樣的大潮流中,將那些重寫曾引起關注的“非常”事件的歷史小說重新放回歷史語境中細細品讀,有其特殊的意義,因為它們是美國種族、階級、宗教矛盾激化的產物,而作家的再現在選材上具有針對性,在思想上具有顛覆性,在呈現方式上具有多元性,提供了“另眼”觀察美國政治和民族道德體系的核心價值問題的渠道,可以引向對美國的建國理想、民族精神、政治信仰等意識形態重大方面的再思考和新認識。
歷史小說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模式,能夠充分利用自己獨特的屬性,如虛構特權、多義性、話語間性來評說歷史。這種評說帶有意識形態批判的性質。作家們多從邊緣人物的小敘事入手,透過具體和個別,放大觀察歷史的某些片段反映出來的更帶普遍性和本質性的問題。優秀的歷史小說家們總是尋找官方歷史表述中省略的東西,通過對歷史素材選擇性的再組合、對歷史事件的想象性推演、對歷史人物的多面性塑造、對歷史語境的補充性鋪陳,讓小說的美學再現填充、修補,甚至顛覆歷史的宏大陳述。“對于所有作家,而非僅僅偉大的作家而言,一旦他們拿過某個故事,寫成自己的文本,他們就已經卷入了一種異質性的闡釋。”正是在虛構敘事與歷史敘事因并置和交疊而生成的巨大闡釋空間中,本研究試圖通過互文解讀,討論作家如何參與歷史的建構,并在這樣的建構中凸顯文學的意識形態批判功能。
(本文節選自《“非常”事件與美國歷史小說——小說再現與意識形態批判研究》,有刪改。)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