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夜讀丨爺爺?shù)闹駡@

作者供圖
周末逛超市,看到蔬菜區(qū)設(shè)了“春菜”專區(qū),主打是筍類。矮胖的春筍,細長的雷筍,褐色的外殼上一層薄泥,露出白嫩的軟殼和細細的絨毛。滿眼都是江南春天的氣息,讓人心生歡喜。
想起來家里還有一包筍干,放了好幾年了,不知道長霉、生蟲子沒。忙回到家,打開包了好幾層的袋子,還好,仍是干干爽爽的,有股淡淡的香味。
這包筍干,是每次回家,母親都要給我捎上的。每次舊的還沒吃完,新的又來了,幾次下來,竟也攢了一大袋。在前幾年那段不便出門的日子里,我用它做了好幾頓菜,用水泡發(fā)后素燜,或加上咸肉和其他新鮮蔬菜一起炒,很有嚼勁。當然,比起果腹,它帶給我的,更多是滿滿的安心感。
筍干產(chǎn)自我家的竹園。老家所在的皖西南多山,漫山遍野的竹子。風(fēng)吹竹林,掀起陣陣綠浪,不知道曾搖曳了多少孩子的夢境,給多少往來忙碌的大人們送去清涼。
不過,我家的竹園屬于“私家園林”,是爺爺在一片長有幾棵野竹的荒原上,劃出一片地,再帶著父親和叔叔們,從河灘上挑來一擔擔的泥土,筑起一道一米多高的圍壩,以防止野獸和放養(yǎng)的家禽闖入。幾年的精心養(yǎng)護,加上竹子開枝散葉的厚積薄發(fā),才有了后來這滿目濃蔭。
其實,在我的家鄉(xiāng),沒有食筍的傳統(tǒng)。春天破土而出的嫩筍,對于孩子們來說,是大自然饋贈的玩具。我最喜歡折一根在手,剝?nèi)ヒ粚訉拥臍ぃ購闹虚g一折為二,就為了聽那清脆水潤的“啪嗒”一聲。在漫長孤寂的童年歲月里,農(nóng)村孩子善于從大自然中開發(fā)娛樂方式。
幾年前,一位親戚查出高血脂,她不知道從哪聽來的法子,說竹筍是粗纖維,可以促進腸胃吸附油脂,減少身體對脂肪的吸收。她早知道我家有一片竹林,便來我家商量,能不能去我家竹林采筍。父母自然同意,也第一次聽說吃筍還有這好處,自此就留了心。每年新筍冒頭之時,父親總要花上一兩天的功夫,去采摘幾籃子的筍子。母親切成細細的筍絲,在好天氣里曬干,儲存起來,等我們放假回家時帶上回城。
可能因為從小沒有吃慣,我不能完全領(lǐng)略筍干的美味。偶爾以“鄉(xiāng)味”“鄉(xiāng)愁”的情懷名義,挑個周末的閑暇時間,吃上一頓,還不錯,但連吃幾次,就味同嚼蠟。總覺得被曬掉了水分的菜蔬,也失去了精華和靈氣,比不上新鮮的。古人有“莼鱸之思”的美談,用鄉(xiāng)中美食寄托游子的思鄉(xiāng)之情,但用的意象也是菰菜、莼羹、鱸魚膾,三種都是新鮮時令之物。如果用一種菜干來比喻,大抵這鄉(xiāng)愁也顯得有些干癟了。
江浙滬的吃筍文化由來已久,一碗“春鮮第一位”的春筍,不知道在江南人家的餐桌上流轉(zhuǎn)了多少年,又由文人雅士衍生出了許多精彩詩句和美好故事。白居易任蘇州刺史時,湖州刺史崔元亮每年都給他送春筍,白居易作《食筍詩》表達謝意,末句說“且食勿踟躕,南風(fēng)吹作竹”,簡直寫出了催人及時吃筍的勸誡意味。“竹癡”鄭板橋,寫下了“江南鮮筍趁鰣魚,爛煮春風(fēng)三月初”,為會吃的中國人又貢獻了一道春日限定款珍饈。
得益于現(xiàn)代食品工業(yè)的發(fā)達,吃筍早已突破了時令限制。還在冬天,單位食堂就推出了“腌篤鮮”’,作為配菜之一的春筍先于春天到來了。在春筍和鮮肉炮制出的濃湯里,打工人們提前感受到了暖暖的春意。
小學(xué)二年級時,爺爺永遠離開了我。他長眠于自己親手建起的竹園,從此與清風(fēng)明月為伴,守護著這片土地。我想,爺爺帶著父親、叔叔們肩挑泥土筑壩之時,一定不會想到,幾十年后的今天,竹園會給在離家六七百公里之外的我,帶來實用性和精神慰藉。這是三代人之間,跨越時空的血脈相連,也是前人勤勞付出對后人的恩澤庇佑。
在這個春天,對已離開我近三十年的爺爺?shù)乃寄睿驗檠矍斑@一袋筍干,因為縈繞心中的那片竹園,是如此清晰而悠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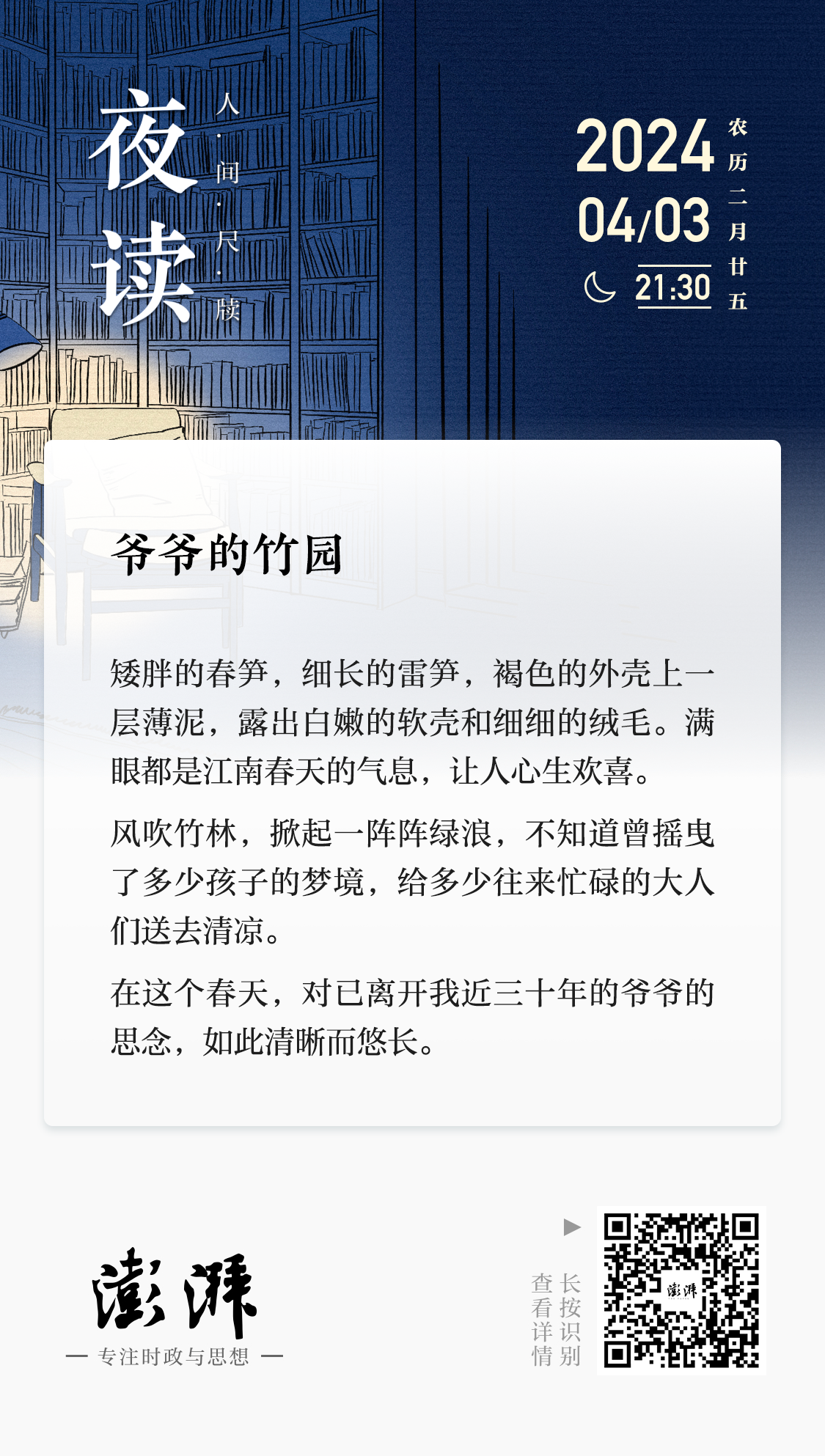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