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紀念陳旭麓先生︱高瑞泉:地平線之外的“史”與“思”
【編者按】
2018年適逢歷史學家陳旭麓先生百年誕辰,也是他逝世三十周年。為更好地梳理傳統、致敬前賢,2018年9月7日,《華東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組織召開了“新陳代謝:陳旭麓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傳統”學術研討會,邀請老中青三代學者深入研討陳旭麓先生的學術成就與深遠影響,并選取部分于近日刊發于學報第六期“致敬大師”的專題策劃中。本文系此專題文章之一,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文章原題《觀念變遷的“史”與“思”——重讀〈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

今年是著名歷史學家陳旭麓先生誕辰100周年,也是他逝世30周年。我們在這里研討陳先生的思想與學術,寄托對他的一份紀念。就我個人來說,應邀參加會議,還帶著對先生的一份特別的情感。三十多年前,我以“中國近代唯意志論思潮研究”為題做博士論文,陳旭麓先生是我的論文開題報告的審閱專家之一,后來又是我論文答辯委員會委員,耳提面命之余對我多有鼓勵。按照舊例,我雖未登堂入室,也曾忝列門墻。其實我受教于先生還要更早,1982年秋我進入華東師范大學,跟隨馮契、曾樂山、丁禎彥諸先生攻讀中國哲學的碩士學位,專業方向是中國近現代哲學。當時馮契先生正在講授“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并著手將其整理刊定成書。陳旭麓先生在給歷史系研究生講述“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后來出版的有著鮮明個性特征的同名遺作,可以說是一本蘊含著觀念史豐富內核、以廣義社會史為主要形態的近代八十年中國通史。馮、陳兩位先生的研究不僅對象重疊,旨趣與方法也有交集。按照馮先生的哲學史觀,哲學雖然有自己獨特的問題和自身的線索,但是根本的動力還是生活實踐,所以哲學史的研究要和社會史相結合。而歷史研究尤其是觀念史研究中,如何處理“史”與“思”的關系,一樣需要辯證思維。這一點,馮先生后來在給陳先生的遺著《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一書所做的序言中說得很明白:“旭麓搞歷史,我搞哲學,兩人專業不同,研究方向不同,卻正因為此,我們可以互相切磋。我認為哲學演變的根源要到社會史中去找,他認為歷史演變的規律要借助哲學的思辨來把握;所以我們常常把自己正在研究、思考的問題提出來向對方請教。”兩位先生可謂相交既久相知甚深。加之,我年輕時對歷史一直很有興趣,經歷過20世紀后半葉那些波潮和迴流以后,更相信龔自珍說的“欲知大道,必先為史。”不過我的趣味和能力都不在于潛心抉發資料、考辨史實,而是私心仰慕司馬遷所云“通古今之變”。所以,當馮先生吩咐我們去歷史系旁聽陳先生的課,我真心覺得十分幸運。因而有機會比較完整地聆聽陳先生講述“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現在我偶爾翻閱當初的聽課筆記,眼前還會浮現陳先生講課的情景:桌上除了一包煙、一聽茶葉供學生自取外,僅僅三五張卡片,復雜的史事用他濃烈的湘鄉口音娓娓道來,意蘊之新則常出人意表。一堂課的內容記錄下來通常就是一篇成熟、嚴謹的著述,情感時而澎湃時而沉郁,文彩斐然更非一般近代史著述可以比肩。這一輪課給我這樣的初學者最大的開悟是:歷史居然可以這樣講!自那以后,許多從事過近現代哲學研究的同行紛紛轉向,我生性愚駑,對中國近現代哲學史研究的興趣數十年未改,且我注重的工作是從思潮到觀念,與社會史和一般思想文化史的關系更為切近。也許因為這一點,《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出版以后,成為我案頭常備書之一。受他的啟發,我還寫了一篇小文,認為《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對研究近代中國價值觀念轉換與重建這類大問題,有重要的方法論啟發:“對價值-文化的核心問題的研究,絕不能停留在觀念的領域,尤其不能化約為單純的義理,而應當把握社會史的具體流程。”對觀念變遷之“思”一定不能離開觀念之“史”。
從觀念史研究中“史”與“思”的關聯看,陳先生著述《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其實有著強烈的現實感。當時,學術界正處于所謂“文化熱”之中,對壘的雙方后來被稱作“文化激進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圍繞著“傳統VS現代”的問題,雙方各執一端。現在看來,文化激進主義有見于現代化需要本民族文化價值的轉型,但卻專注剔除傳統之糟粕而不重視傳統之連續性;文化保守主義有見于重建民族文化認同之重要,但卻蔽于古典傳統之斷裂而忽視現代傳統創生之事實。部分地由于文化權力與政治之間的特殊關聯以及論辯空間的限制,兩方面的觀點一時顯得勢同水火。但是在正視歷史事實人們看來,爭論的雙方有其共同的(有意無意的)盲點,那便是無視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近代社會的變遷以及由此帶來的建設性成果。20世紀80年代活躍一時的反傳統主義,后來被人譏笑為“荊軻刺孔子”,但依其理路,似乎當代中國只是古代的翻版,一切現實的缺陷都是傳統的禍害。毋庸諱言,這一派不久便成強弩之末,它未能洞穿的“魯縞”,倒是在一日日絢爛多彩起來了。傳統主義者更不待言,他們中溫和者技巧性地肯定啟蒙價值,總體上判定新文化運動造成傳統斷裂、權威喪失;極端者則斷言近現代中國文化沒有任何建設性意義。
陳旭麓先生講“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與上述兩者,雖然在具體問題上都有所汲取,但在對歷史的宏觀判斷上卻遠為持平中正。中國近代本質上屬于革命的時代,但它絕非文化“黑洞”,故對新文化或現代文明的成就采取一筆抹殺的態度未免過當;因為既有“推陳”又有“出新”,方構成百年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對近代史的宏觀研究一定需要有對古代史的“思”為前提。與常見的激進主義論斷不同,陳先生并不贊成籠統地說古代社會“停滯”,他說:“過去描述封建社會的長期性,經常使用‘停滯’、‘阻滯’、‘遲滯’三個詞。比較起來,后一個似乎更恰當些。封建社會的長期性,并不意味著中國社會停滯,社會總還是在變化的。這種變化,因為微小,僅以前后相接的兩個朝代而論可能不太明顯,但隔開幾個朝代加以比較,是能夠看得出來的。可以說:代代相承,變化微漸。”對于古代中國社會的如此判斷,即使在古風高飏的今日看來,也是大體成立的。
說古代中國社會“代代相承,變化微漸”,是與現代性的急劇變動相對而明的。與在漫長的盤旋中表現出的“遲滯”不同,近代中國驟然顯得變動頻仍,七八年一小變,三十年一大變,變化之快幾乎讓人目不暇接。其實,西方社會在近現代的變化與其中世紀相比也是驚人的,西方現代性的特征之一就是“普羅米修士—浮士德”精神。如果說西方近代變革是依靠基于科學技術的進步而來的社會自身機制更新來實現的話,那么,中國近代社會的“新陳代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異域文明——先以強制力乃至暴力的方式出現,而后又混雜了理性的力量——的沖擊,在中國獨特的社會機制下推動民族沖突和階級斗爭,表現為一個又一個變革的浪頭,迂回曲折地推陳出新。而且政治社會的新陳代謝既有其生活世界的緣由,又是民族反思的結果:“民族的反思,是在遭遇極大的困難中產生的。一百數十年來,中華民族的第一次反思是在鴉片戰爭后,漸知諸事不如人,只有學習西方;第二次反思開始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運動,何以學了西方仍然失敗;第三次反思是在‘文革’后,何以在大勝利中又大失誤。困難和失敗是新陳代謝的外因,反思是新陳代謝的內因。”
基于社會變遷中的“史”與“思”互相交織,在觀念層面,從鴉片戰爭到新文化運動,同樣有其“新陳代謝”:“八十年來,中國人從‘師夷長技以制夷’開始,進而‘中體西用’,進而自由平等博愛,進而民主和科學。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認識世界同時又認識自身,其中每一步都伴隨著古今中西新舊之爭。高揚民主和科學之旗,包含著八十年中西文化論爭所積累起來的認識成果,又體現了認識的一種飛躍。它由古今中西新舊之爭而來,又是對古今中西新舊之爭的歷史概括。中國人因此而找到了一個最重要最本質的是非標準,然后才可能有完全意義上的近代中國和近代中國人。”總之,陳先生肯定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現代價值重建的里程碑,盡管價值重建的途徑極其迂回曲折,中國人至少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尋找到了現代民族價值和文化認同的基礎。
由于明智的人都能理解的原因,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既是聚訟紛紜的領域,又一直是個高度敏感的領域。有些問題遙遙一望,搖曳生姿而有萬般魅力,行內人卻知道稍加深入便將到處荊棘叢生。1980年代,恰逢改革開放,近代史研究也受“解放思想”的恩澤不淺,陳著《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也只有在那個百年難逢的機遇,才能面世。我這里講“解放思想”,不但指當時國內近代史的強勢研究框架正從“三次革命高潮”模式向“現代化”模式轉變,歷史一元論的宏大敘事正在被多元論消解;而且學術界也打開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之門,尤其是對國外學術思想理論的廣泛引進、汲取,影響中國學者甚深。在近代史研究中,美國漢學界的影響也許是最大的。它自身也經歷了“沖擊—反應”“傳統與現代”、帝國主義話語,在向“中國中心論”轉變。質實言之,美國學者對中國的研究,從服從對策和現實需要漸漸轉至相對單純的學術活動,雖然因為其視角不同、擅于創造概念和理論作為分析框架,對中國同行常有啟發。但說到底,在其“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的每一階段,既有某種合理性,又難免隔岸觀花之嫌,況且一旦東渡成為所謂“模式”,容易現出東施效顰的后果。
上述情況在陳著中是找不到的。我這么說,并不等于陳先生不重視理論,而是說陳著雖然自如地汲取了諸多的分析性概念,卻沒有簡單套用某種西方“模式”,更沒有因襲以往習見的幾次“革命高潮”論,而是握緊新陳代謝這把鑰匙,努力具體地敘述近代中國的獨特變遷。換言之,陳先生對近代以來中國人的觀念世界的新陳代謝的判斷,建立在對歷史現實之復雜、細致的總體性把握之下:它既剖析了經濟結構和政治制度(包括農村社會、城鎮的行會組織和會黨)的復雜沿革,又深入到社會生活、人口壓力、風俗習尚的演化;既有政治思想、哲學觀念文藝審美,又有對社會心理、語言嬗變之描述。其中每一個問題的復雜性自然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但是陳先生以“新陳代謝”為入口,手起刀落,在不長的篇幅中立體地、多視角地、動態地展示了近代社會變革的壯闊圖景。
這里涉及觀念史研究中的“事實與觀念”關系。現在許多人喜歡引用梁漱溟先生的一個說法,他認為中國近代之所以發生危機,是因為知識分子顛倒了事實與觀念的關系:社會變化的秩序本來應該是事實優先的,即觀念應該隨事實的變化而變化。近代中國的文化危機是事實未變而知識分子的觀念變了,由此導致權威喪失或社會失序。梁漱溟先生對現代性的批評混雜著深刻的洞見與無望的鄉愁,不過說到20世紀初中國社會的基本“事實”尚無變化,證之于陳先生對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的巨大震蕩和變化的描述,那就顯出其武斷了。在此問題上,20世紀的文化保守主義比曾、左、李猶遜一籌,他們更樂于用想象和鄉愁來代替歷史的實相。《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在社會史的總體性把握中描述觀念的新陳代謝,揭示了事實與觀念之間的辯證法。其背后更有方法論的自覺:“史與論的關系,事(疑為“史”之誤——引者注)為體,論為用”。描述和解釋歷史的理論作為觀念形態,總是隨事實的變遷而變遷,同時又使得既往的事實成其為“歷史”。
前面說到,我受教于陳先生最多的,還是我更注重的近現代中國人價值觀念變遷問題。它不但可以作為前哲學史的材料,實際上可以是哲學史研究的新論域。馮契先生在論述其《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一書的方法論時曾經說過,與對古代哲學家比較重視體系分析不同:“在近代,由于現實經歷著劇烈變革,思想家一生變化較大,往往來不及形成嚴密的哲學體系。因此,我認為對近代哲學不要在體系化上作苛求,而應注重考察思想家們在一定歷史階段上的獨特貢獻,看他們在當時提出了什么新觀念來反對舊觀念,從而推進了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所以,在基于各種觀念的哲學爭論尚未得以充分展開以前,馮契先生撰寫的這部書,實質上是在廣義認識論視野中研究觀念的新陳代謝史。無論陳先生的《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還時馮先生的《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都涉及到對于觀念變遷之“史”的另一層“思”——評價,以及“新與舊”如何可能成為評價的標準。毋庸諱言,在“新”與“舊”之間,兩位先生的歷史觀都透著進步史觀的底色,復古主義自然為他們所棄。但是此處的進步史觀與凡新皆好、越新越好的單向度的機械論“進步主義”決非一事。即以陳先生而論,在他的著作中,新陳代謝固然是永恒的,但是它常常表現為“新”與“舊”的交織、更替、回復、互滲的歷史。“‘新舊如環’,環者圓圈也,但它不是循環的圓圈,乃是新舊不斷地起承轉合的圓圈。”觀念史研究中的“是與非”絕不是可以表象的“新與舊”可以一目了然的:“許多歷史的是非是隱藏在歷史的深處的,只有透過某些歷史細節的表象,才能把握歷史邁進的步伐和節奏”。故此,陳先生也批評倡導新文化的人群認知上簡單化的偏差,“如常常把中西文化視作是非的問題,甚至全盤否定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在重新審視舊觀念時也往往是批判的激情多于批判的理性,等等”,盡管他們代表了那個時候最進步的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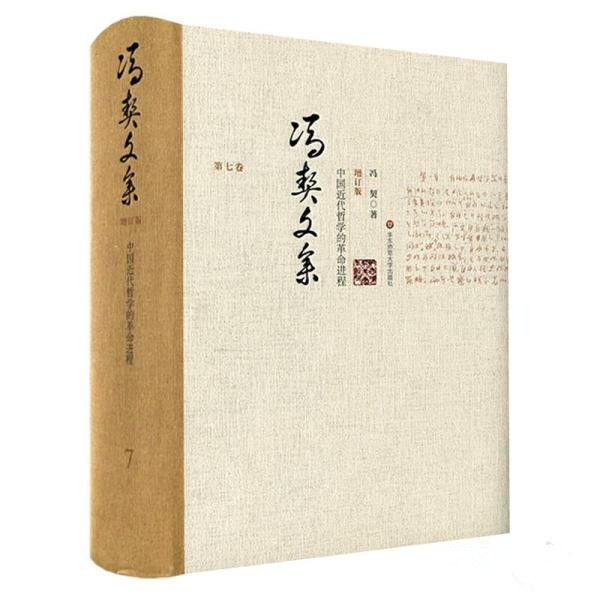
由此,我們可以觀察到陳先生在觀念變遷之“思”中如何處置“情與理”:基于肯定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陳先生對改革、革命、新文化的倡導者總體無疑是“同情”的,但是并非無條件的同情,陳先生并不贊成其激情多于理性的傾向。與此同時,作者又傳達了歷史的悲情。陳先生坦言:“確實,歷史研究會動感情,近代百年中的這一段(指19世紀后期農村的破產——引者注)至今還能使人聽到歷史中的呻吟和悲呼。但是,同情和憎惡畢竟不能代替理性分析。對于歷史學家來說,后者更加重要。”對于一個進步論者,其情之所寄,最復雜的莫過于評價那些保守顢頇,乃至頑冥不化的舊派人物;或者如義和團那樣的被迷信所驅、被愚民者所用的農民;更有在歐風美雨中飽含鄉愁的知識分子的言行。在第一種人那里,“守衛祖宗成法常常同民族主義,同愛國之情聯在一起。不合理的東西被合理的東西掩蓋著,于是而能成為清議,成為‘公論’。頑固的人們借助于神圣的東西而居優勢,迫使改革者回到老路上去。近代百年都是如此”。他們中那些最失敗者,如大學士徐桐等,他們積極策動義和團“以神擊鬼”等動機,多半是“由來已久的積憤。這種積憤攀附于民族感情,但又代表著極端的頑固”。在“義和團的社會相”一節,作者對他們的悲愴、怨憤、倔強寄予很大的同情,但又冷靜地指出:“士大夫階層是壟斷知識的勞心者。他們的非理性化,既反映了傳統社會在民族矛盾面前的倔強和不屈,又反映了傳統社會無可救治的沒落。”這是價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分裂的歷史現象之一。對于第二種人群,作者以為“深沉的愛國主義情感是同植根于自然經濟的保守意識連在一起的;抵御外侮的強烈愿望是同陳舊的天朝觀念和華夷之見連在一起的。這種矛盾,顯示了一場正義的反帝群眾運動中落后的封建主義內容。當舊式小生產者自發地充當民族斗爭主體的時候,他們不能不在代表民族的同時又代表傳統。矛盾不是主體選擇的結果,而是歷史規定性的體現。舊的生產力只能找到中世紀的社會理想,也只能找到中世紀的精神武器和物質武器”。在這類情感的后面,有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動,有物質利益的尖銳沖突。對于第三種人,從20世紀初的國粹派,到后來的“調和”論者,都不同程度地表示對歐風美雨對抵抗,“表現了傳統文化面對著激烈的中西矛盾沖突而力求保全自身優越性的意向。它帶著守舊性,然而它又攀結于民族感情的大樹上,容易使人動情”。在這類情感后面,我們看到的是近代知識分子在文化認同中的困境。
概言之,陳先生筆下的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絕非“滾滾的歷史車輪”那樣無情之物;多層面的情感世界構成了觀念變遷的重要面相。但是,作為歷史學家,陳先生筆下的“情感”又不得不經受理性的分析,來說明其有限的合理性以何種方式進入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的歷史之中。這可以說觀念變遷的另一重“史”與“思”的辯證法。
聽陳先生的課,讀陳先生之書,常讓人有超越知性的快樂,而獲得一種智慧的滿足。陳旭麓先生的著作,對歷史整體的朗朗觀照和對事實細節的出色分析結合得如此完美,常讓人拍案叫絕。一百五十年來的陳年舊事詩賦歌謠,在他那里盡聽調遣。同樣一個看似平常的事件,在他筆下,原先綰結一處的諸多面向徐徐展開。你會由衷地贊成章學誠的說法:“學問文章,聰明才辯,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識也。”平常的世變和事變,陳先生可以“思”出不平常的意義。所以他很自信地說過:“政治家看到的是地平線上的東西,哲學家看到的是地平線以外的東西,歷史學家記下了地平線上的東西,但要把視野從地平線引向地平線之外”。這和他既要注意觀念的變化,又要注意在觀念形態上有所反映的文化現象的方法,恰成一種互補的關系。陳先生那些讓我們后學受惠的“識”,其實就來自這種“思”與“史”辯證法吧。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