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古禮的基本精神
古人對“禮”的理解,大不同于今人。對古人來說,禮不僅是調(diào)節(jié)人倫關(guān)系的準則,而且是安排萬物秩序的“理”,在天地未分以前就已經(jīng)存在。后世儒家雖然主張圣人“緣情制禮”,而以“仁”為禮之本,然而,就禮的本身來說,卻是以“敬”為本,也即強調(diào)其中包含的尊卑等級觀念的重要性。禮中所包含的尊卑關(guān)系,體現(xiàn)了所謂“尊尊”之義,儒家認為出于天理,換言之,即便在自然界,這種道理也是普遍存在的。對此,唐代學(xué)者孔穎達就認為,猶如羊羔之跪乳、鴻雁之飛有行列,這表明尊卑等級觀念并非人倫教化的結(jié)果,而是天道之自然。可以說,禮并非小康時代的產(chǎn)物,而可以追溯到人類誕生之初。
《禮記·曲禮》中說道:“禮從宜,使從俗。”縱觀中國古代兩千多年,禮雖然有不變之道,但同時又強調(diào)與時俱進。尤其是孔子身處周秦巨變之際,對周禮過度強調(diào)的“尊尊”之義有所減損,而另外強調(diào)人類社會與生俱來的另一種精神,即緣于血緣的“親親”之情,從而“親親”與“尊尊”相并列,成了后世禮制的兩大基本原則。可以說,秦漢以后的中國社會,男女、夫婦之間,不獨以情相感,而且以禮相別;至于父子、兄弟之間,以及整個社會、政治等諸多方面,莫不兼取情與義,而不偏重其中一端。
然而,學(xué)界素來有一種相反意見,認為中國自秦漢實行郡縣制以后,君權(quán)不斷伸張,故尤其重視“尊尊”之義,至宋明以后更是如此,古代社會的各個方面,無論婚姻、家庭,還是政治、法律等,莫不受其影響。按照這種說法,則后世中國不屬于“質(zhì)家”(重視實質(zhì)),而是“文家”(重視儀節(jié)),從而導(dǎo)致親親之情愈加缺失,成為今人眼中的“病態(tài)的家庭”。然而,這種說法并不符合傳統(tǒng)經(jīng)學(xué)的基本立場。自經(jīng)學(xué)而言,在周人那里,“尊尊”之義發(fā)展到了頂點,而到了春秋中晚期,隨著宗法制度的崩潰,“尊尊”之義被削弱了。于是孔子順應(yīng)時勢,通過作《春秋》,稍損周文,而益以殷質(zhì)。可以說,自秦漢以后,“尊尊”之義實際上被淡化了,相反,家庭中的“親親”之情則被強化了,乃至君臣之義也被視為源于父子之情。
我們依據(jù)《公羊傳》及《禮記》《論語》中的相關(guān)記載,足見孔子吸納殷人的質(zhì)法,實在于其親親之情。不過,孔子亦未盡用殷法,而是采取“文質(zhì)彬彬”的中道立場,換言之,儒家于親親之情以外尚且重視尊尊之義,于是文質(zhì)并重,情義兼盡,如此方為孔子之道。
那么,儒家制禮,為什么兼取親親與尊尊呢?其緣由大致有這樣三個方面:
其一,孔子改制,損文而用質(zhì),正是有鑒于周人尚文的流弊,而兼取殷人的質(zhì)法,作為補弊的措施。
其二,文質(zhì)各有所施,而不得不有所取舍。對此,《禮記·喪服四制》說道:“門內(nèi)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這是因為恩、義各有所施,恩體現(xiàn)于家庭之內(nèi),義則體現(xiàn)于朝廷之上。這里所說的“掩”和“斷”,固然是由于家庭內(nèi)本自有義,而朝廷上亦自有恩,只是場合不同,故不得不有所取舍。古人通常認為,忠、孝之間不能兩全,然而正因如此,而要求盡量兼取兩者,而不能偏廢其一。
其三,至于一事之間,常有兩義并存,不可偏廢。對此,清代學(xué)者皮錫瑞論情義偏廢之弊,認為“圣人制禮,情義兼盡。專主情則親而不尊,必將流于褻慢;專主義則尊而不親,必至失于疏闊”。就是說,人們偏重于親親,則有褻慢的流弊;偏重于尊尊,則有疏闊的后果。
古人以親親、尊尊二義并重,親親之情出于自然,至于尊尊之義起自何處,歷來聚訟不一。近代學(xué)者多歸因于政治領(lǐng)域中的君臣關(guān)系,然考諸古人言論,實未必盡然。譬如,孟子討論尊尊之義,多以敬兄敬長為言,而未限于君臣關(guān)系,可見,先秦時固有尊尊之義,而與政治關(guān)系中的君臣之義沒有必然聯(lián)系。簡言之,早在君臣關(guān)系出現(xiàn)之前,人們已經(jīng)知道在家庭中敬兄敬長了。
此外,尚有一大原因,即近代學(xué)者多不能理解古禮中的繁文縟節(jié)。《禮記·檀弓》中記載了一段孔門弟子子游與有子關(guān)于禮、情關(guān)系的討論,在子游看來,人的情感很復(fù)雜,表達方式也極其曲折,古人正有鑒于此,故相應(yīng)制訂出種種繁瑣的禮文。可以說,古禮的深密、宏闊,實在不是今人所能想象的。
古人不獨表達情感的方式極盡曲折,而且認為,情感本身即是如此,而且多有委曲、隱微之處,這也是周禮尚文的重要原因。譬如,古禮尤其重視避嫌,正出于對人情之曲折細膩的體察,尤其在男女關(guān)系上,更是如此。凡人之思慕少艾,屬于常情,然而,禮依然規(guī)定有不當思慕的情況,譬如,使君有妻,或羅敷有夫,皆不當相慕。至于亂倫更可謂闔家的災(zāi)難,故古人對此更是加倍小心。古禮中相關(guān)的規(guī)定非常多,譬如,《禮記》中提到“嫂叔之無服”“諸母不漱裳”,無論嫂叔或諸母,都屬于同居之親,較大功以下的親屬,情感更為親厚,古禮所以對此嚴加分別,就是嫌其近而有亂倫的危險;至于出嫁的姑姊妹,雖屬骨肉之親,然而,古禮依然規(guī)定“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大概是因為此時已通男女之事,則彼此接觸時不可能沒有他念,其心已曲,故須避嫌。
可見,孔子制禮,以仁為本,而務(wù)與人情相協(xié)調(diào)。至于后世禮制多有變遷,而其所以變者,也常出于人情。因此,禮愈近于上古,疑禮者少,愈下于今世,疑禮者多,這都是出于古今人情的變化所致。
古今人情相異,古人制禮,亦未必完全曲從人情,而是取情義兼盡的立場。譬如,清代學(xué)者皮錫瑞論父子關(guān)系,認為人子“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可見人子愛父母之深,此為情之自然;至于人子成年行冠禮,其中卻有母子相拜之禮,則體現(xiàn)了父子、母子之間,不獨有情,也當有義。古人彼此行禮,相敬則拜,故父子間的尊卑,乃義之常;至于人子成人以后,也有可敬之道,故母亦拜子,此為義之變。
因此,關(guān)于傳統(tǒng)禮制的基本精神,我們應(yīng)該考慮到如下幾點:
首先,古人重人情,尤其是孔子損周文而益殷質(zhì),即是強調(diào)人情的重要性。然而,古人所講的人情,首先不是夫婦之情,而是父子(包括母子)、兄弟之情,也就是孝悌。基于這樣一種重情重質(zhì)的取向,體現(xiàn)在喪服制度的歷史演變中,便是子為母服喪的不斷重視,以及母系親屬在服制上的上升,至于妻及妻親的喪服,卻基本上沒有什么變化。
其次,古人即便講夫婦之情,也不能還原為男女之情,尤其不能還原為未成夫婦前的男歡女愛之情。今人則尤其尚質(zhì),不尚尊尊而尚自由婚配。
再次,古人重親親之情,又兼取尊尊之義,追求文質(zhì)彬彬、情義兼盡。古人視夫婦為至親,依然主張其中有禮以別之;至于君臣之間,雖有尊卑上下之嚴,卻也講究有恩義以相結(jié)。因此,某人過繼給他人為后,雖無父子之血親,古禮依然主張服斬衰三年,不獨尊之,且又親之也。
最后,古代討論尊尊之義,絕不限于君臣之間,至于門內(nèi)的各種親屬,既有父尊、母尊,又有夫尊,乃至兄尊,而各有其淵源,未必都出于君臣之義。凡人對于其所尊敬,乃至視為上天,因此,婦以夫為天,子以父為天,臣以君為天。并且,婦人不二尊,在家天父,出嫁則天夫;至于男子,雖兼有天父、天君之義,然忠孝則常常不能兩全。
本書于古人“禮”的理解,或有不當,敬祈方家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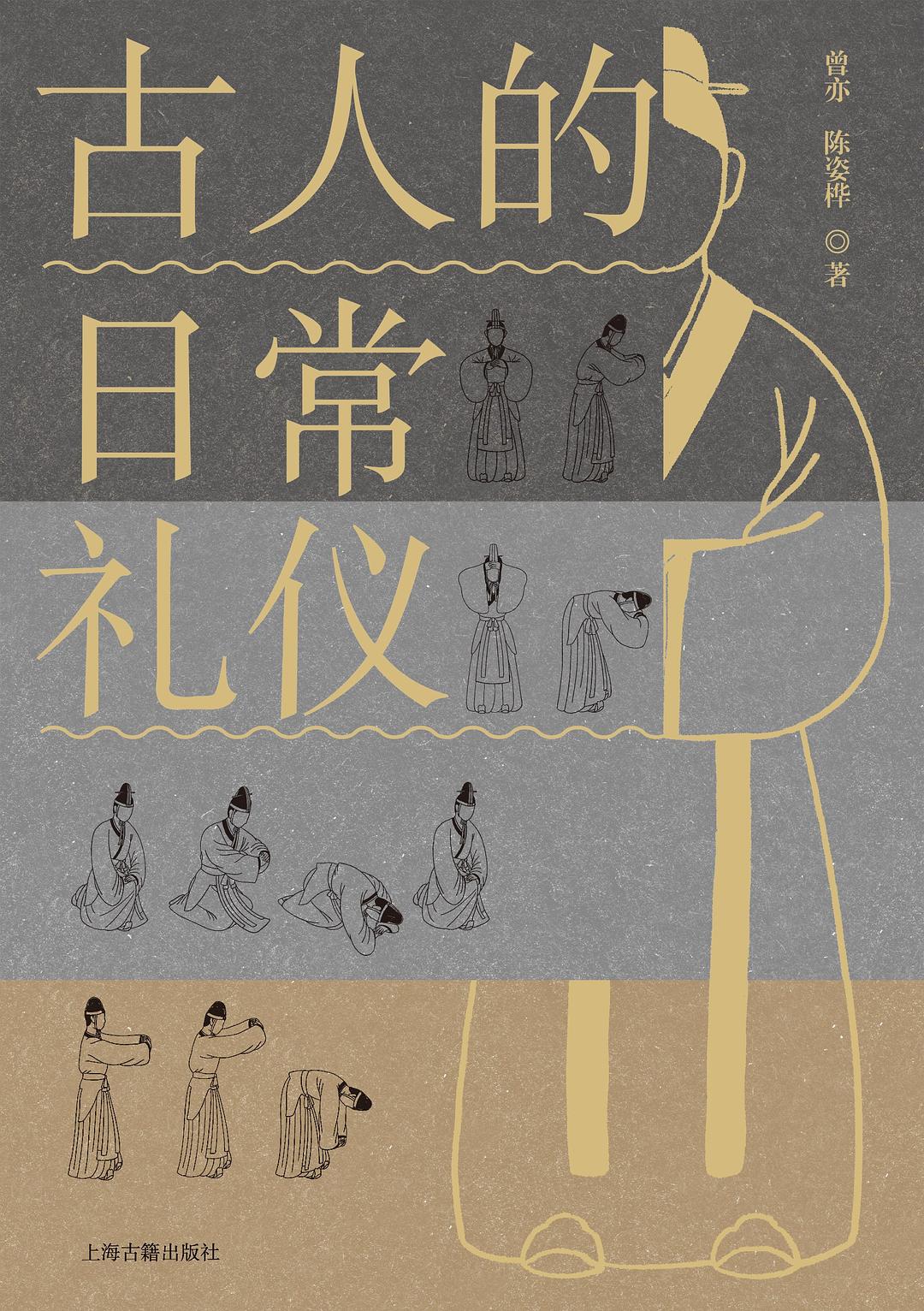
本文為《古人的日常禮儀》(曾亦 陳姿樺 著)一書序言,澎湃新聞經(jīng)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權(quán)摘發(fā)。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