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40年40人|吳心伯:中美磨合后將迎更平等雙邊關系新形態
北京時間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時,中美雙方同時發布《中美建交公報》,宣布兩國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關系。40年彈指一揮間。澎湃新聞聯合上海市美國問題研究所、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跨越大洋兩岸,對話40位重量級人物。他們有當年建交的推動者、親歷者和見證者,更有40年風雨關系的參與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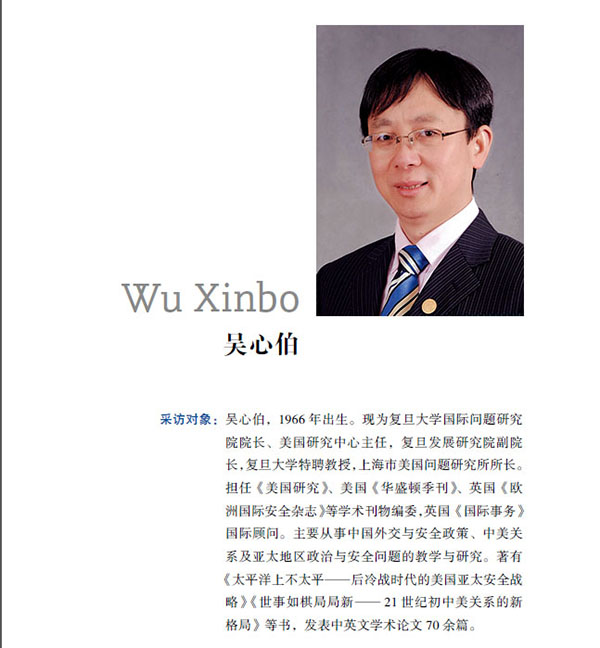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這些年來吳心伯奔走在中美兩地,積極組織學術交流,致力于加深兩國間的相互理解,被媒體譽為“民間外交家”。在近距離觀察美國的同時,吳心伯也在不斷思考,在他看來,中美關系正在經歷一個重要的轉折過渡期,雖然摩擦與分歧不可避免,但兩國在雙邊、地區、全球層面仍然有很大的合作空間。他相信,在經過博弈、探索、磨合之后,中美將迎來一個更加平等的關系,不斷擴大合作,同時開展有節制的競爭,并努力管控分歧。
與美國總統的近距離接觸
澎湃新聞:1998年美國總統克林頓訪滬并與上海市民座談,您是八位代表中唯一一位研究國際問題的專家,在和您的對話中,克林頓第一次在公開場合重申了美國對臺灣的“三不”政策,您能描繪一下當時的場景嗎?
吳心伯:克林頓此次訪華先去了西安、北京,到上海這一站時已經比較輕松、比較適應了。他在上海圖書館與市民代表座談,是一次開放性活動,這種形式在我印象中還是第一次,總體氣氛比較輕松和積極。
我是現場唯一從事國際問題和中美關系研究的學者代表。座談開始后,克林頓先和教育、宗教、文藝等領域的代表作了交流,最后一個才問到我。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細節:在克林頓對我提問之前,當時的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伯格給他遞了一張小紙條,他看了條子后,對我瞟了一眼。我猜想可能是伯格提醒他接下來向我提問。接著,克林頓就問了我對中美關系的看法。我談了我的觀點后,他表示同意我的分析,然后就講到臺灣問題,講到“三不”政策,即不支持“臺灣獨立”、不支持“一中一臺”或“兩個中國”、不支持臺灣加入任何必須由主權國家才能參加的國際組織。
事后我了解到,克林頓是在從北京到上海的飛機上決定要公開重申“三不”政策,這是他整個訪華外交的一部分。實際上,他此前曾在私下里向中國做過類似的承諾,但中方希望他在訪華期間在一個公開場合作相關表述。最后,克林頓按照中方要求,在上海公開發表了“三不”承諾,這是后冷戰時代美國在對臺政策方面作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承諾。從中方的角度來看,意味著他訪華之行取得了重大成功。

澎湃新聞:據媒體報道,當時克林頓訪華的隨團人數達1200多人,是歷來最多的。克林頓為何如此重視那次訪華之行?
吳心伯:克林頓對中國的訪問是在他的第二任期內進行的,他在第一任期內沒有訪華。那也是冷戰結束后,美國總統第一次訪問中國。所以對中美雙方來講,對這次訪問都有很高的期待。克林頓本人經過第一任期的一些摸索,逐漸認識到了中美關系的重要性,所以他在第二任期內把處理中美關系作為一個優先事項,而且希望把一個良好的中美關系作為他個人的政治遺產。
但美國國內當時對發展中美關系的政治支持還不是很強有力,美國朝野有很多人對中國的看法還停留在1989年政治風波后那個時期,沒有看到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所以克林頓一方面想利用這次訪華,更多地了解中國,也讓美國公眾更多地了解中國,感受到中國的發展和變化;另一方面,也確實希望通過訪問來推動中美關系的發展。1998年克林頓訪華的歷史意義在于,奠定后冷戰時代中美關系發展的框架。
澎湃新聞:2009年奧巴馬訪華時,您也參加了他在上海與青年學生會談的活動。您認為奧巴馬的訪華之行又有怎樣的歷史意義?
吳心伯:奧巴馬訪華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他在出任總統的第一年內就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本身就凸顯了美國對中美關系重要性的認識,而他訪華的主要目的,更大程度上是探索如何跟一個崛起的中國打交道,即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中美關系應該怎么定位、應該設立一個怎樣的關系框架。
澎湃新聞:國家元首高訪對中美關系發展有何作用?
吳心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國家元首訪問有不同的歷史任務。一般來說,元首互訪對雙邊關系有幾個作用。其一是定基調,比如,到底是合作接觸還是對抗競爭?兩國領導人需要對雙邊關系的定位達成基本共識。其二是定框架,比如,我們是一個雙邊的關系,還是雙邊、地區、國際多邊結合的關系。其三是定日程,比如,兩國未來將在哪些領域著重開展合作。另外,通過高層訪問可以推動在重大問題上取得突破性進展,例如2013年習主席和奧巴馬總統的莊園會晤,當時雙方就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發展新型兩軍關系達成了重要共識;又如2015年習主席訪美,在準備訪問的過程中跟美方重點探討了如何處理網絡安全問題。
澎湃新聞:特朗普時代,中美元首外交的風格與過去相比有沒有發生變化?
吳心伯:特朗普比較另類,商人出身的他在擔任總統之前,沒有任何公職的經歷。我覺得特朗普對中美關系缺乏宏觀的戰略眼光,不像前面幾任領導人那樣能夠從戰略高度、以寬廣的視野來看待中美關系的重要性。比如,奧巴馬既看到了中美雙邊關系的重要性,也看到了多邊領域的重要性。相比之下,特朗普似乎比較狹隘。另外,特朗普個人風格中的交易性、功利性、投機性很強。他往往關心的是怎樣在解決具體問題上取得快速突破,讓中國做出讓步。在這個過程中,他的立場會不斷變化,這就影響了領導人的誠信度。領導人對雙邊關系的一些重要表態和承諾,應該是有約束力的。但特朗普不太講原則,今天是這樣,明天又可能改過來。所以,與之前的幾位美國總統相比,現在和特朗普打交道,我們確實遇到了很多新問題和新挑戰。
澎湃新聞:您認為中方應該如何應對這些挑戰?
吳心伯:我們必須適應特朗普的風格。第一,由于他有投機性和功利性,對于他的某些話不能太當真,關鍵要看他的行動。第二,不管他怎么變,唯一不變的是謀求美國的國家利益。在這個過程中,中美會進行利益的博弈,有交換、有妥協,也有競爭,甚至一定程度上也會有對抗。比如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到了不得不打的時候,就必須打,否則一味讓步的話,那就掉進了一個無底洞。
培養交流對話的習慣和文化
澎湃新聞:“中美青年外交官對話”從2007 年開始至今已連續舉辦10屆。您作為主要的推動者,和中美兩國的青年外交官有很多交流,能否分享一下您的觀察體會?
吳心伯:組織“中美青年外交官對話”主要是為兩國年輕的外交官搭建一個交流的平臺,他們平時公務接觸的機會較多,但主要談的都是官方層面的事情,沒有機會進行更多非正式的交流,談官方議程之外的事情。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關系會越來越密切,以后會需要更多的對話和交流,所以應該讓年輕的外交官盡早熟悉對方,培養起互相交流對話的習慣和文化,是有意義的一件事。
這么多年下來,我對中方參與對話的青年外交官的印象是:越來越自信,英文也越來越好,而且對業務也越來越熟悉。一開始對話,美方講得多,中方比較沉默,主要是對美方問題的回應。但是到了第三第四次以后情況就開始不一樣了,往往中方會主導討論。不管是表達方式,還是對問題的把握,中方都準備得很好,也確實表現出越來越多的自信。
美方的外交官呢,其中有些人對中國還是有些偏見的,也不乏立場較為強硬的人,對官方立場抓得比較緊。但也有一些人比較靈活,比較務實,愿意參與非正式的交流,從個人的角度討論一些問題。

澎湃新聞:您認為這樣的交流能起到什么作用?
吳心伯: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在開會之外,大家有機會一起吃飯喝茶或參觀游覽,這時你會發現兩國的青年外交官都很談得來,大家很自然就聚到了一起,談生活、談愛好等很多職業之外的話題。這個時候你感覺不出誰是中國人,誰是美國人。所以,應該講兩國的年輕一代的確有許多共同點。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覺得我們的對話就是要推動更多的接觸和交流,為兩國官方關系的發展建立一個比較好的個人關系基礎。
澎湃新聞:您經常參與、組織中美智庫和學者交流互訪活動,長期發揮著民間外交家的作用,您認為二軌對話、民間交流在中美關系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
吳心伯:主要有幾個方面的作用。首先是加深相互了解。官方交流渠道雖然有很多,但通常情況下參與者注重表述官方立場,交談時不會談得很深,也不會放得很開。相比之下,在二軌交流中,沒有了官方身份,大家對很多問題可以深入探討,這就使雙方加深了互相了解,特別是對對方的一些政策背后的考慮,加深了理解。
其次,通過二軌交流、加深了解以后,我們可以更好地提供資政服務,設計出能被采納的政策建議,為務實推進政策的落實而集思廣益。
第三是幫助我們建立人脈關系。很多專家學者可能跟決策圈有著密切的聯系,或者有些人將來有機會進入政府任職,主管相關政策。保持這樣的人脈關系,對推動兩國關系的發展很有幫助。
澎湃新聞:您和包括基辛格、卡特在內的許多政要、學者都有過比較深入的交流。在老一輩政治家、戰略家或學者中,有哪位是您覺得比較佩服的呢?
吳心伯:卡特總統、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等,各自都有令我很佩服的地方。中美建交是在卡特總統任期內實現的,他在90歲那一年(2014年)曾訪問復旦大學,當時他就說,從1979年到現在,東亞地區保持了一個大體和平的狀態,中美關系的穩定功不可沒。他能夠從世界和平穩定的角度來看待中美關系,讓我印象深刻。

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這兩位是戰略家。首先,我覺得他們在對中美關系和國際格局的分析方面有非常高遠的戰略眼光,他們對很多問題的判斷不會拘泥于某個具體問題,不會過多局限于戰術層面,而是能夠運用宏觀的眼光分析戰略層面的問題。第二,他們確實有很強的洞察力,一下子就能抓住問題的本質。這一方面需要經驗——兩位都曾在政府任職,另一方面需要很強的學術積累和深厚的學術功底。

澎湃新聞:老一輩的戰略家,他們對中美關系的分析和把握對當下的中美關系是否還有啟發意義?
吳心伯:我們首先應該學習他們站在戰略層面看待中美關系,不能把視線過分局限在當下發生的事情上。第二,我們也要學著從發展的角度審視中美關系。不同的歷史階段,中美都在適應新環境,兩國關系一直在變化。正如老前輩們所強調的,我們要學會審時度勢,在不同的階段相互調整、相互適應,這也非常重要。
40年回顧:經驗與教訓
澎湃新聞:回顧過去40年中美關系發展的歷程,您認為大致可以分為幾個階段?總體呈現怎樣的趨勢和特點?
吳心伯:中美關系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9年到1989年,這十年是中美關系不斷發展深化的一個過程,從最開始在戰略層面上的接觸合作,擴大到社會經濟文化等多方面互動交流。
第二個階段是1989年到2008年,這是后冷戰時代,中美重新定位雙邊關系框架。這一時期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中國逐漸融入國際體系,并且在這個體系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同時,中美關系也獲得了新基礎,兩國在經貿領域以及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上的合作,構成了后冷戰時代中美關系發展的兩大支柱。
第三個階段是2008年以后到現在。這個階段的背景特點就是中國崛起。中國開始推行大國外交,中美關系也面臨著重新定位、重建框架的問題。在這個階段我們看到,特別是在奧巴馬執政時期,中美合作的領域在不斷擴大和深化;但同時,競爭也在加劇。奧巴馬時期,中美競爭主要體現在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領域,到了特朗普時期,兩國在經貿領域的競爭激化了,甚至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貿易摩擦。
從整體來看,中美關系在這40年間一直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兩國各自發展程度和發展狀況的變化,以及各自外交戰略的變化而不斷演進。在這個過程中,兩國也在不斷地探索如何擴大合作的空間。從冷戰時期的戰略合作到后冷戰時代的經濟、國際事務、全球治理等等,合作的領域在不斷地擴大,在不斷地尋找新的增長點。對于出現的新問題,兩國也在探索如何更好地管控分歧。
澎湃新聞:中美關系在不斷演進的過程中有哪些成功之處?
吳心伯:我覺得成功的地方首先在于中美關系能夠與時俱進。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中美關系也要做出相應調整。應該講中美關系這么多年來還是表現出了對國際大環境很強的適應能力。其次,發展中美關系還是要抓住共同利益這一點。在不同的階段,兩國的利益優先性會有變化,但是發展雙邊關系,一定要尋找共同利益,有了共同利益就能夠合作,能夠合作就能推動雙邊關系的發展。這兩點,我覺得是中美關系發展40年來最成功的地方。
澎湃新聞:最需要吸取的教訓又有哪些?
吳心伯:我覺得主要也有兩點。第一是在涉及對方核心利益的問題上一定要慎重。比如,臺灣問題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問題,如果美國處理不好,就會導致中美關系出現重大的波動。第二,我覺得在處理雙邊關系的時候,還是要適當地和各自的國內政治區分開。國內政治的邏輯和國際政治的邏輯不一樣。如果在考慮雙邊關系的時候,完全從國內政治的角度出發,那關系就處理不好,這方面我們也有不少教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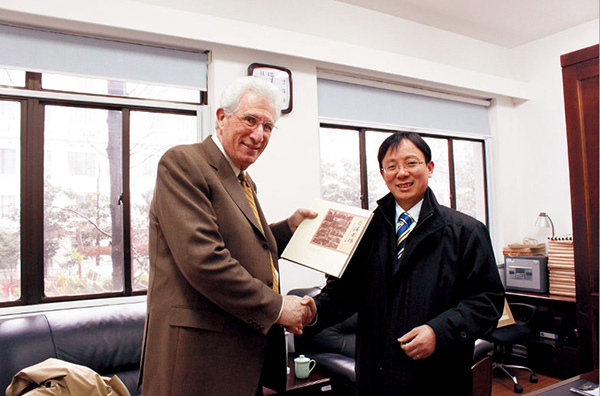
中美關系新常態:競爭與合作并存
澎湃新聞:您曾經與“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提出者艾利森教授進行學術對話,您表示中美關系不同于以往的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的關系。能否具體分析一下有哪些不同之處?
吳心伯:我認為現在的中美關系與歷史上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國家之間的關系有很大的區別。首先,現在是核武器時代,大國之間很難爆發嚴重的、全面的軍事沖突。這從二戰以后的歷史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二,就中美關系而言,我們在經濟等領域實現了高度相互依存,這也決定了兩國不會走向全面沖突,因為利害關系太大了。第三,中國的崛起與過去很多大國的崛起不一樣。中國并沒有在東亞、西太平洋謀求建立一個排他性的勢力范圍,我們從沒想過要把美國趕出去,把這一地區變成中國的勢力范圍。過去的許多崛起的大國,比如日本,曾經就想在這一地區建立自己的勢力范圍;美國崛起后也曾想把整個美洲變成自己的勢力范圍——這就是“門羅主義”的真實意圖。但中國從來沒有這樣的想法,中國沒有意圖取代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
澎湃新聞:美國有一批“鷹派”政客和學者對中國持較為警惕的態度,他們對中國崛起有哪些誤解?
吳心伯:我認為誤解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擔心中國想把美國趕出東亞和西太平洋,把這個地區變成中國主導的勢力范圍。二是擔心中國想要取代美國的首要地位,比如到本世紀中葉全面趕超美國。三是擔心中國想要顛覆現有國際秩序。
我認為針對這些擔憂和誤解,我們需要明確闡述、反復強調我們的意圖和立場。我們需要讓美國人知道:中國謀求一個合作開放的東亞地區,并不是要把美國趕走;中國的發展是基于自身的邏輯,并不是以取代某個國家為目標的;中國是現有國際秩序的獲益者,維持現有國際秩序的基本框架符合中國的利益。
當然,與此同時,我們也希望這個國際秩序能夠與時俱進,進行必要的改革和完善。在這個過程中,中美兩國有很大的合作空間。總體而言,要完全打消美國對中國的疑慮,幾乎不可能,因為中國的實力在上升,但我們可以通過實施很多具體政策來減輕美國的疑慮,這是可行的。
澎湃新聞:您曾撰文指出,21世紀中美關系的范式很可能是以分享權力和領導地位為特征,您認為中美如何才能在競爭中共處?兩國有哪些合作空間?
吳心伯:我認為兩國可以相互共處的地方還有很多。比如,從雙邊關系來看,兩國經貿合作的空間仍然很大,盡管眼下有較大的貿易摩擦,但實際上兩國誰都離不開誰,中美經濟不可能真正實現脫鉤。從地區層面來看,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穩定離不開中美緊密合作。從全球層面來看,兩國也可以在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等許多全球治理問題上進行合作。盡管特朗普政府決定退出《巴黎協定》,但從長遠來講,美國還是會回歸這個多邊合作框架,解決氣候變化問題離不開中美的合作。
澎湃新聞:您曾提到維持對華力量優勢是未來20至30年美國對華政策的核心關切。在這種情況下,中美未來最有可能爆發沖突的領域有哪些?我們可以采取哪些防范和管控措施?
吳心伯:一個就是當下我們看到的經濟領域的競爭。特朗普政府特別重視經濟實力在國家實力中的地位,認為經濟就是國家安全的一部分。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和競爭力持續上升,中美在經貿領域不可避免會有較為長期性的摩擦。在這方面我們需要強調經濟關系的本質是互利共贏,而不是零和的。把握好這點,經貿問題就能夠得到較好的處理。
第二個是在西太平洋地區,隨著中國軍事力量的上升和外交影響力的擴大,美國可能感到它在這個地區的傳統主導地位和優勢面臨來自中國的威脅,所以兩個大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地緣政治競爭不可避免。事實上,奧巴馬時期推出的“亞太再平衡”主要就是著眼于西太平洋,跟中國進行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的競爭。這方面,我覺得美國需要調整和適應中國力量的上升和影響力的擴大;對中國而言,我們在不斷拓展利益空間的同時,也要保持一定的戰略克制和審慎,防止推進得太快太猛,引起包括美國在內的各方的反彈。
第三個可能就是太空、網絡空間等新興領域。中美兩國可能在如何制定游戲規則、更好地反映各自的利益等問題上產生分歧摩擦,甚至是對抗。關鍵在于制定一個相對合理、各方都能接受的規則和秩序,而不是僅僅反映某一方的關切。
在不同的問題領域,中美管控分歧、處理競爭的方式是不一樣的,但有一點在任何領域都適用,那就是:中美關系是21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對任何問題的處理都要考慮到穩定和發展中美關系的大局。
澎湃新聞:展望未來,您對中美關系的發展有怎樣的期許?
吳心伯:中美關系正處于一個重要的轉折期、過渡期,在這個過程中,兩國不可避免會出現分歧、摩擦、甚至對抗,雙方通過博弈,探索新的共處之道。我相信,經過摸索調整階段以后,未來的中美關系應該是一個更加平等的關系,會兼顧合作與競爭。比較理想的應該是以合作為主,不斷擴大合作,開展有節制的競爭,有效管控分歧。今后的中美關系對整個地區和國際格局的影響、對全球治理的作用只會越來越大。在經過一段磨合期后,中美關系將迎來一個新形態,能夠反映兩國力量對比變化的現實,也體現出兩國在處理雙邊關系中摸索出的新經驗和做法。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