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潘綏銘:后30年做了自己愿意且喜歡的事,是莫大的幸福
2014年退休后,潘綏銘如此形容過去的經歷,“后30年做了一件自己愿意做而且喜歡做的事,這已經是莫大的幸福了。”
今年74歲的潘綏銘,是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創始所長,他在中國創立并推廣了性社會學,創立了該學科的基本概念:全性(sexuality)、性革命、初級生活圈等。
而今,他是一個喜歡攝影的退休老人,因一年內跑了112家北京的公園拍鳥,獲得一個觀鳥大賽的“最勤奮獎”。
再次出現在公眾視野中,是因為去年出版的學術自傳《風痕》。2018年,潘綏銘經歷了一場直腸癌手術,這讓他開始回顧自己的一生;網絡上一些不利于性社會學的言論更促使他盡快寫出這本學術自傳——他的性社會學成果集大成。
書的內容按時間線展開,從1981年記錄到2019年。按潘綏銘的概括,研究“性”本是“無心插柳”。他的青春期始于“文化大革命”前,讀男校,“對什么叫無性文化頗有些感受”。
1981年,他以同等學力考上東北師大歷史系研究生,學世界古代史時,他對德國人弗林格爾寫的《原始人的性生活》印象很深,后來查到一套30卷的《東方圣書》,“第一次接觸到‘房中術’的皮毛。”直到1985年,表兄留學牛津,寄回國外博物館里保存的一些中文原件的復印件,“我才開始真正了解房中術和中國古代性文化。”
畢業后,潘綏銘于1984年起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第二年,學校號召青年教師開設新課,潘綏銘報了一門“外國性觀念發展史”,于是他在9月開講了,一講就是28年。
提及自己學術起步之時的背景,潘綏銘在《風痕》中引用了費孝通在《性心理學》后記中的文字:中國正在通過開放和改革向現代化社會轉變,歷來成為禁區的“兩性之學”將能得到坦率和熱情的接受。
“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在性生活中最讓人頭疼”,潘綏銘在書中提到,“人們很少意識到,我們實際上是帶著一大堆社會框框投入性生活的。什么臟,什么丑,什么不像話,其實都是在我們成熟的過程中,由社會悄悄地強加給我們的。”
1993年,潘綏銘在《社會學研究》上發表了《當前中國的性存在》一文,正式提出中國已經發生了一場性革命的論斷,認為這是1985年城市經濟改革開始后出現的。他將性革命定義為:性文化在短期內發生巨大的變化,強調其迅猛。
實際上,退休后,潘綏銘與性社會學的關系仍然交織著。他組織過“老年知性”懇談會,與學生們一起寫《我在現場——性社會學田野調查筆記》。在他看來,他努力構建了性社會學,性社會學也深刻影響了他。
如今,回想這些年的學術生涯,潘綏銘說,“我所選擇的是那種首先滿足自己好奇心的自娛自樂,然后在客觀上也許具有創造知識的意義,但是更大的可能性是成為過眼煙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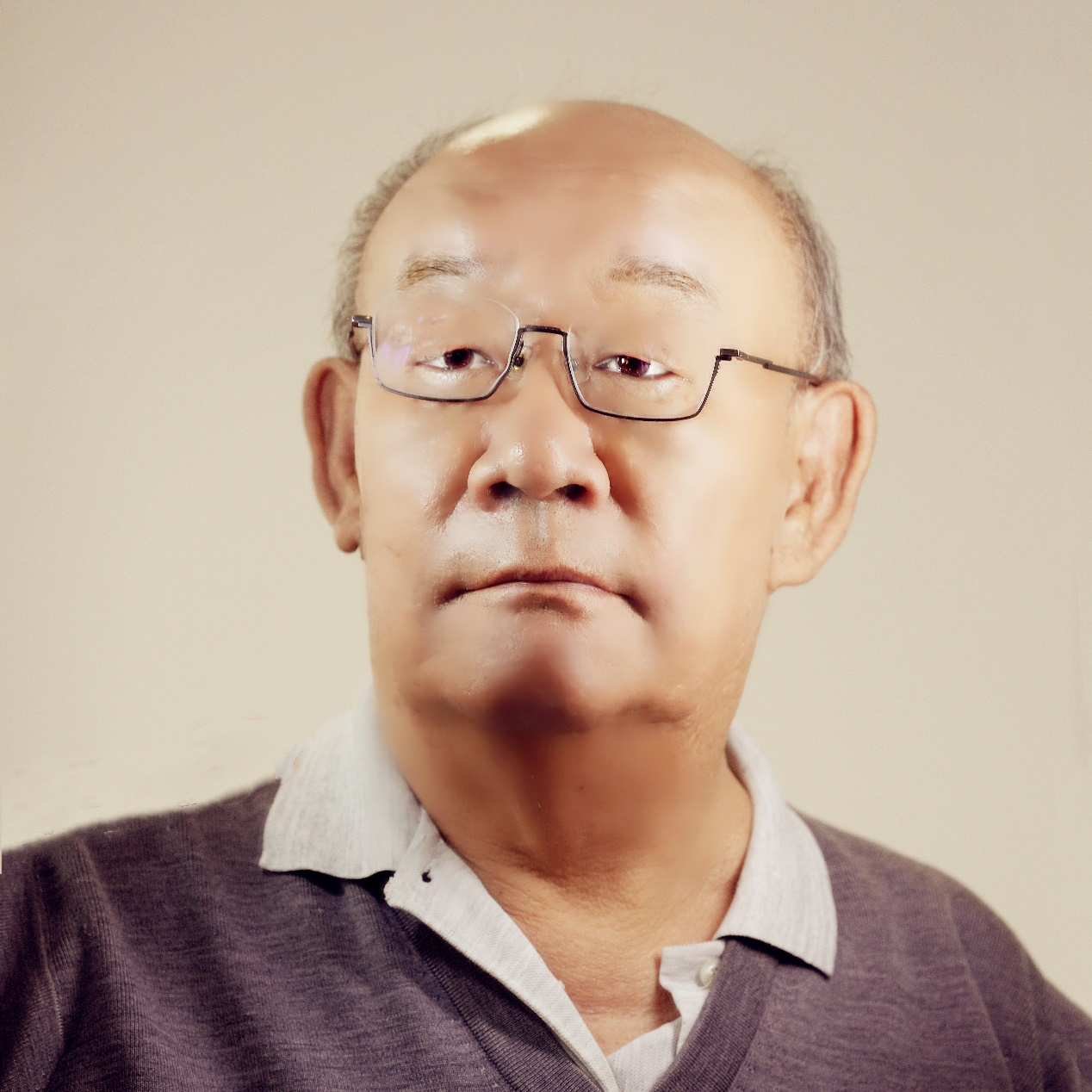
2023年的潘綏銘。(潘綏銘注:美顏無數次)本文圖片為 受訪者供圖
【以下根據澎湃新聞記者與潘綏銘的對話整理:】
“我這一生做的事情,究竟哪些最值得留給后人”
澎湃新聞:您是什么時候開始寫作《風痕》這本學術自傳的,有什么契機嗎?
潘綏銘:在臨退休之前和剛剛退休之時,我其實沒有想過要寫自傳。那時候,我曾經把我主要的論文都匯集起來,做了一個文集,叫做《潘綏銘論性》,有大約50萬字,也沒想要出版,就在網上發布了,反正我也不需要版權,誰想用就用。
到了2018年,我做了一個直腸癌的手術,術后又感染了,在醫院里邊整整住了一個月,差點就走了。這一個月里,我也難免回顧人生。忽然覺得自己的《論性》這個文集都是相互獨立的論文,東一榔頭西一棒子,實在是支離破碎。如果不是一直聽我的課,就很難抓住重點,更難以把握全局。結果,我本想留下一塊餅,卻成了一鍋粥。
當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從我退休之后,至少在網上,至少是一些言論,已經越來越不利于性社會學了。如果單看一些極端言論的話,那么我這一輩子所干的事情,不但可能被一掃而光,還很可能成為十惡不赦。
兩者交加,促使我寫出了《風痕》這本書。它不是個人生活的回憶錄,而是我的性社會學成果的集大成。
澎湃新聞:回顧您的學術經歷,您覺得您最主要的研究是什么?
潘綏銘:在我回顧與反思的過程中,最經常困惑的,也恰恰就是你所提問的:我這一生做的事情,究竟哪些是最重要的,最值得留給后人的呢?
我覺得,從純學術的角度來說,我所組織和完成的4次全國總人口的“性調查”,是最重要的成果。不僅因為這在全世界是唯一的,到現在也沒有被超越;也因為它調查的內容是最廣泛和最深刻的,不但詢問了各種各樣的性關系,也詢問了豐富多彩的性生活方式;更是因為它采用了隨機抽樣的方法,調查員親赴全國一百多個地方,在其居住地找到被訪者,既不是滿大街亂拉人,更不是在網上連對方是不是一條狗都不知道。它的科學性就在于:每一個中國人被調查到的概率是相等的,誤差不超過4%。因此,調查結果能夠代表全中國人民的情況。
但是最廣為人知的,恐怕就是我和我的團隊所做的“紅燈區”與“小姐”的調查。可是到我寫《風痕》的時候,這個主題比我以前調查和出版8本專著之時反而更為敏感,我也就少說為佳,大多數具體內容已經看不到了,但是網上還在,一搜就有。
從社會學這個學科本身來看,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我的兩大獨創成果。第一個是主體建構論。它不是英文翻譯過來的,此前也未見于中文世界。第二個是《論方法》這本書,是論述社會學的調查方法。

《風痕》。
“很少有人去了解,小姐自己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澎湃新聞:研究“性”具體研究的是什么?您在書中提到“全性”的概念,以此對應英語中的sexuality,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潘綏銘:全性是指與“性”有關的一切人類現象。它不僅包括性交、性愛撫等所有直接的性活動,也包括擁抱、接吻、性幻想、談論性方面的事物等所有不那么直接的、具有性的含義的活動,還包括人們對于性的情感、態度、價值觀和性方面的喜好等心理方面的表現。尤其是,它不僅指男女之間的性活動,也包括LGBTQ(一般譯為“性少數”)的性活動 ;不僅指人們普遍認為是“正常”的現象,也包括所有被認為是“反常”的現象。
全性這個概念拓寬了“性”的范圍 :從“唯行為論”(例如性技巧崇拜)走向全部現象(例如身心與情境的三合一);從“本能論”(性欲天然論)走向情境論(社會存在論);從“陰陽二元”(唯男女)走向所有存在形式(包括一切性少數);在研究方法上,從“客觀判定”(求實論)走向研究主體的感受/認同/解釋(主體建構的視角)。
澎湃新聞:您提到的兩大獨創成果之一是主體建構論(注:“建構”的視角反對把性視為天然的靜態存在,強調對于它的形成和發展過程進行分析和解構,尤其重視社會、文化、政治、歷史等因素所發揮的作用;“主體”的視角反對研究的客觀化,主張從主體出發)這是在什么情況下提出的,在怎樣的研究經歷下讓您產生了這個想法?
潘綏銘:這是我與黃盈盈在2007年提出的,又經過反反復復的思索與錘煉,終于在2015年確立為“主體建構論”的初級理論。
我的一切研究經歷,幾乎都在積累和孕育這個理論。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
第一個是純學術的方面。
在大多數性調查中。男人有過的性伴侶的人數,往往多于女人。一些生物學家就據此嘲笑社會學家“不科學”,因為在大的人群中,男女的性伴侶的人數應該是差不多相等的。其實,其中的道理非常簡單:女性,只會把那些與自己多少有些感情的人,才算作自己的性伴侶。也就是說:女人的主體建構與男人不同。
在我自己1990年代調查大學生的性行為時,曾經調查過接吻與性愛撫。我以為,有過接吻的大學生應該更多;性愛撫應該更少。可是調查結果卻是相反的。一開始我以為是我的統計有問題,瞎費了很多工夫去檢查。后來才恍然大悟:這是我的主觀認定違背了被調查者的主體建構。但我沒有詢問具體的原因。
第二個方面是我所做的多次現場訪談。
1987年我訪談過一位女性,問道:“你有過婚前性行為嗎?”她說沒有。我說:“那你還是處女啊。”她卻說:“也不是,因為我愛過。”如果按照“科學”,這就是她在辯解;事實上是她把自己的那一次“性”構建為愛,該女性認為自己做的是愛。
2004年,我訪談到一位三輪車司機。他堅持認為,一位在職的小姐是他的情人,他倆之間是愛情而不是買賣。雖然他們兩個也是給錢和收錢,但是他認為這根本就不矛盾,妻子如果沒工作,那不也是丈夫給她錢?尤其是“她給我做飯吃”。
對于小姐,任何研究者或者旁觀者都會有自己的定義。可是卻很少有人去了解一下,那些被別人稱為小姐的女性,她們自己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我在調查中曾經遇到這樣的情況。我問一位發廊妹,她為什么不去收入更高的桑拿按摩場所工作。她驚訝地反問我:“啊?你讓我去做小姐啊?”可是一位小姐卻跟我說:“我以前是做按摩的,生意不好,才來發廊做小姐的。”這時候我已經有了主體建構論的意識,明白這是研究的寶藏與機會。這些女性都不認為自己現在或者過去是小姐。
我當時是馬上抓住小姐的這句話聊起來,才得以逐漸搞清楚,她們判斷誰是小姐,其實根本就不考慮實際上做什么,而是考慮是不是“被人看見”,也就是公開的程度和羞恥的程度。那位發廊妹認為“背著人沒好事”,所以那些深藏不露的桑拿按摩里的才是小姐。可是那位曾經的按摩女則認為“拋頭露面沒好人”,發廊妹們是明晃晃地在大街上開門迎客,她們才是小姐。
由此我們可以聯想到,有些人總是在糾結“中國到底有多少小姐”,這真的是索然無趣。即使是為了預防艾滋病而不得不統計這個數字,也仍然僅僅是聊以自慰,因為如果一個女性根本就不認為自己是小姐,那么任何預防性傳播的宣傳,對她們來說都只是耳旁風,最多也就是隔靴搔癢。
從更加深入的層次來看,那種不考慮小姐的主體建構而僅僅由研究者來加以定義的思維方式,其實有著深遠的文化傳統,即男人和女人對于“買性”和“賣性”的理解,背道而馳。
在傳統文化中,女人容易把自己通過性來獲取錢財或者其他好處看作天經地義,因為靠丈夫養活的所有妻子從來就是如此。可是男人由于自己是付錢的人,所以很容易認定,凡是收錢的女人就都是賣淫。在這種傳統文化的熏陶下,現在統計小姐人數的那些人,或者本身就是男人,或者是受到男性文化長期規訓的女人,因此他們只能按照男人對于賣淫的理解來定義哪些女人是小姐。雖然被標定的那些女人自己不這樣認為,但是由于缺乏發言權,她們的主體建構默默無聞,即使發聲也會被認為是強詞奪理和狡辯。
被調查對象改變
澎湃新聞:《風痕》副標題是“我與性社會學互構”,如何理解這句話?
潘綏銘:“互構”不是常用詞,很多人都追問過我。其實這就是說,我努力構建了性社會學,它也深刻影響了我。一方面我這個人的理論素養很差,好奇心卻很強,所以適合去做“入住式的相處調查”,才有那么多生動的事例;另一方面,我也做全國總人口的隨機抽樣調查和數據統計,這就培養了我的思維習慣,也促成我不懼獨處和枯燥的生活習慣。
其實讀者從《風痕》里邊也可以看出來。我一開始就是想純粹地“做學問”。即使后來去調查“小姐”,一開始也是只想著做研究。到最后卻做了很多社會工作。這就是被調查對象給改變了。
澎湃新聞:您說在研究者調查過程中都獲得了刻骨銘心的體驗和感悟,您可以舉個自己的例子嗎?“不僅僅是描述被調查者的情況,更是呈現我們自己的人格升華”,對您來說,升華有一些具體的表現嗎?
潘綏銘:我必須說,性社會學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社會調查。雖然會有感動,會有升華,但畢竟是一個規范的工作,我(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去農村調查“酸曲”(注:情歌),當地向導就教育我說:你不是作家。人家來了,看見什么都能寫。你呢,調查不到就寫不出來。也就是說,文藝可以想象和發揮,只要有可能這樣就可以寫出來。但是社會調查卻必須是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自己的感受與體驗應該另外寫出,不能與對于事實的描述混雜起來。
舉個例子,我剛開始考察紅燈區的時候,首初遇到的道德問題是自己的操守。但是后來考察多了才明白,最大的問題不是這個,而是一個根本道義上的問題:我究竟應該如何面對那些小姐和媽咪呢?
我不能否認,像我這樣大談性產業和紅燈區的情況,有可能使得小姐們的日子更不好過。她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所需要和所期盼的,其實只是像小草那樣不顯山不露水地生存下去。在不能“非罪化”的時候,過度的關注就可能像過度的鎮壓一樣,危害到她們的現實生活的質量。
不過,我仍然承擔著道義上的責任。因此我只能遵守中國人的兩條古訓:在精神上堅持“將心比心”;在行動上實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為我跟小姐是生而平等的。我匿掉任何具體的地名和人名,努力學術化。
當然,這是遠遠不夠的。這仍然會使我居高臨下。還是嚴月蓮(注:香港紫藤“一個為小姐人群服務的NGO組織”的發起人)女士說得更加透徹:怎樣才能真正平等地對待小姐呢?只有四個字,就是“自甘墮落”,就是讓自己的一切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光環”徹底休克。否則,請離小姐遠一點,讓她們過自己的生活吧。
性、愛、婚:分離還是一體?
澎湃新聞:您1993年提出中國性革命的論斷,認為這是1985年城市經濟改革開始后出現的,中國的性革命是怎么發生的?
潘綏銘:中國的性革命包括生殖革命(獨生子女政策的嚴厲推行)、性表現的革命(情色的日益公開化)、性關系的革命(各種非主流現象)、性行為的革命(性生活豐富化)與社會性別的革命(性別多元化)。
獨生子女政策所帶來的性與生殖的相對分離,是中國性革命獨特與根本的來源。
性革命的兩大助力,一來自1980年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在這部法律里,第一次明確地規定了離婚的唯一標準,是雙方感情破裂,附帶的條件是經調解無效。這使中國一躍成為世界上奉行自由離婚的領先國家之一。
二來自80年代之后,青少年人口劇增。青少年占高比例,必然會展現出他們自己的文化,從而影響整個社會文化的走向,性革命才可能發生。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提到,“性研究的是人類生活中發生最頻繁、體驗最深刻、意義最廣泛的重大活動之一。人類智慧數千年來對于自身的幾乎一切認識和爭論,都可以在‘性’這里得到集中的體現:精神與肉體、個人與社會、美與丑、生命與死亡,等等,不一而足。不妨說,‘性’是研究人類的最佳切入點之一。”您能具體展開說說這個想法嗎?
潘綏銘:就拿精神與肉體之間的關系來說吧,性是身心一體而且不可分割,還是相反?這集中體現為性與愛能不能分離。為什么有些人說:你不跟我做,就是不愛我。另一些人卻說:你只想做,那不是愛。為什么有人說:(在婚外)我只是要性,又不愛對方,你嫉妒啥!可是也有人把對方的無性的交往說成是“精神出軌”。還有人說:男人通過愛來實現性,女人通過性來實現愛,真是這樣嗎?現在很多人把性生活叫做“做愛”,這是英文直譯過來的,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做的(性)是愛”,二是“愛是要做(性)的”。當然沒人會來問您認同哪個,但是這恰恰是一個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一念不同,絕難相處。
《風痕》里寫過:“性、愛、婚的分離”是目前中國大眾在這方面一切煩惱的直接來源,而背后的原因則是對于“完美的三合一”的崇拜。現在的輿論一面倒地批判前者,可是,如果后者可望而不可即呢?如果選擇前者有理由呢?如果三者都不要呢?你看看,不討論清楚行嗎?
在人類生活中,精神與肉體的關系可以從方方面面來研究,但是人生一世,還有比性生活更普遍、更深刻的體驗嗎?“以性說事”不是最通俗、最吸引人的路徑嗎?無論您的結論是什么,只要思考過,您就會活得更明白、更自主。
再說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只舉一例足矣。出軌,究竟是這個人的獨自行為,還是那個性別沒一個好東西?如果認同前者,可以分手;如果相信后者,很難再愛。你看,又是司空見慣卻又禍福相關的問題,比講什么社會階層理論都通俗易懂,一語道破。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提到“把愛情作為性的最后信仰,這究竟是一種宣誓,還是一種悲鳴”,可以展開說說嗎?
潘綏銘:首先需要搞清楚,咱們要討論什么樣的愛情?《風痕》寫了:自從“五四”以來,西方傳進來的浪漫情愛,與中國傳統上的夫妻恩愛,一直就在相互沖突著,成為當今中國人“性、愛、婚”苦惱的重要原因之一。婚前都追求情愛,婚后都珍惜恩愛;可是外面新的浪漫情愛一沖,夫妻恩愛往往土崩瓦解或者同床異夢。
那么無論情愛還是恩愛,究竟是怎么產生的呢?或者說,它有什么樣的社會功能,才使得人類如此需要它呢?那就是:用愛情來控制性的沖動,控制性的無方向和不確定的突進,以免威脅到婚姻與家庭這個社會的整個結構。只不過在原始時期,是靠性崇拜與性禁忌來控制。在農業時代靠的是性制度與性倫理。到了工業化和現代社會,個人越來越獨立自主,只能用個體化的私人之間的愛情來控制個體的性。道理很簡單,若是一往情深,節外生枝就不那么容易了,也就用不著道德、法律和社會來管了。這些年來,白頭偕老的說法之所以卷土重來,就是某些社會力量合謀,力圖把夫妻恩愛作為整肅性道德的最后思想武器。有的歷史學家干脆認為,愛情根本就是弱方的發明,然后再去培訓強方的。因為,若愛,那么損害對方的可能性就少。
但是到了21世紀的西方,兩個人之間的平等相處,越來越靠人人平等的人權理念來維持,越來越不需要浪漫情愛來調劑。結果,至少在很大一部分人群里,愛情就被視為是性的產物而不是性的前提,甚至只是一種美好的童話,而不是現實生活中的待人之道。例如在某些西來的最時髦的理論中,壓根就沒有愛情這個詞。這恐怕就是愛情的危機了。
澎湃新聞:在反思西來理論那章,您在“本土化:坐井觀天還是酸葡萄心理”這個標題下寫:在這個天大的標題之下,我其實什么也說不出來,只能留給后人評說。可以說說當時寫這節時的考量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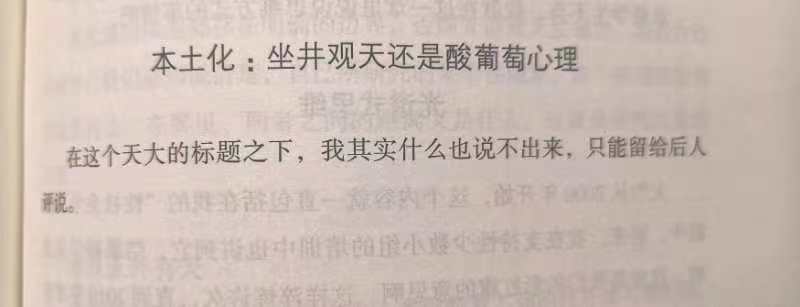
《風痕》中的章節“本土化:坐井觀天還是酸葡萄心理”。
潘綏銘:接著上面來說,浪漫情愛為什么偏偏在西方近代才產生,其他民族和宗教都沒有?它為什么偏偏在“五四”時期傳入中國,為什么與夫妻恩愛如此勢不兩立?為什么西方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性革命”包括沖擊“情愛崇拜”、推崇“性與愛同一”,而在中國80年代以來,性革命卻恰恰從浪漫情愛開始?
就是這些思考,逼得我提出“本土化”的疑問。從純學術來說,如果認同西化,那么“彎道超車”就絕無可能,只好把“克己復禮”說成是“另辟蹊徑”。反之,如果認同本土,那就無法解釋“五四”以來的全部歷史。我之所以只問不答,是因為我隱隱覺得,這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一個既得利益的選擇。
退休后,獲得觀鳥大賽“最勤奮獎”
澎湃新聞:您這兩年再重返校園做講座時,傾向于和學生分享些什么?您有自己特別強調的學術觀念嗎?
潘綏銘:退休后的最初幾年,我還在一個外校里每學期講一節大課《西方性愛史略》,后來被該校的上級叫停,連課程講義也一并被刪除。這是我自從1985年以來從未遭遇過的,也是促成我趕寫《風痕》的原因之一。所以這一問題已經是昨日黃花,無從回答。
澎湃新聞:在您退休后,學術對您來說意味著什么?您目前的生活狀態、生活重心如何?
潘綏銘:在學術方面,我退休以后,除了寫了《風痕》,完全是金盆洗手、心如死灰、不聞不問、無話可說。
在日常生活方面,我一輩子枯燥乏味,目前幾乎所有的老年活動,我都從來不會也不想學,只剩下溜彎兒。
澎湃新聞:您是什么時候開始喜歡攝影的,在其中獲得的樂趣源于哪?有沒有喜歡的幾張攝影作品?
潘綏銘:在攝影圈里有句行話:前一萬張照片都是廢品。就是說,這是個勤學苦練的事。可是我恰恰不是這樣的。
我是2014年退休的,一開始只是觀鳥,買了一臺66×100的大望遠鏡。當時想的是,我自己看看就好,拍下來給誰看呢?后來在一次觀鳥的時候,旁邊一位“打鳥”(拍鳥)的老者對我說:還是拍鳥好啊,一方面攝影的技術門檻低,一學就會;另一方面又必須聚精會神、緊追不舍、不斷琢磨才能拍好,比光看鳥有意思多了。我深以為然,就買了相機開始拍鳥了。當然,有了相機就必然啥都拍,所以陸陸續續積攢下一些各種題材的照片。
我開始學的時候,也上網看了一大堆各式各樣的教材,但是越看越覺得這不符合我的初心。我一不想成名成家,二不是投稿發表,三也不是記錄歷史,僅僅是自娛自樂,是給自己找個理由多多走路,鍛煉身體;是多多觀察這個世界,培養豁達。如果我像學習一個新專業那樣努力鉆研,不但肯定是勞而無功,而且也就違背了修身養性的初心。雖然有一個攝影雜志發表了我的一些照片,但是實在是蹣跚學步、令人見笑,不提也罷。唯一值得我自豪的是,有一年我一年之內跑了北京范圍內的112個公園去拍鳥,因此獲得了一個觀鳥大賽專門為我設置的“最勤奮獎”。

潘綏銘攝影習作。

潘綏銘攝影習作。

潘綏銘攝影習作。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