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許知遠寫游記,有點東西
談話節目《十三邀》的片頭中,許知遠自稱“我是一個笨拙的發問者”。他眉頭緊鎖,目光游移,鏡頭隨著他的目光掃向城市的角落、街頭巷尾的行人。最后,目光與鏡頭都會聚焦到一個那一期的嘉賓身上——一位名人,或是某個行業、某種文化的標志性人物。節目之外,看待更隨處可見的城市文化和普通人時,他也同樣帶著知識分子式的觀察視角。
在許知遠的游記《意外的旅程》里,他在漢族文化昔日的中心、“堯的誕生地”閑逛,發出這樣的疑問:“那位堯真的是我的祖先嗎?今天的中國人真的是古代中國人的延續嗎?”在陜北,他發現靠投資煤礦發際的老板“似乎從未從那個鄉村窮孩子的內心走出來”。
在拍照打卡的游客視角以外,偶爾來一次這樣的“知識分子式”游歷,好像也是一段不錯的旅程。
下文摘選自《意外的旅程》,經出版社授權推送。小標題為編者所擬,篇幅所限內容有所刪減。
01
今天的中國人真的是古代中國人的延續嗎?
灰塵混合著我們身體的汗水,牢牢地粘在我身上,使毛孔難以呼吸。到處都在修路,到處都在鳴笛,到處都是閃爍的霓虹燈。
在漫長的時間里,臨汾被稱作平陽,是“南通秦蜀,北達幽并,東臨雷霍,西控河汾”的兵家必爭之地,也曾是北方工商業的重鎮。它更著名的淵源是,這里是堯的誕生地,堯被公認為華夏文明的開創者,他和另外兩位繼任者——舜和禹——構成了中國最初的統治史,代表了華夏的黃金時代。
我來到了山西南部,中原地帶的中心。我這一代對“中原之地”耳熟能詳,卻很少意識到它到底意味著什么。如果我對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化有所了解的話,它遵從的地理區域也先是東南沿海,或是江浙一帶。
中國近代歷史的變革中心來自沿海,而文化中心則一直在江南。歷史變化總是滄海桑田,如今我們談論的是上海、香港,誰還記得臨汾、商丘與開封?但當華夏文明在后者興起時,前者仍是雜草叢生的亂石堆。
整個上午,我都徘徊在臨汾市區的堯廟廣場。它激起的不是我對遠古文明的幽思,而是一種生理上的不適。飽經戰亂、天災與人為縱火的堯廟當然早已消失,最多剩下斷壁殘垣、青苔野草。遺跡是個不斷被修復的東西,中國的歷史傾向于存留在典籍,而不是建筑之中。我們不喜歡帕特農神廟那種石頭,而傾向于木頭,它們美觀、精巧,卻經不起歷史煙塵。
眼前的堯廟是1998——2002年一連串擴建的產物,它不再是一座孤單的被祭奠的建筑,而變成了一片建筑群,被稱作堯廟廣場。它就像另一種意義上的世界公園,街口的雜貨鋪,建造者費力地想把所有的東西都塞進一個空間里,所有東西都有著顯而易見的廉價感。
我先是在觀禮臺的廣場上游蕩,它坐南朝北,正對著堯宮。它像是一個小型的“天安門”,殿內擺放著那種廉價的工藝品,它是“中國堯都民間藝術博物館”。兩個年輕姑娘無精打采地坐在那里。

電影《站臺》
在同樣微縮的廣場上,擺放著幾輛電瓶車,它們被分別塑造成濟公、火箭的模樣,花上五塊錢,你可以在廣場上“馳騁”一下。然后,我又在堯廟里消耗了一個小時,在那些仿明清的建筑中穿梭。那些懶散的管理員會突然走到你面前:“給先祖敬香吧,三十塊的六十塊的都有。”
如果你拒絕,她就立刻懨懨地走回屋角的同伴那里,繼續她們的聊天。這堯廟是她們的,不屬于游客。
貫穿廣場的堯都大道有四十米寬,兩邊的景區除去“天安門”,還有縮小的天壇,有堯舜禹三座宮門,有用水泥制成的立體中國地圖(可惜福建、臺灣等一些省份,表層水泥已經脫落)。廣場建筑處處夸耀它的規模,二十一米高的漢白玉華表,長達百米的、花崗巖鑄就的千家姓紀念壁——它不但是全國最大的,而且采用了長城造型,還有號稱“天下第一門”的華門——三門鼎立象征了堯舜禹,主門十八米高,是“世界上最高最大之門”……
我在四十米寬的大道上走來走去,這并非特別節日,大道上空空蕩蕩的。我慶幸自己沒有再花五十塊門票去進那個華門,它四周飄蕩的紅旗早已褪色,絲綢的邊角早已殘破。擺設在堯都大道兩旁的攤位和這些宏大的建筑一樣,真實地反映了中國人此刻的精神世界。
一個又一個攤位提供了每一座城市都雷同的消遣方式:汽槍打氣球的游戲,小吃攤,盜版書籍與音像——在上面我看到的幾乎全部是玄幻、武俠小說,還有一本余秋雨的散文,還有《我偷了二嫂》這樣誘惑人心的光盤名稱……
那個微縮的天壇被命名為“幻覺動感の屋”,中文的“的”字被換成了“の”字,而且在說明里特意提及,游戲來源于“日本株式會社”,我甚至看到了一艘仿制的軍艦矗立在華門前……
一位叫劉群良的僧人還給我算了命,但是他的個人簡介上卻印著八卦圖。“不管僧道,都要看八卦的。”他對將信將疑的我說,并確信我“天賦敏感,也可以預測未來”,只要付給他三萬元,學習一年兩載即可。我婉拒了這份“前途無量的工作”,付給他十元錢離去。
如此大規模的混雜仍讓我有點吃不消。那位堯真的是我的祖先嗎?今天的中國人真的是古代中國人的延續嗎?一切變得容易理解,浩大的工程與歷史情懷無關,它只是經濟增長的催化劑,而且它與“大躍進式”的壞品味相連——拜多年的標語化、好大喜功的美學觀念所賜。

電影《天注定》
“旅游業是一個大蛋糕,關鍵是誰能將這塊人人看好的蛋糕做大做強……”一份旅游手冊這樣寫道,“我們的賣點就是四千五百年中華文明的源頭”。
而手冊的編著者則寫道:“我們的先祖創造了太多太多的華夏之冠。如何將先祖們創造的‘無形資產’變為‘有形資產’,使華夏千古文明濃縮在堯都,濃縮在一處看得見、摸得著的藝術經典中……”離開堯廟廣場后,我看到了第一個大幅廣告牌是“紐約,紐約”和“臺北新娘”的婚紗攝影。
02
對風景之愛,曾是中國文化中多么重要的一部分
一陣雨過后,天變得明澈,那輛現代汽車就在山路上行駛,穿過了一個又一個隧道,窗外是清澈的山澗,河灘上布滿了大小鵝卵石塊,鐵青色的巖石取代了黃土丘陵。
我心情舒暢,因為終于要離開北方中國了,我正在穿越的秦嶺是北方與南方的地理分界線。南方氣味在經過眉縣的渭河橋時就已變得鮮明,我看了一家又一家的路邊簡陋飯店都以川菜告人,成都和重慶的力量陡然增強。西安則被遺忘了,仿佛我不再身處陜西,而進入了四川。
我開始覺得潮濕,而旅行節奏舒緩下來,我變得松懈。在漢中的清晨醒來,隔壁的潮皇酒樓門口那個穿著紫色旗袍的年輕女人正擦著玻璃,滿身的慵懶從旗袍側面的開叉溢出來,馬路對面的性保健品商店的門口張貼著這一路上我看到的最有創意的名字——“阿根挺”。
在路邊攤上,我聽著兩個少婦的閑聊,其中一位過分濃妝,像是馮夢龍筆下的小家碧玉。“漢中女人好看,”一位西安朋友提醒我,“她們有點像陜北的女人,個子高,皮膚白”。
“為什么西安人都說漢中人小氣?”我一邊吃著辣椒炒蛋,一邊插話。我的胃口終于蘇醒了,從黑龍江到陜北,我受夠了那種粗糙、沒味道的飲食,四川的辛辣終于到來了。
這句話引發了兩個女人的熱烈情緒,她們開始將之前西安人對她們使用的形容詞,都送了回去:西安人哪有漢中人豪爽,他們做事才小家子氣呢!”
這座城市給我的印象是,女人比男人更有力量,不知道那“阿根挺”的銷量如何。

電影《山河故人》
載我前往勉縣武侯祠的是個女司機,今年正好三十歲。她前額的劉海修剪得過分整齊,像一把精巧的刷子,而后面則長長地飄下來,她的臉蒼白平坦,五官小巧,這使她看上去就像放大的櫻桃小丸子。
“漢中男人太懶了!”我們談話是這樣開始的。一路上,我的攀談水準很低,不外乎“本地人有什么特點啊”,“你對生活滿意嗎”,“一個月掙多少錢”。我很少碰到對自己收入滿意的人,總是“太少,不夠花的”。
說話干脆的櫻桃小丸子也是,她毫不掩飾對自己丈夫的嫌棄。“如果不是孩子,我早就離婚了。”
這輛捷達車正駛在栽了兩排整齊的高大冷杉樹的公路上,而路兩旁則是淺綠色的稻田,綠得讓人心曠神怡。“如果你春天來,更美,都是黃色的油菜花。”她說。
她對于結婚十年的丈夫的主要抱怨是,他賴在一家半死不活的國有企業里,每個月掙一千塊,自己都不夠花的,卻不愿意到外面去闖一闖。
她是個想得開的女人,喜歡在那家鸚鵡酒吧里喝啤酒,和朋友抽煙聊天,她喜歡北京、西安這樣的大城市的生活,后者的麻辣小龍蝦給她的印象深刻:“漢中就沒這種做法。”
她給老板開過車,嫌錢少又不自由,然后就自己買了這輛出租車,準備開上三年掙些錢,再把車一賣,或許能在西安開始個小生意。她是個稱職的投資者,不再開車載朋友了,即使會被他們譏笑“小氣”,她還雇用了一個男員工,每月付他九百元,專門開夜班——閑置的出租車該是多么浪費。
在家里的姊妹三人中,她是最不安分的,總是向往著更刺激的生活,要穿名牌衣服,要下館子吃飯,要去全世界旅游,她也是最自立的一個——除了自己誰也沒法依賴。
夾在秦嶺與巴山之間的漢中,的確仍舊散發著一股置身事外的氣息。對于飽受大城市的節奏折磨的人來說,它悠閑散漫得如此迷人,而對于這位“櫻桃小丸子”來說,它缺乏生氣與活力。
速度正在致力打破這種狀況,八百里秦川如今只需要六個小時的車程,西漢高速公路通車之后,則將縮短成三個半小時,“云橫秦嶺家何在”的感慨變成了徹頭徹尾的遠古景象。這也給“櫻桃小丸子”帶來了新的機會,她希望到時不再在市內掙那五塊一趟的活兒,被別人包車往返一趟西安、漢中,或許就可以收入一千塊。
來到武侯祠時,我是當天最后一位游人,空空的院落里,皮鞋踏在石磚地面上的聲音響亮而清晰,我喜歡上了那棵玉蘭樹,甚至試著欣賞結構對稱的古建筑,還有四四方方的院子,散布著青苔的石板路引人遐想,我突然覺得自己被剝奪了那美妙的傳承,恨不得能就地坐下,撫琴一曲。
對風景之愛,曾是中國文化中多么重要的一部分,站在小小的閣樓之上,穿過一片玉米田,我看到了流淌的漢江水,一陣清風恰好迎面吹來,內心莫名其妙地充盈起來。

電影《山河故人》
對諸葛亮的記憶主宰了這座小縣城。我試著在西方傳統中找到他的對應人物。他是那么機智,那么有操守,那么執著,卻最終還是失敗,充滿了悲劇式的無力感。
奧德修斯有他的機智吧,卻比他更幸運,或者說更明智。中國人推崇諸葛亮,多少因為他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劇性。從劉備到阿斗,他不懷疑既有秩序,甘心成為搖搖欲墜的秩序的維持者。
我對歷史遙遠和模糊的記憶在漢中被一點點喚醒。諸葛亮,馬超,漢中王劉邦的拜將臺,蕭何月下追韓信的地點,還有漢江。中國人的身份是從漢代開始的吧,因為漢朝,我們成為了“漢人”。
03
“沒想到三口人全部下崗了”
抵達伊春時,是傍晚七點。步行街上人群稀落,商店幾乎全部打烊了,在大部分城市,這是最熱鬧的地點,最喧囂的時刻。
在等待本地的朋友時,我坐在一家蛋糕店門口發呆,它是整條街上最后一家小店,店門口的高音喇叭一直在循環播放同樣的短語:蛋糕麻花小甜餅……朗誦者的語速過快,甚至懶得斷句停頓。不知疲倦地重復,是中國商業社會最重要的推銷手段,從中央電視臺黃金時段的廣告,到賣鞋和雜食的街頭小店,都是如此。
天空逐漸變黑卻仍舊藍得透徹,盛夏的時節,空氣卻飄蕩著一股冬日的蕭瑟與感傷,步行街旁的樓房墻面斑駁,墻皮脫落已久。步行街上的大笨鐘開始報時了,報時音樂是《東方紅》。
我被帶回到了三十年前。生活在一個集體主義氣息濃郁的軍隊大院中,清晨六點有起床號,傍晚是下班號,食堂里供應黏稠的米湯與因用堿過多而變黃的饅頭,大院里的人們來自五湖四海,操著不同口音,被共同的紀律塑造。
它不是自由生長而是移植來的,不同的性格、家庭、夢想、口音與口味,被塞進了一個窄小的空間,為同一個目標服務。
伊春洋溢著這種氣氛。它位于黑龍江東北部,是小興安嶺的中心城市,它生產的木材和大慶的石油、鶴崗的石油、建三江的黑土地一樣,是火熱的新中國建設的象征。就像大慶產生了模范石油工人王進喜一樣,馬永順是伊春的象征,他是個不知疲倦的伐木工人,他們都有著“喝令三山五岳開道,我來了”的豪情。
孫鐵軍是那股豪情的產物。我看到他時,他正挑著一擔水從院子里出來。那連成一片的由木板、泥漿、磚頭搭建的建筑群分布在半山上,這算得上伊春的貧民窟。
他看起來四十歲左右,消瘦的臉上流露著一股淡淡的憂傷。早晨九點的伊春,空氣清新,可以蕩滌掉我肺中所有北京的廢氣。陽光則穿過輕輕的云層,暖洋洋地打在身上,皮膚干爽,甚至感覺得到毛孔的呼吸。
孫鐵軍出生于1954年。四歲時,他隨全家搬到伊春市。
他的父親曾是志愿軍的一員,戰爭結束了,作為退伍軍人,父親被分配到伊春市的百貨公司當業務員。這座人造城市居民分成兩類人:林業的、商業的。前者采伐樹木,后者則為他們服務。但他們的界限隨著時間迅速模糊。

影視劇《平原上的摩西》
1969年,鐵軍成為了一名林業工人,在山中,他熟悉了透光、打帶、清林的工序,每月掙三十三塊。接著他成為了一名卡車司機,開著解放牌汽車運送被砍伐得整整齊齊的圓木。
1977年,他結婚了,伊春則迎來了她最繁榮的年代,中國正開啟經濟建設的浪潮。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這里擁擠著來自全國的代表。各地政府、大大小小的公司都派人前來,都想獲得木材。
“到處都是外地人,什么人他們都要,我們這兒的所有人都有工作。”鐵軍的母親也突然插進談話。這個神情淡定的老太太正在窗外抽煙,香煙夾在她左手的食指與中指之間,姿態異常瀟灑,她為志愿軍丈夫生了四個兒子。此前,她一直向我抱怨生活的不公,作為一名抗美援朝老兵的家屬,每個月只能領到一百多元的補助。
對于這個家庭來說,最寒冷的時刻來自1993年。林場的繁榮已經逝去,長期沒有節制的砍伐,沒人控制的盜砍盜伐,令數百年的森林開始蕭瑟,需要封山育林;同時,國有企業的改革也開始了,積壓了兩代人的管理失調,要在一年中解決。
孫鐵軍對此有心理準備,這是全國性的潮流,而非僅僅他個人的挑戰,結果仍令他吃驚。“我做好了家里有人下崗的準備,”鐵軍回憶說,“卻沒想到三口人全部下崗了”。除去自己,他的妻子、女兒——分別在林場的財務科和保衛科工作——也下崗了。
二十五年的工齡最終以一萬八千塊錢作為了結,他的整個青春就值這么多。令鐵軍耿耿于懷的是賠償數字的籠統,他這樣將近三十年工齡的工人,和那些工齡只十年的工人,沒太多區別,似乎相隔二十年的人生其實毫無價值。
那真是段難熬的日子。“工人就像籠子里的雞,放出來之后它還會圍著籠子轉,”孫鐵軍說,“現在回想起來,我都覺得害怕”。
我們見面時已是2007年8月,十五年過去了,他仍未完全從當時的震蕩中走出來。他們在國營的氣氛中成長,他們的家庭、愛情、事業、娛樂,都在一套模式中,而且他那時已人到中年,生命開始由強壯滑向衰弱。
突然間,他要負責一家四口的生活,要交納養老金、醫療保險金。在即將開始的新生活中,沒有他熟悉的路線圖。
他病倒了,一年后才逐漸恢復。像很多代的中國人一樣,當面臨社會的震蕩時,親戚、朋友、同學所締結的網絡開始發揮作用。他先是在山東游蕩了九個月,依靠最初朋友的介紹,從一份工作換到另一份工作。新生活不安定,卻讓他呼吸到從未有過的自由空氣。
“我一口氣跑了很多省份,那些地方我從來都沒去過,哪里有活干,我就去哪里。”他的足跡從山東到了湖北,從四川到了新疆,從廣東到了福建,他重操開車的老職業,在葛洲壩開鏟土機,在攀枝花卸貨,在新疆參與修路。
伊春的經濟沒有起色,甚至更糟了。被包圍在兩座小山之間的市中心的商業區不再有從前的繁華。五十年前,退役的士兵、年輕人涌到這里創造一座新城,三十年前,人們涌向這里,尋找木材與機會,現在本地的年輕一代外出打工,下崗家庭經常全家遷走。

影視劇《平原上的摩西》
鐵軍的女兒在一家小商店賣書包,每月六百塊的工資是家里的主要依靠。她的丈夫在大連工作,每年見面的機會不多。他們六歲的女兒在屋里跑來跑去,一直想打斷我們和她外公之間的談話。
孫鐵軍覺得自己衰老了。那些游歷令他大開眼界,卻沒帶來太多的經濟回報,他在為每年要交納的一千七百元社保基金發愁,聽說它要漲到兩千一百元。他還被胃炎、肝炎、膽囊炎所困,即使如此仍要不時去開長途貨運,經常連續很多天日夜兼程。
鐵軍的家里干凈、整潔,狹小空間里的一絲不茍,顯示出他強烈的自尊。這自尊挽救了他,他知道自己那些下崗的同事中,很多因為長期的積怨而一病不起。兩個月前,他又參加了其中一位的葬禮,不過五十歲出頭。“死得都讓人心寒了。”他說。
墻上掛著的那把蝴蝶牌吉他,記載著他燦爛而浪漫的少年時代。他曾是個音樂愛好者,當年這把三十幾塊的樂器讓他成為聚會的中心,他向少男少女們彈奏《游擊隊之歌》。但琴弦好久都沒被撥動了,以至于他忘記了如何調音。
04
“他從未從那個鄉村窮孩子的內心走出來”
“先來八斤羊肉。”洪波掃視了桌上的其他四個人,然后語調平緩地對服務員說。這個小姑娘有一雙細長的眼睛,看起來只有十六歲。照例,洪波和她閑扯了幾句。他的陜北腔太重了,而且總是吞音,那些詞句就成群結隊地從他微微張開的厚嘴唇中滾了出來。
我大概猜得出內容。自從高中時代,他就是個很討姑娘喜歡的男孩子,知道怎樣在幾分鐘內將她們逗得咯咯笑。如今,那個曾經清瘦、有點像姜育恒的男孩子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個腰身渾圓、腹部凸出的中年形象,上唇毛茸茸的黑胡子和那張胖胖的顏色暗淡、有點油膩的臉,加深了中年的印記。
經過兩天的相處,他對我的問話不那么拘謹了。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一張坐了十個人的大圓桌上,桌上主要是他在榆林中學的同學。距離高中畢業十三年了,當初的少年意氣似乎又回來了,他們稱呼著彼此的綽號,回味著那些尷尬往事。他們大多出生于1971至1973年之間,有的來自鄉村,有的出生于城鎮。
榆林中學是陜北最好的中學,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03年。他們在1990年代初進入這所中學,共同度過了三年高中時光。他們記得那個時刻的榆林,蕭條、貧窮卻不乏詩意。

影視劇《漫長的季節》
他們踢球,傳看金庸小說,瘋狂地寫詩,留郭富城的發型,取笑班主任的健美褲,其中成績最優秀的夢想著考上大學,離開榆林,到省城西安,或者更遠的地方。
洪波坐在人群中,沉默,比周圍人看上去更成熟,或者說更蒼老些。每個人又自動歸位到高中時代的各自角色。在整個高中時代,他沒給其他人留下太多的印象。班里的五十九名同學,一半來自城市,一半來自鄉村,像兩個涇渭分明的陣營。
榆林是一座面積達43578平方公里的城市,包括十一個縣和一個市轄區。榆林中學在這個市轄的榆陽區,它一直是陜北的政治與商業中心。
洪波是那一半鄉村學生中的一個,來自最北的神木。就像東南沿海的廣東、福建的時尚要過上幾年才傳到西北的榆林,而城鄉間從未彌合的差異,則使來自鄉村的同學在物質和精神生活方面,都更匱乏。進入這所好中學,又往往意味著更大的壓力,他們要對得起學費。課間休息時,城里的學生在操場上嘻嘻哈哈,而鄉村的孩子們則安安靜靜地坐在凳子上。
洪波沒有考上大學,五十九個學生中只有三個被錄取了。第二年,他和很多同學一樣自費前往西安讀書,在一所財經學院,他學了三年的會計。在1990年代中期的西安,榆林像陜北的其他地區一樣,是貧窮與落后的代名詞。
“你們竟然還有皮夾克穿。”他的高中同學彩彩曾有這樣的尷尬遭遇。在很多西安人心目中,陜北人仍舊頭戴白羊肚毛巾,張口就是信天游。
三年學業后,洪波回到了神木,他依舊要為自己的生存掙扎。知識看起來沒起什么作用,他成了一家電石廠的一名開爐工,每月五百元的工資。電石有一個更正式的名稱叫碳化鈣,是無煙煤或焦炭與生石灰在爐中經高溫冶煉而成。洪波的工作是每隔一兩分鐘,就把長長的鐵鉤伸進冶煉爐中攪一攪,有時他還負責為爐中加燃料,把一鏟又一鏟黑色煤與白色的石灰送進爐子。
“我曾經喝水喝醉過,”洪波在熱氣彌漫的冶煉爐旁對我說,“那天特別熱,我一直流汗,一直喝水,不知為什么就暈倒了”。在帶我們參觀他曾經工作的電石廠時,他順手奪過工人們手里的鐵鍬,向爐里添煤。他發福的身體突然變得靈巧而有力量,姿勢標準。他和其中一位熱烈地握手,幾年前,他們在一個工作組。
“如果我不離開,頂多像他這樣,成為一名技術人員,管幾個工人。”洪波離開石英廠時說。石英廠巨大的鋼鐵管道、高溫的石英塊、濃重的煙塵、三十七度的廢水,都令我印象深刻。
因為偶然的機緣,他成為了一家焦炭廠的出納。這是他新生活的開始,他天生對數字的敏感和大學的財會知識開始發揮作用。他是個勤奮而謹慎的年輕人,不斷冒出的煤礦和焦炭廠則亟須值得信賴的專業人士。
這是個緊湊的小世界,他的名聲很快就為他贏來了更多的機會,高峰時期,他代理十余家小型煤炭相關企業的財會業務。
2004年起,他用賺來的錢投資參股焦炭生意。
他趕上了煤炭價格不斷上漲的黃金年代。他曾經只期待“當個廠里的會計一把手”,結果他發現自己獲得了從未想象過的財富。他在西安買了房子,他的兒子在一所著名小學念書,他的妻子成為了全職太太。
他每個月的時間則平分在神木縣與西安兩地。去西安叫“下去”,回神木則是“上去”,在陜北口音里,“下”的發音是四聲的“ha”。兩地距離六百多公里,他開著那輛有點舊的黑色索納塔要走上六七個小時,有時會困倦得停車休息幾分鐘。

影視劇《漫長的季節》
有兩天的時間里,我坐在這輛索納塔里,被他帶著去看他的煉焦廠,去登二郎山。從神木縣到府谷縣的路上,我第一次看到傳說中運煤卡車的長龍。每輛卡車載著六七十噸煤,一輛接一輛地等待通過檢查站,大概有三十公里之長。等待是漫長而無奈的,耗上兩三天時光是正常的。
坐在時走時停的車里,洪波斷斷續續地講述著焦慮與期望。他的行業是真正的關系密集型行業,一座煤礦、一個煉焦廠,不需要太多的專業技術,但是獲得作業的許可卻要大費周折。
誰都看得到府谷縣城煙塵籠罩的上空,流經神木的窟野河的一半面積被黑水所占據,城市的居民經常在超市里購買大量純凈水以挨過斷水的日子。這里是中國面臨的環境挑戰的縮影。也因此,“關系”是那些小礦、小廠得以延續的依靠。他們有自己的游戲規則,講究信用和人情。
洪波比從前富有得多,但是生活習慣卻保持著一貫的簡樸,似乎也從未從那個鄉村窮孩子的內心走出來,十二萬元一塊的手表,還是令他很是心痛了一段時間。
他希望離開這種生活,人際交往太疲憊,又擔心政策總是在變。最近一年,他一直試圖將若干小廠合并成一個大廠,然后逐漸退出一些廠礦的股份。但是他又擔心一旦真的離開這些,他該以什么為生活的中心?
他說想“干點喜歡干的事情”,卻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歡什么。他對兒子的未來充滿期待,為了保證他能被最好地對待,他慷慨地送禮給教師們,令一些西安的家長心理失衡。他還準備在北京購置新的房產,比起其他投資,這既具體又可以控制。
這些迷惘不會妨礙他對生活的享受,他是個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發現樂趣的人。我喜歡看他大塊吃羊肉、趴在電腦前聚精會神地玩掃雷游戲,或是用QQ有一搭沒一搭地和朋友聊天。他說最近喜歡上了紅酒,晚上獨自看電視時會喝上幾杯,并按照流行的方式在杯子里加幾塊冰。
十五年前的那個農村少年,從未夢想過有這樣舒適和豐沛的生活吧。
本文節選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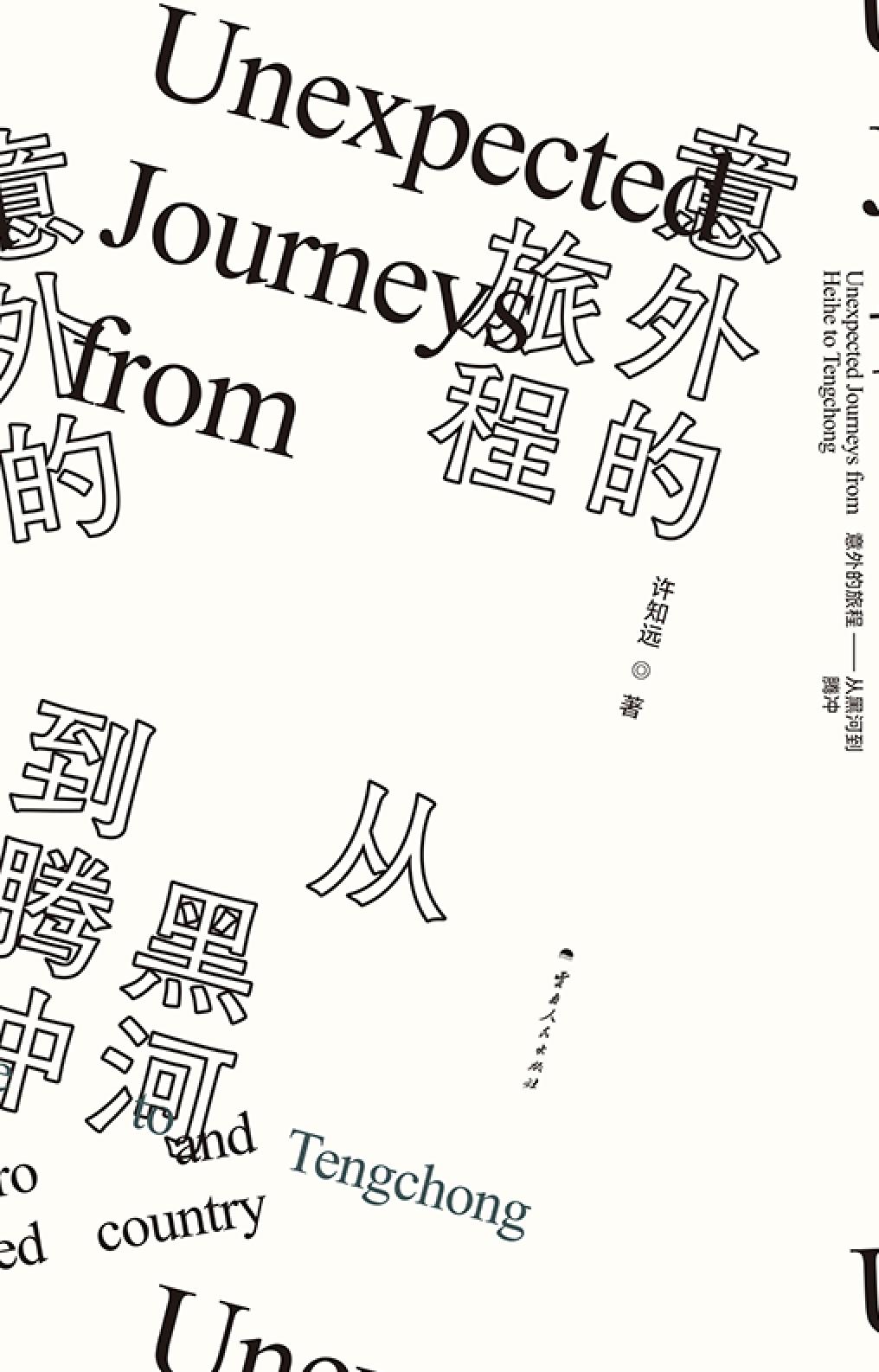
《意外的旅程》
作者:許知遠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理想國
副標題:從黑河到騰沖
出版年:202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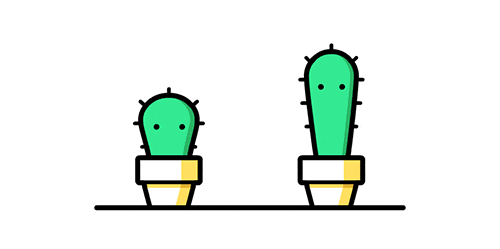
編輯 | 輕濁
主編 | 魏冰心
原標題:《許知遠寫游記,有點東西》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