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理查德·沃特默談啟蒙運動的終結

理查德·沃特默(章靜繪)
理查德·沃特默(Richard Whatmore)是英國圣安德魯斯大學現代史講席(Chair of Modern History)教授、圣安德魯斯大學思想史研究所主任、國際著名期刊《歐洲思想史》(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主編,曾任英國薩塞克斯大學思想史研究所主任。他的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十七世紀末以來的歐洲政治思想和國際關系。他的新書《啟蒙運動的結束:帝國、商業和危機》(The End of Enlightenment: Empire, Commerce, Crisis)于2023年12月由企鵝出版社出版,該書被認為是將“啟蒙運動”這一歷史概念“從循環論證(circular debates)中拯救出來”,回到相應的歷史語境中分析的杰出作品。近期,《上海書評》專訪了理查德·沃特默。
“啟蒙運動”這一歷史概念非常復雜,不同學派對它的理解很不同,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理查德·沃特默:我不確定在多大程度上我們可以總結當代學術界或者一般爭論中有關啟蒙運動內涵的辯論。我最關心的是那種將啟蒙運動與民主人權和包容相聯系的傾向,即好像存在著一種讓所有國家都可以發展出這些價值的簡單路線。在《啟蒙運動的結束》中,我要表達的一個觀點是,如果我們把啟蒙運動視為任何意圖終結宗教戰爭的“策略”(strategy)的話,那么阻止內亂與建立信仰包容的路線有很多種,就會有很多種啟蒙運動。比如對人口的控制,或者我們所謂的“獨裁制度”(autocracy),如果它是意圖阻止暴力發生的話,也可被視作一種啟蒙的策略——這也是我對歷史學者習慣于稱為“開明專制”的定義。在《啟蒙運動的結束》中,我最感興趣的是那些所謂的“自由國家”(free states)和啟蒙運動的關系,因為正是在這些國家,特別是英國和大革命時期的法國,當時的人相信啟蒙運動已經結束了。所以,我的目標是以十八世紀人對這個術語的理解重新定義啟蒙運動,也就是通過“歷史化”(historicizing)的取徑。
《啟蒙運動的終結:帝國、商業和危機》這個書名直接反映了您關注的一個重要論點:十七世紀末歐洲興起的商業帝國(以英國、法國為代表)導致了啟蒙運動的失敗。能具體說說嗎?
理查德·沃特默:《啟蒙運動的結束》一書從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謨寫起,因為他相信啟蒙運動在現實中存在過。他曾很開心地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由宗教激發的意識形態沖突已經過去的時代。后來他逐漸認為,宗教爭端的起源——他稱之為“迷信和狂熱”(superstition and fanaticism)——在世俗的偽裝下再次爆發。休謨將這歸咎于商業帝國,但是他的觀點需要被精確地解釋。當然,歷史上有過很多商業帝國。它們大多數興起后又衰敗了,古代的例子是迦太基,近代的例子是荷蘭共和國。休謨對這些商業帝國沒有特別的興趣,因為他認為在十七世紀末世界發生了一個重要的變化,用他的話說,“商業成為國家的一個理性”(commerce became a reason of state;“國家理性”的翻譯參考周保巍:《國家理由,還是國家理性——思想史脈絡中的“reason of state”》,《學海》,2010年第5期——采訪者注)。休謨認為,因為軍事技術已經非常昂貴,陸軍和海軍規模如此龐大,為了保衛國家,所有的國家都必須從貿易中獲取收入,用以支付潛在戰爭的費用。因此最終所有國家都在思考擴大商業的辦法,這導致帝國化,因為領土更大,勢力更強的國家想要控制小國的市場和財富,而過去大國與小國可以和平相處。商業興起為“國家理性”對十八世紀兩個貿易強國——英國與法國有特別的意義,這讓兩個國家陷入彼此沖突的困境。到了晚年,休謨相信,因為商業帝國的興起,“迷信和狂熱”已經從神學性的沖突轉化為世俗性的沖突。憑借公共信貸(public credit),英法沉溺于戰爭與擴張。這兩個國家通過向民眾傳播仇外形式的愛國主義維持自身。休謨還擔心由他的朋友亞當·斯密定義的“重商主義”(mercantile system)在英國已經被創造出來了,腐敗政客被商人和銀行家賄賂,從而制定出符合商人和銀行家利益而非民眾利益的法律。這些情況讓當時人認為啟蒙運動結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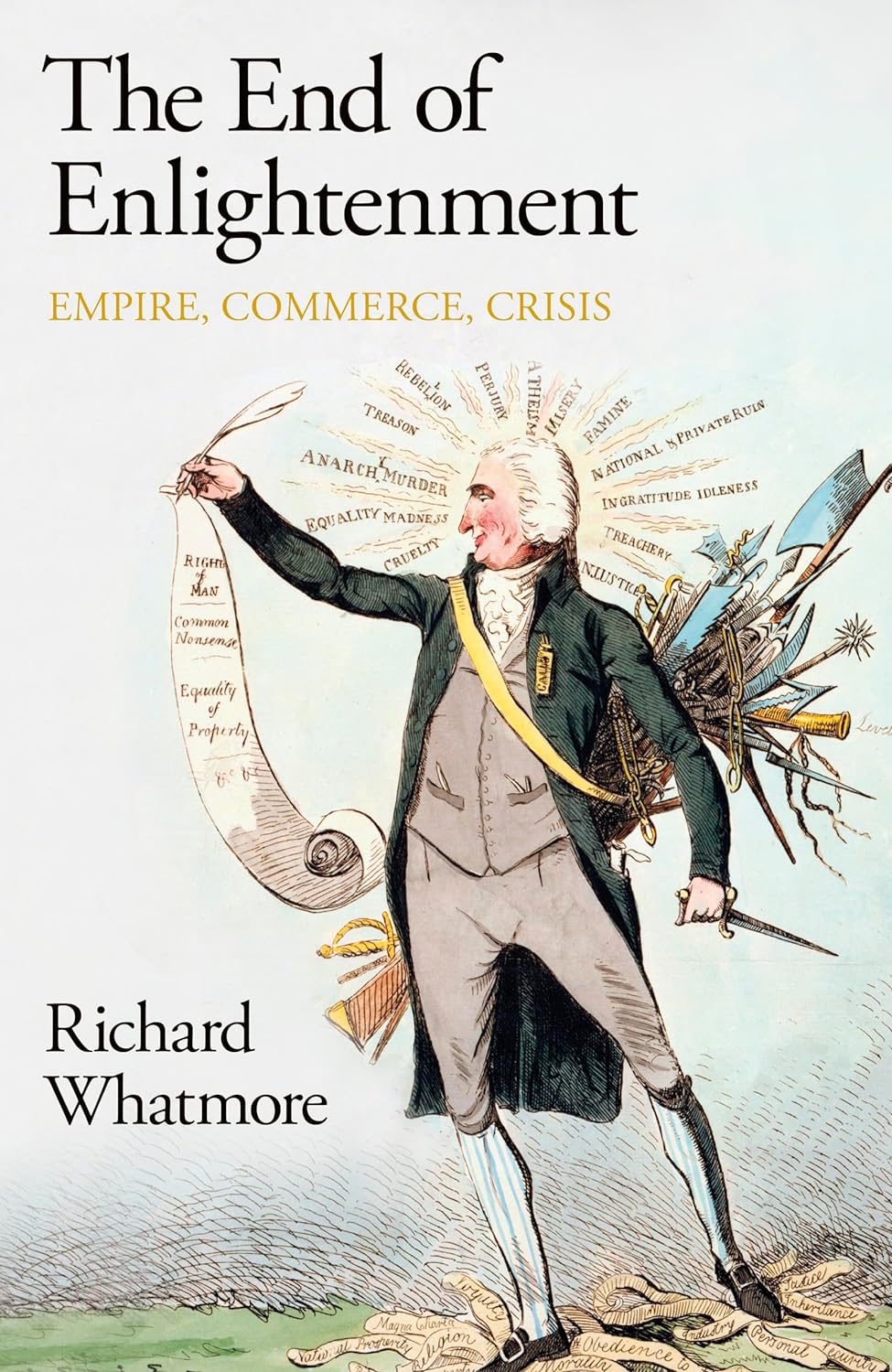
啟蒙思想與帝國、商業三者之間的關系是什么樣的?大國或者說帝國與啟蒙運動能否結合?
理查德·沃特默:我們都需要記住,十八世紀發生的世界巨變,至今仍伴隨著我們——究其原因,部分是緣于商業帝國的興起。小國逐漸消失或者難以維持,被大國特別是商業帝國兼并。一些評論者會說,在十八世紀初,僅在歐洲就存在過幾百個小國。到拿破侖戰爭結束的時候,國家的數量已經遠不如前了。世界已經是大國的世界了,只有大國可以繁榮和存續。小國不是變成瀕危物種就是已經消失了。這種情況在歐洲的自由國家,即自稱共和國的國家特別明顯。日內瓦、熱那亞、威尼斯、荷蘭共和國、瑞士邦聯都是共和國,沒有一個在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后還存在的。十八世紀成了帝國的時代。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你生活在大國的世界并且相信啟蒙運動,那么找到一個讓大國世界和啟蒙運動結合的方法是必須的。我在《啟蒙運動的結束》中提出的觀點是,對大多數當時人來說將商業帝國與啟蒙運動結合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商業帝國傾向于鼓勵戰爭、公共暴力、仇外情緒等邪惡的事情。很多當時人一度以為自己找到了解決問題的辦法,但最終還是失敗了,在抑郁中離世。我不認為他們中有人認為帝國是一個建立或者維持啟蒙運動的可靠辦法,帝國只是他們生活在大國世界中的一個現實。在追逐市場的過程中,大國變得越來越大。如果和平與包容是值得捍衛的價值,這些就是為了實現啟蒙運動必須應對的“真實情形”(straightforwardly the circumstances)。
長期以來啟蒙運動被視為是理性克服迷信的進步時期,催生出了諸如自然權利學說、立憲政府等深刻影響全球現代歷史的觀念和制度。然而,在您的論述中,在十八世紀中后期,甚至在七年戰爭(1763年)結束之際,一些思想家認為他們的啟蒙事業失敗了。請問,為什么至今許多學者都沒有注意到啟蒙運動和國際和平的關系?似乎在啟蒙運動的歷史語境中,和平問題是一個顯而易見的議題?
理查德·沃特默:我不同意將十八世紀的“理性”(reason)這個術語作為建立包容與和平的進步性改革的同義詞。雖然伊曼努爾·康德等人論證過追求和平的計劃是“理性的”(rational),但是康德等人的行動是十八世紀末的故事。在十八世紀末之前,如果你將啟蒙運動定義為任何可以阻止“迷信和狂熱”爆發的策略,那么它不一定與立憲政府或者自然權利有聯系。《啟蒙運動的結束》的一個觀點是,自由國家和啟蒙運動的關系是復雜的。對當時人來說,共和主義很像是在再造激進新教主義的歷史,因為兩者都有生活在一種“同質性”(homogeneous)的文化之中,并且都以自由之名發起斗爭。而激進新教主義的歷史,在當時人看來是一段引起分裂和沖突的歷史,將原本統一的教會分裂成彼此對立的兩種陣營,并且在進一步分裂之前經歷更多的暴力。法國革命時期,很多觀察者相信法國朝新教的方向發展,這不是說法國的天主教徒改宗新教了,而是一種比喻,指法國將重現十七世紀新教徒先是建立一個教會然后內部分裂成不同教會的經歷。法國共和主義有出現類似發展軌跡的跡象。這是自由國家和啟蒙運動之間復雜關系的一個例子,可以提煉出的觀點是對自由的欲望讓人變得狂熱。這也是大衛·休謨在1776年去世前的觀點。
您的研究路徑與以昆丁·斯金納、約翰·波考克為代表的劍橋學派的思想史研究有什么異同?
理查德·沃特默:我想要成為一名思想史學者的想法最初是1980年代在劍橋大學聽了昆丁·斯金納的講座后產生的。自那以后,我受到約翰·波考克作品的影響特別大,我第一次讀他的《馬基雅維利時刻》也是在1980年代。所以,我大概會這樣形容我自己,一名劍橋思想史學派的“忠實成員”(a fully paid up member)——這也是恰當的形容。但是像所有的教會一樣,劍橋學派的內涵很廣,包含了關于思想如何變化以及如何與政治聯系,這里有不同的、并且是經常有沖突的研究路徑和假設。我在《什么是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簡論》里專門寫過劍橋學派不同分支的關系,特別是比較了斯金納、波考克和伊斯特凡·洪特(Istvan Hont)的觀點及影響。《啟蒙運動的結束》受到了這些“大家”(luminaries)以及很多其他學者的影響。我最感興趣的是“行動中的思想”(ideas in action)以及歷史人物如何回應他們謀求改變或者改革的計劃失敗時的挫敗感。像波考克,我對“支撐”政治行動的文化特別有興趣;像洪特,我也感興趣商業社會對傳統文化時常造成的擾亂性影響。總的來說,我最感興趣的還是“行動中的思想”。

約翰·波考克
《啟蒙運動的終結》是否與斯金納、波考克建立起來的古典共和主義傳統有對話?如果有,啟蒙運動的終結是否是古典共和主義在十八世紀衰退的一個結果?
理查德·沃特默: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當然,斯金納和波考克沒有回答的一個問題是“古典共和主義”(classical republicanism)或“公民人文主義”(civic humanism)在十八世紀末發生的變化。我之前認為因為法國大革命,這一傳統消亡于歐洲——朱迪絲·施克萊(Judith Shklar)在1990年代初對我說過這個觀點。現在我認為雖然共和主義到處碰壁,但在美國的特殊環境中得以繁榮,在歐洲則以一種支持建立帝國的意識形態存續,因為共和主義可以是非常仇外并且煽動狂熱愛國情緒的。《啟蒙運動的結束》認為這種共和主義的“變質”是共和主義者獲得的教訓,書里提到凱瑟琳·麥考萊(Catharine Macaulay,輝格黨共和主義歷史學家——采訪者注)的例子,她在1760年代尊崇老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擴張英帝國的戰爭。1760年代之后,古典共和主義者變成自由國家觀念的“熱情捍衛者”(patriotic defenders),特別在美國和法國。《啟蒙運動的結束》部分討論了這段故事,特別是法國大革命前后的共和主義意識形態危機。
《啟蒙運動的終結》與您之前研究的關系是什么?您之前研究了法國、英國、日內瓦和愛爾蘭的一些共和主義者,重農學派和帝國主義者,您也寫過諸如休謨、盧梭等大思想家的論文,請問您之前的研究是如何幫助《啟蒙運動的終結》的寫作?如果對新書有一個定位的話,《啟蒙運動的終結》主要考察的是大思想家還是懷有政治思想或理想的、名氣沒有那么大的人物呢?啟蒙運動的主要參與者是哪些人?
理查德·沃特默:在某種意義上《啟蒙運動的結束》是我過去三十年研究十八世紀歷史的累積,也是我第一次專注于研究英國而非法國或者日內瓦的歷史人物,雖然書里有一章討論的是雅克·皮埃爾·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在寫書過程中,我與波考克討論,他說《啟蒙運動的結束》比《恐怖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共和主義者》最后一章對共和主義的解釋“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這樣說。《啟蒙運動的結束》的主題范圍廣得多,對現有的歷史學解釋也提出了更多的質疑。但是我認為在觀點上延續了我自己之前關于個別共和國與小國(如日內瓦)的研究,《反對戰爭和帝國》就是一個例子。《啟蒙運動的結束》有專章討論愛德華·吉本、謝爾本伯爵(1784年起成為蘭斯當侯爵——采訪者注)、埃德蒙·伯克、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托馬斯·潘恩以及上面提到過的人物。但是其他重要的人物,例如盧梭、杜爾哥(Turgot)、伏爾泰、康德、普萊斯利、約翰·亞當斯或者奧拉達·艾奎亞諾(Olaudah Equiano,十八世紀著名的非洲裔英國作家——采訪者注)也有足夠的證據被包括進《啟蒙運動的結束》的主題討論里。《啟蒙運動的結束》討論了一些十八世紀最知名和最重要的人物,但是人物選擇的標準在很大程度上是任意的,因為“迷信和狂熱”引發的問題再次爆發(1789年法國大革命引發的國際沖突——采訪者注)并且影響了所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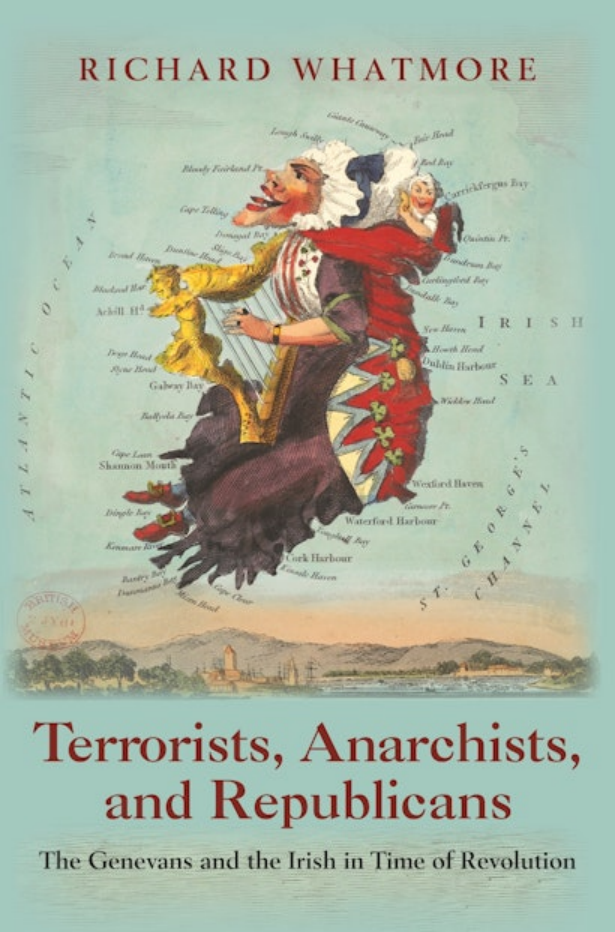
《恐怖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共和主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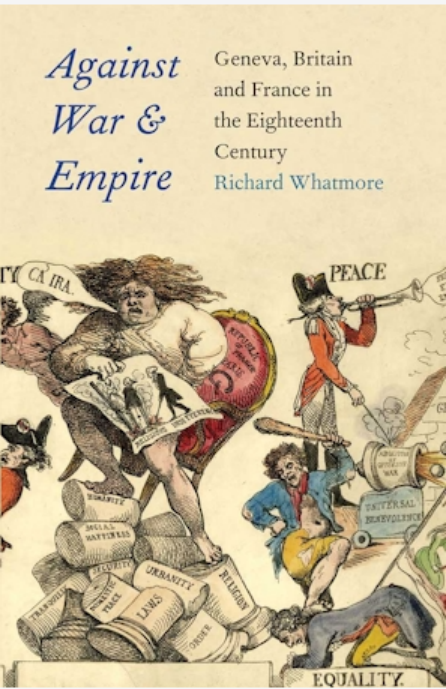
《反對戰爭和帝國》
《啟蒙運動的終結》有明確的國別地域范圍嗎?或者說,在您看來,存在獨立的蘇格蘭啟蒙運動、英格蘭啟蒙運動、法國啟蒙運動么?是不是啟蒙運動自始至終都是一種跨國運動?
理查德·沃特默:如果你將啟蒙運動定義為任何可以阻止宗教戰爭爆發的策略,那么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啟蒙運動。這種邏輯的成立意味著從國家策略角度定義啟蒙運動是不對的,也不存在某種特別的蘇格蘭啟蒙運動或者法國啟蒙運動。而且像“跨國的”(transnational)這樣的詞匯只有在下述兩個條件同時成立時才有討論的意義:“跨國的”事物有著國際性的影響力,并且處理的是連接內政與外交策略的問題。在十八世紀極少數人相信“永久和平計劃”能夠實現。隨著時間過去,更多人確信在一個商業帝國和公共信用的世界里,一定要發展出能夠實現和平與包容的新策略。世界已經不可避免地改變了,沒有回到商業時代之前的可能,突然間“前商業時代”(a pre-commercial age)被重新定義為一個烏托邦。
啟蒙運動在十八世紀僅僅是一場歐洲范圍內的運動嗎?抑或是大西洋兩岸受到歐洲文明影響的運動?主張把大西洋內部及其周邊的島嶼、國家和區域等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研究的路徑對您的啟蒙運動研究有影響嗎?
理查德·沃特默:在我的定義里,不管在哪,只要你發現“迷信與狂熱”就需要發展出一個建立和維持啟蒙運動的策略。所以,啟蒙運動過去是,現在依舊是一個非常全球性的現象。在任何地方建立啟蒙運動,意味著你必須清楚自己所處的區域國家和國際語境,否則啟蒙運動就會失敗。但是啟蒙運動的策略,我稱之為應對“行動中的思想”,是關系到特定時間和地方的,這意味著“過度的概括是危險的”。因為《啟蒙運動的結束》討論的是個別歷史人物提出過的策略,我比較少受到強調歐洲文明作為一個闡釋類型或者大西洋世界作為一個闡釋類型的影響。我的主題和“作者意圖”引導我走向其他地方。
啟蒙運動與歐洲文明是什么關系?
理查德·沃特默:我想要明確的是,由宗教帶來的“迷信與狂熱”問題轉變為世俗化的形式從來都不只是一個歐洲現象。只是,因為商業帝國的興起,在歐洲這一現象特別明顯。但是啟蒙運動的結束絕不意味著故事的結束,因為人們總是想要重建包容與和平,特別是正經歷危機的人。因此啟蒙運動的戰斗沒有結束。十九世紀的某些時段可能經歷過啟蒙運動的恢復,但是二十世紀的災難讓人們再次失去啟蒙運動。可以進一步說,十八世紀末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是可以直接比較的”(is a direct parallel),特別是在對政治意識形態失去信仰并且感到所有改革策略已經失敗或者正在失敗的意義上。
生活在十七和十八世紀的歐洲人認為他們所處的大陸對戰爭上癮了。啟蒙運動很難實現,因為在所有歐洲國家中“市民性質的與宗教性質的動亂”(civil and religious turbulence)似乎變成了一種常態。因此,他們很自然地將目光投向在他們看來世界上更加和平的區域——包容與和平是這些地方的常態而非例外。十八世紀啟蒙策略家著迷于中國,尤其是重農學派(the physiocratic)對中國的濃厚興趣就是一例。事實上如果你生活在一個危機時期,你會想看看別的地方,這種觀察可能會激發能夠建立和平與包容的策略。所以,認為啟蒙運動的時代是歐洲中心的說法,是不對的。正相反,啟蒙思想家認為歐洲的改革更難,因為在這里市民性質和宗教性質的暴力,其歷史更久,得向世界上更加和平的地方去討教、學習。
您書名中的“商業”一詞是否指的是資本主義?在您看來,十八世紀的啟蒙人物是否預見了商業帝國主義對和平的破壞?有沒有人在預見這種破壞后繼續思考用制度化的方法(立法)抵制商業帝國主義,并在您看來是值得今天國際秩序的決策者學習的?
理查德·沃特默:十八世紀有很多類型的商業社會,相對于“資本主義”我偏好“商業”這個術語,資本主義一詞的內涵太寬泛了和模糊了。很多十八世紀的人,例如謝爾本伯爵和他的朋友理查德·普萊斯,相信商業帝國將引發全球戰爭。《啟蒙運動的結束》解釋了他們反對殖民和阻止帝國興起的努力。雖然失敗了,但是他們充分意識到了問題,即貪求戰爭、利潤和貿易的后果。對今天學習這些問題的人來說,我的建議是學習思想史,特別是“行動中的思想”失敗的時刻。我認為重建啟蒙運動的努力總是重復性的失敗,而我們可以從十八世紀末的政治經濟思想中學到很多。認為思想發展有文化屬性的假設是錯誤的。我們的先輩有很多可以教給我們的。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