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楊靖︱1789:歌德并非“歌德派”
1789年是歌德(1749-1832)人生的關鍵之年。這一年年初,他開始與一名做假花的女工克里斯蒂安娜秘密同居。圣誕節前夕,二人的私生子出生——取名奧古斯特——與歌德的恩主魏瑪公爵同名。當年5月,在歌德力薦之下,好友席勒就任耶拿大學歷史教授(其就職演說題為“世界史之意義與目的”),隨后開始雙方長達十余年的文學合作。這一年7月,法國爆發大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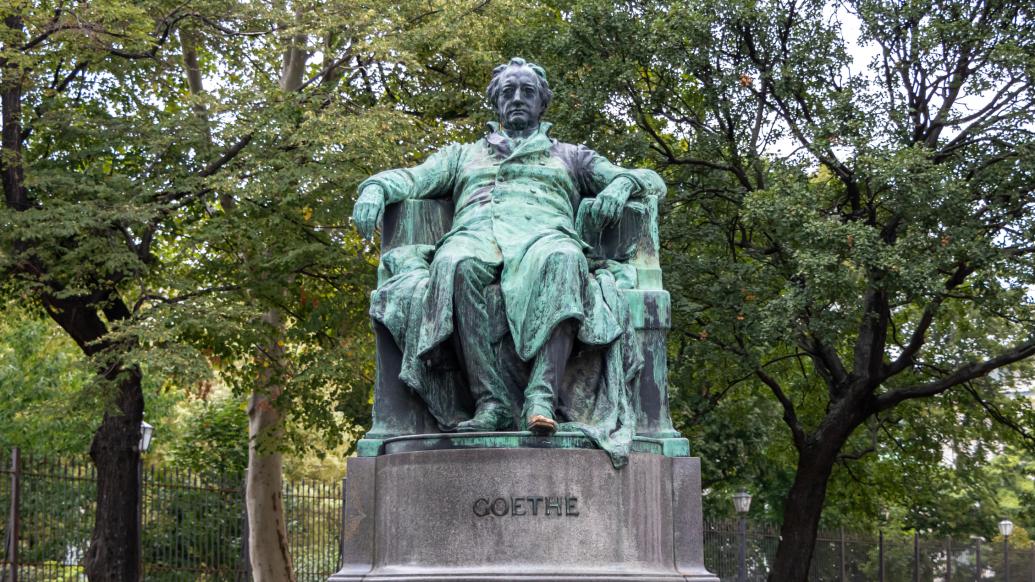
奧地利維也納的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雕像
歌德沒有像他的導師赫爾德(1744-1803)一樣振臂歡呼民主社會的到來,也沒有像他的友人費希特(1762-1814)一樣撰寫政論文章呼喚革命,相反,他一如既往保持懷疑態度,冷眼旁觀,并結合當時德國社會及國民狀況對法國大革命進行反思。他的這一種自由精神和獨立思想導致兩方面的結果:一是催生了大批優秀文學作品——如劇作《大科夫塔》(1792)、《平民將軍》(1793)、《被煽動的人們》(1794)、中篇小說《德國逃難者閑聊記》(1795)和長篇敘事詩《赫爾曼和竇綠苔》(1796)——上述作品大多以法國大革命為題材或背景;一是直接導致他與魏瑪啟蒙派(如赫爾德)以及耶拿浪漫派(如費希特)的分歧乃至“決裂”。歌德義無反顧——以“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戮力前行,因為他堅信唯有自己掌握“詩歌與真理”。
當時的社會現狀,照恩格斯后來致《北極星報》編輯書信中的描述:“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體的討厭的東西。沒有一個人感到舒服。國內的手工業、商業、工業和農業極端凋敝;農民手工業者和企業主遭到雙重的苦難——政府的搜刮,商業的不景氣。貴族和王公都感到,盡管他們榨盡了人民的膏血,他們的收入還是彌補不了他們日益龐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滿情緒籠罩了全國……”作為一名富于人道主義精神的文學家,外表來看,歌德似乎已經取得令人羨艷的世俗成就(不久前由神圣羅馬皇帝頒賜貴族頭銜),然而他內心清楚自己的損失不可彌補——他一直在構思巨著《浮士德》,只是找不到時間動筆。政務之余僅有的閑暇,他卻被迫要為到訪的奧地利皇后奉上《皇后駕臨》《皇后的酒杯》《告別皇后》等應景頌詩。1786年,他曾毅然拋開一切事務,秘密前往意大利漫游,以舒緩胸中積壓已久的郁悶之氣。
此次游歷成果豐碩。歌德沿途創作的風景畫幾乎“完勝專業畫家”,而日后整理出版的《意大利游記》亦成為同類文學的典范之作,唯一令他感到失望的,是他此行最看重的詩作《羅馬哀歌》(主要完成于1789年下半年)遭遇“滑鐵盧”,出版后收獲一片嘲諷謾罵之聲:赫爾德譏諷意大利之旅使得歌德沾染淫蕩、放縱的習氣,反映在詩作中,便是對“性愛的熱衷”。在這位嚴肅的啟蒙思想家看來,歌德此舉不僅敗壞道德,也敗壞了文學。以道德衛士自居的宮廷反對派更是義憤填膺,痛斥詩中展示的“妓院般的赤裸”。他們將詩中的女主與現實中歌德的同居女友畫上等號,認為詩人向她“獻媚”簡直是上流社會之恥。他們強烈要求,按照相關法律,未婚生子的女方應當被逐出教會,而后施以嚴懲;男方(貴族)也要象征性地繳納罰金。多虧公爵百般回護,此事最終不了了之。
但上流社會未肯善罷甘休。他們齊心協力,筑起一道隱形的圍墻:即便數年之后歌德與妻子正式結婚,他們仍無法獲得魏瑪名媛沙龍的入場券——原本喜好社交的歌德很長一段時間只得在書房奮筆(因為他拒絕獨自外出赴宴),心中憤懣可想而知。最出乎歌德意料的是席勒的“變臉”:通過迎娶一位貴族小姐,平民出身的席勒實現了“階層躍升”,相對于歌德的自貶身價(娶平民為妻),席勒似乎覺得自己有足夠資格對歌德進行“提點”,以至于將他之前寫給歌德的求助信忘得一干二凈:“我每年需要兩千塔勒,才能在此地體面地生活……倘若客觀情況不允許把我目前的薪俸從四百帝國塔勒立即提高到一千塔勒,那我就寄希望于公爵的仁慈,現在先批準給我八百塔勒……請您告訴我,您對此事的想法如何?”
法國大革命令席勒歡欣鼓舞。1792年,法國國民公會曾在歐美范圍內遴選同情支持革命的杰出人士,授予其“榮譽公民”稱號,席勒憑借反貴族專制的名劇《強盜》成為其中一員。如果說此前歌德對席勒的某些行為只是感到慍怒,此時則已上升為惱怒。眾所周知,德國大學教授一向地位尊崇,遠過于體制內普通公務員,與之相應,政府對教授的道德及政治素質也嚴格要求。在法德尚處于敵國的情勢下——就在同一年,歌德陪同奧古斯特公爵參加鎮壓法國大革命的普奧聯軍,并于次年(1793)一同親臨前線,圍攻駐扎在美因茨的法軍——在歌德看來,身為國家公務員的席勒不僅沒有拒絕法方頒發的榮譽稱號,反而欣然領受,顯然有失體統。
和席勒相比,被譽為狂飆突進時代“首席文藝理論家”的赫爾德更為浮躁冒進。歌德就任魏瑪樞密顧問之初,力邀赫爾德至魏瑪擔任新教總監,負責教育體制改革。師徒二人聯手,造就公國文教繁興的局面——小城魏瑪被譽為“德國的佛羅倫薩”。二人極為重視德國歷史文化傳統,認為“神授”的君權應該受到嚴格限制,并建議奧古斯特公爵奉行開明專制——公爵從善如流,魏瑪在政治文化層面也煥然一新,成為名副其實的“德國的精神故鄉”。然而,師徒“合作共贏”的模式并未能持久——與歌德的豁達大度相比,赫爾德才氣過人但心胸狹隘,不久便對歌德生出嫉妒之心。
自青年時代起,歌德已然習慣赫爾德“居高臨下”的諷刺與批評——即便歌德平生甚是得意的歷史劇《鐵手騎士葛茲·馮·貝利欣根》,也被這位理論家斷定為不合“三一律”且“虛構過度”(相反,馬克思日后在評論拉薩爾戲劇時極為贊賞歌德筆下“騎士對皇帝和諸侯所作的悲劇性的反抗”,認為這是歌德“正確的”選擇)——作為職業文學批評家,赫爾德似乎從來不會“表揚和贊美”他人作品。據艾克曼《歌德談話錄》記載,歌德晚年曾抱怨,“只有在和赫爾德玩牌時,才能忍受他”——因為其言辭太過刻薄。歌德曾將悲劇《私生女》手稿呈請赫爾德指正,不料后者回復:“相較于你的私生女,我更喜歡你的私生子。”這顯然已超出正常的文藝批評而淪為人身攻擊,不僅惡俗,更兼歹毒。
赫爾德對自己在魏瑪的境遇并不滿意:他肩負重任,為此不惜(像歌德一樣)犧牲自己的文學創作,可是他并未能像歌德一樣獲得公爵青睞。一度壟斷魏瑪文教主導權的教會人士對赫爾德大刀闊斧的教育改革極為反感,于是聯名上書,向公爵告發此人是“可疑的自由思想家”,證據是他在法國大革命前后發表的一系列自由言論。事實也的確如此:即便在殘酷的雅各賓專政時期,赫爾德口頭宣稱反對一切恐怖活動,但他從不懷疑革命的正確性和合法性,并且預言大革命最終必將取得成功。他在給德國啟蒙運動代表人物克洛卜施托克(1724-1803)的信中說:“總之,革命將繼續下去。不論是羅伯斯庇爾和馬拉,還是葉卡捷琳娜和……都無法阻擋”——雖然他在此處使用了省略號,但明眼人一望而知,空格處一定是奧古斯特公爵的大名。
公爵震怒不已。歌德深知此時事態已不可挽回:從政治方面來說,他和赫爾德分屬于兩個敵對陣營;雙方在文學方面的差異也日益公開化——赫爾德固守文學啟蒙觀念,以道德哲理為最高法則,與歌德(以及席勒)倡導的古典文學趣旨格格不入。被公爵解除職務后,郁郁寡歡的赫爾德不僅遠離宮廷,也自動疏遠了魏瑪文學團體,最終于1803年黯然辭世。
赫爾德生病之際,歌德時而前往探望,盡管內心不無怨憤——在赫爾德自命為“革命之友”,吹響沖鋒號向君主(貴族)制發起總攻之際,歌德不止一次對他提出“嚴正警告”:一個人不能一方面享受舊制度下的優渥生活和各種特權(赫爾德向公爵索求無度,令歌德頗為難堪),一方面又要打倒甚至消滅提供特權之人。與赫爾德不同,終其一生,歌德對奧古斯特公爵(1814年后因“反法”有功晉升為大公)感恩戴德,即便屢遭訓飭也不離不棄,并堅持認為這是他“做人的原則”。同時,歌德也將這一原則上升為友誼的“試金石”:面對法國大革命的疾風暴雨,到底是像他本人一樣矢志不移地維護君主及貴族特權,還是像他的革命友人一樣主張推行民主制?針對歌德的這道選擇測試題,他的另一位友人費希特很快便給出了答案——一個令歌德近乎崩潰的答案。
費希特是哲學大師康德的門徒。法國大革命爆發后,費希特發表《吿歐洲軍人書》,引起歌德的關注。于是,身兼耶拿大學總監的歌德決定聘任這位青年哲學家來校任教。耶拿距魏瑪約三十公里,根據時人的說法:魏瑪有宮廷和文學,耶拿有大學和哲學——前者以維蘭德(1733-1813,歌德的另一位導師)、赫爾德以及歌德本人為代表,后者則以費希特、施萊格爾兄弟以及諾瓦利斯和謝林為代表(席勒例外:他在耶拿主要從事哲學研究,返回魏瑪后則專注于文學創作)。費希特將康德唯心主義推向極致,形成所謂“絕對自我”哲學(知識學)體系,鼓吹“心外無物”——據海涅說,當年曾有好事者作漫畫“費希特之鵝”(a Fichtean goose)對此加以嘲諷:畫面中央是一只碩大無朋的鵝肝,以至于人們找不到鵝在何處。
費希特既是出色的演講家(日后以《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聞名于世),更是一流的宣傳家。1793年,受大革命精神感召,費希特發表檄文《向歐洲各國君主索回他們迄今壓制的思想自由》,主張人民擁有革命的權利,同時糾正德國朝野上下對于法國革命的誤解和偏見,引起保守派一片恐慌。1798年,費希特在他主辦的期刊《哲學雜志》上刊登論文《宗教概念的發展》,結果被冠以莫須有的“宣傳無神論”罪名。
當然,對于奉行開明專制的公爵而言,無神論或異端之類罪名不過是羅馬教廷和宗教裁判所的發明,他本人對此毫無興趣。他起初打算派人搞一次誡勉談話,警告費希特“下不為例”。但緊接著事情起了變化:負責調查的手下報告“費希特是一個惡劣的雅各賓派”,他在講演中多次鼓吹在歐洲全境(包括魏瑪公國)發動革命,推翻君主專制——這一次公爵不再容忍,下令立即褫奪費希特登臺演講的資格,與此同時,歌德作為耶拿主要負責人也受到斥責。
費希特顯然不理解歌德的難處。這位性情剛猛而倔強的哲學家發表公開信,將報刊被查封一事形容為新時代的一樁“火刑”,并且威脅當局倘不收回成命,他將辭去耶拿大學教授一職,以示抗爭。費希特的公開信在知識界取得廣泛同情,耶拿大學師生聯名向政府請愿,甚至有名律師自告奮勇為他辯護代言——畢竟,此時距德國最后一座火刑架撤除不過五十余年。
其實,對于費希特這塊“燙手山芋”,魏瑪宗教界及行政當局早就“意欲除之”,只是礙于他的哲學聲望和歌德的情面而已。此時他公然叫囂辭職,可謂正中下懷——據說費希特呈文之際,已然心生悔意,可是對方瞬間已完成簽字蓋章一整套程序,最終他只得悻悻然退場。史上著名的“耶拿風波”由此告一段落。余怒未消的公爵(遷怒于歌德)在書信中寫道:“我大約十次被歌德氣壞了身體。對這類愚蠢和危險的事情,他實在過于幼稚。”歌德一肚皮委屈無處發泄,憤然將費希特耶拿任教期間(1794-1799)二人往來書信悉數焚毀(以致后人對此事件中歌德扮演的角色多有誤會)。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歌德日益疏遠奉中世紀為圭臬的浪漫派(斥之為“病態”),轉而擁抱以希臘羅馬為范式的古典派。魏瑪古典文學時期亦由此到來。
作為貴族制的“死忠粉”和鐵桿保皇派,雖然歌德未能像埃德蒙·伯克那樣寫出論法國大革命的傳世之作,但他的立場卻是一以貫之:用他在《文學上的無套褲主義》(或譯《文學的激進共和主義》)一文中的話說,即任何革命性的變革在德國既無必要也不受歡迎。大約在1790年,他在《威尼斯格言詩》中寫道:“法國的悲慘命運,大人物要考慮!小人物更應好好考慮。/大人物沉淪了,誰來保護群眾/不受群眾的攻擊?群眾是群眾的暴君。/”在他看來,相比于精英統治(即貴族制,Aristocracy)“少數的暴政”,大眾統治(即民主制,Democracy)“多數的暴政”殺傷力更大,對社會的破壞性更強。因此,在歌德眼中,像他筆下的威廉·邁斯特一樣,通過教化(Bildung)約束普通群眾的人性之惡,是社會走向進步和完善的唯一途徑。和后來的馬克思一樣,歌德認為與其他歐洲國民相比,德國人甘于服從威權,平庸且固執,市儈氣十足。在這樣的社會土壤中,歌德斷言,任何政權形式的變更,無非是新舊暴君的更迭,許多時候甚至“一代不如一代”。
從這個意義上說,歌德不贊成乃至反對法國革命,并不能證明他是舊秩序的維護者和舊制度的捍衛者(或如恩格斯所言是“謹小慎微”的庸人),相反,乃是因為他固守自己的信念,即所謂革命根本無法解決“人壓迫人的局面”,其結果不僅不能推動社會進步,反而會破壞“原有美好的東西”,造成禮樂崩壞甚至人類歷史的倒退。
歌德晚年在與艾克曼的談話中重申:“這是真的,我不可能是法國大革命的朋友,因為它的恐怖行為離我太近了,每時每刻都使我感到憤怒,而它的好處當時還看不出來。革命在法國是一個偉大必然的結果,而在德國卻有人要人為地制造類似的革命局面,這我就不能置之不理。”但令人遺憾的是,歌德的政治立場并不能被他的友人理解和接受,1780年9月,在寫給女友兼情人施泰因夫人(1742-1827)的信中,歌德形容自己是一只“懷抱著良好愿望沖進水中的鳥,眼看就要溺水身亡,這時,天神將它的翅膀逐漸變成了鰭。那些圍繞著它的、幫助它的魚兒不明白,為什么它在他們的環境里不能立刻感到愜意”。
為了說服他的朋友(以及民眾),十八世紀九十年代以后,歌德的文學創作明顯轉向關注現實社會問題和政治局勢——這一時期的作品大多與法國革命密切相關,誠如歌德本人所言,“具有世界史意義的當下完全占據了我的精神”。因此,離開法國大革命這一歷史背景,后世讀者便很難真正理解這些作品。
以《大科夫塔》(1792)為例。故事背景是法國大革命爆發前震驚歐洲的“王后鉆石項鏈”丑聞——涉案人員包括王后安托瓦內特、紅衣主教羅昂以及一班宮廷貴婦,結果上述諸人統統被一名叫做大科夫塔的騙子玩弄于股掌之中。最后朝廷迫于壓力,不得不將騙子無罪開釋——當天巴黎民眾紛紛涌上街頭表示慶祝。歌德暗示,法國宮廷腐敗如此,人心盡失,大革命之禍亂已近在咫尺。
再以《平民將軍》為例。在戲劇結尾,鄉村貴族出面制止對暴民的瘋狂報復,并宣稱他雖然反對革命,但他同樣也反對過激的反革命。按照這位貴族的理解(事實上是歌德本人的觀點):革命應當避免而且可以避免;但要避免革命,首先必須消除階級對立,讓社會各階層和諧共處,各盡所能:比如政治歸于公爵,戰爭歸于貴族——歌德假劇中人物之口暗示:自中世紀以來,戰爭抑或和平,向來是貴族之義務,與民眾并無太大關系。
在另一部戲劇《被煽動的人們》中,歌德描繪一位大革命期間到訪巴黎的公爵夫人受到感化后,決定放棄此前她竭力維護的家族特權(她意識到下層階級發動革命乃是“權貴多行不義的結果”),轉而更多“考慮田莊農民的利益”。她在對農民談話中表示,此后面對任何不公正——不管發生在她的領地之內,還是領地之外,哪怕在宮廷——她都會挺身而出,不再害怕別人送她“一個民主派的稱號”。她堅信,位高者權重(noblesse oblige),掌權之人理應更具公平正義和寬容的胸襟懷抱。公爵夫人注意到,自路易十四以來,法國絕對君主專制存在一大弊端:巴黎是唯一的文化中心,其余地方(統稱外省)則處于黑暗蒙昧之邊緣。從某種意義上說,歌德本人正是出于對中央集權專制的厭惡,才選擇了魏瑪公國——在歌德看來,與大一統的法蘭西不同,政治上分散的德意志邦國恰恰能夠保持文化的普遍繁榮和多樣性。這就是歌德日后倡導的“文化世界主義”——根據他的看法,文化民族(Kulturnation)是人類社會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而國家民族(Staatsnation)則是狹隘民族(民粹)主義的產物:它過分夸大民族差異,鼓吹民族仇恨,最終不可避免地導向民族戰爭。照艾克曼的記載,歌德晚年對此仍耿耿于懷:“民族仇恨是一個怪物。——您會發現在文化程度最低的地方,民族仇恨總是最強烈。可是達到了一定的文化程度以后,民族仇恨就消失了;這時人們在某種意義上已經超越了民族,已經感到鄰國人民的幸福和痛苦就是自己的幸福和痛苦。”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歌德“瞧不起民眾”——認為他們不僅智力低下,而且立場搖擺(“如墻頭之草”)——并且斷言“群眾和大多數人的想法總是荒唐和錯誤的”,但正如他在歷史劇《埃格蒙特》(1787)中所言,他始終認為政權的合法性必須來源于“普遍民意”(即盧梭所謂“公意”)。他在與艾克曼談話中曾嚴肅指出,“我從來不是專制統治的朋友,我完全相信,任何一場偉大的革命都不是民眾的過錯,而是政府的過錯。只要政府始終公正,始終清醒,能通過及時的改革應對革命,而不是與之對抗,直到引起來自下層的壓力,革命就不可能發生”。這也是歌德一貫的立場——早在1778年,歌德在致施泰因夫人的信中不無憤慨地寫道:君主(及官僚)專制國家猶如一座龐大的“鐘表”機器,它把每個活生生的人變成了零件和“木偶”,使得整個社會陷入僵化、停滯狀態。因此,歸根結底,包括法國大革命在內,歷史上“任何一場大革命的責任都不在民眾,而在政府”。
1805年,席勒因肺結核病逝,歌德哀嘆“我失去了一半的存在(existence)”。隨后,他辭去一切公職,潛心著作。1823年春,歌德大病一場,自認將不久于人世,康復后便著手整理他與席勒的通信(Correspondence Between Goethe and Schiller 1794-1805)。1832年3月,歌德給老友威廉·洪堡(1767-1835)寫信:“請原諒這封遲到的書信。即使我隱居在離大家很遠的地方,也還是很難找到時間來認真思考生活的全部秘密。”早年洪堡在耶拿與席勒共同編輯文藝期刊《時序女神》(Horen),后赴首都創辦柏林大學(即今日柏林洪堡大學)——據傳記作家考證,這是歌德臨終前最后一封重要信件。
同樣重要的,還有他臨終前念茲在茲的一份聲明:“……因為我仇視革命,就說我是現行秩序的朋友,這是一種含糊不清的說法。我不允許別人強加給我這樣一個頭銜。”歌德畢生對“民主”持懷疑態度,更憎惡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主張通過政治協商實現社會改良和進步,但歌德絕非“歌德派”,亦非刻意“遠離政治”(“distance himself from politics”,《不列顛百科全書》語)的庸人。從這一視角重新審視歌德與法國大革命,或許能給后世更多鏡鑒和啟迪。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