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482封信,一個(gè)上海女人漂泊在香港的20年

采訪、撰文 | 孫思
十點(diǎn)人物志原創(chuàng)
60年代,定居美國(guó)的張愛(ài)玲回憶從內(nèi)地赴港時(shí)的情景:
我們火車(chē)上下來(lái)的一群人過(guò)了羅湖橋,把證件交給鐵絲網(wǎng)那邊的香港警察。拿了去送到個(gè)小屋去研究,就此音信杳然。正是大熱天,我們站在太陽(yáng)地里等著。
……站崗的兵士就在我們旁邊,一個(gè)腮頰圓鼓鼓的北方男孩,穿著稀皺的太大的制服。大家在灼熱的太陽(yáng)里站了一個(gè)鐘頭之后,那小兵憤怒地咕嚕了一句,第一次開(kāi)口:“讓你們?cè)谕忸^等著,這么熱!去到那邊站著。”他用下顎略指了指后面一箭之遙,有一小塊陰涼的地方。
我們都不朝他看,只稍帶微笑,反而更往前擠近鐵絲網(wǎng),仿佛唯恐遺下我們中間的一個(gè)。但是仍舊有這么一剎那,我覺(jué)得種族的溫暖像潮水沖洗上來(lái),最后一次在身上沖過(guò)。
那是1952年7月的一天,內(nèi)地人士出入香港已不如早幾年便捷。前一年,兩地政府先后發(fā)布規(guī)定,內(nèi)地居民前往香港需持公安機(jī)關(guān)簽發(fā)的通行證。張愛(ài)玲以繼續(xù)港大學(xué)業(yè)為由到派出所申請(qǐng)出境,“警察一聽(tīng)說(shuō)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臉來(lái)”,“幸而調(diào)查得不很徹底,沒(méi)知道我寫(xiě)作為生,不然也許沒(méi)這么容易放行”。
那一年她32歲,至死再未踏足內(nèi)地。
四年后的1956年,另一個(gè)32歲的上海女人就沒(méi)那么幸運(yùn)了。申請(qǐng)不到通行證,她只好另尋辦法,揀了條曲折些的路線,在路上多奔波幾日:上海出發(fā),火車(chē)坐到廣州,然后去珠海拱北過(guò)關(guān)至澳門(mén),再?gòu)陌拈T(mén)坐船到香港。
10月4日下午,客輪從澳門(mén)內(nèi)港碼頭緩緩起航,經(jīng)4小時(shí)向東橫穿伶仃洋,最終靠岸香港上環(huán)港澳碼頭。女人著一身深色衣服,只帶了些簡(jiǎn)單的行李,下船上岸,在碼頭張望張望,很快便與來(lái)接她的人碰上了頭。
一番接風(fēng)寒暄,街頭的霓虹燈在傍晚亮起,她隱入車(chē)水馬龍里。
正如這位無(wú)名的上海女性,縱使邊境政策日漸收緊,那幾年里,通過(guò)各種方式抵港的異鄉(xiāng)客依舊源源不斷,二戰(zhàn)結(jié)束至50年代中期,香港人口激增近200萬(wàn)。但除非如張愛(ài)玲這般出人頭地,其中大部分人的故事,將埋沒(méi)于時(shí)間長(zhǎng)軸之中。
在歷史的陰影面,他們中的每一個(gè)個(gè)體 ,后來(lái)都有了怎樣的故事?譬如這個(gè)從海上來(lái)的上海女人,她來(lái)香港做什么?她在港停留了多久?她的人生是否因此變化?
………
2013年11月,山西收藏家劉濤到上海文廟舊書(shū)市場(chǎng)淘寶,市場(chǎng)東南角的臺(tái)階上,有家攤位擺放的東西吸引了他。那是厚厚一沓書(shū)信,他數(shù)了數(shù),共計(jì)8大冊(cè),已全部按時(shí)間順序整理裝訂好。攤主開(kāi)價(jià)1500元,劉濤砍價(jià)到900元,他至今記得,攤主特意打了通電話,征得電話那端的人同意后才賣(mài)給他。
482封信,60余萬(wàn)字,1956年10月5日始,1976年12月12日止——從這些舊紙堆里,我們知道了,原來(lái)那年上岸的上海女人名叫周素錦,這些書(shū)信,是她和她留在上海的妹妹素美長(zhǎng)達(dá)二十年的往來(lái)。
多年以來(lái),劉濤一直整理研究這批書(shū)信。2022年,他和山西作家好友百合共同商定寫(xiě)作框架,由百合執(zhí)筆寫(xiě)作完成4萬(wàn)多字的《素錦的香港往事》一文,發(fā)布在《讀庫(kù)》202202期,獲得當(dāng)年“收獲文學(xué)榜”非虛構(gòu)類(lèi)第二名;2023年,百合將其擴(kuò)充成14萬(wàn)字同名書(shū)籍,由中華書(shū)局出版。

素錦的人生,同她折射出的半個(gè)多世紀(jì)前的香港庶民生活,經(jīng)由兩個(gè)山西人之手,幸運(yùn)地走出歷史的陰影面,在陽(yáng)光下緩緩鋪展開(kāi)。
這是一個(gè)關(guān)于等待和希望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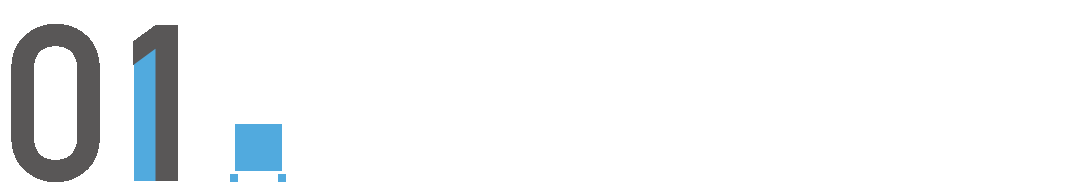
傳統(tǒng)女性的路徑依賴(lài)
“媽媽已于四日下午平安抵港,一切都好,勿念。今天我已看見(jiàn)你爸爸,現(xiàn)在還沒(méi)有結(jié)論……”
起初,這很像一個(gè)傳統(tǒng)女性不幸的宿命:遇人不淑,慘遭拋棄,討要錢(qián)財(cái),養(yǎng)活子女。開(kāi)篇第一封,便是素錦寫(xiě)給當(dāng)時(shí)上海政府的赴港申請(qǐng),大體勾勒出她赴港前的窘迫狀況:
“我于十九歲時(shí),因家庭生活苦難,父親去世甚早,母親身弱,弟妹幼小,一家無(wú)依,為生活逼迫,只得進(jìn)入舞場(chǎng)伴舞。后遇章文勛,愿負(fù)擔(dān)我一家生活 ,我也急欲脫離惡劣環(huán)境,就與之同居。后我母親亡故,妹也結(jié)婚,弟于一九五一年參干,現(xiàn)在朝鮮。現(xiàn)我在上海無(wú)親無(wú)故,只有子女三人。
章文勛于一九五零年七月赴港后,于一九五零年十一月曾來(lái)滬攜領(lǐng)其妻兒一同赴港,其走時(shí),我也不知。后其來(lái)信曰,我們的生活費(fèi)由他每月匯來(lái)家用,我因無(wú)一技能,只得教養(yǎng)子女。……自一九五三年起,匯款經(jīng)常脫期……生活也已感入不敷出……所以目前我的生活確實(shí)陷于萬(wàn)分困難,實(shí)難維持,借貸無(wú)門(mén)……只得赴港以解決三個(gè)子女的生活問(wèn)題。”
父親去世,家道中落;19歲被迫當(dāng)舞女,遇到富商章文勛,匆匆忙忙做了小;后來(lái)丈夫帶著正室一家跑路,答應(yīng)的生活費(fèi)也沒(méi)了蹤影。就像小說(shuō)的楔子,這半封信濃縮了素錦前32年的人生。顯然,她的申請(qǐng)沒(méi)能通過(guò),這才有了后來(lái)借道澳門(mén)的經(jīng)歷。

電影《半生緣》劇照
和小說(shuō)劇情曲折不同,找到負(fù)心人的過(guò)程并不復(fù)雜。抵達(dá)香港的第二天,在親戚的陪同下,素錦就和章文勛在一家咖啡館見(jiàn)了面。夫妻六年來(lái)第一次相見(jiàn),章只是坦白,“我現(xiàn)在生活困難,無(wú)法負(fù)擔(dān)你們的生活”,表示自己的生意要等六個(gè)月才能看出好壞。他還叫素錦先回上海,“假如條件好些,孩子接出來(lái)在港居住”。
冷臉聽(tīng)完章文勛的話,素錦也知道,這些無(wú)非空頭支票,于是她決定,要在香港暫住下來(lái),在章的眼皮底下等出個(gè)結(jié)果。她寫(xiě)信給妹妹素美,希望她和妹夫暫且?guī)兔φ湛慈齻€(gè)孩子:
“如若過(guò)了一個(gè)時(shí)期,章如仍無(wú)信息,我立即返滬,現(xiàn)在種種拜托你們,容后再謝了……”
但誰(shuí)也沒(méi)料到,等著等著,就等過(guò)了二十年。素錦和章文勛在香港若即若離搭伙過(guò)了二十年,素美和妹夫也兢兢業(yè)業(yè)照顧了姐姐的三個(gè)孩子二十年。
這二十年里,章文勛飛往全球各地做生意,不順的時(shí)候居多,手頭時(shí)緊時(shí)松。于是錢(qián)總是艱難地從章的口袋里掏出來(lái),不定期交給素錦作為“側(cè)室”的生活費(fèi),再艱難地從素錦牙縫里摳出來(lái),她省吃?xún)€用,剩余大部分源源不斷地匯往上海的大家庭。
在香港的前兩年,素錦住在小姑姑家里。章文勛見(jiàn)她不走,香港生意圈子又小,不想落個(gè)“拋妻棄子”的名聲,會(huì)時(shí)不時(shí)登門(mén)拜訪,與素錦一道吃飯看電影。但絕口不提生活費(fèi)的事,素錦的應(yīng)對(duì),只是耐著性子磨下去。
1958年1月31日,素錦來(lái)港的第三年,章文勛終于給了她第一筆生活費(fèi),200元港幣。這讓她意外欣喜,第二天就興沖沖給妹妹寄去100元;4月,又是200元,素錦全部寄出。
1958年九十月間,章文勛給素錦租了一間小房間單住。這讓她看到一絲希望,在信中感慨,“……終是慢慢來(lái)的,現(xiàn)在比去年、前年終好點(diǎn)”。章文勛的門(mén)檻還是很精,在素錦身上多花一筆房租,每月生活費(fèi)就降50元,素錦只得精打細(xì)算,每分錢(qián)花在刀刃上,存下一大半給孩子們。
1964年,章的生意全年無(wú)起色,素錦一共只收到20元,但在春節(jié)前夕,她還是從章那里逼出100元,統(tǒng)統(tǒng)寄回上海。特定年代,上海情況也不好,素錦安撫妹妹:“望你不要心中焦急,身體保重為要,耐心一點(diǎn),我一有辦法立刻先匯給你們。”

電影《半生緣》劇照
一直要等到70年代,全球經(jīng)濟(jì)復(fù)蘇,章的生意也隨之好轉(zhuǎn)一些,他每個(gè)月給素錦1000元,香港和上海兩地的家用都包含在內(nèi)。
素錦是如何分配的呢?給上海的,固定250元生活費(fèi)和50元硬性?xún)?chǔ)蓄金,還有逢年過(guò)節(jié)、親戚過(guò)生日、添置衣物等費(fèi)用,算下來(lái)每月高達(dá)五六百元;后來(lái)三個(gè)子女相繼進(jìn)入婚育年齡,又追加每月100元的結(jié)婚儲(chǔ)備金。
而她自己在香港過(guò)著怎樣的生活?過(guò)期面包也不舍得丟,開(kāi)水泡一泡繼續(xù)吃。
經(jīng)濟(jì)上要倚賴(lài)章文勛,那么無(wú)論是否情愿,素錦都只能對(duì)他笑臉相迎,體貼隱忍。有次章文勛糖尿病發(fā),素錦整三個(gè)月里每天起早買(mǎi)食材、熬中藥,服侍一日三餐,累得夠嗆。經(jīng)濟(jì)不能獨(dú)立的傳統(tǒng)女性,事夫君被認(rèn)為理所應(yīng)當(dāng),素錦明白這是一種交換,如她在信中抱怨的:
“我知道我現(xiàn)在是忍受的時(shí)候,那是應(yīng)該忍耐的。有什么別的方法呢?除非我自己有本事能自力更生,經(jīng)濟(jì)獨(dú)立。”
她也不是沒(méi)嘗試過(guò)自力更生。60年代初,她短暫進(jìn)工廠做過(guò)塑膠花,還當(dāng)過(guò)茶餐廳服務(wù)員,但都沒(méi)能長(zhǎng)久。外地女人,年紀(jì)偏大,無(wú)一技之長(zhǎng),語(yǔ)言又不好,在勞動(dòng)力過(guò)剩的香港沒(méi)有優(yōu)勢(shì)。一番嘗試無(wú)果,她也只好回歸家庭,坐在出租屋里繼續(xù)緊衣縮食。
根據(jù)信中提及的數(shù)據(jù),1956年到1966年,素錦共寄去2632元港幣,1966年到1976年,則共寄去33900元港幣、1000元人民幣。
匯率換算后粗略估計(jì),她平均每年寄回1000多元人民幣,而根據(jù)《上海通志》,同時(shí)期上海市職工年平均工資也不過(guò)600-800元。除了錢(qián)款,在內(nèi)地物質(zhì)匱乏時(shí)期,她還多次寄去白糖、罐頭、澳洲牛油、福建肉松……
然而前方吃緊,后方緊吃。三個(gè)孩子對(duì)素錦省出來(lái)的錢(qián)不甚愛(ài)惜,他們仗著自家爸爸是“香港大經(jīng)理”,衣服要買(mǎi)頂新式樣,手表自行車(chē)也要國(guó)外名牌。例如素美在一封信里提到,妹夫曾為素錦兒子小慶花204元買(mǎi)了只手表,小慶嫌老氣,不稱(chēng)心,非要再買(mǎi)新的。
70年代,三個(gè)孩子相繼參加工作,家中經(jīng)濟(jì)壓力變小,素美幾次勸姐姐,不必再寄那么多錢(qián)了。素錦呢,只是一邊答應(yīng)“我不再另外寄衣服錢(qián)了”,一邊又借著各種理由,在下一次匯款時(shí)增添新的門(mén)類(lèi)。
“為了這三個(gè)小赤佬,我傾注了我的全部積蓄。”
這二十年里,素錦始終沒(méi)有忘記當(dāng)初來(lái)港的目的。后來(lái) ,這又變成了她為自己抓住的,存在的意義。

從上海女人到香港市民
剛到香港的頭幾年,素錦不太喜歡這座城市。囊中羞澀的她早早認(rèn)清這里金錢(qián)開(kāi)路的本質(zhì):
“香港這地方現(xiàn)實(shí),窮一點(diǎn)和沒(méi)有好處給人家,連鬼也不睬你。朋友是用錢(qián)結(jié)交,才來(lái)來(lái)往往,想沾人家的光?你想也不要想,都是彼此利用,用過(guò)算數(shù),沒(méi)有什么交情不交情的。”
香港人應(yīng)酬習(xí)慣AA制付帳,這是素錦不能接受的,“有錢(qián)的人也不肯請(qǐng)人的,沒(méi)有錢(qián)的人也不能不還”,她覺(jué)得既浪費(fèi)錢(qián)又無(wú)聊。提到香港社會(huì)快節(jié)奏,她又形容,“此地人人都像吃火藥似的”。
總而言之,不如舊上海老派體面優(yōu)雅。
從親戚家搬出后,素錦的第一個(gè)住處位于港島北角,那是老上海人聚居的地區(qū)。即便日子過(guò)得緊迫,每逢出街,她都要穿得整整齊齊,頭是頭,腳是腳,打理得井井有條。上海女人,體面能干的形象要立住,她對(duì)此頗為得意,“人們或以為我是個(gè)有錢(qián)人,有眼有白的。”
但久居香港二十年,異鄉(xiāng)的風(fēng)土人情潛移默化間,終歸影響了這位上海女性,使她的觀念發(fā)生改變。1962年,她在跑馬地一家名為特美華的茶餐廳做服務(wù)員,這段經(jīng)歷,讓她看到香港商業(yè)社會(huì)的可取之處。

電影《半生緣》劇照
在寫(xiě)給妹妹的信里,素錦把老板一家都夸獎(jiǎng)一通:老板十分擅長(zhǎng)成本控制,進(jìn)貨又便宜又保質(zhì);老板娘精通九國(guó)語(yǔ)言,可以接待各國(guó)來(lái)客;少東家放暑假來(lái)店里做工,和大家一樣上滿(mǎn)時(shí)長(zhǎng),干一樣的活,領(lǐng)一樣的工資,這讓素錦不禁反思,自己對(duì)孩子是不是過(guò)于溺愛(ài)了?
做服務(wù)員的日子,素錦體驗(yàn)到揾錢(qián)不易,每日早出晚歸,工作時(shí)間超過(guò)12個(gè)小時(shí),到手的錢(qián)卻寥寥,大頭都去交了房租。于是她理解了香港人的金錢(qián)至上觀:
“都是辛勤勞苦的工作,即使大資本家也是一錢(qián)如命,因?yàn)橘嶅X(qián)是難,所以每個(gè)人都是這樣的觀念。”
后來(lái),大家把這代港人的努力奮斗、同舟共濟(jì)稱(chēng)為“獅子山精神”。時(shí)代精神成就了香港國(guó)際大都市的傳奇,素錦也曾為此出過(guò)一份力,參與歷史的進(jìn)程。
而這座城市六七十年代的波瀾起伏,素錦也和幾百萬(wàn)香港市民一道,是親歷者和見(jiàn)證者。
1962年8月31日,強(qiáng)臺(tái)風(fēng)溫黛來(lái)襲,導(dǎo)致香港183人死亡,108人失蹤,388人受傷,7萬(wàn)多人無(wú)家可歸。素錦獨(dú)自一人在高樓里面對(duì)溫黛,留下記錄:“我住的是八樓,很高,對(duì)面房子很低,所以更加臨空,風(fēng)力更大,結(jié)果是二塊玻璃被風(fēng)吹去,百葉簾也被吹落……我和房東都走下底層去,因風(fēng)吹得害怕,像房子要倒一樣。”
1962-1963年,香港遭遇水荒,供水從每天4小時(shí)逐漸變成每四天4小時(shí)、每四天2小時(shí)、直至每四天1小時(shí)。素錦那時(shí)下班晚,常常工作出一身汗卻無(wú)法痛快洗澡。此種窘迫狀況,要等1965年?yáng)|江引流入港的”東深供水工程”完全竣工后,才得以徹底解決。
1967年11月,英鎊對(duì)美元大貶值,香港物價(jià)飛漲,素錦再節(jié)儉也力不從心。她向素美說(shuō)明情況,表示不能保證在春節(jié)增加匯款。“因生活費(fèi)上漲,我極難再撙節(jié)剩余多加寄你,望見(jiàn)諒……講來(lái)講去都是講錢(qián),這也是實(shí)情。”
1973年,香港股市最大股災(zāi),恒生指數(shù)一年內(nèi)跌去九成。那時(shí)人人炒股,一向謹(jǐn)慎的素錦也未能幸免,虧錢(qián)后她日日以淚洗面,夜夜失眠,香港市民的慘狀如她所說(shuō)的:
“沒(méi)有一個(gè)不做大閘蟹,被股票綁死。打腫面充胖子,撐的住的硬撐,撐不住的叫苦連天,個(gè)個(gè)都扎死了,借也沒(méi)處借。”
漸漸的,素錦已然是一位香港市民了,吃腸粉吃云吞面,喜歡算命看風(fēng)水,兩個(gè)女兒年紀(jì)大了但戀愛(ài)不順利,她反而贊賞她們似港女硬頸:
“寧愿她自己的硬氣表現(xiàn)那是對(duì)的……兩個(gè)女孩的婚姻都不順利,焉知非福呢?不必心急,不要遷就而讓人占上風(fēng),做人應(yīng)當(dāng)強(qiáng)之處應(yīng)剛強(qiáng)。”
1976年,52歲的素錦迎來(lái)了她到香港后最重要的一件事——章文勛為她買(mǎi)了一套房。軒尼詩(shī)大廈16樓D座,實(shí)用面積大約五六十平,五年內(nèi)分期付款還清。
“總算心定了,搬定了。”

香港軒尼詩(shī)大廈 作者攝
房子對(duì)中國(guó)人的意義毋庸置疑,搬家6次后,她終于在這座城市有了落腳點(diǎn)。寫(xiě)給素美的信里,她高興中略帶點(diǎn)嬌嗔的抱怨,說(shuō)前幾年為了給孩子們寄錢(qián),錯(cuò)過(guò)了低房?jī)r(jià),現(xiàn)在買(mǎi)貴了點(diǎn);轉(zhuǎn)而又祈禱章文勛身體健康,事業(yè)有新發(fā)展,能夠平平安安幫她把房貸供完。
此刻她不知道,她將很快搭上這座城市的又一輪財(cái)富快車(chē)道。
根據(jù)目前可查到的最早數(shù)據(jù),軒尼詩(shī)大廈16樓D座于1996年進(jìn)行過(guò)一次交易,售價(jià)196萬(wàn)元。也就是說(shuō),至少在1996年之前,素錦就已經(jīng)將這套房子出售。而1976年至1996年間,香港樓市經(jīng)歷多輪上漲,價(jià)格翻了好幾番。如無(wú)意外,她在這筆理財(cái)中賺到了錢(qián)。

對(duì)于香港市民周素錦來(lái)說(shuō),這可能是這座城市給她的一次回報(bào)。不知道這次她有沒(méi)有把握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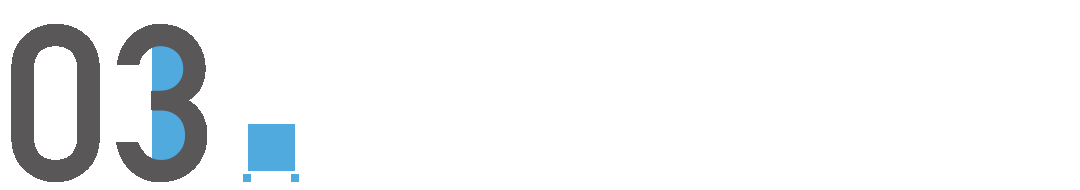
等天空轉(zhuǎn)晴
二十年里,素錦不止一次暢想過(guò),她順利把孩子接到香港后的生活。
1962年,大女兒蓼芬18歲,素錦為她的前途謀劃:“蓼芬能考取大學(xué)是最好,現(xiàn)在的社會(huì)進(jìn)展是以資格而論了,凡是沒(méi)有專(zhuān)門(mén)的技術(shù)和高深的教育,以后要在社會(huì)上謀進(jìn)取實(shí)在是太難了。”
她想好了,如果女兒考不上大學(xué),就把她接來(lái)香港,再去求茶餐廳老板給女兒一份工作。母女倆一起在餐廳做工,付一份房租掙兩份錢(qián),減輕上海的經(jīng)濟(jì)負(fù)擔(dān)。等情況穩(wěn)定了,再把剩下兩小兒接來(lái)。
眼前的困難是女兒來(lái)港的路費(fèi)。章文勛家室多,人還總往外面跑,指望不上,素錦想到了對(duì)她頗有情義的張先生。這位張先生,是她在香港認(rèn)識(shí)的新朋友,性格樂(lè)善好施,同情素錦一家的遭遇,曾幾次資助她房租及其他費(fèi)用。接到素錦的求助,張先生表示,愿意承擔(dān)大女兒小女兒的路費(fèi),外加一年生活費(fèi)。
然而計(jì)劃最終未能成行。蓼芬落榜了,節(jié)骨眼上,素錦自己卻失業(yè)了,母女倆的工作沒(méi)了著落。恰好章文勛又從國(guó)外回來(lái),她和張先生也沒(méi)了下文。不知是安慰自己還是想通了,素錦在這期間的一封信里寫(xiě)道:
“蓼芬來(lái)香港,很容易走上歧路,我自己已經(jīng)哭了多少年才明白,沒(méi)有地位、沒(méi)有名義的人,輪不到經(jīng)濟(jì)和權(quán)力的一切權(quán)利,因此不想孩子再走我的路,做人家的小。”
進(jìn)入60年代中后期,三個(gè)孩子在上海陸續(xù)被分配了工作,素錦在香港的狀況不見(jiàn)起色,她也只得無(wú)奈接受命運(yùn)的安排:
“有時(shí)候想到做不到的事,世界上實(shí)在太多。我根本是想他們來(lái)香港的,可是不如意的事偏偏常八九,我有什么再說(shuō)和再想呢?”

電影《半生緣》劇照
1966年時(shí)局突變,6月到10月間,素錦和素美整整4個(gè)月沒(méi)有通訊。10月24日,素錦來(lái)信,也只作簡(jiǎn)單問(wèn)候,“不知你們近來(lái)可好,孩子們好嗎?你和妹夫身體可有好轉(zhuǎn)和健康嗎?”
這是四百多封信中最短的,只有四五行。寥寥數(shù)語(yǔ),背后每個(gè)字都戰(zhàn)戰(zhàn)兢兢。
兩姐妹有默契, 在信中從不談時(shí)局,但保持政治敏感。譬如素美在那段時(shí)間寫(xiě)道,“如無(wú)事,今后就少來(lái)信與我們,我認(rèn)為亦然,吾姊應(yīng)多注意休養(yǎng)而少耗腦力,希擅自珍攝”。素錦心領(lǐng)神會(huì),回信道,“有事再來(lái)信,沒(méi)有事我也少寫(xiě)信。”
但無(wú)論如何,此后十年間,接子女來(lái)港或是回上海探望的計(jì)劃都擱淺了。素錦故事里的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件事,團(tuán)聚。
時(shí)間慢慢熬過(guò)去,子女們都日漸長(zhǎng)大,素錦在信中見(jiàn)證他們工作、戀愛(ài)、結(jié)婚。1973年,小女兒小芬找了一個(gè)右派家庭男友,急得素錦要回上海,被素美阻攔,“并不是我們不歡迎你來(lái),我也很難講,請(qǐng)?jiān)龠^(guò)一個(gè)時(shí)期看。”
1975年左右,政策松動(dòng),再加上大女兒蓼芬結(jié)婚,素錦終于得以返滬探親。通過(guò)中國(guó)旅行社辦好回鄉(xiāng)手續(xù),她于9月23日上午由尖沙咀坐火車(chē)至深圳中轉(zhuǎn),兒子小慶前往迎接。1956年素錦走時(shí)小慶還是一個(gè)8歲孩童,如今再見(jiàn),眼前已是二十多歲的成年男子。
母子倆當(dāng)天在廣州華僑飯店住宿一晚,24號(hào)火車(chē)再度啟程,于26日下午5點(diǎn)抵達(dá)上海火車(chē)站。此時(shí)距素錦離滬赴港,已過(guò)去整整十九年。書(shū)信中沒(méi)有提及再度見(jiàn)面時(shí)的場(chǎng)景,但想必難免生出滄海桑田的感慨。
半個(gè)月后,素錦返回香港,縱有不舍,那里如今才是家。
第二年4月,素錦再返內(nèi)地,這次是邀請(qǐng)妹妹和兩個(gè)女兒同游廣州。還記得在1965年4月的一封信里,素錦感慨作為女人在時(shí)代中浮游的身不由己:
“這些年來(lái)的周折情形,使我歷歷在目,我真覺(jué)得一個(gè)人的生存,在世上生活,尤似戰(zhàn)士打仗,有時(shí)是失敗,有時(shí)也有成功,愿蓼芬和小芬以后的生活不要像我這樣的困難不如意。”
此次兩代女性出游,期間相處親密愉快,旅途中少不了長(zhǎng)輩對(duì)下一代的祝愿和期許。
這一年的9月13日,素美來(lái)信,頂部一行字:“極其沉痛悼念偉大領(lǐng)袖毛主席。”
一天后素錦回復(fù):“最近港地也竟載毛主席逝世之報(bào)道,各階層也深哀悼,我們雖小市民,看到電視中瞻仰遺容,也流淚不已,心中哀傷。”
這年年底,素美不再保留往來(lái)書(shū)信的底稿。一個(gè)時(shí)代過(guò)去了。子女來(lái)港團(tuán)聚的事再次被提上了日程,素美表示無(wú)條件支持。
自1956年出發(fā),距離素錦想要抵達(dá)的那一天,越來(lái)越近了。為了那一天,她已經(jīng)足足拼爭(zhēng)二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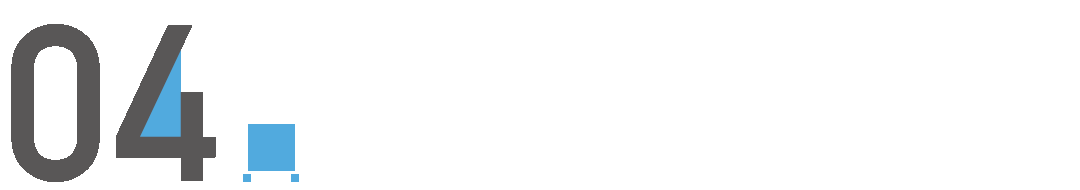
就停留在這里
兩姐妹的書(shū)信,就停留在了1976年的12月12日。如往常一樣,素錦不厭其煩交待著,寄來(lái)的錢(qián)如何安排,并閑聊在香港的生活。
“日子過(guò)得快得很,一年又將過(guò)去了,就要1977年了。……香港的生活越來(lái)越緊張,什么事都要趕快,生活我也只望章身體健康……望大家都是身體健康。”
故事戛然而止。這一家人后面的生活如何?結(jié)局圓滿(mǎn)嗎?——讀者好奇,作者劉濤和百合也好奇。
購(gòu)入這批書(shū)信之后,劉濤一直在嘗試著尋找素錦后人。“我收集的普通人書(shū)信非常多,一般來(lái)說(shuō),找到它們的主人或者后人,是必須要走的一步流程。”人找到了,關(guān)于書(shū)信的疑問(wèn)才能得到解答,也方便對(duì)書(shū)信進(jìn)行合理開(kāi)發(fā)和再次創(chuàng)作。
2022年,媒體《故事FM》曾在香港、美國(guó)、上海三地尋找素錦后人的線索。
在香港,素錦工作過(guò)的茶餐廳早已不見(jiàn),章文勛任職過(guò)的公司也沒(méi)有線索。唯一可確定的,是他們?cè)谲幠嵩?shī)大廈購(gòu)入的那套房子。但房子幾經(jīng)易手,如今屋內(nèi)住的不是素錦家人。委托香港本地媒體調(diào)查,后續(xù)也沒(méi)有音訊。

香港風(fēng)光 作者攝
美國(guó)的線索主要依托于素錦的大弟弟元陵。上個(gè)世紀(jì)60年代,從臺(tái)大畢業(yè)后,元陵去美國(guó)攻讀博士,《故事FM》嘗試咨詢(xún)臺(tái)大北美校友會(huì),還付費(fèi)查詢(xún)了美國(guó)尋人網(wǎng)站,都如大海撈針,沒(méi)有下文。
唯一有進(jìn)展的是上海。素錦的妹夫是一位翻譯家,劉濤托人得知,妹夫有一個(gè)侄子,現(xiàn)今是滬上小有名氣的書(shū)法家。劉濤鼓足勇氣登門(mén)拜訪,打聽(tīng)素錦一家人的去向,終于得知:
改革開(kāi)放后,三個(gè)孩子陸續(xù)去了香港,有一個(gè)最后還去了美國(guó)。
但當(dāng)劉濤繼續(xù)追問(wèn)素錦子女的聯(lián)系方式,書(shū)法家先生拒絕了。因此,目前所有關(guān)于素錦的內(nèi)容,都對(duì)當(dāng)事人的信息做了模糊處理。
作為《素錦的香港往事》一書(shū)的作者,也作為一名女性,作家百合更能體會(huì)這其中的微妙。她隱約擔(dān)心過(guò),關(guān)于尋找后人這件事,會(huì)不會(huì)是一個(gè)潘多拉魔盒?她建議,不要去打開(kāi)它。
“和素錦的故事相遇是緣分,二十年結(jié)束了,沒(méi)有必要再打擾。”畢竟,清官也難斷家務(wù)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行事風(fēng)格,“下一代人的故事肯定也很精彩,但我們沒(méi)有資料,我們只寫(xiě)這二十年就夠了。”
書(shū)已成稿,素錦的故事是一個(gè)好故事,不必再想象,就讓它停留在這里。百合回想起,自己第一次見(jiàn)到這批書(shū)信的那一天:
那是2021年5月的一個(gè)周六,天下著雨,在劉濤位于太原的辦公室,他拿出一個(gè)大箱子,百合隨手打開(kāi)箱子最上面的那封信,恰好是素錦寫(xiě)給上海市政府的申請(qǐng)信。
讀著讀著,她想起《半生緣》里的曼璐,腦子里當(dāng)即蹦出一段話,也成為了后來(lái)全書(shū)的第一句:
“我知道她的名字,見(jiàn)過(guò)她的字跡,卻不清楚她的模樣;我了解她的人生,洞悉她的脾氣,卻不知曉她的結(jié)局。”

電影《半生緣》劇照
素錦的故事里沒(méi)有驚心動(dòng)魄,那不過(guò)是一個(gè)小人物,被動(dòng)地等待和接受命運(yùn),靠著隱忍和堅(jiān)持托住了自己,終于拼到了一絲光亮。
最后,請(qǐng)用她們的書(shū)信作為結(jié)尾,也作為這個(gè)故事的注腳。那是寫(xiě)于1976年11月12日的一封信,她們馬上要熬出頭,妹妹素美引用《基督山伯爵》里的話鼓勵(lì)素錦:
“在抱有希望的前提下,應(yīng)該有所等待。一位先哲曾告訴我們,人類(lèi)的所有智慧,就是集中在等待二個(gè)字。世上最最偉大的,最最堅(jiān)強(qiáng)的,特別是最最敏慧的,就是知道怎樣有所等待的人。”
原標(biāo)題:《482封信,一個(gè)上海女人漂泊在香港的20年》
本文為澎湃號(hào)作者或機(jī)構(gòu)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fā)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jī)構(gòu)觀點(diǎn),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diǎn)或立場(chǎng),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fā)布平臺(tái)。申請(qǐng)澎湃號(hào)請(qǐng)用電腦訪問(wèn)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yíng)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