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們?nèi)松械暮艽笠徊糠制鋵?shí)是在不同的虛構(gòu)世界度過(guò)的
【編者按】
“虛構(gòu)本質(zhì)上的慷慨是對(duì)人類(lèi)自身有限性的一種補(bǔ)償。”
虛構(gòu)文化在我們時(shí)代的構(gòu)建與擴(kuò)張,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們理解世界和存在于世的方式。《事實(shí)與虛構(gòu):論邊界》是法國(guó)巴黎新索邦大學(xué)比較文學(xué)教授弗朗索瓦絲·拉沃卡的作品,該書(shū)完整地評(píng)估了關(guān)于虛構(gòu)從古至今的爭(zhēng)議,重新思考文學(xué)、電影、戲劇和電子游戲中的虛構(gòu)界限。本文摘自該書(shū)第四章,澎湃新聞經(jīng)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授權(quán)發(fā)布。
發(fā)展心理學(xué)研究很早就對(duì)兒童具有的區(qū)別真實(shí)與想象的能力表現(xiàn)出濃厚的興趣。在1970年代末,研究隨莫里森與加德納(Morison & Gardner 1978)、弗拉威爾(Flavell 1987)、迪拉拉與沃森(DiLalla & Watson 1988)等人的成果進(jìn)一步發(fā)展。這些研究修正了皮亞杰(Piaget 2003 [1926])的理論,提出了兒童本質(zhì)上無(wú)法區(qū)分真實(shí)與想象的假設(shè)。例如沙侖與伍利(Tanya Sharon & Jacqueline D. Woolley 2004: 305)不斷強(qiáng)調(diào)一個(gè)事實(shí),即當(dāng)人們要求幼童明確指出不同虛構(gòu)形象的屬性時(shí),他們經(jīng)常表現(xiàn)出困惑而非直接弄錯(cuò);在3—5歲之間,這種猶豫逐漸消失。耐人尋味的是,兩位作者強(qiáng)調(diào),教育部分地扮演了消極的角色,延遲了這種能力的獲得。在虛構(gòu)實(shí)體的屬性上,父母與教師確實(shí)會(huì)故意給兒童一些錯(cuò)誤信息。關(guān)于判斷與幼年適宜的非現(xiàn)實(shí)主義,西方世界普遍流行著某種文化共識(shí)(Sharon & Woolley 2004)。其他研究者側(cè)重關(guān)注兒童對(duì)虛構(gòu)世界的多樣性及封閉性的感知問(wèn)題,在斯科尼克及布魯姆(Deena Skolnick & Paul Bloom 2006)看來(lái),這種感知構(gòu)成了對(duì)虛構(gòu)世界本質(zhì)的成熟理解。在研究中,斯科尼克與布魯姆向兩組人——一組是兒童,一組是成人——提出了問(wèn)題,有關(guān)一些虛構(gòu)人物對(duì)屬于另一個(gè)世界的其他虛構(gòu)人物的本質(zhì)屬性做出的評(píng)價(jià)。問(wèn)題如下:灰姑娘相信超人的存在嗎?她能看到并摸到超人嗎?實(shí)驗(yàn)者預(yù)期的答案是否定的。兒童如果給出反面的回答,就會(huì)被理解為難以在某種非物理?xiàng)l件下采用他人的視角,因而也就是難以理解虛構(gòu)中之虛構(gòu)的屬性(Skolnick & Bloom 2006: 813)。
尤其在2000年以后,這些研究者表明自己屬于某個(gè)普遍的知識(shí)語(yǔ)境,關(guān)注虛構(gòu)性,并對(duì)其關(guān)鍵作用有很深的認(rèn)識(shí)。他們不斷提醒,我們?nèi)松械暮艽笠徊糠制鋵?shí)是在不同的虛構(gòu)世界度過(guò)的。發(fā)展心理學(xué)領(lǐng)域的專(zhuān)家在事實(shí)與虛構(gòu)差異面前,表達(dá)了某種明顯具有二元論色彩的觀念,認(rèn)為對(duì)這一差異的理解對(duì)兒童來(lái)說(shuō)至關(guān)重要。但他們也沒(méi)有停留于某個(gè)簡(jiǎn)單化的二元論,對(duì)多元世界的研究,對(duì)斯科尼克與布魯姆稱(chēng)之為“世界間關(guān)系”(relations inter-mondes)換言之也即跨虛構(gòu)性(transfictionnalité)問(wèn)題的興趣,都表明了這一點(diǎn)。此外,他們視為標(biāo)準(zhǔn)的是虛構(gòu)世界的封閉性,而非它們之間的交流,在轉(zhuǎn)敘式(métaleptique)僭越現(xiàn)象(例如2007的《怪物史瑞克3》)大量出現(xiàn)于兒童娛樂(lè)業(yè)的時(shí)代,他們的態(tài)度不免有些令人吃驚。不過(guò),邊界僭越的樂(lè)趣確實(shí)正在于邊界的存在,以及觀眾對(duì)這一邊界的感知。無(wú)論如何,由這些例子可見(jiàn),跨學(xué)科滲透似乎已是既成事實(shí),尤其當(dāng)我們將這些例子與奧特利(Keith Oatley)的言論聯(lián)系起來(lái)看時(shí):1999年,奧特利哀嘆心理學(xué)家對(duì)虛構(gòu)不感興趣,因?yàn)閷?duì)心理學(xué)家而言虛構(gòu)是輪廓不清的客體,需要運(yùn)用有缺陷的經(jīng)驗(yàn)方法(1999: 107)。
在邊界問(wèn)題上鞏固差別主義理解的所有方法中,我們還可以提及神經(jīng)科學(xué)場(chǎng)域內(nèi)開(kāi)展的一些研究,后者的目的在于通過(guò)磁共振成像的方法,識(shí)別大腦中參與現(xiàn)實(shí)控制任務(wù)的區(qū)域。這類(lèi)研究并非新生事物,2000年以后,此類(lèi)研究大量涌現(xiàn),但其前期研究從1980年代初就已開(kāi)始。在特納等人(Martha S. Turner et al. 2008)或西蒙斯等人(Jon S. Simons et al. 2008)的實(shí)驗(yàn)中,參與者被要求補(bǔ)充完整句子或詞組。參與者隨后必須在他們本人或?qū)嶒?yàn)者的朗讀過(guò)程中,辨認(rèn)出他們讀過(guò)或想象出來(lái)的詞語(yǔ)。大腦的同一塊區(qū)域(前額葉皮層側(cè)面位置)被外部刺激或自我刺激(也就是由想象產(chǎn)生)導(dǎo)致的神經(jīng)元活動(dòng)激活。不過(guò),通常認(rèn)為只與自我指稱(chēng)進(jìn)程相關(guān)的前額葉皮層額極中間區(qū)域只在受到自我刺激時(shí)才會(huì)被激活。此外,特納及其合作者還指出了一個(gè)特殊區(qū)域,前額葉皮層腹側(cè)尾部基底,在編故事時(shí),這個(gè)區(qū)域的大腦活動(dòng)較弱,此時(shí)主體以為有一種刺激被感知,實(shí)際上這只是主體的想象,或者反之。在特納等人看來(lái),這一區(qū)域的作用是執(zhí)行控制任務(wù),大腦可能通過(guò)與其他存儲(chǔ)信息的比較,斷定想象出來(lái)的事件可靠度低。在特納等人(Turner et al. 2008: 1443)提到的另一項(xiàng)研究中(Frith et al. 2006),對(duì)真實(shí)事件的感知會(huì)引發(fā)輕微的認(rèn)知混亂,而當(dāng)事件是想象事件時(shí)不會(huì)發(fā)生這一現(xiàn)象。我們由此得以區(qū)別事件的性質(zhì)。同樣地,在虛構(gòu)癥(confabulation)案例中,被認(rèn)為用于執(zhí)行控制任務(wù)的前額葉皮層某區(qū)域沒(méi)有或者說(shuō)幾乎沒(méi)有被激活。這一缺失狀態(tài)及與行動(dòng)力(agentivité)方面有關(guān)的錯(cuò)誤(病人記不起來(lái)究竟是他本人還是實(shí)驗(yàn)者大聲念了一個(gè)詞),被西蒙斯及其合作者(2008: 455)視作一種精神病癥狀。
除錯(cuò)誤感知問(wèn)題外,還有假性記憶問(wèn)題。假如我們自己的記憶不可靠,那么我們與現(xiàn)實(shí)和虛構(gòu)的關(guān)系又將如何呢?在福爾曼(Ari Folman)的電影《與巴希爾共舞》(Valse avec Bachir) 出品的同一年,神經(jīng)科學(xué)家施耐德(Armin Schnider)出版了一部著作,并意味深長(zhǎng)地為它取名為《患虛構(gòu)癥的心靈——大腦如何創(chuàng)造現(xiàn)實(shí)》(The Confabulation Mind. How the Brain Creates Reality 2008),對(duì)思考上述問(wèn)題深具啟發(fā)性。
《患虛構(gòu)癥的心靈——大腦如何創(chuàng)造現(xiàn)實(shí)》這一書(shū)名緊跟時(shí)代潮流,很吸引人也很容易引發(fā)警覺(jué),盡管如此,施耐德完全無(wú)意宣告一切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感知都是虛假的,或者說(shuō)任何能被接觸到的真實(shí)都是被歪曲的。他的學(xué)說(shuō)主要在于區(qū)別患病主體制造的現(xiàn)實(shí)變異與健康主體的虛假記憶。盡管從治療角度來(lái)看,施耐德最感興趣的是病癥,但是最能解釋我們所關(guān)心的問(wèn)題的是后一類(lèi)人,施耐德在全書(shū)第六章對(duì)其進(jìn)行了談?wù)摗S洃浀娜觞c(diǎn)、目擊證詞的不可靠性很久以前就已被證實(shí)(Kraepelin 1921)。在這一點(diǎn)上,施耐德的觀察不但沒(méi)有什么不同,用他本人的話說(shuō),甚至還有些令人氣餒:“令人不安的結(jié)論是,人類(lèi)大腦借助其聯(lián)想能力,能夠創(chuàng)造虛假的記憶,后者與真正的記憶有著相同的真實(shí)外表以及相同的神經(jīng)生理學(xué)支撐。”(Schnider 2008: 154)仿佛記憶與想象力產(chǎn)物雖被大腦以不同格式存儲(chǔ),但隨著時(shí)間流逝,產(chǎn)生了彼此侵蝕的傾向。實(shí)際上,很容易誘導(dǎo)別人給出虛假的童年回憶:在一組被測(cè)人群中(此前實(shí)驗(yàn)者已向被實(shí)驗(yàn)者講述了一個(gè)事件,這一事件被指曾發(fā)生于被實(shí)驗(yàn)者童年時(shí)期,但真實(shí)情況并非如此),25%的主體承認(rèn)自己能想起這件事(Schnidere 2008: 199)。很可能虛構(gòu)人物、童年時(shí)讀過(guò)的書(shū)從這種記憶磨損中受惠,漸漸被當(dāng)作很久以前認(rèn)識(shí)的人或經(jīng)歷過(guò)的事。無(wú)須提及壓抑機(jī)制,記憶本身構(gòu)成了我們的認(rèn)知機(jī)制中薄弱的一環(huán),想象與現(xiàn)實(shí)的分隔墻上的一道裂痕。然而,在感知現(xiàn)實(shí)方面,我們?cè)瓌t上有進(jìn)行區(qū)別的方法,后者尤其在于“消退”(extinction),也就是學(xué)習(xí)預(yù)想事件不會(huì)發(fā)生的能力。在正常思維下,想象的事物沒(méi)有現(xiàn)實(shí)性(也即沒(méi)有成為現(xiàn)實(shí)的可能世界)。而虛構(gòu)癥患者無(wú)法區(qū)別對(duì)現(xiàn)實(shí)沒(méi)有影響的思想(比如當(dāng)病人宣稱(chēng)要為一群不在場(chǎng)的人準(zhǔn)備晚餐時(shí))與對(duì)現(xiàn)實(shí)有影響的思想。這些患病主體欠缺消退能力,其原因可能在于執(zhí)行這一功能的細(xì)胞受到了錯(cuò)誤引導(dǎo)(Schnider 2008: 291)。
一切似乎都表明,我們擁有一臺(tái)精密的認(rèn)知“儀器”,能夠區(qū)別想象、回憶與感知,但這臺(tái)“機(jī)器”可能出現(xiàn)故障,而且很容易就產(chǎn)生變異。我們很難理解虛構(gòu)(例如童話故事,童話故事代表愿望實(shí)現(xiàn)的狀態(tài),有點(diǎn)類(lèi)似虛構(gòu)癥患者感知到的世界)在上述狀況中所起的作用。是否應(yīng)該假設(shè),虛構(gòu)促使主體——尤其當(dāng)主體是兒童時(shí)——在想象與現(xiàn)實(shí)之間進(jìn)行必要的認(rèn)知區(qū)分?實(shí)際上,兒童確實(shí)很早就懂得,通過(guò)魔力實(shí)現(xiàn)愿望的事情只發(fā)生在虛構(gòu)世界。或者說(shuō),應(yīng)該認(rèn)為虛構(gòu)構(gòu)成了現(xiàn)實(shí)與想象之區(qū)分的對(duì)立面,由此允許我們嘗試或者說(shuō)在認(rèn)知層面模擬一種類(lèi)似虛構(gòu)癥患者的精神狀態(tài)?目前沒(méi)有任何實(shí)驗(yàn)支撐或證實(shí)這些假設(shè)。
有關(guān)區(qū)別事實(shí)敘事與虛構(gòu)敘事的能力,今日(至少據(jù)我們掌握的資料)也不存在涉及神經(jīng)科學(xué)的測(cè)試。海沃德(Malcolm Hayward,從教于英語(yǔ)系)的研究處于文學(xué)與心理學(xué)研究的交叉點(diǎn)。在一篇發(fā)表于1994年的文章中,他提到一項(xiàng)實(shí)驗(yàn),接受實(shí)驗(yàn)的是45名年級(jí)不同的文學(xué)系大學(xué)生,還有幾位老師,他們被要求辨認(rèn)40個(gè)短句,這40個(gè)短句是從隨機(jī)選擇的史學(xué)著作或虛構(gòu)作品中抽取出來(lái)的,這些作品全部出版于1900—1975年間,且其作者全部是美國(guó)人。歷史小說(shuō)、傳記、回憶錄及后現(xiàn)代小說(shuō)被排除在外,因?yàn)樗鼈兛赡軙?huì)主動(dòng)模糊界限。實(shí)驗(yàn)結(jié)果表明,錯(cuò)誤率比較低,且與研究水平無(wú)關(guān),當(dāng)短句中的詞語(yǔ)數(shù)量增加(從5個(gè)增加至15個(gè))時(shí),錯(cuò)誤率隨之降低。事實(shí)文本中抽取的句子引發(fā)的錯(cuò)誤超過(guò)虛構(gòu)文本,因?yàn)樘摌?gòu)標(biāo)記更為明顯。對(duì)于虛構(gòu)性標(biāo)記,實(shí)驗(yàn)參與者提到了專(zhuān)有名詞、對(duì)話、第一人稱(chēng)的使用,尤其是段落的語(yǔ)氣(虛構(gòu)作品的語(yǔ)氣被認(rèn)為更具“戲劇性”)。這些標(biāo)記出現(xiàn)在事實(shí)文本中時(shí)常會(huì)引發(fā)誤判。不過(guò),一切會(huì)出問(wèn)題的情況都被排除在外,因而對(duì)調(diào)查結(jié)果的解讀也變得困難。
這些研究在目標(biāo)、方法及其想揭示的能力方面顯然存在很大差異。兒童區(qū)分真實(shí)與想象實(shí)體的能力(取決于他們所處的文化環(huán)境以及他們?cè)谀硞€(gè)特定時(shí)期的認(rèn)知發(fā)展),成年人區(qū)別感知、想象與記憶的能力(尤其屬于神經(jīng)元進(jìn)程),還有區(qū)別事實(shí)敘事與虛構(gòu)敘事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對(duì)從閱讀經(jīng)驗(yàn)中獲得的類(lèi)型符碼的吸收),我們不能將這些能力置于同一個(gè)層面進(jìn)行討論。
然而,在海沃德的實(shí)驗(yàn)中,大學(xué)生提出的非敘事學(xué)標(biāo)準(zhǔn)意味著還有可能從認(rèn)知角度給出答案,從源頭就不同于給文本貼上事實(shí)或虛構(gòu)標(biāo)簽的做法。對(duì)語(yǔ)調(diào)的關(guān)注令人聯(lián)想到,辨認(rèn)虛構(gòu)性主要是一個(gè)風(fēng)格問(wèn)題,除此之外,將專(zhuān)有名詞作為重要標(biāo)記也值得一提。具有事實(shí)的或虛構(gòu)的專(zhuān)有名詞的場(chǎng)景很可能確實(shí)會(huì)引發(fā)不同的神經(jīng)元進(jìn)程。無(wú)論如何,這是亞伯拉罕(Anna Abraham)及其合作者進(jìn)行的兩項(xiàng)研究(2008、2009)的結(jié)論。我們后面還會(huì)提到這兩項(xiàng)研究。
近期的神經(jīng)科學(xué)研究在涉及事實(shí)與虛構(gòu)區(qū)別問(wèn)題時(shí),并不太關(guān)注讀者判斷藝術(shù)品屬性的能力。這些研究更為關(guān)注同一個(gè)文本在被標(biāo)記為虛構(gòu)或記錄時(shí),所引發(fā)的對(duì)立的認(rèn)知反應(yīng)。
這一問(wèn)題在基德和卡斯塔諾(David Comer Kidd & Emanuele Castano 2013)的一項(xiàng)實(shí)驗(yàn)中順帶得到考察。實(shí)驗(yàn)結(jié)束后,基德和卡斯塔諾發(fā)表了一篇頗具影響力的論文,獲得學(xué)界及大眾的一致好評(píng)。他們宣布的實(shí)驗(yàn)結(jié)果確實(shí)很吸引人,因?yàn)檠芯拷Y(jié)論清楚無(wú)誤地證實(shí),閱讀文學(xué)虛構(gòu)能比閱讀通俗文學(xué)作品或非虛構(gòu)作品(遺憾的是,研究完全沒(méi)有說(shuō)明使用的是哪一類(lèi)事實(shí)文本,是報(bào)紙還是電話號(hào)碼簿)帶來(lái)更多的好處。在文學(xué)作品閱讀過(guò)程中暫時(shí)被改進(jìn)的是心智理論(ToM),心智理論由一項(xiàng)測(cè)試得到衡量,在測(cè)試中,被測(cè)者要觀看一些有表情的雙眼的照片,并為這些眼睛配上合適的情感(RMET)。不幸的是,這項(xiàng)實(shí)驗(yàn)結(jié)果近期受到幾個(gè)科學(xué)團(tuán)隊(duì)的質(zhì)疑,因?yàn)楹笳咦C實(shí)這一實(shí)驗(yàn)無(wú)法復(fù)制。如果說(shuō),與一群什么都不讀的人相比,在有閱讀(無(wú)論何種讀物)經(jīng)驗(yàn)的主體人群中能夠觀測(cè)到心智理論有些許的改進(jìn),反過(guò)來(lái),閱讀過(guò)虛構(gòu)文本(無(wú)論文學(xué)性如何)或事實(shí)文本的主體身上體現(xiàn)不出任何差異(Panero et al. 2017)。
這一令人失望的結(jié)果產(chǎn)生了一個(gè)后果:它應(yīng)該會(huì)促使當(dāng)前那些大肆吹捧虛構(gòu)的人采取更為審慎的態(tài)度。我們不能忽視一個(gè)事實(shí),即神經(jīng)科學(xué)無(wú)法為某些判斷提供不容置疑的科學(xué)依據(jù),這些判斷通常是純粹的假設(shè),根據(jù)這些假設(shè),閱讀虛構(gòu)文本能夠培養(yǎng)共情能力與社會(huì)能力(尤其參見(jiàn)Zunshine 2011)。盡管如此,仍有一些研究清楚表明,閱讀虛構(gòu)文本或事實(shí)文本時(shí),主體的神經(jīng)元進(jìn)程確實(shí)有所區(qū)別。雅各布斯(Arthur M. Jacobs)所屬團(tuán)隊(duì)的研究尤其具有代表性(Altmann et al. 2011; Schrott & 2011; Jacobs 2015)。他們進(jìn)行的實(shí)驗(yàn)內(nèi)容是向兩組讀者分發(fā)同樣的文本,但把給一組的文本標(biāo)明為事實(shí)文本,把給另一組的文本標(biāo)明為虛構(gòu)文本。研究表明,虛構(gòu)文本與事實(shí)文本都會(huì)激活與想象和模擬(simulation)相關(guān)的進(jìn)程,但激活的方式有所不同。如果將“模擬”一詞泛泛地理解為對(duì)行動(dòng)的再現(xiàn)與摹仿,那么事實(shí)文本與虛構(gòu)文本一樣,都能激起模擬進(jìn)程。不過(guò),虛構(gòu)激活的是大腦中與模擬相關(guān)的區(qū)域,且此時(shí)模擬被理解為假想性情境的建構(gòu)(Altmann et al. 2011)。虛構(gòu)所引發(fā)的文學(xué)閱讀模式促使讀者進(jìn)行更為緩慢的閱讀,關(guān)注每一個(gè)詞(Zwaan 1994),其目的在于重構(gòu)人物的動(dòng)機(jī)。這種閱讀模式也有利于思想的神游,更注重可能發(fā)生的故事,而非采集信息或召喚存儲(chǔ)于情景記憶中的現(xiàn)實(shí)回憶(Jacobs 2015)。
虛構(gòu)文本與事實(shí)文本引發(fā)的閱讀模式毫無(wú)疑問(wèn)是彼此有別的,即便虛構(gòu)能夠改善理解他人動(dòng)機(jī)的能力(ToM)的假設(shè)并沒(méi)有得到證實(shí)。
綜上所述,不同領(lǐng)域的多項(xiàng)研究給差別主義假說(shuō)帶來(lái)了重要論據(jù)。研究表明,我們擁有一種認(rèn)知結(jié)構(gòu),能夠辨別真實(shí)與想象,在涉及記憶進(jìn)程時(shí)尤其如此,即便這一認(rèn)知結(jié)構(gòu)并不完美。這些結(jié)果產(chǎn)生自一些實(shí)驗(yàn),其間實(shí)驗(yàn)者通過(guò)不同方法,對(duì)人類(lèi)區(qū)別實(shí)體、感覺(jué)及指稱(chēng)現(xiàn)實(shí)的文本的能力進(jìn)行了測(cè)試。當(dāng)其他類(lèi)型的問(wèn)題被提出時(shí),實(shí)驗(yàn)結(jié)果也發(fā)生了變化。
實(shí)際上,在情感與信仰確立模式等領(lǐng)域進(jìn)行的研究確實(shí)傾向于模糊事實(shí)與虛構(gòu)的邊界,或從連續(xù)統(tǒng)的形式來(lái)考察這一邊界。這些理論時(shí)常與領(lǐng)域內(nèi)兩個(gè)頗具影響力的隱喻相伴出現(xiàn),即轉(zhuǎn)移隱喻和模擬隱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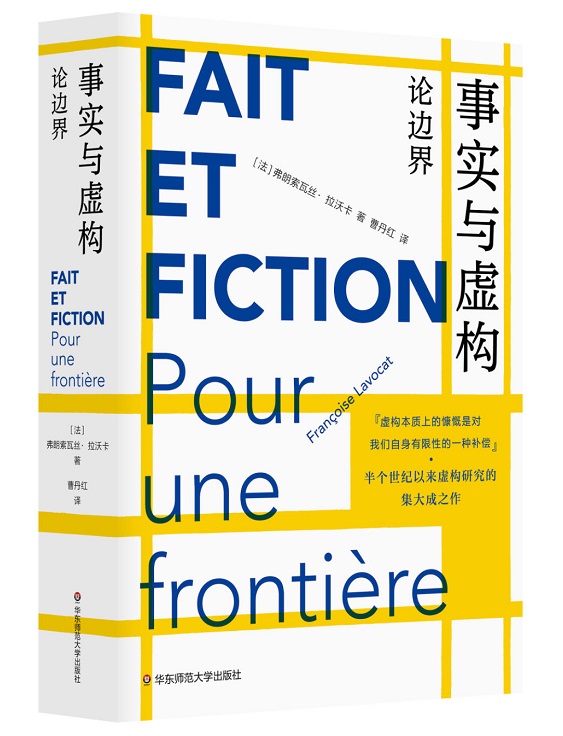
《事實(shí)與虛構(gòu):論邊界》,[法]弗朗索瓦絲·拉沃卡著,曹丹紅譯,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24年1月。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yíng)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