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年度閱讀|時代中的大人物與小人物
或許是因為2023年一整年的工作壓力大,我力圖使自己的私人閱讀回歸“休閑”“輕松”的簡單目的。但當我真的應邀盤點這一年的閱讀體會時,卻赫然發現在自己想聊聊的兩本書上依然回歸了本行,那個流傳已久的網絡梗“打工人打工魂”看來所言非虛。
“君主宇宙”的落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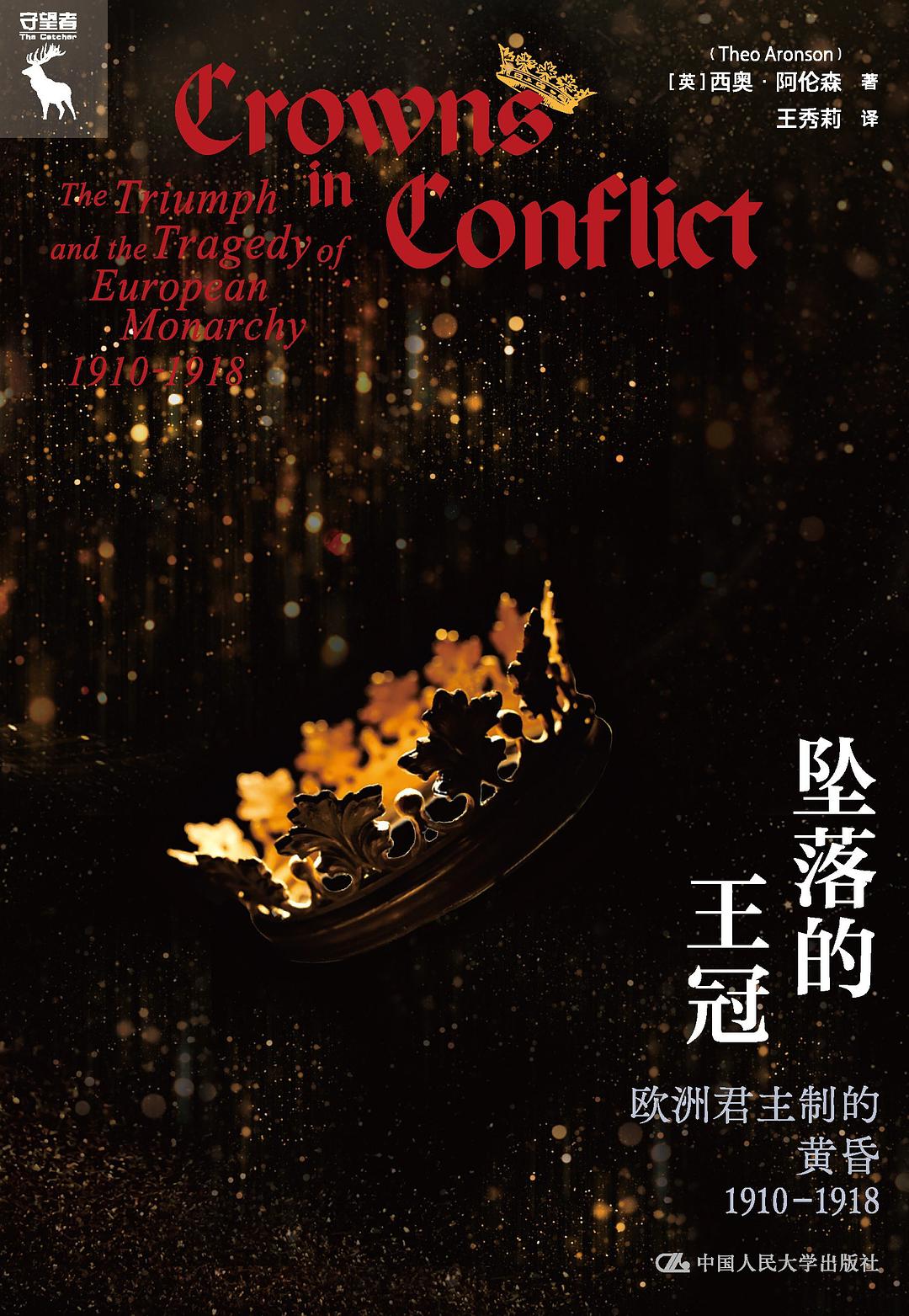
《墜落的王冠:歐洲君主制的黃昏 1910—1918》,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
正如開篇所言,《墜落的王冠》的定位并非專研1910-1918年歐洲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的學術著作,作為皇室傳記作家,西奧·阿倫森(Theo Aronson)順理成章地將自己的關注重心放在各國君主“家長里短”的親屬關系上,但這也讓讀者得以從君主制變化的角度注意到一戰“王冠落地”的全過程,兩組矛盾因此格外引人矚目:首先,彼此沾親帶故(有些甚至是直系近親)且往來密切的各國王室成員,為何彼此會走向對立并最終兵戎相見?其次,歐洲君主制挺過了從法國大革命至1848年革命期間各類自由主義、民族主義思潮與政治運動沖擊,甚至到1910年時,君主們的數量達到“歷史最高峰”的二十位之多。然而,這個看似處于興盛期(至少表面看來仍花團錦簇)的“君主宇宙”卻在1918年黯然落幕——盡管并非所有國家都將其君主掃地出門,但曾經高高在上的王朝秩序顯然已徹底瓦解。
除了三位著名的姑(姨)表兄弟,即英王喬治五世、德皇威廉二世和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外,像黑森家族這樣因兄弟姐妹的聯姻分化成同盟國與協約國陣營的情況——俄國末代皇后亞歷山德拉即出自這個家族,她的幾位姐妹又分別嫁給德俄的重要王室成員,而她的兄弟則是黑森大公——在王室貴圈更是比比皆是。對此的一般解釋是國家至上原則:且不論君主個人權力極大的德俄等國,即便是在君主立憲制極為成熟的英國,國王(或皇帝)作為國家元首依然位于整個社會結構的最頂端。更為重要的是,此時的君主成為國家的人格化身。
雖然諸如“君主被認為幾乎不亞于神”“君主的地位僅次于上帝”,抑或“皇室家族是一個超乎凡人的種族”之類的言論代表了當時流行的君主觀;而各國君主和皇室也在利用各類刻意為之的儀式或以營造氛圍的方式身體力行地迎合這種觀點。但毫無疑問,20世紀初作為國家象征的歐洲君主與前現代時期的“君權神授”截然不同。此時君主地位的提升,本質上源于工業化與現代化發展:伴隨著歐洲各國(特別是大國)在經濟貿易、殖民擴張、全球勢力范圍等各方面的迅速拓展,歐洲人對民族國家甚至帝國的認同得到不斷強化,無論是德國人、俄國人、英國人,還是奧地利人、意大利人,都會傾向于認為自己所從屬的集體(國家)有區別于其他集體的過人之處,而君主制的那套規則與排場,成為大多數歐洲人精神寄托的對象,即諾貝特·埃利亞斯(Nobert Elias)所說的“理想的‘我們’”(ideales “Wir”)的代表。在各國民眾的心目中,20世紀君主及王室正如他們所代表的“國家”一樣,實際上并非活生生的個人,而是構成民族認同基礎的象征符號。因此,王室家族利益抑或親屬血緣紐帶必然會讓位于國家形象的塑造。在英國這樣的多黨制議會國家,王室言行需要符合國民對他們的期許(例如喬治五世在1917年將家族姓氏變更為更加英范兒的“溫莎”),在個人權力極大的巴爾干國家也是如此,君主們同樣對履行君主義務有著清晰的認知。并致力于以不同的手段統御民心、維持國家獨立。
從19世紀下半葉起,君主及其家族作為民族象征和集體理想化身的地位日益鞏固,但其實他們作為“神”的地位是有限的。毫無疑問,作為被等同于非人符號的君主仍是一個個鮮活存在的人。而在王位繼承的血統原則下,君主可能缺乏執政能力,也可能存在性格缺陷。這方面舉世聞名的“典范”自然是德皇威廉二世和沙皇尼古拉一世,但知名度略低的保加利亞沙皇斐迪南同樣是一位“不著調”的君主。本書作者對各國君主們的評價大多言語克制,至多是溫和嘲諷,但在談及保加利亞的斐迪南時,則反復出現“做作、驕奢淫逸、墮落頹廢”及類似含義的措辭。
但君主神話的破滅并非源于君主們缺乏成為優秀的士兵、軍事戰略家和統治者的天賦,其根本原因是時代的變化。民族主義的抬頭固然讓各國需要一個象征物,但國際關系與國內政治現代化與專門化,連同現代社會層出不窮的新訴求,讓君主們所承擔的職能退化為儀式性的——且這一跡象在一戰爆發前就已經出現。一戰的結果進一步表明,一方面,無法解決國家內部的根本性矛盾會讓一些君主失去自己統治的國家,而不僅僅是失去自己作為“神”的地位;但另一方面,現代國際關系中的博弈又可以讓另一些國王們雖然自己失去統治權但依然得以(暫時)保全本國的君主制,奧匈帝國與保加利亞在一戰后的不同發展走向便是一對可以相互映照的例子,而君主個性稟賦顯然在其中并不占據絕對作用。作者甚至還在書中提醒讀者,“逆境往往能激發出王室成員的最佳狀態。在位時以殘忍、愚蠢或專治著稱的君主,在失去王位時往往會表現出非凡的謙遜、尊嚴和不屈。”(第256頁)威廉二世、沙皇尼古拉一世皆是如此。
表面看來,《墜落的王冠》是一則關于歐洲君主制消失、傳統生活方式在一戰和戰后走向終結的故事,即如作者所寫,“在1910-1918年的軍事、政治和社會動蕩中,君主將被證明既沒有力量,也無關緊要”。(第18頁)曾經被認為功能復雜的王權在面對現代國家體系已無能為力,而以親屬關系維護國家間關系也因為大戰的爆發而變得毫無用處,在這種情況,君主及其家族作為國家社會象征的功能甚至也到了可有可無的境地。
酷刑與瘟疫背后的盲目

《恥辱柱的歷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
與《墜落的王冠》是一部當代作品不同,《恥辱柱的歷史》出自19世紀意大利著名作家亞歷山德羅·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之手。最初它并不構成一個獨立完整的故事,而是計劃作為曼氏最著名的作品《約婚夫婦》(I Promessi Sposi, 1840)的背景之一,以“附錄”形式出版。由于《約婚夫婦》是一部描繪17世紀西班牙統治下倫巴第地區社會現實的歷史小說,不可避免地涉及這期間諸多的歷史事件,例如戰爭、起義和瘟疫。《恥辱柱的歷史》講述的正是1629-1631年米蘭大瘟疫期間真實存在的一場審判:1630年,米蘭的一名衛生專員及一名理發師因被指控在無辜市民家外墻上涂抹“有毒”油膏傳播瘟疫而被處以極刑;案件辦結后,人們夷平了理發師的店鋪,并在原地豎起 一根記載案情與處罰的“恥辱柱”“警示”后人。
曼佐尼對案情的敘述極為簡單,因為即便以他所生活時代(甚至更早的18世紀)的常識看來,“涂油膏”案也是一樁錯得離譜的冤案,完全是刑訊逼供的產物。因此他將敘述的主要重點放在對子虛烏有的罪名羅織及殘忍酷刑的討伐上。曼佐尼甚至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從法制角度分析刑訊逼供及酷刑產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當時的法律缺乏對刑訊規則及“應用此項權力的條件”規定;另一方面,在羅馬法傳統下,法官又被授予為查明真相而對被告施刑的權力,從而彌補了采取殘忍手段逼供的“合法性”。這種對“由于無法制定具體規范,一切全部取決于法官的意志”批判,無疑是啟蒙時代的反權威、反傳統思想的延續。但曼佐尼的憤怒并不僅止于此,他強烈譴責為達成調查和懲戒目的的酷刑背后普遍的人類野蠻與反人道。值得注意的是,曼佐尼這一反酷刑的立場不僅基于他作為受啟蒙思想熏陶的人道主義者的身份,或許還帶有一層血緣意義上的傳承:撰寫《論犯罪與刑罰》(Dei delitti e delle pene, 1764)反對酷刑與死刑、奠定現代刑法學基礎的切薩雷·貝卡利亞(Cesare Beccaria)正是曼佐尼的外祖父;而他書中多處引述觀點的《論酷刑》(Osservazione sulla tortura,1777)一書,其作者、意大利啟蒙運動的另一位先驅皮耶德羅·維里(Pietro Verri),則據信是曼佐尼真正生父的兄長,并與曼佐尼一家始終保持密切往來。
1630年“涂油膏”案的審訊過程顯然符合曼佐尼對酷刑代表的盲目權威與人類殘暴的批判。各級審判者們從一開始就完全不相信衛生專員的清白。除了重拳出擊施以酷刑,還用免罪承諾的方式誆騙“罪犯”交代“同伙”。這種查明真相的極端方式,雖然用曼佐尼引用的羅馬法條款是解釋得通的:“法官們不得以刑訊逼供開始,而應首先利用似真的、可能的證據。如果這些高度真實的證據表明應運用酷刑查清真相,那么法官可在被告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對其施刑。”(第29-30頁)但“涂油膏”案中“似真、可能的證據”僅僅是兩名婦女基于自己的偶然所見腦洞大開的推論,而輿論的不斷發酵最終讓司法部門認定許多居民家的外墻和門上被涂上了誘發瘟疫的致命油膏,因而是一場性質極為惡劣的大眾投毒案,“罪犯”對此必須從實招來。
倒逼真相構成“涂油膏”案中審判者們野蠻執法的起點,野蠻執法又揭示出案件的另一個顯著特征:愚昧。當然這種愚昧與當時醫學發展水平有限直接相關——用曼佐尼的話來說這是一種“時代的無知”。由于缺乏對瘟疫起源、病理的正確認識,讓17世紀早期的歐洲人對各種導致瘟疫爆發的說法深信不疑;然后又因缺乏有效治療辦法,當時的政府與大眾只能采取最嚴格的“人防”防止瘟疫傳播。在此背景下,兩名米蘭婦女因懷疑有人在城市里散播瘟疫而毅然告官,而當地審判者則力圖為找出有毒的證物而對兩名“罪犯”嚴刑拷打,似乎是解釋得通的。
曼佐尼本人倒是完全不認為醫學知識欠缺一定會造成不公正的發生,他明確提出,“不健全的制度也不會自行運轉”(第3頁),但他確實忽視(或簡化了)“涂油膏”一案所折射出的大眾恐慌心理之嚴重及隨之而來的行動取舍。1629-1631年米蘭大瘟疫是17世紀對意大利影響最大的兩次鼠疫中的一次,因米蘭公國受影響最嚴重而得名——疫情僅在米蘭就造成六萬人死亡(而米蘭當時的總人口不過13萬)。這場疫情還被認為造成了意大利經濟在近代的衰退。一面是死亡、貧困和兵荒馬亂(時值三十年戰爭期間),讓米蘭人對于反復來襲的瘟疫充滿了恐懼并成為驚弓之鳥;另一面自14世紀歐洲進入第二個黑死病大流行期,意大利城市就成為了“推動公眾努力控制瘟疫”的典范,為了確保健康人能夠逃脫死亡,避免本城“失守”而導致疫情的擴散,當時以城市為單位的防疫措施極為嚴苛。(說來諷刺,本案主犯之一擔任的“衛生專員”一職原本就是為確保城市環境清潔避免瘟疫傳播而設立的監督崗位。)在這樣的背景下,舉止“可疑”的人物就極易因為他人的謠言和恐懼而成為公眾獵巫的對象。就這一點而言,1630年“涂油膏”案的兩名死者連同他們因此事身敗名裂的家人,就不僅是酷刑背后人類殘忍的受害者了。
盡管兩本書成書年代相差近一個半世紀,寫作志趣也大相徑庭,但都呈現出歐洲社會結構長期發展過程中人的心理與行為變化。所謂“墜落的王冠”,其實并非單純指代歐洲王室在一戰后的陸續倒臺,還意味著幸存下來的君主必須“確保與全體人民相聯系,而非僅僅與貴族階層相聯系”(第283頁)。而曼佐尼對于恥辱柱歷史的記錄不僅揭示出近代歐洲普通人身處瘟疫時代的集體恐懼及對殘暴“執法”的不以為意,他本人作為接受啟蒙思想熏陶的人道主義者對于17世紀酷刑背后權力濫用的堅決批判也同時躍然紙上。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