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近代的讀書人如何看待傳統文化?新舊中西糾葛依然困擾著今人

梁啟超有言:“今日之中國,過渡時代之中國也。”過渡表現在方方面面,思想文化的過渡變遷也是“千年變局”中的重要一環。傳統的思想、文化在近代面臨著西潮的巨大沖擊,這是中國古代所未有的。自從80年代“國學熱”興起以來,傳統是什么,傳統如何與現代結合,不僅僅是當代中國人面臨的問題,也是在“過渡時代”下的中國轉型的重大議題。
一、西潮沖擊下的中國
作為歷史上主體相對統一并延續至今的國家,中國在全世界僅此一例。但就是這樣一個國家,歷史悠久,思想文化自成體系,今人看來自然十分自豪。但這在梁啟超眼中,卻是不折不扣的“老大帝國”,傳統在他看來是“一老朽者流,死守故壘,為過渡之大敵,然被有形無形之逼迫,而不得不涕泣以就過渡之途者也”。這樣的觀感無意中點明了一個現實,當中國在近代面對著西方文化的沖擊時,似乎難以轉身,甚至不知何去何從。
中國在漫長的古代歷史中從不缺乏文化自信,這表現在傳統天下體系下的“夷夏之辨”。在天下體系中,中國顧名思義是處于天下之中的,西周何尊的銘文即有“宅茲中國”一語。當時的中國尚單指洛陽一地,但隨著疆域的擴張和文明的擴展,中國也成為王朝統治下地域的稱呼。中國內的百姓,皆是華夏,是知禮儀、明是非、孝父母、尊君長的人群。孟子有言:“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華夏文質彬彬,而蠻夷則是野蠻的代表。在中國古人看來,華夏的自信便來自于文化,來自于傳統的禮樂制度。孔子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通過文化的感染力,自然可以懷柔遠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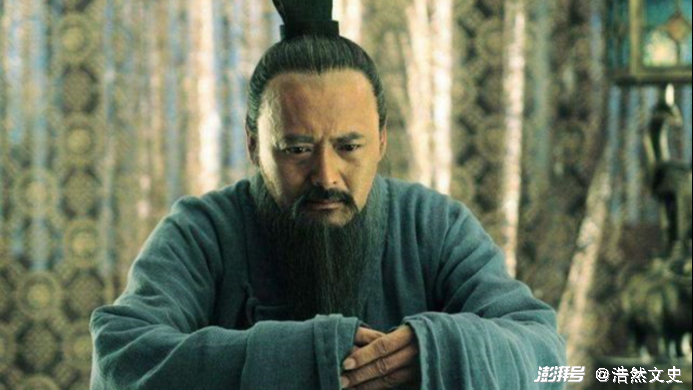
周潤發飾演的孔子
但在近代,這種情況有所變化,華夷態勢逆轉,中國由“文”至“野蠻”,從“華夏”降格為“蠻夷”。
作為較早睜眼看世界的郭嵩燾,在出使英國時,切身感受了西方文明,不由大加贊賞,心中已對既有的“華夏”“蠻夷”之分存有疑慮。早年留學美國的胡適曾說:“當中國酣睡之時,西人已為世界造一新文明。”這是一個不斷演進強化的傾向,愈往后的讀書人,對中國傳統的懷疑愈重,對其批判也愈激烈。百日維新的參與者譚嗣同,便曾大加批判中國兩千余年的制度:“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稍后的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更是說:“傳統既然是個整體,就必須全面反對,即使孔教并非無一可取,也不能不徹底否定之。”可以看出,中國對傳統的信心已經消失,更重要的是,傳統作為一個“整體”,被認為是負面的文化,所以要被遺棄。

胡適
這種全盤否定中國傳統的做法,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前所未見。古代中國也經歷了多次文化變遷,域外文明的傳入也曾經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知識思想體系。但其都被中國傳統消解、融合,例如中國化的禪宗。此外,古代士大夫從未對儒學,對整個歷史所遺存下來的“先王之法”做完全的切割。同樣是西潮的傳入,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也尚未引起士人對自身的全面懷疑。
如若將原因全部歸結為政治上的失敗和西方船堅炮利的極大誘惑,似乎不大能講得通。古代中國也多次面臨“蠻夷”的入侵,且大多時候中國武力不占優勢。例如宋朝被元滅國,清朝作為滿人入關,也是被華夏傳統所“涵化”。應該說中原王朝即使處于戰略守勢,甚至被外族滅國,但文化依然保持著生機,并同化了入主中原的外族。近代中國雖然在西方侵略下被打開國門,但主權尚能維持,亡國滅種的危機并不太顯著,況且在以往中國人的認知中,并不以一時成敗論英雄,為何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的傳統文化首先就立不住呢?原因當在于中西學戰、文化戰的過程中,中國傳統落下陣來。
近代的西潮傳入,是西方有準備的學戰的結果。傳教士進入中國,帶有傳播西方文明的任務,西方以成體系的知識對抗中國。國人的觀念逐步被西方的判斷準則所改變,便不得不對西方亦步亦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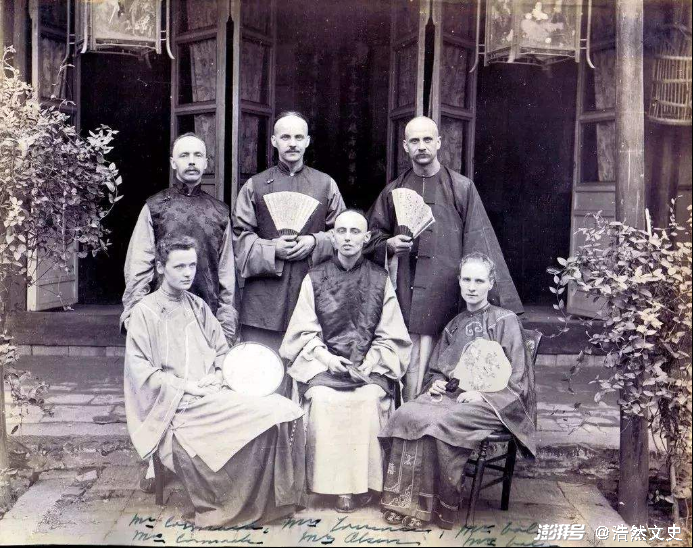
傳教士
二、社會權勢的轉移
近代的西方文明,帶有全球擴張的性質,對全世界的前現代國家都有著巨大的沖擊。在這種沖擊下,前現代國家不是被征服成為殖民地,就是自身內部的社會結構開始變化。中國的情況屬于后者,社會結構的改變,更使得傳統無法立足。
清末新政里一個重要的內容便是廢科舉。在傳統中國社會,科舉制是相當重要的一項國策。諾大的一個農業國家,政權控制無法有效地下達到鄉村地區。“皇權不下縣,縣下唯宗族”的說法可能稍顯絕對,但在整體社會結構上確實如此。而科舉制不僅提供了相對公平的社會流通渠道,更是將國家所提倡的思想文化和價值理念傳播到基層。儒學以此成為帝國內部通行的價值體系,也使得整個國家結構相對穩固。這其中,士大夫(鄉紳)的作用不可忽略,他們在朝為官,在鄉為紳,是國家的中間階層。一方面,士大夫是“道統”的傳承者,他們自身便是讀書人、學者,維護著既有的價值體系,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地方權勢的掌控者,肩負著維持地方秩序,教化百姓的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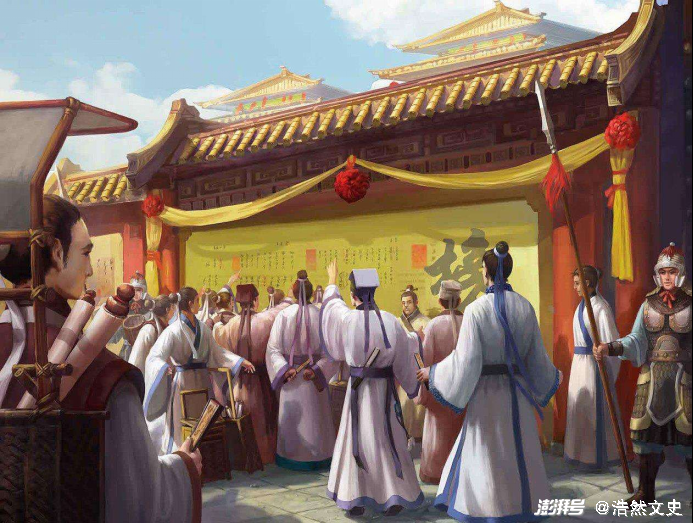
1905年,科舉制廢除,導致社會權勢發生了改變。科舉制廢除后,曾經的上升通道被斷絕,改以新的方式選拔人才,這些鄉間的士大夫們,無法再以曾經的方式上升。而且科舉改革后,西學逐步成為主流,代替中學成為主要考試科目,而西學在傳統的鄉間是無法習得的,無奈之下,大批士人只得走向城市,另尋出路。這不僅帶來了城鄉分離的結果,更導致中國傳統文化失去了傳承人。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生長的土壤,中國傳統文化便是扎根于農業社會的鄉間土地上。離開了鄉土的士大夫,放棄了地方的權勢,也放棄了傳統的文化,從以往社會權勢的重心,變為了社會的“邊緣人”。
大批進入城市的士人,思想不中不西,不新不舊,既未受到嚴格的中學訓練,一時間也無法系統學習西方知識,他們初通文墨但不精,他們不再留戀鄉土,在認同方面,更傾向于西化的城市精英。例如尚處于上海求學時期的胡適,“見人則面紅耳赤”的不自信、“自命為新人物”的渴求以及一直在等待“我的機會來了”的心理,正是思想文化過渡時期士人尷尬處境的體現。在城市中,這一批人只是邊緣知識分子,像胡適這樣做到留洋而成為知識精英的尚為少數。要跟上城市的腳步,被認同為精英,他們必須趨新,由此便走向了激進化的道路,更為強烈地反對傳統。
傳統社會結構的解體,傳統士人的轉型,當然不會使中國傳統文化走向消亡。但是,曾經傳統文化的辯護人已然轉型,鄉間的農民又無法有意識地以中學對抗西學,種種變化自然導致思想權勢移位。

三、失去思想重心:中西、新舊的糾葛
近代中國應當可以說是失去思想重心的時代,不同的個體表現出不同的糾結。中國的傳統文化在西學體系下,逐漸無法自我表述,而民族主義的情緒,使得當時人不得不去重新審視中國傳統文化。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各方面的轉型都面臨著許多問題。
且以學科建設和中醫為例。中國傳統并無如近代西方一般的嚴格學科劃分,經史子集并不如歷史、哲學、政治等學科有著明確的界限。近代中國跟隨西方的腳步,以西方的學術分科框架來審視中國傳統學術,不免會有削足適履之感。胡適對歷史的態度是“截斷眾流”,倡導“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便是希望以西方的學問重新整理中國傳統文化,以此再造出適應現代文明的中國文化,但這個過程卻異常艱難。讓胡適暴得大名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的書名,便被陳漢章所嘲笑,他說:“我說胡適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講義的名稱,就知道他不通。哲學史本來就是哲學的大綱,說中國哲學史大綱,豈不成了大綱的大綱了嗎?”以今天的眼光看,哲學史自然不是哲學的大綱。但在新舊交錯的近代,陳漢章之言不得不重新審視。大綱和史的差別,其實體現了兩人對史學和哲學的不同理解,在近代的分科體系下,各科畛域不明,傳統文化是史學還是哲學,一直是爭論至今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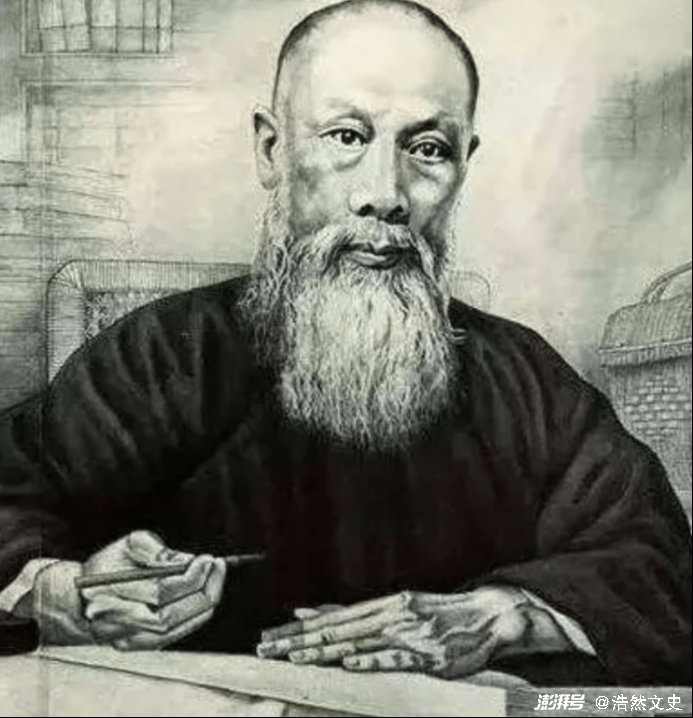
陳漢章
中醫是中國的傳統醫學,在近代西醫的沖擊下也顯得無法適應。傳統中醫并不是一門孤立的學問,其與傳統的思想有著很深厚的聯系。中醫的上層被稱為“儒醫”,與儒學有著共同的可理解的話語和知識,一定程度上,中醫也是中國人傳統世界觀的表現。中醫因其直覺性的思維,以及更多經驗性的診斷方法,面對西方科學體系的沖擊,往往“理屈詞窮”。相當程度上,中醫的衰落是儒學體系對抗科學體系的縮影。當然,時人也有拯救中醫的措施,歷來希望將中西文化接頭的梁漱溟,便有志于溝通中西醫。但當他親身研究后卻失望地發現,中西醫是“徹頭徹尾的兩種方法,竟然是無法溝通的”!所以他得出,溝通中西醫在他那個時代,是不可能的,但在將來卻有可能,但這需要依靠西醫自身的轉變。顯而易見,仍然有人相信傳統,但這種自信卻無法用已經占據話語主導地位的西方科學來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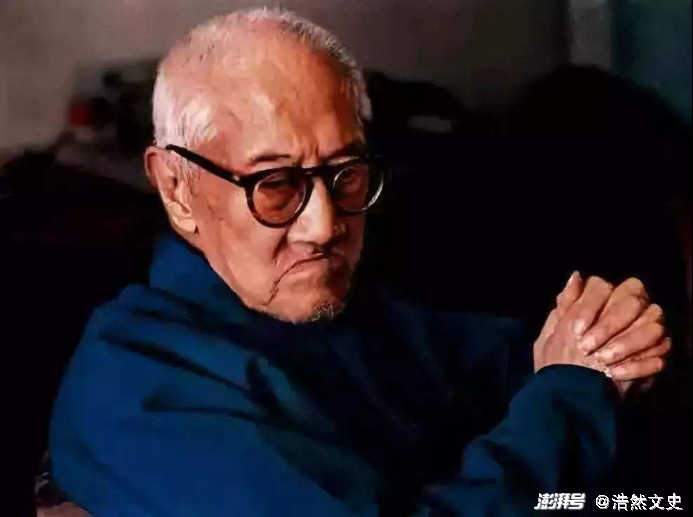
梁簌溟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的思想人物并無完全的新舊、中西劃分,更多是新中帶舊,舊中有新的混雜狀態。所謂的守舊派,例如錢穆、陳寅恪,實則含有新的成分,更顯著的例子是留著長辮子卻精通西學的辜鴻銘。而新派中的胡適、傅斯年等人,卻認為“我們思想新、信仰新,我們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處,我們仍舊是傳統的中國人”。這種狀態,使得中國近代的思想界,缺乏一個穩固的重心,總是興起一撥人未過多久,又一批更新的人興起,直斥前者守舊,顯示出老師跟著學生走的趨勢。
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國,無法在新舊、中西里找到穩固的落腳點,而溝通中西又難以完成,中國近代的思想也愈發激進化。

辜鴻銘
文史君說
近代中國傳統逐漸“失語”,而新思想的重心又無法有效建立,導致近代中國思想界錯綜復雜。今天我們仍舊面臨著同前人一樣的問題,在高談文化自信,重新發掘傳統的今天,由誰來定義和解釋傳統,仍然懸而未決。錢穆先生言,“文化只能放在歷史中去理解”,當傳統只屬于歷史時,如何面對現實呢?若只將傳統當作維系今人認同歷史的工具,或許太對不起心系天下的古人了。
最后借用陳寅恪先生的話,“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中國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不僅僅需要“坐而論”,也需要大眾的“起而行”。這個工作,不是近代時人可以完成,也不是我們這一兩代人可以完成。或許,向古人學習,多一些“天下胸懷”,渾融中西古今,在將來并非不可完成。
參考文獻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三聯書店,1984年。
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與社會》,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
羅志田:《新舊之間:近代中國的多個世界及“失語:群體》,《四川大學學報》1999年第6期。
(作者:浩然文史·秋山散人)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