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3,他們和世界重建聯(lián)系的瞬間|鏡相年終特別策劃

【編者按】
此刻,我們即將站在新的起點(diǎn)上。回望2023年,自我在生活的縫隙中流動(dòng),我們慢慢張開(kāi)自己,與這個(gè)世界握手擁抱。
這是重申聯(lián)系的一年。我們展出羽翼,再度感知遠(yuǎn)方的風(fēng)景;我們重啟對(duì)話,找回彼此信賴的溫度;我們探索內(nèi)心,校準(zhǔn)人生航向的坐標(biāo);我們也擁抱變化,在時(shí)代洪流中蓄積破土的力量。“世界”是我們的限度,也代表著我們的可能,而重要的永遠(yuǎn)是聯(lián)系,是我們主動(dòng)或被動(dòng)與萬(wàn)事萬(wàn)物的纏繞。
2023年末,鏡相欄目邀請(qǐng)了十位來(lái)自各行各業(yè)的嘉賓,從各自的角度,闡釋“重申與世界的聯(lián)系”這一主題。他們中有高校學(xué)者,站在歲末的門檻,開(kāi)啟對(duì)自我來(lái)路的審視;也有跨界作家,深入自身的內(nèi)在,為人生找到一個(gè)支點(diǎn);還有一直在路上的旅行者,在自然中放下自己,感受聯(lián)結(jié)的力量。2023年即將過(guò)去,希望我們的文字也能讓你回想起和世界重建聯(lián)系的瞬間,帶著這份新的體悟,我們重新出發(f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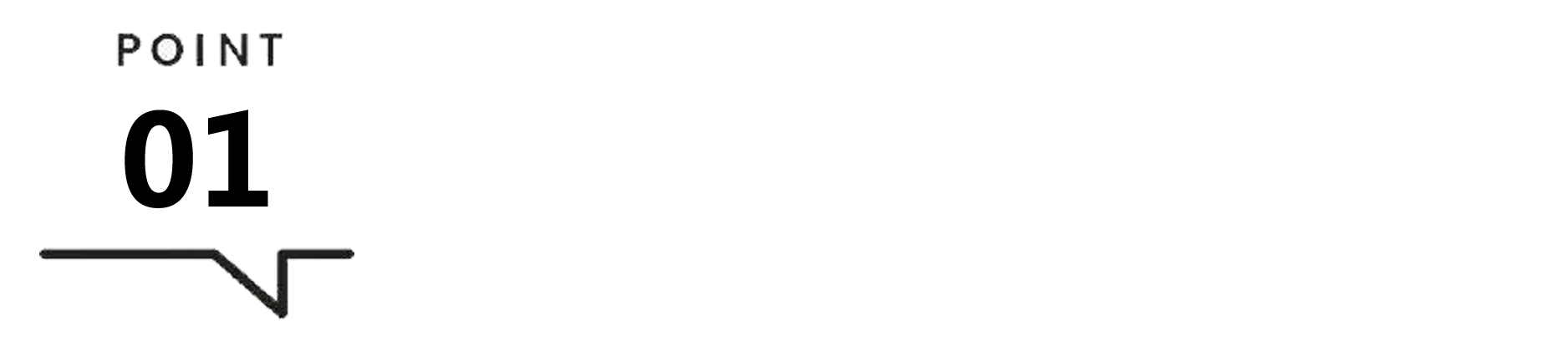
“世界”是我們的限度,
也代表著我們的可能。

節(jié)慶將至,匆忙的社會(huì)節(jié)奏似乎短暫放緩;氣溫下降,寒冷的空氣也會(huì)讓人被迫清醒。因此除舊迎新的歲末往往是“自我”浮現(xiàn)的時(shí)刻,站在人為劃定的時(shí)間的門檻上,感慨已經(jīng)發(fā)生的種種,憧憬即將到來(lái)的一切。在這個(gè)冬天,對(duì)于很多人而言,思考“如何好好生活”不再是一種虛張聲勢(shì)的矯情,它開(kāi)啟了某種對(duì)自我來(lái)路的審視,但卻沒(méi)有提供相應(yīng)的答案選項(xiàng)。經(jīng)驗(yàn)有失效的風(fēng)險(xiǎn),積累有干涸的可能,我們所熟知的那些結(jié)論,以及支撐那些結(jié)論的物質(zhì)和精神基座開(kāi)始搖晃。“世界”、“人生”、“價(jià)值”、“意義”之類宏大到幾乎有些蠻橫的詞迎面撲來(lái),無(wú)可閃避。除了公司的獎(jiǎng)金、單位的福利之外,我們很多人都在這個(gè)新年收到了屬于自己的人生大哉問(wèn)。
流行的勵(lì)志專家號(hào)召我們?cè)儆赂乙淮危鲃?dòng)出擊、把握機(jī)遇、扼住命運(yùn)的咽喉。
體貼的親朋好友安慰我們不要再勉強(qiáng),放過(guò)自己、享受當(dāng)下、“你已經(jīng)足夠努力了”。
我們或許已經(jīng)忘記,在做人生的莽夫和躲入一枚溫暖的殼之間,生活更尋常的面向是維持某種微妙的平衡。勉強(qiáng)的“我能行”和退卻的“我不敢”或許可能在某些時(shí)刻扶我們一把,不要跌倒。宣誓或棄守過(guò)后,答案并未增殖,疑問(wèn)也沒(méi)有衰減,每一日每一月依然可能用讓我們不適的方式運(yùn)轉(zhuǎn)。
作為一門癡執(zhí)著于探索口號(hào)和喧囂之下川流不息的日常經(jīng)驗(yàn)之河的學(xué)問(wèn),人類學(xué)更相信平衡的意義:給定的條件和限制并不是泥石流那樣可以吞噬自我的滅頂之災(zāi),而看似開(kāi)疆拓土的英武背后也充滿對(duì)既定事實(shí)的承認(rèn)乃至妥協(xié)。這個(gè)世界“加上我”,不只是我的天賦和強(qiáng)項(xiàng),也包含我的局限、脆弱甚至不堪;這個(gè)世界注定會(huì)“減去我”,但確定移除的也只是我肉體意義上的生命,那些看似讓人心煩的錯(cuò)綜關(guān)系和怎么都無(wú)法上綱上線的普通經(jīng)歷反倒會(huì)讓我的回響綿延日久。重要的永遠(yuǎn)是聯(lián)系,是我們主動(dòng)或被動(dòng)與萬(wàn)事萬(wàn)物的纏繞,是我們不斷贈(zèng)予拿取之后留下的一筆糊涂債務(wù)。
即使是蹩腳的哲人,也會(huì)明白不應(yīng)把問(wèn)題封印在“我”的疆域之內(nèi)。“我”的本相就是這個(gè)世界所固有的開(kāi)放性以及隨著這開(kāi)放性而來(lái)的、不可避免的混亂和粘連。所以,“放過(guò)自己”,放過(guò)的是企圖靠一個(gè)單薄的自我去實(shí)現(xiàn)關(guān)機(jī)重啟、明哲保身的妄念;“主動(dòng)出擊”,朝向的是我們不可回避的關(guān)系和牽絆,是勇敢的承認(rèn)許多人和事“與我有關(guān)”,在承擔(dān)中尋求出路,在責(zé)任里尋求安穩(wěn)。
“世界”是我們的限度,也代表著我們的可能。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跟世界握手擁抱,在新的人、新的事那里,重新找到家的感覺(jué)。

2023年是焦慮之年。我和朋友們一起經(jīng)歷了工作上更大、更復(fù)雜的壓力,也要一起面對(duì)更多不確定性的挑戰(zhàn)。2023年也是大家在社交媒體尋求自我療愈的一年。有人沉迷短劇中的人生逆襲,有人沉迷悲傷的凈化。正因?yàn)榇蠹叶歼^(guò)得不容易,把自己作為方法,竭盡全力消除讓自己不幸福的因素,成為了我們一起奮斗、一起渡劫、一起克難的主題。有人想松弛、有人想更好地照顧自己當(dāng)個(gè)隱世的i人,也有人想要走出狹隘的自己,走出自我憐憫的愉悅,為精神生活添磚加瓦。遭遇挫折的時(shí)候,也許我們會(huì)與社會(huì)生活短暫斷聯(lián)。但再度開(kāi)放自己的內(nèi)心,廣泛地聯(lián)結(jié)他人,傾聽(tīng)他人的聲音,是為最樸實(shí)的生計(jì)累積經(jīng)驗(yàn)和信心的窄徑。
行走和勞動(dòng),就是在憑借自己的方向?qū)ふ疑畹男问健Ec工作有關(guān)、與情感有關(guān)、與一句話有關(guān)、與一個(gè)念頭有關(guān)。有些場(chǎng)景,原先是隔膜的,走走就成了參與。有些人,原先是無(wú)話可說(shuō)的,說(shuō)著說(shuō)著,就都成為了情景中人,成為記憶,和召喚。它們匯聚在一起,儲(chǔ)蓄著我的生命記憶,我通過(guò)書寫、對(duì)談,記下生活的演變,仿佛是在做一項(xiàng)十分基礎(chǔ)的園林工作,修剪、拔除、焊接,余下一些材料再留有一些,最終成為了文字的演變。那便是生活的輪廓,也是在茫茫世界中定錨自我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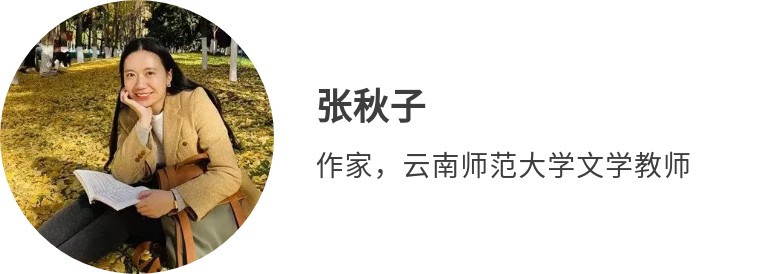
如果問(wèn)到今年和世界重新建立聯(lián)系的瞬間,我覺(jué)得應(yīng)該是可以逛街了,街頭有人氣了。
我喜歡逛街,喜歡貪婪地看櫥窗里的衣服、首飾、雜貨,所以真的難以想象住在無(wú)法逛街的鄉(xiāng)間的寂寞。每所大學(xué)外面應(yīng)該都會(huì)有一條商業(yè)街或者步行街,曾經(jīng)走在路上一片冷清,可今年春天開(kāi)學(xué)后,人流一下子涌到了街頭,置身其中,只覺(jué)得是被人潮推著往前走,光是看各種食物、耳環(huán)項(xiàng)鏈、寵物、水果、小吃都已經(jīng)目不暇接。我不一定買東西,但一定要看,看里面有一種強(qiáng)烈的新奇感與滿足感,就像伍爾夫?qū)懕说每床贿^(guò)來(lái)時(shí)的感覺(jué)——“眼前一連串景象好像冰冷的溪水,看不清了,他的眼睛猶如一只滿溢的杯子,里面的水在瓷杯四周淌下來(lái)”——雖然許多哲人們都認(rèn)為這種現(xiàn)代性的街頭奇觀里暗藏著資本主義夢(mèng)幻世界的廢墟與殘骸,但是對(duì)于這時(shí)的我來(lái)說(shuō),我想到的只是生活又恢復(fù)了,人與人又走到了一起。這令人慶幸。
比較尷尬的是,我這兩年也一直在講一部關(guān)于逛街的小說(shuō),就是伍爾夫的名作《達(dá)洛維夫人》。這部小說(shuō)有一個(gè)比較重要的特點(diǎn)是它的許多核心內(nèi)容都是以逛街作為線索串聯(lián)起來(lái)的。伍爾夫?yàn)樽x者留下了一段段獨(dú)一無(wú)二的二十世紀(jì)初的倫敦夜景的描述,文字在這個(gè)時(shí)候變成了流動(dòng)的鏡頭,貪婪地捕捉著街頭人、物、聲、光、味、色。
不管怎樣,那是一種美感。既非一目了然的粗俗的美,也不是純粹的美——貝德福德大街通向拉塞爾廣場(chǎng)。當(dāng)然是筆直的,可也是空蕩蕩的;還有勻稱的走廊;燈光閃亮的窗子,鋼琴,開(kāi)著的留聲機(jī);一種享樂(lè)的感覺(jué),隱隱約約,不過(guò)有時(shí)也露出來(lái),譬如通過(guò)打開(kāi)的不掛簾子的窗口,看得見(jiàn)一簇簇人坐在餐桌邊,青年們翩翩起舞,男人和女人在密談,女仆們懶洋洋地向窗外眺望(她們干完了活兒,就怪里怪氣地品頭論足);高層壁架上晾著長(zhǎng)襪,一只鸚鵡,幾株花木。這生活的景象,如此魅人,神秘,無(wú)限地豐盈。寬闊的廣場(chǎng)上,汽車接二連三,風(fēng)馳電掣,迅速地繞著彎兒;一對(duì)對(duì)漫步的戀人,打情罵俏,緊緊地?fù)肀В[入濃陰匝地的樹(shù)下……就這樣向前走,投入一片噪聲和炫目的光海中。
這是現(xiàn)代性的街頭,也是現(xiàn)代人的街頭。狄更斯在《荒涼山莊》里寫倫敦的街頭,但那街頭滿是泥濘,好像洪水剛從大地上褪去,從破曉起就有成千上萬(wàn)的人在那里跌倒和滑跤,煙煤則從煙囪頂上紛紛飄落,化作一陣黑色的毛毛雨;笛福在《瘟疫年紀(jì)事》里寫倫敦的街頭,甚至笛福的小說(shuō)就是以街道為中心的,只是街道上要么因?yàn)橐卟《諢o(wú)一人,留下意味深長(zhǎng)的寂靜,要么就變成露天的停尸房,塞滿尸體;在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集》里,倫敦街頭也好不了多少,雖然不乏人流涌動(dòng),但依然泥濘不堪,櫥窗店鋪的刺眼黃光也無(wú)法穿透街頭的霧霾,而且街道形如迷宮,很容易迷路。
我和我的學(xué)生們?cè)陂喿x這些作品的場(chǎng)景的時(shí)候,其實(shí)是很受限的,你只能坐在教室里面,你甚至不能邁出大學(xué)校園,逛街已經(jīng)變成了一個(gè)非常奢侈的東西,我們只能非常干癟地從文學(xué)作品中來(lái)了解街頭的景觀。但是今年春天開(kāi)學(xué)以后,人流終于重新涌到街頭。讀者不應(yīng)在書中去想象伍爾夫與本雅明所描述的街頭,而應(yīng)該真正地走到街頭的人流里去感受,這樣一來(lái),“震驚”、“現(xiàn)代性”就不再是令人捉摸不透的抽象大詞,變成了一種與人摩肩接踵、交錯(cuò)而過(guò)的親歷感。我們真的可以通過(guò)走上街頭來(lái)感受人氣,而不再僅僅通過(guò)閱讀文本里的街景來(lái)感受,我想這可能就是今年以來(lái)我感到和世界重新恢復(fù)聯(lián)系的一個(gè)很重要的點(diǎn)。
談到人氣,其實(shí)就是人的氣息的存在,而人的氣息會(huì)讓我想到力量、青春、活著的感覺(jué)。上帝造人就是往他捏的泥土人偶中吹了一口氣。小時(shí)候我們家附近有一個(gè)做豆腐的人,他跟我們傳授做豆腐的秘訣,不僅僅要大豆發(fā)酵才能做成,在做的過(guò)程中人的氣息呼進(jìn)去了,也加速或者參與了某種神秘的發(fā)酵,讓豆腐有了人味。
無(wú)論是做豆腐還是上帝造人神話故事,我想人氣都是最為關(guān)鍵的,它提示著我們一個(gè)非常切實(shí)的感受,就是活著。與人肩并肩,面對(duì)面感受他的氣息、溫度,感受與他擦肩而過(guò)時(shí)帶來(lái)的速度感,甚至一小陣的風(fēng)。逛街這件看起來(lái)好像特別俗氣也沒(méi)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卻成為了我今年我去感受和世界重新建立瞬間的最重要的一環(huán)。

很多年輕人在2023年對(duì)生活都有了一些新的體悟,我去書店分享新書,接待我的編輯們、年輕的聽(tīng)眾們,他們都有一個(gè)心情,就是對(duì)生活、對(duì)生命更加珍惜了,同時(shí)對(duì)感情也更加珍惜了。在一個(gè)不確定的世界上,希望有一個(gè)確定的人,有一份確定的美好情感。大家的閱讀熱情也更高了,在閱讀里我們代入了自己生存里的各種困惑、焦慮、不解。年輕人對(duì)生活的定義,尤其是他們的精神需求在變化,2023年,大家有一種新的對(duì)于人生價(jià)值的理解。
這一年里,我去了古徽州,也就是現(xiàn)在的黃山市,其中有一個(gè)古村落叫黃村,那里原生態(tài)的農(nóng)耕文明保存得特別完整。我和一個(gè)姓黃的老太太聊天,她說(shuō)現(xiàn)在的生活在物質(zhì)方面比以前好太多了,沒(méi)有什么大的憂慮,但還是有一些難以排解的心情。按照她的總結(jié)就是生活富有了,但是人更加孤獨(dú)了。這是一種在徽州文化里挺典型的狀態(tài),在一個(gè)家族社會(huì),原有的那種緊密的親情關(guān)系越來(lái)越稀落了。黃村這種古老村落里的生活很淡然,有著時(shí)光滄桑感,有傳統(tǒng)社會(huì)的種種氣息。我就感到,我們社會(huì)的變化是有梯度的:很多古老的文化,它的種種因子還保留著,但是心的變化又很大。
我們的2023年,大家的生活有不同的色澤、不同的文化選擇,我感受到時(shí)代發(fā)展中的一些普遍性和差異性。
我去四川時(shí)也有一個(gè)大發(fā)現(xiàn):成都周邊有很多鄉(xiāng)村,現(xiàn)在出現(xiàn)了很多“新鄉(xiāng)民”。比如成都蒲江縣明月村,就有原來(lái)著名的電視主持人、女作家在明月村建立的一大片民宿。而且民宿的設(shè)計(jì)也特別彰顯文化創(chuàng)意,里邊也有她自己的服裝品牌。她也請(qǐng)一些藝術(shù)家、文化人到那里免費(fèi)住宿,比如在這里住一個(gè)月,然后完成一點(diǎn)作品。類似這樣的創(chuàng)作者去到農(nóng)村,帶著很大的自主創(chuàng)造性,建立起了一個(gè)特別舒展的環(huán)境,很有年輕人的朝氣。他們不僅僅是自我表達(dá),也結(jié)合當(dāng)?shù)氐霓r(nóng)業(yè)生產(chǎn),結(jié)合鄉(xiāng)村振興的價(jià)值要求,去開(kāi)創(chuàng)一些東西。比如給當(dāng)?shù)氐囊环N橘子一個(gè)新的品牌效應(yīng),引入新科技、追溯它的歷史、聯(lián)合農(nóng)業(yè)科研改善品種等等,給予了農(nóng)村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很大的推動(dòng)力。這種城鄉(xiāng)之間的新的關(guān)系,包含著文化藝術(shù),也包含著新的鄉(xiāng)村生活方式的打造,我覺(jué)得這是我們年輕人可以大有作為的領(lǐng)域,比我們都擠在一線城市內(nèi)卷自在得多。
還有一點(diǎn)感觸是,年輕人對(duì)生活的認(rèn)識(shí)有了很大的變化,他們?cè)谒伎肌叭艘惠呑釉撛趺醋鲆稽c(diǎn)自己喜歡又有創(chuàng)造性的事情”?
年初我跟三個(gè)學(xué)生聚會(huì),聽(tīng)他們分享他們的體會(huì)。碩士畢業(yè)六七年了,剛出去的時(shí)候很迷茫,很喜歡創(chuàng)作,但是作品還沒(méi)有被人承認(rèn),靠創(chuàng)作生存壓力也很大,很多人都放棄了,去做別的事情了。但是這幾個(gè)同學(xué)還堅(jiān)持寫作。有了六七年的艱苦磨練之后,慢慢的,他們感覺(jué)自己對(duì)自己的內(nèi)心、生命的方向、文學(xué)的價(jià)值、怎么去寫等等問(wèn)題,有了不一樣的體會(huì)。他們忽然發(fā)現(xiàn)世界變得簡(jiǎn)單了很多,誘惑都不是誘惑了,不是自己要做的事情,不是自己尋求的價(jià)值,就淡然了許多,人變得從容了。
如果沒(méi)有六七年的積淀,如果隨波逐流讓自己的生活朝著容易的方向走,可能就什么生命的成長(zhǎng)都沒(méi)有了。我聽(tīng)完大家的感悟覺(jué)得非常感動(dòng)。在各種各樣的不確定中依舊能夠逆流而上,我覺(jué)得這是一些人在2023年會(huì)體會(huì)到的一份內(nèi)心的認(rèn)定。
2023年以后回想起來(lái),可能是我們很多人生活重新出發(fā)的關(guān)鍵年,它為我們未來(lái)的新生命奠定了一個(gè)基本的認(rèn)識(shí),很多變化的起點(diǎn)可能就在2023年。祝大家新年快樂(l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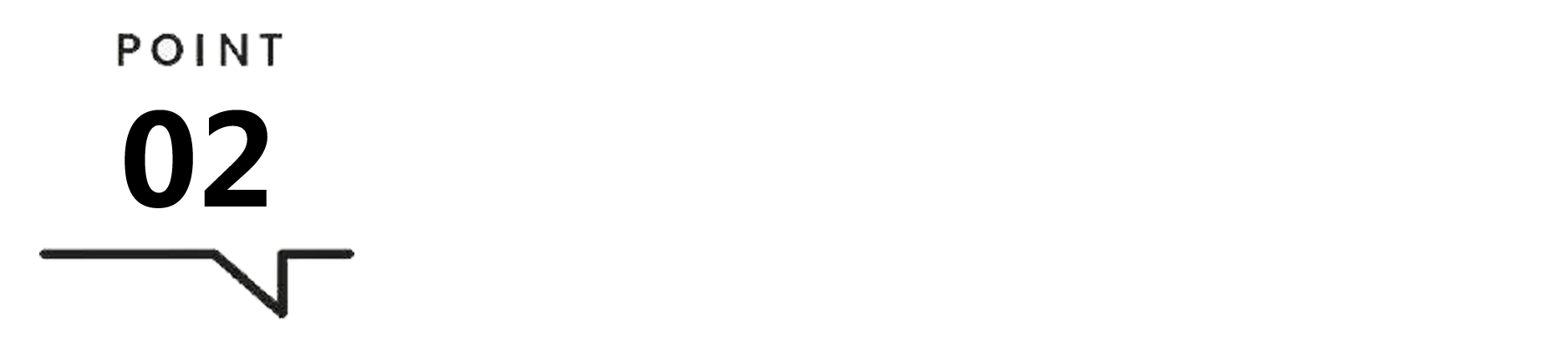
回到這個(gè)真實(shí)的世界,
打磨生活的光澤、銳角和刃口。

這一年的開(kāi)始對(duì)大多數(shù)人來(lái)說(shuō),應(yīng)該有兩個(gè)層面上重新與這個(gè)世界的聯(lián)系,首先是物理上的,這自然伴隨著許多身體的痛苦甚至是離別,另外一個(gè)層面,是心理上的,我們依賴了互聯(lián)網(wǎng)太久,走進(jìn)真實(shí)的世界,感知它的真實(shí)冷暖和變化。
今年我出版了2本書,還有1本小說(shuō)因?yàn)闀?hào)太晚要拖到明年,拿了課題,職稱上也有了小小的進(jìn)步,但事實(shí)上,我這一年更多的工作上最大的變化是,我給出建議的比例要遠(yuǎn)遠(yuǎn)大于治療。換句話說(shuō),人們來(lái)找我,更多是希望我給他們出個(gè)主意,而并非告訴我這個(gè)病該怎么治。我想,這可能不是我主觀上的改變,而是大眾對(duì)我新的認(rèn)識(shí)和定位帶來(lái)的。一個(gè)朋友拿了一沓病例來(lái)找我,我發(fā)現(xiàn)他希望我?guī)退崂淼牟⒎侵委熀椭改希驗(yàn)檫@些他可以在網(wǎng)絡(luò)上輕易查到。他希望我?guī)椭斫猓t(yī)生為什么要給A方案而不是B方案,為什么同樣大小的結(jié)節(jié)別人要手術(shù)我卻只能觀察,醫(yī)生說(shuō)的話里潛臺(tái)詞是什么,醫(yī)生有什么自身的行為背后會(huì)有怎樣的動(dòng)機(jī)?林林總總的問(wèn)題告訴我們,我們開(kāi)始一方面對(duì)于這個(gè)世界有美好的預(yù)期,但又同時(shí)開(kāi)始理解并進(jìn)入這個(gè)世界,選擇最有效的解題方式,來(lái)應(yīng)對(duì)世界中的不確定性,解決一個(gè)個(gè)具體的問(wèn)題。
這一年我最喜歡的還是線下的見(jiàn)面,無(wú)論是線下的讀書會(huì),還是當(dāng)面的問(wèn)診,我都能更放松地給出“建議”。而且我直觀地感受到,現(xiàn)實(shí)中人們的戾氣比網(wǎng)絡(luò)要淡化許多,當(dāng)人與人眼睛看著眼睛,手握著手的時(shí)候,這種基本的信任可以極大減少一個(gè)詞,一句話的偏差所帶來(lái)的誤解甚至是憤怒。物理的接觸會(huì)產(chǎn)生信任,而信任很多時(shí)候是醫(yī)療的前提。當(dāng)一個(gè)人誠(chéng)心希望你給個(gè)建議,你又竭盡所能努力為他找一條更好的路,最后的結(jié)局大多都是完美的,或者說(shuō),無(wú)論醫(yī)療的結(jié)局如何,我們都做好了當(dāng)下應(yīng)對(duì)這個(gè)世界最好的解法。
重新回到這個(gè)真實(shí)的世界中來(lái)吧,朋友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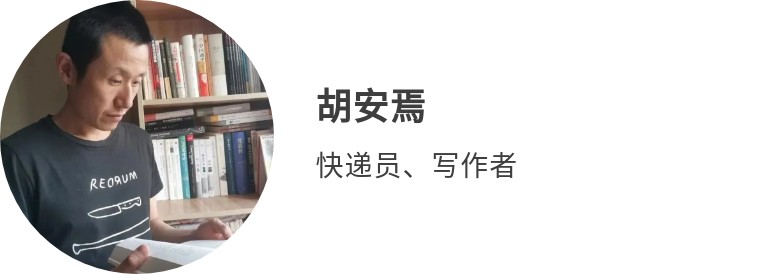
今年3月份,因?yàn)槌霭媪艘槐敬蚬ぷ詡鳌段以诒本┧涂爝f》,很多讀者對(duì)我的寫作經(jīng)歷也產(chǎn)生了好奇,不少人關(guān)心一個(gè)問(wèn)題:為什么我有寫一本書的能力,卻去做快遞員這種體力工作。
首先,在幸運(yùn)地得到一個(gè)出版機(jī)會(huì)之前,我在寫作上并沒(méi)有取得過(guò)什么可以用來(lái)找工作的成績(jī);我的年齡和履歷對(duì)找工作也沒(méi)有幫助,實(shí)際上還拖了后腿。其次,送快遞在扣除所得稅和五險(xiǎn)之后,我到手的年薪有八萬(wàn)多一點(diǎn),相對(duì)而言還算不錯(cuò),假如我去找文字方面的工作,憑我的條件可能還掙不到這么多。
我的書剛出來(lái)的時(shí)候,曾經(jīng)有媒體記者問(wèn)我,說(shuō)網(wǎng)上有讀者稱我為“網(wǎng)紅作者”,不知道我同不同意。讀者會(huì)有這種印象,當(dāng)然是因?yàn)椋沂窍仍诰W(wǎng)上“紅”了一下,然后才被出版方注意到,并最終促成了這本書的出版。但是在聽(tīng)到“網(wǎng)紅作者”這個(gè)稱呼的那瞬間,我還是覺(jué)得有點(diǎn)兒恍惚,因?yàn)槲覐膩?lái)沒(méi)有想過(guò),這個(gè)稱謂有天會(huì)落到自己頭上。
我的寫作始于2009年,在之前的十幾年里,我一直都默默無(wú)聞,不為人知。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我已經(jīng)建立了充分的認(rèn)知,理解并且接受了:自己的寫作就是不被大眾需要的,既換不來(lái)錢,也引不起關(guān)注,很大程度上,類似于個(gè)人的修行,不斷深入自身的內(nèi)在,反思和消化自己的生活經(jīng)驗(yàn),通過(guò)創(chuàng)造性的寫作,同時(shí)也是以一種審美的形式,為自己的人生找到一個(gè)支點(diǎn),盡管過(guò)程中也充滿了彷徨、苦悶和自我懷疑。
2023年對(duì)我來(lái)說(shuō)是特別的一年,因?yàn)槌霭媪艘槐緯彝蝗恢蒙碛诖蟊姷哪抗庵校⒁赃@樣一種頗為戲劇化的方式,和外部世界重新產(chǎn)生了聯(lián)系。對(duì)此我并沒(méi)有太多準(zhǔn)備,我相信大多數(shù)和我情況相似的人,都沒(méi)辦法提前為此做好準(zhǔn)備,一定程度上都是措手不及的。所以,我還在反思自己今年的所有表現(xiàn),包括在所有采訪、播客、視頻和現(xiàn)場(chǎng)活動(dòng)中的言行,以及這些特殊經(jīng)歷對(duì)我產(chǎn)生的影響、我隨之發(fā)生的改變等。我肯定有做得不恰當(dāng)?shù)牡胤剑@將成為一個(gè)我繼續(xù)認(rèn)識(shí)和完善自己的起點(diǎn)。

我是王計(jì)兵,目前是生活在昆山的一名外賣騎手。2023 年對(duì)我來(lái)說(shuō)是特別神奇的一年,這一年我先后出版發(fā)行了兩部個(gè)人詩(shī)集,銷售量突破了 10 萬(wàn)冊(cè)。同時(shí)這一年我獲得了徐州詩(shī)歌節(jié)年度詩(shī)人獎(jiǎng)、江蘇省第八屆紫金山文學(xué)獎(jiǎng),還有外賣行業(yè)的最美騎手獎(jiǎng)。這一年我有幸加入了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成為這個(gè)大家庭中的一員。
最讓我激動(dòng),最讓我興奮的是,10 月底我跟隨代表團(tuán)出訪美國(guó),參與了中美兩國(guó)的民眾對(duì)話,對(duì)于兩國(guó)關(guān)系的歷史、現(xiàn)在和未來(lái)發(fā)表了我的個(gè)人看法。這很大程度上滿足了我作為一個(gè)普通人的愛(ài)國(guó)熱情,讓我感覺(jué)到心里特別踏實(shí),感覺(jué)到生活充滿了幸福感,并且對(duì)著未來(lái)信心十足,進(jìn)一步讓我相信世界是美好的,最終仍然是美好的。這就等同于我們的生命始終是美好的。
今年我發(fā)朋友圈最多的一句話是,“如果我低著頭,一定不是因?yàn)檫^(guò)時(shí),而是因?yàn)楸池?fù)著恩情”。生而為人是沒(méi)辦法的事情,我很抱歉。生命是一個(gè)線段,也是沒(méi)辦法的事情,所以我只好濃烈地增加生命的寬度。可韌性,也許就是我們?nèi)松Φ囊饬x。很多時(shí)候,我們感覺(jué)到生活是鈍性的,需要我們不停地打磨出生活的光澤、銳角和刃口,以便保證我們的七情六欲,保證我們的喜怒哀樂(lè)。于是就有了我們對(duì)這個(gè)世界的感知,對(duì)父母的感知,對(duì)兄弟姐妹的感知,對(duì)朋友們的感知。
俗話說(shuō),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所以人生才會(huì)變得特別美好,令人珍惜。我們不管失去了什么,無(wú)論如何不能失去對(duì)生活的熱愛(ài),熱愛(ài)產(chǎn)生信仰,產(chǎn)生力量,沒(méi)有了信仰的人生,怎么活都是一條軟綿綿的道路。我喜歡被文字點(diǎn)亮的夜空,喜歡感受文字里涌起的波浪,喜歡那些獨(dú)自綻放在一些角落里的花,喜歡他們?cè)谀瑹o(wú)聞之中依然不負(fù)春光。
生命是一個(gè)過(guò)程,所以我們時(shí)時(shí)刻刻都要做最努力的自己,無(wú)論何時(shí),我們回頭,對(duì)來(lái)時(shí)的路都不感到后悔,所有的結(jié)局都是人生最美好的結(jié)局。
其實(shí)說(shuō)到這里我特別感慨,特別感恩,感恩這個(gè)世界讓我們有著活生生的生命,感恩即將到來(lái)的2024,讓我們對(duì)生活充滿了渴望,也祝朋友們?cè)谖磥?lái),一直開(kāi)開(kāi)心心,圓圓滿滿,盡有我們生命最大的努力,去發(fā)出能夠溫暖這個(gè)世界的光。朋友們,我們一起加油,一起為了這個(gè)世界變得更加美好而加油。

聯(lián)結(jié)的力量,
可以使柔軟的水草變成浮島。

以前我去旅游的時(shí)候,當(dāng)?shù)厝藙澊瑤胰チ艘粋€(gè)地方,在一個(gè)大湖上,有許許多多水草纏結(jié)在一起,變成了一塊厚厚的大氈子,浮在水面上,像個(gè)筏子,非常的結(jié)實(shí),人可以踩在上面行走,里面還有野鴨,還有各種水鳥(niǎo)筑巢產(chǎn)卵,為許多動(dòng)物提供了容身之地,有一些特別毛茸茸的草,會(huì)存蓄陽(yáng)光照在上面的熱量,踩上去能感覺(jué)到特別溫暖,你可以看到有小魚在空隙里游來(lái)游去,還有更微小的生物。
看到“與世界的聯(lián)系”這個(gè)主題的時(shí)候,我就想起了這片水草氈子。那種聯(lián)結(jié)的力量,可以使柔軟的水草變成浮島,能承托起很重的分量,容納許許多多細(xì)小的、相互依存的生命,要是還有一點(diǎn)動(dòng)力,又比較志同道合,也許還能變成筏子,前往某個(gè)方向。我們的生命在這浮世上也是同樣非常細(xì)小和短暫的。去做更多事,與更多人發(fā)生聯(lián)結(jié),才有可能盡量試著避免沉下去,被大風(fēng)或湍流卷走、吹飛、粉碎。和朋友相處,發(fā)展自己的興趣,看書,這些都能讓我有抓住四周、不飄飄蕩蕩的感覺(jué),能定下來(lái),定住神,感受自己跟從前過(guò)去的人和世間萬(wàn)物都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
從前兩年開(kāi)始我被苔蘚植物吸引了,它們小而柔軟,仔細(xì)觀察的話千姿百態(tài),它們能在很惡劣的環(huán)境中生存,能儲(chǔ)存大量的水,再在干旱時(shí)緩慢地釋放出來(lái),即使經(jīng)歷長(zhǎng)期干旱,也能再次恢復(fù)生機(jī),它們還能將巖石轉(zhuǎn)變成土壤,或?qū)⒇汃さ耐寥擂D(zhuǎn)變成適合種子萌發(fā)和生長(zhǎng)的生境。很多時(shí)候人們會(huì)用苔蘚來(lái)當(dāng)作墊材,保護(hù)其它植物。我想我也可以是苔蘚,我們可以彼此保護(h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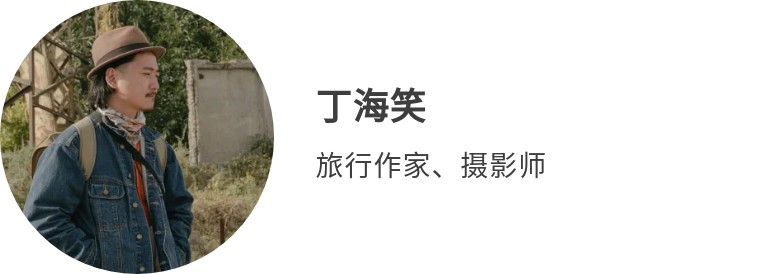
曾經(jīng)在《搭車十年》里寫過(guò)一段話:“我討厭不停的旅行,但我更討厭一蹴而就的生活,直到找到真心愿意和我去哈薩克斯坦牧羊的人……”二〇二三年,我去了哈薩克斯坦。這其實(shí)是一趟返魅之旅,異域帶給我的不再是饜足之感,而是些許漠然。資訊越來(lái)越冗余,那種牧羊人萬(wàn)花筒般的萬(wàn)千世界已然消失,一切皆可數(shù)字化,探索的樂(lè)趣被信息檢索取代,旅行者皆被手機(jī)驅(qū)牧。
哈薩克斯坦是我重返世界的第一站,但我對(duì)它的異邦想象卻早已消逝,況且還有一大堆生活所要考慮的事宜,也就喪失了游牧而居帶來(lái)的浪漫意象。遠(yuǎn)行只會(huì)讓我變得越來(lái)越平靜,世界坍縮得非常小,小得和牧羊人的帳篷一樣。故事不過(guò)“一切遙遠(yuǎn)而陌生的陳述”,以及時(shí)間與荒片的堆疊。
我一直都認(rèn)為,我腳下不過(guò)是方寸之地,談不上旅行,更無(wú)所謂壯游,環(huán)亞僅是逃離之借口,無(wú)奈為此荒游數(shù)年,竟成了主業(yè)。不知是否因?yàn)樾木车钠鸱以絹?lái)越感覺(jué)得到,很多東西永遠(yuǎn)都回不來(lái)了,譬如大部分平庸的快樂(lè),有些錢,某些遺憾,初中抽屜里的一些小說(shuō)手稿,曾經(jīng)念念不忘的科索沃明星主持人……
而我知道還會(huì)有更多更美的時(shí)刻,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朋友和回憶都會(huì)朝我涌過(guò)來(lái),釜山港的日出,古登鄉(xiāng)的迷夜,未赴的酒局,會(huì)再來(lái)呢嘎。

我對(duì)澎湃新聞懷著非常深厚的感情。2018年夏天“鏡相”欄目創(chuàng)立,我受邀成為專欄作者,借此機(jī)會(huì),探索世界的遼闊:我以深圳為坐標(biāo),去往寒冷陌生的東北小鎮(zhèn),也深入離開(kāi)了很久的故鄉(xiāng)湖南,同時(shí)書寫廣東在地故事。我也嘗試探索人心的遼闊,書寫友誼、絕望和愛(ài)。兩年后,部分女性故事結(jié)集成書《木蘭結(jié)婚》,是那兩年一個(gè)珍貴的總結(jié),也是志同道合的美好見(jiàn)證,可以說(shuō),我對(duì)“鏡相”提供的支持是心存感激、永不相忘的。五年過(guò)去了,我依然在以獨(dú)立記者的方式與世界創(chuàng)造聯(lián)系。
今年夏天,我搬到海南居住半年,觀看之前不熟悉的海島生活,在“鏡相”發(fā)表了海南故事《鷺鷺從此跑得遠(yuǎn)遠(yuǎn)的》,入選了澎湃支持創(chuàng)作者的“9月口碑佳作榜”,我在文中寫過(guò):“當(dāng)開(kāi)始在一個(gè)誰(shuí)也不認(rèn)識(shí)的地方重新生活,我會(huì)在抵達(dá)的第一個(gè)晚上,尋找一份可能長(zhǎng)久的與人的聯(lián)結(jié)”;同時(shí),我也希望自己對(duì)世界保持開(kāi)放,敢于接受智識(shí)和陌生領(lǐng)域的挑戰(zhàn),會(huì)不定期出差,撰寫人物特稿,采訪了建筑師胡如珊、繪本畫家蔡皋、作家張怡微、影視明星和散文作家林青霞等在某一領(lǐng)域表現(xiàn)杰出的女性。
雖然有時(shí)人難免陷入低迷,但我希望自己睡一覺(jué)之后能夠像太陽(yáng)一樣打起精神。我希望五年前,澎湃“鏡相”帶給我的勇敢和熱情的品質(zhì),能夠保持得更久一點(diǎn),再久一點(diǎn)。要是能保持到八十歲就好啦。畢竟個(gè)人的品質(zhì)是我們?cè)谶@個(gè)不確定的世界里,唯一可能擁有的美好確定。
本文為澎湃號(hào)作者或機(jī)構(gòu)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fā)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jī)構(gòu)觀點(diǎn),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diǎn)或立場(chǎng),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fā)布平臺(tái)。申請(qǐng)澎湃號(hào)請(qǐng)用電腦訪問(wèn)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yíng)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