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陳曉律:英國民族主義的回歸——從帝國到聯邦
歐洲作為一個文化統一但政治分裂的文明單位,是現代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發源地。自1500年開始,民族國家興起導致的歐洲分裂和二戰后的重新融合成為世界歷史上最獨特的現象之一。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陳曉律的新著《魅力與迷惘:歐洲民族主義五百年》梳理了歐洲各主要民族國家發展歷史,力圖破解歐洲民族主義的迷思,闡明歐洲民族國家演進的歷史趨勢。本文節選自其中討論英國民族主義的章節。

陳曉律教授
殖民地的民族獨立意識增強,英國的實力經過二戰的打擊繼續衰落,加之國際輿論的壓力,使得英國在殖民問題上進退維谷。抓住不放,無疑與時代潮流背道而馳,勢必被斥責為人人痛恨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國家,更何況英國也無力再把殖民地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自動放棄,任苦心經營的帝國毀于一旦,也會被世人看作是英國衰落的表現,更是某一屆政府無能的結果。這是英國政府和每一個英國人都不甘心接受的結果。更不必說帝國與聯合王國的利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統計表明,英國的資本輸出在1958—1960年約有60%流向帝國其他地區。即使英國不再是世界霸權國家,依然擁有遍及世界的經濟利益。英國進口羊毛的66%、進口奶油的55%、進口肉類的29%依賴于澳大利亞,50%的非鐵金屬制品依賴于南非和加拿大,81%的茶葉依賴于印度,54%的進口谷物來自加拿大,糖類則來自西印度群島,橡膠來自馬來亞,金屬和蔬菜制品來自赤道非洲。換言之,英帝國對于英國實在太重要了,英國民族主義是否回歸英倫三島,并不僅僅是一個民族情感問題,更多地涉及英國人自身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
但是,戰后的自治領變得更加成熟,要求取得更為完整的主權。而在英國的殖民地中,即使在二戰期間,自治運動與獨立運動也從未間斷。二戰后的非殖民化進程迅速發展,英國的殖民體系趨于瓦解。這一過程經歷了三個階段:戰后初期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南亞和東南亞國家爭取民族獨立,英國從這一地區撤出;50年代中期以后,中東和阿拉伯國家掀起反帝斗爭,英國從此結束了對中東和阿拉伯世界的控制;50年代末及60年代是非洲人民的覺醒時期,大批英屬殖民地、保護國擺脫了殖民統治。獨立后的英帝國成員多以主權國家的身份加入了英聯邦,這一舉措使英聯邦居然經歷了一次“輝煌”,其成員國數目猛增,英國人似乎又找回了帝國時代的光榮和夢想。然而,英聯邦畢竟不是英帝國,已經不再能夠完全由英國控制,英聯邦日益松散、衰落,不過是全球化進程中一個帶有英屬印記的沒有強制性權威的國際組織而已。
1957年3月6日,加納宣布獨立,1960年通過公民投票,成為一個獨立的共和國留在英聯邦內。1960年7月,索馬里獨立。1960年10月,尼日利亞宣布獨立。1961年4月,塞拉利昂獨立。1961年8月,喀麥隆獨立。1961年12月,坦噶尼喀獨立。1962年10月,烏干達獨立。1963年12月,肯尼亞獨立。1963年12月獨立的桑給巴爾在1964年與坦噶尼喀合并成立坦桑尼亞。1964年7月,尼亞薩蘭獨立,并改名為馬拉維。1964年10月,贊比亞獨立。1965年2月,岡比亞獨立。1966年9月,“貝專納保護地” 獨立,定名為博茨瓦納。1966年10月,巴蘇陀蘭獨立,定名為萊索托。1968年3月,毛里求斯獨立。1968年9月,斯威士蘭獨立。
由于英國對這些國家的民族主義基本采取“和平”政策導向,所以獨立后這些國家大多繼續留在英聯邦內,但他們畢竟再也不是殖民地。到1974年2月向風群島的格林納達獨立時,幾乎每個殖民地都擺脫了英國的殖民統治。
英帝國無可奈何地撤離了,不過它有意無意留下的隱患至今影響當地的政治經濟發展,也威脅到地區安全。印度、巴基斯坦獲得獨立,但雙方關于宗教與領土的爭端仍在繼續,孟加拉國是沖突的產物,克什米爾問題仍然困擾著印度和巴基斯坦。英國早在1947年2月就宣布將巴勒斯坦問題提交聯合國,結束了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然而“英國政治家們從不斷變化的眼前利益出發,在巴勒斯坦推行一種毫無原則、反復無常的政策,隨意踐踏當地人民的正當權益,結果人為制造出一系列矛盾,種下了今日動亂的禍根”。巴勒斯坦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日趨嚴重,從歷史的角度看,英國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不過,從虛幻的世界帝國回歸其民族國家的本位,畢竟可以使英國人擺脫很多不必要的麻煩,對于構建新的民族國家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然而,要使英國人真正回歸自己的民族“本位”,又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為英帝國的擴張與英國現代民族的塑造幾乎同步進行,兩者之間產生了其他民族幾乎難以想象的密切關系。同時,英國在擴張過程中向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大量地移民,而一些殖民地的人民作為英國一些技術或簡單低級勞動需求的補充勞力,也來到了英倫三島,并且英語已經成為廣大的英帝國區域內的公共語言。這就使英國人要割斷與英帝國的聯系,回到民族國家的本位,比其他國家和民族更為麻煩。而英聯邦國家之間的人員流動也產生了英國民族認同的新的困難,“英國的移民歷史和民族認同是通過作為殖民帝國的大英帝國和英聯邦的核心國家而打上了深刻的歷史烙印”。因此,當二戰結束,英國在1948年實施了《英國國籍法》,將英聯邦的公民分為兩類:一類是獨立的英聯邦國家公民,另一類是聯合王國及其殖民地公民,但兩者都有移居英國的權利。一直到1962年的《英聯邦移民法》實施之前,英國本土對其他的英聯邦國家和英國殖民地的居民都是完全開放的。當20世紀60年代的亞非拉反殖民斗爭取得偉大勝利之時,在原英屬殖民地的大量英國外遷移民和殖民地的非白人移民不得不進入英國。“從1953年到1962年間,到達英國的來自殖民地的移民數量估計有39.1萬人,這其中包括每年的6000個伊朗人。到了1968年,由于肯尼亞政府推行非洲化的政策,不承認雙重國籍,發生大規模的排擠持有英國護照的亞裔人的現象,于是出現了大批亞裔人移民英國的浪潮。依據英國當時的移民法和國籍法,他們屬于英國公民,因此可以自由地返回英國。這樣,僅在1968年的頭兩個月就有1.3萬人來到了英國。”
這種情況一直到1971年后才開始改變,英國終于開始限制來自英聯邦國家的移民。但出于殖民帝國的情結,英國依然保持著與這些國家的種種特殊和優先關系。據估計,英國每年僅非法移民就有萬人左右,而目前在英國的非法移民總量應該有100萬。由于各種類型移民的涌入,英國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種構成發生了變化,英國已經逐漸從單一民族國家向多種族國家轉變。現在,英國已經有54個種族。在某種意義上,英國已經是一個“多民族國家”。
“生而自由的英國人”是英國自大憲章以來一直引以為豪的立國原則,也是英國的“國民性”之一。不過這一原則在英帝國的擴張過程中已經變得含混不清,畢竟征服者要使這樣的原則貫徹始終是很困難的。英國的侵略擴張與民族利己主義的行為使自身形象如同海盜,而英國主張的自由法治卻又使其帶上了一絲人道主義的光彩。但在20世紀,經歷了兩次慘痛的世界大戰和殖民地的解放與獨立后,這樣一個矛盾的混合體已經在悄然地發生改變。此前自由與征服的形象已經讓位于一種英國似的鄉村形象:適度的,徐緩的,帶著薄霧的田園般的,甚至有些可愛的形象。傳統的英國性似乎在消失,這主要是由于兩個方面的影響:大眾傳媒的作用與大眾旅行的盛行。而各種移民大量持續地進入英國本土,也改變了英國的人口構成。在戰后的50年中,英國的認同問題已經轉為英國認同的危機。因此,有學者預測,以后英國的認同也許會被歐洲認同取代,而“英國人的故事也就結束了”。
這樣的預測似乎過于悲觀,因為最近蘇格蘭獨立運動的勢頭證明這個故事顯然還未到結束之際。但不能不承認,在世界民族主義的幾種類型中, 英國式的民族主義顯然是極為獨特的。按照漢斯 魯道夫·維克的看法,這種高度工業化國家民族主義的特點就是在其現代化的過程中,使國家政權與經濟利益能在民族的理念中聯合起來,而資產階級就是這種民族政治最積極的支持者,因為它認為這有助于促進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與世界其他一些民族主義的發展進行比較,可以認為英國民族主義發展的最大特點是其發展歷程完全與英國的現代化進程一致。換言之,英國民族主義的訴求與英國現代化的目標幾乎自然地融為一體。由于這樣的特點,人們往往更多地關注英國現代化特點,而忽略了其民族主義的性質。也正是由于這樣的特點,英國民族主義的種族色彩并不強烈,這使人們在關注其特點時,愿意更多地從現代觀念而不是種族特點來分析問題。
而這種現代觀念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強調人們的權利。近代以來英國幾乎所有有關政治的書籍,都在不同層面上強調人們的權利。這些權利被視作基本的人權,包括人身、言論、結社和財產四大自由,人身自由被視為自由最重要的支柱。1765年,英國在貨幣與其他的案件中就明確堅持這樣的原則,即對一個沒有被法官定罪的人進行拘捕是非法和無效的。同時,假如一個人被冤枉監禁、襲擊或毆打,他或她還可以通過社會和普通法獲得一系列救助。此外,在英國還有一些古老的對個人自由的保證,如令狀等,確保每一個人都能要求被帶到法院進行公正的審判。而能夠自由表達政治意愿被認為是一個民主社會最基本的權利,缺少這樣的權利則被認為是最明顯的壓制的征兆。政治基本上是一種集體的行為,是個人自愿的組合,因此,結社自由也被認為是基本的權利之一。財產自由則被認為是最核心的權利,英國人的家通常被認為是他自己的城堡,這樣的觀點也被英國的法律承認,早在1603年塞姆伊案件的判決中就宣布,如果一個盜賊進入一個人的房子試圖搶劫或殺人,那么這個人或他的仆人都有權利殺死盜賊以保護自己的生命和財產。
這樣的觀念在英國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人們認為這是一種不證自明的真理。應該說,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英國民族主義是一種較為理性的民族主義,它最發人深思的地方在于,這種民族主義賦予了這個共同體內所有成員應有的權利,并讓所有成員始終都有權維護自己的權利。一種以權利為紐帶聯接起來的共同體,不僅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而且比任何強制性的共同體都富有凝聚力。這或許是英國民族主義不那么極端、容易被人忽視的真正原因。同時,以權利為紐帶形成的共同體,似乎也更容易實現自己的現代化目標,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獲得更大的利益。
因此,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如何使民族主義的訴求與自己的現代化目標合拍,應該是值得繼續思考的問題。
當然,英國這種幾乎是“自然”的民族主義也產生了一些微妙的麻煩,那就是它的民族整合工作似乎被遺忘了。英國的“自然”邊界在哪里,應該如何界定自己的民族特性,外來移民是不是要融入英國社會等等,英國人似乎從未考慮過這些“不入流”的問題。在英國脫歐之后,蘇格蘭的獨立問題也開始發酵,如何處理這一棘手的問題,對長期順風順水發展的英國人而言是一個巨大的考驗。
英國民族主義的獨特之處,在于它認為其他民族才會有民族主義,而其自身是超越民族主義的存在。英國人產生這種傲慢的原因,在于英國的民族主義將其價值訴求尤其是個人權利放在首位,淡化了一般民族主義那種種族的色彩。由于這些價值訴求與英國的普通法、憲政架構乃至基層自治纏繞在一起,的確很難厘清一個剝離了上訴關系、十分“純粹”的英國民族主義。在這個意義上,英國民族主義的確不是一種典型的民族主義,它是民族主義中的另類,是英國發展歷程中的特殊產物。也正因如此,不認真研讀英國歷史,就無法真正理解英國這種“特殊”的民族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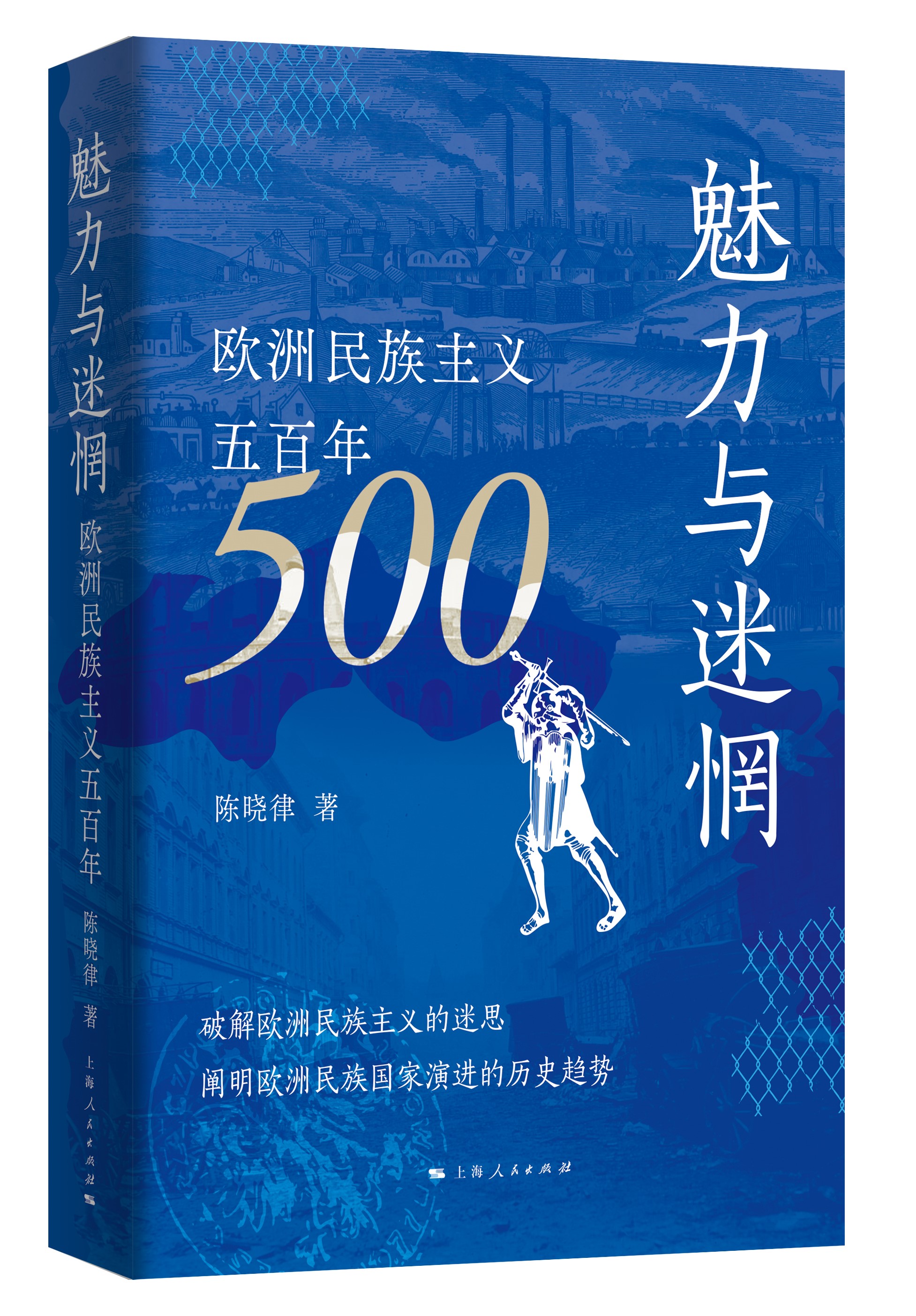
本文節選自《魅力與迷惘:歐洲民族主義五百年》,陳曉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12月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