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破產(chǎn)法的溫度|現(xiàn)代破產(chǎn)法為什么強(qiáng)調(diào)“第二次機(jī)會”?
近五十年來,世界各國的破產(chǎn)法都進(jìn)入一個十分強(qiáng)調(diào)“第二次機(jī)會”的時代。回顧這段歷史,重整的全面普及、細(xì)化和深入,無疑是其中的主旋律。細(xì)言之,從重整的預(yù)重整、從上市公司重整到中小企業(yè)重整、從個體重整到集團(tuán)重整……重整制度可以說花樣百出,不一而足。
現(xiàn)行美國破產(chǎn)法,無疑是“第二次機(jī)會”的代表。1978年《美國破產(chǎn)法》在既往經(jīng)驗(yàn)的基礎(chǔ)上,全面升級第11章重整程序。即便在個人破產(chǎn)法領(lǐng)域,2005年《破產(chǎn)濫用防止及消費(fèi)者保護(hù)法案》的通過,也讓原本以破產(chǎn)清算和免責(zé)為本位的個人破產(chǎn)法,頗具有爭議性地進(jìn)入重整的時代。
在現(xiàn)代破產(chǎn)法中,“第二次機(jī)會”理念風(fēng)靡全球。2019年歐盟通過的《預(yù)防性重組指令(第2019/1023號)》,其序言第1條、第4條中,均提到了“第二次機(jī)會”。該指令序言第1條宣布立法宗旨,即在不影響職工基本權(quán)利和自由前提下,該指令旨在移除成員國法差異導(dǎo)致的障礙,以便確保:
(1)陷入財務(wù)困境但有拯救價值的企業(yè)和企業(yè)家,都能夠通過成員國的預(yù)防性重組框架來保持繼續(xù)經(jīng)營;
(2)誠實(shí)但支付不能(insolvency)或者過度負(fù)債(over-indebted)的企業(yè)家,能夠在合理時間后,從對債務(wù)的全面免除中受益,并因此獲得“第二次機(jī)會”;
(3)改進(jìn)涉及重組、破產(chǎn)和債務(wù)免除的既有程序,尤其注重縮短其期限。該指令序言第4條確認(rèn)了一個事實(shí),即在給予陷入財務(wù)困境的企業(yè)家“第二次機(jī)會”方面,不管是在免責(zé)考察期的長度還是免責(zé)條件方面,歐盟各成員國差別確實(shí)太大。
在歐美社會之外,大量發(fā)展中國家也在以重整制度為圭臬,全面革新各國的破產(chǎn)法。與此同時,聯(lián)合國國際貿(mào)易法委員會在破產(chǎn)法趨同方面的努力,讓“第二次機(jī)會”理念接近成為全球性標(biāo)準(zhǔn)。過去十多年間,世界銀行營商環(huán)境評估也以重整為核心設(shè)計“辦理破產(chǎn)”指標(biāo),也為全球范圍內(nèi)各個經(jīng)濟(jì)體圍繞重整展開互“卷”提供了重要動力。
那么問題是,現(xiàn)代破產(chǎn)法為什么特別強(qiáng)調(diào)“第二次機(jī)會”?
最近拜讀美國學(xué)者勞倫斯·弗里德曼的《選擇的共和國:法律、權(quán)威與文化》,可能為這個問題找到部分答案。
弗里德曼是斯坦福大學(xué)終身教授,美國當(dāng)代著名法學(xué)家,在比較法與法律文化學(xué)研究領(lǐng)域享有世界級的聲譽(yù)。這本《選擇的共和國:法律、權(quán)威與文化》是其代表性作品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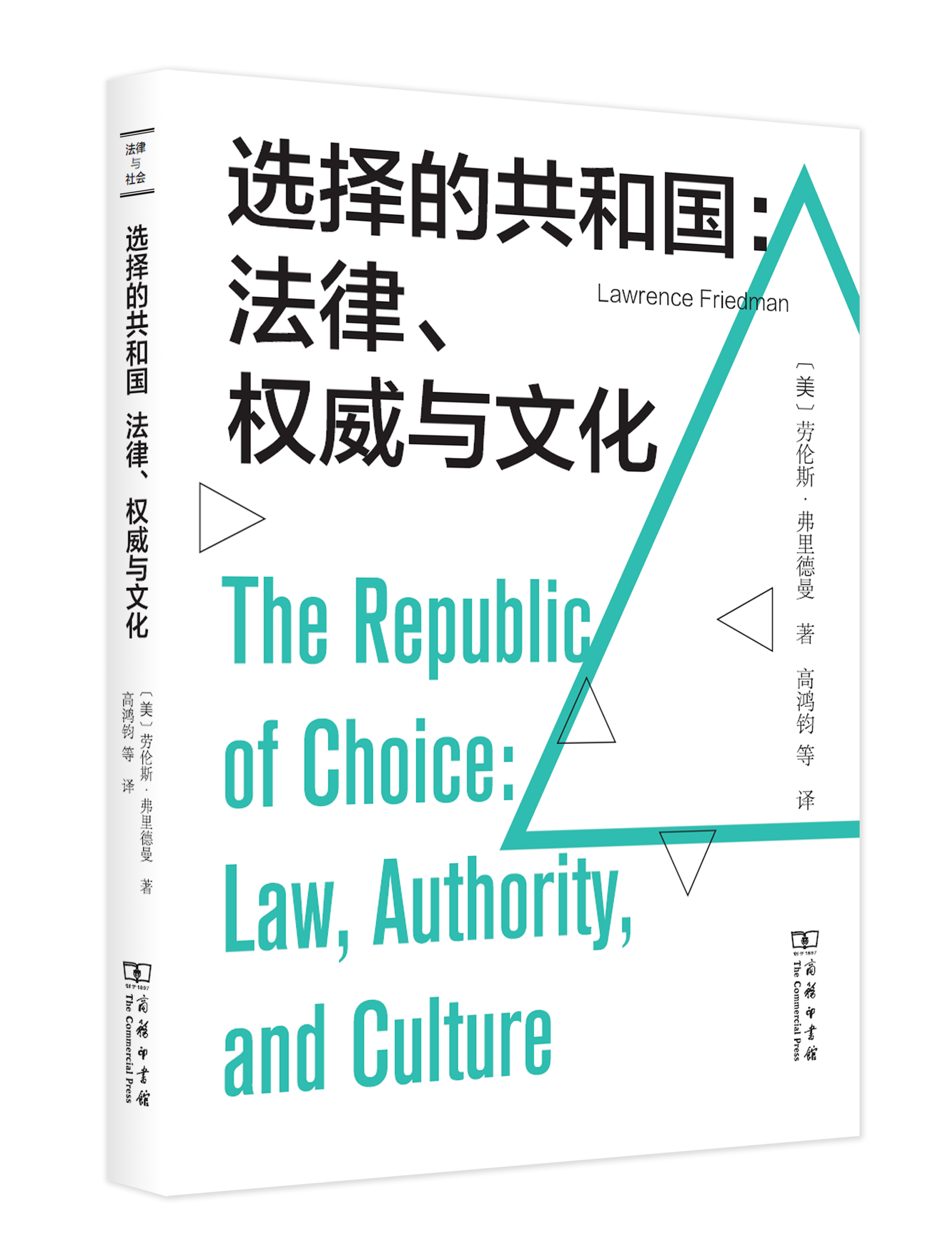
《選擇的共和國:法律、權(quán)威與文化》,勞倫斯·弗里德曼 著,高鴻鈞 等 譯,商務(wù)印書館2023版
在弗里德曼看來,以個人主義和消費(fèi)經(jīng)濟(jì)為核心元素的現(xiàn)代化,創(chuàng)造了“選擇共和國”;在這種經(jīng)濟(jì)模式驅(qū)動下,選擇文化在歐美諸國的國家社會制度及法律制度中,都占據(jù)著重要地位,影響深遠(yuǎn)。按照弗里德曼的觀點(diǎn),選擇的背后,既是制度的豐富、權(quán)利的勃興,也是寬容理念被廣泛接受后順理成章的后果。當(dāng)選擇文化席卷全球,破產(chǎn)法自然難以置身“化”外。
弗里德曼提出,破產(chǎn)制度是現(xiàn)代社會對抗不確定性和風(fēng)險的保護(hù)傘。這個觀點(diǎn),是弗里德曼通過歷史比較發(fā)現(xiàn)的。
弗里德曼指出,“在19世紀(jì)或早一些時候,生命的脆弱程度是我們現(xiàn)在難以想象的。……工作、生活也充滿了不確定性和風(fēng)險。沒有貸款擔(dān)保,沒有補(bǔ)貼,也沒有預(yù)防和處理災(zāi)難的公共計劃,破產(chǎn)制度也尚未成熟,濟(jì)貧法調(diào)整范圍狹小而粗暴。人們終日在充滿災(zāi)難的陰影中生活,與饑餓和貧窮相伴。”在這樣的氛圍下,“雖然社會允許甚至鼓勵某些冒險活動(主要是經(jīng)濟(jì)方面的),但它也會相當(dāng)嚴(yán)厲地懲罰失敗者。”
而到了20世紀(jì),社會觀念與時俱進(jìn),對于選擇的需求與日俱增,對于那種不可逆轉(zhuǎn)甚至剝奪未來選擇權(quán)的選擇,同仇敵愾。社會觀念的變化,推動了法律的革新。在破產(chǎn)法領(lǐng)域,“第二次機(jī)會”成為一種原則。弗里德曼論述道:
在破產(chǎn)法領(lǐng)域,境況不可逆轉(zhuǎn)性的原理在字面上不怎么重要,但在實(shí)踐中卻十分重要,這是推動第二次機(jī)會被承認(rèn)的動力的商業(yè)形式。如果沒有破產(chǎn)制度或者其他一些類似的制度安排,那么一個由于經(jīng)營失敗或者其他原因而債臺高筑的企業(yè)家,也許就無可避免地完全被毀了。
破產(chǎn)制度是一種復(fù)雜的法律安排。它的目標(biāo)之一就是確保無論破產(chǎn)企業(yè)還余下多少財產(chǎn),這些財產(chǎn)都要在債權(quán)人之間公平分配。但是,它同樣也讓破產(chǎn)者有一個干凈的、全新的開始。破產(chǎn)是現(xiàn)代法律理念的一個必然組成部分。當(dāng)然,它產(chǎn)生與商業(yè)相關(guān);曾幾何時,它是為商人而不是為大多數(shù)群眾保留的特權(quán)。但是在現(xiàn)行制度下,大多數(shù)普通人都可以從債務(wù)中完全脫身出來,然后像一個新生兒一樣再次出現(xiàn)。破產(chǎn)制度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紀(jì);1898年通過的、現(xiàn)在仍然有效的美國破產(chǎn)法確立了一些全國適用的準(zhǔn)則。
為了上述這段論述,弗里德曼可謂下足功夫。在這段論述的腳注中,弗里德曼既列舉了查爾斯·沃倫1935的名著《美國史上的破產(chǎn)》,也提及彼得·克勒曼1974年的佳作《美國的債務(wù)人與債權(quán)人:支付不能、債務(wù)拘禁及破產(chǎn)(1607-1900)》。就美國破產(chǎn)法史而言,這兩本佳作可謂是開山的經(jīng)典。
在弗里德曼看來,“失敗者的正義”概念的崛起與流行,與破產(chǎn)法律制度與“第二次機(jī)會”的緊密結(jié)合遙相呼應(yīng)。弗里德曼指出,“失敗者的正義”作為民主觀念的核心,與“安全網(wǎng)”理念互為表里:“安全網(wǎng)”作為經(jīng)濟(jì)上的緩沖帶,成為福利國家的基礎(chǔ);而“失敗者的正義”既是社會性的緩沖帶,也是針對個人的緩沖帶,它以尋求權(quán)利和提出主張中的失敗者作為適用對象。弗里德曼特別指出,從概念和后果上,“失敗者的正義”與破產(chǎn)、失業(yè)補(bǔ)償?shù)确砂才胖g,具有可比性。
當(dāng)然,破產(chǎn)并不必然等于“第二次機(jī)會”。弗里德曼很清醒地指出,“……比如前文提及的破產(chǎn)制度,它作為一個偏向第二次機(jī)會的例證,顯示出境況不可逆轉(zhuǎn)性是多么不受贊同。但是,沒有人會經(jīng)歷了破產(chǎn)程序而毫不受損。并且,在某種程度上破產(chǎn)制度自身就是第二次機(jī)會的對立面:它是債務(wù)之劇的最后一幕;它意味著貸款之門永久關(guān)閉了。在某種意義上,損失和債務(wù)會變成不可逆轉(zhuǎn)的負(fù)擔(dān),選擇必須在破產(chǎn)和毀滅之間做出。”
即便如此,“第二次機(jī)會”理念依然為現(xiàn)代破產(chǎn)制度注入活力,甚至成為指導(dǎo)現(xiàn)代破產(chǎn)制度進(jìn)化的元規(guī)則。如果沒有“第二次機(jī)會”理念的勃興,可能現(xiàn)代社會的債務(wù)人,還只能在破產(chǎn)清算與和解程序之間猶豫和徘徊。正是在“第二次機(jī)會”的刺激下,破產(chǎn)制度進(jìn)入選擇的時代,越來越多的債務(wù)人都可以量體裁衣,選擇一款性價比最高的破產(chǎn)程序,通過“第二次機(jī)會”獲得經(jīng)濟(jì)上的新生。也只有從“第二次機(jī)會”的原點(diǎn)出發(fā),才能夠理解為什么破產(chǎn)清算作為破產(chǎn)法的底層制度依然存在,但其重要性卻大大降低;才能夠理解為什么不管是個人、企業(yè)、地方政府乃至國家,都試圖在重整制度的護(hù)翼下,依托“第二次機(jī)會”東山再起。
宋代詩人楊萬里詩云,“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現(xiàn)代破產(chǎn)制度與“第二次機(jī)會”結(jié)合,恰恰是這種歷史趨勢的體現(xiàn)。我國《企業(yè)破產(chǎn)法》修訂工作方興未艾,大到理念、中到制度、小到措辭,都需要盡可能尋求共識。毫無疑問,深刻理解“第二次機(jī)會”,無疑會為相關(guān)制度的革新和建構(gòu)提供底層邏輯。
就此而言,弗里德曼和他的選擇文化論,還有他在選擇文化體系下對現(xiàn)代破產(chǎn)制度的精準(zhǔn)評析,都會為我們提供必要的參照。
(作者陳夏紅為中國政法大學(xué)破產(chǎn)法與企業(yè)重組研究中心研究員)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