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梓者法身:跨學科的書籍史研究
2023年11月18日至19日,由浙江大學文學院主辦、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研究所承辦的“梓者法身:近世書籍文化跨學科工作坊”在杭州召開。來自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四川大學、湖南大學、安徽大學、杭州師范大學、江西師范大學、贛南師范大學、閩南師范大學、香港樹仁大學、上海社科院、天一閣博物院等高校和科研單位的三十余位學者,發表了各自有關書籍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
“梓者法身”出自萬歷十八年(1590)王世貞應紫柏真可之請為新刻《大藏經》所作募緣疏:“百應者化身也,不動者法身也。梓者法身也,流傳者化身也。”工作坊試圖搭建一個促進跨界對話的平臺,邀請來自文獻學、文學、歷史學、宗教學、人類學等學科的學者,共同探討由印本串聯起來的整體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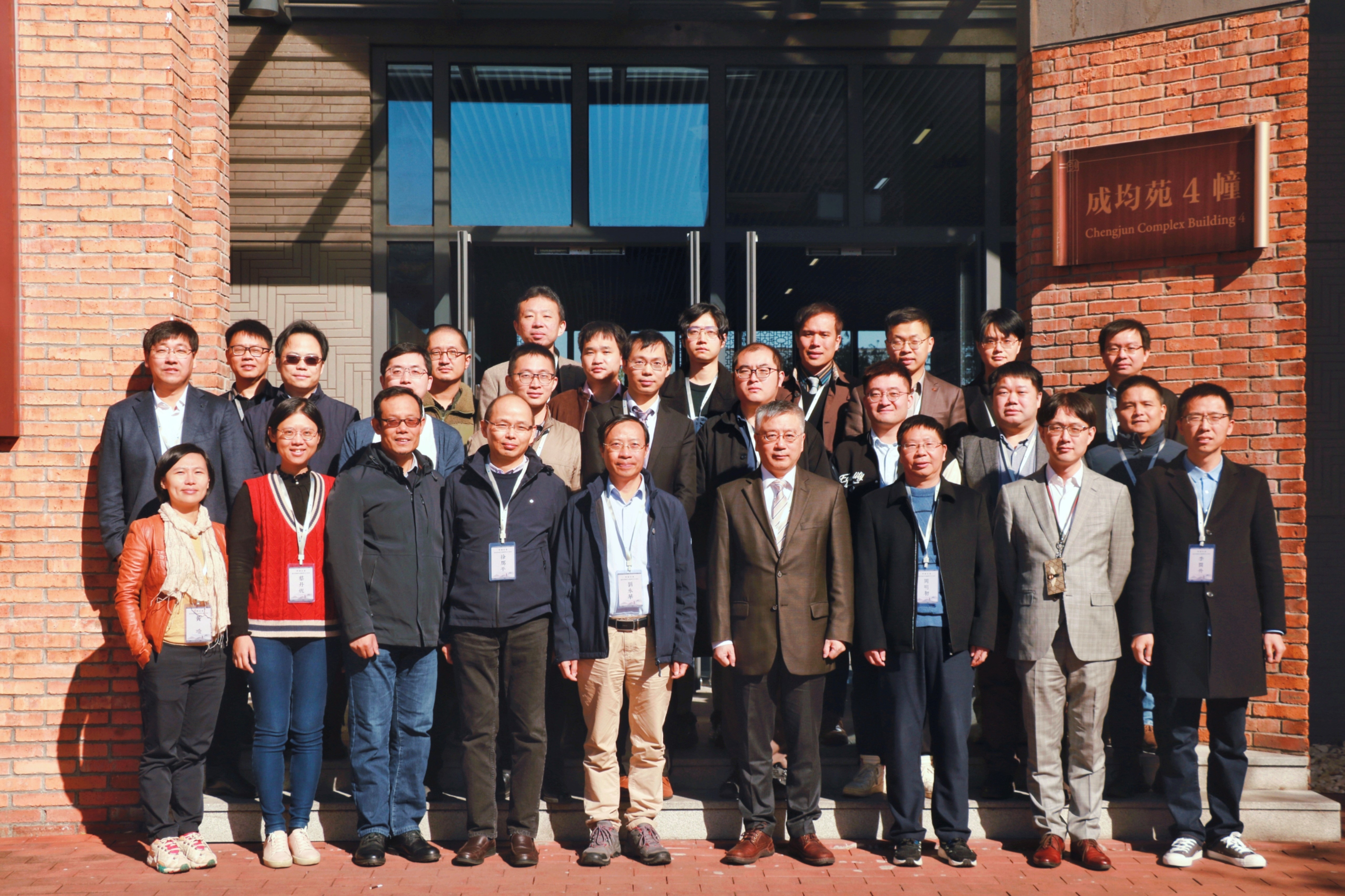
本文圖片均由宋佳霖拍攝
18日上午,浙江大學文學院徐隆垚研究員主持開幕式,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馮國棟、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周明初先后致辭。馮國棟提出,書籍史作為一個跨學科的研究對象,學術的專門分科可能對書籍史的問題造成遮蔽,不同學科的“會診”有利于發現和展開問題。周明初肯定跨學科的意義,同時也正視這一工作的難度。
首先,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葉曄教授主持下,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張伯偉教授作特邀講座《知識環流:佛教、政治與性別——東亞書籍史研究方法例釋》。
張伯偉以全球比較的視野審視東亞書籍史的現狀與前景,認為這一領域生機勃勃,不僅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依賴,還要對當下模式之不足加以批判改造。這迫使學者調整中國文史研究的重心,從對碎片化的新材料的癡迷膜拜,轉向探索原理性的理論方法。在東亞書籍與知識的“環流”過程中,域外刊本總是由于宗教、政治、個人等復雜原因而發生變容。南唐《祖堂集》傳入高麗之后產生了“海東新開印版”,后者將中華與東國的禪宗燈史匯為一脈,意在標榜“江西禪脈,總屬東國之僧”。海外漢學家的書籍史研究重心在于商業出版,但是東亞書籍史中王權與政治文化的支配作用不容忽視。如18世紀初朝鮮通信使與新井白石之間對話的《坐間筆語》《江關筆談》,引發不同國家、不同年代的讀者介入評價,其間產生的扭曲、沖突就與爭奪華夏正統的心態密切相關。

隨后,與談嘉賓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劉永華教授、復旦大學古籍所石祥教授就講座內容進行對話。
劉永華認為報告注意政治因素在“環流”當中的作用很有啟發性,而達恩頓對于審查、版權的研究就是對政治的強調。同時,也應注意漢文訓讀在“環流”中如何發揮作用,東亞“環流”與由拉丁語所連通的歐洲“環流”與有何異同,以及不同的階層如何參與“環流”等問題。石祥認為報告所言“環流”具有空間大、時段長的特點,其中蘊含諸多可能性。目前日本、韓國所藏各類漢籍著錄書目,內容和體例并不完備,亟待重整。另外,書籍版本流傳的中間環節也有待清晰化。

本次會議共分為七個專題。第一場“文本可曾凝定?”由復旦大學石祥教授主持。
許建業(香港樹仁大學)的報告主題是《凝而未定:明代古典詩歌總集之文本信息動態》,梳理了明代全錄式總集對經典文類文本的存儲實踐、對辨體式總集的刪述求精,以及讀者閱讀心態影響下的稗販挪借。與此前學者關于明代發生“文本凝定”的判斷不同,他提出明代古典詩歌總集體現出“凝而未定”的文本信息動態。
羅鷺(四川大學)《書棚本唐人詩集在明代中期的翻刻與流通》聚焦于明人翻刻宋本唐集的出版實踐。翻刻書棚本導源于弘治,至嘉靖年間成為一種普遍風尚。翻刻者并未完全忠實于底本原貌,而是進行了一定的加工,對底本有所校改或是增加了訛誤。這些新刻版本推動了書棚本唐人詩集在明代中期的流通與傳播。
徐隆垚(浙江大學)《宋元明的辨體與博古——比較文藝復興視野下近世文人歷史意識初探》關注近世文獻生成的底層邏輯。通過“文章辨體”觀察宋明文人的“時序意識”,通過“博古學”觀察其“證據意識”,這樣以宋元明的文本觀念和知識經驗為依托,與彼得·伯克關于“文藝復興歷史意識”的概念建構進行對話。
第二場“文字下鄉:近世以來中國基層社會的讀寫實踐”由北京大學陸胤主持。
朱忠飛(贛南師范大學)在《文字入畬:明清以來中國東南畬民的社會轉型與讀寫世界》中,指出文字入畬的歷史進程與畬民的社會結構轉型相互牽連,文字在明中葉后的畬民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同時畬民形成了自身的識字傳統,即在選擇學習識字的文本類型、文本形態和雜字歌中,保留了濃厚的口傳性遺跡。
黃瑜(中山大學)在《習字與立契:清代中國西南“洞苗”村寨的讀寫實踐初探》報告中,考察分析了“洞苗”村寨中一戶家庭延續四代使用的漢字文本性材料,結合該村寨的其它各類型契約文書,指出在清光緒年間,漢字所承載的契約規則、權利和義務觀念在整個都柳江流域由干流沿岸村寨向高山地帶村寨推廣而普及。
溫海波(江西師范大學)在《“文字下鄉”與近世中國雜字讀物的生產流傳》中,從時間、空間以及文本物質形態三方面,考察了明清以來各類地方性雜字的流傳使用情況,指出傳統中國鄉村不僅有多元的文字需求,還催生出輔助生產生活的文字供應和讀寫實踐。雜字的生產流傳是“文字下鄉”的結果,反映了近世中國社會文化史的進程。
董思思(閩南師范大學)報告題目是《新中國成立后干部群體的閱讀取向——以張健民帳簿中的購書記錄為中心》,以個案研究為出發點,考察了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層干部的閱讀書目和閱讀愛好,指出張建民的購書偏好與其干部身份和工作性質有明顯關系,并隨著新中國成立后不同歷史時段的變遷而變化,同時還受到了教育背景和讀寫能力的影響。
第三場“版本學·書志學·Bibliography”由四川大學羅鷺教授主持。
馮國棟(浙江大學)報告題目是《刻石填金 建閣庋藏:宋代佛教寺院對御集、御書的安奉與收藏》。將前世皇帝著述編集,并建閣收藏,至遲在真宗時代已漸成制度。終宋一代,幾乎每個皇帝皆有御集之編纂。宋代寺院高度重視御書、御集的迎取、裝幀、供養、保存,這一系列活動展示了宋代政治、王權與佛教的互動。
石祥(復旦大學)《〈斲硯山房書目〉〈存吾春室書目〉解題》中,討論了上圖所藏清人沈炳垣的兩種稿本書目。《斲硯山房書目》強調基于書籍內容性質的邏輯性,《存吾春室書目》則是體現實藏狀態的登記薄。沈氏兩本目錄的編目對象應是藏書的不同部分,將兩目合觀方能接近沈氏藏書的總體面貌。
李開升(天一閣博物院)《論〈西湖游覽志〉〈志余〉范鳴謙本和季東魯本》的報告中,討論了明中葉流行的《西湖游覽志》《西湖游覽志余》兩種版本的刻印情況。考證得知,范鳴謙本和季東魯本都屬于嚴寬刻本的“重修本”而非“重刻本”。版本研究應當明確區分“刻”與“修”,以避免版本混淆和性質認識不清的問題。
尹敏志(復旦大學)《明洪武初年庶人祭三代禮考》利用靜嘉堂文庫藏《漢書》紙背文書,證明洪武間明太祖已經改而允許庶人祭三代禮,并下令刊布胡秉中所繪祀先等三圖。成化以后相關認知混淆,誤以為胡秉中制定庶人祭三代禮。萬歷間類書的流通擴大此說影響。至清代方志中,胡秉中事跡日益失真。

第四場“重思明人之學:出版史與知識史的視野”由天一閣博物館副研究館員李開升主持。
王啟元(復旦大學)在《未有方冊之前:萬歷初年佛教文本出版與知識傳播》一改以紫柏真可為中心的敘事,指出若從佛教知識傳播的角度來看,早在嘉靖、隆慶之際,在紫柏僧團介入以前,出身大報恩寺的云谷禪師與其周圍的精英群體就已經開始關注了書籍流通這一佛教弘法方式,而這應當與嘉靖以來書籍印刷之發展有直接關聯。
耿勇(上海社科院)《明代后期當代歷史知識的生產和傳播——一個來自科舉鄉會試策問角度的考察》,指出明代正德以降的鄉會試策問中,以當代歷史為出題對象的問目比例顯著增多,這為當代歷史讀物在知識階層中傳播創造了社會空間。陳建《皇明通紀》的編撰意圖,就是為士子答題提供參考,實際也確實發揮舉業用書的功能。
張赟冰(北京師范大學)《晚明的史書出版與史學普及——以<皇明通紀>為中心》同樣關注《皇明通紀》,但更加聚焦于書籍的內部特征。著重分析出版者關于版面形式、符號標記以及副文本的設計,以及依托名家、增廣內容等策略。勾勒出這部晚明暢銷歷史書的制作細節,以及此形式與中下層讀者之間的互動關系。
湯志波(華東師范大學)《改寫與被改寫:書籍史視野下<雪庵清史>的成書與接受》以明萬歷間樂純編撰的《雪庵清史》為例,揭示樂純創作中采取的改寫、化用、套用等方式,以及《雪庵清史》后來為其他筆記繼續改編與襲用的命運。更進一步,思考商業出版環境下晚明小品文類的生產傳播模式及其文學史意義。
第五場“‘日記之眼’:顯微鏡下清人的讀寫與出版”由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黃瑜主持。
陸胤(北京大學)《格式化日常:日記預印版格的本土傳統與外來資源》注意到一種日記文獻的物質形態,即預先制作印好版格的簿冊后填寫日記。晚清商務印書館的日記冊移用明治日本從西歐導入“日記賬”的經驗。而作為南宋以來雕板刻書的衍生品,預印版格又與南宋以來“讀書修身”的傳統相始終。長時段的“格式”演進展示了讀書人的時間控制欲。
堯育飛(華中科技大學)《清人日記成“例”的讀寫“驅動”》提出日記體例是日記文體研究的關鍵。清人受所讀日記體例影響,在寫作實踐中不斷變化體例。以俞樾日記為例,可知日記成“例”受擬訂制例、日常生活、日記寫作技巧因素影響,最終表現為流動性的日記體例。諸種日記之間不斷影響,使得日記體例在晚清呈現趨同之勢。
吳欽根(湖南大學)《譚獻文章代筆及其“以代作入集”的文學史意義——以稿本<復堂日記>為中心》以晚清一般士人譚獻為切口,依據稿本《復堂日記》中有關詩文創作的詳細記載,考證出譚獻生平文章代筆的總體規模與文學網絡,并由此探究了“以代作入集”這一文學行為的產生及背后蘊含的文學史意義。
第六場“清代的通俗讀本與‘小讀書人’”由武漢大學文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員韋胤宗主持。
徐雁平(南京大學)在《桐城派前史:探求一種研究文學流派的新方式》中以潘江輯《龍眠風雅》與《龍眠風雅續集》的詩人小傳與關聯文獻為中心,嘗試探索古代文學流派生成機制研究的新路徑。報告提出桐城文派所以興起的四個條件:存史的精神意涵,偏好軼事的風氣及將其轉化為普遍的寫作方法,擅長講談的氛圍,文人并稱推助群體間的共同認可。
楊珂(南京大學)的報告題目是《清初駢文的“應世”之風及其轉向——以“指南類”書籍為中心的考察》,勾勒出清初至清中葉“指南類”駢文書籍的演變史。可見以“流麗”為典范、以人際酬報為目標的清初駢文,如何朝庸俗化、程式化方向發展,又如何經過《四庫》館臣的改造,最終完成“雅正化”的美學轉向。
胡琦(北京大學)在《考古之鈐鍵?:<困學紀聞>與清中后期考據學的通俗化》關注介于“經說”與“策括”之間的通俗入門讀物。以王應麟《困學紀聞》在清代中后期經典化的歷程為中心,揭示了“考據學”在進入通俗知識世界后的多元面向,為今人反思“古典知識”在近代流傳、再生產的方式提供了一面有趣的鏡鑒。
蔡丹妮(杭州師范大學)的報告題目是《國文教育與尺牘教材:以<高等女子尺牘教本>(1907)為中心》,著重分析了《高等女子尺牘教本》出現的時代背景與編纂細節。《教本》以真實女性書信《雙桂軒尺牘》改編而成,并傳達出當時的國文教育趨勢,其對普及古典文學知識所作的嘗試,同樣能滿足男性知識群體的讀寫需求。
第七場“明清讀者與‘紙上帝國’的周旋”由江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副教授溫海波主持。
葉曄(北京大學)在《<華胥放言>東傳與清初文人周銘的海客夢——兼論清初江南當代出版物的東亞流通》中,通過對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華胥放言》“戊集”的考察,梳理了編纂者周銘中年的行跡、思想及文學創作實踐。展示了清初江南中下層文人與康熙海禁周旋及突圍的過程,并由中挖掘了其時新版書籍在東部海域的流通細節。
韋胤宗(武漢大學)的報告主題為《明清世俗圖像中的書物形象與大眾閱讀實踐》,通過對明清秘戲圖譜中的書物形象予以整理及考察,描繪出雅、俗兩種文化在圖像媒介中較量的情景,進一步指出在明清時代,精英文化與價值觀在以一定方式向大眾滲透的同時,大眾文化實際也以自己的方式對精英文化發起了世俗化的改造。
王赫(南京大學)《陸隴其<三魚堂四書大全>與明清朱子學》探討《四書大全》在清初的增補出版,系統梳理“四書”講章傳統自清初分流狀況,揭示了近世朱子學傳承的演變特征與趨勢。指出在朱子學思想喪失活力的前提下,乃是由政治權威與科舉制度維系著朱子學“正統”的地位。
杜歡(安徽大學)在《宗教殖民與國際法的創生:16世紀西班牙傳教士的中國書籍訪購和閱讀》的報告中采取了跨文化的視角,將關注點聚焦于菲利普二世執政時代西班牙傳教士對中國書籍的訪購與閱讀活動,聯系西班牙政策環境與大航海時代的國際環境,深入描寫16世紀中國明代書籍在進行國際化流通背后的殖民與宗教內涵。

之后,浙江大學文學院馮國棟教授發起了主題為“梓者法身:跨學科的書籍史”的圓桌討論,韓琦、徐雁平、劉永華、張伯偉教授相繼致辭。
馮國棟簡單回顧了會議各方面議題的展開,同時認為,當前書籍史存在三個新的轉向:一是理論資源上,由過去與經濟史、社會史結盟,轉向與人類學、文化史的深度結合;二是研究對象上的實踐轉向,更加關注讀寫、儀式、表演等實踐活動中書籍的作用;三是研究范圍上的全球化轉向,特別是“書籍環流”概念的提出,顯示了全球史背景下書籍史的新方向。
韓琦首先回顧了張秀民先生撰著《中國印刷史》的歷程:最初深受卡特《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西傳》的觸動,孜孜耕耘宋版書的系統性研究;至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完善刻工、寫工等印刷質料的內容以外,又賡續了王國維開創的地域史研究,也對明代地區印刷史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后,韓琦從材料與問題意識兩個角度強調了全球史視野的意義。一方面,國內保留的與出版技術史相關的材料十分罕見,但在法國、德國、英國、美國還保留了不少17世紀以來不同國家的漢文活字實物與印刷樣品。另一方面,研究視野的開闊并非局限于打破文史學科間的壁壘,研究者需有一種追索西學東漸、中華文明西傳及文明碰撞交融等議題的遠大關懷。全球化時代到來,西方科學傳入中國,傳教士的書籍購藏與閱讀在中西交流中發揮怎樣的作用?把史實置于全球史的大視野下,以更廣闊的角度去審視并復原中西文明傳播的歷史真相,這或許是當下頗具挑戰性亦兼有活力的書籍史課題。
徐雁平充分肯定各位與會學者為拓展書籍史研究領域邊界做出的努力。就積極的面向而言,可以觀察到中國本土近世時段書籍史研究的理論方法與典范正在形成,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環節。首先,目前研究對象集中在東部海域和大陸東南部,對西北、中部地區的關注仍顯不足,這個問題不能避開。其次是書籍和讀者階層的問題。經典的地位不可否認,但也要從社會文化層面特別注意“中間層次”的書籍和讀書人在當時的影響力。如何通過這一中間階層把精英與庶民的世界慢慢勾連起來,值得我們繼續努力。最后,談及當下書籍史研究的流量和熱度,徐雁平持有一種冷靜的擔憂。他希望各個學科的同仁在預流的同時堅守各自的專業研究,“想要保住這個領域長久的發展,就一定要把自己專業的東西做好,然后互相交流、學習”。
劉永華直言自己作為“參與觀察者”,不同學科、不同領域學者所貢獻的最新經驗令他印象深刻。學者們關注的問題相當多元,所討論的文本類型也十分豐富,既有精英文本,也有下里巴人的讀物,在空間上能看到“地域—中國—東亞—全球”的立體層級。在此基礎上,可以進一步思考:首先,各位學者的問題和方法產生于不同的學科背景,是否可以作更好的整合。其次,當我們把研究范圍從“書籍”擴大到“文獻”,好處是讓我們對書籍本身的邊界不會作強硬的切分,但與此同時,文書、冊籍、書籍之間的界限也變得模糊。最后,書籍史研究者若要開啟并推進與其他領域的交流,就必須回到書籍史范式對大歷史過程的基本關懷。比如羅伯特·達恩頓的書籍史研究,其實是在回應20世紀早期法國學者提出的問題,即書籍流傳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法國大革命?而這個問題并不是孤立的,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發生的大規模的集體行動當中也許都普遍存在。類似的討論有助于進一步提升書籍史研究在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當中的位置。
張伯偉贊揚了本次工作坊的組織形式,可以感受到青年學者的朝氣、開拓精神和求知欲。“學術盛衰,當于百年前后論升降焉”,具體到書籍史領域,每個議題自有其研究價值,但無可否認的是,其中最重要卻也是最棘手的部分當屬“閱讀”。而相比“誰在讀”“讀什么”,關于“怎樣讀”“閱讀以后的效果如何”討論更加稀缺。出于識字率的原因,中下階層的主要閱讀方式是“朗讀”,至今在俄羅斯,朗誦仍是詩歌傳播中相當普遍的形式。這也提示我們,在還原中國本土閱讀情境時,“間接閱讀”或許比“直接閱讀”更為常見,應該引起充分的重視。同時,閱讀方法也會受到時間、空間、群體、對象等具體情境因素的影響而呈現出個性化與多樣化的特色。學者應把握個案與模式之間的動態平衡,既有的理論方法都是變化的、多元的、復數的,而這也正是書籍史作為交叉學科的魅力所在。
最后,北京大學葉曄教授致閉幕辭,本次跨學科工作坊圓滿結束。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