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什么是理想的工作?它真的存在嗎?
人是追求意義的動物,這也是為什么有人干著毫無意義的工作會不快樂、陷入虛無,即使這份工作能帶來豐厚的收入。經濟學理論(理性經濟人假設)雖然有助于我們解釋復雜的人類行為,但正如美國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在《毫無意義的工作》中所說,經濟學的假設在關于工作的討論中不再完全成立。格雷伯提到一位名叫埃里克的年輕人,他的工作內容很少,工資很高,但他覺得這份工作毫無意義,一種茫然無目標感深深折磨著他。如果人總是傾向于以最小的花費去獲取最大的利益,能找到活少錢多的工作該多么幸福,但事實并非如此,因為工作若是毫無意義也會難以忍受,人總是需要意義感、目標感。那么,人生的意義是什么?每個人的答案里或許都包含了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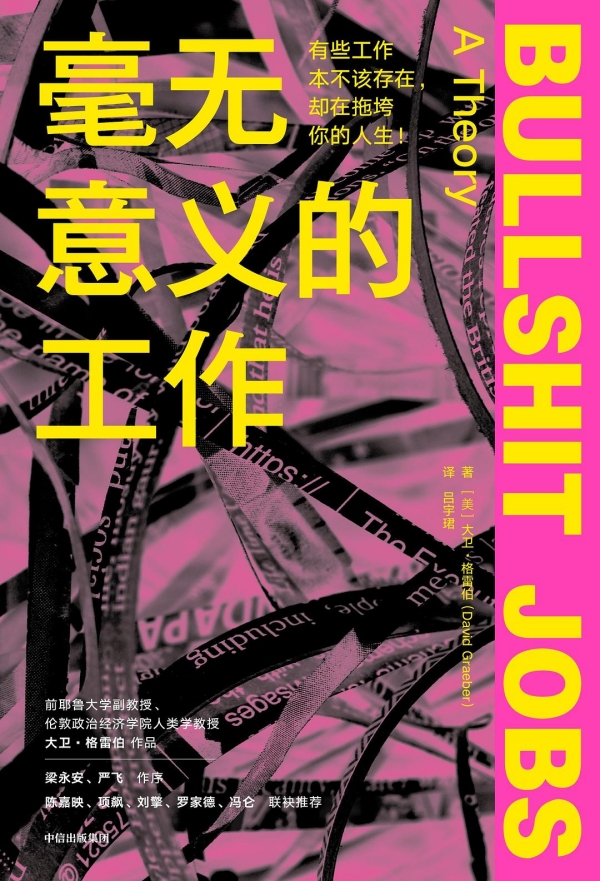
《毫無意義的工作》,【美】大衛·格雷伯/著 呂宇珺/譯,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7月版
工作,何以理想、如何熱愛?古羅馬的知識階層就認為一切有償的工作本質上都是羞辱人的,休閑是幸福生活的唯一基礎。由阿蘭·德波頓(Alain de Botton)主編的“人生學校”(The School of Life)系列之一《理想的工作》一書中提到,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人類工作的目標無非是為了物質生存,但自中世紀末開始,以威尼斯藝術家提香(Titian)為代表的一批人引入了一種新的工作理念:工作應該且能夠成為你真正熱愛的事情,同時它還能給你帶來體面的收入。自此人們開始在工作中追求物質與精神的統一。這也與大衛·格雷伯所謂工作需要有意義一脈相通。

《理想的工作》,【英】人生學校/編著 王紹祥/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未讀·生活家,2018年11月版
既可以滿足我們的物質需求,又能使我們的精神富足,這樣理想的工作真的存在嗎?追求物質精神統一的目標是如此宏大,而人們在談到理想時又往往將其浪漫化。“我們堅信在對的人或想法降臨之際,我們萌生的不過是一種特殊的情感沖動”,“我們把這份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信任托付給了直覺”。但真正有益的做法不是默默等待一份從天而降的“使命”,而要找到理想的工作也需要訓練和學習。
首先,我們要勇于承認自己的“無知”——不知道該從事什么工作是完全正常的事情。接著,我們要盡力克服一系列心理障礙:討好他人的壓力、完美主義陷阱、冒充者綜合征、妄自菲薄……然后,我們才能更好地去探索發掘自己的興趣所在。
《理想的工作》中還提到了許多具體的練習方式:識別自己的樂趣點并將它們排序(包括賺錢的樂趣、美的樂趣、創造的樂趣、理解的樂趣、自我表達的樂趣、科技的樂趣、幫助他人的樂趣、領導的樂趣、教學的樂趣、獨立的樂趣、秩序的樂趣、自然的樂趣),以此了解自己在工作中最看重什么;分析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思考這些內容是否只局限于某個特定的行業,讓自己走出對某類工作的“癡迷”;不要只從某個行業“輸出”的產品/服務來判斷我們是否喜歡,從“輸入”角度出發,思考其具體工作內容是否與我們的興趣吻合;試想如果有機會采訪正在從事某項工作的員工且能夠獲得真實回答,你可能的問題清單包含什么?
當然,練習不是萬能藥,在找尋理想工作的路上,我們很可能會以失望告終。或許也正是這種無法逃脫的命運使得現代社會充滿了倦怠與焦慮。理想難以觸及,現實的工作也走向格雷伯所謂“狗屁化”、無意義的趨勢,現代人該如何自處?
當下所謂“躺平”文化的流行便是這一趨勢下的產物。在越來越焦慮的現代社會,“躺平”帶來了另一種可能,人得以慢下來、靜下心,抵抗快速發展、競爭激烈的外部世界對身心的損害。在這個意義上來說,“躺平”也與喬納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所論述的“睡眠”存在相通之處。在《24/7: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一書中,克拉里提到現代社會對于人類睡眠的侵蝕,比如美國有科學研究正試圖發明無眠技術,可以讓士兵至少七天無休止地作戰;還有標志著現代文明的電燈,讓徹夜通明變得可能,仿佛白天與黑夜并不存在邊界。而如今的各類電子產品就像是現代生活的隱喻,它可以永遠“休眠”,消解了開機與關機的二元對立,“以至于沒有什么能夠徹底關機,也不存在真正的休息”。但人總是需要睡覺,因此睡眠是抵御資本主義對人的異化的最后一道屏障,克拉里說:“想象一個沒有資本主義的未來是以睡夢為開端的。”

《24/7: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美】喬納森·克拉里/著 許多、沈河西/譯,南京大學出版社·三輝圖書,2021年5月版
就“躺平”而言,其本身就有躺下、平臥的意思,與睡眠有著直接關聯。而正如睡眠可以抵御資本主義對人的異化,“躺平”同樣也是競爭越來越激烈、內卷越來越嚴重的社會現實下的一股抵抗力量。“躺平”不等同于不努力,而是現代人應對過度競爭的方式。克拉里的睡夢就是我們當下的“躺平”,我們也可以說,想象一個更加健康競爭的社會是從“躺平”開始的。
《理想的工作》也給了我們同樣的慰藉:關于就業的希望和夢想在歷史上其實是被夸大其詞的,我們不必把希望定得太高,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在追尋理想工作的路上,我們總會遇到挫折,因此也需要自我同情(self-compassion)。或許我們只是運氣不好,或許人總是無可避免地會做出瘋狂的決定,或許失敗本來就比成功的概率更高,又或許我們只是已經筋疲力盡。自我同情并非宣稱自己無辜,而是理性地認識失敗本就存在種種原因。
理想的工作難覓,但任何一份工作都難免會有糟糕的部分。格雷伯也區分了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和狗屎工作(shit jobs):前者往往能帶來不錯的收入,只不過毫無意義;后者對社會來說往往必要且有益,只是工作中存在糟糕的部分。因此,我們也需要重新理解何為理想的工作。或許,它并非毫無一點糟糕之處,而是我們對其真正有興趣,從事這份工作會讓我們覺得有意義。這樣一份“足夠好”的工作或許“有時無聊,有時煩瑣;有時會讓我們有挫敗感,有時會令我們焦慮;有時還得忍受你不是特別尊重的人的品頭論足;它不會完美地發揮你的特長;你也永遠都不可能發財……但是你會知道,你是帶著榮譽與尊嚴在工作的”。
同時,我們要意識到并不存在唯一的一份理想工作。現代社會的精細分工要求我們成為某個領域的專才,但實際上每個人都有各種各樣的潛能,適合做不同種類的工作。但我們也要意識到,我們需要學習與工作長期相處,因為正如你可能會突然迷戀某個人,你也會突然迷戀某份工作,而這種迷戀或許只是短期而隨意的。
回到那個問題:我們該如何自處?在席卷而來的倦怠與焦慮之中,我們首先需要確保自己的身心健康,但這不是說我們應完全地無作為,相反,當我們從過度的競爭中退出之后,我們反而可以去探索自己真正的興趣所在,去追尋那一份理想的工作。理想不是浪漫化的想象,實際的探索才能幫助我們了解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即使毫無頭緒,《理想的工作》已為我們提供了及時的慰藉:“每個人都無法挖掘自己的所有潛能。”
作為“人生學校”系列的主編,阿蘭·德波頓的《哲學的慰藉》也可撫慰我們的心靈。在追尋理想工作的過程中,乃至整個生命的歷程中,我們或許都會面對種種問題:遭受困難挫折、心灰意冷、因自身的缺陷而自卑、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德波頓認為,哲學最大的功能便是能以智慧慰藉人生的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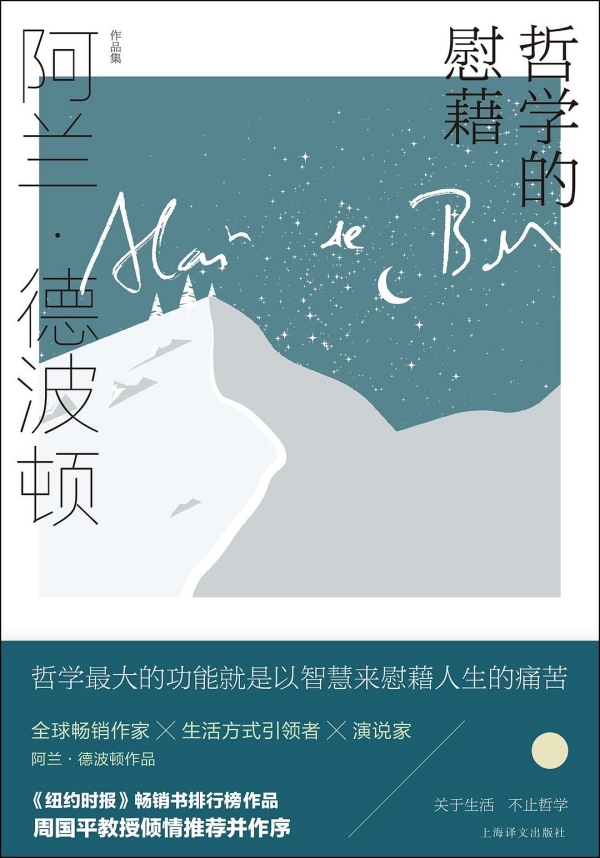
《哲學的慰藉》,【英】阿蘭·德波頓/著 資中筠/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年8月版
如果你覺得自己格格不入,不妨看看蘇格拉底。他被雅典人民判處死刑,也依然堅持不放棄自己信仰的真理。與別人不同并不代表就是錯誤或者真理,在完全聽從和絕不聽從輿論意見的極端之外,蘇格拉底提供了另一條路:聽從理性。如果你因遭受挫折而痛苦,不妨聽聽塞內加如何說:“何必為部分生活而哭泣?全部人生都催人淚下。”這位斯多葛派的哲學家不是讓我們對一切逆來順受,而是說對于無可改變的現實,我們至少還有自由去選擇泰然處之。如果你總覺得沒有“錢途”,不妨看看伊壁鳩魯,這位將快樂定為人生目標的哲學家追求的并非奢華的享樂,他的快樂清單包含三樣東西:友誼、自由和思想。“快樂可能得之不易。不過障礙不在金錢方面。”財富對于快樂的增加總是有限。
所以,理想的工作真的存在嗎?它取決于我們如何定義“理想”,以及是否付出實際的行動。它的確難以觸及,但這是我們每個人都會面對的命運,無需陷入焦慮。在這個充滿了不確定的時代,我們不妨帶著這些慰藉,去找尋屬于自己的答案。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