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這些無從定義的文字被阿來堅持記錄著”
阿來在小說創作上取得的成就與他最初的詩歌創作及穿行而來的散文寫作密不可分。帶著反思自覺、不停在路上穿行的阿來用炙熱的內心貼近故土、近乎零距離探究人與自然的關系,使得文本中充滿了自然力。
阿來用廣博悲憫的內心、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謙遜態度去關注現實、觀照歷史,他的作品越來越接近自己一直以來追求的境界——“語自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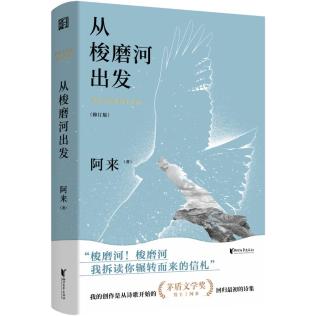
阿來詩集《從梭磨河出發》
(二印修訂版)
在路上穿行,就這樣日益豐盈
阿來的詩歌與散文創作新論
鞏曉悅 | 文
倒著回溯阿來近些年來的文學創作,當回到他創作的起點時,無論如何都不能再忽視他的“詩人身份”,雖然在過去的一些研究中已有成果刊發出來,但關注和提及者以及專題性的研究數量遠不及對他后來陸續發表的長篇小說所做的研究。
如果想要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阿來的創作全貌,那么他最初的詩歌創作是不應該被繞開的。一個作家在文壇成長為一棵參天大樹,都始于默默無聞的萌芽時期。
詩歌創作就是阿來成為參天大樹的萌芽階段。而阿來的散文創作是這棵參天大樹上的枝杈,也可以說是樹皮上的紋路、葉片上的脈絡,因了芽和枝葉的供給與支撐,這棵大樹才有了粗壯的主干,就這樣日益豐盈了。
1
詩人身份與語言經驗
“1982年,阿來在《草地》第2期發表詩歌《豐收之夜》。詩尾標明‘作者系中文教師,這是他的處女作’。”阿來在詩集自序中說“這些詩不僅是我文學生涯的開始,也顯露出我的文學生涯開始的時候,是一種怎樣的姿態。我始終相信,這種寂靜之后,是更加美麗與豐富的生命體驗與表達的開始”。
阿來道出自己從貝多芬的音樂中汲取了靈感,直言自己的詩歌受到詩人聶魯達和惠特曼的巨大影響。仔細讀完阿來的詩,筆者更加確認阿來的詩歌創作是他后來小說創作的基石。萌芽階段的詩歌創作也許稚嫩,但詩歌里充沛而飽滿的情緒為阿來以后的創作輸送了源源不斷的養分。
《豐收之夜》收錄于阿來詩集《從梭磨河出發》(點擊圖片即可購買)
《豐收之夜》寫的是“小麥”和“青稞”的收獲:“擁一懷小麥的甜美/枕一片青稞的芬芳”,詩人的內心喜悅輕盈,對未來充滿期待;“過去的日子彎著腰,在濃重的山影里/寫下這樣的字眼:夢,青稞麥子,鹽,歌謠,銅鐵,以及四季的橋與風中樹葉”,此段詩中出現的“夢”、“青稞麥子”、“歌謠”等意象都在阿來后來創作的小說中反復出現,“一個‘意象’”可以一次被轉換成一個隱喻,但如果它作為呈現與再現不斷重復,那就變成了一個象征,甚至是一個象征(或者神話)系統的一部分”。
“麥子”在后來的小說中反復出現,成為旺盛、昂揚生命力的象征。令阿來在文壇扎根的《塵埃落定》的第24節名字叫作“麥子”,“麥子”是使得傻子少爺贏得越來越多人臣服的重要食物。
一株“麥子”在阿來的小說里細化為麥粒、麥穗、麥花、麥苗等多種樣貌,這與阿來平日喜愛細致入微地觀察大自然中的花花草草是密不可分的。“成熟的麥粒在人們腳前飛濺起來,打痛了我的臉①。我痛地大叫起來②。麥粒跳起來,打在我臉上,已不是麥粒而是一粒粒灼人的火星了③。”整段中的“我”居于敘事的中心,麥粒是副中心;①②中的“我”情緒飽滿、感覺異常靈敏,麥粒飛濺起來的動作是迅速的一瞬;這時的“我”是動態的,而“麥粒”雖然飛濺起來,卻是被狂奔的人們踢起來的,實際上“麥粒”只是麥粒本身,是靜態的糧食。
敘述由“麥粒”到“我”,處于往外伸展的狀態。③中的“麥粒”成了該句的敘事中心,是動態的,有“跳”的動作,具有了昂揚的生命力;而“我”只是傻子少爺本身,是靜態的,退居副中心;本句將敘事的中心收縮到“麥粒”的視角。③中將“麥粒”比擬為“火星”,不僅是因為陽光下的麥粒帶著溫度,還透過麥粒反映出人們狂奔的熱情程度,而人們的狂奔與少爺的冷靜在此段中形成了強烈反差,這段文本敘述因此有了先伸展后收縮的折疊效果。
鐵凝回憶過:“我曾與阿來同去新疆參加一個活動。我們都為那拉提草原神話般的仙境所迷醉,大家都在留影,只有阿來,抬著他沉重的相機離開了喧鬧的人群。后來,他趴下來,側身半躺,鏡頭對準了草原上一支獨自搖曳的小花。那朵小花,打從來到世上,是從未被人注意過的。一路上,阿來都在專注于這樣的無名花草,發現它們短暫而異乎尋常的美麗”。
“身材魁梧的恩波急急地從中闖過,正在揚花的麥穗上,一片片花粉飛濺起來,在陽光下閃爍著細密的光芒①。江村貢布還看見:麥苗深處的露水也被身材魁梧像一頭野獸的光頭男人碰得飛濺起來②。”此時的麥子正在揚花,①中的敘述者像擁有著一把放大鏡,看到了閃爍著細密光芒的麥花的花粉,此時的麥花正在孕育生命。②中借助江村貢布的視角,看到的是“身材魁梧的像一頭野獸”的恩波,此段中出現了兩次“飛濺”二字,分別表現了動作的速度之快與身體的壯碩敏捷,讓敘事呈現出恣意昂揚的效果。①與②呈現出來了完全不同的兩種畫面:①可以稱作是“微型畫面”,那么②就是“巨型畫面”;二者雖然反差極大,但它們又呈現出和諧共存的狀態,都指向了旺盛的生命力。

《塵埃落定》
阿來在《翻譯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中提到了“語言經驗”:“我們在使用‘漢語’或者說‘華語’這種公共語言的時候,并不完全處于被動狀態,我們也曾主動地把自己原來的方言,或者是不同民族語言中的審美感受與表達方式帶進了這種語言。一種語言獨特的詞匯系統中一定還包含了當地的獨特的生活體驗,很多少數民族也把自己的語言經驗帶進了漢語之中。”
阿來在進行他的詩歌與小說創作時一直處于主動狀態,他始終將自己在家鄉獨特的生活體驗、審美感受以及藏族的語言經驗帶進漢語之中。
《寬廣谷地之歌》是阿來寫給家鄉的梭磨河谷的:“梭磨河,我的衷情記憶之手/滑行于你的寬闊谷地/撫摸到流水中的陽光和花粉/劃過被冰川損毀的巖石的面孔/撫摸到清晨的霜針與黃昏的雨水/撫摸到你莊重的沉默,我只看到你夏日天空下/一群裸浴的女子/以及一團狗狀的云朵看護潔白的羊群。” “流水中的陽光和花粉”、“被冰川損毀的巖石的面孔”、“裸浴的女子”等等,這些都與阿來在故鄉的生活體驗息息相關,詩人輕輕地“撫摸”這些故鄉的印跡,即便是被損毀的巖石面孔也被放置在美好而柔軟的氛圍里,絲毫不顯得突兀。
“詩歌從某種心境中自然流出,這種心境自然表現為一種有節律的語言,從而形成韻文;同時也表現為形象的、繪畫般的語言,它是‘作詩心境的自然結果’。”阿來的詩歌就是他對家鄉如嬰兒依賴母體那般熱愛地自然流出,他擅長用光的變化來襯托自己的心境,他的詩顏色絢麗,宛如一幅幅唐卡,呈現出“美麗而豐富”的特點。
“美麗”體現在他詩歌的色彩耀眼奪目:湖是蔚藍的(《撫摸蔚藍面龐》)、光是金色的(《金光》)、冰鑲滿星光(《冰凍》)、花朵是鮮艷的、火燭是明亮的(《夜歌》)、野花像火焰(《這些野生的花朵》)、柏樹滾出金色的淚滴(《俄比拉尕的柏樹》)、月光像牛奶般新鮮(《靈魂之舞》)、青稞與燕麥有綠色光焰、野草成熟的籽像黃金點點(《三十周歲時漫游若爾蓋大草原》)等等,這些描寫都是阿來對于自己家鄉獨特的審美體驗在詩歌中的自然流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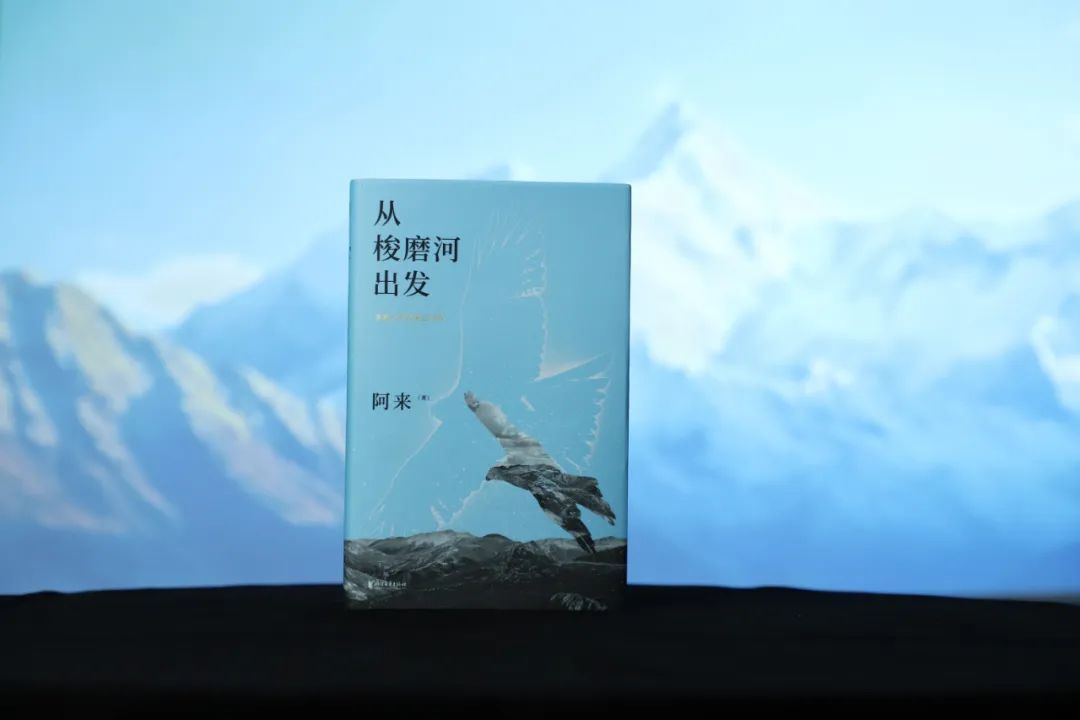
詩歌的“豐富”體現在其中很多詩歌整篇涵蓋的意象較多,內容充實飽滿,而這些經常出現在詩歌中的意象常帶著阿來家鄉的生活體驗,經幡(《撫摸蔚藍面龐》、《巖石上面》)、歌謠(《高原,遙遙地我對你歌唱》、《牧場》)等等常常出現。正是由于阿來有著自覺的文化歸屬,才使得他的詩歌有了“美麗而豐富”的特點;也正因為阿來從最初的詩歌創作就主動將自己在家鄉獨特的生活體驗、審美感受以及藏族的語言經驗帶進漢語之中,并在以后創作中一直保持這樣的自主性,才使得我們在讀他之后創作的小說時,時常發現帶有獨特的藏地味道。
2
自然力與穿行反思
《大地的階梯》(2000)、《就這樣日益豐盈》(2002)、《看見》(2011)、《草木的理想國:成都物候記》(2012)、《語自在》(2015)收錄了阿來近些年來發表的主要散文,這些散文大致分為三類,可以用三個直觀的詞語來概括:花草、穿行、反思。
無論是最初的詩歌創作還是后來的散文與小說寫作,阿來都用最貼近自然的姿態去進行敘述,他的內心與大自然近乎于零距離,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很強的“自然力”,從沒見過其他任何一個作家像阿來這樣如此熱愛大自然中的花花草草。
阿來能準確地說出風毛菊屬和景天屬的植物在最短暫的東南季風中綻放,清楚地知道草原上盛開的藍色花兒們是翠雀、烏頭和勿忘草等等。阿來寫過一本小冊子叫《草木的理想國:成都物侯記》,“就在這不斷穿行的過程中,有一天,我突然覺悟,覺得自己觀察與記錄的對象不應該只是人,還應該有人的環境——不只是人與人互為環境,還有動物們植物們構成的那個自然環境,它們也與人互為環境”。阿來不僅喜愛大自然中的花花草草,他還在心中充滿對它們的敬畏,如同故鄉一樣,這些花花草草也是阿來文學生命中的一部分。

阿來高原訪花
自然力首先表現為阿來非常喜愛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對渺小的花花草草的敘述,這常與文本中大的歷史背景反差極大,阿來在敘述它們的時候,一直保持著輕松自在的狀態。詩歌中有很多這樣的描述:羚羊在四時不斷的花香中奔跑(《歌唱自己的草原》)、蘋果花香氣四處游動(《春天》)、穿過核桃樹蔭里午寐的村莊(《穿過寂靜的村莊》)、斑頭雁的灰翅膀也這樣柔和地起落(《哦,草原》)等等。
小說中有這樣一段:“這時,我才開始發呆。望望天空,天空里的云啊,風啊,鳥啊,都還在。望望地上,泥巴啊,泥里的草啊,草上的花啊,花叢里我的腳啊都還在,好多夏天的小昆蟲爬來爬去,顯得十分忙碌。”如果單純只看這些文字,誰能想到這是《塵埃落定》里的段落,而正是有了這些文字,《塵埃落定》敘述的不僅僅是土司王朝的分崩瓦解,還有動物們、植物們與人們共同生活的自然環境,以及處于這個環境下所有物種的生存狀況。
這個“環境”不會因為一個王朝的瓦解而消失,“動物們、植物們與人互為環境”像是真理,不會因為一個王朝的瓦解、一種制度的解體而有任何改變。
自然力還表現在阿來從創作之初就將探究人與植物、動物們的關系作為重要的主題。自然力同時屬于人與植物、動物們,所有生物的關系始終被自然力平衡著。阿來用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謙遜態度去對待大自然中的花花草草,接受了來自于它們的自然力,同時它們也賦予了文本以積極正面的力量。
在《草木的理想國:成都物侯記》中,阿來提到了一本叫作《植物的欲望》的書,書中說植物長出炫示的花朵和大大的種子,以此吸引其他的物種,并依賴它們將自己的種子散播出去,讓自己能夠繼續繁衍,阿來認為從這種意義上說,人也是被植物利用的動物之一。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謙遜態度也被阿來延續到小說創作之中。
“那頭熊蹲距在夢境中央。那頭熊是他多年的敵手。這樣的敵手,是一個獵手終生的宿命。死于獵物之手,也是獵人善終的方式之一。熊卻只是伸出手掌,拍了拍厚實的胸膛,不慌不忙地從樹上下來,從從容容地離開了。時間一年又一年過去,他又與這頭熊交手幾次,因為仇恨而生出一種近乎甜蜜的思念。”機村中的獵人與熊不是殺與被殺的關系,而是“英雄惜英雄”。
獵人與熊的故事穿插到整卷小說當中,一是豐富了獵人格桑旺堆的形象,再是舒緩了人與政治之間激烈的沖突,調節文本的敘事節奏,豐富小說的內涵;讀者也在閱讀過程中有了適時的喘息機會,還會好奇這樣的“甜蜜的思念”——獵人與熊的關系到底是真是假。
阿來不是一位專業的植物學家,也不是一位社會學家,他并不僅僅用純科學的方法觀察那些花花草草,寫下觀察筆記,而是通過它們反映過去、思考現在,因此這些散文也具有了很強的文學性。在散文《看望一棵榆樹》里,阿來講述他去馬爾康鎮真正要做的兩件事情之一是去看一棵樹。這棵樹在當地人的口中有自己的傳說,阿來想從這棵樹的傳說里找到過去歷史中的些許感性碎片。當馬爾康寺已消失不見,“只有這株樹還站在這里,在一個逼仄的空間中,努力向上,尋求陽光,尋求飛鳥與風的撫摸。有風吹來的時候,那株樹寬大的葉片,總是顯得特別喧嘩”。
那些象征了人類過去痕跡的建筑已經被摧毀,可這棵樹卻依然朝氣蓬勃地站立著,阿來深知只有關注到這棵樹的來歷,才能更好地觀照當地人過去的歷史。這棵樹一直存在,不曾隨著人類歷史的演進而消失,這樣看來“喧嘩”的似乎不是這棵樹,而是人類的歷史,這是有余味的結尾。阿來借助一棵樹的力量打開的是過去的歷史,看到的是歷史帶來的結果、行進著的現實與人類自身的命運。
另兩類“穿行”與“反思”的散文,也可以合并為一類,一句話概括為“在路上穿行,在穿行中反思”。阿來對穿行的熱愛不亞于對花花草草的熱愛,對于花花草草的熱愛其實也是在穿行中實現的。三十周歲那年,阿來穿行于若爾蓋大草原,寫下詩歌《三十周歲時漫游若爾蓋大草原》。1999年的西藏之行之后阿來寫下《大地的階梯》,為了準備《格薩爾王》的寫作,那三年多的時間里他時常在川藏交界的金沙江邊行走。

“現在去瞻對,早上從康定機場下了飛機,驅車西經道孚縣、爐霍縣、甘孜縣、再轉而南下,大半日之內,就已抵達新龍縣城了。從縣城出去,鄉鄉都有公路相通,最遠的鄉也可當天往返”。《瞻對》作為非虛構的紀實小說,可想而知,阿來絕不是坐在書齋里悶頭苦寫出來的,為了搜集資料、查閱縣志、尋訪舊事,一定是在這條線路上穿行奔波了許多次。
阿來在不斷的穿行中收集素材、豐富自己的創作,同時因穿行于不一樣的地理與文化之間,得到了新的精神啟示與引領,新的精神啟示帶來了更多、更深的反思。阿來對于穿行的態度是“順著大地的梯級、歷史的脈絡,拾級而下”,最后為我們呈現的是有溫度的回憶、切身的自我體驗與心存悲憫的憂思。阿來是反思意識強烈、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他反思著正失去活力的教義、擔憂生態的惡化、欣喜于土地上的巨變同時又懷著深重的憂慮等等。
阿來將這些因“穿行”而得來的“反思”注入到散文與小說文本中,使得這些作品不僅僅是穿行時的記錄與回憶,更具有了很強的思想性,發人深省,耐人尋味。阿來心中的西藏是平實的、豐碩的,同樣充斥著人間悲苦歡樂。他認為要走進西藏首先要走進西藏的人群,走進西藏的生活,于是他借由雙腳與內心的切實丈量、親身體會的穿行,用如同觀察花花草草那樣謙遜的態度最終將自己融化進了所要寫的那片土地里。
3
“語自在”
阿來在《離開就是一種歸來》(收錄在《就這樣日益豐盈》,2002)里寫下:“‘語自在’,從古到今,對于一個操持語言的人來說,都是一種時刻理想著的,卻又深恐自己難于企及的境界”。2015年由重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集子,題目就叫作《語自在》,里面收錄了阿來過去的一些散文,并且分了三輯“大地的詠嘆”、“草木之名之美”、“病中讀書記”。
“語自在”統領著這三輯,是這些文字的首領;可見,它是阿來一直以來的文學理想與追求。毫無疑問,阿來已經在文壇長成了一棵參天大樹。他不僅憑借第一部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獲得了第五屆茅盾文學獎,還陸續推出了《機村史詩》《格薩爾王》與《瞻對》。對阿來來說,三十幾年的文學創作,四部長篇小說問世,數量看上去并不多,但每一部都來自于他用心的勘探與追尋,“穿行”像是他進行寫作時必經的過程與儀式,這四部小說都不是速成得來的,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持續創作的阿來有沒有達到“語自在”的境界呢?“語自在”包含了幾層含義:有沒有語出自在的內容,語出這些內容時是不是自在的狀態,呈現出來的文本有沒有給讀者帶來自在的感受。筆者認為,阿來在進行最初的詩歌創作時已經拿到了通向“語自在”的鑰匙,而阿來這些年創作的散文使得他入了“語自在”的大門。
筆者注意到《瞻對》之前的小說寫作與他的詩歌和散文創作相比,呈現出了較大差異。這四部長篇小說中,最大程度上實現了“語自在”的作品是非虛構的紀實作品《瞻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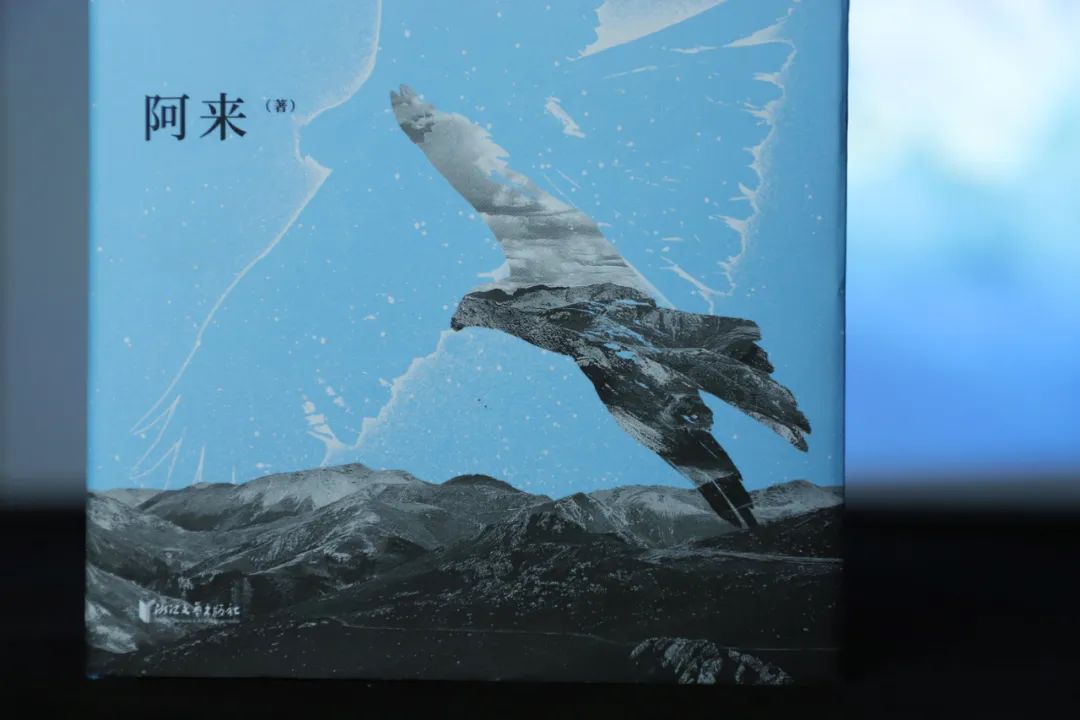
萌芽階段的詩歌創作有著天真爛漫的氣韻,阿來可以完全跟隨自己的內心,眼前的實物只需包裹著那時那刻的心情,加上天然的感觸、顏色的裝點,詩意自然而然就流淌出來了。
阿來的詩歌里沒有多少異化的形象與感受,而是像一顆顆人人都可能吃過的蜜糖,放在嘴巴里都不需咀嚼,慢慢自己就融化了;融化之后的甜味還可以在嘴巴和心里留存一會兒,但留存的時間不會太久,這也許就是萌芽時期稚嫩的體現。雖然稚嫩,但阿來在這些詩歌里存放了他的天真與浪漫,而這天真與浪漫的氣質也影響了他后來的小說創作。
阿來在談及《塵埃落定》時說“雖然過去似乎意味著落后,但那是一個盛產英雄的時代,而且允許浪漫出現。這種浪漫不同于現實生活中調情那種浪漫,是一種精神氣質鮮明的大浪漫。”這種精神氣質鮮明的大浪漫不僅是時代所有的,更是阿來在他的創作之初自己也擁有的。
“詩一般的語言、詩一般的意境”是《塵埃落定》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后評論界一致的評價,2002年在“阿來作品研討會”上,李敬澤認為“阿來作品的語言從一開始就有一種透明的氣質,在寫作中以新鮮、單純、透明的狀態,真切地接近事物的質地,并變得詩意、華美甚至壯麗”,這“透明的氣質與狀態”與阿來最初寫詩的經歷直接相關,他的創作一開始就充滿了“詩意”。
起先阿來對于“散文”有很多困惑:“必須承認,對我來說,所謂散文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當詩歌因為體裁本身的問題,開始限制自己作更自由更充分表達的時候,我便漸漸轉向了小說。至多,我所知道的散文很寬泛之處在詩歌與小說這兩個王國之間的游擊地帶,但這種無從定義的文字多多少少還是會寫下去吧。”
這些“無從定義”的文字被阿來堅持記錄著,這是他找到的更自在表達內心的言說方式。散文集《大地的階梯》就是這樣產生的,他堅持用感性的方式進入西藏,進入西藏的人群,去反應真實的西藏,他企圖化解形容詞化的西藏。太過虛擬化的小說很難使他做到這一點。同時,這些“無從定義”的文字很好地滿足了他記錄花花草草與穿行反思的需要,他能夠動情快速地記錄下那時那刻的感受,這些文字是形成小說文本之前的預演。
阿來的散文里呈現出溫軟、舒緩、甘甜的氣韻,而他發表的前三部長篇小說里卻多有掙扎、痛楚、沉重和矛盾,寫散文時的阿來是最輕松自在的。只有在他隨手記下的筆記里才會有“雨停了,四野里,花草們細密的聲音絮絮地響起,星光還沒有來,我要睡了”。
阿來對于穿行的熱愛,勤奮記錄“無從定義的文字”直接影響了他的小說創作,寫出《瞻對》是必然。《瞻對》是部有些復雜的紀實小說,氣韻和之前的《塵埃落定》《機村史詩》《格薩爾王》都不同,大氣與扎實的程度超越了前三部。阿來大量引用歷史文獻,借助史料盡量還原當時的歷史場景,敘述采取了夾敘夾議的方式,敘述者時不時跳出來發表自己的看法,文本里經常有阿來講述自己是如何收集史料的、對一些歷史事件發表自己的看法。閱讀這部小說,可以經常看到寫散文時的阿來,到目前為止,阿來在《瞻對》里實現了最大程度的“語自在”。
《瞻對》在敘述策略上作出了非常突出地改變,很難在其中找到一個公共的敘事頂點,取而代之的是對群像的描摹。小說里不僅有統一瞻對全境的貢布郎加、瞻對人的英雄布魯曼,還有領導瞻對民間起義的鐵匠撒拉雍珠;有清朝政府的官員紀山、慶復、琦善、趙爾豐等人;還有國民政府中央、中國人民解放軍、縣城鄉鎮的公職人員等等。這些在歷史上真實出現的形形色色的人們都有自己的故事,只是作者著墨多少不同,他們共同支撐起整部小說。
在《瞻對》里,筆者看到了一個從過多聚焦個體生命到展現群像與時代風云變換的阿來。阿來是能夠寫歷史的,也是能夠寫群像的,這部小說已經充分表明他對歷史敘事有很強的把控能力。《瞻對》使阿來在小說創作上實現了一次革新與突圍。

阿來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三層含義,“語自在”還是作家本人、文本與讀者三者達成的平衡關系,筆者在阿來的詩歌與散文創作中看到了他的質樸與本心,更看到了他為讓三者逐漸達成越來越和諧關系所作的努力,對阿來的詩歌與散文創作的重新審視,可以更全面地貼近他創作時的內心狀態。
我們以往在判斷一首詩歌、一篇文章、一部小說是否達到“語自在”境界時,過多地關注了有無獨創的聲音,卻漸漸忽視了內容本身是否合乎自然,是否合乎我們經驗里的基本形態。變異、扭曲、花樣翻新可以成為一種審美追求,卻絕不是文學的終極審美追求。
樸實的文字、飽滿的情緒、對歷史的審視、自然的表達等等,應該依然成為文學創作的主流追求。對阿來而言,這些都可以在不停地穿行中實現。
也許作為詩人的阿來在未來的某一天會回歸,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會停下穿行的腳步。阿來始終在路上穿行,并且在穿行中實現了文學創作的日益豐盈。
原文刊載于《當代文壇》2018年第3期
作者簡介:鞏曉悅,山東淄博人,1989年出生,文學博士。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做博士后,現就職于山東大學文化傳播學院中文系。主要研究方向為當代文學與文化、兒童文學、圖畫書等相關問題,撰寫當代作家作品評論,教授中國新時期以來小說研究、西方理論與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繪本鑒賞等課程。《中國原創繪本的多維度研究》取得一項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面上資助。為美國凱迪克銀獎作品《吉萊斯皮和守衛》、繪本《狐貍》、《說書人》,中國原創繪本《如果我不去上學》、《俺老孫來也》撰寫了導讀。將持續追蹤相關領域的最新動態,做熱情飽滿、有生命力、真誠的寫作與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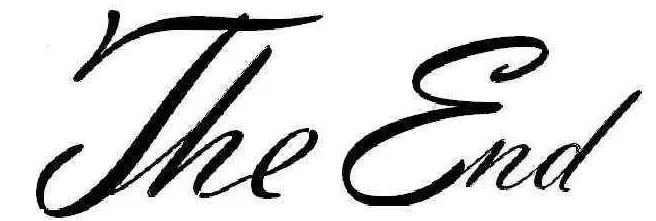
原標題:《“這些無從定義的文字被阿來堅持記錄著”》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