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講座|閻克文×趙英男:馬克斯·韋伯,一個復雜的人
馬克斯·韋伯是德國著名思想家,在他150年誕辰之際,韋伯研究專家迪爾克·克斯勒教授出版了《韋伯傳》一書。在將近十年之后,這部傳記的中譯本出版。新書推出之際,出版方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邀請了浙江大學“馬克斯·韋伯著作翻譯與研究中心”主任閻克文以及同濟大學法學院趙英男,圍繞自身的學術歷程、韋伯作品翻譯心得或閱讀體驗、韋伯思想與日常生活的關系等,進行了一次對談。以下為兩位老師對談內容的整理,經本人審定。

對談現場
趙英男:從1999年開始,閻老師就一直沉浸在韋伯著作的翻譯中。翻譯韋伯是許多學者都做過的一項工作,但是像閻老師這樣多年持之以恒、持久不懈地沉浸在韋伯著述的翻譯與研究之中的學者,在中文世界可以說少之又少。有機會能在這里與閻老師交流,我也感到非常開心。今天我們對談的環節包含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由閻老師分享自己對于韋伯這么多年翻譯研究的心得和體會;第二個部分是由閻老師,包括我自己,分享一下對于韋伯本人、韋伯的學說以及他個人魅力的體會或者說是思考。我們也希望能夠與現場各位朋友共同探索: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我們關注馬克斯·韋伯究竟有怎樣的價值和意義?
閻克文:總的來說,我有二十多年比較長期地惦記著韋伯著作的翻譯問題。今天的主題是克斯勒(Kaesler)先生的《韋伯傳》,我是審校,但是我首先得說出版社還是有眼光的,能把這本書作為出版選題,我認為是有價值的。這是一件好事,對于了解韋伯是非常有幫助的大動作。如果我們希望相對比較全面地了解韋伯,這本傳記是個非常好的渠道。除此之外,大家還可以看看他遺孀所寫的《馬克斯·韋伯傳》,劉北成先生主持翻譯的《馬克斯·韋伯思想肖像》,再一個是我個人翻譯的《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這幾部書加起來對于了解韋伯這樣復雜人物的全貌是非常有幫助的。另外,還有我現在正在處理的一本韋伯傳,是柏林自由大學的拉德考(Radkau)教授寫的,按照合同規定是今年年底要交稿,大概明年上半年就能出版。這幾本傳記加起來對于了解韋伯就比較可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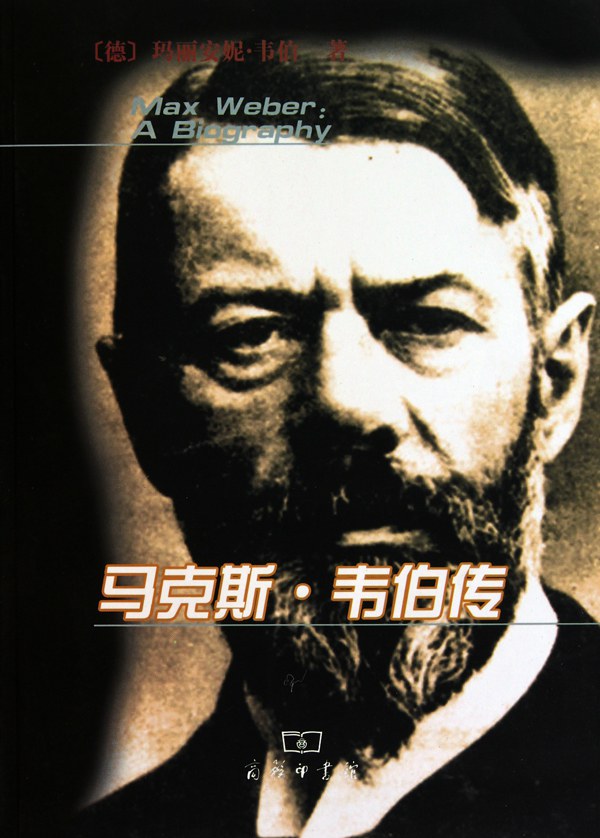
韋伯遺孀瑪麗安妮·韋伯所寫的《馬克斯·韋伯傳》
我相信各位對韋伯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為這個人實在是太復雜了,說個大白話,復雜得簡直一塌糊涂。他對于德國的學術思想、文化傳統是一個叛逆性人物,因為他不遵循德國的哲學傳統,他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個哲學家——我看到學界或讀書界有些人把韋伯叫作哲學家,感覺是個非常滑稽的事情。韋伯對于哲學史、哲學人物、哲學理論、哲學著作非常了解,但是他極少談論哲學。為什么?因為他一反德國學術文化傳統的核心特征就在于他是個經驗理論家,他不是個純理論家,尤其不是那種形而上的玄學理論家,所以他對于哲學領域的東西非常了解,但他非常不感興趣。雖然我們常說、也知道哲學是科學的終極指南,但事實上韋伯終生所關心的就是實證研究。不知道各位了不了解,馬克斯·韋伯的弟弟阿爾弗雷德·韋伯(Alfred Weber)也是個名人,他有一本很著名的著作叫《工業區位論》,從地區分布的角度論述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生成發育。但是馬克斯·韋伯就認為他的純理論內容太多了,實證研究的內容太少,他認為這樣干是沒出息的,所以他的弟弟很郁悶,就和哥哥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分歧。不過,結果還是證明韋伯的看法更有說服力。
我僅僅是一個譯者,都不想說自己在研究韋伯,但是20多年的翻譯過程當中,難免有一點個人的心得,對韋伯的了解和認識,至少從我的個人經驗來說,可能比很多同仁、同道要多一些。我們可以從文本信息的接受程度來佐證一下。比方說,假如從1953年開始算起的話,到2020年韋伯逝世100周年,德國人完成了《韋伯全集》的編撰和出版工作,一共是56卷,這56卷到目前為止,能夠被英國人譯成英譯本的規模,僅僅是新版《韋伯全集》的17、18卷,而譯成中文的文本也差不多,因為我們大體上都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極少是從德文翻譯過來的。所以這就導致了一些非常嚴重的問題。第一,文本的信息流失和失真程度很嚴重,我自己的經驗就足以寫本書了。比如韋伯的名著《經濟與社會》,它的譯者之一是京特·羅特(Guenther Roth)先生。我覺得這個事很奇怪,因為京特·羅特先生是正宗的日耳曼人,納粹上臺之后跑到美國,他的英語也非常老練,最重要的是他終生都是韋伯研究者,英譯的《經濟與社會》從形式到內容的扭曲、歪曲、失真和流失的情況,可以說不勝枚舉。我曾經奇怪得不得了,也想跟他聯系一下,問問他究竟是什么原因這么做,結果老先生去世了,就沒法再討論這個問題了。還有一個我個人的親身經驗,也是很令人驚駭的。我們知道韋伯終生都在“腳踏兩只船”。哪兩只船?學術與政治。他出身政治世家,同時他對于學術又情有獨鐘,所以始終高度關切這兩個領域,實際操作的投入不同凡響。所以他去世之后,他的遺孀瑪麗安妮·韋伯(Marianne Weber)為了抓緊向他表達敬意和紀念,收集整理他的遺稿出了一些韋伯的書,其中就包括《馬克斯·韋伯政治著作全集》。彼得·拉斯曼(Peter Lassman)與羅納德·斯佩爾斯(Ronald Speirs)覺著《韋伯政治著作全集》是非常有價值的,他們就合作,想著把這個政治著作譯成英文。瑪麗安妮整理出來的德文原著是整整560頁,還不包括注釋、索引、各種說明,結果您猜猜英譯本是多少頁?
趙英男:300頁。
閻克文:380頁。大家可想而知這種信息的流失和失真到了多么駭人聽聞的程度。英譯版編譯者們的解釋是,為了照顧英語讀者的閱讀習慣做了這樣的技術處理。我認為這純粹是一個謊言,以他們的語境來說,再怎么照顧英語讀者的閱讀習慣,也不至于砍掉三分之一以上的內容,冒充韋伯政治全集。這本身就是譯者的人格缺陷了,而不是他的學術缺陷。按照這種經驗,我們對韋伯的了解還是相當有限的。
很早我就有個奢望,認為能譯出并出版《韋伯全集》最好,然后就開始做。無疑個人力量實在單薄,最終還是多虧當時浙大羅衛東副校長力主和主導,在浙大高研院搭建了翻譯與研究的平臺,組織力量先做文本翻譯的基礎工作。現在正在進行著,已經完稿八卷,人民出版社在編輯過程當中。
翻譯《韋伯全集》能夠讓我們的中文讀者盡可能從文本信息的角度,相對比較全面地去了解韋伯,我們才能談得上比較準確完整地去談論韋伯。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是個非常典型的事情。典型在哪?從背景上我們就可以看出來,當時韋伯寫這本書的思想和文化背景是非常清楚的,韋伯是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潮沖擊的第一代歐洲知識分子的一員,更是德國知識分子的一員。我們都知道,馬克思主義成為一個社會與政治動員的話語系統后,確實被簡單化、教條化了。一個很重要的標志,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簡單化為經濟決定論。韋伯就遭到了這樣的沖擊,他覺著這種一元化的決定論是有缺陷的,其他的因果要素也都在對歷史現象發揮著程度不同的決定性作用——為什么只能首先專門在西歐的土地上生育生成發展,然后對外擴張?這有它的道理。他就從“新教倫理”這個角度來探索這一點。后來隨著文本的擴展,韋伯對于宗教社會學的領域一直是非常用心的,他擴展了之后形成了自己的宗教社會學的比較研究,比方說古代猶太教、印度教……
趙英男:包括《儒教與道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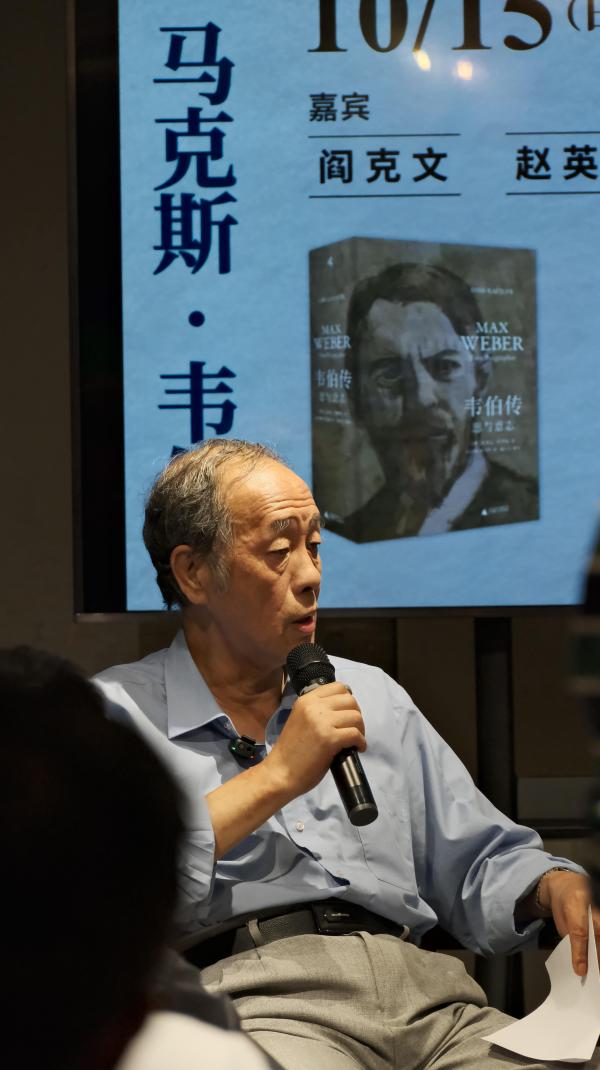
閻克文
閻克文:他本來還想寫伊斯蘭教等,沒來得及就去世了。但是作為一個比較研究的系列來論證觀念系統對于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的決定性作用,這也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其他的當然還有,比如像政治問題、政治力量,比如權力的力量也是經濟過程和經濟現象的一個決定性因素,軍事力量、宗教力量、文化力量都是不可或缺的,這是他和卡爾·馬克思產生方法論分歧很重要的一個方面。說到這個問題,我覺著應該強調一點,韋伯和馬克思,我們都知道是對頭,甚至是不可調和的對頭,但是有一點很多人都忽略了:他們的對立不是意識形態的對立,而是方法論的對立。比如對于現代資本主義的憤懣、不滿和抨擊,他們是共同的,語言上的共同性簡直是不可想象,但是在方法論的問題上分歧就大了,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是一個發展階段,而韋伯就認為資本主義是個永恒性的經濟現象,但是它作為一個現代現象已經完全不同于前現代的現象了,前現代可能單純是其它因素影響下的經濟現象、經濟過程,比方說政治資本主義、軍事資本主義、海盜資本主義、掠奪性資本主義等等,但是現代資本主義正好碰上了新教倫理,它作為一個杠桿力量起了很大作用,同時又碰上了歐洲政治局面的巨大平衡時期,就是權力系統的平衡對于形成經濟上的統一大市場有非常大的作用。再一個就是羅馬法的復興、日耳曼法重新的調整,還有盎格魯-撒克遜法的普及,特別是對于西歐現代資本主義的發育、生成和發展擴張都是一些決定性的因素。在這種方法論的認識問題上,他和卡爾·馬克思是有沖突的。除此以外,韋伯對馬克思的尊重是有目共睹的,他甚至還說過這樣的話:“衡量一個當代青年學者是不是有良知,就看他對兩個人的態度,一個是馬克思,一個是尼采。”就看能不能對這兩個人保持知識誠實,否則的話你就是不稱職的。但我們現在可以說,看一個中青年學者是不是老實、是不是正派,得看他對三個人的態度,包括韋伯。如果不遮遮掩掩的話,我想不妨坦率地承認,韋伯的復雜程度要比馬克思多得多。特別是面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無理性擴張趨勢的時候,我們知道卡爾·馬克思的方法論原則就是一腳把它踢走,韋伯不是這樣的,韋伯認為現代資本主義不是不可顛覆的,但是成本將遠遠超過收益,在這種情況下怎么樣去證實它的未來就是個問題,就是說它是不是可救,他真是沒辦法,拿不定主意。比方說他在出版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后,當時這個題目在德國引起了轟動,一堆德國媒體采訪他,認為他是個全知全能型的人物。媒體記者急功近利的時候比較多,就要求或者請求韋伯預見一下歐洲資本主義的未來。韋伯面對這么大的一個題目,想了好一陣,然后告訴在場的記者——要是譯成中文的話就四個字——無可奉告。這就說明他對前景的觀察和判斷并不是靠著簡單的意識形態教條來解決的,就像我們前面說的,他和他弟弟一個重大分歧就在于他始終關切著實證研究,這就導致韋伯本人極度的復雜性。韋伯的復雜性并不完全在于他本人怎么復雜,而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這個經驗世界本身就這么復雜,他無非是揭示了這個復雜性,甚至他自己很苦惱,沒有揭示出它的完整本相。這確實比較困難,面對無比復雜的經驗世界,面對無比龐雜的因果鏈條,我們哪怕拿出一個邏輯切片、一個因果片段來,都可能說不太清楚。當然,從概念到概念的“概念游戲”就比較省事了,它可以大大降低你的思考成本,你玩概念就行了,至于我們所不得不面對的這個經驗現實究竟是怎么回事,尤其是它的因果要素怎么回事,它的因果可能性、因果趨勢是怎么回事,靠玩概念游戲是永遠說不清楚的。韋伯始終在這個問題上嘔心瀝血,但是他也不是糊里糊涂地跟大家說這個事,因為他最終形成了一個——我好像還沒有發現其他人這么說過,我給它造了個詞叫作——“概念工具箱”。
趙英男:“概念的工具箱”這個概念怎么理解?
閻克文:因為韋伯作為一個原創性的作家,他原創性地發明了一系列的核心術語、核心概念,比方責任倫理和信念倫理,這是一組,其他還有很多,都比較著名,比如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目的理性和價值理性、材料至上和意義至上等等,作為有效的分析工具都非常有助于誠實地面對經驗世界本身,而不是陷于空洞的概念游戲,甚至文學化發情。
趙英男:還有“三種支配類型”。
閻克文:對,支配類型是分了三種,足以囊括經驗世界本身的概貌。你可以借助它的分析手段進一步挖掘它的相關作用過程,這就表明了他的核心概念、核心術語是資源性的價值,而不是像其他很多概念那樣很單一,你用完了就完了。他的概念,可以說有無限的擴張性。
趙英男:我在這里想插一個問題。您覺得韋伯這種反傳統、反體系性的研究,是他的突然去世所導致的,還是他在某種程度上有意為之的?
閻克文:我剛才說過了,就是有意為之。因為他是個經驗理論家,不是純理論家,不像康德那樣。比如他和康德的關系就很清楚,我們不得不承認他是新康德主義者,他喜歡引用康德的一句話:“每個人都是自己的目的,不是任何別人的手段。”這是他作為一個新康德主義者的突出標志,但是他極少談論康德,非常非常少,提他的名字也少,提他的著作也少。他只是把這些觀念性的東西納入了實證分析過程。所以在這個問題上,他就顯得特別復雜。
趙英男:在這種反體系或者非體系的意義上,是不是您也分享著《韋伯全集》編者們的觀點:我們所認為的《經濟與社會》這本書,可能并不是一部邏輯結構非常完整的著作,而是像現在《韋伯全集》所體現的一樣,它是分卷出版的,相關材料分散在不同的題目或者篇章之中。
閻克文:它原來是《社會經濟概論》的版本之一,但因為其他作者老是拖拖拉拉、言而無信,很少有人能夠按時兌現自己的諾言,按時交稿,從傳記資料上看,他比較著急,就基本上獨立地承擔了大部分工作。《經濟與社會》是其中一個,它分了幾個方面,總結了他個人的思考:社會學的基本概念、經濟方面的問題、支配社會學、宗教社會學、城市社會學等等,實際上這是他比較系統的但又不是一個整體的思考成果。他去世之后,他的遺孀瑪麗安妮?韋伯為了紀念他,和溫克爾曼(Winkelmann)——按照現在標準的說法,溫克爾曼很牽強地把它合成了一本著作,實際上不是的。
趙英男:所以,它有可能是圍繞在這個主題之下的一個多卷本的著作?
閻克文:對。再一個,所謂“社會學”也是讓韋伯一直猶豫不決的問題,因為社會學在韋伯那個時代,在法國已經高度成熟了,這是從法國傳入德國的一個概念和學科,但是在德國還是剛剛開始打造。所以很多人把自己的學科叫作社會學,韋伯對這個事情是很不滿的,而且終其一生他都不愿意自己被人叫作社會學家,他也不愿意把自己從事的社會研究叫作社會學著作。但是迫于當時的輿論環境他可能不得不隨波逐流,不得不承認。同時我們也能看到,無論是他的傳記資料還是他的著述,都提到他更重視的是“社會科學”這個概念,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理解他所說的社會學應該就是社會科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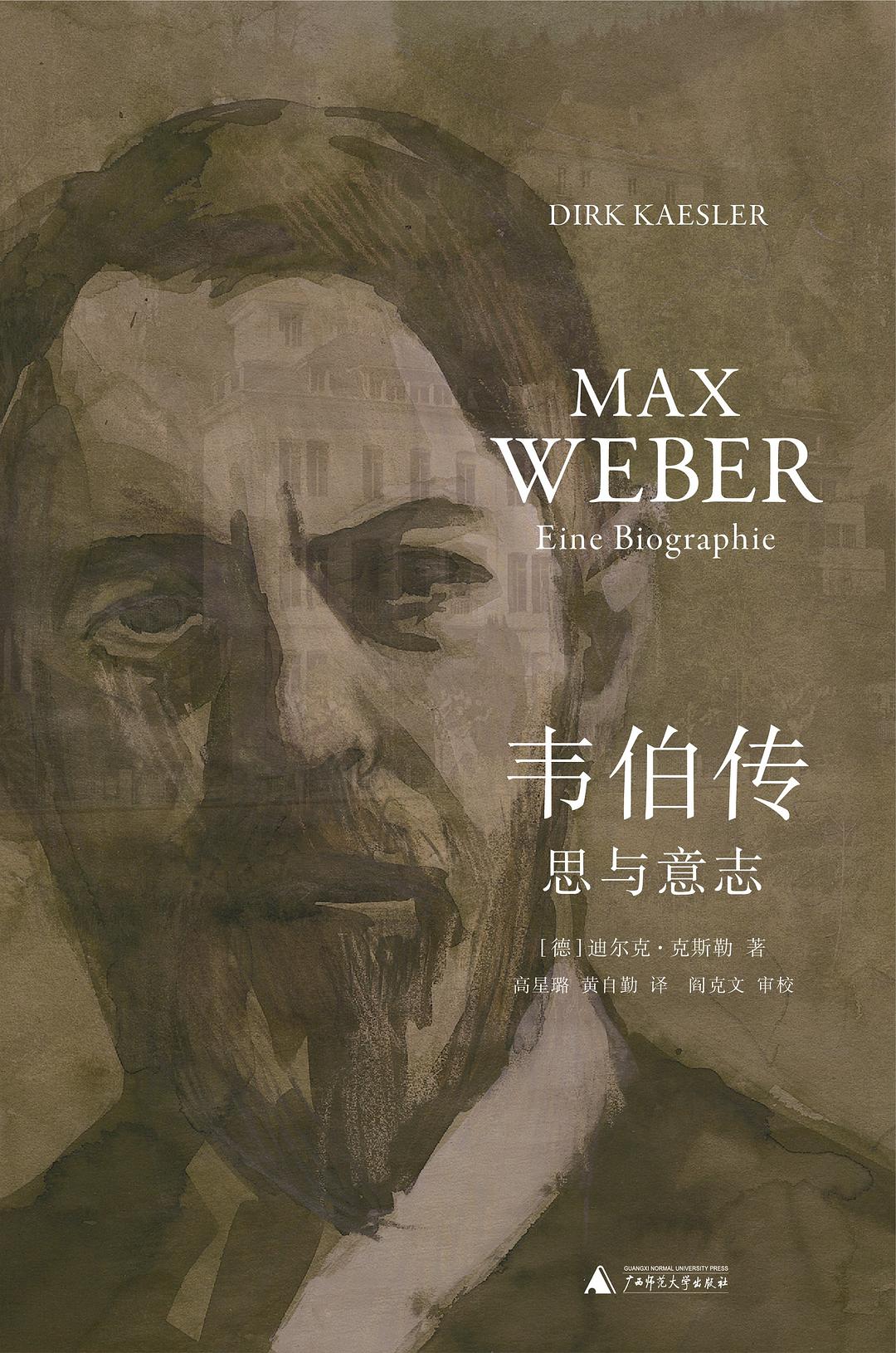
《韋伯傳:思與意志》,【德】迪爾克·克斯勒/著 高星璐、黃自勤/譯 閻克文/審校,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新民說,2023年7月版
趙英男:在這個意義上也能體現出韋伯本身像閻老師所說的那種復雜。韋伯其實接受的是法學訓練,獲得了法學博士學位,但是他拿到的教席名稱是“國民經濟學”,同時他認為自己從事的是社會科學研究。那我現在想請教一下閻老師,您覺得像《韋伯傳:思與意志》這樣一部無論是中文譯本還是德文原版都已經超過一千頁的著作,在呈現韋伯的形象方面有哪些比較獨到的特征?
閻克文:通過審校過程我有很深的體會。克斯勒教授能夠很準確地把握韋伯思考的多元化方法論問題,他非常準確地理解了韋伯對多元化力量的論述,知道任何一個歷史過程、一個歷史現象都是多種原因決定的,它一定會有多種多樣的因果要素在起作用,你把它歸結到任何一個單一要素去強調它的一元化決定論,任何這樣的做法都是錯誤的,不管你認為一元化決定論,它來自軍事、政治、宗教、文化還有經濟哪個方面,只要你想強調一元性的決定論肯定是錯誤的,肯定和韋伯是有巨大出入的。
趙英男:我覺得閻老師的這個看法也印證了我讀這本傳記時一個很粗淺的感受。我覺得相較于韋伯的夫人瑪麗安妮·韋伯所寫的傳記,克斯勒寫作的傳記在材料選用方面是更為多元和廣泛的。我注意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克斯勒在描述韋伯的人生經歷時,可能從韋伯進入大學的第三個學期之后,就很少引述,特別是大段地引述瑪麗安妮·韋伯所寫的韋伯傳當中的內容了。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或許此時韋伯無論是從思想還是人格上的成熟,都到達了一個新的階段,以至于我們已經無法依靠某種單一的材料去理解這個叫作“馬克斯·韋伯”的人。“多元性”可能是《韋伯傳:思與意志》一個很突出的特征。
在活動開始之前,我一直在和閻老師聊天。我自己也做一些翻譯工作,知道翻譯是非常辛苦的。閻老師跟我說,他每天的工作時間都在10到12個小時。閻老師接下來說,偶爾也有例外——我以為有時工作時間會減少,但他說有的時候會在15個小時。我想問的是,雖然閻老師一再云淡風輕地講自己只是一個韋伯著作的譯者,但我覺得譯一篇文章很簡單,譯一本書也不太難,但是二十多年來孜孜不倦地投入到對于韋伯著作的翻譯中,到底什么樣的一種感受在推動著您?內心的動力到底在哪里?
閻克文:對我個人來說,我覺得讀了韋伯之后有一個被導彈擊中的感覺:這個歷史還能這么看?這個政治還能這么看?人還能被這么看?這是一個。再一個,我覺得從公共話語角度來說,韋伯的著述、他的學術作為一種資源性的學術價值,到現在還不過時,用雅斯貝爾斯的話說:韋伯是一個永遠的現代人。
趙英男:同時代人。
閻克文:永遠是我們的同時代人。我想把他作為一個永遠的現代人是非常合適的,除非你有足夠的膽量宣布現代性結束了,只要你不敢這樣宣布,韋伯就一直在起著作用。我覺得,他作為資源性的價值是長期存在的,到現在還不過時。我們中文讀者最熟悉的就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學術與政治》,恐怕足可以作為例證,盡管這還不是全部。
趙英男:包括《儒教與道教》,還有《經濟與社會》。
閻克文:《經濟與社會》對于多數讀者來說,恐怕僅知其名而已。這里我想插個閑話,2014年韋伯誕辰150周年的時候,我因為要去德國開一個會,德方希望能知道一下中國對韋伯的翻譯、傳播和了解的現狀,我就做了個500人的調查,收回問卷498份。其中有一個小項目讓我挺吃驚的,你要知道調查對象都是學院派和研究人員,而且都是有針對性的研究人員,這498份調查問卷回來之后,我發現只有2個人通讀過《經濟與社會》的中譯本。
趙英男:我想八卦一下:這兩個人當中包括您嗎?因為您就是《經濟與社會》的譯者啊!
閻克文:不包括。
趙英男:那說明還好,499人當中有3人,比例上升了。
閻克文:我覺得特不好意思,就在那會上介紹一下情況,結果沒想到施魯赫特(Schluchter)教授——主持人之一,也是《韋伯全集》的主編之一——聽了之后大為震驚,他說:“中國人比德國人有出息!500個德國人里頭有兩個通讀過《經濟與社會》?不可能的事!”這就是說德國人對韋伯的了解未必比我們中國人多或者全面、準確。
趙英男:作為從來沒有通讀過這部書的400多人之一,我想為我們這些沒有通讀過的人做一個簡單的辯解。雖然我是學法律出身,但是韋伯的《法律社會學》我從來沒有完完整整地讀過,我只讀過他的《支配社會學》《社會學的基本概念》這樣一些著作。其實根據克斯勒教授在這本傳記當中的描述,由于《經濟與社會》本身是源自韋伯筆記材料的匯編,我們可以看到在這部著作的不同章節,韋伯寫作的成熟度或完成度不是很一致。在某種程度上,如果真的要通讀這本書,而且是帶著學術研究的目的的話,確實非常非常艱難。我在這里還想請教閻老師一下,您覺得韋伯哪一個理論或者哪一個論斷最能夠擊中您?您剛才給我們科普了韋伯很多著名的學說,您覺得哪一個最能夠有“導彈”的感覺?
閻克文:我最早開始對韋伯產生入迷感覺的時候,就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雖然當時沒看懂。我坦率地說我很愚蠢,很蠢笨,看了三遍之后才看懂,后來我發現之所以有些內容看不懂,而且到現在都看不懂,是翻譯的問題,不是原文的問題,因為他的著作知識密度和思想密度實在是太高了。最后我終于讀懂了之后,就真是感覺非常新穎奇特,歷史還能這么看?社會還能這么看?和我們原來接受的那種灌輸和教育已經是完全不同的路徑。包括費正清,大家可能知道他有一本名著叫《美國與中國》,他對中國歷史的敘述當然是完全站在西方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觀看的,他有他的認知角度,這一點都不用去奇怪,關鍵是能夠和我們的認知水平匹配嗎?這就很難說了。但是看到韋伯的東西之后,我就覺著匹配度太高了。
趙英男:仿佛他懂中文。
閻克文:對,是這樣子的。我想說明一下,韋伯從來沒來過中國,他一個中國字兒都不認識,他僅僅是借助記者、傳教士、商人的二手資料來了解中國——當然也憑著一些學者對中國文獻的翻譯來了解中國,但是他了解的準確度,我可以保證比我們許許多多的中國學者要高得多。舉個非常簡單的例子,他的閱讀量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夠比的。他的閱讀量大到什么程度?傳記資料說過一個小例子,他14歲過圣誕節的時候給全體家人送了一份禮物。什么禮物?他寫的論文。14歲的時候,他頭一次寫論文——《論教皇對皇帝和日耳曼歷史的影響》,光聽這個題目,然后再看看收錄他全集的文章本身,可以不夸張地說,就我們現在的博士生恐怕寫起來都費思量。
趙英男:從這個角度來說,他33歲時經歷了某種精神崩潰,好像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
閻克文:他的思想負擔太重了,給他造成了一定的生理上的后遺癥。他的筆跡之所以那么難以辨認和這個后遺癥是有關系的。他寫不清楚。他自己經常認為,對他來說這是一種折磨,因為他的思想的流動性和豐富性是他自己來回記錄的,想著及時把它記下來,就不得不產生這樣的后果。剛才我們說他的方法論、工具箱的問題,他里頭有許多的原創性觀念、術語、概念是別人沒有過的,或者說加以更新之后重新使用再廣為人知,成了標準的分析手段。這些東西對我們所觀察的歷史和現實是非常有價值的。

趙英男
趙英男:我自己去過他和他夫人曾經去過的萬國博覽會。我在美國的圣路易斯城做過一年的訪問學者或者說是交換學生——為了好聽,我經常說是訪問學者。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這個城市是韋伯美國之行的重點,但是去了以后我在讀一些跟這個城市相關的歷史資料時無意中發現,當時韋伯去的萬國博覽會,現在已經變成了圣路易斯城中著名的森林公園,與我所在的學校只隔著一條馬路。萬國博覽會的原址現在變成了一個藝術博物館,其中有一些當年曾陳列的展品。我有時候會想,韋伯和他夫人在100多年前游歷美國,他們看到了什么?以及,他們心中想到了什么?我思考這個問題,其實并不是說要自比于韋伯,也不是某種自戀的幻想,而是我認為我們在閱讀韋伯的每篇論文或著作時,會感受到韋伯的著作及其理論都隱含著他的某種長期關切,這種關切影響了他的遣詞造句、他的文本結構以及他對于理論資源的選取。我想現場以及線上的一些朋友們可能讀過我在《澎湃新聞·上海書評》上為這本傳記寫過的一篇書評。在書評中我舉了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在《以學術為業》這篇演講中,韋伯談到我們現在的學術生活其實是一個無止境的發展過程,而在這樣一種過程當中,一個人是不會有享盡天年之感的,他總會覺得很疲憊。在這個意義上,生與死對于一個人來說并不是特別有意義。這樣一句感嘆其實是與他在其它文本中對于現代社會理性化過程的分析不太一致的。在韋伯其它的論述中我們會看到,在談到理性化的時候,韋伯會非常詳盡地講到生活各個領域理性化的表現,但是在這篇演講中,他突然宕開一筆,拋出一個托爾斯泰式的問題,探討人生的義。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關注韋伯的理論,就要關注韋伯這個人,知其人而論其事。關注韋伯,一方面是關注他的思想,如閻老師所說,他的思想能給我們帶來理解現代社會、理解自身以及周遭世界的一種視角或者資源,是一個非常具有原創性的工具箱;另一方面,關注韋伯是因為他無論作為一個愛好政治且投身于政治但最終失敗的人,還是作為一個愛好學術卻始終沒有一個良好身體狀態能夠長期擔任教職的人,都為我們列示了一種獨特的人生或者人格類型。他大概能夠給我們展現出,在一個現代生活當中,面對日復一日的生活,一個人可以忍受或者可以堅持到怎樣一種程度。讀到這本書的時候,我的一個體會是,智識上的收獲非常多,但有的時候是一種心靈上的收獲。
我的書評原來的標題是《舉起時代的重負,擲入心靈的深谷》,是韋伯的夫人所引的里爾克的一句詩,但是后來想到或許不要那么煽情,就在編輯的建議下改為了《孩子,結過我的長矛,我的手臂已不堪其重》。這個典故來自韋伯博士論文答辯的那一天,非常著名的羅馬法專家特奧爾多·蒙森(Theodor Mommsen)對韋伯所說的原話。蒙森在這里說的接過他的長矛,某種程度上指的是學術衣缽的傳承。但這句話對于我們來說,對于我們這些作為韋伯的后人或者作為他的同時代人來說,這似乎隱喻了韋伯面臨的一些問題也是我們所面臨的,他所探討的許多問題,比如理性化、權力支配以及經濟發展等,我們今天也會思考,也會遇到。我們未必會面臨他所面臨那種程度的沖突和糾結,但是所有這一切無時無刻都會影響到我們。
對談的時間也差不多到了,最后想請閻老師分享一下,您覺得在今天——現在是2023年,明年就是2024年,韋伯誕辰160周年的日子——我們為什么要關心韋伯?我們作為中國人,為什么要關心韋伯?他對于我們當代、對于我們中國的意義究竟是什么?
閻克文:我覺得這個問題很有意義。就我個人來說,最有價值的在于韋伯的客觀性。他的客觀性不是說兩面討好、八面玲瓏、和稀泥,不是的,他最厭惡的就是價值至上或者說信念至上。咱們一再說過,他是個經驗理論家,他一生都在關注實證研究,就是經驗現實本身的多元性和復雜性,這些東西我覺著對于我們觀察日常,不管是微觀的還是宏觀的現象、過程,都是極有幫助的。可以舉個比較具體的例子,比方說他去美國考察,幾個月的時間,他居然就認識到現代資本主義新教倫理精神已經沒有了,最后就剩下一個經濟鐵殼在那擱著。美國尤其具有兩重性的危險,因為美國是整個歐洲歷史上,甚至是整個人類歷史上最沒有歷史負擔的一個國家,所以對于它的民主,韋伯給了一個詞叫“現代大眾民主”。這種政治現象對于美國人來說,如果你單純從意識形態角度去把它美化、神化、迷信化,不是不可以,但不符合事實。事實是什么?現代大眾民主往往就是民粹和反智的直通車,他說這個危險在美國一直存在著——你說,他說的是不是事實?美國人對于韋伯也是不大感興趣的,但結果一個民主黨人,比方說前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居然說了一句話:學會從政實際是從韋伯那里來的。
趙英男:如果我們用“學術”與“政治”這兩個詞來概括韋伯的一生及其念茲在茲的問題,閻老師剛才其實是從政治的角度強調了韋伯對于我們今天的意義。我想把這樣一個問題從政治的角度轉回學術的領域,歡迎大家去查找和翻閱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這篇長文。我大概讀了有四五遍,每一次讀完開頭都沒有再讀下去,但是通過很多二手文獻和介紹性的文獻我大概知道,其實閻老師剛才談到的這個問題體現在學術領域,就是有關學術研究的“價值無涉”和“價值關聯”的關系。韋伯指出,我們基于某種價值關聯而去做一些事情,將這些事情作為自己終生的事業,但當我們投入到這些事業中時,一定要以非常客觀的、價值無涉的角度來展開我們的研究。
閻克文:這個價值無涉對于一個人的判斷和認知能力是絕對可靠的檢驗方法,而且最終它會要求你的責任問題、責任意識、責任能力是不是匹配。你光會嘴里一串一串的大詞,沒用,一串一串的“信念至上”,都沒用。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