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音樂人張培仁為什么不做音樂節要做生活節?

從這個角度來看,張培仁、賈敏恕和李宗盛三位臺灣樂壇前輩終于把簡單生活節變成以市集為靈魂的樣子就不奇怪了。
臺北的簡單生活節落地上海的頭三年里(2014-2017),音樂陣容長了一副流行/獨立音樂節的面孔,市集精致細膩,論壇的議題設置幾近書展。今年,簡單生活節從狹長的世博公園搬至氣場違和且小得多的西岸營地,音樂陣容變得輕量,小攤位和京東、攜程、三草兩木等品牌的入駐使之更貼近“生活節”的本質。

不做音樂節做生活節有一個現實的原因,周而復始的經濟規律令高潮過后必然迎來低谷。2006年開始的臺北簡單生活節前所未有地聚集起一批本土文創品牌,為經歷戒嚴—開放,經濟起飛—金融危機的臺灣經濟提供了另一條出路。有兩件事張培仁很驕傲:一,2006年他和伙伴們辦的“臺客搖滾嘉年華”,是第一次有人在報紙上說:“臺灣的創意人們站出來”。二,現在的松菸誠品里,有一半品牌是當年看了廣告誕生的。
從小玩搖滾,做唱片企劃一只鼎的張培仁是簡單生活節的創始人和總策劃,他和臺灣很多文化人一樣能說。“我會不會太自戀了”和“不是我太自戀”是他侃侃而談里不時插入用以自謙的話。并且他熟知兩岸的游戲規則,說話謹慎,對概念的提煉和包裝有超強的能力,對文化和世情亦有深刻洞見。他和合作伙伴們的誠懇,就體現在簡單生活節的現場。
關于這個節的氛圍,主辦方做了很多街采,收集了形形色色的故事。有一個被記錄下的細節尤其可愛:“(草蜢)唱著一首首上個年代的大金曲,攤主們紛紛失了神,不少都‘丟’下攤位跑到離舞臺更近一些的地方看。”(《上海簡單體驗:在這里,感受每個年輕品牌背后的夢想與溫度》)

張培仁和他的團隊為“生活節”賦予令人振奮的概念,希望通過市集和音樂支撐起一個空間,喚起都市人對生活本質的認知。簡單說,他們希望這個現場平等、自由而快樂,參與者能夠因為愉悅而愿意為自立和創造添薪火。
光鮮的概念更需要冷靜消化,背后的邏輯是否合理才是能否走下去的關鍵,情懷不能當飯吃。
簡單生活節背后的邏輯大概是這樣的:制造一個聚合創作者的空間(手工創作者和音樂創作者),用這樣一群人聚集在一起時產生的巨大快樂感染參與者,幫助他們從全球化和商業的桎梏中掙脫些許,重新定義流行和生活這兩個重要概念。順利的話,認同這個理念的城市中產階級自然能認同在這個語境里聽到的獨立音樂。“這樣推廣音樂的效果會比我硬要向你推薦一個獨立音樂人好多了。”

這樣做商業上的優勢則是精準定位。愿意“買”簡單生活的理念,并且買得起門票的人,很自然地成為文創產品和京東、攜程等品牌的目標客戶。在“生活節”這個場景中,雙方兩情相悅,順理成章就做成了生意。
邏輯合理,但簡單生活節也非完美,比如廁所真的比較少。以及,像一個真正的市集一樣,它不能提供凈化靈魂、震蕩三觀的神奇體驗。它有點保守,音樂的選擇太清新好聽。換句話說,太符合城市中產和文藝小清新們的品味,就像算法精確的流媒體,總能為用戶提供符合他們審美的音樂。然而一不小心就視野狹隘又易沾沾自喜的都市人,更需要挑戰而不是迎合審美的刺激。這一點上,以“臺客”、“搖滾”和“嘉年華”三個既接地氣,又擁抱土味亞文化的概念奇妙結合的“臺客搖滾嘉年華”,藝術生命力會更強。
和張培仁聊天的前一刻,他還在奮力寫稿,企劃人的本分一直沒有丟掉。他很驕傲,“吳鉤寫宋朝,講到蘇東坡還幫馬桶寫過廣告,把我和李宗盛兩個寫文案的樂壞了。”
從人類社會和市集的關系,東方在長期復制西方文化和被動接受定義后的反思,青年的普遍困境,到“生活節”的本質、商業模式和愿景,定義流行和生活形態的可能性,行動者張培仁講推動行動的源頭,很精彩。
【對話】
“這是核彈浩劫后孵化出的新芽”
澎湃新聞:簡單生活節其實是在創造一個節日,一個城市中產階級的節日,替代現在生活中已經消失了的傳統節慶聚會活動。你們有從這個角度考慮過它的屬性嗎?
張培仁:有。2006年我們辦了一個叫“臺客搖滾嘉年華”的節,很迷人。它是臺灣民俗的精華,媽祖、保生大帝、關公、哪吒的人偶都出來了,裝置很多來自戲曲傳統,有一套完整系統在里面。我們搭了一個臺灣鄉間常見的場景,把搖滾臺、嘻哈臺、偶戲臺、布袋戲臺、鋼管花車等等這些都放在里面,還搭了一個大大的圓臺里面都是小吃。這種鄉土的東西精英會蔑視,但是我在里面頭一次看到小孩子們沖過去抱著三太子拍照,之前他們會抱的只有哆啦A夢這些。我們也是第一次在報紙上號召“臺灣的創意人站出來”的人。

澎湃新聞:如果要貼標簽的話,簡單生活節會給貼上“文藝小清新”的標。小清新這個“類別”蠻廣的,對文化和生活品質有追求的人都愿意埋它的單。簡單生活節呈現的這個面貌是你們精確定位的結果,還是自然而然,順應時勢?
張培仁:臺灣的金融風暴是2006年。那一年我們開始在臺灣辦簡單生活節,蔡康永、孫大偉他們來了,感嘆:“哪里有金融危機?沒有啊!”孫大偉形容說:“這是核彈浩劫后孵化出的新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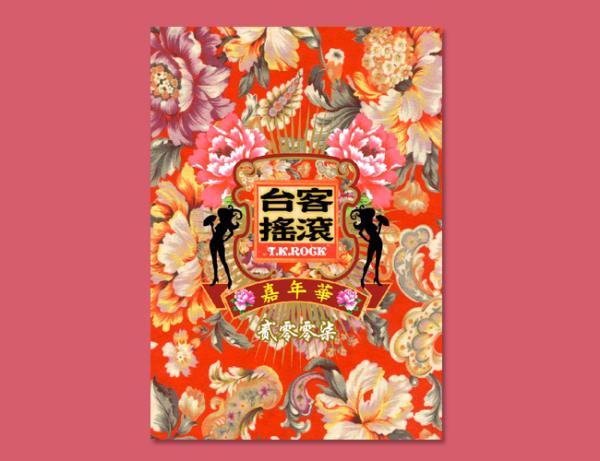
在當年的臺灣,人口紅利消失以后,有一代人已經占據了關鍵位置。如何讓底層的人找到快樂生活的方式?是先快樂,然后變有錢,而不一定非要是倒過來,這是邏輯問題。
雖然人都想做大事,但是你會察覺到人的處境在資訊化時代的變化。
澎湃新聞:所以你們順應時勢,決定不做大型的音樂節,而是做一個新形態的東西叫“生活節”,去解決現代人的問題?
張培仁:對。
早在1980年臺灣音樂還不太有原創力的時候,我和一些伙伴就在臺北做了一個音樂節。到了2000年有海洋音樂祭和春天的吶喊的時候,我們已經在思考(音樂節)到底能提供什么,以及行業需要什么。
1990年左右,臺灣的音樂環境經歷了幾個變動。一個是幾大國際唱片公司進駐臺灣,還有全球的資訊涌入。我們開始憂慮,本土創作人擺在全球環境下會怎樣。
西方音樂的產業能力、文化縱深、消費習慣、資本規模、全球的傳播力,都有一個成熟的工業體系。而我們的這個體系至今仍不成熟。如何生存,對文化內容來說非常值得關注,因為標準隨著全球化而改變。
文化是一種競爭,是很多事物的本質,包括經濟。


到了1998年,互聯網來了,你就知道大勢已去。臺灣戒嚴到開放,雖然信息開放了,但進入的內容仍然是經過精挑細選的。而互聯網時代無人篩選,每個人可以尋找自己喜歡的文化源頭。
經過這十多年的轉換,沒有人有空可以閑下來體會創作。所有東西都可以用買的,只要尋找全球代理就可以。沒有人會覺得怪怪的,有哪里不對。
但是總會有一天,有人會想找到來自生活中的藝術。怎么樣讓來自本土的創作發生?這是我們定義生活節的原點。
找審美的共識,找到傳播的路徑,來推動音樂。這就是最初期的定義。
“我們所有在做的事情,都是運用西方對生活的看法”
澎湃新聞:你們希望在西方文化的壓倒性優勢下找到本土原創生存的空間,甚至去造一個空間。
張培仁:是的,因為我們逐漸意識到,我們聽的所有音樂類型,都是西方青年一時一地的生活方式產生出來的價值觀、審美和作品,傳播的是他們對世界的看法。我們所有在做的事情,都是運用西方對生活的看法。我們在復制,又如何競爭?
全球的流行音樂取代了的宗教和哲學,給了你很實在的屬于一個人群的生存哲學。我們不應該復制西方的生活。臺灣的民歌運動,最流行的作家是三毛,余光中的詩,李雙澤的字句。它已經不止是音樂運動,而是青年處境的思考。
羅大佑出來的時候,幕后操盤是詹宏志。宏志說了,這是大佑的社會意識,所以叫“黑色旋風”。它促進的思考遠遠超過音樂本身。到李宗盛出來的時候,臺灣的經濟已經到一定程度,個人的思維方式也在變化。“總是平白無故的 難過起來/然而大伙都在 笑話正是精彩”(《寂寞難耐》)反映了時代心情,把這種心情說重了,就會得到共鳴。

澎湃新聞:一個可以孵化原創的空間可以有無數形態,為什么從市集著手?
張培仁:當大家都在關注產業的時候,我們的問題不是產業,而是對生活的態度。文化必須是來自生活的自然體悟。
因為資訊的關系,每個人都有解讀生活的權利。我們希望梳理出對生活的共同看法,因此發明出“生活節”這個定義。
我們用最單純的當時來做審美。我們的美學有點天真。我們不走“高大上”的路徑。我們希望做的每件事都是生活里實用的物件,是基礎的審美。
生活節的定義就是食、衣、住、行、閱讀和娛樂。簡單生活節雖然是很多商家的聚合,但都經過篩選。你無法向別人推薦一個他沒有聽過的獨立音樂,因為你沒有音樂傳播的場景,好像抖音提供的場景,它是倏忽即逝的。它解決不了雋永的人生觀,讓你知道自己是誰,想要什么。
只有當你決定生活的樣子,你才可能決定喜歡什么樣的音樂。

澎湃新聞:你們鼓勵年輕人“做喜歡的事,讓喜歡的事有價值”。在這個年輕人普遍焦慮和浮躁的年代,這個口號蠻奢侈的。
張培仁:經濟浪潮周而復始,臺灣或大陸年輕人的困境并不是日光下的新事情。
曾經有人問我臺灣的青年問題,我覺得就是三件事:
1、目前的狀況是人類歷史上沒有發生過的,即沒有資源的人都有資訊,這樣會產生對立和誤解。
2、臺灣的富裕已經四五代了,貧富差距非常大,階級固化的問題在臺灣很嚴重。
3、心理上,年輕人覺得不可能超越前人或別人做過的事。
所以音樂上出現一個大浪潮,叫“擼瑟系”(Loser)。日本和歐美也都有過,日本的“去死去死團”(最早源自1972年由著名特攝作者川內康范所推出的《虹之戰士》中的反派角色Mr. K率領的團體),美國的Haters,都源自階級固化和資訊通化。
要怎么辦?你會不會覺得這個太復雜了,不想加入世界的競爭?現在年輕人的貧窮,大都屬于一個月不工作也不會餓死的“新貧窮階級”。讓這樣的人安靜地做東西去賣,不必加入大公司去廝殺爭做第一,會不會比較好?臺灣的簡單生活有個做領結的,現在誰還戴領結?但是他在那兩天里領結賣了6萬多臺幣,已經比上班強了。
“如果沒有定義審美的權力,怎么去做文化行業?”
澎湃新聞:脫離比較有保障的體系出來單干,不僅賣商品還賣商品背后的故事和情懷,越來越多人開始這么做了。
張培仁:流行可以被創造,有定義解讀權,它是創造市場的方式。互聯網時代,我們來想一點復雜的事,看看有沒有辦法做“風格”這件事。
風格是文化行業最重要的事,可是風格如何定義和描繪,它和人有什么關系?這是文化行業的第一個問題。
有了它,就會很好做生意。沒有,就需要花很大的精力去吹,去弄大。很多人都知道,下一個世代經濟的驅動力來自審美和產品背后的價值。如果我們沒有定義審美的權力,怎么去做文化行業?


澎湃新聞:定義流行是很大的一樁生意,但是具體到文創產品這個生意會不會太小,很難做大,形成氣候。

西方的很多創業都是這么來的,而我們的很多創意的源點都是看別人有了才去做。所以說現在才是創業的好時代。大陸現在的處境和當時的臺灣是一樣的,經濟是一個循環。
愿意相信年輕人,買他們的作品,才叫文化自信。
澎湃新聞:去給對生活的取向下定義,塑造一個有共識的風格是你們在做的,具體到里面的攤主,他們有沒有獲得收益?
張培仁:每個攤主都很賺錢,我們預料現場整體銷售有三四百萬,比如來一次可以賺五六萬塊。他們平日里可能做不到這樣,但是當你有了知名度,一個月平均可以兩萬吧,比上班強。那些人相信做這些東西的價值,就會比較快樂,于是傳播出去的價值也很快樂,而且還能賺到錢。
澎湃新聞:接下去呢,會不會和商業品牌有更多的合作?
張培仁:接下去我們想做一個基金。我們不適合代理,因為不管是音樂人還是做文創產品的,推廣和定義是他們自己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能做的是提供資本和廣義上的推廣:請你相信我們周圍的年輕人能做出好的東西。這是自尊問題。
“每座城市都應該有一個地方保留下來,讓自己人可以在里面呼吸”
澎湃新聞:最早你們的態度是不做巡回,但是現在簡單生活不僅從臺北到了上海,而且今年已經擴展到成都、武漢和廈門,為什么?
張培仁:我們一開始確實不主張節要去巡回,從臺北到上海已經是一個轉變。但是在臺北,場地和人數無法擴充,因為種種限制每年的場地越來越小,越來越難。
后來思路轉變了,我們是生活節,不是巡演,每到一處是要深挖當地的生活方式和文創品牌。就像街聲的目的是幫助音樂人得到發展的動力和對市場的理解,讓他們有信心可以發展下去一樣。
簡單生活公園要做常態化的運營。每座城市都需要自己的創作者形成的場景,有一個本地音樂人的聚落。
澎湃新聞:簡單生活找到可持續的商業模式了嗎?怎么解決音樂節很難賺錢這個問題。在大陸,音樂節的規模和門票上限幾乎難以突破。
張培仁:音樂節確實不會賺什么錢,除非像Summer Sonic,東京大阪兩城,一張票平均1600塊人民幣,賣25萬張票;除非像Coachella買10萬張票,Burning Man(美國一個難以描述的大型狂歡節)賣50萬張票,否則你別想。
在國內如果有50個賣票的明星,就有500個音樂節。大家都要做(音樂節),拿到資本或者政府補貼之后就可以做,但是很少有長期的模式。
早先我們就說,簡單生活節做三年規模要轉小,然后再轉大也沒關系。我們愿意跟著時代去演化。

澎湃新聞: “生活節”的理想狀態將會是什么樣的,你有沒有一個藍本?
張培仁:溫哥華有個地方叫Granville(格蘭佛島),以前是鐵路倉庫,后來變成農夫市集,大家拿水果、蔬菜和海里捕上來的魚在那邊擺攤賣。因為他們自己生活的審美非常好,所以擺出來的蔬菜水果攤就很美。Emily Carr(艾米麗卡爾藝術與設計大學)在那邊蓋了校區,島上漸漸地有學生在街頭拉琴,藝術老師們的雕刻和繪畫也在那邊販售。這塊地方于是變成了北美最舒適的休閑場域,是自然生成的聚落和樣貌。

每座城市都應該有一個這樣的地方保留下來,讓自己人可以在里面呼吸,不是只有商業和名牌。
澎湃新聞:有沒有想過以后在一塊更大的場地做,縮短音樂節的周期?今年的新模式人流量波動情況怎么樣,和事先的預估有什么出入?
張培仁:七天來了五萬人,除了臺風來那天比較慘淡,生活公園的部分票房都好過預期。
去年我們就想來西岸了。場地更小,意味著動線更短,商業回流度就更高。從前在世博公園,簡單生活節得以呈現全貌,有音樂、市集和論壇,很好。但是這里人群的聚合度會更高,來的人不會因為要走太長的路奔波得很辛苦,它會更接近“生活節”的樣貌。
目前階段我們還是希望做主題的分類,常態化之后甚至每個周末都有不同主題的固定化場景。現階段風格的清晰化很重要。
澎湃新聞:未來還有什么打算?
張培仁:這次我們嘗試在入口處招募會員,一下收獲了5000個。我們的本意是不要賣票,將來為他們提供各種生活選項和優惠措施。
我們還在繼續尋找商務伙伴,希望擴充和穩定下來。正在考慮城市的數目要不要增加,但關鍵是希望在每個城市生根,產生固定化的場景。
(本文部分圖片來自簡單生活節微信公眾號)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