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石一楓《逍遙仙兒》:面對(duì)教育內(nèi)卷化,如何逍遙與想象都市?|新批評(píng)

新批評(píng)
石一楓“新世情”小說之“新”或許正在于小說的現(xiàn)代精神、現(xiàn)代氣質(zhì)和現(xiàn)代內(nèi)核,這種現(xiàn)代也賦予他的作品以“新京味”。在精彩、曲折甚至荒誕的故事背后,是有關(guān)精英話語與平民本色、啟蒙與反啟蒙、主體性的發(fā)現(xiàn)與失去這些嚴(yán)肅話題,這也是石一楓的創(chuàng)作有別于故事會(huì)式類型小說的根本所在。

文 / 張鵬禹
在教育內(nèi)卷掀起網(wǎng)絡(luò)輿論聲浪的今天,石一楓的長(zhǎng)篇新作《逍遙仙兒》無疑是對(duì)這種社會(huì)現(xiàn)象深具當(dāng)下性的回應(yīng)。小說以北京海淀“牛小”周邊學(xué)區(qū)為空間背景,描繪出一幅現(xiàn)代北京的浮世繪。在這片炙手可熱的“教育高地”上,“雞娃”家長(zhǎng)們因“都是為了孩子”齊聚一堂,而這一切真的是為了孩子嗎?隨著拆遷暴發(fā)戶王大蓮、中產(chǎn)知識(shí)精英蘇雅紋與北京土著莊博益夫婦卷入自辦補(bǔ)習(xí)班風(fēng)波,一臺(tái)臺(tái)圍繞子女教育的好戲輪番登場(chǎng),有關(guān)教育的真諦也在故事的跌宕起伏中得以揭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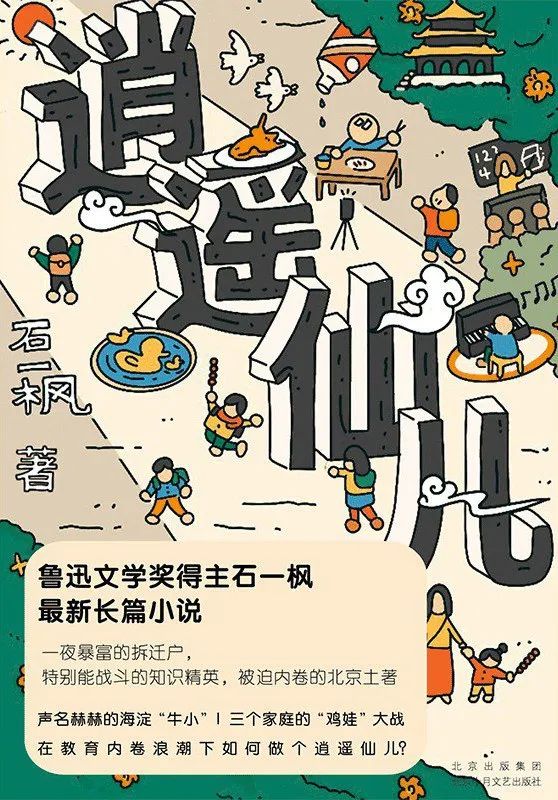
《逍遙仙兒》是教育題材,突出反映了焦慮驅(qū)使下教育內(nèi)卷化的時(shí)代癥候。這種時(shí)代癥候又以三位一體的形式在小說中被集中書寫。教育資源不均衡導(dǎo)致學(xué)區(qū)房畸形發(fā)展,擁有相當(dāng)經(jīng)濟(jì)實(shí)力的中產(chǎn)群體在此定居,形成“雞娃”共同體,家長(zhǎng)群是其聯(lián)系的紐帶之一。而上了“牛小”還不夠,作為義務(wù)教育課堂競(jìng)爭(zhēng)的延伸,大量課外補(bǔ)習(xí)班成為孩子另一個(gè)競(jìng)爭(zhēng)賽道。隨著“雙減”政策落地,課外補(bǔ)習(xí)班停辦,在蘇雅紋的誘導(dǎo)下,王大蓮在自家拆遷取得的豪宅中開起“地下補(bǔ)習(xí)班”,又一次填滿了孩子們的“課外剩余時(shí)間”。學(xué)區(qū)房、家長(zhǎng)群、補(bǔ)習(xí)班成為觀察當(dāng)下教育癥候的有力窗口,但小說不是論文,不能通過理性分析來揭示問題、說明道理,而要用人物故事使其義自見。石一楓是講故事的高手,向來追求“把精彩的故事講精彩”,在《逍遙仙兒》中,他塑造了一位當(dāng)代版的“劉姥姥”——王大蓮,也即小說的主人公。這個(gè)人物一出場(chǎng)就鬧起了笑話,因游泳班暴雷索賠無果,她把泳池中的黃鴨子“偷”走作為抵價(jià)賠償,不巧被抓,在一眾媽媽面前栽了跟頭。她再次登場(chǎng)時(shí),已經(jīng)通過拆遷成為穿著打扮浮夸的富婆新貴。盡管家里有了“半扇樓”和小半條街的門面房,經(jīng)濟(jì)地位早已遠(yuǎn)超“牛小”家長(zhǎng)們,但她依然不被家長(zhǎng)們接納。她在家長(zhǎng)群發(fā)問,什么是管樂,什么是弦樂,遭到大家明里暗里的冷嘲熱諷;在家長(zhǎng)會(huì)上不合時(shí)宜地提問誰是蘇格拉底,什么是“啟發(fā)式談話法”,洛克、杜威、皮亞杰又是干什么的,被博士班主任教育了一通;連給兩個(gè)孩子取名“大”和“二”,也讓家長(zhǎng)們覺得粗俗不堪,紛紛提醒自己的孩子不要與王大蓮的孩子來往。通過這個(gè)格格不入,被家長(zhǎng)群體排擠的人物,我們得以反觀城市中產(chǎn)的靈魂畫像。王大蓮菜農(nóng)的樸素出身,讓她骨子里的率真、坦蕩、未曾修飾,與精明世故的媽媽們裝腔作勢(shì)的行事風(fēng)格形成了鮮明對(duì)比,她的提問如同小孩戳破皇帝的新衣一樣,揭開了后者的假面。

文化的一種含義是“使一種特定的生活方式顯得與眾不同的符號(hào)的創(chuàng)造與使用”。(見阿雷恩·鮑爾德溫 等《文化研究導(dǎo)論(修訂版)》)由于在衣著打扮、言談話語、形象氣質(zhì)、文化水平諸多方面,王大蓮沒有像多數(shù)中產(chǎn)精英家長(zhǎng)一樣共享這些“符號(hào)”,她被孤立、被嘲弄和被排擠的命運(yùn)也就順理成章。王大蓮抱怨說:“‘他們’成天把‘愛’呀‘同情’呀掛在嘴邊,家里死條狗都像死了親爹一樣,恨不得老少三代披麻戴孝,怎么就學(xué)不會(huì)把‘我們’當(dāng)人呀?”小說想說明的是,決定中產(chǎn)身份的不僅是經(jīng)濟(jì)條件,更多是對(duì)某種地位群體的文化和身份認(rèn)同。這與如下的社會(huì)學(xué)觀點(diǎn)不謀而合:“中產(chǎn)階級(jí)內(nèi)部存在諸多的地位群體(status groups),同一地位群體擁有大致相似的職業(yè)聲望、生活方式和品味格調(diào),他們當(dāng)中的很多人未必有中產(chǎn)階級(jí)的自我認(rèn)同,卻更認(rèn)同自己所屬的地位群體,他們往往賦予這種地位群體以階層的意義。”(見熊易寒《精細(xì)分層社會(huì)與中產(chǎn)焦慮癥》《文化縱橫》2020年第5期)《逍遙仙兒》里的地位群體,通俗講就是“雞娃圈”,圈里的“媽媽頭”是出版社副主編蘇雅紋。她妝容精致,談吐優(yōu)雅,常穿一條英倫風(fēng)大衣,說話總是“悠悠的”,由于兒子“斯坦利”學(xué)習(xí)拔尖,她也母以子貴,成為家長(zhǎng)們的召集人。小說巧妙地栓了一個(gè)扣,將蘇雅紋與王大蓮這兩個(gè)風(fēng)馬牛不相及的人物系在了一起。原來,在王大蓮還是商場(chǎng)保潔工時(shí),蘇雅紋為她“偷”黃鴨子說過話,在眾家長(zhǎng)中,對(duì)她也比較友好。尤其是,隨著“雙減”政策落地,補(bǔ)習(xí)班關(guān)停,王大蓮家寬敞的房子正可用來私下辦一個(gè)小班,蘇雅紋想借王大蓮實(shí)現(xiàn)自己的愿望。而慣于遭人白眼的王大蓮,也想借此機(jī)會(huì)出把力,獲得家長(zhǎng)們尊重。更重要的是,辦班也有她的心氣兒——讓孩子脫離原生階層,成為她所羨慕的知識(shí)精英。兩人于是一拍即合。但王大蓮為辦班得罪了自己的老父親“道爺”。得知要砌墻辦班,讓孩子免受鄉(xiāng)下人習(xí)氣影響時(shí),道爺生氣了:“像我們一樣怎么啦?”王大蓮答:“被人看不起。”由此,經(jīng)過痛苦的蛻變,王大蓮終于從家長(zhǎng)們口中的“他們”變成了“我們”,更深層次的隱患也由此埋下了種子。

評(píng)論家孟繁華把石一楓的小說命名為“新世情”小說,這個(gè)“新”或許正在于小說的現(xiàn)代精神、現(xiàn)代氣質(zhì)和現(xiàn)代內(nèi)核,這種現(xiàn)代也賦予他的作品以“新京味”。在精彩、曲折甚至荒誕的故事背后,是有關(guān)精英話語與平民本色、啟蒙與反啟蒙、主體性的發(fā)現(xiàn)與失去這些嚴(yán)肅話題,這也是石一楓的創(chuàng)作有別于故事會(huì)式類型小說的根本所在。一開始,王大蓮試圖在蘇雅紋的幫助下洗刷掉自己身上菜農(nóng)、暴發(fā)戶的影子,在啟蒙與被啟蒙的話語中,她的平民本色被附加上了一層中產(chǎn)標(biāo)簽。她不僅穿上了流行品牌“露露檸檬”,打扮成了一個(gè)戶外愛好者,連神色、談吐、嗓門、氣質(zhì)都變了。更深層次的是,她的價(jià)值觀向“他們”靠攏了。王大蓮向精英中產(chǎn)靠攏的過程中,與原生家庭父親道爺、丈夫六子的割裂,亦成為她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重。作者借對(duì)“偽啟蒙”的揭示與嘲諷,批判了中產(chǎn)精英拉大旗扯虎皮的虛偽。
當(dāng)王大蓮成為家長(zhǎng)們的召集人,成為“他們”、獲得尊重以后,她卻一時(shí)間迷失了自我,“天哪,我是怎么了,我過去看著我爸爸的眼色活著,現(xiàn)在卻看著蘇雅紋的眼色活著了……不不,我是先變成了蘇雅紋又用蘇雅紋的眼色看著我……我能對(duì)我的房子、孩子做主,但到底沒能做了自己的主。我從舊的我活成了新的我,但究竟哪個(gè)才是真的我?”蘇雅紋的“啟蒙”讓王大蓮有了主體性意識(shí),可這種意識(shí)又如空中樓閣那樣縹緲,宛如給一個(gè)精神貧瘠的人穿上華麗的外衣,總透露著蹩腳的尷尬。王大蓮主體性的困惑,又何嘗不是一種今天十分普遍的身份認(rèn)同危機(jī)。

在此,小說觸到人文主義的一個(gè)古老命題——何為文化?蘇雅紋以及她所代表的“偽文化精英主義”從本質(zhì)上說只是將文化當(dāng)作一種功利性手段,借以實(shí)現(xiàn)中產(chǎn)地位的代際延續(xù)。按照馬修·阿諾德的觀點(diǎn),“文化是甜美,是光明,它是我們思想過和言說過的最好的東西,它從根本上說是非功利的,它是對(duì)完善的研究,它內(nèi)在于人類的心靈,又為整個(gè)社群所共享,它是美和人性的一切構(gòu)造力量的一種和諧。”(見陸揚(yáng)、王毅《文化研究導(dǎo)論(第三版)》)顯然,小說中城市中產(chǎn)媽媽們的立場(chǎng)、態(tài)度和方法與此背道而馳。這也就難免讓他們?cè)谔K雅紋的孩子“斯坦利”患上躁郁癥后,對(duì)其群起而攻之,勒令其轉(zhuǎn)學(xué)。而這時(shí),因地下培訓(xùn)班取締對(duì)蘇雅紋心生芥蒂的王大蓮卻站了出來,不僅堅(jiān)決不在起訴蘇雅紋的律師函上簽字,還用她樸素的辦法——陪讀,化解了“斯坦利”的轉(zhuǎn)學(xué)危機(jī)。作者寫道:“但再一細(xì)想,除了王大蓮,似乎別人也很難想到這個(gè)辦法,因?yàn)槟沁€關(guān)乎到了‘思維習(xí)慣’和‘底層邏輯’——不僅需要閑暇,需要行動(dòng)先于思考的本能,還需要一種別的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一種什么東西呢?”這個(gè)東西就是樸素的世道人心——仁義。王大蓮的父親道爺當(dāng)年在村子里當(dāng)村長(zhǎng)時(shí)對(duì)村民仁義,六子在王大蓮?fù)煹罆r(shí)守著,防著別人欺負(fù)她是仁義,王大蓮自己倒貼錢給孩子們辦補(bǔ)習(xí)班是仁義……正是這種樸素的價(jià)值觀,在關(guān)鍵時(shí)刻,戰(zhàn)勝了現(xiàn)代理性給人帶來的文明矯飾,不僅解決了實(shí)際問題,也令其擁有者獲得了大眾尊敬。

小說至此,對(duì)內(nèi)卷有一個(gè)發(fā)人深省的疑問:“我又想起了自己小時(shí)候:放了學(xué)就滿院子瘋跑,鑰匙拴在脖子上都能弄丟了,等到炊煙升起,還要和大人展開一場(chǎng)氣急敗壞的追逐戰(zhàn)……童年的模樣不是本該如此嗎?也沒耽誤我們成長(zhǎng)為堅(jiān)忍、奮進(jìn)的一代人。怎么我們的常態(tài)反而成了下一輩的奢侈?倘若如此,我們的辛苦究竟是給他們積福還是造孽呢?”由孩子的卷,上升到家長(zhǎng)的卷,再上升到整個(gè)社會(huì)的卷,其中又有多少對(duì)人本性的扭曲?“斯坦利”的悲劇不正源于此?他想抓住那只童年的黃鴨子,卻多么難!小說結(jié)尾處,道爺回了農(nóng)村種菜,王大蓮的違規(guī)辦班得到豁免,爺倆的關(guān)系也修復(fù)如初,而蘇雅紋亦隨丈夫到外地工作,這個(gè)看似大團(tuán)圓的結(jié)局,實(shí)則說明了作者的核心觀點(diǎn)——各安其位,才能成為“逍遙仙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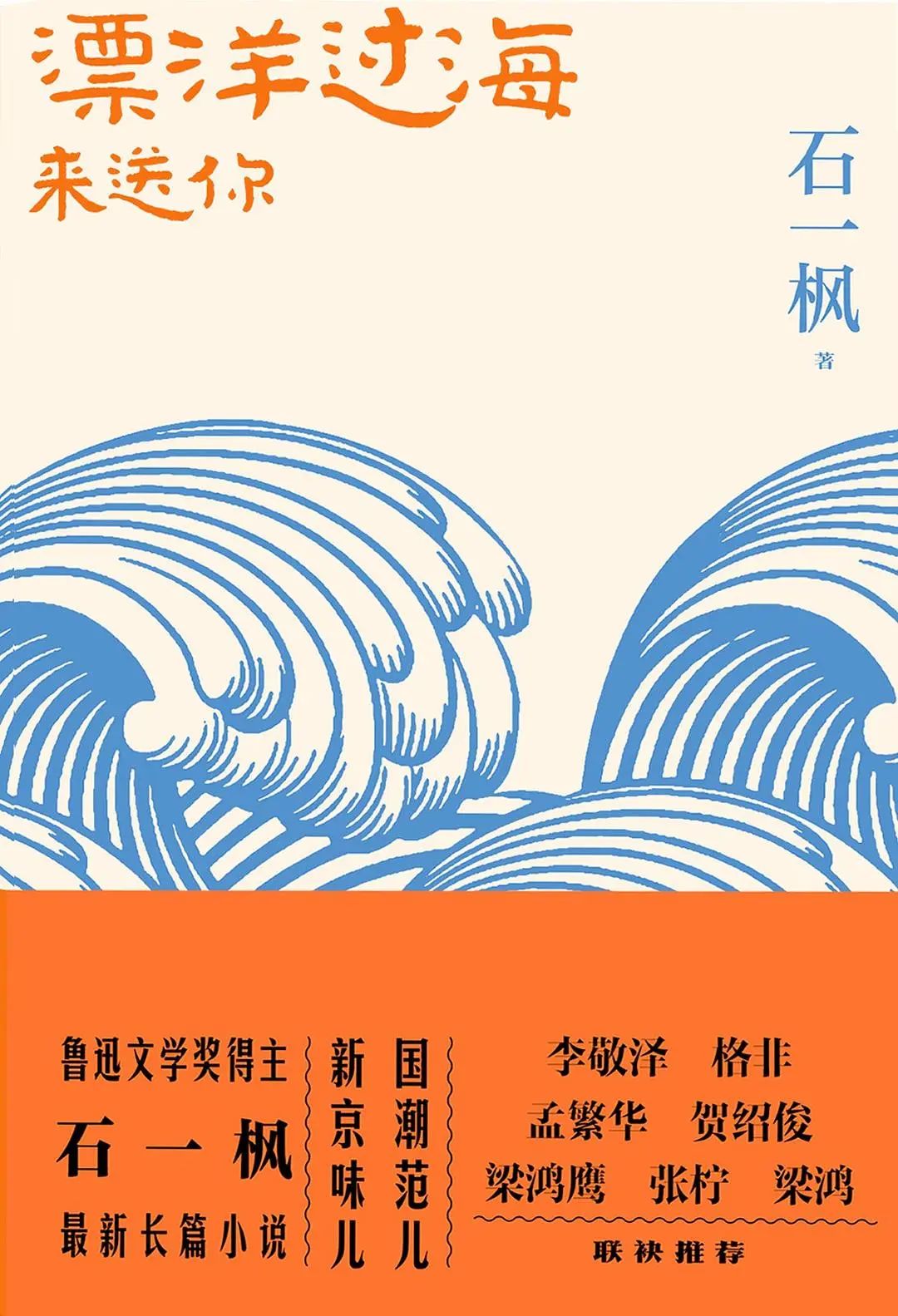
以上是從故事層面分析,從空間層面看,《逍遙仙兒》是石一楓書寫北京的又一力作。他想象北京的方式歷來是去中心化的,不論是《戀戀北京》《世間已無陳金芳》,還是《玫瑰開滿了麥子店》《漂洋過海來送你》《入魂槍》,北京在石一楓筆下都是一個(gè)平民世界。《逍遙仙兒》也一樣。小說中的“道爺”一改拆遷暴發(fā)戶的傳統(tǒng)形象,他身上留存著老北京人講禮、好面兒、軸等性格特質(zhì)。莊博益與道爺合作,拍攝吃播紀(jì)錄片,構(gòu)成了小說的另一條線索,將互聯(lián)網(wǎng)短視頻風(fēng)潮與老北京美食巧妙嫁接。從流量巔峰到為次館子代言被網(wǎng)暴,作者將道爺“事業(yè)”的潮起潮落與跟女兒王大蓮斗法融為一體,為小說植入了一重本土視角。道爺與三兒的兄弟情深,與六子的亦父亦兄,與大蓮子的血濃于水,刻畫出這位以失去土地為代價(jià)而一夜暴富的老村長(zhǎng)、老北京的心靈畫像。他的江湖已遠(yuǎn),與在家庭中話語權(quán)的喪失,構(gòu)成了一曲舊時(shí)人物的挽歌,是作者向上世紀(jì)七八十年代京味小說傳統(tǒng)的致敬。而伴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創(chuàng)業(yè)熱潮來去匆匆的蘇雅紋夫婦,也賦予北京這座城市以移民視角。
說句題外話,以我之見,道爺?shù)脑陀鞋F(xiàn)實(shí)生活中短視頻主播@牛道的影子,那個(gè)標(biāo)志性的單臂大回環(huán)配上一句“地道”很可能取材于此。有人開玩笑說,短視頻中的北京與現(xiàn)實(shí)中的北京區(qū)別在哪?恐怕是前者沒有“道”,全是“地道”。老北京形象的娛樂化,讓“京味”在互聯(lián)網(wǎng)短視頻時(shí)代以找樂子、逗悶子的形式得以流傳,殊不知是可喜還是可憂。
文章編輯:傅小平 ;新媒體編輯:鄭周明
配圖:攝圖網(wǎng)

原標(biāo)題:《石一楓《逍遙仙兒》:面對(duì)教育內(nèi)卷化,如何逍遙與想象都市?|新批評(píng)》
本文為澎湃號(hào)作者或機(jī)構(gòu)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fā)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jī)構(gòu)觀點(diǎn),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diǎn)或立場(chǎng),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fā)布平臺(tái)。申請(qǐng)澎湃號(hào)請(qǐng)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yíng)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