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導論|從天書時代到古文運動:北宋前期的政治過程
本文為《從天書時代到古文運動:北宋前期的政治過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0月版)一書“導論”,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摘發。
一,古文運動的政治背景:“天書時代”
學者談論古文運動多并稱唐宋,實則“唐宋古文運動”涵蓋多個不同的歷史時期,時代脈絡也各有不同。韓愈(768—824)、柳宗元(773—819)面對的是安史之亂后的中唐,柳開(947—1000)的歷史時空則為宋代的初興,而孫復(992—1057)、石介(1005—1045)、歐陽修(1007—1072)等人經歷的,是真宗(997—1022在位)到仁宗朝(1022—1063在位)的變化。因此,所謂唐宋古文運動,與其說是一個連續發展的過程,不如說是存在許多斷裂面。不同時空背景下的古文家,所面對的歷史課題也大相徑庭。宋代古文家對唐代古文學者的引述與頌贊,與其說是受到前輩們跨時空的“影響”,不如說是后來者在面臨當下的時代課題之際,提取、詮釋了前輩古文學家的思想與理念。

歐陽修
北宋古文運動的要角孫復、石介、歐陽修等人的成長背景,正是真宗一朝的“天書”時代。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三日,真宗獲得降于皇城承天門的天書。從此,真宗供奉著天書,進行一連串的祭祀禮儀:祥符元年十月到泰山舉行祭天的封禪大典,祥符四年(1011)二月到汾陰祭地,隔年,真宗自言道教神仙同時也是趙宋祖先的“圣祖”,親自降臨在他面前;祥符七年(1014)正月,真宗到亳州朝謁老子太清宮,天禧元年(1017)奉上玉皇、圣祖圣號寶冊。這一連串夾雜怪力亂神的奉神禮儀,對現代學者來說,可謂匪夷所思。認為大中祥符時代的奉神禮儀,乃是真宗君臣合謀作偽,以化解澶淵之盟帶來的恥辱,便成為通行的觀點。但也正是“天書”的時代,構成了宋代儒學運動的起點——古文運動的政治背景。
本書以“天書時代”指稱這段時期:真宗祥符元年到劉太后(968—1033)過世的明道二年(1008—1033)。這樣的指稱,不僅在于“天書”在這個統治階段,被君主視為政權正當性的主要象征,也在于這段時期的政治文化,由于天書的存在而有其特殊性。雖然“天書時代”的稱法,將真宗統治的大中祥符(1008—1016)、天禧(1017—1021),與劉太后主政的天圣(1023—1032)、明道(1032—1033)視為一個整體,但本書同樣重視的,是梳理從真宗到劉太后統治期的差異與變化:劉太后統治期,一方面可視為天書時代的有限度延續,另一方面卻也是天書時代的消退與萎縮,古文運動在此過程則悄悄醞釀。
二,政治史與儒學史的內在聯動
本書通過梳理北宋前期的政治過程,分析宋代古文運動展開的歷史脈絡。本書不僅探究北宋前期的政治史與儒學史,更重視析理這兩個學術范疇如何彼此牽動。北宋前期政治史研究已經累積了可觀的成果,但既有研究以單篇論文為主,以專書形式、系統性探討北宋前期政治過程的著作仍不多。其中,有三部作品盡管成書多年,但仍構成理解此時期政治史的重要著作,也是本書討論得以展開的前沿研究:劉靜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們的權力》、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何冠環(Koon-wan Ho)Politics and factionalism:K'ou Chun(962-1023)and his‘t'ung-nien’。
這三部作品分別代表了政治史研究的三種典范:以帝王為中心、以議題為導向、以士大夫黨派斗爭為核心。它們都揭示了北宋前期政治史的重要面向。但也因此,若欲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推進或突破,則必須探索不同以往的研究方法與切入視角。鄧小南在《祖宗之法》中,這樣期許后繼研究:找到一個能夠牽動某時代的政治過程、文化思維、社會活動、思想探索,并對歷史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課題。
盡管批判與否定構成宋代以降士大夫對天書時代的立場基調,但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天書時代”為一極具牽動力的議題。這個時代援引、镕鑄了諸多漢唐儒學思想,并打造了一個世代獨特的政治文化與社會氣氛,影響所及不僅及于中央朝政,亦下至地方社會。真宗打造的天書時代,與緊接而來的仁宗朝古文運動,更有著內在發展的理路。換言之,“天書時代”這一被歸為政治史的議題,如何牽動思想史的關鍵課題“古文運動”,便是本書探究的主題。古文運動與慶歷改革,向來是北宋儒學史與仁宗朝政治史的重要課題。余英時先生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便指出宋初古文運動是宋代儒學的第一階段,古文運動的學者熱心于得君行道,從而引發慶歷改革。研究宋代古文運動的代表性著作,依出版時間排列有:金中樞《宋代古文運動之發展研究》;劉子健《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何寄澎《北宋的古文運動》;祝尚書《北宋古文運動發展史》;漆俠《宋學的發展和演變》。這些著作在個別細節上詳簡有別,但總體而言,他們的研究為宋代古文運動勾勒出一個“典范敘事”。此一敘事包含三項結構性要素:第一,宋初古文運動先鋒柳開,主張文章應闡揚古圣人之道,從而改變了五代的弱質駢文;第二,楊億(974—1020)與劉筠(970—1030)在真宗一朝,吹起一股重視修辭、對仗的反古文精致文風;第三,仁宗朝由范仲淹(989—1052)、歐陽修、孫復、石介、穆修(979—1032)、尹洙(1001—1047)等開啟反楊億文風的古文運動。古文家的共通趨向是不再依循漢唐經典注疏,而是從儒家本經著手,直探圣人之道。且此“道”,必須借由政治改革加以實踐。因此,慶歷改革經常被學者視為仁宗朝古文運動學者的政治實踐。
上述古文運動的“典范敘事”,構成學界對仁宗朝儒學運動的基本認識,似乎難再突破。漆俠先生在21世紀初作《宋學的發展和演變》,對個別儒者的經學思想、政治活動有十分細致的討論,但在整體架構上,并未挑戰這個典范敘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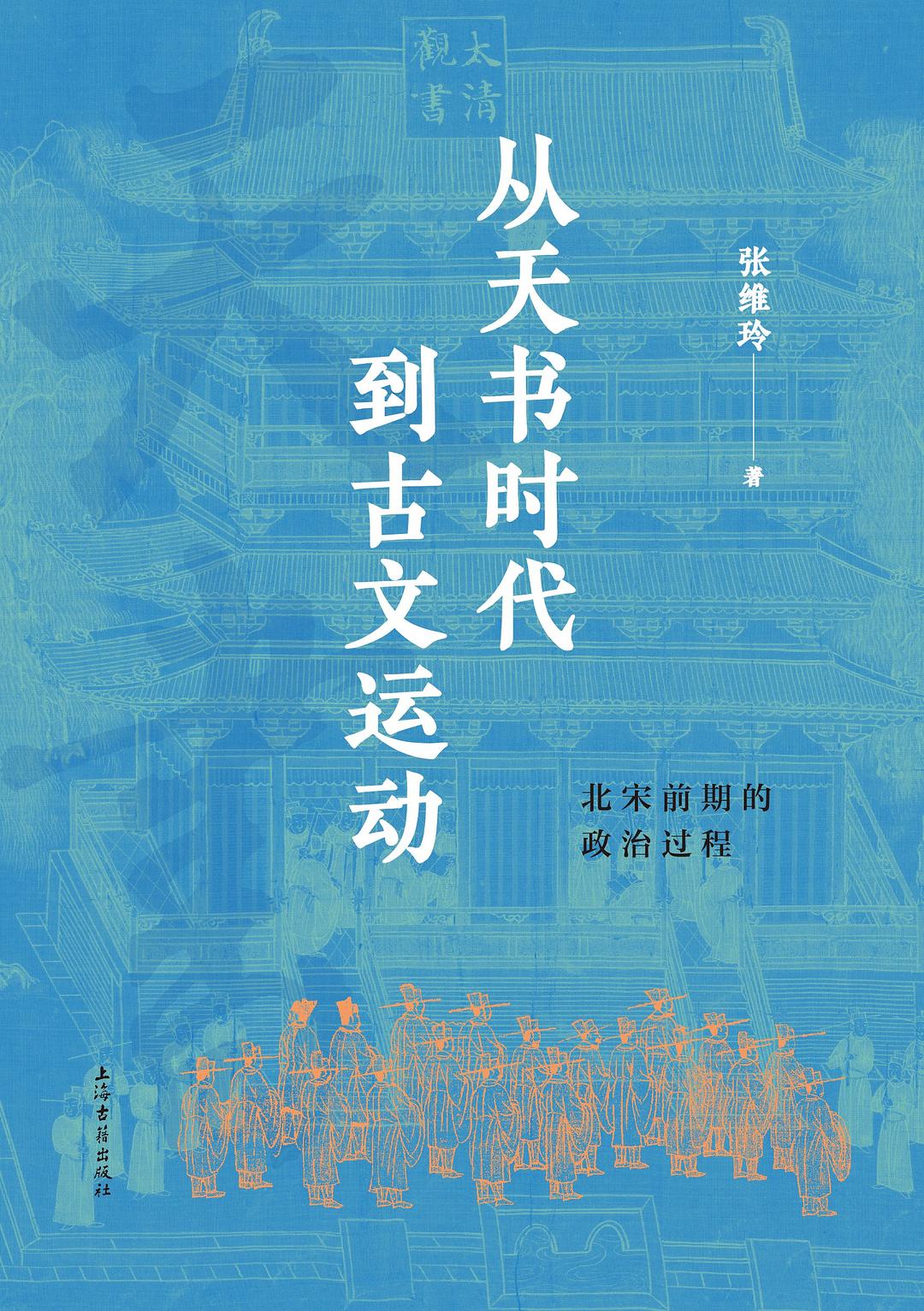
《從天書時代到古文運動:北宋前期的政治過程》
那么,此“典范敘事”是如何產生的?筆者認為,這三階段的結構敘事,最早完整地呈現在范仲淹所作尹洙文集序:
唐貞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寢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涂(開)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涂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洎揚大年(億)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于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洙),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修)游,力為古文,而師魯深于《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其深有功于道歟!
短短二百多字便概括了現代學者對古文運動的理解框架。然而,細究這段文字,其實有諸多問題尚待解答。首先,為什么范仲淹將古文運動追溯到已過世半世紀的柳開?柳開在世時,僅官至知州,且從未進入中央任職,柳開的影響力,為何能夠改變所謂五代“薄弱”文風?柳開“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于天下者”是哪些人?他們對古文運動有何貢獻?其次,范仲淹的詮釋,無疑有其特定的立場與視角。這篇序既是為尹洙文集而作,序文難免突出尹洙及其師穆修的重要性,文末更強調了范仲淹與尹洙共同好友歐陽修的貢獻。我們是否能把此書序的敘事,視為古文運動的發展實況?
檢視范仲淹的尹洙書序,實際上是在放大個別人物的影響力的同時,模糊化了歷史發展的脈絡。范仲淹的書序,并沒有告訴我們為什么柳開或楊億能有如此大的影響力,也沒有說明為什么尹洙與歐陽修能夠改變重視雕琢的文風。而這個文風變化的時代—從柳開過世,到所謂歐陽修等重振古文、古道,正是以天書時代與慶歷改革為政治背景。
因此,欲突破古文運動的典范敘事,便有必要重新梳理真宗到仁宗朝的政治過程,從而還原古文運動復雜的發展歷程。真宗朝的天書時代,并不是在真宗過世的那一刻便畫上句點,而是影響了一整個世代的政治意識形態,與配合此意識形態的文章撰作。楊億是這個時代的佼佼者與代表人物,但并不是影響這個時代的關鍵人物。真宗的過世,確實帶來政風、文風轉變的契機,但這個轉變的過程,亦非單憑數人能夠翻轉,而是由身處不同權力位置的士大夫們,在不同的時間點,做出關鍵性的建議與決策。范仲淹、歐陽修與尹洙等慶歷改革核心人物,雖是其中要角,但卻不是對此轉變做出貢獻的唯一群體。
基于上述的反思,融合政治史與儒學史(以本書所關注的面向而言,更確切的說法是經學史)成為本書最關鍵的切入角度。既有研究往往將政治史與儒學史劃分為兩個不同的研究領域,政治史是歷史學者關心的課題,儒學史則為中文研究學者所關注。兩個研究社群有各自的研究傳統,卻也因此較少相互對話。故而,天書時代為歷史學所注目,古文運動則被劃入儒學史或文學史的范疇。這便導致真宗朝的天書統治,與仁宗朝的古文運動,盡管在時間上前后相續,但似乎各自獨立、無所關聯。然而,至少在北宋以前,儒家士大夫對儒家經典的闡述與詮釋,往往是為了回應現實的政治問題;儒士作為政治場域中的主要參與者,他們腦海中的儒學思維與觀點,也深刻影響了政治發展的走向。
本書認為,過去屬于政治史范疇的“天書時代”,本質上是真宗君臣利用、詮釋儒家經典,最后卻以破壞儒教統治告終的歷史過程。宋太宗后期至真宗統治前期,趙宋朝廷頒布了主要由漢唐儒者注疏的“十二經”經典詮釋。天書時代的神道禮儀,即是操辦者對官方經典注疏進行選擇性的接受,與詮釋性的應用結果。另一方面,天書時代又大量融入了道教奉神之禮,并將之接架于儒教祭禮之上,從而對儒教祭禮進行突破。從儒家本位立場的士大夫來看,則不啻是對儒教統治的破壞與否定,從而引起他們對政治現狀的焦慮與反省。故而,真宗、仁宗之際政治文化的變遷,本質上也是士大夫對儒家經典的維護與反思。
其次,過去被認為屬于儒學史與文學史范疇的古文運動,亦必須放在真、仁之際的政治史脈絡中,重新解讀。正如學者一致贊同,仁宗朝古文運動帶有強烈的政治改革、重建秩序的目的。這背后蘊含的潛臺詞是:他們對既有的政治秩序頗感不滿。這個令他們不滿的政治秩序,自然不會是二百多年前安史之亂后的中唐,亦不會是一百年前五代的分裂格局,而是直接構成仁宗朝統治基礎的天書時代。天書時代正是范仲淹、孫復、石介、歐陽修等人年少時的親身經歷;也是他們及許多同時代的士大夫,希望將之掃除的政治遺產。換言之,正是在與天書時代所利用、破壞的經典詮釋進行不斷對話的過程中,激發了新一波的古文運動。
總之,從天書時代到古文運動,一方面意味著帶入儒學史的視角,以翻新北宋前期的政治史;另一方面則是將古文運動鑲嵌入其政治史脈絡,以深化我們對古文運動的認識。需要說明的是,本書探討北宋前期的“政治過程”,討論的時間下限大抵在慶歷改革,而不涉及仁宗晚期或北宋后期古文的發展。換言之,本書探究的主題與時代范圍,與從文學觀點討論北宋古文與文學的研究,有根本差異。
三,推動政治過程的政治派別
本書既是探討北宋前期的政治過程,推動此“過程”的君主與士大夫群體,毫無疑問是本研究的主角。本書將中央的政策走向視為一個權力競爭的場域,不同派別的士大夫都欲爭取最高權力者—君主的支持,以將他們的政治理念付諸實踐。本書揭示的政治“過程”,正是在不同派別士大夫的理念抗衡與權力競爭中推進。
本書以“派”或“派別”來指稱推動政治過程的政治團體。“派”與“派別”包含兩個互為因果的內涵,其一是同屬一派的士大夫,彼此有著較為緊密的人際往來;其二是同屬一派的士大夫,有著相近的政治立場與政治理念。本書將以派別人物中,具領袖地位,或政治影響力最大的士大夫,指稱該派士人群體。盡管任何一個派別都不可能有固定、明確的邊界,其成員也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減,但我們仍可借由人際網絡與政治立場的分析,辨識出不同派別士大夫如何在特定時間點,推動著政治的發展。其中,有些派別士人內部存在較明確的師生關系,使他們構成該派領袖人物的“后學”。因此,為了避免指稱上的單一,本書有時也以領袖人物的“后學”指稱具有較明確師生關系的士大夫群體。
學者們同意以范仲淹為首的慶歷改革者懷抱著政治理想,但很少注意到打造祥符天書時代的徐鉉(916—991)王欽若(962—1025)一派文士,也有其獨特的政治理念,并且說服真宗將之付諸實踐。不過,真、仁之際政治過程的推演,并非單靠王欽若與范仲淹兩派政治群體便能推動,他們甚至不是這段時期權力最盛者。本書將納入更廣的士大夫群體,探討他們如何參與真、仁之際的政治過程。其中包含李昉(925—996)王旦(957—1017)楊億派文士、柳開后學,與孫奭(962—1003)派士大夫。這幾個群體獲得現代學者的關注度,遠不及范仲淹及其政治支持者,但他們卻是在慶歷改革以前,與仁宗關系最親近、影響朝政甚巨的士大夫。這些不同派別的士大夫,在真、仁之際的政治過程與古文運動的發展上,扮演著立場不同但又都相當關鍵的角色。唯有將他們也納入分析視野,才可能深入了解古文運動如何在復雜的權力競爭中展開。
四,《宋會要輯稿》與士大夫文集的史料價值
李燾(1115—1184)《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無疑是研究北宋政治史最為重要的史料,但若過度依賴《長編》來探討北宋前期的政治過程,亦有風險。蔡涵墨分析《長編》與《宋會要輯稿》在北宋各朝的史料比重分布,發現《長編》中,真宗一朝的史料比例偏低,仁宗朝,特別是慶歷時期的史料分量則特重。真、仁兩朝的《會要》內容,分別源自慶歷四年(1044)王洙(997—1057)上奏的《會要》,與元豐四年(1081)王珪(1019—1085)續編的《會要》。盡管仁宗在位四十二年,遠超過真宗在位的二十五年,但在今存《宋會要輯稿》中,真宗朝的條目竟略多于仁宗朝。這顯示李燾在編寫真宗朝歷史時,在他所能見到的真宗朝材料的基礎上,進行了大幅刪減。這個現象無疑是由于仁宗朝以降的儒家士大夫,貶低真宗天書時代的價值。這也警醒現代學者:依靠《長編》討論真宗朝的歷史,是遠為不夠的;《宋會要輯稿》則是重建真宗朝歷史更為早期、豐富的材料。
因此,本書除了引用約五百則《長編》,亦引用約一百二十則《宋會要輯稿》中的材料。特別在第二、三章,我們將看到,《長編》如何刪減了《宋會要輯稿》中的關鍵信息。此外,本書也引用了約五十則宋綬(991—1040)、宋敏求(1019—1079)所編的《宋大詔令集》,這些詔令亦是研究北宋政治史的重要原始材料。
北宋前期的士大夫文集,也是本書倚重的史料。除了第二、三章大量引用徐鉉文集外,第五章更是以仁宗朝文士文集作為主要的史料依據。李燾《長編》雖然為仁宗朝留下十分豐富的材料,但李燾對范仲淹及其政治盟友的同情,導致反對慶歷改革的士大夫,在《長編》中的能見度遠無法匹配其在當時的影響力。幸好,目前留下文集的仁宗朝士大夫,不僅包含慶歷改革的中堅人物,如范仲淹、歐陽修、韓琦(1008—1075),還包含支持改革但人際網絡頗為復雜的石介。石介人際網絡的多元性與豐富性,為我們認識這段歷史提供了珍貴材料。此外,與范仲淹等人關系緊張的宋庠(996—1066)、宋祁(998—1061)兄弟,也留有文集,能幫助我們探索范仲淹盟友之外士大夫群體的政治與思想動向,從而為本書勾勒出更為立體的歷史圖像。
五,從天書時代蛻變出的古文運動
本書分為兩部分。上篇“天書時代的形成”為前三章,分析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奉天書而行的神道禮儀,如何從漢唐政治中的儒學與道教神仙信仰汲取思想資源,這些思想資源又構成怎樣的宗教統治邏輯,以肯定政權的正當性;下篇“歷史中的古文運動”包含后二章,探究天書時代如何在真宗及劉太后相繼過世后,遭到在朝、在野士大夫的反思與批判,從而推展出古文運動與慶歷改革。一言以蔽之,本書將揭示:仁宗朝的古文運動是在批判天書時代的過程中蛻變而出。
第一章探討天書時代的前奏—太祖(960—976在位)、太宗君臣如何追求統治正當性,以擺脫五代短命而終的陰影。在漢唐歷史發展中,“封禪”大典象征著統一帝國“致太平”的成就。太祖、太宗皆渴望封禪,卻未能實現。換言之,封禪并非真宗在澶淵之盟后才欲進行的典禮,而是繼承父志的舉措。本章亦探討君主祭天之禮如何為太宗朝的文臣創造發揮的舞臺。太宗雖因與契丹的軍事挫敗而未能封禪,但儒教的祭天之禮因為象征統治者的“天子”身份,而獲得太宗的高度重視。為太宗操辦大禮的,便是以李昉為首的北方文士,他們因此獲得太宗青睞,而經常位居宰執之位。相對而言,以徐鉉為首的南唐降臣,盡管得到李昉等北方文士的禮遇,但并未獲得太宗的信任。
第二章探討天書時代的兩種思想成分:讖緯與道教,以及徐鉉后學如何镕鑄這些思想成分,以打造號稱太平的天書時代。讖緯學形成于東漢初,并在漢唐儒者的援引下,與儒家經典注疏緊密結合。讖緯學的核心概念認為,得到“天命”的君主,皆會獲得龍、龜等靈獸獻上的河圖、洛書,即天書。真宗統治初期,已流露出對“河圖、洛書”的向往。本章即分析徐鉉派文士—以王欽若、陳彭年(961—1017)、杜鎬(938—1013)為核心,如何在真宗朝與北方文士展開新一波的競爭,并爭取到真宗的信任,而將他們的道教統治理念結合讖緯思想,實踐于祥符時代。
第三章探討天書時代所依循的統治概念與世界觀,以揭示真宗君臣對太平后的宇宙秩序想象;以及在此統治秩序下,從中央到地方的士人如何主動或被動地卷入這場頌贊太平的政治運動。依據天書時代的統治概念,儒教昊天上帝已非最高主宰,而是位居道教尊神之下。祥符時代崇奉道教神仙的儀式,不僅在朝堂上進行,更是以多層次的方式推廣到地方,從而輻射出更廣的影響力。此時,自認成功交通天、地、神靈的真宗,將自己定位為依循《洪范》“皇極大中”思想,居于絕對正確位置的帝王。他開始大量撰寫文誥,來“教導”臣民;中央朝士與地方士人,則撰作歌頌真宗太平之政的文字,以交換政治與文學上的聲譽與地位。在此政治文化下,原本對神道禮儀感到疏離的王旦派士大夫,為了與王欽若一派競逐權力,也逐漸卷入天書時代的各種活動。
第四章探討仁宗統治前期,天書時代的政治文化如何逐步破損,以致“太平無為”的意識形態瓦解,政治改革則逐漸成為君臣的共識。真宗過世后,立即浮現一個問題:年幼即位的仁宗不可能接續真宗如導師般的帝王角色,這便使天書時代的政治文化出現破口。本章首先分析劉太后主政時期,皇權如何致力于維護太平之下的統治模式,而這樣的統治模式,又如何屢屢遭到臣僚的挑戰。其次,探討仁宗親政后至慶歷改革前(1033—1043),士大夫們如何更積極地調整、打破真宗以來的“太平”論述。我們將看到,仁宗統治前期,君臣長期在“說法”上,將“太平”視為既定事實;直到慶歷改革前夕,“太平”才在君臣的政治話語中成為過去式,政治改革的正當性也才得以獲得肯定。

《清平樂》中的范仲淹
從天書時代到慶歷改革的政治過程,范仲淹及其支持者無疑最受學者注目,但他們并非唯一對真、仁之際政治文化轉變做出貢獻的群體。此章分析仁宗朝堂上兩股重要的政治勢力—楊億派與孫奭派士大夫。相較于范仲淹及其支持者在仁宗親政后才崛起,楊、孫派士大夫與真宗朝宰相王旦有緊密的關系,同時也是仁宗年少時親近熟悉的士大夫群體,他們長期把持朝政,并與范仲淹一派士大夫明爭暗斗。此章將從這個結構性的權力關系,解釋為什么慶歷改革很快以失敗告終:獲得仁宗更多信任的孫、楊派士大夫,并不樂見范仲淹一派勢力的崛起。
第五章分析古文運動如何在批判天書時代的過程中蛻變而出。首先討論仁宗朝士大夫對祥符時代的批判,從而說明古文運動對儒家圣人之“道”的強調,如何在方方面面針對天書時代而發。其次,重新考察古文運動的發生與擴展。此章將指出,歐陽修與尹洙雖然也參與、支持古文撰作,但卻非促成古文在景祐年間(1034—1038)蔚為風潮的關鍵人物,柳開后學與楊億派士大夫的貢獻,實際上更為關鍵。最后,探討仁宗朝士大夫對天書的理論根據—河圖洛書的深刻反思。他們否定河圖洛書為帝王受命文書的讖緯學解經傳統,從而瓦解天書在儒家經典詮釋中的理論依據。這一方面促使儒者批判漢唐以讖緯解經的傳統,另一方面也開啟了直探本經的儒學運動。換言之,仁宗朝士大夫對“天書”的批判,正構成了疑經思潮的關鍵起點。
王欽若以“城下之盟”詆毀寇準,并說服真宗偽造天書的故事,自北宋仁宗朝起即開始流傳,并衍生出多個版本。這個著名的故事主宰了后世對真宗天書的認識,但也模糊化了天書時代的發生脈絡與后續影響。天書時代的形成,奠基于北宋前三帝致力于擺脫短命而亡的陰影,以追求太平的統治理想;此太平理想的追求,為朝中儒家士大夫創造可競逐的舞臺,并最終歸結于徐鉉后學對漢、唐政治文化的汲取與镕鑄,從而打造了天書統治的時代。
真宗末到仁宗前期的政治過程則是天書時代的逐步瓦解,同時也構成中國儒學發展的關鍵時期。經歷了仁宗朝古文運動的洗禮,漢唐儒家經典詮釋喪失了權威地位,宋儒開啟了自解經典的新道路。仁宗朝參與古文運動的學者盡管提出許多新的經學見解,但他們并未達成任何共識;也沒有任何一位儒士的經學見解,能夠爭取到仁宗的認同;仁宗朝的政治革新,也仍停留在摸索、修正的階段,而非如熙寧變法那樣大刀闊斧的改革。但正是這些不成功的嘗試,揭開了宋代儒學的序幕,而后我們才可能見到王安石(1021—1086)新學、蘇學與二程理學的互相爭勝,與抱持不同得君行道之法的儒士所主張的政治改革。總之,仁宗朝乃一大破而未立的時代,它充滿了破壞力與爆發力,它否定了镕鑄多重漢唐思想元素的祥符天書時代,為宋代儒學開啟了百家爭鳴的盛況。
真、仁之際的政治過程,也是中國政治文化史上的關鍵轉折期。真宗的東封、西祀并非創發,而是漢唐盛世君主漢武帝(141—87B. C. E. 在位)、唐玄宗(712—756在位)皆曾舉行。然而,東封、西祀在真宗以后便成絕響,這與天書時代從中央到地方的廣泛影響力,與隨之而來仁宗朝士大夫的深刻反省與批判有絕對的關系。此外,漢武帝、唐玄宗、宋真宗皆在統治后期,追求神仙與道教,真宗更是明確將神仙之道凌駕于儒道,打造道教統治的帝國。因此,天書時代的破產,再次確立了儒教在中國統治理念上不可取代的地位。總之,本書將揭示,真宗的天書時代可說是將漢至宋盛世君主對太平盛世的認知與想象,更系統化地進行重組與展演,其結果卻是將漢宋時期的盛世禮儀,化作歷史的塵埃。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