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韓炳哲:無論是抑郁癥、注意力缺陷多動癥或疲勞綜合征,都指向一種過度的肯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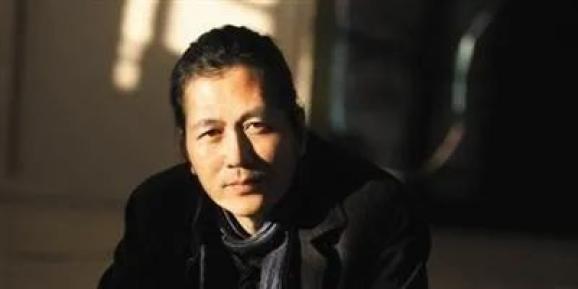
韓炳哲
每個時代都有其占據(jù)主流的疾病,例如歷史上的細(xì)菌時代,隨著抗生素的發(fā)現(xiàn)而走向終結(jié)。盡管我們對于大型流感仍然懷有強(qiáng)烈的恐懼,然而如今我們已不再身處病毒時代。有賴于免疫科學(xué)的發(fā)展,我們已經(jīng)擺脫了這一歷史階段。從病理學(xué)角度看,21世紀(jì)伊始并非由細(xì)菌或病毒而是由神經(jīng)元主導(dǎo)。各種精神疾病,如抑郁癥、注意力缺陷多動癥(ADHS)、邊緣性人格障礙(BPS)或疲勞綜合征(BS)主導(dǎo)了21世紀(jì)初的疾病形態(tài)。它們不是傳染性疾病,而是一種梗阻病,不是由免疫學(xué)上他者的“否定性”導(dǎo)致,而是由一種過量的“肯定性”引發(fā)。免疫科技以抵御外來者的負(fù)面影響為基礎(chǔ),從此失去了往昔的地位。

倦怠社會
作者:[德] 韓炳哲 著 王一力 譯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tuán)·見識城邦
出版時間:2019-06
精神暴力
文/韓炳哲
譯/王一力
20世紀(jì)是免疫學(xué)的時代。在這一時期,內(nèi)外、友敵、自我和他人之間存在著清晰的界限。冷戰(zhàn)也遵循了這種免疫學(xué)模型。20世紀(jì)的免疫學(xué)范式中充斥著冷戰(zhàn)話語,由一種嚴(yán)格的軍事化規(guī)則控制。攻擊和防御主導(dǎo)著免疫學(xué)式行動。這種免疫學(xué)原則超越生物學(xué)范圍,到了社會領(lǐng)域,最終蔓延至整個社會層面,一種盲目性被烙印其中:對一切陌生之物,都采取防御措施。免疫防御的對象即是這種陌生之物。即便陌生者毫無惡意,即便他不會產(chǎn)生任何威脅,仍然會基于他的“他者性”(Andersheit)而受到排擠。
近年來出現(xiàn)的種種社會理論,都明顯以免疫學(xué)詮釋模型為基礎(chǔ)。免疫學(xué)話語的流行并非意味著,當(dāng)今社會比過去更加受制于免疫學(xué)原則。一種范式自身成為反思的對象,這往往標(biāo)志著該范式的衰落。近年來已經(jīng)悄然發(fā)生了一場范式的轉(zhuǎn)移。冷戰(zhàn)的結(jié)束就發(fā)生在這場范式轉(zhuǎn)移的進(jìn)程中,叫當(dāng)今的社會狀況,更加徹底地擺脫了免疫機(jī)制和防御模式。他者性(Andersheit)和陌生性(Fremdheit)的消失標(biāo)志著這種轉(zhuǎn)變。他者性是免疫學(xué)的根本范疇。一切免疫反應(yīng)都是面對他者的反應(yīng)。現(xiàn)在,“差異”(Differenz)取代了他者,不再引起免疫反應(yīng)。后免疫學(xué)、后現(xiàn)代式差異不再導(dǎo)致疾病。在免疫學(xué)層面上,它們是等同的。過去,在陌生者(Fremdheit)的刺痛下,產(chǎn)生激烈的免疫反應(yīng),如今這些在差異性中消失殆盡。陌生者被弱化為一種消費(fèi)用語。陌生性讓位于異國情調(diào)。游客們在旅行中尋覓它的蹤跡。游客或顧客不再是免疫學(xué)式主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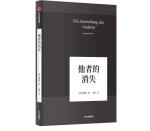
他者的消失:當(dāng)代社會、感知與交際
作者:[德] 韓炳哲 著 吳瓊 譯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tuán)·見識城邦
出版時間:2019-06
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的免疫理論也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假設(shè)之上。他認(rèn)為:“過去幾年中,任意哪一天的報紙,也許甚至在同一版面,從表面看來都報道了不同的事件。例如,對抗一種新型傳染病的爆發(fā),反對被指控侵犯人權(quán)的外國首腦的引渡申請,加固抵制非法移民的壁壘,以及清除最新電腦病毒的策略。這些現(xiàn)象之間有何共通之處?如果人們將它們置于各自所屬的領(lǐng)域——醫(yī)學(xué)、法學(xué)、政治學(xué)和電腦科技中單獨(dú)觀察,那么它們之間毫無關(guān)聯(lián)。然而,如果換一種詮釋范疇,情況也隨之發(fā)生變化。這種詮釋范疇自身的特殊性在于,它能夠橫向剖析各種獨(dú)立的話語,將它們匯聚至同一個意義視域(Sinnhorizont)之中。如同本書標(biāo)題所顯示,我將這一范疇稱為‘免疫’。……忽略其措辭的多樣性,上述的種種現(xiàn)象全部都指向同一種機(jī)制,即面對危險侵襲時的保護(hù)反應(yīng)。”埃斯波西托援引的案例中沒有一則表明,我們正身處一個免疫學(xué)時代。如今所謂的“移民者”不再是免疫學(xué)上的“他者”(Anderer),也不是具有真正危險性、引發(fā)恐懼的“陌生人”(Fremder)。移民或難民更多地被視為一種負(fù)擔(dān),而不是威脅。電腦病毒問題也不再導(dǎo)致嚴(yán)重的社會動蕩。埃斯波西托在他的免疫學(xué)分析中無一例外地援引了過去的事件,而非當(dāng)下的現(xiàn)狀,這種選擇絕非偶然。
免疫學(xué)范式和全球化進(jìn)程彼此不能相容。免疫反應(yīng)喚起了對他者的感知,這與消除界限的進(jìn)程相違背。按照免疫學(xué)原則組織的世界具有獨(dú)特的地貌。它由種種邊界、通道、門檻、圍欄、溝渠和城墻組成。它阻礙全球溝通和交流的進(jìn)程,一種普遍的混雜無序控制了當(dāng)下的一切生活領(lǐng)域,免疫學(xué)上的他者的缺失和普遍的混亂,二者互為條件。雜糅性(Hybridisierung)不僅主導(dǎo)著當(dāng)下的文化理論話語,同時也操控了現(xiàn)今的一切生活體驗,這與免疫原則恰恰相反。免疫學(xué)上的知覺過敏(Hyper?sthesie)不能容忍雜糅性。
免疫學(xué)的基本特征是否定的辯證法。免疫學(xué)上的他者是否定的,侵入自我個體并試圖否定它。如果自我不能夠反過來否定侵略者,它將在他者的否定下走向滅亡。通過這種否定之否定,完成了免疫學(xué)上自我持存(Selbstbehauptung des Eigenen)。自我抵御了否定性的他者,從而確立自身。預(yù)防式治療,即注射疫苗,也同樣遵循了否定的辯證法。一小部分他者被允許進(jìn)入主體,由此觸發(fā)免疫反應(yīng)。否定之否定,這種情況不導(dǎo)向死亡,由于免疫反應(yīng)并未與他者直接對峙。人們甘愿對自身施加少許暴力,為了避免更大的、致命的危險。他者的消失意味著,我們生活的時代缺乏否定性。21世紀(jì)的精神疾病也遵循一種辯證邏輯,但并非否定的辯證,而是肯定的辯證。它是一種由過量的肯定性導(dǎo)致的疾病狀態(tài)。
超文化:文化與全球化
作者: [德] 韓炳哲 著 關(guān)玉紅 譯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團(tuán)
出版時間: 2023-01
暴力不僅源于否定性,也源于肯定性;不僅來自他者或外來者,還來自同類。鮑德里亞明確指出了這種肯定性的暴力,他寫道:“誰依靠同類存活,也將由于同類而死。”鮑德里亞還論及“一切現(xiàn)存體制的肥胖癥”,包括信息、交流以及生產(chǎn)系統(tǒng)。目前尚不存在針對肥胖癥的免疫反應(yīng)。然而鮑德里亞卻從免疫學(xué)角度描述了同類的極權(quán)主義,這也正是其理論的弱點(diǎn),“這絕非偶然,人們現(xiàn)在如此頻繁地討論免疫、抗體、移植和排泄物。在一個匱乏的時代,人們專注于吸收和同化。而在過剩的時代,問題是如何排斥和拒絕。普遍的交流和信息過剩正在威脅全體人類的免疫機(jī)制。”在一個由同類控制的系統(tǒng)中,只能在一種比喻的層面上談?wù)撁庖叻磻?yīng)。
從嚴(yán)格意義上講,免疫反應(yīng)僅針對他者和外來者,同類之間不能產(chǎn)生抗體。在一個由同類控制的體系中,增強(qiáng)免疫反應(yīng)是毫無意義的。我們必須區(qū)分免疫式和非免疫式的排斥反應(yīng)。后者來自過量的同類、過剩的肯定性,否定性并未參與其中。它也不是一種排他反應(yīng),這種反應(yīng)需要免疫學(xué)上的內(nèi)部空間為前提。相反,免疫反應(yīng)則不取決于數(shù)量,它只針對他者的否定性。免疫學(xué)主體為了保護(hù)其內(nèi)部空間而抵抗他者,將其排除在外,無論他者的數(shù)量多么微不足道。
妥協(xié)社會:今日之痛
作者: [德] 韓炳哲 著 吳瓊 譯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團(tuán)
出版時間: 2023-01
由過度生產(chǎn)、超負(fù)荷勞作和過量信息導(dǎo)致的肯定性暴力不再是“病毒性的”。免疫反應(yīng)無法與之溝通。由過量肯定性引發(fā)的排斥反應(yīng)不等同于免疫反應(yīng),而是一種消化神經(jīng)上的功能異常和障礙。由于過量導(dǎo)致的疲乏、困倦和窒息感也并非免疫反應(yīng)。它們都是神經(jīng)暴力引發(fā)的現(xiàn)象,由于它們不是由免疫學(xué)的他者所致,因此是非病毒性的。鮑德里亞的暴力理論中充滿了論證上的偏差和混亂,因為這種理論試圖用免疫學(xué)方式描述肯定性或同類的暴力,盡管沒有他者參與其中。他寫道:“它是一種病毒性暴力,一種網(wǎng)絡(luò)的、虛擬的暴力。一種溫和卻具有毀滅性的、遺傳學(xué)的、交流式的暴力;一種對立雙方共識的暴力……這種暴力是病毒性的,因為它并不正面作戰(zhàn),而是通過傳染、連鎖反應(yīng)或消除一切免疫力來側(cè)面進(jìn)攻。和否定性的、歷史上的暴力不同,這種暴力通過過量的肯定性發(fā)揮作用,如同無止境地蔓延、生長和轉(zhuǎn)移的癌細(xì)胞。在虛擬世界和病毒傳播之間存在隱秘的關(guān)聯(lián)。”
按照鮑德里亞的敵對關(guān)系譜系學(xué)(Genealogie der Feindschaft),第一個階段的敵人以狼的形象出現(xiàn)。他是一個“外部的敵人,發(fā)起攻擊,人們通過修建防御工事和城墻來阻擋敵人”。在第二個階段,敵人呈現(xiàn)為老鼠的形態(tài)。敵人在地下暗中行動,人們通過衛(wèi)生措施將其清除。經(jīng)歷了第三個階段即甲蟲階段之后,敵人最終以病毒的形式出現(xiàn):“第四個階段是病毒,它事實(shí)上活動于第四維空間中。人們很難對抗病毒,因為它們位于系統(tǒng)的中心。”由此產(chǎn)生了一個“幽靈般的敵人,彌漫于整個空間,如同病毒一般四處滲透,侵入每一處權(quán)力的裂痕之中”。病毒性暴力從各自的獨(dú)特性出發(fā),作為沉睡細(xì)胞如恐怖分子一般潛伏在系統(tǒng)中,并試圖從內(nèi)部侵蝕整個系統(tǒng)。恐怖主義成為病毒性暴力的主要形式,在鮑德里亞看來,這也構(gòu)成了個體對全球化發(fā)起的暴動。
敵對關(guān)系即便采取病毒形式,也依然符合免疫學(xué)模式。危險的病毒入侵系統(tǒng),按照免疫機(jī)制的運(yùn)作方式,系統(tǒng)將病毒入侵者擊退。然而敵對關(guān)系的譜系不等同于暴力的譜系。肯定性的暴力不需要一種敵對關(guān)系作為前提。相反,它正產(chǎn)生于一個寬容、平和的社會。因此它比病毒性暴力更加隱蔽。它存在于一個缺乏否定性的同質(zhì)的空間內(nèi),沒有敵我、內(nèi)外、自我與他者的兩極對立。
透明社會
作者: [德] 韓炳哲 著 吳瓊 譯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團(tuán)
出版時間: 2019-10
世界向肯定性發(fā)展,由此產(chǎn)生了新的暴力形式。它們不來自免疫學(xué)式他者,而源于系統(tǒng)內(nèi)部。正是基于它的內(nèi)在性,免疫反應(yīng)對它失去效力。這種神經(jīng)暴力將導(dǎo)致精神上的梗阻,是一種內(nèi)在的恐怖。它完全有別于那種由免疫學(xué)的他者引起的恐慌。美杜莎是最極端形式的免疫學(xué)上的他者。她代表了一種極端的另類形式,以至于人們一旦正視她的顏面,便走向毀滅。神經(jīng)暴力則取消了一切免疫學(xué)表征,由于它不含有任何否定性。肯定性暴力不是剝離式(privativ),而是飽和式(saturativ);不是單一排他,而是兼收并蓄。因此,人們不能直觀地感受到這種暴力形式。
病毒性暴力并不適用于描述抑郁癥、注意力缺陷多動癥或疲勞綜合征等神經(jīng)癥狀,因為病毒性暴力依然遵循免疫學(xué)模式,區(qū)分內(nèi)外、敵我,并以一個對系統(tǒng)充滿敵意的單一的他者為前提條件。神經(jīng)暴力并不來自一個系統(tǒng)之外的否定性他者,而是源自系統(tǒng)內(nèi)部。無論是抑郁癥、注意力缺陷多動癥或疲勞綜合征都指向一種過度的肯定性。疲勞綜合征即自我在過度狂熱中燃盡了自身,源自過量的同類者。多動癥中的“過量”概念也不屬于免疫學(xué)范疇,它僅體現(xiàn)了肯定性的過度。
(原題為:《韓炳哲 | 精神暴力》,轉(zhuǎn)載自微信公眾號:實(shí)踐與文本)
韓炳哲(Byung-Chul Han),德國新生代思想家。1959年生于韓國首爾,80年代在韓國學(xué)習(xí)冶金學(xué),之后遠(yuǎn)渡重洋到德國學(xué)習(xí)哲學(xué)、德國文學(xué)和天主教神學(xué)。他先后在弗萊堡和慕尼黑學(xué)習(xí),并于1994年以研究海德格爾的論文獲得弗萊堡大學(xué)的博士學(xué)位。2000年任教于瑞士巴塞爾大學(xué),2010年任教于卡爾斯魯厄建筑與藝術(shù)大學(xué),2012年起任教于德國柏林藝術(shù)大學(xué)。他的主要研究領(lǐng)域是18—20世紀(jì)倫理學(xué)、社會哲學(xué)、現(xiàn)象學(xué)、文化哲學(xué)、美學(xué)、宗教、媒體理論等。作品被譯成十幾種語言。西班牙《國家報》(El País)譽(yù)其為“德國哲學(xué)界的一顆新星”。清新的文風(fēng),清晰的思想,深察洞識,切確而犀利的論述,這都讓韓炳哲對于數(shù)字信息時代人類精神狀況的分析批判,顯得尤其重要而富于啟發(fā)。
原標(biāo)題:《韓炳哲:無論是抑郁癥、注意力缺陷多動癥或疲勞綜合征,都指向一種過度的肯定性 | 純粹哲學(xué)》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jī)構(gòu)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fā)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jī)構(gòu)觀點(diǎn),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diǎn)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fā)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