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王欽評柄谷行人《探究(二)》|專名與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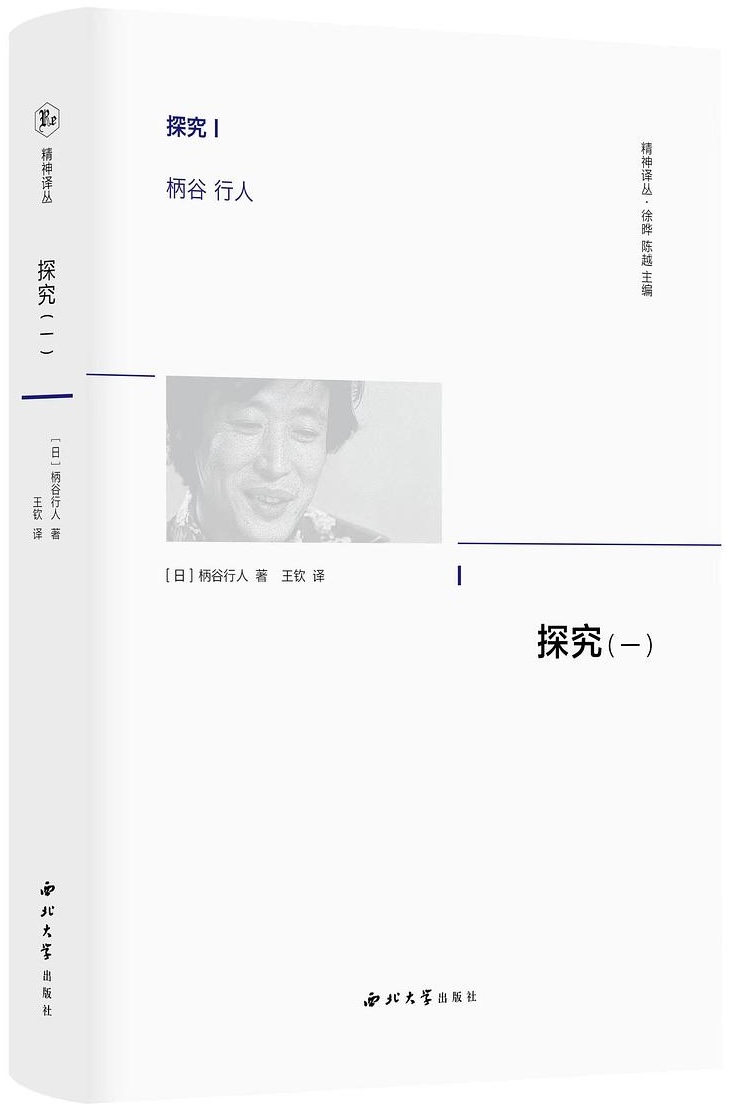
《探究(一)》,[日]柄谷行人著,王欽譯,西北大學(xué)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256頁,6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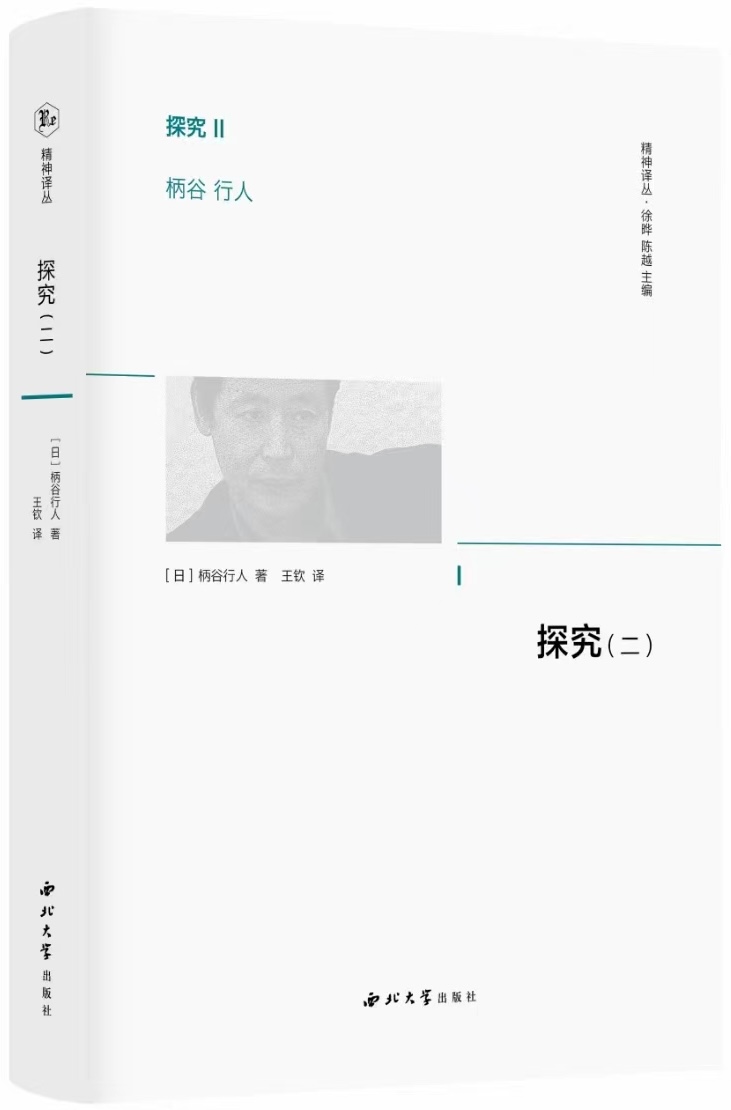
《探究(二)》,[日]柄谷行人著,王欽譯,西北大學(xué)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360頁,88.00元
柄谷行人對于“專名”問題的最為詳細(xì)討論,出現(xiàn)在1989年出版的《探究(二)》一書中;也可以說,《探究(一)》中作為關(guān)鍵概念和問題意識出現(xiàn)的“他者”,在《探究(二)》中通過與“專名”問題相聯(lián)系而得到了進(jìn)一步的闡述和發(fā)揮。因此,簡要地考察一下柄谷對于“專名”問題的論述,我們可以更好地揭示在柄谷思想中貫穿始終的“外部”“意識”等議題,如何在他經(jīng)歷了思想“轉(zhuǎn)回”而撰寫的《探究》中得到發(fā)展,并進(jìn)而與其后以“跨越性批判”為題出版的“探究(三)”的工作形成緊密的關(guān)聯(lián)。
在1991年的一篇題為“個(gè)體的地位”的文章中,柄谷就“專名”作為哲學(xué)和語言學(xué)問題寫道:“如索緒爾以后的語言學(xué)家所說,語言(langue)和指涉對象或意義無關(guān),它是差異性的能指的關(guān)系體系。然而,由于專名是固定指涉,它就偏離了這種關(guān)系體系。因此,語言學(xué)家在考察語言的時(shí)候就排除了專名,認(rèn)為專名正是將語言和指涉對象結(jié)合在一起的謬論的源泉。這是一種與認(rèn)為可以將專名還原為確定謂述的思考相平行的論述。”(柄谷行人『ヒューモアとしての唯物論』,講談社學(xué)術(shù)文庫,1999年,23頁)在這篇文章里,柄谷沒有繼續(xù)闡明這兩種“平行論述”之間的關(guān)系,但他所提示的這條由瑞士語言學(xué)家索緒爾所開啟的語言學(xué)“內(nèi)在研究”的進(jìn)路,卻和他“前期”的思考緊密相關(guān)——在這個(gè)意義上,提出這種“平行論述”卻對之存而不論,或許是一個(gè)關(guān)鍵提示:柄谷在討論“專名”的時(shí)候,已經(jīng)放棄了他此前的論述和思考方式。或者,反過來說,如果仍然陷于此前的思考框架,那么“專名”問題的思想啟示就無法得到闡明,故而必須進(jìn)行思想上的“轉(zhuǎn)向”。此話怎講?
讓我們先簡略地回顧一下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xué)教程》中對于語言學(xué)研究的對象和性質(zhì)做出的規(guī)定。在討論語言的一般性質(zhì)時(shí),索緒爾開宗明義地將外在指涉(即實(shí)在對象)排除出語言學(xué)討論的范圍:“語言符號連結(jié)的不是事物和名稱,而是概念和音響形象。后者不是物質(zhì)的聲音,純粹物理的東西,而是這聲音的心理印跡,我們的感覺給我們證明的聲音表象。”([瑞士]費(fèi)爾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xué)教程》,高名凱譯,商務(wù)印書館,2004年,101頁)于是,在索緒爾的論述中,構(gòu)成符號的音響形象(能指)和概念(所指)的兩個(gè)層次,都是在一個(gè)語言系統(tǒng)內(nèi)部運(yùn)作并通過差異化而產(chǎn)生意義(價(jià)值),整個(gè)過程都和傳統(tǒng)意義上的“語言與指涉”的關(guān)系截然不同。對于上述差異關(guān)系,索緒爾解釋道:
我們在這些例子里所看到的,都不是預(yù)先規(guī)定了的觀念,而是由系統(tǒng)發(fā)出的價(jià)值。我們說價(jià)值與概念相當(dāng),言外之意是指后者純粹是表示差別的,它們不是積極地由它們的內(nèi)容,而是消極地由它們跟系統(tǒng)中其他要素的關(guān)系確定的。它們的最確切的特征是:它們不是別的東西。(同前,163頁)

索緒爾
也就是說,在同一個(gè)系統(tǒng)中,能指通過與其他能指的差異性關(guān)系、所指通過與其他所指的差異性關(guān)系確定自身的意義;同樣,在索緒爾的另一段話中,符號的一切意義都被還原為差異性:
如果價(jià)值的概念部分只是由它與語言中其他要素的關(guān)系和差別構(gòu)成,那么對它的物質(zhì)部分同樣也可以這樣說。在詞里,重要的不是聲音本身,而是使這個(gè)詞區(qū)別于其他一切詞的聲音上的差別,因?yàn)閹в幸饬x的正是這些差別。(中略)起作用的只是符號的差別。(同前,164頁)
通過以上述方式規(guī)定語言符號的兩個(gè)層面,索緒爾否認(rèn)了所有試圖在語言和實(shí)際指涉對象之間確立因果或?qū)Φ汝P(guān)系的嘗試。同樣,作為音響形象的能指和作為概念表象的所指之間的結(jié)合的偶然性,截然不同于,也不可還原為所謂語言符號和實(shí)際指涉之間對應(yīng)的偶然性。“專名”所預(yù)設(shè)的語言符號與實(shí)際指涉之間貌似天然的聯(lián)系,自然也就無法在這樣一種差異性符號系統(tǒng)中找到一席之地。那么,柄谷如何理解索緒爾的這種論述?
需要提請注意的是,柄谷在不止一個(gè)場合討論過索緒爾,而每次討論的側(cè)重點(diǎn)乃至結(jié)論也未必一致(在這一點(diǎn)上,尤其能顯示柄谷的思考“轉(zhuǎn)向”的無疑是他寫于1992年的《書寫與民族主義》一文,在這篇與德里達(dá)的索緒爾批判展開對話的文章中,柄谷就索緒爾的“內(nèi)在語言學(xué)”進(jìn)路寫道:“必須指出,索緒爾堅(jiān)持‘內(nèi)在語言學(xué)’,不是因?yàn)闊o視‘外在’,而是為了批判將‘外在’事物的產(chǎn)物予以內(nèi)在化的語言學(xué)。他通過‘內(nèi)在語言學(xué)’的主張,反而將‘外在’事物的外在性揭示出來了。換言之,索緒爾始終把語言學(xué)的對象局限在聲音語言,不是出于聲音中心主義,反而是為了暴露歷史語言學(xué)的聲音中心主義的欺騙性。”參見柄谷行人『ヒューモアとしての唯物論』,講談社學(xué)術(shù)文庫,1999年,72頁);在此,我們可以選擇以1980年代初期撰寫的《內(nèi)省與溯行》中的討論為例——哪怕僅僅是因?yàn)檫@部被批評家淺田彰稱作“驚人的失敗的記錄”的著作標(biāo)志著柄谷的“前期”理論思考的頂點(diǎn)。針對索緒爾的差異性體系,柄谷在收錄于《內(nèi)省與溯行》中的主要論文《語言·數(shù)·貨幣》(1983)中寫道:
語言從來就是關(guān)于語言的語言。也就是說,語言不單單是差異體系(形式體系·關(guān)系體系),而是自我談及·自我關(guān)系性的,換言之,語言是這樣一種差異體系:它對自身而言是差異性的。在自我談及的形式體系或自我差異性的差異體系中,不存在根據(jù),不存在中心。或者,它是尼采所謂的多中心(多主觀),索緒爾所謂的混沌和過剩。語言(形式體系)存在于自我談及的禁止之處。(柄谷行人『內(nèi)省と遡行』,講談社文蕓文庫,2018年,171-72頁)
這段對于索緒爾的創(chuàng)造性重寫和批判的要點(diǎn)在于:柄谷強(qiáng)調(diào),索緒爾的差異體系之所以能夠作為一個(gè)“封閉”的體系而成立,端賴于一種回溯性的視角,即從已經(jīng)產(chǎn)生意義的差異關(guān)系出發(fā)來想象性地重構(gòu)意義產(chǎn)生的過程,仿佛這個(gè)符號系統(tǒng)從一開始就是封閉的、給定的。換句話說,當(dāng)我們依從索緒爾的上述討論而將語言學(xué)研究限定在某個(gè)“語言系統(tǒng)”內(nèi)部,進(jìn)而在能指和所指的層面談?wù)摫舜瞬町惖臅r(shí)候,“差異”關(guān)系實(shí)際上已經(jīng)被還原為能夠生產(chǎn)意義的“對立”關(guān)系(比如“cat”和“hat”“cut”等等的對立)。柄谷用一種非常具有德里達(dá)色彩的口吻告訴我們,在這樣一種有關(guān)“差異”的論述中,恰恰是純粹的差異、自我與自我的差異、無法通往意義的生成和確定的差異,被事先排除在外——依靠一種柄谷所謂“究極的所指”的縫合,所有差異性關(guān)系都得以發(fā)生在一個(gè)封閉的系統(tǒng)之中:
究極的所指封閉了無限后退的連鎖,以此來完成符號系統(tǒng)。反過來說,無論是哪個(gè)符號系統(tǒng),只要是系統(tǒng),暗中就會(huì)以這種究極的所指(超越者)為前提。如前所述,語言學(xué)·符號學(xué)只有在現(xiàn)象學(xué)式的還原那里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說,符號只有在對意識來說某物(聲音也好事物也好)有意義的情況下才是符號;而只要我們從這里出發(fā),我們所發(fā)現(xiàn)的就不可避免的是封閉了的系統(tǒng)(語言)。即便主張能指與所指之結(jié)合的任意性,或兩者的偏差的可能性,根本而言,能指與所指的二分法本身也只有通過這種體系性(使系統(tǒng)成為系統(tǒng)的東西)才能成立。(同前,218頁)
所謂“究極的所指”,就是本身并不在能指和所指的差異性系統(tǒng)中出場,卻保證了系統(tǒng)的封閉性和意義生成之規(guī)則的“不在場”的所指。在這里,就系統(tǒng)之為系統(tǒng)而言,這種“究極的所指”是在結(jié)構(gòu)上被預(yù)設(shè)的前提——換句話說,重要的問題不是如何再現(xiàn)這種所指(它與其說是不可能被再現(xiàn)的,不如說是一個(gè)必要的“缺席”),甚至不是這種所指是否真的“存在”,而是這種在結(jié)構(gòu)上作為系統(tǒng)成立之可能性條件的、占據(jù)“超越者”位置的“符號”,在系統(tǒng)運(yùn)作起來之后便被遮蔽了,仿佛各個(gè)符號從一開始就僅僅是在一個(gè)給定的、差異性的穩(wěn)定系統(tǒng)中形成彼此關(guān)系并生產(chǎn)意義。柄谷將這種“究極的所指”稱作“符號0”:
符號0……是對缺席的消除。但是,由符號0消除的是自我差異性(自我談及性)。這種缺席的消除,恰恰就是對根據(jù)的缺席——因而“不均衡”才是常態(tài)——的消除。(同前,219頁)
盡管柄谷在這里似乎是從積極的角度描繪“符號0”的作用,但我們需要時(shí)刻記住的是,柄谷討論的并不是一種時(shí)序性的發(fā)展或生成,仿佛的的確確先有一個(gè)超越性的“符號0”(無論它是什么),然后再通過它的消除(或自我消除)產(chǎn)生封閉的差異性系統(tǒng),就如《圣經(jīng)》里上帝無中生有的創(chuàng)世過程那樣。事實(shí)上,“符號0”僅僅是將貌似封閉的差異性系統(tǒng)的差異化過程推到極端所產(chǎn)生的結(jié)果,是我們追究系統(tǒng)之成立的可能性條件的后果。正如“早期”柄谷經(jīng)常借用哥德爾定律表明的那樣,這里的關(guān)鍵在于,任何形式系統(tǒng)都無法在自身內(nèi)部給出自身之自洽性的完整說明。但正因如此,柄谷在《內(nèi)省與溯行》等著作中試圖做的工作,就是嚴(yán)格把自己限定在系統(tǒng)內(nèi)部,通過不斷加劇差異化來尋求“向外”的突破口——“符號0”便是他找到的、似乎可以通往“外部”的關(guān)鍵所在。
因此,經(jīng)歷了思想的“轉(zhuǎn)回”之后,在1985年為《內(nèi)省與溯行》所寫的“后記”中,柄谷如此回顧自己在過去數(shù)年里嘗試的理論工作:
我在《內(nèi)省與溯行》中第一次從正面開始思考語言,這時(shí)候我封閉在所謂“內(nèi)部”。或不如說,我所發(fā)現(xiàn)的是,無論人們怎么想,他們都已經(jīng)被困在“內(nèi)部”了。要想從單義的、封閉的結(jié)構(gòu),也即從“內(nèi)部”邁向尼采所謂“巨大的多樣性”的“外部”、作為事實(shí)性的外部——換言之,作為缺席的“外部”——并不是容易的事。我當(dāng)時(shí)認(rèn)為,這只能通過將內(nèi)部或形式體系進(jìn)一步徹底化,以此使它自我破壞,才有可能做到。可以說,我是積極地將自己局限在“內(nèi)部”的。(同前,322頁)
但是,即便發(fā)現(xiàn)了“符號0”的悖論性作用——它既是系統(tǒng)成立的前提條件,也是系統(tǒng)無法再現(xiàn)卻始終遮蔽的“缺席”——柄谷似乎也無法跳脫出自己這種與“內(nèi)部”的搏斗,正如批判始終無法擺脫它的批判對象。在這個(gè)意義上,柄谷揭示的“外部”似乎反倒成了“內(nèi)部”所產(chǎn)生的另一個(gè)效果,盡管是一個(gè)顛覆性或解構(gòu)性(在這個(gè)詞的嚴(yán)格意義上)的效果。
于是,根據(jù)柄谷自己的說法,經(jīng)歷了思想“轉(zhuǎn)向”后撰寫的系列隨筆《探究》,便成為對此前工作的“根本批評”(同前,323頁)。這也就提醒我們,對于《探究》的理解,需要在柄谷迄今為止的問題意識以及對此的自我反省和批判的延長線上進(jìn)行。反之,如果僅僅在知識的意義上執(zhí)著于柄谷對于具體思想家的具體解讀,點(diǎn)評哪些部分恰當(dāng)哪些部分不恰當(dāng),不僅有見木不見林之虞,甚至完全無法把握柄谷的意圖。而如果將《探究》與《內(nèi)省與溯行》放在一起,很容易發(fā)現(xiàn)柄谷自始至終試圖回答的問題是:如何與“外部”產(chǎn)生交流。具體來說,《探究(二)》中涉及的“專名”問題,提示我們柄谷對于“外部”進(jìn)行思考的新方向。
***
在《探究(二)》一書中,柄谷對于“專名”問題的探討,是與對于所謂“獨(dú)特性”的探討聯(lián)系在一起的。從一開始,柄谷就區(qū)分了“獨(dú)特性”與“特殊性”:如果后者與“一般性”相聯(lián)系并呈現(xiàn)為某個(gè)一般性的概念范疇下的個(gè)例,那么“獨(dú)特性”就跳脫出了一般概念范疇的規(guī)定。柄谷舉例說明:
在此,我把“這個(gè)我”或“這條狗”的“這個(gè)”性(this-ness)稱作單獨(dú)性(singularity),并把它區(qū)別于特殊性(particularity)。如后文所述,單獨(dú)性并不是只有一個(gè)。特殊性是從一般性出發(fā)得到的個(gè)體性;與之相對,單獨(dú)性則是決不屬于一般性的個(gè)體性。(柄谷行人『探究II』,講談社學(xué)術(shù)文庫,1994年,11頁)
有意思的是,柄谷的入手點(diǎn)——即所謂“這個(gè)”——正是羅素所認(rèn)定的、唯一真正的邏輯“專名”。不過,在羅素那里,“這個(gè)”“那個(gè)”被認(rèn)定為最基本的簡單事實(shí)或邏輯原子,是沿著他的“摹狀詞理論”對名稱進(jìn)行分析和化約之后得出的結(jié)果——如不少論者所說,將這兩個(gè)詞視作真正的“專名”不啻“一場邏輯災(zāi)難”(斯特勞森語)。另一方面,柄谷指出,“獨(dú)特性”問題的悖論在于:事實(shí)上,我們無法通過(例如)“這只貓”這樣的表述來表達(dá)它所指涉的貓的獨(dú)特性,以至于“這只貓”無法抵達(dá)所指涉的貓的“這個(gè)”性,因?yàn)橐坏斑@只貓”通過特指而被從一般意義上的“貓”那里選定出來,它就在同一個(gè)過程中預(yù)設(shè)(并且回到)了一般意義上對于“貓”的概念規(guī)定上。在這個(gè)意義上,當(dāng)我們試圖用“這只貓”來表現(xiàn)眼前這只貓的獨(dú)特存在的時(shí)候,我們就必須重新理解或界定“這個(gè)”,否則這個(gè)表述反而會(huì)使我們希望表現(xiàn)的“獨(dú)特性”淹沒在“特殊性”之中。對此,柄谷寫道:
“這個(gè)我”或“這條狗”里的“這個(gè)”,不同于指示某物的“這個(gè)”。指示某物的時(shí)候,“這個(gè)”將“我”或“狗”等一般存在給特殊化了(做了限定)。在這個(gè)意義上,堅(jiān)持“這個(gè)我”,便是主張我如何與他者不同,也即我如何特殊。不過,這么做的前提恰恰是把他者也當(dāng)作“我”,即一般意義上的“我”。(同前,21頁)
這段話的最后一句頗為關(guān)鍵:正如“這只貓”的表述無法呈現(xiàn)眼前這只貓的“獨(dú)特性”,在“這個(gè)我”式的唯我論的思考方式中,“自我”與“他者”的差異實(shí)際上從一開始就被回收到自我同一性的視野之中,以至于“他者”一開始就遭到了排除。換言之,如何揭示“獨(dú)特性”的問題,同時(shí)也是如何與“他者”相遇的問題。那么,對于柄谷來說,如何從“這只貓”這一表述通往事物的獨(dú)特性呢?
的確,“這只貓”中的“這”從邏輯上無法提示貓的“獨(dú)特性”,而只能把所指涉的貓還原為特殊性的一個(gè)事例。但這一邏輯事實(shí)無法抹去的一個(gè)更為簡單的事實(shí)是:我們恰恰試圖通過“這只貓”這個(gè)表述來(不可能地)表達(dá)“獨(dú)特性”,不然我們究竟為什么要使用“這只貓”的表述就是不可理解的。請注意:這并不是把問題還原為經(jīng)驗(yàn)主義或心理學(xué)問題,仿佛重要的只是言說者自己的想法或意圖;恰恰相反,我們在此談?wù)摰娜匀皇且粋€(gè)形式性的問題,也即“這只貓”的“這”恰恰提示了它所指涉的貓和其他貓的差異,盡管這個(gè)表述無法積極地再現(xiàn)這種涉及“獨(dú)特性”的差異。一旦試圖將這種差異命題化,我們就落入了“特殊性/一般性”的窠臼,但這一困境并不會(huì)使差異消失。正是在這里,“專名”問題與“獨(dú)特性”問題的聯(lián)系呈現(xiàn)了出來:
單獨(dú)性不屬于一般性。但是,單獨(dú)性不是孤立而游離在外的東西。單獨(dú)性反而以其他事物為根本前提,并在與其他事物的關(guān)系中得到揭示。但單獨(dú)性不是那種不能用語言表達(dá)的深邃之物。前面已經(jīng)提到,[單獨(dú)性]出現(xiàn)于專名之中。(同前,22頁)
在柄谷看來,之所以“獨(dú)特性”出現(xiàn)在“專名”那里,是因?yàn)椤皩C辈⒎莾H僅是對事物的命名,而更涉及“如何看待‘個(gè)體’”的問題(同前,29頁)。換句話說,“專名”之無法還原為一連串謂述,其原因和“這只貓”無法表現(xiàn)所指涉的貓的“獨(dú)特性”如出一轍:例如,通過將“富士山”還原為一系列描述性的特征(假如真的可以做到窮盡性描述的話),我們也恰恰在此過程中丟失了“富士山”這個(gè)專名中包含的固有性。或者,用一個(gè)更顯豁的例子加以說明的話,這里的問題類似于“誰”(whoness)和“什么”(whatness)的區(qū)別:當(dāng)我們問道“誰是柄谷行人”的時(shí)候,回答可以是諸如“當(dāng)代日本左翼知識人”“著名思想家”“《日本現(xiàn)代文學(xué)的起源》的作者”等等;但是,這一系列特征性描述所回答的問題都只是“什么”層面的問題,而無法觸及“柄谷行人”這個(gè)專名所指涉的是“誰”。
反過來說,如果“專名”提示的固有性或“獨(dú)特性”無法在所指涉事物的描述性特征那里得到揭示,那么“專名”在語言上的形式標(biāo)記也決不是看上去那么明顯的事情;毋寧說,與它希望揭示的“獨(dú)特性”一道,專名的形式標(biāo)記消失在了(例如)“這只貓”的表述所包含的、無法在形式上做出區(qū)分的兩種不同方向——(1)將所指涉的貓還原為“特殊性”的一個(gè)特殊事例以及(2)提示所指涉的貓與其他貓的純粹差異——之中。在語言的形式標(biāo)記層面,沒有什么能夠阻止我將自己的貓命名為“狗”甚或“貓”,盡管一般認(rèn)為“貓”“狗”是普通名詞而非專名。在這個(gè)意義上,“專名”對于事物的“獨(dú)特性”的提示,前提就是之前提到的、“專名”所標(biāo)記的差異性——沒有什么明確的形式標(biāo)記可以區(qū)分作為“專名”的“貓”與作為普通名詞的“貓”,這一事實(shí)并不意味著兩者都可以還原為一連串謂述,而恰恰顯示了“專名”與言說者的密切關(guān)系。在同一時(shí)期所做的一次題為“關(guān)于專名”的講演中,柄谷對此說道:
通過專名指示的“獨(dú)特性”,不是“僅有一個(gè)”意義上的“獨(dú)特性”。就算只有一個(gè),我們也未必會(huì)用專名來稱呼。某樣?xùn)|西的“獨(dú)特性”,只有在我們用專名來稱呼它的時(shí)候才出現(xiàn)。并且需要注意的是,某個(gè)語詞能夠成為專名,并不是由于我們以它來指示個(gè)體的個(gè)體性,而是由于我們用它來指示“獨(dú)特性”。(柄谷行人『言語と悲劇』,講談社學(xué)術(shù)文庫,1993年,393頁)
重復(fù)一遍:當(dāng)柄谷強(qiáng)調(diào)某個(gè)語詞是否是專名取決于我們是否用它來提示“獨(dú)特性”的時(shí)候,他并不是把“專名”對于事物的指涉關(guān)系徹底還原為言說者的意圖或主觀性;毋寧說,這里的“我們”不能被等同于“我”,因?yàn)樗婕翱死锲湛藢τ诹_素的批判中提出的共同體。延續(xù)上面的例子,只有在他人知道我把自己的貓叫做“狗”的時(shí)候,才能理解當(dāng)我使用“狗”這個(gè)語詞的時(shí)候,我有可能是在用這個(gè)“專名”指涉自己的貓,而不僅僅在說一般意義上的狗。在這里,并不是我的主觀意愿將“狗”這個(gè)語詞從一般性的使用中抽離出來,讓它變成一個(gè)獨(dú)特的“專名”;相反,“狗”(或“約翰”“小花”等等)之所以能夠成為我對自己的貓的命名,離不開與“專名”及其指涉無關(guān)的一個(gè)“外部”背景,即“命名儀式”所處的共同體之中的交流。甚至在“這只貓”的表述這里,情形也同樣如此。讓我們仔細(xì)看一下柄谷的一段話:
然而,羅素的“這個(gè)”就僅僅是“這個(gè)”,不帶有“這個(gè)”以外的其他事物的可能性。但與此相對,[“這個(gè)”指的是]“不是其他而就是這個(gè)”(這個(gè)這個(gè))。當(dāng)我說“不是其他”的時(shí)候,已經(jīng)將“其他(或多個(gè))”作為前提了。專名與這種“不是其他而就是這個(gè)”有關(guān)。專名所指示的“這個(gè)”,是在“其他=多個(gè)”的可能性中被揭示的。換句話說,克里普克作為出發(fā)點(diǎn)的“現(xiàn)實(shí)世界”,不是單純的經(jīng)驗(yàn)世界,而已經(jīng)是在可能世界之中被揭示的世界。
他并不是在下述意義上思考“可能世界”的,即唯有經(jīng)驗(yàn)世界是現(xiàn)實(shí)的,其他都是想象的。相反,恰恰在諸多可能世界或諸多可能性中,才能思考現(xiàn)實(shí)世界或現(xiàn)實(shí)性。從現(xiàn)實(shí)世界出發(fā)思考“可能世界”,事實(shí)上相當(dāng)于說,已經(jīng)從可能世界出發(fā)來思考“現(xiàn)實(shí)世界”了。將專名置換為限定摹狀詞,會(huì)在可能世界中產(chǎn)生不合邏輯的情況——這就說明:專名所涉及的現(xiàn)實(shí)性,已經(jīng)是包含了可能世界的現(xiàn)實(shí)性。(柄谷行人『探究II』,59頁)
在這段話中,柄谷對克里普克的羅素批判進(jìn)行了頗為獨(dú)特的闡述。我們可以將他的解釋整理如下:克里普克所謂的“可能世界”,并不是如萊布尼茨筆下的情形那樣,呈現(xiàn)為抽象的、與現(xiàn)實(shí)世界無關(guān)的設(shè)想;相反,它是為了說明現(xiàn)實(shí)世界的“這個(gè)”性——或偶然性——而被提出來的思想實(shí)驗(yàn)。從“可能世界”出發(fā)來思考“現(xiàn)實(shí)世界”,意味著將現(xiàn)實(shí)中看起來理所當(dāng)然的、不可改變的事物特征還原為偶然的結(jié)果:某物在如其所是的同時(shí),也提示著它不必如此的可能性。這里的關(guān)鍵在于,由此一來,如果“專名”既不能被還原為事物的描述性特征,也不能被還原為言說者的意圖,那么“專名”之所以為“專名”,就完全是一個(gè)關(guān)乎交流之形式性的問題:正是在與他人的實(shí)際交流過程中,“專名”被確定下來。當(dāng)我說出“這只貓”的時(shí)候,這個(gè)表述所指涉的貓的“獨(dú)特性”恰恰是在我用這個(gè)表述來與人交流(哪怕是未知的讀者)的情況下得到提示的。正因如此,在不同的“可能世界”中,我完全可以設(shè)想這只貓?jiān)谔卣魃系牟煌兓鵁o需確定哪些性質(zhì)是本質(zhì)性的,而哪些不是。只要交流可以實(shí)現(xiàn),哪怕在“可能世界”中我用“這只貓”來指涉一種莫可名狀之物,“這只貓”在“專名”意義上的指涉作用仍然不會(huì)發(fā)生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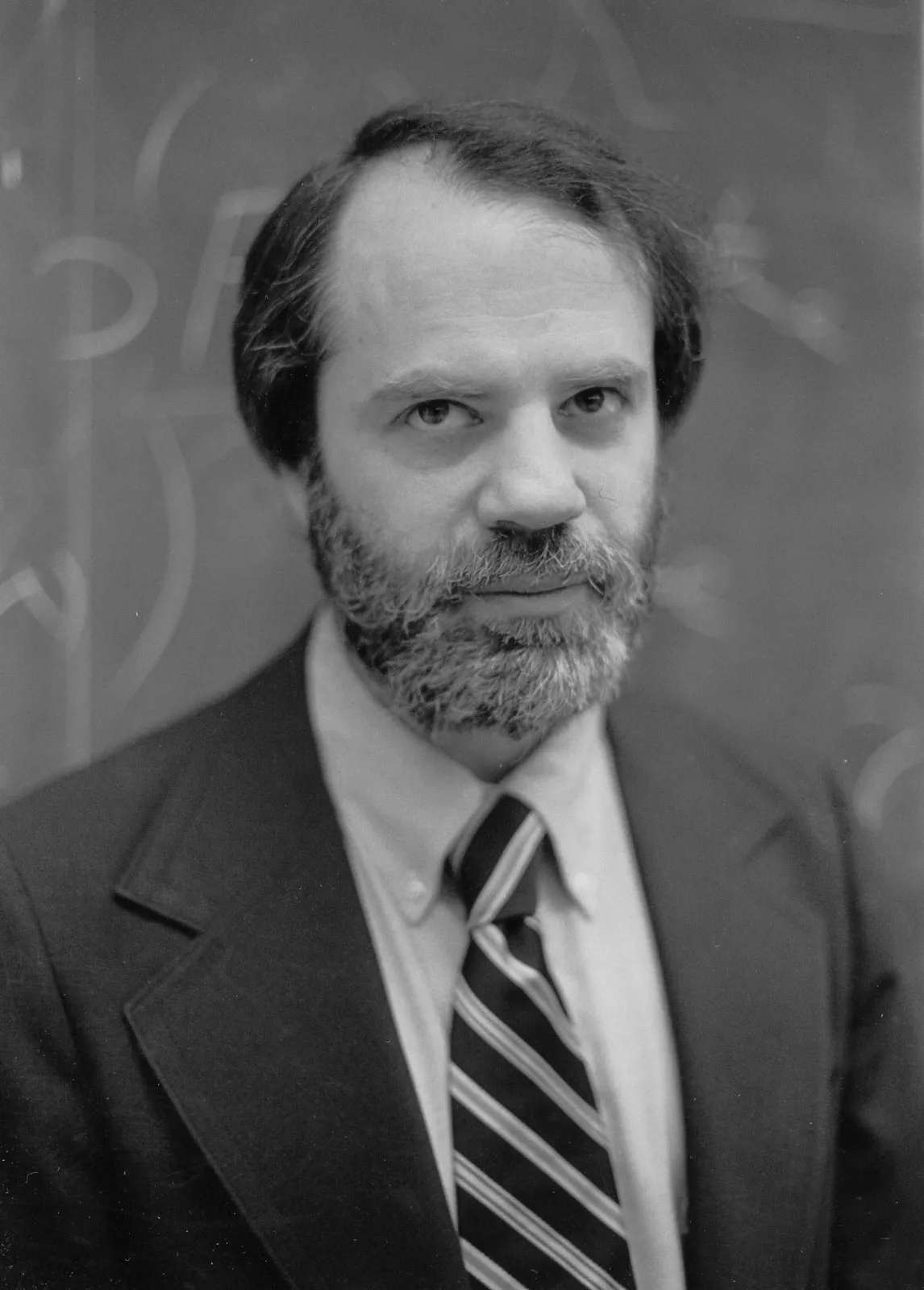
克里普克
同樣,擁有相同名稱的事物(例如同名同姓的人)盡管很多,但我們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使用某個(gè)“專名”的時(shí)候,不需要特意說明我們以此來意味什么;事實(shí)上,當(dāng)我們在與他人的交流中使用某個(gè)常見的名稱時(shí),根本不需要做出任何說明,他人也不會(huì)要求確認(rèn)這個(gè)名稱的指涉。(在特殊的場合下,也許對方的確會(huì)出于驚訝或疑惑而提問說:“你說的是那個(gè)柄谷行人嗎?”但與其說這個(gè)問題是在向言說者請求確認(rèn)“柄谷行人”這個(gè)“專名”指涉的對象,不如說是以雙方共同認(rèn)知的對象為前提、以這個(gè)“專名”所指涉之對象的非含混性為前提,表達(dá)自己的驚訝或疑惑態(tài)度。)
那么,如何在與他人的交流中就“專名”達(dá)成合意?我們是否要像克里普克表明的那樣,將“專名”的穩(wěn)定和傳遞追溯到某個(gè)初次的、起源性的“命名儀式”那里,追溯到某個(gè)恰當(dāng)意義上的“述行句”那里,以至于所有“專名”都必然隱含一句“我在此將此命名為……”?當(dāng)然不是。事實(shí)上,關(guān)于“專名”之傳遞的上述想象,恰恰是“專名”作為“專名”成立之后回溯性地追認(rèn)的一條線索,它是“專名”發(fā)揮作用的效果而非原因。因此,克里普克那里假定的、我們仿佛在其中習(xí)得“專名”的用法和意義的那個(gè)共同體(系統(tǒng)),本身也是交流達(dá)成合意之后產(chǎn)生的效果之一。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柄谷論述道:
名稱傳達(dá)者和接受者的關(guān)系(遭遇)是外部的、偶然的。也就是說,這是與“其他事物”之間的關(guān)系。(同前,62頁)
簡言之,“命名”的偶然性,不過是語言交流的偶然性的一個(gè)環(huán)節(jié);反過來說,“專名”所揭示的內(nèi)容,正是我們所有的語言交流都包含的內(nèi)容。在《探究(一)》中,柄谷通過對于維特根斯坦筆下著名的“語言游戲”的討論指出,交流并不發(fā)生在既定的規(guī)則基礎(chǔ)上;相反,交流的規(guī)則只是事后才被確立,并被回溯性地規(guī)定為仿佛一開始就存在于那里。而在每個(gè)實(shí)際交流的現(xiàn)場,沒有什么能夠保證交流雙方達(dá)成合意。柄谷從而借用克爾凱郭爾的說法,將交流合意的實(shí)現(xiàn)稱作“致死一躍”。同樣,在實(shí)際的交流過程中,與其說我們在對其“起源”習(xí)焉不察的情況下使用著“專名”,不如說對于“專名”的“起源”的想象本身,也是“專名”發(fā)揮作用的效果之一。“專名之所以可以固定指示,反倒是因?yàn)樗鼛в袩o法在共同規(guī)范的意義上被內(nèi)在化的那種關(guān)系的外在性。”(同前,63頁)
在這個(gè)意義上,在放棄了將自己局限于系統(tǒng)內(nèi)部、試圖以內(nèi)部的自我瓦解來發(fā)現(xiàn)“外部”的思考進(jìn)路之后,柄谷選擇以“專名”問題為線索而討論“他者”“外在”等主題,并不是因?yàn)椤皩C碧烊坏刂赶蛘Z言的“外部”(否則就退回到傳統(tǒng)認(rèn)知上的語言符號和現(xiàn)實(shí)指涉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上去了),而是因?yàn)椤皩C敝疄椤皩C彼耐獠康慕涣骰蚪涣鞯耐庠谛裕?/p>
專名看上去保存了和語言體系外部的聯(lián)系,這不是因?yàn)閷CС滞獠繉ο螅且驗(yàn)樗姓Z言體系之內(nèi)無法內(nèi)在化的某種外在性。(柄谷行人『ヒューモアとしての唯物論』,24頁)
如果說在索緒爾那里,能指和所指在各自的差異性系統(tǒng)中通過消極性的差異而產(chǎn)生積極意義的過程,需要一個(gè)“符號0”的“缺席性在場”,需要一個(gè)本身無法被表征的超越者來確保系統(tǒng)的封閉性,確保差異向意義的生成,那么柄谷提醒我們:“專名”在我們?nèi)粘=涣鬟^程中的使用和指涉,并不需要經(jīng)過這樣一種超越者的中介,或者不如說,超越或外在于“專名”及其現(xiàn)實(shí)指涉的,正是對“專名”而言不可或缺的、言說者與他者的交流本身。在此,“前期”柄谷苦苦思索的問題通過一次看似簡單的顛倒得到了消除:我們不需要通過徹底的“內(nèi)在化”而尋求“外部”,因?yàn)樗^的“外部”無時(shí)無刻不構(gòu)成我們交流、理解、認(rèn)知的前提。歸根結(jié)底,“前期”柄谷所批判的、封閉的符號系統(tǒng)所遮蔽的,并不是只有通過徹底的內(nèi)部差異化才能窺見的“符號0”,而是從一開始就存在,卻無法被系統(tǒng)內(nèi)在化的交流的外在性和偶然性。
柄谷的這一發(fā)現(xiàn)意味著什么?如果僅僅是要擁抱或贊美偶然性、強(qiáng)調(diào)事情本來可以是另一個(gè)樣子,那么就如有的批評者所說,批評家小林秀雄早在1930年代就已經(jīng)觸及了這個(gè)問題,而且更加“深刻”地指出了我們作為“偶然如此”的存在者的有限性和悲劇性。通過強(qiáng)調(diào)偶然性和差異性的不可還原性,柄谷究竟想要說明什么?為了回答這個(gè)問題,讓我們重新回到前面提到的“專名”與言說者的關(guān)系上:如前所述,“專名”不僅提示了所指涉的對象的“獨(dú)特性”,而且提示了言說者對于該對象的態(tài)度或位置(盡管不是言說者的意圖)。不僅在我說出(例如)“柄谷行人”或“這只貓”的時(shí)候如此,當(dāng)我使用“我”這個(gè)語詞的時(shí)候同樣如此。這里發(fā)生的情況與其說是“我”作為言說者經(jīng)由“我”這個(gè)語詞而被收編到一個(gè)差異性的符號系統(tǒng)內(nèi)部,從而作為言說主體的“我”僅僅是語言的效果——在結(jié)構(gòu)主義和后結(jié)構(gòu)主義的背景下,這是一個(gè)非常常見的理解——不如說恰恰相反:當(dāng)我使用“我”這個(gè)語詞的時(shí)候,我希望借此提示的、與他者之間不對稱的差異性(作為言說主體的“我”并不是在通過與其他“我”的對比中得到“我”的固有的差異性,而正是通過說出“我”這個(gè)語詞來顯示形式性的、不可還原的差異性),無需經(jīng)過某種抽象而一般的、關(guān)于“自我”或“主體”的先驗(yàn)性規(guī)定才能得到揭示;通過言說“我”,作為言說主體的“我”已經(jīng)包含了無法被語言系統(tǒng)內(nèi)在化的、差異性的“外部”。重復(fù)一遍:這里說的不單是作為經(jīng)驗(yàn)事實(shí)的外部存在,而更是對語言使用而言不可或缺的交流的外在性。
對于“他者”“外部”乃至“差異”的揭示無需經(jīng)過一個(gè)“缺席性在場”的超越者,這進(jìn)一步意味著:對于任何話語和制度的批判和反省,不需要批判者占據(jù)一個(gè)超越性的“元立場”。在針對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進(jìn)行闡述時(shí),柄谷寫道:
“主觀”只有在笛卡爾以后的哲學(xué)中才顯現(xiàn)出來,這如果說的是先驗(yàn)結(jié)構(gòu)的首次顯現(xiàn),那么的確如此。因?yàn)槿绲芽査f,在此之前的哲學(xué)從屬于所謂“語法”。但是,在笛卡爾那里已經(jīng)發(fā)生的事情是,這種先驗(yàn)結(jié)構(gòu)那里出現(xiàn)的“主體”,一旦僅僅作為認(rèn)識性的主觀而被積極地確立下來,那么它就消失了。(同前,97-98頁)
在柄谷看來,如果我們依照笛卡爾主義的主客二分法來表達(dá)所謂的認(rèn)識論主體,那么這一做法已經(jīng)使得我們落入了一種圍繞所謂“先驗(yàn)結(jié)構(gòu)”而確立起來的有關(guān)認(rèn)識的封閉系統(tǒng)之中。在這里,非常關(guān)鍵的一點(diǎn)在于,柄谷所強(qiáng)調(diào)的并不是所謂主體的“消失”,就像結(jié)構(gòu)主義者或后結(jié)構(gòu)主義者在批判“主體”時(shí)所做的那樣;相反,柄谷強(qiáng)調(diào)的是:如果我們在使用語言時(shí)不可避免地包含著無法被語言系統(tǒng)內(nèi)在化的、關(guān)系的“外在性”,那么在面對“批判何以可能”“認(rèn)識何以可能”“反思何以可能”等貌似處于“元層次”的問題時(shí),我們不必為自身的批判或反思建構(gòu)額外的條件,仿佛只有從一個(gè)抽象而高高在上的“普遍性”——無論它被叫做“理性”“人性”還是“精神”——出發(fā),我們才能對種種“特殊性”做出價(jià)值評判。相反,在每一次的交流中、在每一次與他者的偶然關(guān)系中,都包含了批判的可能性,因?yàn)槊恳淮蔚慕涣鳎ɑ蛴帽葟?qiáng)調(diào)的一個(gè)詞:“交通”)中都不可避免地發(fā)生著主體位置的“跨越”:
作為先驗(yàn)結(jié)構(gòu)的主體的場所,或作為場所的主體,不是在“深處”而是在“旁邊”;換句話說,必須把它稱作“作為差異性的空=間”。當(dāng)然,這不是心理意識,也不是客觀空間。(同前,104-105頁)
因此,柄谷指出,在笛卡爾的“我思”那里得到揭示的,便是主體的這種“作為差異的場所”——不是一個(gè)穩(wěn)定而抽象的思考主體,而是一個(gè)處于不斷移動(dòng)中的、在“交通”過程中進(jìn)行思考、比較和批判的主體。不固著于某種“主體的先驗(yàn)結(jié)構(gòu)”,而是以“交通”過程中與他者的偶然關(guān)系為著眼點(diǎn):在我看來,這構(gòu)成了柄谷在《探究》《跨越性批判》到《世界史的構(gòu)造》的一系列著作中一以貫之的思考方式和論述姿態(tài),也是我們評價(jià)其“交換樣式”時(shí)不可忽略的重要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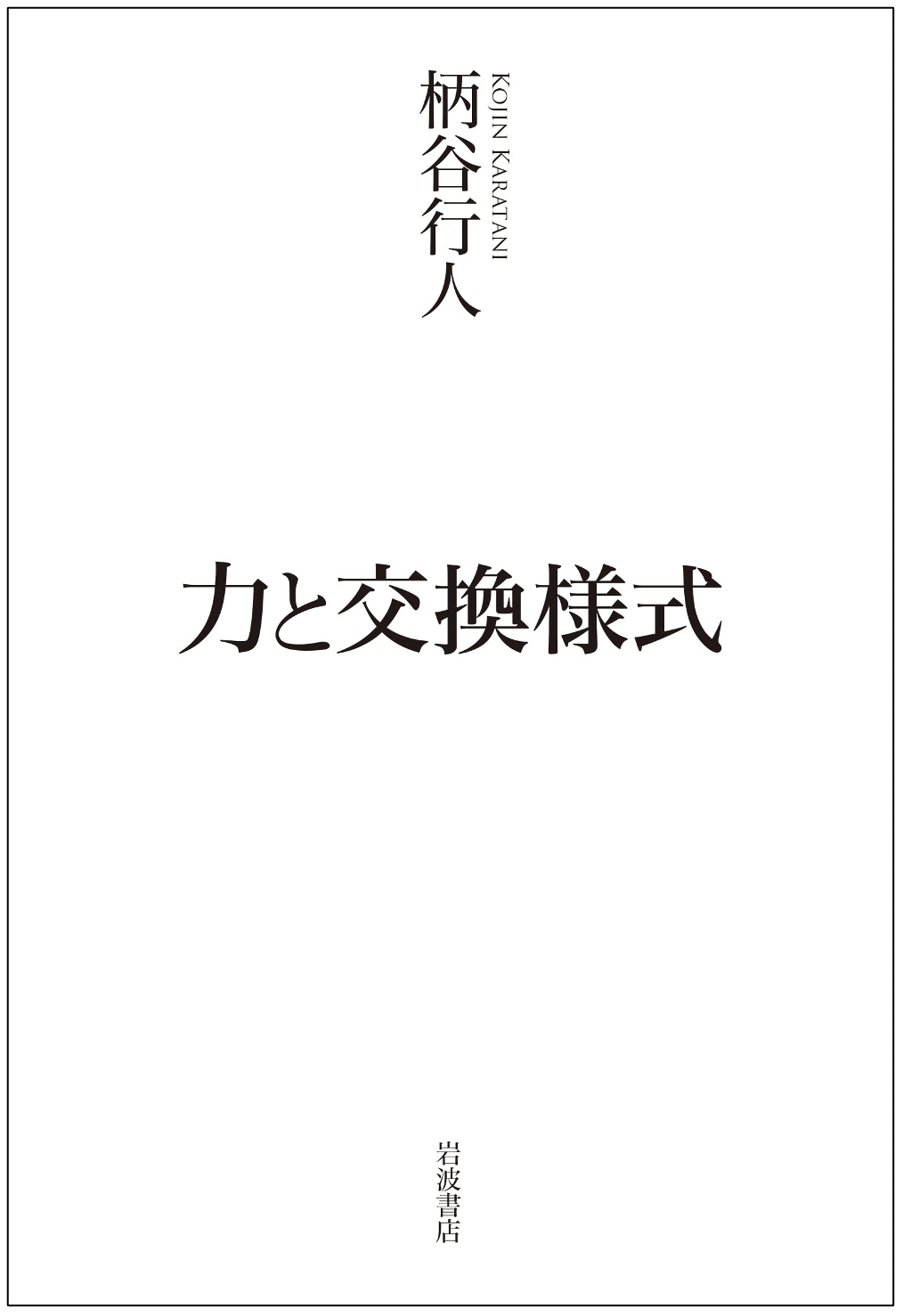
柄谷行人『力と交換様式』,巖波書店2022/10/5刊行
結(jié)合專名的討論,柄谷關(guān)于“我思”的討論告訴我們:在日常使用語言的時(shí)候,事實(shí)上我們無時(shí)無刻不在使用“專名”的意義上使用語言;我們無時(shí)無刻不與語言(的所謂字面意思)之間保持著一種無法還原的距離——不是一種物理上可勘測的距離,不是“先驗(yàn)主體”與經(jīng)驗(yàn)之間的距離,不是一般性與特殊性之間的關(guān)系,而始終是作為“差異性的場所”而存在的、標(biāo)志或烙印著言說者之主體性和獨(dú)特性的距離。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