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韓國新生代科幻作家金草葉:書寫屬于女性與植物的未來

金草葉
自2017年以《館內遺失》和《如果我們無法以光速前行》獲得韓國科學文學獎中短篇大獎、最佳作品獎以來,金草葉正以迅猛的姿態成為韓國乃至東亞地區備受關注的科幻作家。她出生于1993年,有生物化學的學科背景,雖說還很年輕,職業生涯起步不久,但已經出版了《如果我們無法以光速前行》《行星語書店》《剛剛離開的世界》三部短篇集,以及長篇《地球盡頭的溫室》。
這些作品多次登上圖書暢銷榜,作家本人又在2019年拿到了韓國的今日作家獎。可以說,當下“韓國科幻時代來了”的風潮背后,金草葉和她的作品無疑是重要的推動力之一。
讓金草葉進入文壇視野的短篇《館內遺失》是她的第一篇創作,小說設定在未來,去世的人可以將自己的思維上傳到圖書館,供親友悼念。主角智敏是一名待產的準媽媽,她發現自己與其他孕婦不同,對身體里的胎兒沒有任何愛意。這讓智敏想起了自己的媽媽,媽媽已去世多年,思維被存放在圖書館。原本對媽媽不再有留戀的智敏,疑惑于自己對胎兒異于常人的感受去了圖書館,卻發現媽媽的思維搜索不到了。
想要重新找回媽媽,要用到媽媽生前的一件遺物。智敏聯系了彼此間早已疏遠的弟弟和爸爸,曾經偏執的媽媽,破碎的母女關系再次被喚醒。在智敏的印象里,媽媽是那個“總是把自己搞得像一個受害者”的人。智敏出生后,媽媽患上了抑郁癥,在正常時對智敏說“我愛你”,不正常時說“你毀了我的人生”,智敏時常為此感到愧疚,覺得自己的出生是一種原罪,但同時她又不愿像物品一樣被媽媽控制。她與媽媽的最后一次對話就是由此引發的爭吵。
智敏最后找到的遺物是印有媽媽名字的一本書,在成為“抑郁癥媽媽”之前,她叫金銀河,是一名圖書設計師。這是智敏從未意想到的,媽媽的過去原來不僅限于待在家里,恰恰是孩子的到來讓媽媽失去了身為母親以外的生命體驗。所謂的“館內遺失”,言下之意其實是關于身份或過去的遺失,智敏尋找的并非是媽媽的思維,而是媽媽不被記得的那段人生。在這個過程中,智敏也正好站在了從“金銀河”變成“媽媽”的路口,她不再被分配工作,被勸告要看淡事業心,以家庭為重。當她最后在圖書館的虛擬空間里看到媽媽時,她覺得自己“可以理解媽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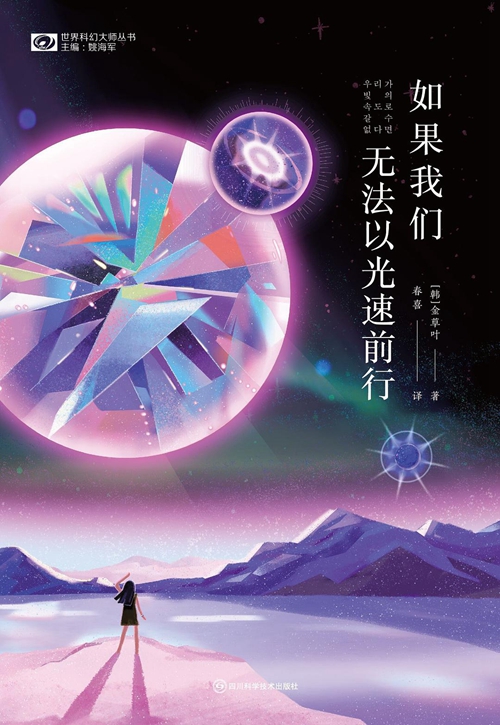
從這個短篇里,可以看出金草葉偏愛的寫作模式,她往往會塑造一個近似旁觀者的角色,引導讀者的視線深入一段往事或記憶——短篇《光譜》里,“我”拿著外婆年輕時的照片,回想曾是生物學者的外婆登上探測器,在太空遇險后與名為“路易”的外星人共同生活過的經歷。短篇《如果我們無法以光速前行》里,年輕男人遇到廢棄航空站里退休的老年研究員,聽后者講述自己在太空航行高速發展的年代,如何研究深度睡眠技術,又如何因為蟲洞隧道的開發被迫與家人分離。
當讀者已摸清往事或記憶的全貌,才真正迎來故事的核心。在這里,第三類接觸、太空航行這樣的科幻設定充當的更像是一具帶有魅惑性的外殼,金草葉想要探討的是在這層外殼的影響下,角色的情感和行為是否會發生相應的變化。于是我們看到的是,《光譜》里的外婆即便無法用語言和路易進行深度交流,也難以參透路易用光譜做出的畫,但依然能感受到彼此間累積的善意。從技術革命的弄潮兒變成失意者,研究員難以割舍對家人的思念,在一百多年里依靠深度睡眠技術延長壽命,只為等一列早已不存在的航班,帶她去往家人移居的星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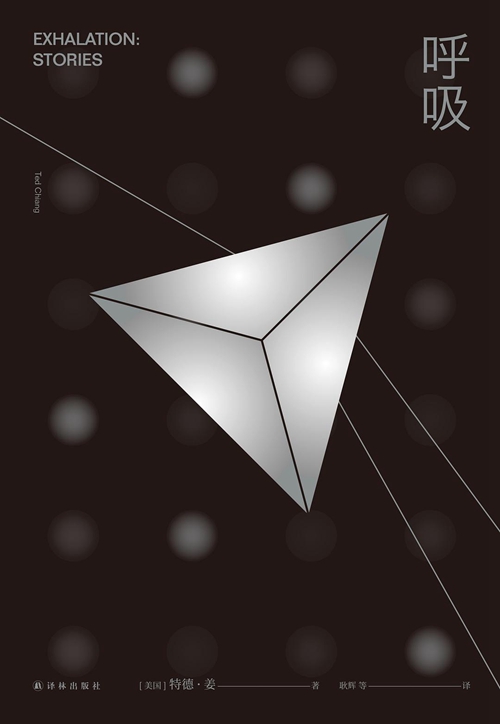
華裔科幻作家特德·姜的《呼吸》
從這個角度來看,金草葉的寫作與華裔科幻作家特德·姜類似,巧合的是,兩人都曾在故事里探討過AI育兒對嬰兒心智的影響(金草葉的《共生假說》和特德·姜的《達西的新型自動機器保姆》)。但金草葉的落點要更具體,更貼近現實,正如《館內遺失》觸及了當下社會普遍存在但又不被重視的一個問題:女性在身份轉變過程中面臨的情緒和個人價值上的落差。另一個短篇《朝圣者們為什么不再回來》里,出身不好且身體有缺陷的生物學家利用不受監管的胚胎改造技術創造出一個充滿善意的烏托邦村落,直指在人類社會里從未平息的歧視問題,小到校園和職場暴力,大到種族隔絕。
在以現實主義寫作見長的當代韓國文學里,將這種寫作傳統與科幻結合起來,是金草葉作為新生代作家發現的一條新的小徑。需要指出的是,她筆下寫到的思維上傳、胚胎改造等科幻設定,在今天看來不再新鮮。加上故事里對現實問題的表達,使得“科幻”這一原本應與未知、想象力掛鉤的元素被大大削弱,它幾乎不再提供現實之外的更多可能性。
意外的是,名為《關于我的太空英雄》的短篇填補了這個空白。故事里,人類為了到達宇宙彼端,會對航天員的身體進行“賽博格鍛造”。主角佳允加入了這個項目,她的姨媽在景曾是這個項目的一員,完成“賽博格鍛造”后,在任務出發的那天因爆炸犧牲。視在景為太空英雄的佳允后來才被告知,在景并沒有犧牲,她只是在任務前一天逃離了航天員中心,跳進了大海。
對真相疑惑的佳允開始搜尋與在景有關的記憶。在景是一名未婚媽媽、太空研究員,讀博期間一邊育兒一邊完成學業,參加“賽博格鍛造”項目后因為年齡較大,體型瘦弱,并且是唯一一個有孕育經歷的東亞女性等身體特征飽受爭議,有人因她不符合完美而標準的航天員形象質疑她,也有人看中她身上女性、未婚媽媽、女科學家的標簽,借此追捧她。
在跟佳允和自己女兒的對話里,在景曾說過“我更想超越人類極限。我們身體的局限太多了”,她厭倦了人們對自己的期待和憎惡。聯想到漢娜·阿倫特對身份的感悟,“仿佛僅僅身為人的人,已經喪失了一切資質,而不能被其他人視為同類”,跳進大海的在景不是自殺,而是不再順從人類社會施加在她身上的種種定義和標準,她要擺脫的不只是身體的極限,還有觀念的牢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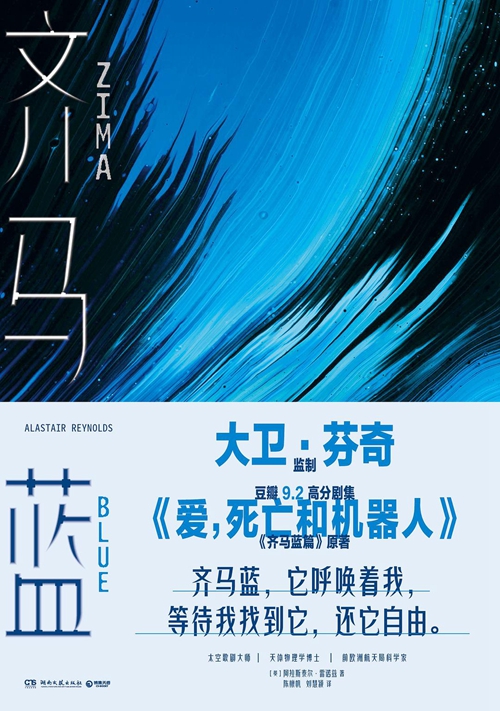
因為在景的縱身一躍,賦予了這個短篇超越般的屬性。在筆者有限的閱讀里,在景的形象總是與阿拉斯泰爾·雷諾茲筆下的齊馬交替出現。在名為《齊馬藍》的短篇里,身為改造機器人的齊馬憑借完美的機體走遍宇宙的角落,它用獨創的藍色作畫,將宇宙作為展廳,成為人類社會備受追捧的藝術家。它的最后一幅作品是跳進泳池,將自我拆解以回到初始狀態——一個清潔泳池的小型機器。那抹標志性的藍來自泳池瓷磚的顏色,藍是齊馬自我意識的起點,也是它在藝術創作中追尋真我的潛在引導,它以回到起點完成對真我的追尋,它的“自毀”與在景殊途同歸,在做出選擇的那一刻,純粹的生命和心靈形態無需再依靠無限的“得到”和“成為”,小型機器和賽博格軀體,泳池和大海,又有什么區別?

動畫《齊馬藍》劇照
相較短篇而言,金草葉的長篇《地球盡頭的溫室》略有不同,短篇里簡約、潔凈的風格折損了,取而代之的是接近當下流行的科幻網劇的嘈雜感。故事沿用了金草葉熟悉的敘事模式,主角依舊是女性,背景設定在“粉塵風暴”過后完成重建的人類社會,研究員雅映發現了一種名為“摩斯巴納”的發光植物,進而想起自己幼時曾在鄰居的院子里看到過類似的植物。院子的主人——名為李喜壽的老人如今已失聯,她離群索居,除了植物還熱衷收集各種報廢的機器人。

在調查李喜壽和“摩斯巴納”的過程中,雅映知曉了一段“粉塵風暴”時期的故事:名為知秀的機械師認識了名為瑞秋的賽博格改造人,兩人投靠了幸存者們成立的森林村。知秀幫助瑞秋維護軀體,身為植物學家的瑞秋在搭建好的溫室里研究植物,同時用制造好的粉塵分解劑從村落里交換她和知秀需要的生存用品。
氣候災難,末日求生,烏托邦與反烏托邦……金草葉的這個故事匯集了科幻文學里常見的經典元素,又加入了帶有中性和自然色彩的植物為整個故事穿針引線,重心則回落到知秀與瑞秋的情感糾葛。兩人原本以利益關系共處,某次幫瑞秋維修時,知秀希望引導瑞秋的善意來讓兩人的關系變得友善,未經瑞秋同意啟動了后者身上的情緒穩定模式,瑞秋也逐漸對知秀產生了依賴性的愛意。
身為賽博格改造人,瑞秋的身上依然留有人類的情感與思維,她對植物近乎偏執的愛便是證明。“粉塵風暴”下的世界臨近毀滅,即便清楚溫室里的植物可以吸收粉塵,甚至有可能拯救世界,瑞秋卻并不關心,她想要的只是在溫室里與植物待在一起。這正是知秀對瑞秋的愛意存疑的原因:是自己按下按鈕的行為引導了這種愛?還是瑞秋原本就對自己有愛意?
當雅映終于見到故事里的瑞秋,她同樣對此難以釋懷:“我對知秀的感情真的是因為人為誘導而產生的嗎,還是從一開始就存在的呢?如果是誘導而生,那為什么幾十年過去了,離開溫室這么久之后還是無法遺忘呢?想到這些,我就憤怒得沒辦法死了。”
知秀的疑慮并非沒有緣由。叢林法則至上的末世,在頻繁目睹人性墮落后要積蓄怎樣的勇氣才能確信彼此間的善意?知秀在內心里渴望被善意對待,同時又下意識地跟這份以愛為名的感情保持距離。聯系這部長篇剛好處在新冠大流行期間,它或許也可以看作“新冠敘事”的另一種表達——來自災難時代的個體情感,如此脆弱,又如此稀薄。
瑞秋的植物最后拯救了世界,被知秀告知真相后,她選擇離開。知秀則變成李喜壽,她把瑞秋的植物留在身邊,在余生里尋找可能成為報廢機器人的瑞秋。這是重建之后的全新時代,辜負愛意的人要奔走在這片敷上新土的大地,用漫長的時間償還愛。這也是舊的時代在每個人身上早已劃下的痕跡,必須去消化,去治愈。因為身為人類的肉身并不長久,就需要故事的發現者和講述者——比如雅映和你我。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