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煉油廠三代人走過的“大江大河”|鏡相
本文由鏡相 X 上海大學文學院合作出品,入選高校激勵項目“小行星計劃”。如需轉載,請至“湃客工坊”微信后臺聯系。
采寫 | 鄭沁辰
指導老師 | 呂永林
編輯 | 吳筱慧
東海邊,矗立著一片三萬余畝的鋼鐵森林。各色煉油塔罐織著錯雜的管道爬架,在不同塔層里煉著航空煤油、汽油、柴油……最高的煙囪紅白相間,像海上的燈塔。這些鱗次櫛比的煉油設備,從高處看,像這片大地上豐收的莊稼。
白天,煙囪向天造云;夜晚,塔罐綴滿明亮的白色燈盞,輝映成一片恢弘的水晶城。那是我至今所見的任何一座特大都市都不能比擬的夜景,在東海之上接住一片銀河,晝夜不息。
再向內去,好像有一座小城挨著,居民樓、菜場、公園、文化宮、醫院、學校……這是鎮海煉化的生活區。一條河貫穿而過。人們靠海、沿河,活成一條小船。國企改制前,這里住著一個小社會。連著廠區、生活區,煉化人都叫它:煉油廠。
我和我的祖輩、父輩就從煉油廠走出來。有人說,刻在石化人基因里的是一種“輪回”,像一張網,兜住了每個人。煉化人和煉油廠共同織著這張網,將煉油廠的歷史印記與煉化人的生長痕跡一道織進幾十年的紋理。

晨曦中的鎮海煉化(圖源網絡)

“先生產,后生活”
1974年底,爺爺奶奶帶著三個兒子和全部家當,從溫州坐著卡車來到鎮海。卡車在盤山路和泥巴石子路間穿梭。半路上發動機過熱,車趴在了路邊。司機用鐵桶從農田里打來水降溫,才又徐徐上路了。這桶水,舀來了煉油廠的第一把火。
1975年,鎮海煉化在一片蘆葦叢和棉花地的灘涂上打下第一根樁。除了爺爺奶奶的溫州化工廠,同來的還有各地石化企業的工人:蘭州煉化、湖南長林化工廠、衢州化工廠……每廠調三四十人,在海涂上組起一個大的新家。從那時起,煉化人開始織著一種沒有血緣卻血脈相通的親情。
從蜿蜒的小土路走,經過小賣部、幾個糞缸和摞著的農家肥,一戶戶的黑瓦青墻房,就是第一批工人落腳的俞范村和后施村。爺爺奶奶家租在村大隊一間老會計室。第一年冬天下大雪,房里下小雪,大家連夜趕制棉被棉鞋。
第二批工人住在海涂,叫“七千平”。“七千平”由紅磚砌起,蓋上棚子,就算臨時家屬房了,足綿延七千平米。工人們自己挖井,有時候靠“天落水”。第一個臨時的“廠子弟學校”就搭在那,竹編的頂,裸露的紅磚墻和地面,架子是毛竹筒。

鎮海煉化生活區一角
奶奶工作的設計院最早也在那里,是營房樣的尖頂屋子。不僅如此,煉油廠的其他臨時辦公點,也紛紛就著棉場留下的舊工棚運轉起來。在這樣的“湊合”中,煉油廠的第一代開始了“先生產,后生活”的建廠歲月。
這片貧瘠的土地上,支持他們的首先是理想與熱血。奶奶畢業于浙大建筑系,早年大學生分配難,只能“隨便塞塞”,奶奶就被“塞”到了溫州化工廠。溫化撐不下奶奶的理想,“學了那么多年的東西在溫化一點也沒用到,很失望。我想到一個新的地方去發揮自己的才能”,奶奶語氣平緩又如數家珍,“到了煉油廠以后,的確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設計了好幾棟房子。”設計院方案競賽,選中了奶奶的那套,我小時候就住在奶奶設計的房子里,每間都有朝南的窗。我問奶奶,算是在煉油廠實現理想了嗎?奶奶笑答:“我的夢想還要高,不可能實現的。但就這樣為止了。”
建新廠,也是第一批工人們理想中的一部分,“來的時候什么都沒有,但有盼頭。大家從四面八方來,就靠自己的一腔熱血,帶著老廠作風和石化精神,心很齊,關系也很親密。”
有年元旦前夕,工人們組織了一場頗具儀式感的活動:零點起,大家不沾枕頭,都相約著上廠里干活去了。那代人是帶著心中的保爾·柯察金來的,他們都想成為自己平凡生命中的英雄。“那時候一心為了把煉油廠搞起來,不是幸福在物質上,生活雖然不富裕,但苦中有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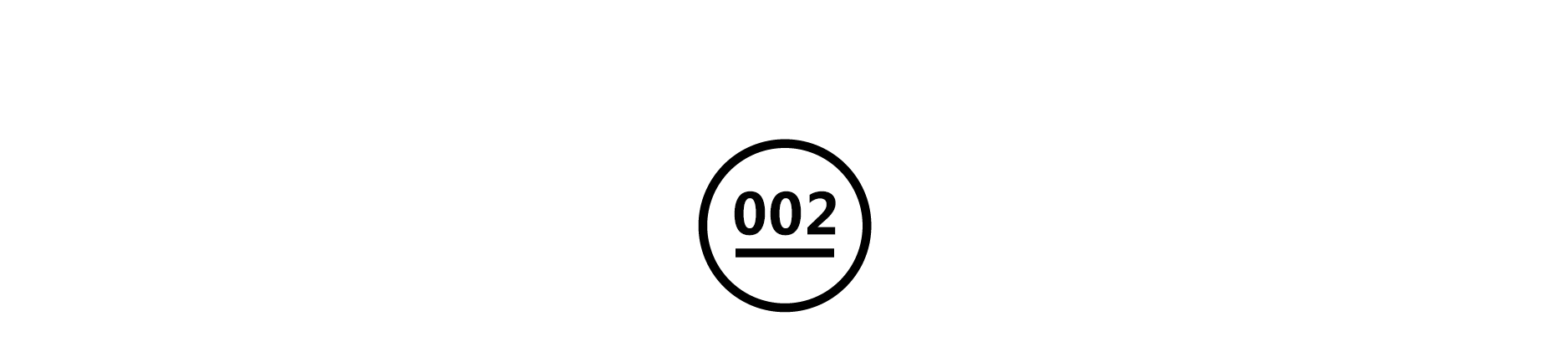
“調回家,總是好”
支持他們的另一副骨架,是團聚與回家。早年祖輩一代的夫妻,由于工作分配,多是分隔兩地。爺爺奶奶曾分居兩地十年,煉油廠這次面向全國的召喚,讓兩人看到了團聚的曙光。
“調到一起覺得很安逸,生活好像從此再也沒有顧慮了。父母都在寧波,等于回家了”,奶奶這樣說。同樣如此的,還有外公外婆。
外公在省水電局,跟著建設走,寧波奉化、臺州天臺縣、武義牛頭山,就這樣在浙江各地飄游。夫妻一年聚一回,開銷又大。
1982年,38歲的外公抓住煉油廠新建變電站的檔口,輾轉調至地方上的五鄉泵站,雖不在總廠,“跟‘老百姓’比起來,條件是很好的了。”1984年,外公到了總廠電氣車間,成為煉油廠籌建鄞縣白渡泵站的儲備人員。
外婆是按職工家屬調來的。來之前,外婆在慈溪公社辦的塑料廠工作,“那時候業務都靠自己,動不動發不出工資。路道粗的人有,路道不粗就沒有,我們經常失業。”外婆辭職去了煉油廠,慈溪的人們認為,外婆是去了“城里”,能穿上漂亮的工作服,過上更好的日子。

外婆家的窗口
外婆初來乍到,沒有正式工作,就被安排在機動組,同來的還有十幾個職工家屬。外婆形容機動組的工作“像打游擊,像救火兵”。在機動組幾個月,外婆種過花、拔過草、冷卻過設備、植過樹。偌大的廠區,外婆不認路,也不會騎車,就坐在別人后座,跟著任務分配,今天去幾號油庫,明天又是幾號……
“我那時候經常坐在鐵路邊上講大道,一批從一個地方來的家屬,湊起來聊得很開心,聽著火車隆隆來了……”他們就這樣盼著,等著,不止團聚,還翹首于那份屬于“煉油廠雙職工”的“榮光”,刻進他們命運中新的高位。后來,外婆分到了廠技校門衛的工作,一直干到退休。那時,從技校畢業的廠子弟,都將四平八穩地進入煉油廠工作。
那是外婆一生最開心的日子,工作穩定離家近,三五同事沒事聚攏,一起盼著要領工資、發工作服了。看著周圍的三職工,四職工,外婆想自己以后也會有的,“每天想著什么時候女兒讀出技校就能分配工作了,一天天過得很快。沒有心思,又自由。來了煉油廠,就像吃了定心丸。”
“煉油廠是老家,父母姐妹都在,調回來就是要回家,夫妻團圓。那時候不管什么單位,調回家,總是好。”外公回想起來,還有喜悅的滋味。
那些年,廠里的生產生活蒸蒸日上:工人們搬進了嶄新廠區和家屬樓;棉田上被征了地的農民,都成了煉油廠的后勤職工,有的供應果蔬副食,有的當了食堂師傅;職工家屬也被安頓到各個崗位。煉油廠總領著包括生產和生活在內的各個子公司。

2023年 拆除的老文化宮
生活區也漸有一個小城的樣貌,從幼兒園到技校、集電視臺和活動場于一身的文化宮、用菜卡就能買到實惠菜品的菜場、廠里的影院、百貨商店……生活區的福利分房按著職稱和工齡分配;雙職工和帶孩子的單職工,不花一分錢,就能擁有一間屬于自己的小房。每年深秋起,廠里的生產余熱給人們免費供應南方少有的特殊標準——暖氣。北邊有片海涂,廠里用來自種西瓜、蔬菜、養魚,分給職工。
在外婆的記憶中,煉油廠最興旺的時候,燙頭只用券,房子不要錢,飯菜一直有,子女有歸宿。外公記得有一年,廠里給每位工人發了一筆666元的獎金,一舉轟動全市。人們說孫玉寶是一位“很厲害”的廠長,凝聚著萬眾一心,把收益最大地返給職工,他是帶著“大慶精神”來的。在他們言語的流光中,孫廠長像一條海岸線,托起東海上的朝陽,照著彼時燦爛的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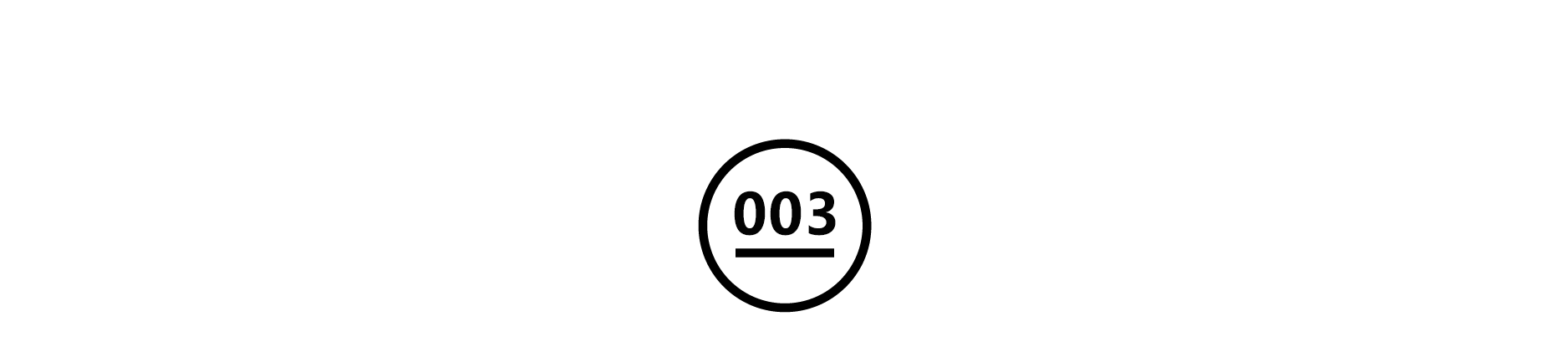
被按下了的那股“勁”
有人說,石化人的職業生涯不是寫在自己身上,而是在父輩的基因里。我的父輩一代,或多或少也是如此;而屬于第二代人的“首個家園”,也冥冥中被煉油廠所選擇。一張由血緣“傳承”的煉化網,開始向下織開來。
八十年代,隨著煉油廠創業初期的成功,第二代廠子弟們不僅生活在那片寬宏地允許所有煉化人不用為“過日子”而操心的天地;也在這曾經承載過第一代人理想的地方,成了舞臺的下一代主角。
從技校入學到離開煉油廠,這十余年,爸爸找到了他人生中“最閃亮的日子”。爸爸是煉油廠高中技校名列前茅的尖子生,“那時候有找回自己的感覺。所有專業課像有天賦一樣,不需要花力氣,聽老師講完,就能學以致用了。”畢業時,爸爸以全校第二的優異成績進入煉油廠,成為一名儀表工。

鎮海煉化大門
爸爸的儀表維護工作,是膽大心細的活,他經歷過各種現場:高溫高壓、石油刺鼻,目睹班組同事在身旁中毒倒下。冬天,西北風呼呼吹,爸爸穿著工作棉襖,爬到煉油塔上排除故障;遇上細高的“火炬塔”,好幾十米,人就在半空和塔一起晃。
爸爸曾和同事們檢修完畢爬下半程,旁邊爐子的氣體瞬間爆炸,響聲震徹廠區,炸飛的爐磚簌簌地往安全帽上落。即便如此,爸爸近乎日夜“鎮守”在他的崗位以防任何突發狀況。
煉油廠每每開發出新裝置,會讓老師傅帶著年輕人去學習。爸爸工作第二年就參加了最先進裝置的培訓。他進步很快,不久便成了崗長,帶了好幾個徒弟,“后來廠里又有新的裝置出來,那時候我就成了‘老師傅’,帶著年輕人去,雖然我也只有三十歲。”
跟爸爸相比,媽媽的核心詞則是“穩”。但過分的平穩,從這代開始,正悄然滋生出裂痕。
和大部分煉化父母一樣,外公外婆也希望子女技校畢業后得個煉油廠的穩定工作。但媽媽曾想找一條特立獨行的路。
“當時所有人都在考技校,但我想考高中,我覺得應該走走別人沒走的路”。小時候,媽媽就不斷萌生與眾不同的想法。她說,她要抓壞人,外婆嗔怪道:“公安局都是男人做的,你一個女人家殺氣騰騰的干什么。”
不出所料,媽媽不想當工人的想法,也在中考前被父母熄滅了。在他們心中,煉油廠穩穩的庇護,象征永遠安定的生活;而不隨大勢的選擇,意味著要面對風浪更大的世界,讓人“心不定”。
媽媽上了技校,學的是鉗工,到頭來還是做了“男人的活”:每天技術操練、敲榔頭、打磨、鋸鋸子。“鉗工是男的干的活,女的進去要開后門,因為出來不用倒班。”從此,媽媽唯一的盼頭就是畢業后在廠里上白班的日子。
1991年,19歲的媽媽進了煉油廠機修車間。說是鉗工,女的上了崗,就是記筆記、擦桌子類的工作,“有時候去現場,也就是給人跑跑腿、打打下手,弄點柴油、搬搬設備。有些儀器設備拿不動,人家就不用你拿了。”
媽媽就這樣日復一日地隱在所有的自行車和工作服中。外婆回憶起大家騎車上班時的場景,“淡藍的工作服,連聲音都沒有,看過去像海浪一樣的一片,讓我在里面找你媽媽,我找不到。”
有時候,媽媽覺得一天時間很漫長,因為沒事做,連天也聊完了,于是,她就盼著下班換下工作服,穿好看的衣服,看看電影、逛逛街;直到我出生,媽媽的一天里又有了新的盼頭……這段過分平淡的生活中始終埋著的,是媽媽從來都被按下了的那股勁。

廠子弟的后代不再是廠子弟
1992年,市場經濟的風吹向全國,大批國有企業陸續加入上市大潮。兩年后,鎮海煉化也上市香港,成為股份制公司,企業的重心漸漸更集中向生產。也就是那段時間起,人們感到煉油廠在悄然變化。
當爸爸和很多人一樣,還拿著廠里穩定收入的時候,早年肄業離開煉油廠的朋友已趕上了深圳賣電腦的風口,他的隨身包里總有厚厚的百元鈔票。外面的世界帶著無窮的機遇和寶庫,以風馳電掣的速度將煉油廠從曾經那個萬眾矚目的“神壇”卷了下來。像一個被從外敲破了殼的雞蛋,一些刺和光,都透過裂縫,刺著第二代煉化人。
伯伯是處里第二個走出煉油廠的。
他在廠環保處的氣象站里,邊工作邊念完了同濟大學的環境工程。大學畢業時正逢煉油二期工程建成,原油加工能力躍居杭州灣地區首位,開始開拓國外市場。于是,伯伯加入了煉油廠800萬噸改造水污染治理的國家項目。污水處理項目交流結束前,法方代表將一把家族制的小刀送給伯伯,“他說,‘我要送給我在技術上交流最合拍的人’”。幾十年過去,這把刀伯伯一直帶在身邊,刀柄是一只華麗的長靴,或許,這早成為一種遠行的伏筆。
1999年,辭職的時候,伯伯敲了二三十個章,每一個都仿佛敲下萬眾矚目的決心。那時,廠里的原油加工能力已上升到1600萬噸,伯伯看到日益加重的污染,又想起童年時那條清澈見底的河。同時,他也不愿在那些退休后的第一代職工身上,一眼望見自己的未來。“總想往更高更遠的地方跑。一是為了孩子,一是還想在更高的舞臺做出更多項目。那時候改造的一陣風過了,或許在煉油廠,已經到頭了。”
2000年,我出生,正逢藍印戶口制度,退休的爺爺奶奶已在上海買房落戶。和很多第二代煉化人一樣,因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爸爸不希望我繼續成為廠子弟。2005年,爸爸打頭陣來了上海。
媽媽埋著的那股勁,也是在那時破殼的。“以前的想法都被爸媽掩蓋了,這次我想自己跨出這一步。”媽媽自學拿到電大文憑,又考出了會計證,她相信自己并不是父母口中鄙夷的那個“成績差,又粗心,離開煉油廠就無處可去”的人。“想感受不同的生活狀態,想看更廣闊的東西。”

夜晚的鎮海煉化
如今,在更大的東海畔,伯伯不斷攻下新的污水領域,而煉油廠,是曾經那片給足他底氣的大海。同樣在上海找到自己生活軌道的媽媽,也說煉油廠是“曾經的自己”——但她更喜歡“現在的自己”。爸爸創過業,也輾轉不同公司上過班,雖然似乎沒有煉油廠的日子那般左右逢源,但回想起來,爸爸仍覺得要不斷向上走。他有了更豐富的閱歷和變化,“或許當人生走到最后,我就比一輩子在煉油廠的人能講的故事更多一些。回憶起來,好像‘經歷了一些事情’,不管是有沒有意義,但這些是永遠忘不掉的。”
原來屬于第一代人的保爾·柯察金始終不曾離開過。數十年間,那個實現過第一代人的煉油廠,在第二代煉化人心中,漸漸成了撐不下奶奶理想的“第二個溫化”。
煉油廠的第二代,是和鎮海煉化一起生長的一代。從早年騎自行車就能很快穿越廠區,到后來坐班車都要用上一段時間,他們見證了鎮海煉化發展最迅猛的三十年。但大船終歸載不動理想與志向沉甸甸的小船,小船要向自己選擇的更廣闊的未來家園出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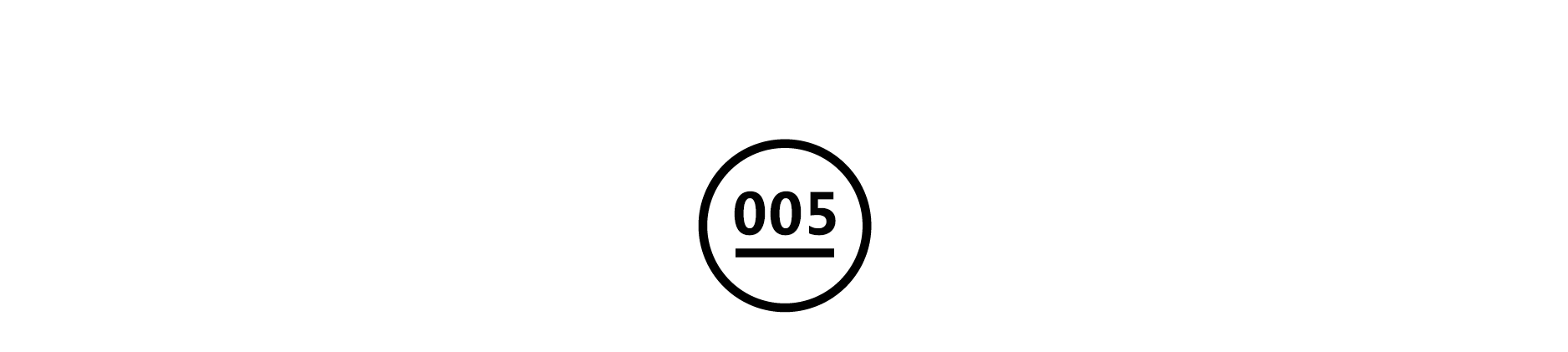
00后眼中的“煉油廠”
2000年,我出生在鎮海,正是父母計劃離開的前幾年。
每天傍晚五點是我最喜歡的時刻。“一片海水”從廠區大門涌出,有說有笑彎進各自的單元樓,又被歸還成很多條小溪。鍋碗瓢盆開始碰撞,各層樓道的聲控燈一串串明滅,像慢速的鞭炮歡慶每個黃昏的節日。
對煉油廠的第三代來說,生活區是與我們相關的所有。文化宮的哈哈鏡和“黑水潭”,是我和同伴的“探險地”;公園里有對那時的我們來說足夠巍峨的小草坡;有游泳池和體育場門口夏天蓋著棉被的移動冰棍攤;有一家小牛奶店,店鋪雖小,卻永遠有我們愛喝的牛奶;還有煉油廠醫院,作為曾經的常客,連護士都知道我是那個吊針只能扎腳背的小孩……

搬遷后的牛奶店
小時候,大人們最讓我訝異的一項能力,是“識人”。路上隨見的人,幾乎都能脫口而出對方的名字、車間;有時遇到爺爺輩的人,還能叫出是某人的爸爸、媽媽。
2006年一個晴朗的下午,在石化幼兒園過完最后一個兒童節,我跟著媽媽坐火車離開了煉油廠,去往更大的一片海。就在那年前后,國企改革深入煉油廠。許多職能處和子公司陸續分離出鎮海煉化,交由社會或個人負責。變化是寸縷滋生的,但對往后逢年過節才落回煉油廠的我而言,一切如天翻地覆,像一部掉出太多幀的電影。
曾經讓我訝異的“識人術”和“點頭禮”消失了,生活區有了太多陌生面孔和方言,又一批人陸續帶著自己的“小生意”來了;煉油廠在寧波和莊市造了新房,職工依然優惠,他們說,生活區環境不好,得肺癌的人多,于是年輕人都搬了出去,剩下老人與和他們一樣老的房,其余則租給新的外來客;電影院大部分時間都上著一把銹跡斑斑的掛鎖,二樓大廳有時給社區老人打針;文化宮的聯歡會、體育場的運動會也相繼隱匿;離退休中心成了社區服務中心,從一科室的40人到一辦公室的4人……不久前回到煉油廠,車子駛出生活區的一刻,父母嘆道:“還好當初走了,否則一輩子窩在這個地方要窩死了……”
我始終覺得煉油廠進入了它的下行時代,而長輩們告訴我從未如此,鎮海煉化始終是中國石化一面耀眼的旗。在他們的回憶中,自己永遠是煉化人。每代人對煉油廠的留戀同中有異,或是歸屬、安心,或是氛圍、人情,是“廠子弟”這個概念,是曾經那個煉化集體和他們青春的鐫刻處,是煉油廠織出的每一種家園。
奶奶說那時的煉油廠,“好像個大熔爐,里面是我的安身之處,大家都感到很溫暖,很有凝聚力”;外婆說,“以前天塌下來好像有煉油廠頂著,后來慢慢各家管各家”;外公說,改制前的煉油廠對職工,都像“一家里的子女,每個人都要關心到”;伯伯說,不變的是煉化情結,是在任何時候接觸到石化企業都感到的親切;爸爸說,煉油廠是多少個午夜夢回的地方,曾經從進入后施村開始就有的安全感和歸屬感,在上海,縮進了自己的房子;堂姐說,即便現在生活習慣和物質追求已經偏向上海,但情感上的追求還是偏向煉油廠時的感覺。
如今,鎮海煉化已成為國內最大煉化一體化企業。有太多人離開,也有不少人堅守,還有更多人不斷想進來,伯伯形容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
十多年后,我又看到那片廠區燈火,我仍認為那是我至今所見的任何一座特大都市都不能比擬的輝煌夜景,包括上海。我才驚覺,設備上的每盞燈,都是一個人。那是祖輩貢獻的全部青春,是父輩韶華所有的閃亮,是我們記憶深處恒為一種支點的光。
??????(本文頭圖來自電視劇《大江大河》劇照,其他圖片均由作者提供,實習生王悅穎、吳爭對文本亦有貢獻)
歡迎繼續關注本期“小行星計劃”專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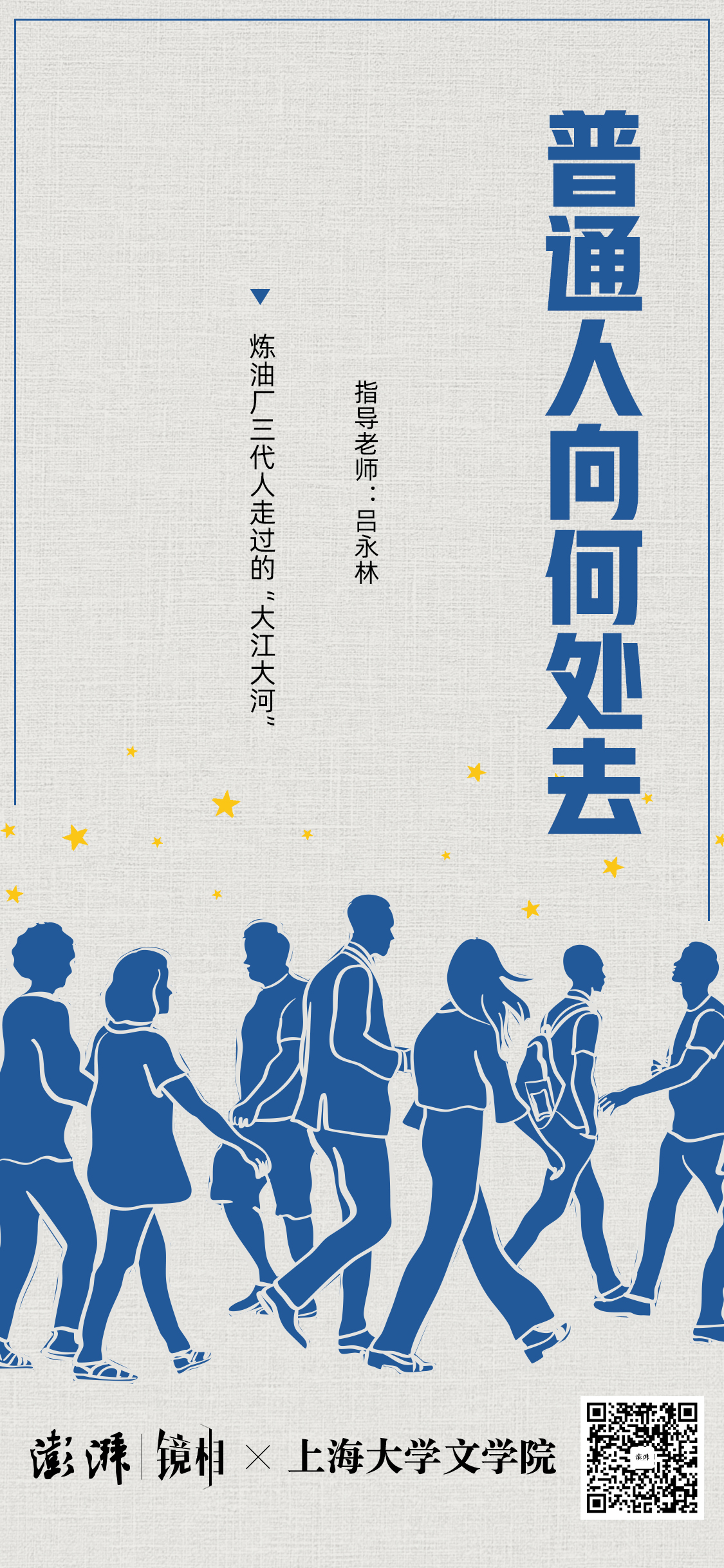
海報設計:周寰
目前鏡相欄目除定期發布的主題征稿活動外,也長期接受投稿。關于稿件,可以是大時代的小人物,有群像意義的個體故事,反映社會現象和社會癥候的非虛構作品等。
投稿郵箱:reflections@thepaper.cn
(投稿請附上姓名和聯系方式)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