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位小兒神經外科醫生眼中的治療和治愈
【編者按】
《開顱:“牽動神經”的醫療故事集》的作者杰伊·韋倫斯是一位美國小兒神經外科主任醫師,據說在全北美地區,這個細分專科,只有約250名執業醫師,在我國也不超過400名。小兒神經外科醫生面對的患者通常是未成年人,甚至是嬰兒,在技術和專業層面都給醫生提出了比成人患者更大的挑戰,作者記錄的工作故事雖然語言質樸但驚心動魄。本文摘自該書后記,作者分享了他在每周例行研討會上實踐的一次“敘事醫學”,希望通過互相交談的方式,幫助醫患一同走向治愈。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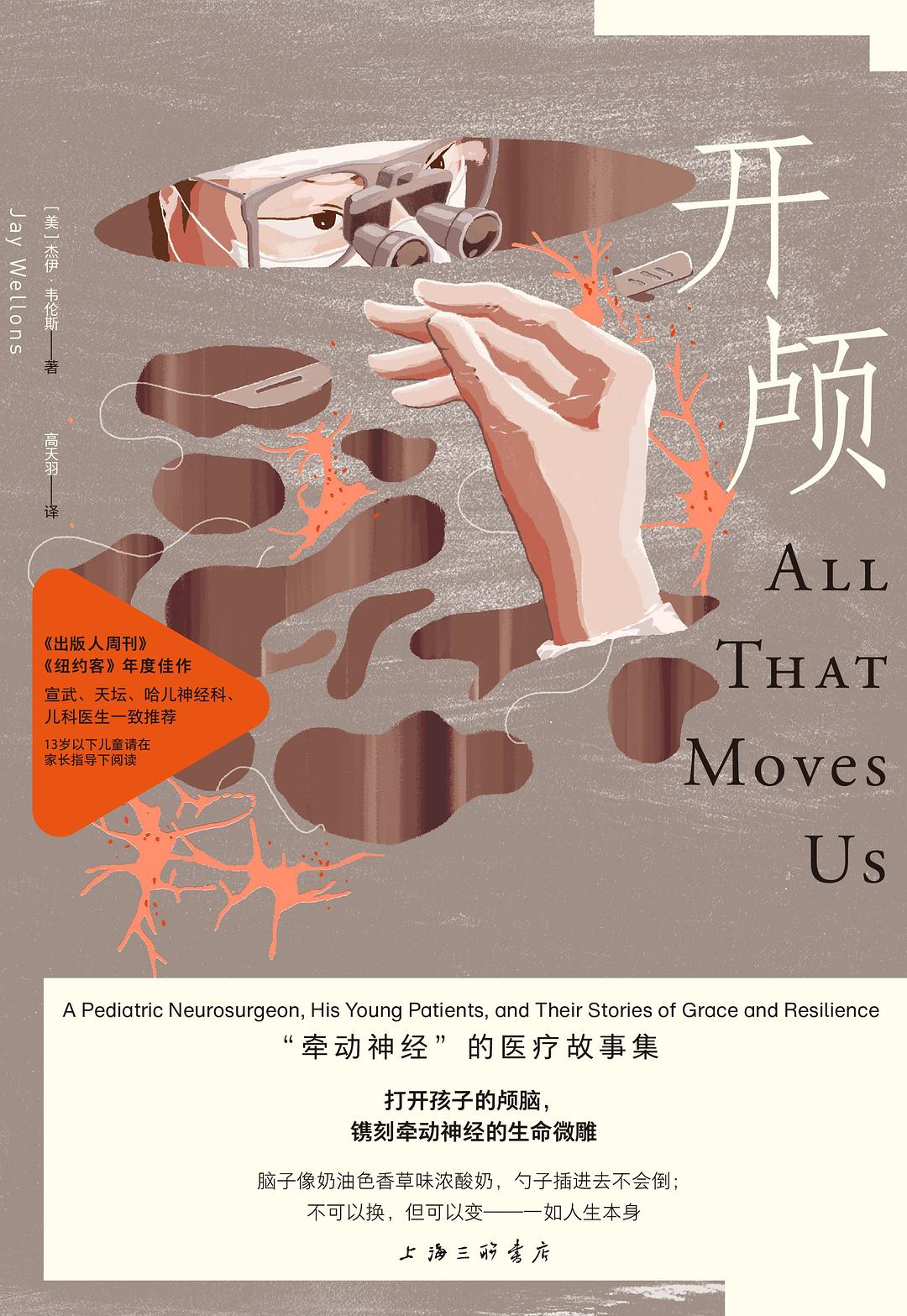
《開顱:“牽動神經”的醫療故事集》,[美]杰伊·韋倫斯,高天羽 譯,上海三聯書店·理想國,2023年8月
每周二晚上,我們醫學中心的神外住院醫師都要聚到一起開期刊研讀會,雷打不動。會上討論的話題,覆蓋了本學科的很大范圍:有對腦干內解剖結構的細致評述,有對復雜顱底腫瘤手術方法的分步驟討論,有最近發表在《神經外科雜志》上的某篇劃時代的論文,也有將頭環背心用于頸椎骨折治療的動手培訓。總之,既有先進科學,也有實踐學習。
還有吃的。
每一回都少不了吃的。他們這么辛苦,這是我們起碼能做到的。神外培訓有一個著名的原則(出于日程的不可預測和漫長的工作時間):能吃就吃,能睡就睡,別#%^&下丘腦(普外的版本是“胰腺”)。于是每周二夜里,他們都要湊到一起吃一吃,學一學。
但是說老實話,他們能來,主要還是為了有機會見見和自己以一樣的方式辛苦了一天的同類,盡可能把這一天的緊張消化掉。神外培訓是一條艱難的戰壕。
不過這個周二的晚上,他們沒有坐在潔凈的醫院會議室里,拉下百葉窗來聽投影儀嗡嗡作響,而是十個人在我家的后門廊,在白色椅子上圍坐成一大圈。我們每一個都穿著藍色刷手服,帶著白天工作的疲憊。盛滿食物的盤子隨意擱在膝頭,喝了半空的精釀啤酒罐擺在身邊的地上。那些仍在手術或應付急診的住院醫師沒有參會,但這仍是一場極好的展示。我有一個理論 :說出對自己影響最深的故事能夠拯救心靈,并幫所有人(包括病人和醫護)更快愈合。根據這一理論,我要他們各講一個病例,這病例或是教會了他們什么,或是令他們難忘,甚或是糾纏心間令他們難以釋懷。這是我們第一次以團體的形式發起此類挑戰,它的正式名稱叫“敘事醫學”,坦白說我也擔心,生怕他們找出各種聽上去合理的借口不來參與——“抱歉老板,有個病人得再去檢查一次”或者“明天有個大手術,今晚得預習”——最后搞得只有不超過三個人出席,每個戰戰兢兢地說上兩句,也鮮有討論(中東烤肉串也剩下許多)。謝天謝地,實際并沒有如此。在我就這個問題發表了兩篇論文之后,有幾名住院醫對我提起他們自己也有一些經驗想跟大家分享,問我是否可以。
夜色漸深,大家安靜下來,故事會開始了。有人講了自己引以為豪的挽救病人或避免災難的故事:自己一介住院醫做出了或大或小的臨場應變,或是解決了一個復雜問題,病人因此活著出了院。也有人坦白了自己的深深失落,在他們的故事里,家屬永別了親人,令他們一時自責難當,覺得是自己不夠努力、不夠聰明,沒把問題解決,可這些時候多半是無計可施的。
我也說過,這一行可不容易。
醫學中滿是故事,跌宕起伏的故事。在醫院待久了,你就明白這些故事根本無須潤色。而神經外科的故事往往更加起伏跌宕。這些故事往往發生在生死之際,其中有痛苦也有喜悅,還有深刻的心靈危機和堪堪得到回應的祈禱。當生命顯露出最寶貴也最有意義的一面時,你不可能不被這些根本性的瞬間所吸引。居于這方天地之中,往往一切都會升華:親人的擁抱會比以往長那么一點,在自然中徒步時的呼與吸也更深沉了一分,對安全和健康的感激也浮現得更多。
新冠疫情使醫學的許多分支離這個境界更近了。
寫作本書時,我大多時候都盡量對新冠避而不談。這場大流行的故事應該由別人來講,他們是染上病毒發病的人,是幸存下來收拾殘局的家庭成員,以及那些英勇奉獻、守在前線上治療患者的人。在未來幾年,當我們終于將新冠病毒視作一場公共衛生災難和一項歷史事件時,這樣的故事將涌現更多。
不過在這場危機中,有一段手術經歷對我確實不同一般。當時疫苗剛剛分發給全國的醫務工作者,大家終于第一次感到疫情結束似乎有望了。正常的氣氛再次恢復,雖然只維持了片刻。2021年2月的一天晚上,暴雪覆蓋了南部大片地區,我們的值班團隊匆忙地布置著手術室,準備開展一臺急診開顱術,患者是一名10歲男孩,患硬腦膜外血腫,在他的顱骨和覆蓋腦子的硬膜之間,出現了一個危及生命的血塊。之前當暮色轉入黑夜時,男孩和幾個朋友一起玩兒雪橇,從家附近的一座結冰小丘上滑下來。男孩的最后一滑太快、太遠,一直沖到了冰封的街上,停在了對面一輛轎車的下方。當時他的頭正抬著觀看方向,于是撞上了車門下框,撞得很重。幸好他及時扭頭,以左側頭部而非面部承受了撞擊。
在現場,他短暫昏迷后很快恢復了知覺。急救人員趕來將他送往當地醫院時,他談吐自如,并無意識錯亂的跡象,只是撞到車門框的地方感到頭疼。最初的腦CT顯示沒有大礙,但仍令人擔憂,因為他頭部有一小處骨折,硬膜外還有那一小塊血腫。等他被轉運到我們這里接受觀察時,情況已然惡化不少,血塊面積大大增加,對腦的壓迫顯而易見,他也陷入了昏迷。不做手術活不成了。
手術室的門砰地撞開了。巡回護士、麻醉團隊還有我的住院醫一起接來了病人。
“各位,”巡回護士說,“現在有一個問題。”現場的人,洗手護士、已經進手術室正在調閱CT片的住院醫師、麻醉護士還有我,齊刷刷地抬起了頭。
又怎么了?我心說。
“快速新冠檢測結果還沒出來。”
別忘了,這時快速又可靠的新冠診斷法才剛問世,疫苗也剛剛發放給老人和醫務人員。在這之前,每次要做急診手術卻不知道病人是否陽性,我們都會穿足防護裝備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但每次進手術室醫治創傷病例時,你總免不了想到這個決定可能威脅自己的生命。年初時,《福布斯》報道有近30萬醫務人員感染新冠,其中已有約900—1700人死亡。這些醫務人員大多在急診部和ICU工作,雖然不是我們科室,但你也很難不覺得自己注定要成為下一個統計數字。
然而這時,一年來的第一次,事情有了轉機。
“你們都打過疫苗了吧?”我問他們。
“打了。”房間里的每一個人都回答道。
洗手護士插進來說:“好,那大家開始吧。我們有活要干了。”
我們很快進入了熟悉的手術節奏,在深夜中忙碌起來。凌晨時手術完成,以往這時我們總是各自散去,先瞇一會兒再去查房或準備第二天的手術,但今天我們都留了下來,看著麻醉醫師抽出了男孩的呼吸管。當男孩聽從指令舉起雙手的三根手指并扭動腳趾時,我們都在口罩下笑了。那一刻,我們在男孩的床邊握手慶賀,世界仿佛又回復了正常。
但世界并不會那么輕易回復正常。
因為,新冠、新冠疫苗乃至基本公共衛生措施,都會將我們的社會深深撕裂。撕裂的雙方,是科學和反科學,是理性和非理性,是大城市和小城鎮——落在我自己身上,則是我的過去和我的現在。來參加期刊研讀會的神外住院醫都有心事需要交流抒發,好不致獨挑重擔;我也有這個需求。在寫完本書之際,回顧一路上的經驗教訓,下面的故事令我的內心感到無比沉重。
在寫下這段文字前的幾周,我在新聞里看到了納什維爾附近—所學校的校董會如何演變成了一場混亂。聽眾用叫囂蓋過了幾名醫務人員的說話聲,還跟著他們來到了他們的轎車旁。一位小兒重癥監護醫師在此地工作多年,挽救了千百名兒童的性命,她到董事會上發言支持在學校佩戴口罩的強制令,結果遭到一群煽動者的威脅,他們握緊拳頭圍住了她的轎車。
“我們知道你住在哪兒!我們會找到你!”
隨著疫情和此種政治態度的泛濫,這種態度似乎在美國南部特別集中,而這里正是我出生、長大并居住至今的地方。本書寫至此處,老家密西西比仍在這種致命病毒的疫苗接種率上接近墊底。而在現在的家田納西州,我只要環顧周圍的情形,就能認出異見者。他們很像我在阿拉巴馬州診治過的那些人,我在那里度過了執業的頭十年;他們也很像北卡羅來納的人,我在那里接受了住院培訓;或者說像密西西比州哥倫比亞市的人,那里是我小小的老家。從人口學角度看,這些人跟我多有多相似:白人,南方人,基督徒。他們許多都像和兒時我一起在后院玩耍、后來又一起上小學、一起參加中學舞會的朋友。他們也很像每次珍珠河(Pearl River)行將泛濫時和我的家人一起壘沙袋保護我們歷史悠久的內城的人,或是我祖母生病時帶食物探望她的人,還有我父母葬禮時前來致哀的人,以及無論順境還是逆境始終關愛著我們一家的人。我們也愛他們,無論過去還是現在。
我就出生和成長在這樣的地方,距密西西比和更南邊的路易斯安那的州界20英里。我們家挨著主路,是一座方形柱子撐起的白色房屋,寬大、溫暖,總是燈火明亮。我的父親、母親、兩個姐姐和我本人以各種組合在其中生活多年。在我寫作本書時,我的大姐伊芙正帶著幾只動物住在里面,標志著我們韋倫斯家的成員在那里生活超過了50年。以前我的朋友們常到我家來玩,近些年也來參加過兩場葬禮,他們總是親切地稱這所房子是一座家庭博物館。“你們這兒有導游嗎?”其中一個問我,“禮品店呢?”
不久以后,我就要把它打掃干凈準備出售了,這種感覺,就仿佛父母之外又有一位長輩將要離世。我的家族史和林林總總的記憶,都依然活在那里。也許有人想看看我二姐薩拉二年級在學校演戲時穿的那件手工縫制的多彩蝴蝶戲服,我母親保留了它,就放在整齊的閣樓上,罩了塑料膜掛起來了,衣架上還套著帶觸須的頭箍。有人好奇我在中學科技節上贏的獎牌嗎?它們都在我長大的那間屋子里,掛在墻上留作了永久紀念。補充一句:我父親最后一次入院之前,也是在這間屋里度過了最后幾個禮拜。20年后,同樣在這間屋里,我母親在家人的環繞中告別人世。對,這間我小時候生活的屋子,也是我雙親離世的地方。所以,在未來即將交付的時候,如果我必須再三回到這里治療內心的感傷,請允許我進去。要說再見真不容易。
兩個姐姐到我讀初中時都離開了家,于是我一開始是三個孩子中最小的,后來是兩個孩子中最小的,到最后又成了家里唯一的孩子。我們這一家人傾盡所能給予了彼此最大的愛。我們去當地的圣公會教堂禮拜,教友只有16個人,不同于當地動輒成百上千名教徒的其他教派(教友中包括我只有兩個小孩,我倆上的主日學校,班里全是成人,我們六年級就知道“末世論”[eschatology]這個詞了)。我們一家一有機會就一起度假,晚上圍在餐廳的桌子旁一起吃飯,每個人都有許多缺陷和心結,但當時我們只有朦朧的認識。那些年里,我們常在家里的車庫制作花車迎接兩個姐姐回家,一個姐姐的某位短期男友曾騎著摩托車來過我們家,我們也經歷過一些悲劇,足以提醒我們生命脆弱,要繼續堅持。
這是曾經的我,也是現在的我。不過,現在的我也有著別的面向。如今,我橫跨兩個世界——一個是老家密西西比的小鎮,一個是位于納什維爾范德比爾特大學的世界級醫學中心。置身于科學世界,我免不了會有人生的演化,科學、文化、宗教方面都是如此。這當然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故事,而是當今世界中許多人的經歷,無論他是否在醫學界。我們被家庭和家鄉形塑,被生命體驗鑄造,漸漸褪下迷信,明白在信仰之外也需要證明,現在也準備好了去改變社會。
隨著病毒的進犯,本應該針對泛濫的假消息和偽科學的不信任感,如今卻指向了醫生、護士和挽救生命的醫學研究者們,而這股狂潮大量來自我最熟知的那個世界。在《無處還鄉》(You Can't Go Home Again)中,美國大作家、北卡仔托馬斯·伍爾夫(Tho mas Wolfe)講了這么個故事 :某作家寫了本暢銷小說,書里專門編派老家,激怒了鄉親們。“無處還鄉”一名即由此而來。但伍爾夫還有一個意思,就是人不能向過去尋求庇護:“你回家……無法回到舊的習俗和套路中去,你曾以為它們千秋永續,但其實它們總在變遷——回家也無法逃回時間和記憶中去。”
如果有什么東西能抵擋向著時間和記憶的逃避,那就是科學。科學只遵守自己的時間表,不受多變的選舉、新聞周期、文化癖好及歷史負擔的左右。要讓真正有效的研究能以嚴謹的目光考察治療結果和并發癥,就必須等待一段時間,在那之后,你才能為某種干預手段找到最好的證據或否證。如今,各種答案都是全部信息立時奉上,我們已經習慣了這種方式:每天每時金句不斷,一篇報道的位置全取決于點擊量,而非它的真偽或對社會的實際價值。要開展合理的研究,至少是不想讓研究得出虛假甚至有害的建議的話,當然就不能一味地求快和取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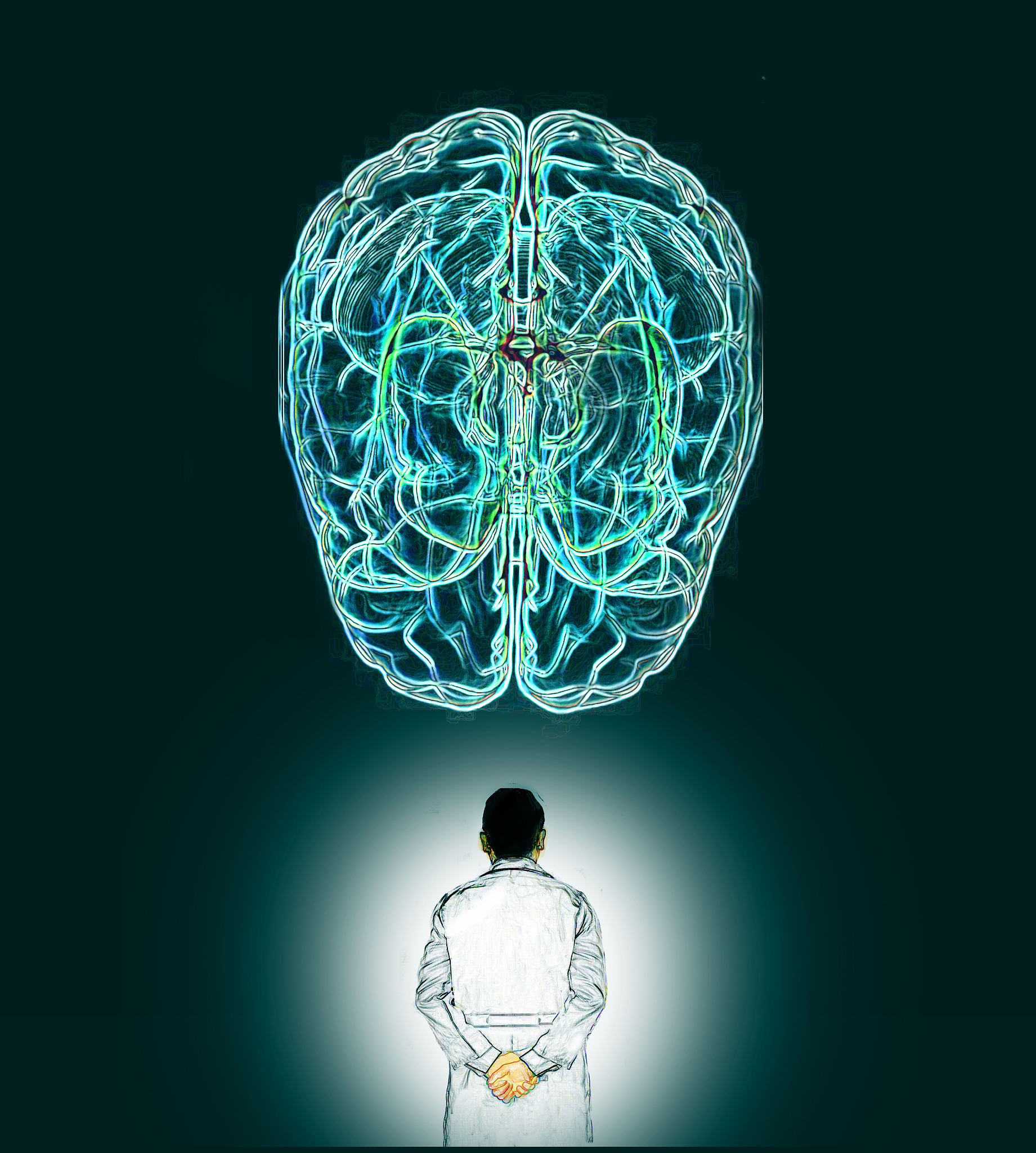
有一個例子很值得我們深思,就是早先所謂的兒童疫苗與孤獨癥有關,它現在已被駁倒。1998年,廣受尊崇的醫學期刊《柳葉刀》發表了一項小規模研究,指出在12名病患中,有8人身上出現了兒童疫苗與孤獨癥的意外關聯。這篇論文只是觀察性的,沒有證明任何因果性。但這項小規模研究卻幾乎顛覆了一個兒童疫苗項目,此前該項目已經功能性地消滅了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風疹和其他兒童疾病,杜絕了它們曾經對社會造成的嚴重沖擊。兒科醫生以前總是自動為孩子們接種疫苗,此時卻遭到了家長的堅決抵制。有一件事說來很是反諷:和今天相比,那一輪抵制往往來自政治立場偏向自由派的家長。對,當年的“疫苗猶豫”主要來自中間偏左的年輕家長,在當時媒體的夸大宣傳之下,在一篇篇家長為自家孩子的孤獨癥尋找原因的孤立報道中,在多年來某個不斷重復、一再回響的迷思之下,他們受害不淺。12年后,最初那篇論文的作者被發現偽造了數據,這項研究全系編造,整篇論文都是一個謊言。《柳葉刀》聲明,對該論文作完全撤銷,但危害已然造成。我們到今天仍在清算這一危害。
或許我也像托馬斯·伍爾夫筆下的主人公一樣,無處還鄉了。但另一方面,我也從未離開。因為上蒼眷顧、福氣不淺,加上優秀的父母和朋友,我有幸和本書記載的病人們一起走過了一段段旅程,而這一切就發生在南方的此地——離生我養我的家鄉只有短短的車程,但又仿佛隔了一個世界。總有一天,這場全球疫情將退入記憶。但是我們的文化中將會殘存它的影響,特別是對我們自己眼中的異類動輒痛加批判的做法。為自身福祉計,我們必須讓這種文化分裂也退入記憶:要忘記怒火;要記住無論你將羅盤上的什么方位稱作家鄉,我們都是共性多于分別;要記住我們往往有著十分相似的來處,最初的軌跡只有毫厘之差,后來才在生活中漸行漸遠。我們必須記住,寬恕是人類交往的重要一環。本書中的那些孩子及其父母所展現的風度和堅韌,我們人人都能做到。這也是我決定寫作本書的一個主要原因——伸出手來迎向彼此,分享生命深處的故事,說出我們的喜悅還有痛苦,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記得彼此都是人類,誰也不是生來更加低賤、疏遠或怪異,每個人都面對著同一批關鍵又難以估量的基本生存狀況。互相交談,說出自己的經歷,跨過隔閡去溝通,或許是我們的一味解藥。我相信,當我們相互幫扶一同走向治愈時,書中這些家庭以及其他類似家庭的經歷,將是不可或缺的參考。
* * *
那天晚上,我家的期刊研讀會臨近結束時,紙盤子都塞進了堆肥桶,食物也打包了準備拿去給值班的住院醫吃。參會的住院醫都發了言,只有一人沒說。我在討論中稍微領了領頭,但主要是閑坐著聽他們陸續發言。一名住院醫說起了一位老太太,她從急診部收治了她,在治療中產生了感情,她形容她有種“鄉下人的強壯”。老太太被診斷為惡性腦瘤,接受了切除術,最后卻過早死亡,這令這位住院醫師相當悲痛。“她是怎么從鄉下人的強壯,發展到丟掉性命的?是我們哪里沒有做到嗎?”她問道,“我們為什么離治愈腦瘤還那么遠?”
最后說話的一名住院醫羞怯地承認自己沒寫稿子,但是不是可以直接說說自己的經歷?他接著說起了一個二十四五歲的男青年,被送到急診部時已經半死不活。向腦干供血的主要動脈——基底動脈堵塞了,他就在這位住院醫師的眼前發作了中風,看樣子會大事不好。一般而言,人是無法從這樣的中風中恢復的,往往會陷入“閉鎖”:對環境還有意識,但無法活動或交流。這名住院醫當時正對血管內技術發生興趣,他迅速將病人送入造影室,隨即就和主治醫師一起打開了血管。“簡直是奇跡。”他說。說到這兒,他的聲音微微地有些顫抖:“術后病人醒了,”他頓了頓又說,“是徹底地恢復。”他的視線越過我們頭頂繼續向前,仿佛在看著我們身后上演的另一重現實。然后他收回了目光,重新聚焦。“我現在知道這是我想做的事了。”他說。他重新坐下,這次集會結束了。
我明白,這些年輕醫生必須把自己的經歷告訴彼此,為了理解每日里工作的意義,也為了厘清每夜帶回家中的感情。要想清楚這些事情并不容易。但這些住院醫師在說起自己的病人時,是懷著極深的共情、極大的尊重的。他們忘不了在將病人推進手術室或是看著病人術后在ICU中蘇醒時,病人流露的那種面對未知的勇氣。應該說,這些共同記憶給予了我們不可限量的幫助,使我們能與那些只憑個人無法抵擋的巨大力量搏斗。
在神經外科,我們和病人一起行走,一路從他們身上學到深刻的教益。我們明白了自身的脆弱,人生可能瞬息改變。這些對所有人都是永恒的真理,無論你走何種人生道路。要知道我們和我們所愛之人誰也無法免除痛苦,艱難本就是此生的必有特征。而從這種恐懼中獲得救贖的法門,就是我們所擁有的那種足以令人敬畏的堅韌、寬厚和愈合之力——要找證據,看看本書中的孩子們就行了。
我很榮幸能成為這些故事中的一個角色,也很感謝故事背后那一條條寶貴的生命,我感謝一位位住院醫師及同行,以及神外專業內外的其他使我保持清醒并向我提出寶貴見解的各位同事。我很珍視這個機會,能在這些了不起的孩子及其父母的生活中截取一段,傳遞給大家。并且告訴大家,在此生中,我們既在治愈別人,也被別人治愈。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