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藝術鄉建談 ‖ 何效義×劉建國:藝術介入鄉村需遵循地方特質
【編前話】
2021年,《崖邊》MOOK推出《崖邊2:藝術里的村莊》,梳理中國六個典型的藝術鄉建項目,共有12位作家、藝術家參與了討論。他們都有體悟大地和人民、反思資本主義危機、生發中國本土文明的摯真。近期,我們摘發部分訪談內容,以“藝術鄉建談”歸欄發布,以繼續藝術鄉建話題。
今天關注“安口窯復興實踐”。
劉建國是一位長期從事傳統藝術的藝術家,年輕時選擇了“北漂”。十多年之后,他逐漸意識到自己所選擇的道路并不是自己真心想要的原初。五年前,他回到故鄉,以復興“安口窯”為總抓手,開展了一系列藝術鄉建項目。
篆刻藝術家何效義對劉建國的實踐做了深入采訪。下面為訪談內容。

原安口陶瓷廠滯銷瓷
安口的失落,從丟掉“吃飯碗”一步步下墜
何效義:曾經的安口鎮因給大半個甘肅的隴東、隴中一帶生產百姓“吃飯碗”而輝煌,二十世紀后期隨之而來的是安口瓷器的減產下滑和閉廠休業,但這里有著獨特的民間和工業文化遺產,這跟你介入這里的鄉建是不是有某種情感上的存在?
劉建國:在1997年左右,我第一次到安口,那時候因為我剛從學校畢業,我媳婦是安口人,就到安口來過。那時候安口已經屬于滑坡的狀態了,很多工廠,廠礦已經開始倒閉。后來我成家的時候,因為我媳婦在安口小學里面,我岳父只有這一個女兒,他的想法就是讓我成家的時候,最好能到安口來辦結婚的儀式。我們家因為有三個小孩,我父母那時候也都同意,最后我結婚的時候就是在安口這邊結的婚。那時候的安口已經很蕭條了,但是跟現在比,又過了20年,跟現在相比完全又不一樣。所以對安口我實際上接觸的時間也比較早,也跟我媳婦,我岳父母到安口生活,有情感方面的關系。后來到安口來的就很少,但是安口這個地方總有一種東西吸引著我。可能就是這種氣質,這種復雜的,糅合在一塊的這種工業物質遺產,混亂有序的那種建筑,攪混著不一樣的氣息,讓人迷戀。不完全像周邊縣里面的氣息,所以比較吸引人。
何效義:農村人口追求“城市化”的趨向不僅表現在農民進城打工,他們掙了錢的目標是在城里住進高樓。我這些年回老家白莊時發現,村民開始用“混凝土”來建房,原先木格子的窗戶也不用了,換成鑲玻璃的鋁合金門窗,它的內生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那么在這樣一種背景下,鄉建的核心在哪里?有些專家也指出除了單向的面貌重建,更重要的是心靈的重建,如果要挖掘民間動力?安口還有民間動力嗎?
劉建國:現在農村人追求城市化的趨向確實是越來越強,城鄉結合完全打破了鄉村原有的結構,價值觀的混亂、子女教育、婚配觀念等確實是鄉村存在的問題。我們也做過調查,包括我和程立仁之間的接觸,調查木板年畫中也發現了很多鄉村的問題。現在基本上都是留守老人、留守兒童,青壯年都生活在城市里打工,或者他回來,他也不愿意住在農村。農村的孩子要成家,必須要在城里買房、買車,基本上都是這樣的標配條件,你沒有這些東西,子孫兒女的媳婦都娶不上。也確實是這樣的,農村已經完全失去了過去農村的生產模式和生活結構,基本上是留守的人在守護著農村,是這種狀態。
我覺得每個地方都不一樣,你比如說別的村莊可能是手工業生產,主要是去幫助他們建立審美,幫助他們建立對過去歷史的重新的書寫和梳理,幫助他們通過現在的媒介平臺把這個東西推向大眾,或者推向小眾。對接職業設計師,幫他們做產品包裝和推廣,或者深挖掘。
安口完全不一樣,他的很多東西交織在一起,他的核心主要是沒落之后人的自信心的喪失和尊嚴的坍塌,這是對他們打擊非常大的,就是我們說的人窮志短。安口人過去經歷過輝煌,他們的工業文明來得那么早,他對外面的新鮮事物的接觸也非常早。你比如說6.26北醫下放的那些專家、教授,當時到安口的時候,他們帶著縫紉機、自行車,還有德國產的照相機,而且有很多當地人從沒見過的東西都帶到安口來。他們帶著縫紉機來了之后,安口鎮里的老百姓天天敲他們家的門,問他能不能做衣服。你想想這是在1960年代,1965年左右,很多新的東西人家都帶到這里。
再早一點,民國的時候,像電磁場,有外國留學的人到這兒建廠子。他們很早之前接觸的是外面的新知識,一直在和新鮮的事物打交道。陶瓷業生產的時候,不光是把自己生產的陶瓷從這兒賣出去,還有一個交換的過程。當地人,或者附近的人,還有外面的客商把新的觀念,新的產品,新的文化帶到安口來,再把安口的陶瓷轉換出去,他們很早都在接觸外面的世界,安口不是一個封閉的地方。但是現在安口沒落了,曾經的這些東西已經早被人遺忘,而且這些東西你也不能光給年輕人說,說教并不能建立起他們的自信心。他們覺得安口已經這樣了,外面那么發達,每個周邊的縣城都發展得比安口好。過去安口的行政中心華亭,過去比安口差太多了,就是一個小縣城都升成縣級市了。
安口過去完全是一個不一樣的地方,他集合了全國300多個縣里的人,而且各種身份的人在這兒來參與到安口的建設,參與到安口的生活里面,所以他完全是不一樣的狀態,他的核心比較復雜。我們主要是把過去的東西整理出來,用影像或者照片,或者出版物的方式和口述史的方式復原一部分現場,把那些珍貴的文獻收集起來,順便再復活安口窯的燒制。這樣就能幫助安口對接到有利資本,合理激活安口的動能,從鄉村美學、兒童教育、生產實踐、景觀營造等領域做一些項目,對安口將來的發展蓄積一些能量。
安口目前沒有大面積開發,當然過去也因為各種原因拆除了一部分遺產,但還保留了一些建筑,這些遺產其實就是安口最飽滿的原動力。
藝術介入鄉村主要取決于當地的地方特質
何效義:從現階段我們所看到的鄉建,基本是旅游和建筑面貌突顯一種新農村的環境設計,這顯然是走不長的,前面別人走過的路你可能是走不成,那么新的路如何走?當然你是以藝術家身份介入的?藝術家介入的身份是否與當地傳統融合?
劉建國:是的,別人走的路,我們肯定是走不成的,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我覺得,他的特質是什么,你得按他的特質去做,你不能用你原有的知識或特殊的身份去一意孤行。
一個藝術家,你如果只是關注藝術這一塊,或者是以藝術固有的身份來做這個,限制了自己的身份就局限了。這個工作是非常復雜的,你怎么樣去尊重它,不要利用它,不要欺騙,你怎么樣跟它合理互通、平等交流的一個合作過程。如果帶著偏見和固有的知識經驗,很難融入進去。那我們目前做的就是安口的幾大塊,一個是陶瓷行業,又牽扯到安口窯的復蘇,因為安口窯從2000年前后,陶瓷廠倒閉之后,就等于說安口窯實際上已經消亡了。我們所說的安口窯就是過去,目前沒有任何生產,只有一個生產砂器的,是一個私人的廠子還在做。他是用一種新知識在做,但是他所用的材料主要是安口本地的砂料為主。
我們目前通過對老匠人的走訪和搶救性的挖掘,打算把安口窯復蘇。能不能幫助把這個工作完成,目前也存在很大的困難。因為窯的燒制是一個持續的過程,我們考察過之后,柴窯一年燒制費用可能得20、30萬,還有前期的人工,基礎建設等等這方面成本也是非常高。當前還沒有合適的資本介入,所以目前只能是對這些老手藝人做一些深入的調查,等待機會吧。
如果政府力量或者說資本能介入的話,這個事是可以做的,這是一方面。還有一方面是工業的遺產,安口廠礦過去非常多,有電磁廠、陶瓷廠、水泥廠、磚廠、電廠、燈泡廠等,燈泡廠的前身是平涼玻璃廠。而且這里不光有煤和陶土,還有很多別的礦產資源,現在雖然說工業時代的這些廠子都倒閉了,但是他遺留下的遺產,完全可以做工業旅游,做遺產文獻的展播,還可以嘗試做一種新的旅游的方式或者改建一些不同的生活社區,這些都是有合理的利用價值的。
再就是原來“三線建設”這塊,有一些軍工廠,老工人,軍工二代,還有一批軍工二代恢復高考制度之后這些人都考出去了,有的還出了國,這都是一批很豐厚的資源。他們對這個地方的情感是非常深厚的,每年都有人回來看自己生活和工作過的地方,可以很好地把他們對接起來。這個點不能去利用老工人的情感,可以在這里改建幾個配套的設施,做幾個文獻展覽室,把現有的遺址保護起來,讓老工人“回家”時有個給他們提供回憶的場域和物件。這可能是一種精神上的安慰,也是讓死文獻活起來的辦法。

安口陶瓷堆積層殘片
何效義:我記得我上次田野考察的時候,林興旺說村莊里的人大多是移民來的,我記得是他講的,你再靠實一下,如果是這樣,就可以討論一下新的問題,即當地村民不一定和內部有關,它在輝煌期是不是和外部及整個世界的物質產生了聯系?
劉建國:是,興旺說的沒錯,安口人的結構非常特殊,非常復雜,基本上全國各地人都有。1980年的時候人口普查,好像說安口有340多個縣的人口。安口移民不光是從解放初期,可能從古代就一直在不停地移,人口在不停地變換,一直有新鮮的血液在輸入,所以不是完全靠安口和華亭的原住民。其實安口、華亭的原住民也不多,近靠關山這里的水也不好,過去各種地方病也多,醫療條件差。這個地方有煤礦,吸引了很多外面來的人,包括前面說的“三線建設”來了很多人,那塊要好幾萬人,在安口的土谷堆,石堡子。所以安口確實不同于別的地方,這里的人經過不同知識的漂洗。外面來的那些人不都是普通的工人,有很多是專業技術人員,你比如說醫院里面來的那些很多都是研究尖端微生物,很多教授,各種各樣的專家都有。軍工廠也是,都是當時這些行業里的骨干,還來了很多全國的學生,安口有非常復雜的人員構成,他在輝煌的時候,確實是和整個世界產生了聯系。不是老家的農民,除了種地,可能見到的是親戚、鄰里,他帶來的知識是有限的。安口完全是不一樣的,他輝煌時期確實是周邊這些地區都不能比的,所以人的這種氣質也是完全不一樣的。
人上不上學不是很重要,但一定要有知識
何效義:最后一個問題,我們都中年了,不得不面對現實生活中家庭的種種無奈和困惑,比如孩子的教育問題,你是如何面對這個現實的?我知道你的兒子沒有完成初中學業,也沒有接受體制性的高等教育,你妻子又是一名教師,我想聽聽你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
劉建國:這個問題也是比較尷尬的一個問題,因為我的兒子念到初一之后就沒有再正式上學。這個原因也是各方面造成的,也不是說我自己主導這么去做的,當然與我對體制學校隱性的對抗有一點關系,不能說完全沒有關系。當時我在北京,每年的暑假我老婆跟我兒子都會到北京來度暑假。因為我長時間在北京呆了十幾年,為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很自私地在那兒奮斗,漂著。
過去我的生活是比較寬松的,那時候他們來每次走的時候都是哭著走的,我也心里很難受,我就想,實在不行就把小孩弄到北京去讀書,我老婆那些年也是單位請假,在北京也呆了一段時間。他們對大城市跟我不一樣,他們可能更迷戀大城市那種模式和生活,很多東西對他們來說是非常新鮮,有吸引力的,所以他們對北京的向往跟我不一樣。當然我一個是待的時間長,再一個可能我從小不喜歡在人多和非常吵雜煩鬧的地方待,我還是喜歡處在偏僻的地方,安靜的地方。那時候,他們來北京搞得我心里邊也很動搖,就慢慢想著把小孩弄到北京去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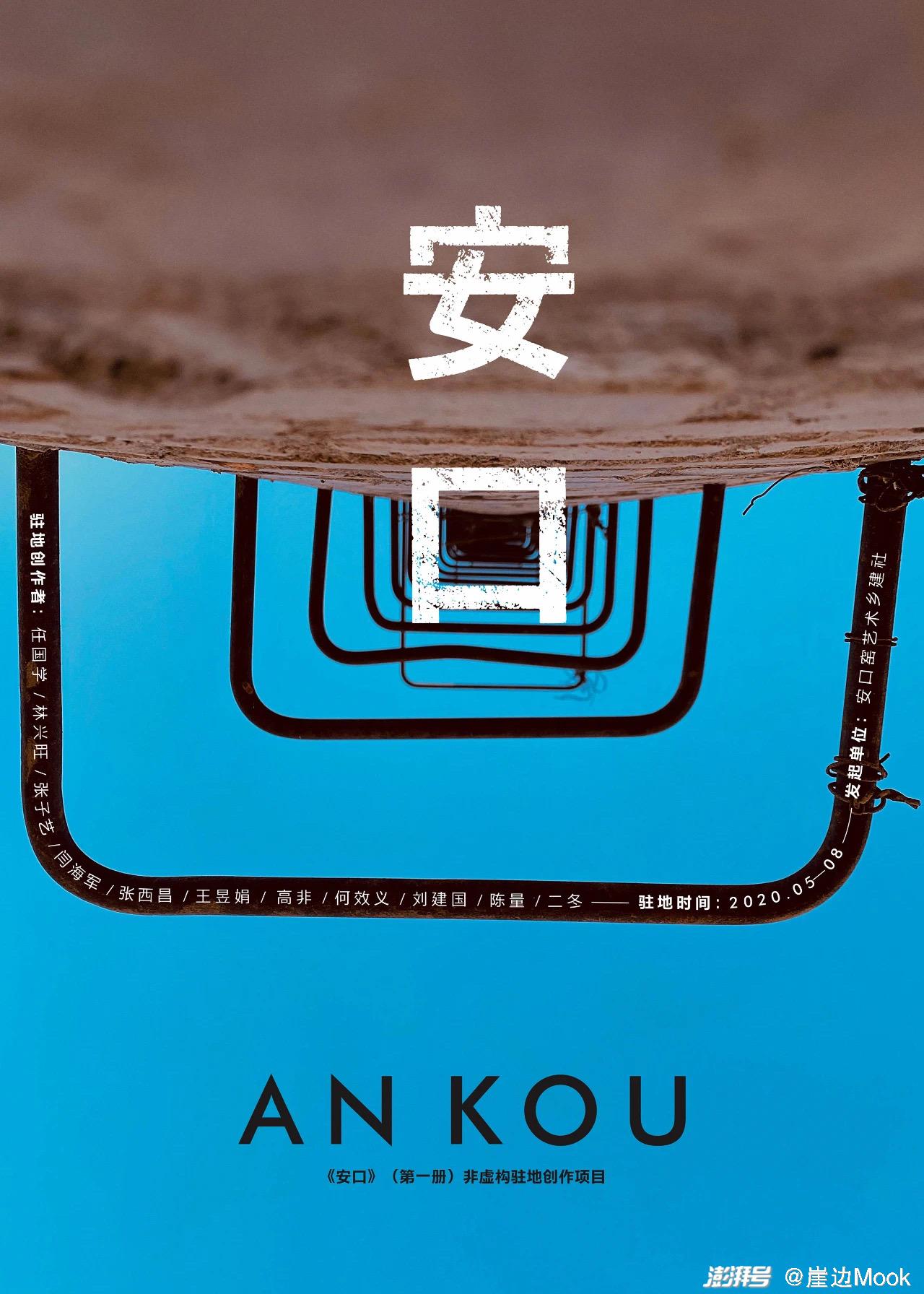
海報
在這個過程中,就發生了我的小孩讀初一的時候在北京上了一年學。要去體制內讀很麻煩,就想著去讀一個私立的學校,結果讀得也不理想。結果小孩對上學也有厭倦,對那個環境很排斥。后來,我想了一下,覺得自己也是太草率了,考慮這些問題考慮得太荒唐。導致小孩回來之后,他的同學上初二,他也不愿意再到初一去讀。然后就在家里慢慢讀書,我當時教他學點書法、繪畫之類。在這個過程中,書畫市場已經開始滑坡,微拍剛開始出現,人對這個東西又比較新鮮。過去書畫市場非常畸形、離譜。微拍出現之后價格低,人有一種對新事物的好奇感,所以我兒子那時候一邊畫畫,一邊學習,我還幫他在微拍上去賣一些作品。搞得他那兩年收入也挺好,一個小孩子一年賺1到2萬塊錢,他對上學,對別的東西好象突然之間沒有啥興趣。各種各樣的原因,造成我的小孩沒有上學。緊接著微拍像泡影一樣就幻滅了,他突然之間感覺自己沒有希望,他將來的生活的立足點在哪里?他也開始出現這種焦慮,這個事情當時其實害了他。
我對這個事情相對來說比較淡定,我覺得人上不上學不是很重要,我覺得一定要好好讀點書,學點東西,人只要有知識,對人生和價值觀有一個清晰的判斷,對生命有一個明確的認知,這樣的話人的生命方向也能找到,會活得有使命感。
可能我作為一個成年人的思考和小孩不一樣。
我兒子其實這中間情緒是非常不穩定的,出現了很多他自己無法解決的問題,但是隨著這兩年他年齡大一點,這些問題基本上通過自己的閱讀,通過自己思考和身邊的同學、朋友的交流、對照,他對這個想得很開,所以現在對這些事情處理得挺好。
現在我們一起做鄉建,他每天也是畫點自己喜歡的油畫,畫點插圖,寫點文字,讀點書,該玩的玩,該做什么做什么。(訪談內容摘自《崖邊2:藝術里的村莊》)
相關書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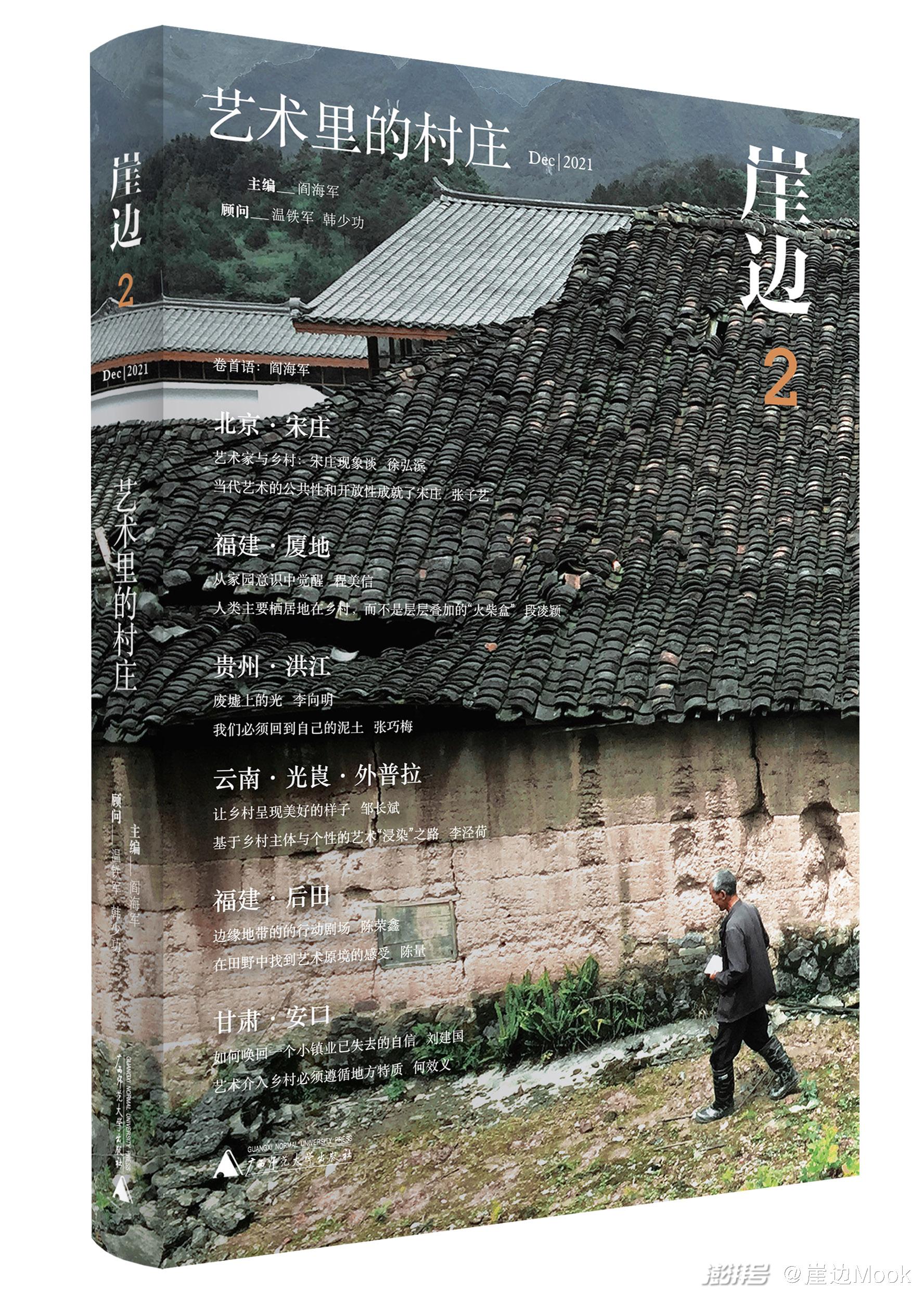
主編: 閻海軍
出版社: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副標題: 藝術里的村莊
出版年: 2021-12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