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徐圖之︱用筆與鋼鐵書寫的韓國現代史

2017年,既是韓國反對威權政治的六月抗爭勝利暨確立民主化的1987年體制三十周年,也是創造韓國經濟成長奇跡的樸正熙誕辰一百周年。然而,在韓國國內,前者的紀念活動此起彼伏,從官方到民間,紛紛以慶祝儀式、紀錄片、電影及書籍等方式撫今追昔。后者則顯得頗為冷清,原定的官方紀念活動因樸正熙之女——樸槿惠總統被彈劾罷免而紛紛取消,只剩民間擁護者自行出版的一套九卷本《樸正熙全集》聊堪慰藉;另有一部名為Miss President的紀錄片選在樸正熙遇刺身亡的10月26日公映,但僅有六千七百四十九人觀看,與前一年同一天上映后獲十九萬人觀看的前總統盧武鉉紀錄片《武鉉:雙城記》天差地別。盡管兩片都是拍給各自粉絲看的——Miss President甚至兩面不討好,片名盡管一語雙關,既指未婚的女總統樸槿惠,又指有人懷念前總統樸正熙(他們結成了粉絲聲援組織“樸愛會”),但有觀眾認為該片美化“樸愛會”,也有人聲稱它是批判“樸愛會”。由此可見,韓國社會對民主化(以盧武鉉為代表人物)與產業化(以樸正熙為代表人物)的看法兩極分化,似乎兩者水火不容;盡管就同樣死于非命的結局而言,他倆是韓國總統中唯二稱得上悲劇的人物。

紀錄片Miss President海報
韓國首爾大學歷史學者樸泰均顯然也注意到了上述傾向,他最近在中國出版了《韓國現代史:十個代表性事件的深度解讀》一書,可以使讀者對此有全新又全面的認識。該書韓文版在韓國光復七十周年、朝鮮戰爭爆發六十五周年、韓日協定簽署五十周年的2015年出版,自然包括了這三大事件。但不同于2014年在中國出版的前作《那時今日:透過事件解讀韓國現代史》,本書原書名是???? ?? ???,即“樸泰均的issue韓國史”,issue即問題,但如果譯成“問題韓國史”給中文讀者感覺比較奇怪,叫“議題”則較好。書的副標題?? ??? ??? ??? ??? ??意即“即使只有兩人聚在在一起,意見也會截然不同的現代史爭論點”,“議題”比“事件”涵蓋面更廣,更適合“深度解讀”,尤其相對以月份為章介紹韓國史及世界史的《那時今日》而言,所以中文版的副題半對半錯。
此外,這個副標題也忽略了韓文語境中的“雙方意見的爭論點”。因為在韓國社會,除了一般國民對同一歷史議題意見分歧外,學術界和教育界觀點也是分裂乃至對峙的:比如受惠于樸正熙經濟發展的人很少會講他的壞話,而在他統治時期受盡打壓乃至牢獄之災者自然不會講他的好話,這都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而學者和教師本應該彌合歧見,促進國民融合,但因為政見分歧反而將偏見帶入學術與教學:要么只講樸正熙的產業化功績,忽略他的執政劣跡,要么一味抨擊樸正熙是獨裁者及萬惡之源,抹殺他對韓國的貢獻。結果形成了教育界、學術界在歷史教科書及專著中壓倒性地批判樸正熙,而大眾傳媒尤其是《朝鮮日報》《中央日報》《東亞日報》這三大占據韓國輿論高地的媒體集團基本上肯定樸正熙的局面。
同樣畢業于首爾大學的學者金正仁《歷史課的攻防戰》一書詳細介紹了韓國的上述歷史內戰,她聲稱,“韓國的歷史學者之間幾乎沒有任何矛盾,一致團結起來對抗保守的政治勢力與新右派史觀”(見該書第6頁)這句話本身就自相矛盾:難道持新右派史觀的學者就不是韓國的歷史學者嗎?難道在人數上占優勢的主流歷史觀點就是正確的嗎?學術觀點難道是像選舉那樣按支持者多寡定優劣的嗎?
所以,樸泰均在這本《韓國現代史》前言中就對韓國把歷史作為高考必考科目提出擔憂:如果學到的是錯誤、歪曲的歷史,那么反倒弄巧成拙,還不如不學。他指出,社會上流行的歷史大部分都是政治化、神化的故事,是為了某些人的一己之私而編湊出的結論。從后面的正文可以看出,他說的“社會上”既指被左翼進步派把持的歷史教科書,也指右翼保守派的媒體報道(包括網帖)。因此,他于2014年在韓國CBS電臺錄制了十個月的“樸泰均說歷史”節目,以此來使受眾擺脫神化歷史觀,本書就是以節目為出發點創作完成的。
需要補充的是,這不是樸泰均第一次在大眾媒體上傳播歷史,身為歷史學者的他,除了完成多本韓國近現代史專著如《友邦與帝國:韓美關系的兩個神話》外(《那時今日》是在《中央日報》的專欄結集),還曾擔任七十九集KBS歷史紀錄片《人物現代史》及一百集的MBC歷史紀錄片《現在可以說了》的顧問委員,這兩個互相競爭的節目于2005年先后播完,后者更創下平均百分之十的高收視率(見《歷史課的攻防戰》第25頁),現在每周日還在《京鄉新聞》連載歷史專欄。
從樸泰均活動的媒體政治光譜來看,他得到了左中右派的一致認可。僅從書中舉一例,以見他論證的全面客觀:二戰后韓國要求日本賠償損失,日本則稱應由韓國賠償日本,乍看這是倒打一耙,但樸泰均指出,韓國當然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日本就強征慰安婦、勞工等進行賠償,同時戰后初期駐韓美軍政廳由于缺乏經費,不僅沒收了日本在韓國的公共財產,也沒收了日本人的私有財產,后者是違反國際法的,這些財產后來都移交給了韓國政府,所以作者認為日本的主張并非無中生有,但由于美國政府也不愿出面解釋,此事成為日韓談判中的一大癥結。樸泰均并沒有因為自己是韓國人就一味為韓國辯護,而是根據國際法和歷史資料講清了事件的是非曲直,這是相當難能可貴的。類似例子還有幾個,感興趣者可自行查閱。

言歸正傳,樸泰均《韓國現代史》討論的十個議題,以李承晚時代開始,在樸正熙時代落幕時結束,以章節篇幅而論是四比六,即更側重于樸正熙時代。1961年樸正熙率領一群少壯派軍人以“軍事革命”為名發動五一六政變奪取了政權,當即發布了六條“革命公約”,到1979年他遇刺身亡,這六條公約中有四條兌現,成績在及格線以上,作者也認為執政初期的樸正熙政府頗具革命性。
就兌現的而言,“五一六革命公約”第一條是將“反共”理念落到實處,這條執行之嚴到了寧枉勿縱的程度,所以制造了一批冤假錯案,這是它的副作用;第二條是搞好與美國等友邦的關系,這是樸正熙成事必須的外部條件,不僅關乎美國援助的獲得、駐韓美軍的去留,而且是其后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的成敗關鍵;然而,樸政府與美國肯尼迪政府就還政于民問題、1968年青瓦臺遇襲與“美軍普韋布洛號被扣危機”的處理、與卡特政府就韓國核武開發計劃及人權問題的分歧,使兩國關系一波三折,但還不至于到翻臉的地步。
為了修補關系并防止駐韓美軍移防縮編,1965年樸正熙向越南派兵以支援當地的美軍,此舉據說起初是出于韓國自身的安保理由,但樸泰均統計了1965年至1968年朝鮮半島發生軍事沖突的次數,發現激增了十幾倍,因此他認為派兵并沒有達到目的。不過,隨派兵而來的軍費補貼、帶動出口的“戰爭特需經濟”,著實讓韓國發了一筆戰爭財。此外,1965年,令二戰后僵持二十年的韓日關系正常化也是樸正熙的一大政績,雖然也冒了被發起示威游行的學生和在野黨指罵為“親日派”“賣國賊”的風險,樸正熙在首爾實施“衛戍令”穩住了局勢,這一招以后被他屢試不爽,但到了1980年代已捉襟見肘。
兌現得比較徹底的是公約的第四、五條:解救在貧困與饑餓邊緣的百姓、解決民生問題、重建國家自主經濟,為完成統一而加強和鞏固國家實力(主要指國防安保)。作者特別指出,對韓國經濟增長有兩種謬論:一是經濟增長必須依靠獨裁統治,二是今天韓國經濟中的一切問題都是由樸正熙引起的。他的反駁是:實現民主化后的1988年至1992年,是韓國經濟增長率和人均GDP增長最快的時期(見本書第193-194頁);而歷來批評樸正熙只扶持財閥的人可以看看1972年他實施的“八三措施”——韓國政府強制凍結民間貸款,并規定企業要把民間貸款用于生產活動,此舉顯然違反市場原則,但它使中小企業可以暫時不用還貸,很大程度緩解了它們的負債問題。
樸泰均把樸正熙時代劃分為三個階段:政變初期傾向于改革、1960年代中期以后強調在控制社會的基礎上發展經濟、1970年代初期以后選擇以鐵腕而非民主方式應對暗流洶涌的社會經濟問題。他認為,歷史學家的責任是呈現客觀事實,而對歷史人物的具體評價應由個人進行,因此反對以“一言以蔽之”的方式評價樸正熙。

言既至此,就不得不提跳票的兩條公約:第三條:整頓國家腐敗和舊惡,喚醒頹廢已久的國民道德和民族正氣;第六條:完成上述課業后,我們準備把政權移交給有良心的政治人并回歸本來崗位。諷刺的是,腐敗和舊惡并沒有被一時的霹靂手段肅清,反而隨著經濟成長而復燃并增加新惡;而還政于民的承諾則變成軍人脫下軍服從政。不過,一旦戒嚴狀態下對政治活動的限制解除,政治家就積極重組政黨參與選舉,到1978年國會選舉時,通常在樸正熙指定三分之一議席之外,能與在野黨平分另外三分之二席位的執政黨竟然大敗,結果失去了對國會的控制權,可見即使在最寒冷的第四共和國時期,不死的韓國民心思變。這也證實了作者的論點:韓國現代史并不是按照建國、產業化、民主化、先進化這樣的直線順序機械式前進的,產業化與民主化并非天然對立,而是相輔相成的。請看樸泰俊本人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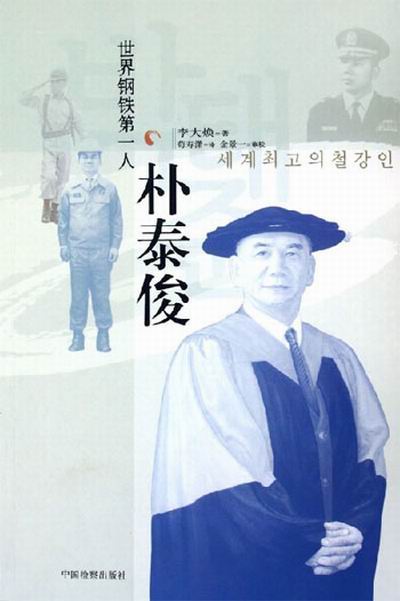
李大煥著《世界鋼鐵第一人樸泰俊》
沒錯,這回是樸泰俊用鋼鐵而非樸泰均用筆書寫的韓國現代史。這位參與過朝鮮戰爭及五一六政變后的國家再建最高會議的軍人,用韓國人視為屈辱的“對日請求權資金”(即日本賠款)中的一億多美元興建了浦項制鐵,該公司后來與他創辦的浦項工大一起名滿天下。
按理說,身為樸正熙的前部下和軍校弟子,當1969年中央情報部長金炯旭派人找他在支持樸正熙三選改憲的聲明上簽字時,樸泰俊是很難拒絕的,但他回復:“光是制鐵所就夠我忙的了,我不參與政治”,樸正熙知道后也沒怪他(見 李大煥《世界鋼鐵第一人樸泰俊》第194頁);1971年總統大選前夕,身為國企社長的樸泰俊五次抗拒了樸正熙所屬的執政黨財政委員長要他讓特定企業中標,進而索取回扣用作選舉政治資金的壓力(同上書222-223頁)。如果這些只是與威權政治保持距離、被動地說不的話,那么接下來的故事,則是這位韓國產業化的代表人物對韓國民主化事業的積極支持。
1987年,執政黨代表(黨首)盧泰愚為回應六月抗爭,發表了包括年底舉行總統直選的“6·29宣言”,而在樸正熙時期被《東亞日報》和《朝鮮日報》解雇的記者們,此時在醞釀眾籌創辦新報紙《韓民族日報》,他們找到浦鐵常務理事李大公,希望浦鐵對募股辦報活動提供協助。創辦這份報紙的,是當時的現任總統(全斗煥)下任總統(盧泰愚)視為眼中釘的勢力,身為國企社長的樸泰俊的反應卻是:“這個國家也需要那些人的聲音啊!”他讓李大公想辦法,后來通過子公司、合作公司入股的方式為《韓民族日報》募集了五億韓元,占該報創刊基金的十分之一。李大公還記得,1976年他建議公司聘用被《朝鮮日報》解雇的攝影部長時,樸泰俊也是欣然同意:“照片拍得好就行,盡管聘用。”(見同書386頁)
樸正熙死后不到一年,他通過兩次政變創建的國家也被全斗煥用兩次政變取代,這就是第五共和國。能夠忍受樸正熙十八年威權統治的韓國人,這次連全斗煥八年的統治也受不了了,因為把“實現社會正義”口號刷得到處都是的第五共和國,不僅爆出多宗社會不義事件,后來連最高領導人的親屬乃至他本人都卷入了巨額貪腐案件,這是樸正熙時代未曾發生過的。然而,即使韓國全國掀起了反抗軍警催淚彈的街頭運動,如果執政者不讓步、反抗者不妥協的話,韓國的世道也不會改變。
這就是韓國1987年體制的由來,韓國那一年同時實現經濟高增長和民主化,在世界上也比較少見。三十年過去了,韓國已躋身發達國家,民主體制是否鞏固了呢?從最近曝光的“機務司戒嚴文件”可見端倪:機務司令部的前身就是全斗煥發動政變時任司令官的保安司令部,作成于2017年3月的戒嚴文件顯示,一旦3月10日憲法裁判所否決了國會對樸槿惠總統的彈劾案,而燭火示威的群眾仍不散去的話,就會在韓國全國戒嚴。
目前機務司已解體并改名重編,而獨立調查結果還沒出來,雖然兩派都有說法:一方說這文件只不過是停留在紙面上的應急預案,另一方則堅持這是有預謀的政變計劃。然而,從文件可以明確知道,戒嚴的前提是彈劾案被否決,這說明至少機務司仍然尊重憲法裁判所的裁決,而不是相反——在彈劾案通過后戒嚴,那就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政變了。所幸,這一幕并沒有發生。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