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杜尚與日本美術(shù)”昨起東京展出,首次呈現(xiàn)比較二者關(guān)系
“杜尚與日本美術(shù)”10月2日在日本東京國(guó)立博物館開(kāi)幕。“澎湃新聞·藝術(shù)評(píng)論”獲悉,此展是日本東京國(guó)立博物館(Tokyo National Museum)與美國(guó)費(fèi)城藝術(shù)博物館(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之間的交流展,第一次將杜尚與日本美術(shù)進(jìn)行比較,旨在一邊走近和了解杜尚的新式思維,一邊探索鑒賞日本美的新方法。
展覽分為兩個(gè)部分,第一部分“杜尚 人與作品”呈現(xiàn)來(lái)自費(fèi)城藝術(shù)博物館的約150件杜尚油畫(huà)、“現(xiàn)成品”(Ready-made)作品、照片資料等,介紹杜尚的理念與思維探險(xiǎn)。第二部分“通過(guò)杜尚重新解讀日本藝術(shù)”,通過(guò)展出迥異于西方、誕生于東方文化的日本美術(shù)作品來(lái)引導(dǎo)觀眾思考日本美術(shù)的定義與價(jià)值,提出鑒賞日本美的全新方法。
杜尚 人與作品
畫(huà)家杜尚
此章將回顧1902年至1912年期間,畫(huà)家杜尚所作出的成就。這一時(shí)期,從印象主義到象征主義,再到野獸主義,杜尚在自己的作品中嘗試性地融入了各種前衛(wèi)的元素。本章著重介紹杜尚十五歲的作品《布蘭維爾的風(fēng)景》(1902)、因?qū)αⅢw主義獨(dú)到的闡釋而使其備受關(guān)注的《下樓的裸女二號(hào)》(1912)、最后的繪畫(huà)作品《新娘》(1912)等在1902-1912期間杜尚作為畫(huà)家時(shí)所創(chuàng)作的油畫(huà)作品。除此之外,展覽還將陳列杜尚幼年時(shí)期的照片,出生家庭、故鄉(xiāng)的風(fēng)景照片,家人的肖像照等,力圖將畫(huà)家身份的杜尚更立體地展現(xiàn)在世人面前。

作品以分解的形式呈現(xiàn)裸體從臺(tái)階上下來(lái)時(shí)的動(dòng)態(tài),于1913年發(fā)表。
能否創(chuàng)作“非藝術(shù)”作品?
此章將一覽1912-1917年期間杜尚的活動(dòng)軌跡。叛離正常“繪畫(huà)”創(chuàng)作的杜尚,獨(dú)自探索用其它手段表達(dá)對(duì)藝術(shù)的見(jiàn)解,自身也借此獲得了全新的起點(diǎn)。杜尚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新娘甚至被光棍們剝光了衣服》(通稱《大玻璃》)(1915-23)便是在這一時(shí)期構(gòu)想而成的。
另外,被統(tǒng)稱為“現(xiàn)成物藝術(shù)品”的系列作品的創(chuàng)作也可追溯回此階段。“現(xiàn)成物藝術(shù)品”是與“創(chuàng)作”相對(duì)的概念,它將某種功能性物品從日常的用途中分割,并將其定義為“藝術(shù)品”。
在本章,通過(guò)圖示板介紹在美國(guó)費(fèi)城的原作《大玻璃》的同時(shí),展會(huì)也將展出東京大學(xué)駒場(chǎng)博物館收藏的東京版《大玻璃》復(fù)制品,通過(guò)鑒賞作品來(lái)思考杜尚的創(chuàng)作意圖與作品本身的涵義。

杜尚曾說(shuō)過(guò):“看著車輪轉(zhuǎn)動(dòng),內(nèi)心也變得無(wú)比平和。”

杜尚在瓷制男用小便池上簽上R.Mutt的化名后拿去參展,遭到拒絕。
女性身份“羅絲·瑟拉薇”
此章將介紹20世紀(jì)二三十年代期間在巴黎滯留、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在紐約避難的杜尚。1921年,杜尚對(duì)外宣稱今后自己的職業(yè)方向要從藝術(shù)轉(zhuǎn)向國(guó)際象棋,之后便以專業(yè)象棋手的姿態(tài)樂(lè)在“棋”中。同期,杜尚開(kāi)始以“羅絲·瑟拉薇”的女性身份出現(xiàn)在大眾視野。以這個(gè)人格為根基,杜尚嘗試起俏皮話、雙關(guān)語(yǔ)等語(yǔ)言游戲,投身到了全新的創(chuàng)作領(lǐng)域。另外,憑借在透視法、視覺(jué)等方面長(zhǎng)期累積的研究經(jīng)驗(yàn),這一時(shí)期的杜尚也涉足了機(jī)械式繪制方法。
另一方面,杜尚在紐約的“達(dá)達(dá)”反藝術(shù)活動(dòng)中表現(xiàn)十分活躍。這類活動(dòng)、交流,最終在達(dá)達(dá)中心人物之一的攝影師馬雷的幫助下,以前衛(wèi)試驗(yàn)性電影的形式在1926年得到了呈現(xiàn)。
20世紀(jì)三十年代中葉,杜尚開(kāi)始重新思考如何復(fù)制自己的作品。在這種興趣的驅(qū)動(dòng)下,誕生了眾所周知的《手提箱式盒子》(1935-41)——一個(gè)微型可攜帶的美術(shù)館。
四十年代,杜尚化身展覽會(huì)的策劃人,專注于推介年輕藝術(shù)家。他以策劃人、管理人的身份,而非藝術(shù)家的身份活耀在幕后,收獲了名聲。杜尚拒絕以藝術(shù)家身份參與藝術(shù)活動(dòng),用自身的行動(dòng)打破了固有的對(duì)藝術(shù)、對(duì)藝術(shù)家的界定。

杜尚將自己過(guò)去的作品微縮后裝入皮革制手提盒子內(nèi)。
《遺作》 欲望之女
在最后一章,我們將解密藝術(shù)界、文化界的傳奇人物杜尚的最后20年。
《給予:1、瀑布 2、燃燒的氣體》(通稱《遺作》)展示了杜尚與費(fèi)城美術(shù)館的關(guān)系。這副作品是杜尚預(yù)設(shè)自己會(huì)把它陳列在費(fèi)城美術(shù)館內(nèi)的《大玻璃》旁邊而創(chuàng)作的,是杜尚的臨終遺作。整整20多年,杜尚對(duì)外保密,一個(gè)人默默地制作了《遺作》里的每一個(gè)配件。杜尚離世后,人們發(fā)現(xiàn)了他用來(lái)記錄如何制作《遺作》的備忘筆記,隨后杜尚秘密制作的所有配件也被轉(zhuǎn)移到了費(fèi)城美術(shù)館。配件組搭而成的,便是現(xiàn)在常設(shè)在該館館內(nèi)的作品《遺作》。該作品有幾個(gè)主題與《大玻璃》相呼應(yīng),杜尚生前強(qiáng)烈希望能一直將其陳列在《大玻璃》的旁邊。
本展通過(guò)視頻介紹《遺作》,同時(shí)也將展出作品面世前杜尚的想法筆記、備忘錄等書(shū)面材料,以及《遺作》的部分物品、展覽會(huì)的照片等等各種生動(dòng)表現(xiàn)杜尚最終作品創(chuàng)作狀況的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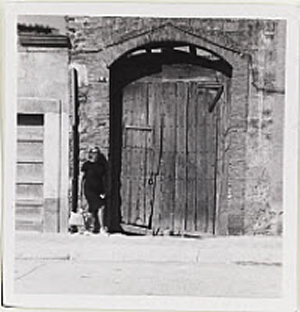
透過(guò)杜尚重新解讀日本藝術(shù)
本展將同時(shí)陳列包含東京國(guó)立博物館館藏的國(guó)寶、重要文化財(cái)產(chǎn)在內(nèi)的24件日本藝術(shù)品。通過(guò)展出迥異于西方、誕生于東方文化的日本美術(shù)作品來(lái)引導(dǎo)觀眾思考日本美術(shù)的定義與價(jià)值,提出鑒賞日本美的全新方法。
杜尚在“破壞”傳統(tǒng)西洋美術(shù)價(jià)值觀的過(guò)程中開(kāi)展自己的創(chuàng)作活動(dòng)。與此相仿,在400年前的日本,千利休(1522-92)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餐具里同樣發(fā)現(xiàn)了“美的存在”。因杜尚的創(chuàng)作活動(dòng)而風(fēng)行的西洋價(jià)值觀與日本傳統(tǒng)追求的“美的特質(zhì)”,在某種程度上達(dá)成了共鳴。
本展在與“杜尚 人與作品”一墻之隔的展示廳內(nèi)舉辦。通過(guò)五個(gè)切入角度來(lái)呈現(xiàn)日本美術(shù)的特征的同時(shí),希望觀眾能在杜尚的鑒賞余味中感知日本美術(shù)的核心所在。
400年前的現(xiàn)成物作品
據(jù)稱1590年,千利休隨行豐臣秀吉出征小田原。途經(jīng)伊豆時(shí),千利休取用韭山竹制作了《竹一重切花入》。該作品非常簡(jiǎn)潔,僅保留了剛竹的二段竹節(jié),在表面劃開(kāi)了一道切口。千利休沒(méi)有像陶藝工匠一般制作精美的容器或花瓶,而是隨手妙取路邊的竹子,制成插花瓶,為其注入無(wú)限價(jià)值。這便是日本版本的用日常之物打造藝術(shù)——現(xiàn)成物藝術(shù)品。

安土桃山時(shí)代·天正18年(1590)

日本的現(xiàn)實(shí)主義
自古以來(lái),日本繪畫(huà)都以記號(hào)化的形象來(lái)表現(xiàn)事物,對(duì)視覺(jué)感官上的寫(xiě)實(shí)幾乎不做追求。江戶時(shí)代的浮世繪畫(huà)師東洲齋寫(xiě)樂(lè)沒(méi)有學(xué)習(xí)過(guò)傳統(tǒng)的繪畫(huà)方法,他在描繪歌舞伎演員時(shí),因如實(shí)將飾演女角的演員畫(huà)成男性而受到了批評(píng)和非議。



時(shí)間的推移
日本的繪卷物有其獨(dú)特的發(fā)展演變規(guī)則。特別是“異時(shí)同圖”的畫(huà)法,采用在同樣的景觀、建筑內(nèi)多次刻畫(huà)同一人物,以此來(lái)表現(xiàn)時(shí)間與情節(jié)的推移。徐徐將畫(huà)卷攤展開(kāi)時(shí),看畫(huà)卷的人仿佛能感受到出場(chǎng)人物活靈活現(xiàn)的動(dòng)作。我們甚至可以稱繪卷物是動(dòng)漫的源頭。

圖中身著紅衣的人物多次出現(xiàn),以此表示時(shí)間的推移。
原創(chuàng)與模仿
藝術(shù)的價(jià)值在于創(chuàng)作者竭思而造就的唯一無(wú)二性。然而近世之前的日本卻理所當(dāng)然地推行參考前人作品的“模仿行為”。擁有400余年歷史,日本畫(huà)壇的狩野派繪師們制作了很多參考臨摹前人畫(huà)帖的作品。


書(shū)法的藝術(shù)性
書(shū)法是東方文化中造形藝術(shù)的極致表達(dá)。在日本,書(shū)法同時(shí)還與繪畫(huà)等諸多工藝有著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書(shū)法家光悅曾委托俵屋宗達(dá)等一流的畫(huà)師描繪文字底稿,自己則在底稿上書(shū)字寫(xiě)詞。文字的“形”已不僅僅只是字面含義,更是文字形態(tài)和設(shè)計(jì)美感的直觀呈現(xiàn)。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yíng)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