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古代中國邊疆移民的多元文化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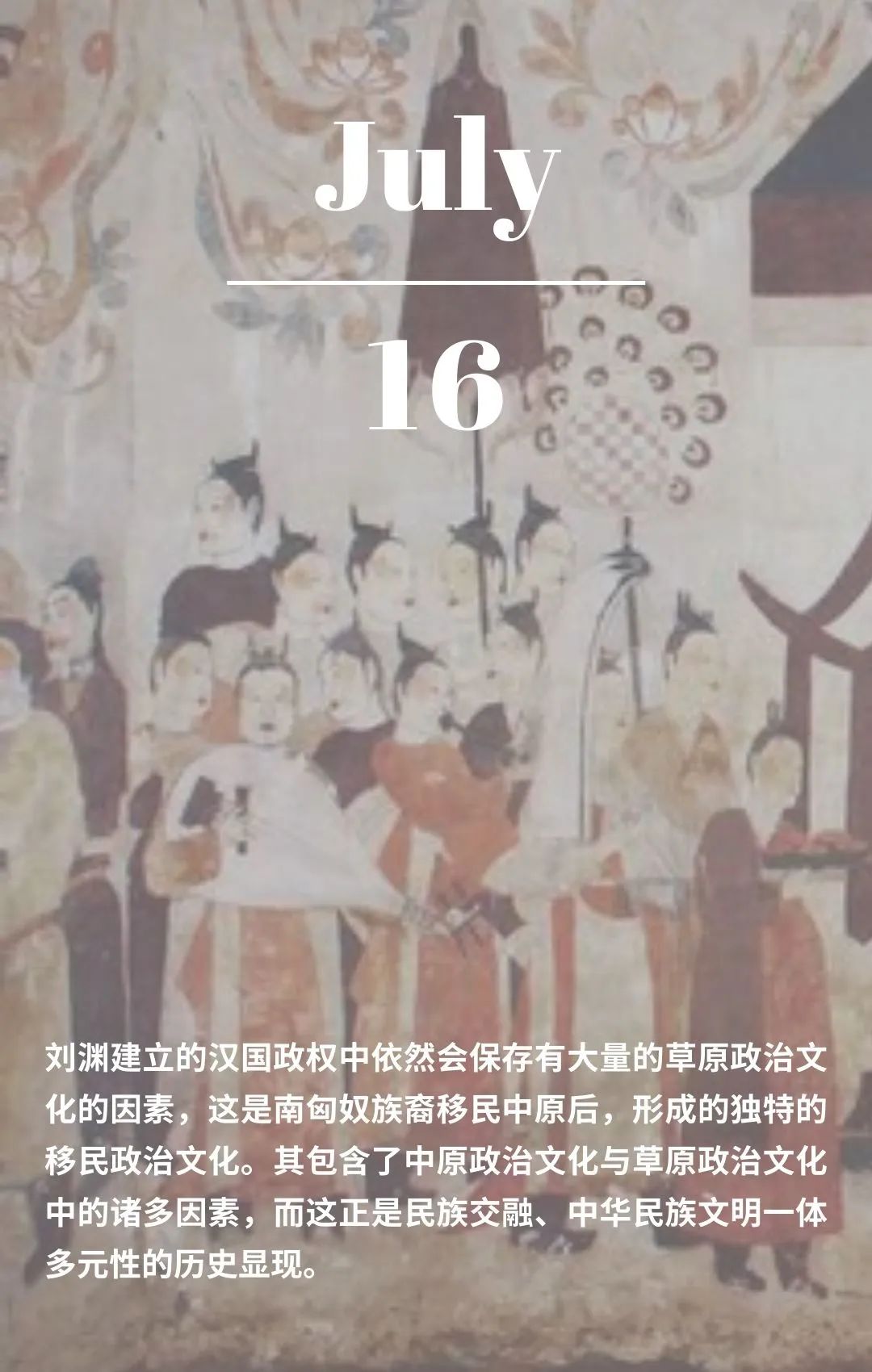
下文為《古代中國邊疆移民的多元文化考察——以劉淵興漢立國為例》,張晉著。摘自《宗教信仰與民族文化(第14輯)》,由何星亮主編,郭宏珍為執(zhí)行主編。
古代中國邊疆移民的多元文化考察
——以劉淵興漢立國為例
張晉
匈奴是傳統(tǒng)中國歷史上,第一個(gè)統(tǒng)一蒙古草原的政治軍事共同體,代表著草原游牧文化正式成為中華文明形成來源中的重要文化之一。因此,其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故此學(xué)界關(guān)于匈奴的論著中佳作非常之多。從史書上記載匈奴的傳記來看,冒頓無疑是使匈奴走進(jìn)中國王朝正史的標(biāo)桿性人物。那么匈奴歷史人物中堪與冒頓相媲美的另一個(gè)杰出人物,應(yīng)該是劉淵。劉淵是中國王朝正史給予書寫立傳的第一個(gè)匈奴人。劉淵著名于史的事件,是建立了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政權(quán)“漢”國,這一創(chuàng)舉拉開了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政權(quán)的序幕。劉淵作為南匈奴單于一族的后裔,在起兵反晉之時(shí),并沒有把恢復(fù)匈奴政權(quán)模式作為目標(biāo),反而以復(fù)興漢王朝為目標(biāo),選擇建立中原王朝政治體系。通過傳世的歷史文獻(xiàn),查詢其原因,顯然不只是漢王朝國祚長久,天下民人心向往之,這么簡單。“漢”國號(hào)可以招攬人心自然是歷史事實(shí),但這也只是歷史表象。劉淵宗漢立國實(shí)質(zhì)上是政治文化認(rèn)同下,構(gòu)建政治秩序行為正當(dāng)性的顯現(xiàn)。因?yàn)椋煌赜蛳隆⒉煌挝幕諊碌恼沃刃蛐螒B(tài)是不同的。跨越地域邊疆之后,政治文化會(huì)發(fā)生交匯融合。正如,拉鐵摩爾所言,游牧民族深入中原之后,社會(huì)結(jié)構(gòu)會(huì)向非游牧化轉(zhuǎn)型。而在社會(huì)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之后,不可能不影響到政治文化的認(rèn)同,進(jìn)而影響到政體的建設(shè)。這涉及南單于一族在南遷中原后,融入中原王朝政治秩序后的政治身份變化,劉淵本人的成長歷程以及其的學(xué)識(shí)與交友圈,匈奴族裔對(duì)中原傳統(tǒng)文化的吸收、借鑒等諸多因素。因此,劉淵借亂世以興漢為名建立政權(quán)的動(dòng)因是有研究價(jià)值的。所以,本文擬在充分借鑒前輩學(xué)人成果的基礎(chǔ)上,以傳統(tǒng)中國時(shí)代移民政治文化為視角,通過分析梳理史料,來探討劉淵在八王之亂時(shí)期做出興漢抉擇的歷史事實(shí)。
一 超凡魅力型首領(lǐng)的多重政治身份
歷史研究的主要對(duì)象是人,劉淵作為本文主要的研究對(duì)象,其本人的出身、經(jīng)歷及所處的時(shí)代背景,無疑對(duì)本文的書寫邏輯展開是至關(guān)重要的。同為南匈奴單于后裔的劉宣對(duì)劉淵的評(píng)價(jià)極高,將其品評(píng)為具有超凡魅力的首領(lǐng)。劉淵“姿器絕人,榦宇超世”,是常人所遠(yuǎn)遠(yuǎn)不及的,在匈奴上層貴族中,無人能出其右,故而其是復(fù)興匈奴霸業(yè)的希望所在。
本文中的“‘超凡魅力’將用于指稱個(gè)人的某種品質(zhì),而這是由于這種品質(zhì),他被看作不同尋常的人物,被認(rèn)為具有超自然或超人的,至少是特別罕見的力量和素質(zhì)。這些力量和素質(zhì)為普通人不可企及,而且被認(rèn)為出自神圣來源或者被當(dāng)作楷模,在此基礎(chǔ)上,有關(guān)的個(gè)人則被視為‘領(lǐng)袖’”。傳統(tǒng)中國的正史中,具有超凡魅力的領(lǐng)袖(皇帝)為數(shù)并不少。西漢王朝的創(chuàng)立者劉邦無疑是其中之一。劉邦從出生之前起,就籠罩著神圣性,其母“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mèng)與神遇。是時(shí)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于其上。已而有身,遂產(chǎn)高祖”。無獨(dú)有偶,數(shù)百年后,宣稱要興復(fù)漢王朝的劉淵,其出生之前的神跡與劉邦出生前的神跡頗為相近,只是更加詳細(xì)、豐富、精彩。
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于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髻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嘉祥也。”其夜夢(mèng)旦所見魚變?yōu)槿耍笫职岩晃铮笕绨腚u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征也。吾昔從邯鄲張冏母司徒氏相,云吾當(dāng)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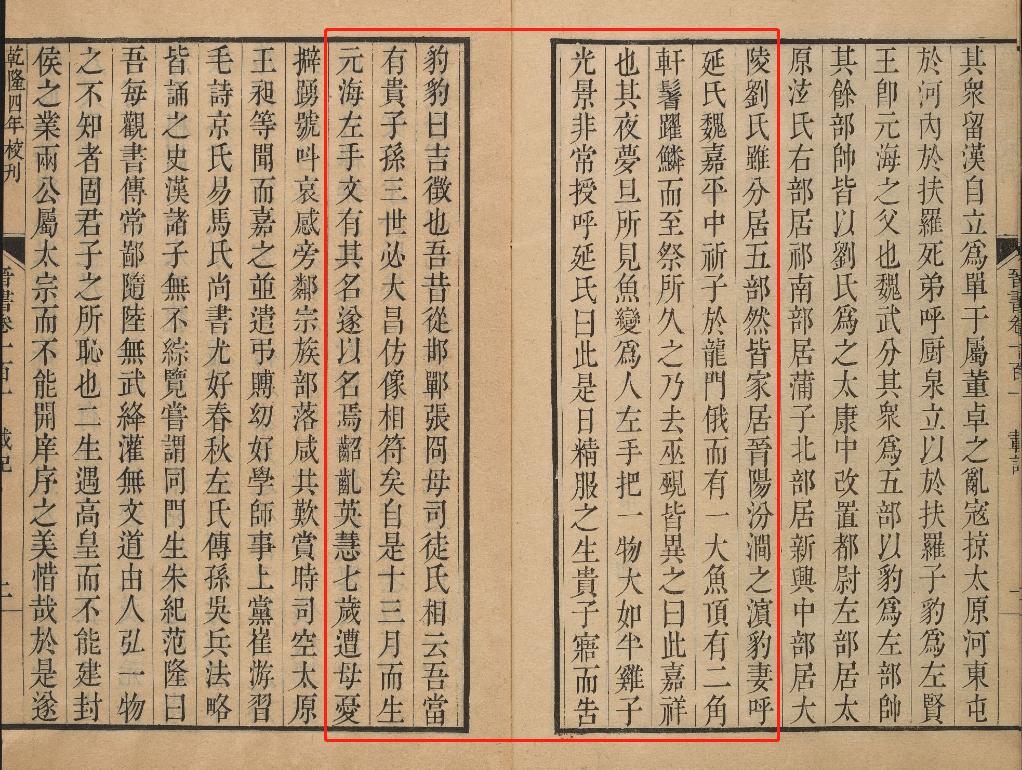
《晉書卷一百一·劉元海載記 》書影
清乾隆時(shí)期武英殿刊本
上述記載劉淵神跡的史料來源于大唐宰相房玄齡與中書侍郎褚遂良監(jiān)修的《晉書》中。當(dāng)時(shí)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親自參與《晉書》的編撰工作,曾“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jī)、王羲之四論,于是總題云御撰”。由此可知,《晉書》是可以代表唐太宗李世民的史觀與價(jià)值評(píng)判尺度的。而劉淵出生前的神跡作為一種歷史記憶被以書面化的形式呈現(xiàn)出來,不可能沒有得到李世民的同意。在《晉書》中,劉淵因?yàn)椤懊父咦鎻R諱,故稱其字焉”。因此,如果李世民不同意,關(guān)于劉淵出生神跡的歷史記憶顯然不會(huì)出現(xiàn)在《晉書》中。那么這段史料顯然有其特殊的歷史意義。與劉邦相對(duì)比,關(guān)于劉淵出生神跡的這段史料描述,是很典型的中原王朝創(chuàng)始之君受命于天的傳說敘事模式。陳序經(jīng)認(rèn)為,“《史記》、《漢書》、《后漢書》記載匈奴風(fēng)俗,沒有述及匈奴婦女拜神祈子。這種傳說當(dāng)然是受漢族文化影響的結(jié)果”。劉母呼延氏一族是匈奴族群中僅次于單于孿鞮氏的貴族,而且“孿鞮氏單于世娶呼延等氏女為‘閼氏’”。而祈求神靈賜子是中原習(xí)俗,這意味著劉母呼延氏日常生活行為中已經(jīng)打上了很深的中原文化烙印。劉父豹是南匈奴單于于扶羅之子。而劉豹言,有卦師給他算出,其當(dāng)有優(yōu)秀杰出的子孫,三代之內(nèi),必然會(huì)使劉家發(fā)達(dá)昌盛。這番言語,與中原的官宦之人已經(jīng)沒什么差別了。從春秋至漢魏,相人術(shù)已經(jīng)成為構(gòu)成社會(huì)精英文化的一部分,不只是問吉兇,對(duì)社會(huì)精英們來說,更關(guān)注的是前程如何。《三國志》轉(zhuǎn)引《魏書》記載了魏武帝曹操少年時(shí),被當(dāng)時(shí)名士橋玄預(yù)測(cè)前程的往事。“太尉橋玄,世名知人,睹太祖而異之,曰:‘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為托。’由是聲名益重。”曹操先祖父是宦官曹騰,而東漢王朝在經(jīng)歷黨錮之禍后,宦官群體深受天下士人的鄙視。橋玄是當(dāng)時(shí)名士,由其以善識(shí)人而譽(yù)滿天下。因此,橋玄之言辭對(duì)曹操個(gè)人的發(fā)展前途影響極大。眾所周知,于扶羅故去后,南單于位并非由其子繼承。這樣,劉豹看相的原因中,自然有其對(duì)前程憂慮感的存在。而相師之言給出了劉豹的希望在未來。那么,從出生之前起,劉淵身上就潛藏著多重文化的基因。而劉淵所屬的南匈奴單于家族,在其出生前,由于不斷地南遷,政治身份已然發(fā)生了大轉(zhuǎn)變。
漢宣帝時(shí)期,匈奴政權(quán)五單于并立,相互廝殺。呼韓邪單于被其兄郅支單于擊敗。左伊秩訾王建議呼韓邪向漢王朝求助,“稱臣入朝事漢”,只有這樣才可以生存。呼韓邪思量再三,決定采納左伊秩訾王的建議。漢宣帝大喜,對(duì)呼韓邪單于“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有了西漢王朝這樣強(qiáng)大的后援,呼韓邪最終戰(zhàn)勝了郅支單于,成為匈奴唯一的單于。漢元帝初年,在匈奴發(fā)生饑荒時(shí),“漢詔云中、五原郡轉(zhuǎn)谷二萬斛以給焉”。此時(shí),漢王朝與匈奴的關(guān)系由兩強(qiáng)并立,轉(zhuǎn)變?yōu)樾倥驖h王朝表示臣服。這樣,匈奴單于的政治身份多了一重含義——漢王朝的屬臣。在表示臣服后,匈奴單于往往會(huì)將自己的兒子送來做人質(zhì),納質(zhì)成為“邊疆民族政權(quán)和西漢王朝保持藩屬關(guān)系的重要保證之一”。
東漢王朝時(shí)期,匈奴徹底分為南北兩部分。建武二十五年(49),匈奴“南單于復(fù)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xiàn)國珍寶,求使者監(jiān)護(hù),遣侍衛(wèi)子,修舊約”。建武二十六年(50),東漢王朝派遣中郎將段彬、副校尉王郁幫助南單于在五原郡西部塞八十里處,設(shè)立了單于庭。而這一行動(dòng)正是應(yīng)南單于請(qǐng)求“使者監(jiān)護(hù)”而為之的。南單于庭在漢郡的設(shè)置,使東漢王朝對(duì)匈奴南單于具有了實(shí)質(zhì)性的控制與管理。匈奴南單于的政治身份也在實(shí)際意義上變成東漢王朝的臣子,同時(shí)匈奴最高統(tǒng)治者的政治身份依然存在。此時(shí),南單于的政治身份具有了雙重性。
南匈奴內(nèi)附后,東漢王朝掌控了南單于繼任的話語權(quán)。中平五年(188),南匈奴內(nèi)訌,羌渠單于被殺,匈奴國人不認(rèn)同羌渠單于之子于扶羅繼任單于位,另立單于。于扶羅趕到洛陽,向當(dāng)時(shí)的皇帝漢靈帝申訴,請(qǐng)求得到支持與認(rèn)可。此時(shí)的南單于幾乎等同于中原王朝政府委任的封疆大吏,而這一現(xiàn)象有助于具備繼承南單于資格者很好地融入王朝政府官僚群體之中。曹魏時(shí)期,劉豹被冊(cè)封為匈奴左部帥之職。這一任命可以看作匈奴貴族正式開始融入中原政權(quán)體制的標(biāo)志。南單于一族改姓劉氏,“大約始于曹魏時(shí)期”。而匈奴貴族要想真正融入中原政治秩序中,離不開對(duì)中原主流文化的學(xué)習(xí)。據(jù)《漢書·儒林列傳》記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xué)……悉令通孝經(jīng)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xué)。”由此可知,早在漢光武帝時(shí)期,匈奴貴族子弟便已進(jìn)入東漢王朝的最高學(xué)府太學(xué)學(xué)習(xí)儒家經(jīng)典。所以,《晉書》中記載匈奴貴族大多通曉儒學(xué)是可信的——畢竟他們接觸儒家經(jīng)典有近200年的歷史了。此時(shí)在魏晉做官的匈奴貴族已經(jīng)深受政治精英文化的熏陶,故而會(huì)有劉豹找相師預(yù)測(cè)前程之事。
漢王朝自從漢武帝時(shí)起,便以儒家經(jīng)典為主要意識(shí)形態(tài)來指導(dǎo)政府如何治理國家。孝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東漢進(jìn)入仕途的主要方式便是舉孝廉。劉母亡故時(shí),劉淵年方7歲,頓足捶胸,號(hào)啕大哭,“哀感旁鄰,宗族部落咸共嘆賞”。年紀(jì)幼小的劉淵便是至情至孝之人。此事,使得劉淵初次聞名于以司空太原王昶為首的一眾名士圈中。劉淵自小好學(xué),跟隨上黨崔游學(xué)習(xí)期間,于詩書經(jīng)傳,孫吳兵法,皆有所涉獵。其成年之后,文武雙全,尤其武藝,“妙絕于眾”。當(dāng)時(shí),“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師彧等,皆善相人,及見元海,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于是深相崇敬,推分結(jié)恩。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jì)拜焉”。從這些史料記載的事件來看,青少年時(shí)期的劉淵便已經(jīng)融入并州士人圈之中,而且頗具影響力,成為當(dāng)時(shí)公認(rèn)的、頗具潛力的政治精英。
因此,對(duì)于南遷中原的南匈奴單于一族來說,到了超凡魅力型首領(lǐng)劉淵的時(shí)代,他不再是具有自南匈奴單于因?yàn)橐泼裰性谌胫性醭沃刃蛑械碾p重性政治身份,而是具有了多重政治身份:其一為繼承南匈奴單于資格者;其二接任其父曾經(jīng)擔(dān)任的左部帥之職,為晉室臣子;其三為士人群體中的政治精英。
二 支配權(quán)力角逐下的移民騎兵
魏元帝咸熙年間,劉淵以任子身份居住在京師洛陽,受到實(shí)際上掌控支配權(quán)力者晉王司馬昭的賞識(shí)與優(yōu)待。魏晉更迭之后,王渾多次極力向晉武帝司馬炎推薦劉淵。
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jì)曰:“劉元海容儀機(jī)鑒,雖由余、日無以加也。”濟(jì)對(duì)曰:“元海儀容機(jī)鑒,實(shí)如圣旨,然其文武才干賢于二子遠(yuǎn)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huì)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珧進(jìn)曰:“臣觀元海之才,當(dāng)今懼其無比,陛下若輕其眾,不足以成事;若假之權(quán)威,平吳之后,恐其不復(fù)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為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
通過這段史料可以得出,晉武帝司馬炎很是賞識(shí)劉淵,認(rèn)為其可以做晉室的由余與金日。與劉淵交好的王濟(jì)認(rèn)為,劉淵才華蓋世,是不可多得的棟梁之臣,希望朝廷委以其重任。而在孔恂與楊珧看來,劉淵除了才華之外,還有一個(gè)隱藏著的政治身份,即潛在的支配權(quán)力競爭者。這一政治身份,對(duì)劉淵今后的個(gè)人發(fā)展以及傳統(tǒng)中國歷史的發(fā)展都是至關(guān)重要的。
“后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憙時(shí)任司隸校尉乘此良機(jī),繼王濟(jì)之后再次向司馬炎推薦劉淵為將率兵平叛。李憙列舉劉淵軍事才能出眾,同時(shí)麾下又有驍勇善戰(zhàn)的匈奴騎兵,定能一舉蕩平禿發(fā)樹機(jī)能的叛亂。面對(duì)李憙的力薦,孔恂再次極力阻止。在孔恂看來,劉淵的上述優(yōu)勢(shì),卻是對(duì)晉王朝最大的威脅。司馬炎斟酌再三,決定棄用劉淵。劉淵仕途受阻,心灰意冷,對(duì)晉王朝已不抱希望。
后王彌從洛陽東歸,元海餞彌于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渾、李憙以鄉(xiāng)曲見知,每相稱達(dá),讒間因之而進(jìn),深非吾愿,適足為害。吾本無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與子別。”因慷慨噓唏,縱酒長嘯,聲調(diào)亮然,坐者為之流涕。
晉室之齊王司馬攸當(dāng)時(shí)恰好在九曲,聽聞劉淵與王彌及眾賓客宴飲之事,派遣屬下前去打探消息。并上書晉武帝司馬炎,言辭間希望盡早除去劉淵,否則恐怕劉淵會(huì)割據(jù)并州一帶。王渾聽之進(jìn)言,以己身力保劉淵。實(shí)則,司馬攸的上書中,也不無合理之處。劉淵在并州一帶的士人群體中,頗具威望,儼然穩(wěn)居中心之位。劉淵在悲憤的自白中,也提及這一點(diǎn),王渾、王濟(jì)父子與李憙等人正是因?yàn)椤班l(xiāng)曲”之誼,才力薦、力保劉淵的。同時(shí),劉淵還具有常人無法企及的杰出才干,中原世家大族所沒有的精銳騎兵。這幾點(diǎn)優(yōu)勢(shì)確實(shí)不能不令人生畏懼之心。
眾所周知,魏得國于漢,晉得國于魏。雖然,這三朝之間的輪換,形式上是以禪讓制和平交接支配權(quán)力來完成的,但是,實(shí)際層面上卻是由于強(qiáng)大武力致使支配權(quán)力發(fā)生流轉(zhuǎn)的。東漢末年,曹丕如果沒有手握重兵,如何能使?jié)h獻(xiàn)帝禪讓江山?同理,司馬炎如果不是有強(qiáng)大的軍力,如何能替換魏帝?因此,極力阻止司馬氏重用劉淵的諸臣,是在擔(dān)心劉淵變成另一個(gè)曹操或司馬懿。而這正是劉淵多重政治身份中隱性的政治身份——支配權(quán)力強(qiáng)有力的競爭者。
晉王朝建立后,“帝懲魏氏孤立之弊,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同時(shí),司馬炎設(shè)計(jì)司馬氏宗室諸王可以有統(tǒng)兵權(quán),“封諸王,以郡為國。邑二萬戶為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萬戶為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五千戶為小國,置一軍,兵五百人”。想以此來護(hù)衛(wèi)晉朝皇帝對(duì)支配權(quán)力的永久掌控。
可惜,天不遂人愿,正是司馬炎賦予宗室諸侯王的權(quán)力,致使西晉王朝變成了傳統(tǒng)中國歷史上的短命王朝之一。“帝疾篤,未有顧命。勛舊之臣多已物故”,在司馬炎沒有安排好后事即駕崩的情況下,西晉王朝外戚與宗室之間圍繞誰來掌控支配權(quán)力展開了一連串的爭奪。而圍繞權(quán)力的角逐離不開強(qiáng)大武力的支撐。
從東漢王朝中后期時(shí)起,南遷中原的游牧移民部眾成為帝國騎兵的主要兵員。東漢末年,政治秩序崩潰后,游牧移民騎兵更是成為軍閥割據(jù)稱雄的有力武器。袁紹起兵時(shí),就把倚重游牧騎兵作為爭霸天下的利器。“吾南據(jù)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曹操統(tǒng)一北方后,三郡烏桓成為其麾下的天下名騎。同時(shí),析分南匈奴為五部,任命匈奴上層貴族分別擔(dān)任部帥之職,其中劉淵父劉豹“為左部帥,部族最強(qiáng)”。這樣做自然是為了更好地控制匈奴部眾。
劉豹去世后,劉淵接任了左部帥之職。晉武帝太康末年,改任北部都尉。晉惠帝初年,再次改派,“以劉元海為離石將兵都尉”。周偉洲認(rèn)為:“將兵都尉一職,不見記載,其在離石,且云‘將兵’,很可能是晉朝所派至離石領(lǐng)兵監(jiān)督匈奴五部的職官。也就是說,此職有一定的實(shí)權(quán),掌握一定的軍隊(duì),非五部都尉的虛銜可比。”因此,史料上所說的,劉淵“明刑法,禁奸邪,輕財(cái)好施,推誠接物,五部俊杰無不至者。幽冀名儒,后門秀士,不遠(yuǎn)千里,亦皆游焉”。這樣,游牧移民部眾與幽、冀地區(qū)的儒生名士紛紛前來歸附的盛況,最有可能發(fā)生。劉淵擔(dān)任離石將兵都尉一職時(shí)期,也就是在擔(dān)任將兵都尉期間,劉淵憑借個(gè)人才干,迅速積累了雄厚的政治資本。
晉惠帝外祖父楊駿以輔政之名,掌控支配權(quán)力時(shí),任命劉淵為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并冊(cè)封漢光鄉(xiāng)侯的爵位,其目的自然是想拉攏劉淵為己所用。后因匈奴五部眾中有人叛逃至塞外,劉淵被罷免官職。惠帝后賈氏聯(lián)合楚王司馬瑋盡滅太后楊氏一族。這一宮廷政變引發(fā)了司馬氏諸王內(nèi)訌的八王之亂。成都王司馬穎出鎮(zhèn)鄴郡,上表請(qǐng)封劉淵為“行寧朔將軍,監(jiān)五部軍事”,以此招攬劉淵至麾下。由于劉淵文武兼?zhèn)洌鸥晒诮^于當(dāng)世,因此成都王司馬穎很是器重他,并委以重任。“自鄴懸秉國政,事無大小,皆先關(guān)咨,以淵為太弟,屯騎校尉。”
當(dāng)時(shí),正值八王之亂高潮期,左國城以劉宣為首的匈奴貴族密謀,推舉劉淵為大單于,認(rèn)為“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fù)業(yè),此其時(shí)矣”,并派呼延攸前往鄴郡,稟告劉淵。司馬穎軍政大事皆需劉淵謀劃,因此劉淵暫時(shí)無法脫身回歸左國城。只得命呼延攸先行返回,并轉(zhuǎn)告劉宣,以聲援司馬穎為名召集匈奴五部及雜胡人馬。
八王之亂后期,實(shí)質(zhì)上爭奪王朝支配權(quán)力的雙方是成都王穎與東海王司馬越。雙方為了戰(zhàn)勝對(duì)方,急需擁有壓倒對(duì)方的武力,因此,自漢王朝時(shí)起,南遷中原的游牧移民便成為他們急需的強(qiáng)大后援。
司馬越的弟弟并州刺史司馬騰與幽州刺史王浚聯(lián)兵進(jìn)攻鄴郡,王浚軍中的烏桓、鮮卑騎兵尤其驍勇善戰(zhàn)。面對(duì)烏桓、鮮卑騎兵快如疾風(fēng)般的進(jìn)攻,司馬穎心生恐懼之感,竟意欲避之鋒芒,棄城而逃。苦于困在鄴郡不能脫身返還左國城的劉淵緊緊地抓住了這一良機(jī),匈奴五部的精銳騎兵成為他名正言順脫身的借口。
元海說穎曰:“今二鎮(zhèn)跋扈,眾余十萬,恐非宿衛(wèi)及近都士庶所能御之,請(qǐng)為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眾可保發(fā)已不?縱能發(fā)之,鮮卑、烏丸勁速如風(fēng)云,何易可當(dāng)邪?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銳,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勛于王室,威恩光洽,四海欽風(fēng),孰不思為殿下沒命投軀者哉,何難發(fā)之有乎!王浚豎子,東嬴疏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一發(fā)鄴宮,示弱于人,洛陽可復(fù)至乎?縱達(dá)洛陽,威權(quán)不復(fù)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為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逾五部,愿殿下勉撫士眾,靖以鎮(zhèn)之,當(dāng)為殿下以二部摧東嬴,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穎悅,拜元海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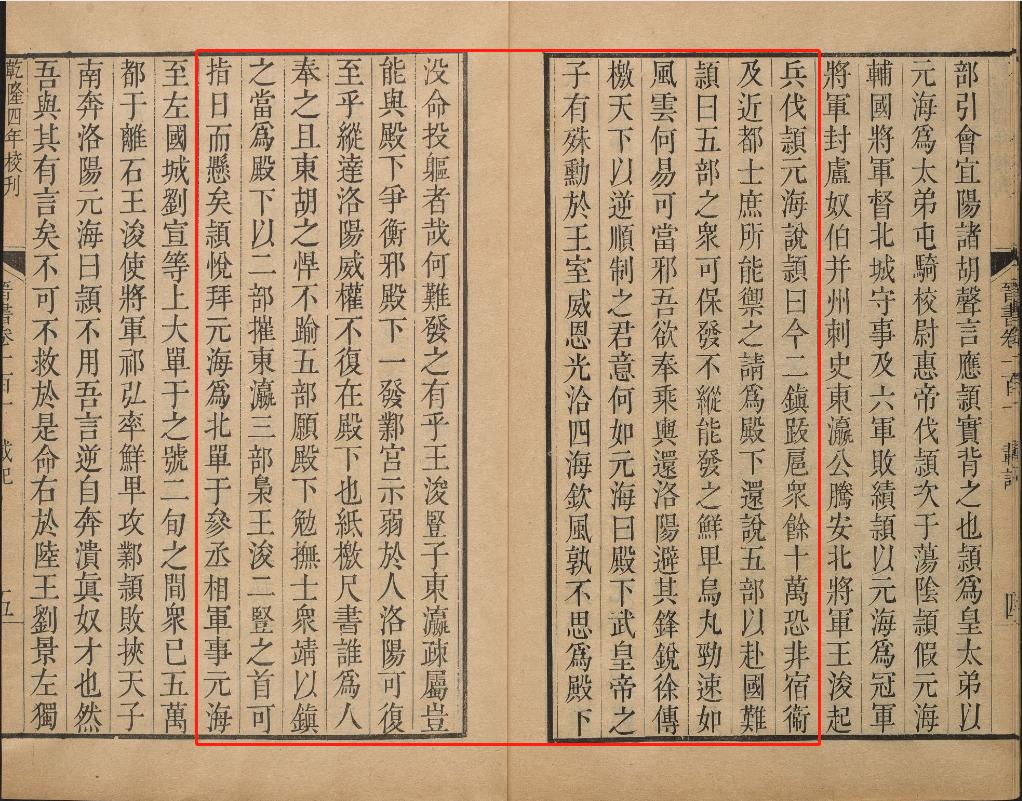
《晉書卷一百一·劉元海載記 》書影
清乾隆時(shí)期武英殿刊本
這樣,劉淵口銜王命以正當(dāng)身份返還了左國城。同時(shí),通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以下幾點(diǎn):司馬穎與劉淵關(guān)系密切,劉淵是司馬穎麾下極為重要的謀臣良將;司馬氏諸王之間的內(nèi)訌慘烈,兵強(qiáng)馬壯成為掌控王朝支配權(quán)力的基礎(chǔ),南遷中原的游牧部族中“鮮卑、烏桓起兵所支持的是司馬越,匈奴起兵所支持的是司馬穎”。
而這些游牧移民部族騎兵深度參與司馬氏諸王之間的混戰(zhàn),在客觀上“促進(jìn)了融合著游牧族群騎兵與農(nóng)業(yè)社會(huì)官僚行政體系的國家的建立”。
三 重構(gòu)政治秩序的正當(dāng)性
當(dāng)年正是由于秦漢之際的中原戰(zhàn)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fù)去,于是匈奴得寬,復(fù)稍度河南與中國界于故塞”。隨后冒頓又侵入燕、代之地,誘發(fā)了西漢王朝初期的邊疆危機(jī)。同樣,晉室的八王之亂使王朝政治秩序崩潰,整個(gè)北方陷入了刀兵戰(zhàn)火之中。
劉淵回歸左國城之后,在以劉宣為首的匈奴貴族的擁戴下,任匈奴大單于。在短短的二旬之間,“內(nèi)遷匈奴及雜胡紛紛投附”,五部部眾發(fā)展到了5萬人。此時(shí),王浚部將祁弘率領(lǐng)鮮卑騎兵進(jìn)攻鄴城,司馬穎不敵,棄城南逃洛陽。劉淵以“吾與其有言矣”,決定派兵阻擊鮮卑騎兵,以救司馬穎。劉宣極力勸阻,并進(jìn)言劉淵,“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于我”。此時(shí)起兵應(yīng)該建立什么樣的政治秩序模式,成為亟須解決的問題。而政治秩序的重建必須有合理的正當(dāng)性,這樣才能國運(yùn)長久。
劉宣等人認(rèn)為,方今天下大亂,又有劉淵這樣才德蓋世的英雄,正是上天要讓匈奴復(fù)興之時(shí),所以應(yīng)該“復(fù)呼韓邪之業(yè)”,同時(shí)聯(lián)合鮮卑、烏桓諸部為盟軍。實(shí)際上劉宣的主張?jiān)诋?dāng)時(shí)的歷史情境幾乎不具有可行性。首先,來看劉宣口中的呼韓邪單于。匈奴歷史上的呼韓邪單于一共有兩位。而如本文前述,這兩位單于無疑都是在身處困境之時(shí),請(qǐng)求歸附漢王朝,以求獲得資源來自保與發(fā)展。因此,兩位呼韓邪單于執(zhí)政時(shí)期的匈奴無論在形式上或者是實(shí)際層面上,已經(jīng)不是曾經(jīng)與中原王朝對(duì)等的政治體,而是轉(zhuǎn)型為漢王朝藩屬。如果要恢復(fù)冒頓時(shí)代的草原帝國,則需出塞返回草原。在長城以南的并州建立冒頓時(shí)代的政權(quán)形態(tài),顯然是不可行的。因?yàn)椋文撩褡逶趦?nèi)遷中原后,會(huì)不可避免地發(fā)生社會(huì)轉(zhuǎn)型,生活習(xí)俗與行為趨同于中原民眾。其次,再看以鮮卑、烏桓為援說。秦王朝建立之初,“東胡強(qiáng)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此時(shí),東胡實(shí)力強(qiáng)于匈奴,冒頓曾為質(zhì)于東胡。冒頓成為單于時(shí),故意示弱,使“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chǎn)”。東胡徹底被擊潰,余部潛逃化為烏桓與鮮卑二部。烏桓以山為族名,“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烏桓與匈奴生活習(xí)性相同,但滅國之仇,卻不可不報(bào)。烏桓實(shí)力轉(zhuǎn)強(qiáng)時(shí),曾“發(fā)掘匈奴單于冢,將以報(bào)冒頓所破之恥”。而鮮卑拓跋部常常協(xié)助司馬騰、劉琨等與劉淵部作戰(zhàn)。因此,匈奴與烏桓、鮮卑二部相互為敵的歷史頗為久遠(yuǎn),相生相殺數(shù)百年,在草原游牧空間中是競爭對(duì)手,同樣融入中原王朝政治秩序之后依然如此。由此,可見劉宣的政治主張?jiān)诋?dāng)時(shí)注定是無法實(shí)現(xiàn)的圖景。
劉淵面對(duì)晉王朝政治秩序崩潰后的天下亂象,贊同劉宣起兵割據(jù)的主張,但在政權(quán)形態(tài)方面,則認(rèn)為應(yīng)該建立中原王朝式的政治秩序。
當(dāng)為崇岡峻阜,何能為培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眾十余萬,皆一當(dāng)晉十,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yè),下不失為魏氏。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jié)于人心,是昭烈崎嶇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后主,以懷人望。
這段史料清晰地再現(xiàn)了劉淵當(dāng)時(shí)的政治意圖。夏之大禹、周之文王均不是中原人士。建功立業(yè),帝王無問出處,有德之君居之中原是天意。而精兵銳騎在刀兵四起的亂世中,是建功立業(yè)的基礎(chǔ)。今,這兩者齊聚于劉淵之身,正是大顯神威,開創(chuàng)萬世基業(yè)之時(shí)。那么,劉淵何以要延續(xù)漢祚,以興漢為政治旗幟?
在匈奴單于向漢王朝皇帝形式上奉藩稱臣之后,“有威名于百蠻”的草原霸主的權(quán)威已然在逐漸消退。“匈奴日削,不能取復(fù)”是當(dāng)時(shí)的歷史事實(shí)。到東漢末年,“2世紀(jì)后期,南單于喪失其權(quán)威的事態(tài)是越來越深刻而嚴(yán)重的”。劉淵作為“超凡魅力”型首領(lǐng)的存在,匈奴以劉宣為首的上層貴族認(rèn)為是上天要匈奴中興的預(yù)設(shè)。而匈奴中興要實(shí)現(xiàn)什么,對(duì)此劉宣是有期望的。乘亂起兵是為了擺脫“晉為無道,奴隸御我”的悲慘境地。而之后怎么做,劉宣也只是提出“復(fù)呼韓邪之業(yè)”。但令劉宣等人懷念的是“昔我先人與漢約為兄弟,憂泰同之”的地位。而要實(shí)現(xiàn)劉宣等人的期望,必須制定符合當(dāng)時(shí)形勢(shì)的路線與方針。
因此,劉淵在深思熟慮、審時(shí)度勢(shì)之后,做出了“追尊后主”,以“興漢”為旗幟的歷史抉擇。劉淵的成長環(huán)境以及他的人生經(jīng)歷,無可辯駁地已經(jīng)使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融入了他的意識(shí)之中。所以,起兵割據(jù)必須要有正當(dāng)?shù)睦碛桑酉聛斫⒌恼?quán)才會(huì)有正當(dāng)性。在起兵前,劉淵在晉王朝的政治秩序中擁有重要的政治身份。故而,他起兵絕不是要做晉王朝的叛臣,而是要成為復(fù)興漢王朝的功臣。漢魏禪讓背后是強(qiáng)大武力的脅迫,魏晉禪讓也是如此。劉淵以興漢來對(duì)抗晉室,自然在道德方面已居于有利位置。劉淵決定以興漢為旗幟后,從離石遷居左國城,返回左國城對(duì)劉淵來說是意義重大的。東漢中期以后,在南單于任免的問題上,漢帝很有話語權(quán)。南單于在某種意義上是漢王朝政治秩序中地位很高的藩王身份。劉淵返回左國城后,據(jù)史料記載“遠(yuǎn)人歸附者數(shù)萬”。這些“遠(yuǎn)人”自然不是“晉人”,而是心懷漢室者。而這正印證了劉淵前面所說的,漢室國運(yùn)長久,恩德廣播于天下的論斷。劉淵在左國城稱漢王與劉備在成都稱漢中王實(shí)質(zhì)上是相同的,劉備屬漢室宗親疏支,劉淵只是“漢室之甥”。同時(shí),二人均是在國家社稷蒙塵,不得不挺身而出的形勢(shì)下稱王的。劉淵祭天文書,言辭懇切,動(dòng)容處不禁潸然淚下,稱漢王絕非為一己之私,而是“大恥未雪,社稷無主,銜膽棲冰,勉從群議”的壯舉。劉淵冠冕堂皇的言辭行為,背后是對(duì)中原王朝政治文化的認(rèn)同以及為即將建立的政治秩序謀求正當(dāng)性的行為。

《中國一百帝王圖》劉淵畫像(圖源網(wǎng)絡(luò))
劉淵在左國城南郊設(shè)壇祭天,并“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通過郊祀與宗廟來昭告天下,漢王朝將再次中興。劉淵的這一系列舉動(dòng),震驚了晉王朝。在當(dāng)時(shí)的中原政治文化中,郊祀對(duì)王朝的正當(dāng)性有著無可替代的功效。因?yàn)椋捞於Y儀是皇帝與上天之間的對(duì)話,以此儀式來證明,皇帝是受上天委任而具有統(tǒng)治天下與民眾的權(quán)力。魏晉時(shí)期,有一段時(shí)間皇帝是不親自執(zhí)行郊祀儀式的。在劉淵稱漢王之后,晉室懷帝親自執(zhí)行郊祀活動(dòng),這無疑是對(duì)劉淵漢國建立的回應(yīng)。以此來昭告天下,司馬氏依然是秉天承命的擁有者。在有君主的社會(huì)中,儀式彰顯君主本人具有超自然地位,以此來證明其政權(quán)具有的正當(dāng)性。這樣,漢與晉都宣稱各自的政權(quán)擁有來自上天所授予的統(tǒng)治權(quán)力,展開了對(duì)王朝政治秩序正當(dāng)性的競爭。此時(shí),任何一件無意中出現(xiàn)的偶然事件都可以成為印證構(gòu)建政治秩序正當(dāng)性、天命所歸的例證。比如,“永嘉三年,劉淵徙平陽,于汾水得白玉印,方四寸,高二寸二分,龍紐。其文曰:有新寶之印,王莽所造也。淵以為天授,改永鳳二年為河瑞元年”。從歷史事實(shí)來講,劉淵宗漢立國是南遷中原的游牧移民第一次將中原王朝式政治秩序作為建立政權(quán)的模式。這表明,當(dāng)時(shí)無論是中原人士還是游牧移民,如果要逐鹿中原,取得支配天下的權(quán)力,必須認(rèn)同中原王朝政治文化,以建立中原王朝式的政治秩序?yàn)榻⒄?quán)的模式,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建立王朝政治秩序的正當(dāng)性。
當(dāng)然劉淵的漢國政權(quán),有著為數(shù)不少的游牧文化的印記。其中以游牧民眾組成的騎兵為征戰(zhàn)、角逐天下的主力軍隊(duì)。統(tǒng)治集團(tuán)的核心成員大都也是游牧移民出身的人。同時(shí),設(shè)有不同于中原官僚體系管理游牧民眾的機(jī)構(gòu)。而這些,也已經(jīng)不同于游牧民在草原空間中所設(shè)立的機(jī)構(gòu),其是在移民政治文化下,出現(xiàn)的融合著不同文化因素的管理機(jī)構(gòu)。
綜上所述,八王之亂時(shí)期劉淵以興漢為名建立政權(quán)立國的重要?dú)v史事件,究其原因絕不僅僅是劉淵為了招攬人心的權(quán)宜之舉。這一歷史抉擇是多重原因促成的。首先,劉淵本人文武兼?zhèn)洌烈暼盒鄣慕艹霾湃A。其次,南單于家族南遷中原后,在王朝政治秩序中,有了新的不同于草原空間中的政治身份,到劉淵這一輩更是具有了多重政治身份。再次,匈奴部眾強(qiáng)悍的騎兵部隊(duì),使劉淵集團(tuán)有了乘勢(shì)起兵的機(jī)會(huì)。此外,還有一個(gè)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劉淵認(rèn)同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并獲得了當(dāng)時(shí)部分士族人物的支持與擁戴。與此同時(shí),劉淵建立的漢國政權(quán)中依然會(huì)保存有大量的草原政治文化的因素,這是南匈奴族裔移民中原后,形成的獨(dú)特的移民政治文化。其包含了中原政治文化與草原政治文化中的諸多因素,而這正是民族交融、中華民族文明一體多元性的歷史顯現(xiàn)。
書籍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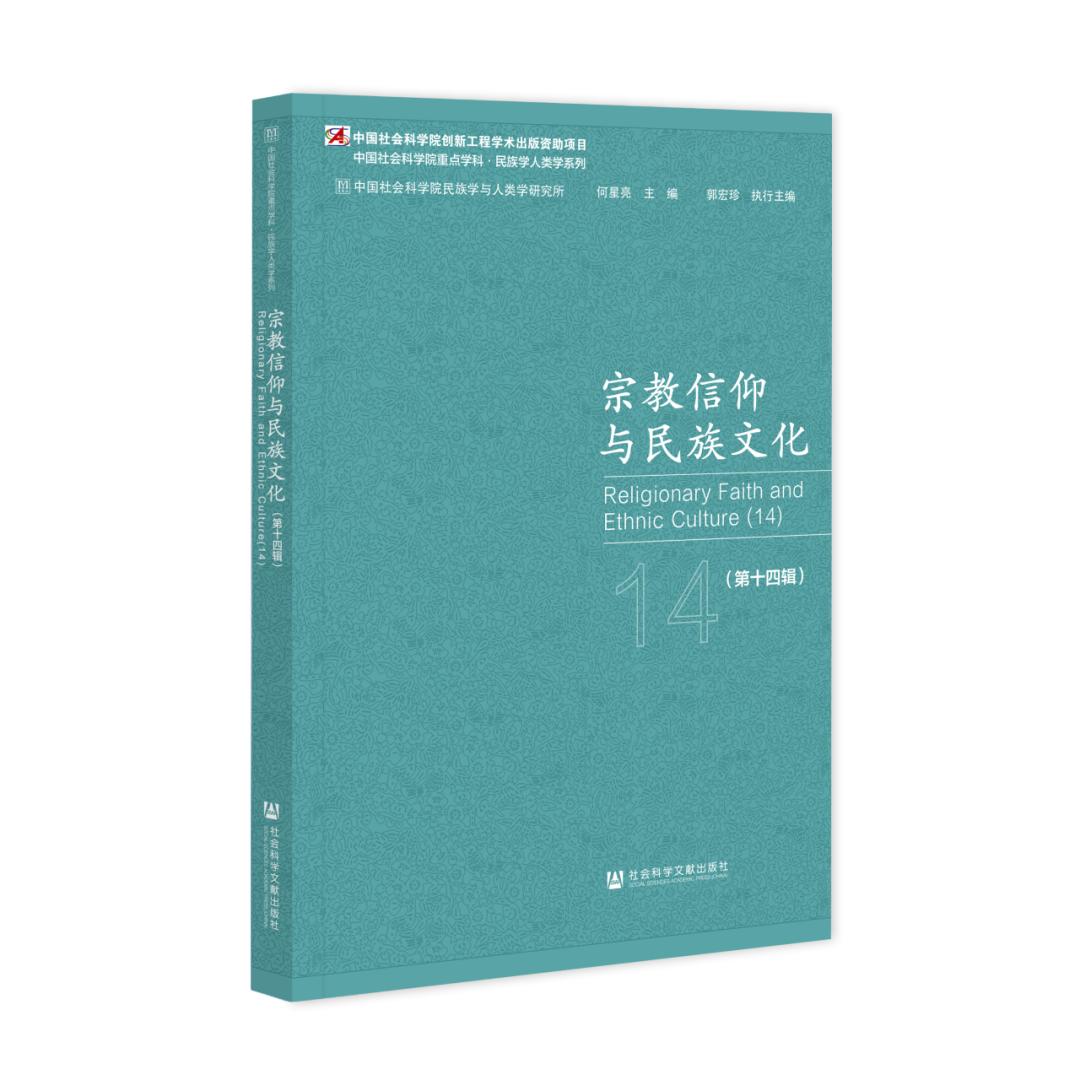
宗教信仰與民族文化(第14輯)
何星亮 主編
郭宏珍 執(zhí)行主編
2023年5月出版/89.00元
ISBN 978-7-5201-7553-1
內(nèi)容簡介
本書所收錄論文是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院民族學(xué)與人類學(xué)研究所重點(diǎn)學(xué)科宗教與文化研究成果。第14輯共收錄文章21篇,分為經(jīng)典再讀、歷史探微、民族文化、譯介述評(píng)四個(gè)欄目,相關(guān)文章從不同角度關(guān)注了理論前沿、歷史文化、民族分類與中華民族宗教文化的多樣性以及與社會(huì)認(rèn)同以及宗教信仰與文化變遷等,資料豐富,觀點(diǎn)鮮明,具有一定學(xué)術(shù)參考價(jià)值。
書籍目錄
經(jīng)典再讀
理性化的命運(yùn)與價(jià)值行動(dòng)的難題
——理解韋伯的一個(gè)線索 馮雨萱
歷史探微
鳩摩羅什譯《中論》“空”概念的詮釋研究 李進(jìn)
古代中國邊疆移民的多元文化考察
——以劉淵興漢立國為例 張晉
合縱連橫:開天之際唐蕃軍事斗爭的新趨向 李學(xué)東
簡析土族的形成與蒙古族之關(guān)系
——兼論“土達(dá)”的來源及歸宿 秦永章
民族交融背景下的元代河南哈剌魯人 李喬
試述安多拉卜楞寺與西藏哲蚌寺的法緣關(guān)系 張利軍
維多利亞時(shí)期的英國文學(xué)與基督教傳統(tǒng)的研究 張靜波
宗教認(rèn)同與國民認(rèn)同的歷史沿革探析:以波蘭為例 劉泓
民族文化
拉卜楞地區(qū)尼姑的生活習(xí)俗 華銳·東智
被放逐的僧侶:哲蚌寺、色拉寺流傳“糌粑團(tuán)印記”類型故事的搜集和解讀 魏毅
亞洲文明交流互鑒視角下南傳上座部佛教相關(guān)器物的跨境流通現(xiàn)象觀察 張海超
升平之境——德欽阿墩子的人與神 馬斌斌
民間信仰的建構(gòu)與傳承:以山東定陶仿山廟為中心的考察 胡夢(mèng)飛
俗世中的他界:北京東岳廟神靈譜系考察 梁茵
從葉向高到嚴(yán)復(fù):陽岐陳文龍信仰的臺(tái)灣因素新探 劉濤
“一帶一路”視域下湄洲祖廟發(fā)展分析 謝雅卉
譯介述評(píng)
猶太人職業(yè)選擇的決定因素:外界限制、少數(shù)群體需求還是教育 博蒂奇尼 埃克斯坦因 著尚萬里 譯
改革開放40年來的中國伊斯蘭教研究:回顧、反思與展望 馬成明
原標(biāo)題:《古代中國邊疆移民的多元文化考察》
本文為澎湃號(hào)作者或機(jī)構(gòu)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fā)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jī)構(gòu)觀點(diǎn),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diǎn)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fā)布平臺(tái)。申請(qǐng)澎湃號(hào)請(qǐng)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