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柳理對話祝安順:熱浪或時雨?中華經典教育在當代何以可能
政邦茶座>>
暑假出游的熱浪,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迅猛升溫。若不刻意提醒,很多人會忘記,這是三年新冠疫情全面解封后第一個能真正自由出行的暑假。隨之而來的,還有遍地開花的研學班、夏令營及教師研修活動。掃描其主題,你會發現,其中的大多數項目,都與中華傳統文化有著強關聯。也就是說,在中國大陸的青少年假期消費供應鏈上,傳統文化相關內容已占有相當高比例。
這不難理解,一方面,“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研學傳統,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另一方面,過去十年,國家層面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視程度全面升級,在基礎教育方面的表現最為顯著,例如,2017年開始采用的中小學“部編本”,古詩文篇數大幅增加;2018年開始的普通高中新課標,古詩文背誦量從14篇(首)增至72篇(首);特別是中高考,逐年增加傳統文化內容的比重,以考試“指揮棒”驅動傳統文化在學科中的全面滲透。
傳統文化教育以高調的姿態強勢回歸國民教育體系,是過去十年來顯而易見的現象。其背后的象征意義,或者說造成這一大勢的根本動因,官方及主流媒體均已反復闡釋,茲不贅言。真正需要下沉思考的,是如何因應這一時勢,將傳統文化的“熱浪”轉化為中國教育的“條風時雨”,讓傳統文化教育的目標及相關要素,在官方與民間變成共識,從而有效地推動中國教育的現代化,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通俗點說,傳統文化教育能否在當代中國生出茁壯的根,發出健康的枝條,開出鮮麗的花,結出安全的果,需要有嚴謹可行、與時俱進的“方法論”。這是個系統性的技術活,誰在思考?誰堪擔當?
2023年3月,祝安順的專著《中華經典教育三十年》由清華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該書對于教育研究者和實踐者整體把握傳統文化教育的發展歷程、深入探索傳統文化教育的現實策略,具有相當的啟示價值。應該說,“經典教育”只是作者在研究傳統文化教育這個宏大課題時所使用的一個工具。祝安順認為,民族核心經典蘊藏著民族的思維本源、價值方向和意義世界,而經典教育訓練了整個民族的思維方式。比如,中華經典教育,千百年來影響著中國人的歷史思維和“象思維”。而這種教育在“現代化”的百年大潮中如何調適,中小學階段有無必要以及能否開展以思維訓練為主的經典教育,則是此書關注的重點。——這正是上文所提及的“系統性的技術活”。如何解構這個大問題?祝安順的研究,究竟觸及了現實當中哪些真問題?
本期政邦茶座嘉賓:
祝安順,字易欣。安徽樅陽人。清華大學訪問學者。中華書局編審,深圳大學副教授,中國教育學會傳統文化教育分會副理事長,深圳市金聲玉振黃金與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等。致力于中華經典的課程化、常識化、體驗化研究。在《孔子研究》《全球教育展望》《中國教育報》《中華讀書報》等發表文章多篇。著有《中華經典教育三十年》。
本期政邦茶座主持人:
政邦智庫副理事長 柳理。鳳凰網國學頻道創始主編,華人國學大典策劃顧問、總撰稿,深圳大學中國傳統文化創造轉化研究所兼職研究員,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國學研究與傳播中心客座研究員,中國文化書院會員。

柳理:您以專業研究者的視角關注中華經典教育,迄今已有多久了?
祝安順:我對經典感興趣,從1994年入大學時就有苗頭,四年本科反復閱讀的一本書就是陳戍國先生點校的簡體橫排的《四書集注》(岳麓書社版),那個時候很難買到其他版本特別是中華書局的繁體豎排版。現在我還清晰記得的就是根本讀不懂,也不知道朱熹的章句和集注有什么特別的地方,但一直反復閱讀,一直堅持從頭看到尾,這本書被我翻得快破碎了,到現在還帶在身邊,它具有一種象征意義。
要說對經典教育有興趣,有研究的問題意識,是從2000年準備碩士論文時候開始的,我后來寫的碩士畢業論文就是《清末新政經學課程設置演變之研究》,蔡元培先生就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時,發布的政令中就有“小學讀經科一律取消”和“廢除經學科大學”這兩條,我就試圖追問這一教育法令背后的教育制度變遷和教育思潮演變。
如果從2000年開始計算,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
柳理:毋庸置疑,經典教育是當下很重要也很宏大的課題,在您的著作里,我注意到您梳理和列舉了國內外很多學者的相關論述與觀點。如果做個概述,您覺得當前中國正在鋪展開的“經典教育運動”,最主要的問題或者局限在哪兒?
祝安順:最主要的問題就經典教育能不能課程化,尤其是在基礎教育階段開設課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西方近代以來的教育制度和學科制度席卷全球的態勢之下,在現代的中國教育仿照歐美為主的外來教育制度和課程制度的現實面前,經典課程化解決的前提和基礎性問題就是傳統的國學經典課程與現代性學科化課程的關系問題。他們之間是先后替代關系,是平行共生關系,是滲透融合關系,還是異質沖突關系(有你就沒有我,有我就沒有你),抑或是一種輻射關系。
這個問題從明中后期就已經開始萌芽,到1860年以后突起,到1895年以后備受關注,中西、古今、新舊之學在近現代史上沖突和融合,在教育課程化上面體現得更加明確。如果兩者是替代關系或者是沖突關系,那就保留作為替代者而去除被替代者就好,或維持占據優勢的西方化的課程制度一統的局面就可以了;如果兩者是平行共生關系,經典課程與外來課程可以共存,但在目前中小學生課程負擔不斷加重而經典學習又需要較多學時的前提下,勢必造成教學的負擔,這是當下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和中小學教育管理者最難以協調的問題;如果兩者是滲透融合關系,就需要時間將中外文化進行多方面的交融滲透,實現深度融合,這是目前現實中很多中小學校在努力探索的一種方式。
然而我認為作為中華文化的核心經典,它對當下的學科化課程是一種輻射的關系,也就是看上去沒有內容的交叉,其實經典課程的開展,塑造的是課程參與的教師和學生,對他們的教學態度、教學關系和教學方式產生間接的構建作用,一個好的課程教學,一定是教師和學生的文化共識、思維共振、價值趨同和意義共享。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在中國大地上辦有中國特色的教育,就必須在接受外來課程設置的同時,適度、合理和便捷地開展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經典課程教學,不僅有利于課程教學的開展,也有利于人才的健康成長。
柳理:您在書中梳理了中華傳統文化教育的百年歷程,以世紀為刻度,您如何評價當下的這場傳統文化復興運動?
祝安順:發軔于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這場經典傳承發展活動,我認為有如下幾個特征:
第一,自下而上,從自發到自覺;
第二,海內外同步,全球華人參與,傳統文化尤其是經典試圖再次進入社區生活,進入學生的學習課程,力圖成為文化傳承發展和文化育人的重要一部分;
第三,持續時間長,影響廣泛,作為一次重要的歷史事件,必將載入史冊;
第四,參與主體多樣,形式豐富,內容多樣,但目標不一,爭論激烈,效果不一;
第五,中華經典從誦讀到閱讀再到研讀,經典傳承發展活動必將從自發的文化活動向自覺的文化教育發展。
柳理:您在序言里所說的“對中國教育的未來我們充滿信心”,是否包括了對中華經典教育/傳統文化教育的信心?這種信心因何而來?
祝安順:是的。這種信心,一是來自三千年中華文明發展歷程中形成的一體多元的文化格局,二是以儒道兩家文化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一直以來不斷接受內外部其他文化的沖擊和融合,三是當今文化維持多樣性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同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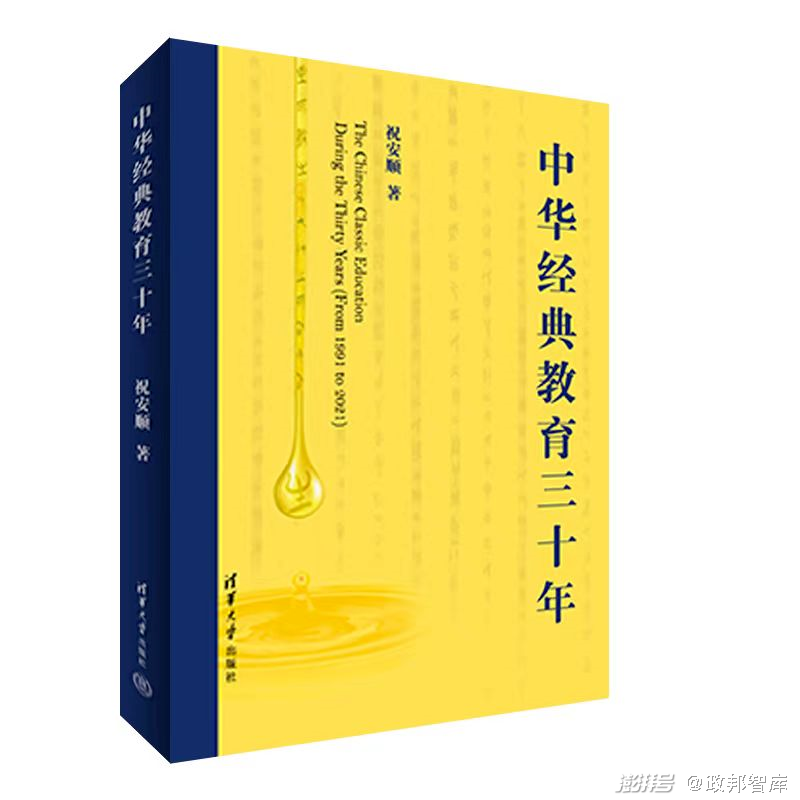
柳理對話祝安順:熱浪或時雨?中華經典教育在當代何以可能
柳理:“經典教育訓練思維方式”,這個觀點我非常認同。當然,思維的對象、目的不同,方式也會不同。中華經典的“工具包”里,哪些“思維方式”是西式教育不太重視或者有所欠缺的?能否簡要介紹一下。
祝安順:首先感謝您對這一觀點的認同,很多師友讀了我的書之后,也基本認同這個提法,很是好奇,特別希望我能把這個提法說清楚,更希望能有操作性。
其次,我要聲明,如何通過經典教育訓練思維方式,主要是中華民族的特有思維方式,這是我下一階段工作需要攻克的難題,對我而言是最大的挑戰問題,如果這一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在我的思考中,經典教育的主要目標就落空了。
第三,根據王樹人先生、劉長林先生、張祥龍先生、王南湜先生和劉家和先生等前輩學者的研究,他們分別從哲學、藝術學、易學、醫學、兵學、道學和史學等角度研究論證中華民族具有一種本源性的象思維方式,而西方科學具有概念思維方式,兩者是不同但可以并存的思維方式,在當今,概念思維方式占據了我們日常生活和學術研究的主導地位,而象思維方式卻需要重新挖掘和弘揚。
第四,象思維方式體現在哪里呢?它鮮明地體現在漢字、中醫和琴棋書畫太極等文字、文藝和文化現象中,人們也能清晰而準確地體驗到這種中華民族特有的思維方式。
第五,用什么方式來訓練我們的思維方式?最佳的就是《周易》,這部經典里蘊含著濃厚的象思維方式,周易學本來就分為象數派和義理派,象是周易學當中重要的術語之一,其物象、意象和法象的詮釋活動貫穿在《周易》的經文和傳文以及歷代的注釋之中,如果我們有意識地從訓練民族思維方式的角度,重新整理和開發《周易》中的象思維資料,應該可以重新激活《周易》這部古老的經典。當然,我們民族語言中的歇后語、語文教材里的經典課文、歷史典故、文學故事、詩文意象等都可以作為訓練民族思維方式的教學材料。
柳理:這些年來,國家層面出臺了很多文件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學術界、教育界的討論也不絕于耳,總感覺“行動派”的聲音弱于“建言派”。比如,中華經典教育在學校的“落地”問題,繞不開課程體系、教學標準與師資隊伍等要素,那么,“行動派”需要的是有效的標準和有用的工具,就您的研究看,目前全國中小學校里的中華經典教育,處于什么樣的水平,專家們提供的“工具包”、教育主管部門提供的“標準”,夠用嗎?好用嗎?
祝安順:進入21世紀以來,傳統文化教育的發展,整體上是不斷推進,不斷探索,不斷完善,不斷提升,國家政策不斷出臺,各地方政府也是積極落實,各級各類學校也積極開展。對于各類有關經典教育的課程體系、教學標準和師資養成的理論和實踐成果,社會各界還是非常關注的,但是由于經典教育在中小學校當中設置課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尚缺乏共識,這些理論和實踐成果具有很重要的借鑒意義,每一步都走得非常難的,都很有歷史開拓意義,但要想從根本上來解決經典教育的課程化問題,可能還需要一段時期探索和實踐。
柳理:有人說,對于“00后”而言,對未來的興趣遠大于對過去的興趣。您對此是否認同?面對新生代,教育工作者以及家長,如何在教育理念和教學方法上尋求科學與人文、世界眼光與中國底色的平衡?或者說,有沒有必要去追求平衡?
祝安順:這個問題非常好。過往的歷史已經無法重復,當下的發展受制于很多社會因素制約,作為解決人的教育的重要途徑的經典教育,只有把眼光看向未來。從一個實事求是解決問題的角度而言,經典教育就是面向未來的,因為經典具有永恒性和元初性,挖掘這一點才能讓經典的光芒照亮人類歷史的始終。
比如在親情、友情、生死、意義等方面所呈現的人性問題,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人與他人的關系問題,人與智能機器人的關系問題,這些都是歷代人都需要思考,需要借助經典開展深度思考的問題,經典在這里會提供樸素的、直接的、本真的參考。
中小學基礎教育界很早就提出要培養“有中國心的世界公民”這一教育追求,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設想和追求,在全球文化一體化沒有到來之前,每個民族都不能也不應該丟棄自己的優秀文化,但這種優秀是異質的優秀,不是普遍的一致文化,就是與全球化普遍化的文化之中保持民族文化的差異性,這其實就是多元差異文化與一元普遍文化之間的一種平衡。
基礎教育界追求學習者的全球化與民族化的文化平衡,既是一種理想,也是一種實踐,其導致的結果就是對于新生代而言,不僅要追求文科和理科的平衡,追求身心的平衡,更要在世界眼光下追求一種全球化與民族化的平衡。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