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著作權法修改后,青年編劇的署名權是否還能被任意剝奪?
【原創】文/汐溟
對青年編劇而言,署名權較報酬權更為重要。署名權決定著編劇的職業前景和未來。但青年編劇的署名權被任意剝奪的現象卻也普遍存在。剝奪的方式以如下幾種情形較為常見:第一,在編劇聘用合同中明確約定編劇僅享有報酬權而不享有署名權;第二,要求編劇出具放棄署名權的書面聲明;第三,編劇在勞動關系存續期間創作劇本,僅能領取薪酬但無權獲得署名;第四,既無書面合同關系也無勞動關系,編劇受邀請、委托或其他原因創作劇本,口頭約定給予署名但實際上未兌現承諾。第五,以助手或其他協助者身份參與劇本創作,創作內容被劇本使用,甚至是構成其主要內容,但未被署名。無論哪一種情形,造成的結果均是編劇署名權的喪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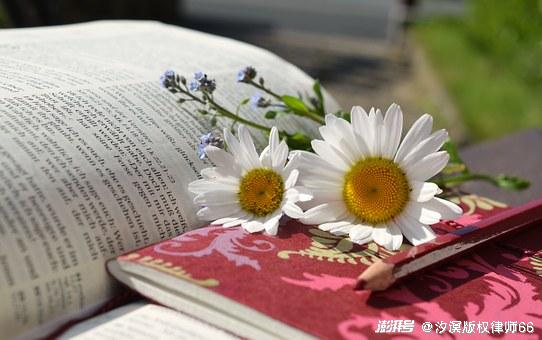
署名權,是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權利。傳統著作權理論認為,署名權具有“父權”的色彩,因其彰顯的是作者與作品之間的創作關系,體現的是作者對作品的創作者的身份。甚至有觀點認為,作者的四種人身權中,最為重要者便是署名權。青年編劇初涉劇本創作事業,行業地位低,話語權弱,創作劇本后卻無署名甚至是被署他人之名,坐視自己耗費心血創作的智力成果被他人占有卻無能為力。即戕害編劇的權益也不利于行業的健康發展。但值得注意的是,剝奪編劇署名權的行為卻鮮有訴訟發生,青年編劇較少有因署名被剝奪而以法律途徑維護權益者。這種現象的背后是青年編劇對著作權法及署名權相關規定的誤解。他們普遍認為,合同約定不享有署名權或自己放棄署名權的聲明是有效的。易言之,前述諸種剝奪署名權行為或是合法,或是其無力對抗,他們只能被迫接受。2020年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改,且不日將生效,我國的著作權法制環境將進入新的時代。著作權法本次修改,是否能為青年編劇帶來曙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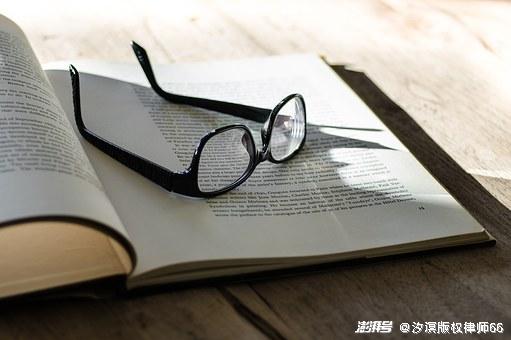
《著作權法》(2020年修改版)對“署名權”的規定予以保留,并無變化,依然是“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權利(《著作權法》第十條第二項)”。但這是對署名權的基本規定,對特殊作品如職務作品、委托作品和合作作品等又有其特別規定。本文認為,編劇的署名問題應區分作品的性質、編劇自身情況及創作事實綜合判定。
首先,署名權的內容中包含署真名、署假名,同時還包含不署名。作者有權拒絕在作品上署名。青年編劇不在作品上署名也是其行使署名權的方式。因此,編劇的放棄署名的聲明,其含義應解釋為不在作品上署名,不對外公開編劇與劇本真實的創作關系。該聲明本身也是其行使署名權的一種方式,而非其不享有署名權。本文認為,署名權屬作者的精神權利,自作品創作完成之日便產生,具有天然性和當然性,與作者人身緊密依存。作者不得放棄,即便放棄也無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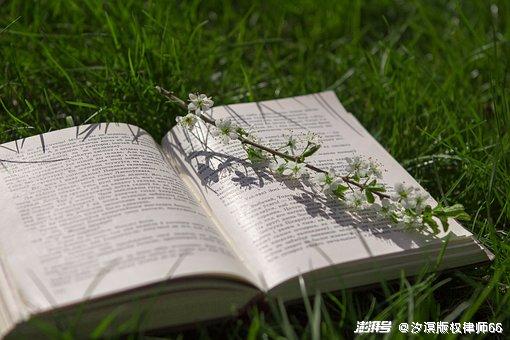
其次,對委托作品的規定,著作權法未作修改,仍為“受委托創作的作品,著作權的歸屬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過合同約定。合同未作明確約定或者沒有訂立合同的,著作權屬于受托人(原《著作權法》第十七條,《著作權法》修改后第十九條)。”結合本文所涉話題,該條可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編劇受委托創作劇本,雙方簽訂有合同且在合同中明確約定,編劇不享有署名權。那么編劇無署名權的條款是否有效?《著作權法》(2020年修改版)對此未作規定。《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權案件審理指南》第3.7條第二款規定,“受托人與委托人對著作人身權的行使進行約定,未違反公序良俗的,不宜一概認定無效,可以根據合同內容進行審查。”著作人身權中包含署名權,盡管規定的是“行使”而非歸屬,但該處理方式對本文問題的解決有借鑒意義。易言之,若委托合同中明確約定編劇不享有署名權,該約定不必然無效,其效力的審查應取決于合同內容。其次,委托合同中未明確約定編劇無署名權,編劇享有署名權。第三,委托人與編劇未訂立合同,編劇當然享有署名權。此處的未訂立合同,應作狹義還是廣義理解?狹義是指雙方無書面合同,廣義是指不但無書面合同,而且也無口頭協議,即委托人僅要求編劇創作劇本,但未提及報酬或署名,或者僅提及報酬未涉及署名問題。本文傾向于狹義解釋,即只要無書面合同,編劇便應享有署名權。因為狹義解釋顯然更能保護作者的權益,這也與在無明確約定時,作品著作權歸屬于受托人的精神一脈相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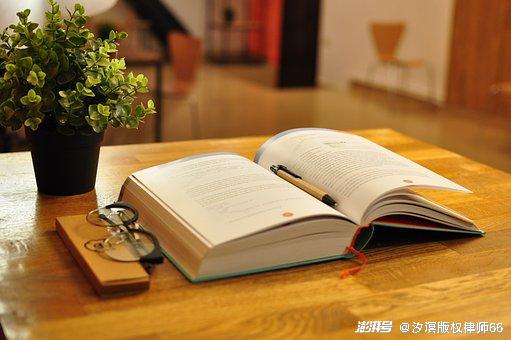
再次,編劇如果在單位如編劇工作室、影視公司任職期間所創作的劇本,單位未對其署名,該行為是否正當合法?編劇是否享有署名權?本文認為,應根據編劇的職務、合同約定內容及劇本的創作情況綜合判定作品的性質,即先區分出作品的法人作品、特殊職務作品、一般職務作品或者個人作品的法律性質,進而根據著作權歸屬來認定署名行為的合法性。逐一分析:
第一種情形,編劇在單位職務是編劇,勞動合同約定其工作內容為創作劇本,且勞動合同中約定編劇在任職期間,完成單位安排的工作任務所創作的劇本,劇本的著作權由單位享有,編劇不享有署名權。此種情形下,編劇創作完成的劇本性質涉及到是否為法人作品的認定問題。《著作權法》(2020年修改版)第十一條第三款規定,“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主持,代表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意志創作,并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承擔責任的作品,法人或者非法人視為作者。”同時該條第一款規定,“著作權屬于作者,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如編劇的創作由單位來組織主持,代表的是單位的意志,且由單位來承擔責任,同時滿足前述三個條件,則該劇本的性質可為法人作品。單位是劇本的作者,署名權也由單位享有,編劇除薪酬待遇外不享有署名權。此外,若勞動合同中未對署名一事作出約定,是否可因其約定不明,編劇可主張署名權?本文認為,是否約定署名不是法人作品的構成要件,對法人作品的認定不生影響,自然也就對署名權的歸屬無影響。

第二種情形,除前述構成法人作品的情形外,編劇在單位任職期間所創作的劇本,均享有署名權。編劇在任職期間所創作的劇本,按其性質可分為一般職務作品和特殊職務作品。《著作權法》(2020年修改版)第十八條規定,“自然人為完成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工作任務所創作的作品是職務作品,除本條第二款的規定以外,著作權由作者享有……”若編劇創作的劇本不符合法人作品的要件,則更多的具備一般職務作品的性質。編劇是劇本的作者,自然也就享有署名權。即便勞動合同中明確約定編劇不享有署名權,基于作品的一般職務作品性質,編劇依然有權依據著作權法的規定主張署名權。此外,基于劇本的創作特點,一般不具特殊職務作品的性質。《著作權法》(2020年修改版)第十八條第二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職務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權,著作權的其他權利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享有,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可以給予作者獎勵:……”即便是特殊的職務作品,作為作者的編劇同樣對劇本享有署名權。
第三種情形,盡管具有編劇身份,但在用人單位擔任的是非編制職務,工作內容中不包含劇本創作的任務。編劇于此期間創作的劇本,除非構成法人作品的情形,否則無論屬于職務作品還是其個人作品,編劇都享有署名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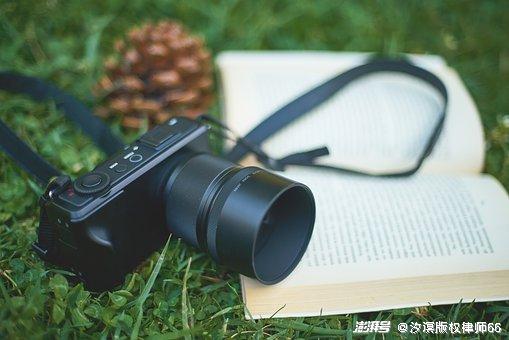
最后,討論多名編劇一起創作劇本的情況。如發生多名編劇一起創作劇本,但均未簽訂合同,但對其中某一位編劇不予署名的情形。我國《著作權法》(2020年修改版)第十四條規定,“兩人以上合作創作的作品,著作權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沒有參加創作的人,不能成為合作作者。”只要編劇參與劇本的創作,且對劇本貢獻出獨創性智力勞動,其成果為劇本所吸收,編劇即具有作者身份,其署名權便存在。其次,若參與創作的編劇作出放棄署名權的聲明,其含義應解釋為以不署名的方式來行使署名權,而非其不享有署名權。再次,若多名編劇合作創作劇本但有合同關系,但于合同中明確約定不予某位編劇的署名,該約定的效力可參照委托作品的規定來處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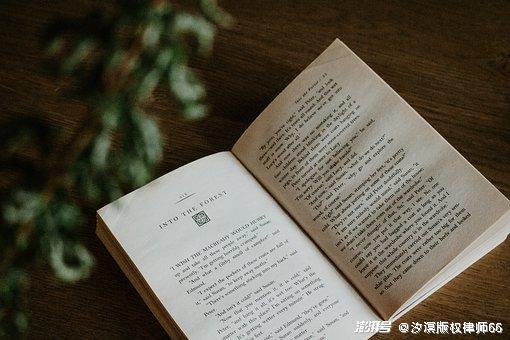
綜上,本文傾向于認為署名權屬于作者的人身權,且為至關重要的人身權。該權利因涉及作者人身及精神權利,應不得放棄,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剝奪。編劇放棄的意思表示,無論是合同還是單方聲明均不該發生效力,而任何人對其的剝奪行為也因違反公序良俗而可被否定或追責。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