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弗朗茲·法農(nóng):黑皮膚,白面具
有些人把鐵燒熱,是為了趁熱打鐵。我們更愿意燒熱人的身體、激發(fā)人們體內(nèi)的激情之后再離開。我們最終會得到這樣一個結果:人類通過自燃,可以保持火焰的存在。
——弗朗茲·法農(nóng),《黑皮膚,白面具》
一、生命的怒焰
弗朗茲·法農(nóng)(Frantz Omar Fanon,1925-1961),一個出生于法屬西印度群島馬提尼克島法蘭西堡富裕中產(chǎn)階級家庭的黑白混血兒,接受了白人的教育,操一口腔調(diào)純正的法語,青少年時代有著單純的殖民宗主國認同。這樣一個法農(nóng),正是自己筆下描述的“想要變成白人”的有色人。

弗朗茲·法農(nóng)
法農(nóng)的父親任職于殖民地政府機構,而母親身上混雜著法國東部阿爾薩斯某個家族的白人血統(tǒng),這使法農(nóng)的出身掛上了幾分貴族色彩。憑借這些與殖民化進程相關的條件,法農(nóng)得以進入殖民地公立學校,接受良好的“法國式”教育。其典型的模式是,課程用法語教授,學生被告知應努力成為法國人,其目的在于規(guī)訓殖民地臣民的法國認同,使其心智發(fā)展自幼年時代起便與法國緊密相連。法農(nóng)早期步入殖民地精英教育軌道所接受的同化教育,阻滯了真實自我和自覺觀念的形成。
不過,這種單純的宗主國認同很快受到了挑戰(zhàn)。二戰(zhàn)期間,讀中學的法農(nóng)經(jīng)歷了維希法國政府的高壓統(tǒng)治,并在老師艾梅·塞澤爾(Aimé Fernand David Césaire)的影響下,開始對種族意識及其根源產(chǎn)生了認知。1943年,法農(nóng)懷著對于宗主國的忠誠抵達歐洲,加入法國自由軍團,先后在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服役,并參加了阿爾薩斯的戰(zhàn)事。他負了戰(zhàn)傷,立了功勛,體驗了為法國而戰(zhàn)的榮譽。不過,在軍旅生活的大坩堝里,同時煎煮著與這種英雄主義情懷和價值相矛盾的種族主義情緒,即白人對黑人“理所當然”的蔑視。法農(nóng)第一次經(jīng)歷了黑色皮膚所代表的意義與母國認同之間的矛盾,并滋養(yǎng)了義憤情緒與反抗精神。
二戰(zhàn)后復員的法農(nóng)返回馬提尼克,通過了高中會考,于1946年再赴法國,次年決定前往里昂學醫(yī),遂轉向精神病學專業(yè),并在此后的學習中廣泛涉獵哲學、人類學與文學,接觸了弗洛伊德、拉康、榮格等人的精神分析學說,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與現(xiàn)象學等理論。在此期間,他雖未加入任何黨派,但參與了反殖民主義運動,且參與了殖民地留學生小型期刊《達姆-達姆報》(Tam Tam)的編輯工作。1951年法農(nóng)取得心理學家資質,在圣亞爾邦(Saint-Alban)精神病院待了一年有余。其間,他師從社會主義精神病學家托斯克爾(Francois Tosquelle),為后來的精神醫(yī)學與政治之路奠定了基礎。法農(nóng)發(fā)現(xiàn),對罹患精神病的黑人的治療與黑人主體性的解放之間存在密切關聯(lián)。1952年,法農(nóng)在《思想》(Esprit)雜志上發(fā)表第一篇文章《北非癥候群》(“Le Syndrome Nord-Africain”),探討背井離鄉(xiāng)的北非勞工所承受的身心痛苦,他們與故鄉(xiāng)切斷了聯(lián)系,卻無法達成終極目標。同年,法農(nóng)發(fā)表第一部至今仍產(chǎn)生持續(xù)影響的重要研究著作《黑皮膚,白面具》(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殖民宗主國大都市的白人并不認可他作為精神病科醫(yī)生和知識分子的智識資質,此時的法農(nóng)更為敏銳地感受到了種族歧視。該著正是法農(nóng)基于自身黑皮膚的經(jīng)驗,深入殖民主義雙重主體的身體與心靈基底進行探索后,所發(fā)的冗長而微妙的怒言。這是最早審視殖民地種族主義所產(chǎn)生的破壞性影響的文本之一。
1953年,法農(nóng)通過精神科醫(yī)師資格考試,遂被派往阿爾及利亞的布里達(Blida)精神病院。此時正值醞釀已久的阿爾及利亞革命爆發(fā)前夕。在醫(yī)院,他救治窮人、殘疾人以及受戰(zhàn)爭恐怖陰影所影響的人。同時,他與院方傳統(tǒng)精神醫(yī)學格格不入,其主張也與阿爾及爾派精神醫(yī)師所奉行的“土著的原始狀態(tài)”理論相齟齬。他在院內(nèi)倡導了一場小型的精神醫(yī)學革命,引入“社會治療法”,與信奉伊斯蘭教的本地人一同試圖恢復本土的文化、語言、生活習俗和社會組織,旨在形成他們的本土文化意識與認同。與底層民眾的接觸、對當時阿爾及利亞殖民地現(xiàn)狀的體察,以及其他種種因素很快將他推向了政治反對派的立場。同時更為復雜的是,他本人在阿爾及利亞的處境并不樂觀,他發(fā)現(xiàn)自己非但不是被壓迫者,反而被視為壓迫者——即歐洲裔的法國人,因而既受到上層的鄙視,又不被下層所信任,這種經(jīng)驗決定了法農(nóng)對種族主義、殖民主義結果的反思與分析不可能是簡單的對殖民者的極端抵抗。1954年,阿爾及利亞獨立戰(zhàn)爭打響,次年,法農(nóng)加入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FLN(Front de Liberation Nationale),其反殖民主義立場日漸聞名。后應“阿爾及利亞之友”(Amities Algeriennes)運動的動員與請求,他開始為一些飽受精神錯亂之苦的游擊隊員進行醫(yī)治。在精神病學實踐與政治活動的交替進行中,法農(nóng)全力投身于阿爾及利亞的獨立戰(zhàn)斗。
1956年底,法農(nóng)公開辭去醫(yī)院職務,稱自己無法解救某些人,“使他們得到應有的待遇,這是一個把剝奪人權及不平等和謀殺當成合法原則的國家,當?shù)厝嗽谧约旱膰依镉肋h都是瘋子,生活在一種完全沒有人格的狀態(tài)下。”法農(nóng)公開的反殖民主義與支持殖民地獨立的主張與立場,導致他1957年被驅逐出阿爾及利亞。法農(nóng)隨后旅居法國,繼續(xù)為不可逆轉的阿爾及利亞獨立趨勢營造輿論聲勢。在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法國總會的協(xié)助下,他前往民族解放陣線的境外組織所在地突尼斯,正式與法國決裂。他在突尼斯繼續(xù)從事精神病醫(yī)學與政治活動,逐漸成為阿爾及利亞革命的主要發(fā)言人之一,并定期為民族解放陣線的周報《斗士報》(El Moudjahid)撰稿,兼任編輯之職。盡管親眼目睹民族解放陣線內(nèi)部暴露的種種問題與矛盾,包括政治代表與軍隊之間愈發(fā)嚴重的爭執(zhí),他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其民族解放運動。法農(nóng)去世后的1964年,其發(fā)表于《斗士報》的文章,以及部分未出版的文本集結成書,命名為《朝向非洲革命》(Pour la revolution Africaine)。為阿爾及利亞獨立解放戰(zhàn)爭而奮斗的經(jīng)歷,不僅改變了法農(nóng)的生命運動軌跡,并促使他從基于黑膚色經(jīng)驗的種族主義分析轉向了更廣泛的殖民地政治、經(jīng)濟、文化領域的實務經(jīng)驗和去殖民化進程的關注。
他的活動也不再局限于北非地區(qū),而是越發(fā)關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民族解放議題,并進一步轉向了聲援全非洲解放、全面反殖民主義的政治書寫。1959年底,他被阿爾及利亞共和國的臨時政府任命為黑非洲巡回大使,奔赴加納、喀麥隆、安哥拉和馬里等地,為各國獨立事業(yè)鼓吹戰(zhàn)斗。同年,法農(nóng)出版《阿爾及利亞革命最后五年》(L'an Cinq de la Revolution Algérienne,英譯為《垂死的殖民主義》,A Dying Colonialism)。此作表明,法農(nóng)處于其反殖民主義與去殖民化理論建構的關鍵捩轉點,一方面,他繼續(xù)運用早期的精神分析理論探索反殖民主義議題;另一方面,他開始在社會學層面思考殖民制度下精神壓迫的根源問題,表現(xiàn)出一種認同革命、選擇行動的明確傾向。種族主義和殖民統(tǒng)治的經(jīng)歷與其在阿爾及利亞所見所聞的極度恐懼并置,該作呈現(xiàn)出一個在壓迫統(tǒng)治體系中充滿緊張和報復、酷刑和暴力、仇恨和謊言的世界。至為明顯的是,法農(nóng)所表達出來的對于種族主義、殖民主義極端統(tǒng)治造成恐怖的憤怒。

1959年,弗朗茲·法農(nóng)在突尼斯舉行的作家新聞發(fā)布會上。圖片來源:IMEC
法農(nóng)的激進言論與行動,使其在生命的最后幾年屢遭暗殺,但總能幸免于難。1960年初,他任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駐加納代表。同年年底,在經(jīng)歷了一次穿越馬里到阿爾及利亞南部邊境的艱苦探險之旅后,他被診斷出患有白血病。1961年,法農(nóng)先后赴蘇聯(lián)與美國接受治療,12月辭世。正是在生命旅程的終年,他于病榻之上口述完成了《全世界受苦的人》(Les damnes de la terre)。在更廣闊的視野下,法農(nóng)探索了殖民主義治下被殖民黑人的主體性受到壓迫的問題。面對生命將盡的威脅與其去殖民化志業(yè)的急迫使命,他以一貫的義憤之辭,表達了支持暴力革命和號召所有殖民地人民團結一心的主張,并訴諸黑格爾-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表達了反抗并超越殖民主義暴力結構束縛的存在主義觀點,即被殖民的黑人經(jīng)過意識覺醒,訴諸暴力反抗,以確立自我信念與價值,克服對于殖民者的恐懼,并迫使后者對此加以承認,由此超越自我與他者的結構對立,在人的存在層面與白人形成真正的互動關系。
二、超越黑色皮膚的自卑
在法農(nóng)短暫的生命里,持續(xù)燃燒著一股因種族主義與殖民統(tǒng)治的制度性宰制所激發(fā)的怒火,從中爆發(fā)的充滿主觀沖動與激情的灼灼言辭,形成了其極具辨識度的、融合詩文與檄文風格的文體。不過,盡管他的著述以激情主觀著稱,但我們?nèi)钥勺R別一個相對完整的、經(jīng)過理性構筑而成的思想體系,即以啟蒙(黑人被殖民者的主體意識覺醒)、抵抗(政治與暴力抗爭)為手段,以人的全面解放(超越存在層面的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的對立結構)為終極目標的反殖民主義、反種族主義與去殖民化的理論體系。
從法農(nóng)的思想發(fā)展歷程看來,其理論建構始于其作為有色人的切身經(jīng)驗,因黑色皮膚所受到的歧視,首先啟迪了他的種族身份意識;從事精神醫(yī)學的學習與實踐之路,則啟發(fā)了他的反種族主義觀念的形成。《黑皮膚,白面具》可被視為其早期理論發(fā)展的代表著述。在書中,法農(nóng)開創(chuàng)了跨學科研究的先風,運用精神分析、精神病理學、社會學、現(xiàn)象學、存在主義哲學等多學科研究方法,探究殖民統(tǒng)治下的黑人心理問題,從黑人的主體經(jīng)驗出發(fā),拷問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制度下黑人的精神異化問題。及至該著出版時,法農(nóng)已體驗了殖民地條件下無所不在的種族歧視,開始對黑人受奴役的狀態(tài)產(chǎn)生質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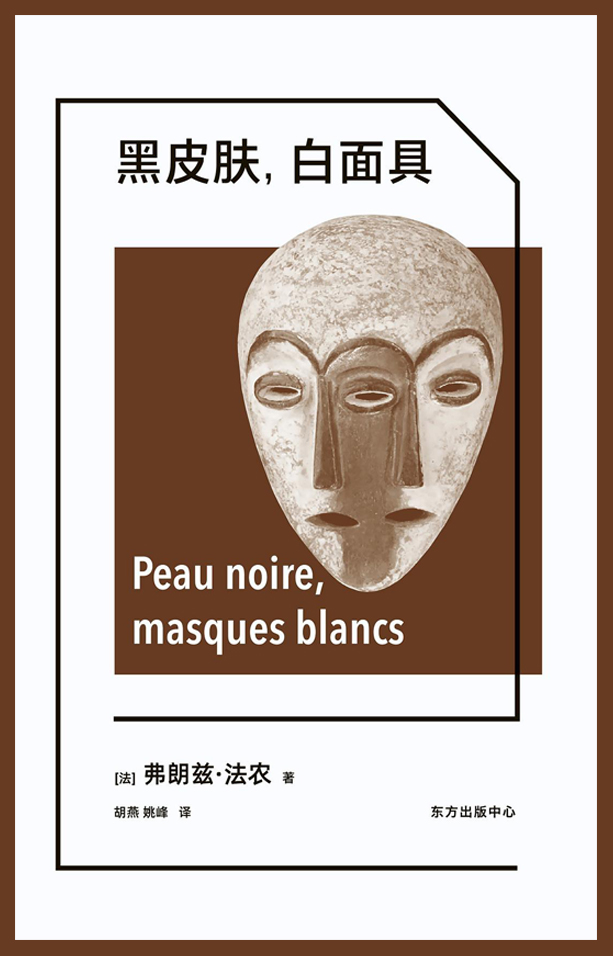
《黑皮膚,白面具》,胡燕、姚峰/譯,東方出版中心,2022年5月版
法農(nóng)依據(jù)對安的列斯人的觀察,在書中描述了以下現(xiàn)象:黑人想要變成白人,因為白人比黑人優(yōu)越。受到良好教育的黑人努力練習發(fā)音,力圖說一口純正的法語,因為掌握殖民者語言的純正程度與他們變白的程度成正比;黑人女性非白人不嫁,因為白人代表美貌與美德;黑人男性的性欲望只針對白人女性,因為只有通過白人女性才能讓他變成白人,獲得白人女性的愛則證明,他達到了白人世界與白人文化的標準。這一切都源于一個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假設,即黑人天生低白人一等,白人是人,而黑人尚未進化為人。
種族主義偏見引發(fā)的糟糕結果是,黑膚色與缺陷等同,膚色于是決定了等級;黑人將自卑內(nèi)化,自覺不如白人。在這種心理結構中,黑人因自卑而患上了神經(jīng)官能癥,其癥狀恰是以上所提及的,并包括以下種種:黑人由于自卑,于是努力證明自己擁有與白人相同的智慧,這種價值的實現(xiàn)途徑只有一條,即白人他者的認可。事實上,黑人對自己黑色皮膚的意識,已經(jīng)是一種自我否定的活動。這些想成為白人的黑人,不惜一切代價尋求白人的認可,結果丟失了黑人的種族自我意識,他們沒有內(nèi)在的價值,總是依賴白人他者的存在,而自身的存在只是為實現(xiàn)白人的存在。
法農(nóng)對膚色的分析表明,種族主義結構中的黑人男女通過稀釋血統(tǒng)來“漂白”黑人種族的欲望,植根于自我憎恨。如前所述,它源于一種觀念,即自己的種族有缺陷,或有需要克服的障礙。種族主義預設將黑人限定在非人性化的位置,這種非人性化反過來又助長了黑人的精神病理傾向。他們陷入雙重困境。一方面,他們被告知,只有表現(xiàn)得像白人,他們才會被認為是人類。另一方面,他們與白人的接觸不斷提醒自己不是白人,也永遠不可能成為白人。他們的任何努力都無法糾正這種狀況。事實上,只要他們接受了這種等級化的預設,他們變成白人的努力只能是神經(jīng)質的精神錯亂表征。
在另一個殖民主體——白人——的心理方面,存在同樣異化的事實。他們的神經(jīng)質癥狀最典型地表現(xiàn)為,無端端把事實上在種族結構中屬于弱勢群體的黑人假想成性侵略者;黑人成了引發(fā)白人恐懼的對象,而恐懼常常與厭惡、痛恨并行。因為對于白人而言,黑人除了代表原始狀態(tài)下的性本能,還代表邪惡與罪惡。法農(nóng)認為,產(chǎn)生這種恐懼的根源在于黑人男性的生殖器神話。白人男性嫉妒黑人男性的性活力,并擔心因此失去自己的女人,繼而產(chǎn)生恐懼。甚至,當接受了白人教育的黑人有能力講一口純正法語時,白人就開始產(chǎn)生危機感,于是他們要么屈尊俯就使用皮欽語與黑人交流,要么有意無意地強調(diào)純正法語與黑人本質之間的差別,其目的卻是將種族間的分離強加于黑人。白人與世界之間是一種占有與征服的關系,當黑人意識到種族主義的壓迫,繼而奮起反抗時,其逃脫束縛的欲望與企圖,成為白人的痛苦與失落。在與黑人漫長的接觸歷史中,白人想要的始終是,不擇手段將黑人固定在他者的位置上,永遠作為白人世界里的次要存在。
當黑人因自卑、白人因恐懼而生仇恨時,必定會出現(xiàn)兩個相互敵對的陣營。在這種以對立為基本結構的殖民語境中,殖民者自詡為一切正面價值的載體,在其單方面宣告的文化統(tǒng)治中,種族歧視本質上是一個制度問題,這個制度賴以建立的基礎,是一個特定種族被另一個種族剝削,人類的一個特定分支被一種假定優(yōu)越的文明所蔑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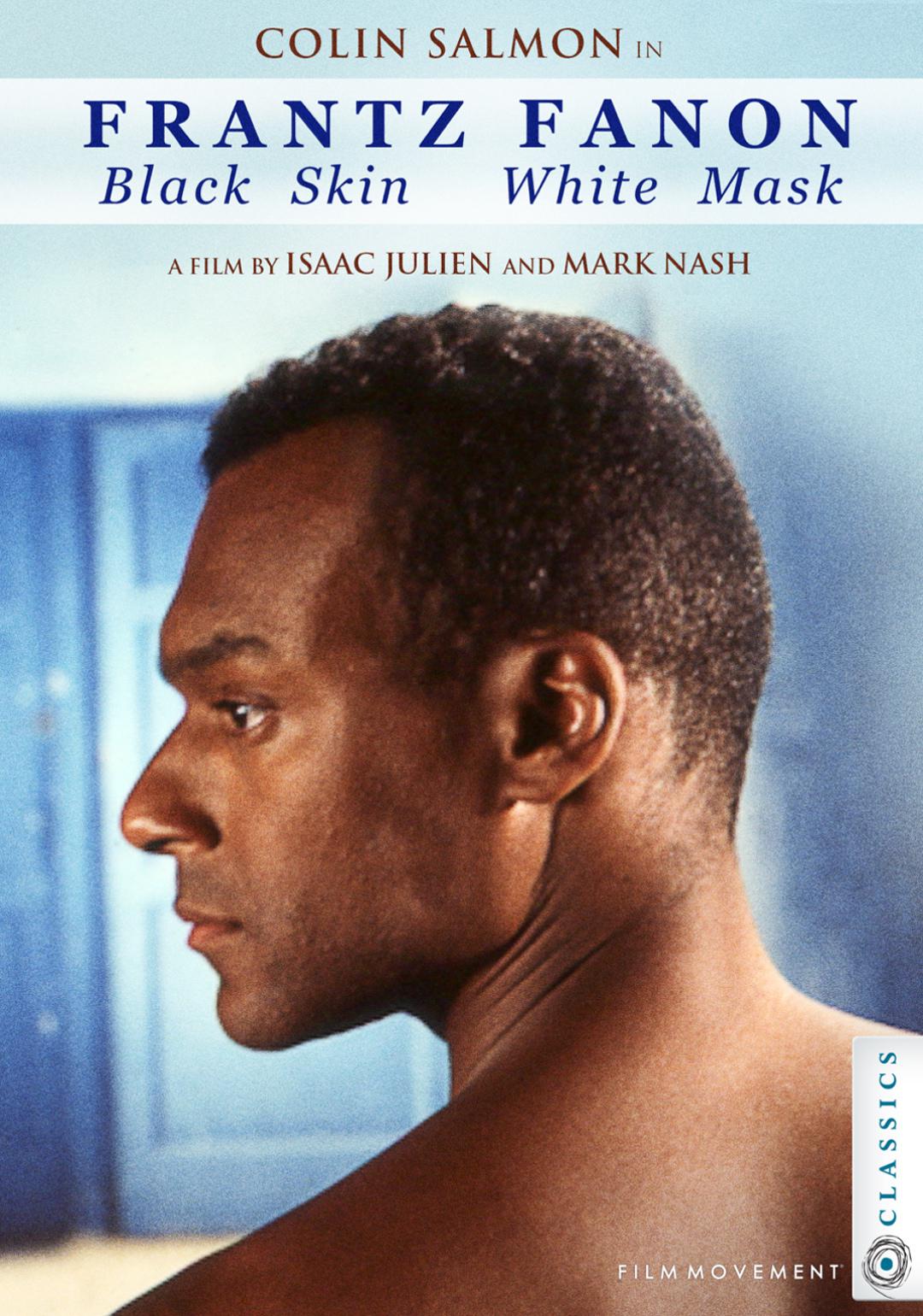
紀錄片《弗朗茲·法農(nóng):黑皮膚,白面具》(1996)海報
當然,法農(nóng)并未止步于揭露這種對立關系。在《黑皮膚,白面具》中,法農(nóng)也描述了一類能直面自己種族的黑人——如法農(nóng)本人、桑格爾(Léopold Senghor)與塞澤爾(Aimé Césaire)等。與“想要變成白人”而失去黑人自我的那一類黑人不同,他們被黑人種族意識驅使著去發(fā)現(xiàn)身為黑人的意義,并意識到白人他者不愿意認可自己,于是決定讓自己為人所知。他們坦然地承認自己是奴隸的后代,企圖去發(fā)現(xiàn)自己種族的文明和本質。黑人性詩人們對黑膚色之美的極度贊美,及其對黑人非理性的本質主義的辯護,極易掉入具有自戀傾向的黑人性之中——但法農(nóng)告訴我們,這種求索依然是黑人進行斗爭、獲取自由的必經(jīng)之路。
在書中那些義憤激昂的文字里,法農(nóng)奮力追尋的目標有三。第一,揭示種族主義造成了黑人的自卑感,這種自卑情結,是殖民主義的經(jīng)濟掠奪與黑人自卑感的內(nèi)化(或曰自卑的表皮化)的雙重運動的結果。第二,呼吁黑人在這兩個層面發(fā)起抗爭——未受教育的黑人在種植園里和工地上起來戰(zhàn)斗,受過教育的黑人在文化、精神領域進行戰(zhàn)斗。第三,在黑人與白人世界之間建立連接,打破白人封閉在白人性之中、黑人封閉在黑人性之中的雙重自戀的情勢,達成雙向的開放,以實現(xiàn)黑人的去異化。黑人既要承認過去被奴役的事實,又不應束縛在為過去復仇的偏執(zhí)中,而應以人的姿態(tài)面對當下和未來,超越種族與歷史仇恨去爭取自由與平等。于黑人而言,這是一種承認自身他者身份、并將白人他者客體化的努力;于白人而言,從未有哪個黑人如法農(nóng)那般,以如此的敏感與睿智,洞察出在黑人種族心理層面運作的白面具,也從未有哪個黑人如法農(nóng)那般,以如此的擔當,以一個觀察者的主體身份,將白人轉化為客體,深入其心理,揭露白人種族面對黑人他者的緊張、焦慮,以及面對黑人斗爭的失落。
三、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法農(nóng)的早期論述盡管呼吁反抗行動,但偏重以黑人的表皮化心理結構為基礎的反種族主義理論建構,更傾向于抽象概念的闡發(fā)。1953年以降,法農(nóng)的精神醫(yī)學實踐和政治活動,與阿爾及利及其他非洲國家的民族獨立與解放戰(zhàn)爭息息相關,這種經(jīng)歷促使其在廣闊的社會歷史語境中,更系統(tǒng)地審視殖民主義以及去殖民化議題,并在理論上轉向激進的行動主義。從其臨終遺作《全世界受苦的人》中,我們已可見較為完整的法農(nóng)思想體系。在其中,他不僅探究了殖民地環(huán)境中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的關系,也提出了解放的條件;不僅是政治的解放,也是文化與個人的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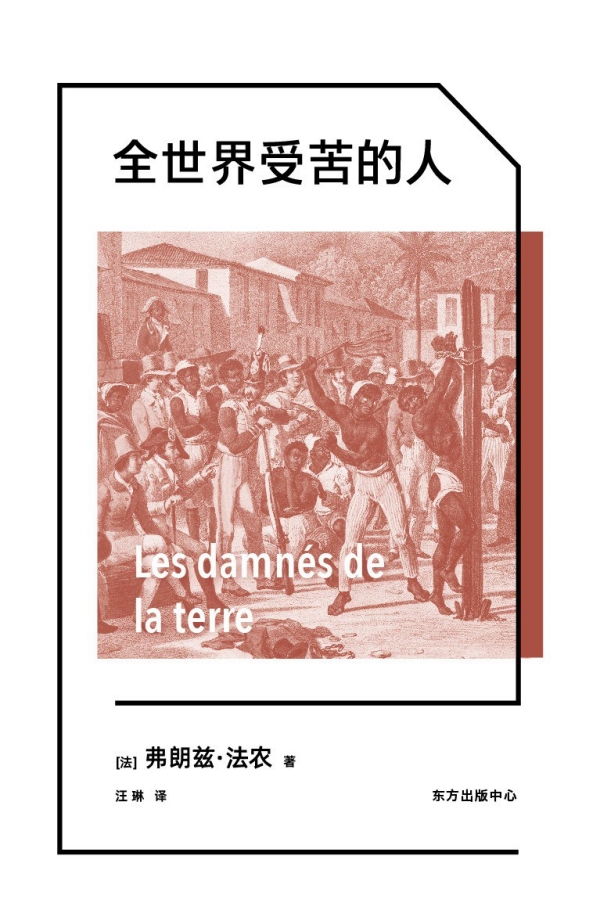
《全世界受苦的人》,汪琳/譯,東方出版中心,2022年11月版
以種族主義為基礎的殖民預設是:被殖民者天生比統(tǒng)治者低劣,其文化與價值同樣低劣。基于這種預設,殖民主義者“理所當然”地將自己的文化與價值強加給被殖民者。以法農(nóng)當時在阿爾及利亞和非洲的見聞經(jīng)歷,他意識到,并竭力使同胞意識到:殖民地是涇渭分明的摩尼教二元論世界,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分別生活在截然分割、對比鮮明的兩個世界,這兩個地帶,并不呈現(xiàn)相互補充的狀態(tài)。為了維持這個分化世界的秩序,殖民者嚴重依賴軍隊和警察所組建的機構及其結構性暴力。當這個二元世界陷入極端失序的狀態(tài)時,被殖民者反殖民、反奴役、反異化的斗爭只能通過暴力手段加以終止。極端統(tǒng)治對個體被殖民者造成的后果是:這個個體沒有出路,只會漸失人性,變成鐵石心腸,或充滿可怕的暴力沖動,最終付諸激進的對抗行為。法農(nóng)注意到,被殖民者對殖民者世界既仇恨,又艷羨。他們在暴力統(tǒng)治中的極度驚恐、壓抑的情緒長期無處宣泄,甚至會轉化成部落間的血腥屠殺,或是使其退縮到傳統(tǒng)巫術文化中集體著魔、徹夜熱舞狂歡的歇斯底里狀態(tài)。但是法農(nóng)認為,這種暴力,不應加以否定,而應加以組織,以服務于解放斗爭。在他看來,暴力之所以必要,恰是因為異化本身即經(jīng)由暴力而造成。以暴力形式展開的反抗殖民壓迫的民族解放戰(zhàn)爭,是一塊利于心理疾患破殼而出的土壤。暴力使被殖民者意識到自己的價值,重獲信心,使被殖民者的主體性認知上升至實踐層面,并獲得殖民者的承認。因此,暴力斗爭是一種能動的實踐,它不只是直接反抗殖民統(tǒng)治的斗爭形式,而且使人民獲得啟發(fā)和教育,使他們團結一致。暴力的目的并不是為了以暴制暴,而是作為補償,以便開拓一個超越殖民主義對立關系的全新未來。
文化領域的戰(zhàn)斗也必須遵循同樣的邏輯。法農(nóng)力圖使同胞認清殖民主義貶損被殖民者過去文化的不光彩企圖。“殖民主義不滿足于把它的法律強加于被統(tǒng)治國家的現(xiàn)在和將來……也不滿足于把人民禁錮在他的網(wǎng)中,清除被殖民者頭腦中的一切形式和內(nèi)容。殖民主義通過一種邏輯上的倒錯,扭曲、破壞、抹殺被壓迫人民的過去。”而這種貶損被殖民者文化、使之異化的企圖與殖民主義的系統(tǒng)工程高度契合,因為,“一切并非偶然,殖民統(tǒng)治追求的總體效果就是說服土著,殖民主義要救他們于水火。殖民主義繼續(xù)有意識地將一個想法灌輸進土著的頭腦:一旦殖民者離開,他們就會重返野蠻、墮落、獸性。”如此,被殖民者即便獲得了政治獨立,也將在精神與心理層面不得擺脫殖民主義的宰制。
基于這種超前的洞見,文化層面的去殖民化,對于法農(nóng)而言尤其重要。他認為,民族解放運動時期,黑人性文化運動聲稱非洲存在一個輝煌的傳統(tǒng)民族文化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并且在被壓迫者的存在層面具有重大意義。從精神和情感的平衡上看,對于過去民族文化的聲稱,有助于促使被殖民者意識到殖民主義貶損被殖民者過去文化的企圖。不過,他也意識到黑人性知識分子捍衛(wèi)傳統(tǒng)文化的局限。為了恢復傳統(tǒng)文化聲譽、努力逃避殖民主義殘留的傷痕,黑人性知識分子在邏輯上陷入了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的思維范式,他們力圖證明一種黑色文化的存在,在方法上卻繼續(xù)與白人文化進行對照。但在法農(nóng)看來,傳統(tǒng)文化在殖民主義的蓄意壓制下,與當代現(xiàn)實已有距離。因此,在一種折中的情況下,他主張用舊文化創(chuàng)生新的民族文化,而且,文化重建不能脫離當前政治的民族解放工程獨自進行。無論如何,民族文化不在過去,其形成和凝固,必須參與到人民的戰(zhàn)斗中才能達成:“我們不能滿足于潛入人民的過往,尋找一些一致性因素,來對抗殖民主義的篡改和貶低。我們應該和人民一起,用同樣的節(jié)奏工作、戰(zhàn)斗,以便明確未來,耕耘已經(jīng)長出茁壯幼苗的土地……民族文化不是一些純潔行為的沉淀物,或越來越脫離民眾當前現(xiàn)實的東西。民族文化是人民在思想層次所做的全部努力,目的是描述、解釋、歌頌人民得以構成和維系的行動。”而知識分子與政治領導人,也只有在深入體察廣大人民的實際行動及生活訴求中,才能真正培養(yǎng)出脫離善惡二元論的辨別能力與責任感,才可能實現(xiàn)民族與民族文化的重建。
在個體的解放層面上,殖民主義導致人的存在危機,因為這種統(tǒng)治是“一方對另一方的系統(tǒng)性否定,是一方瘋狂地決定拒絕承認另一方一切人的屬性。殖民主義把被殖民的人民逼得……常常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我到底是誰?’”反殖民的斗爭與去殖民化的進程,最終要解決人的存在問題,這也是法農(nóng)思想發(fā)展進程中始終未曾改變的終極關切:黑人獲得人的地位和尊嚴,成為與白人具有差異,但平等的存在。利用辯證法超越對立結構的努力,自法農(nóng)早期理論建構時便已開始,且從未停止。這使我們不得不回到他對表皮化的分析。他所見證的黑人與白人的關系,遠未實現(xiàn)黑格爾辯證模式下的主奴斗爭的互動關系——一種人與人之間的絕對的相互作用:人只有將自己的存在強加于另外一人,以得到另外一人的認可時,他才為人。人自身的價值和現(xiàn)實所依賴的,正是那另一個存在以及被另一個存在所認可,而后在雙方互相承認中承認自己。人的生命意義就凝結在另一個存在中。黑人最終要實現(xiàn)的,正是這樣一種與曾經(jīng)的主子白人之間的絕對的相互作用;黑人欲望著的,是做個人,是通過自己的斗爭,獲得同樣作為人的白人的認可。盡管法農(nóng)期待的去異化與去殖民化目標至今仍未實現(xiàn),但正是在為著人的主體性而奮斗的意義上,法農(nóng)的論著超出了作品所書寫的歷史時代與種族分歧的局限。
四、余燼重溫
20世紀60、70年代,法農(nóng)被譽為革命家、第三世界和反殖民運動的英雄。他對殖民主義導致的心理和社會學后果所做的透徹分析,自20世紀中期起產(chǎn)生了程度不同的影響,但其重要性最早出現(xiàn)在英語國家。在美洲,法農(nóng)的思想影響了黑人寫作和流散的黑人身份理論的發(fā)展;在非洲,則影響了泛非意識形態(tài)形式的發(fā)展。
《黑皮膚,白面具》也許是法農(nóng)最經(jīng)久不衰的著述,20世紀50年代,他的種族主義分析與當時盛行于法國的觀念——殖民主義有益于殖民地社會發(fā)展——相抵牾,在法國并不受重視,直至1967年英譯本問世,始在美國以及加勒比海和非洲的前殖民國家受到更廣泛的關注。《全世界受苦的人》出版時在法國引發(fā)的評論褒貶不一,亦未產(chǎn)生大的影響,但其英譯本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受到美國人的歡迎,成為美國黑人權力運動的靈感來源——盡管法農(nóng)對暴力的支持引起了極大爭議。20世紀70年代該作在社會科學領域享有知名度,但80年代逐漸消退,主要原因在于,法農(nóng)所關注的,是已經(jīng)過去的革命時代,他對于被壓迫者精神錯亂現(xiàn)象的解釋、對于暴力的分析和對農(nóng)民力量的關注并不被重視。不過,隨著世界進入全球化發(fā)展階段,盡管殖民主義統(tǒng)治造成的壓迫不再是顯性問題,但前殖民國家所滋生的嚴峻腐敗與新殖民主義、越來越大的南北差距、新的中心/邊緣格局的形成、人的不斷物化等事實的存在,使得法農(nóng)的理論再度在社會學領域受到重視。

弗朗茲·法農(nóng)的墓
自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隨著后殖民理論的興起,法農(nóng)在文學領域獲得越來越多的關注,并在21世紀持續(xù)發(fā)酵。法農(nóng)的分析文本最初問世時,對于宗主國絕不是一種受歡迎的話語。他揭示了被殖民者在殖民主義制度中被異化的事實與根源,而正是對這根源的探究與質疑,刺痛了歐洲的神經(jīng),以及帝國思維的邏輯基礎。薩特在為《全世界受苦的人》所作的序中表達了一種驚訝:黑人開始顛倒秩序,將歐洲,即白人與統(tǒng)治者,作為客體加以審視。他的雷人發(fā)聲,在諸多議題上對既定的殖民主義話語及權威造成了挑戰(zhàn)。阿希克洛夫特等后殖民理論家指出,法農(nóng)始終從政治反對派的立場出發(fā),將殖民二分法(殖民者-殖民者)描述為“摩尼教式譫妄”的產(chǎn)物。這種情況最終導致徹底分裂的兩極對立,諸如善與惡、真與假、白與黑。在這種分裂對立中,初始符號(primary sign)在殖民關系的論述中享有不證自明的特權。法農(nóng)所感知到的是,這種話語如何被用作神秘化的把戲,以及它所產(chǎn)生的收編、從而解除反對派的力量。但他也承認,這種話語具有作為一種去神秘化的力量、作為一個新的反對立場的出發(fā)點的潛力,其目的是通過構建新的解放敘事,將被殖民者從其失去效能的殘廢立場中解放出來。對于后殖民理論家而言,法農(nóng)思想的最大意義在于,他既揭示了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結構的宰制性事實,又證明了被殖民者在權力結構中所具有的主體性與顛覆性效應。
被稱為后殖民主義“三劍客”之一的霍米·巴巴(Homi Bhabha),將法農(nóng)形容為“尼采、弗洛伊德和薩特反傳統(tǒng)精神的繼承者”、“僭越和過渡真理的傳播者”。于巴巴而言,法農(nóng)最具理論誘惑力的地方在于他對邊緣的探究,對邊緣化人物的在場的恢復,因為他能“最有效地從歷史變化的不穩(wěn)定的間隙中說話:即從種族與愛欲之間的矛盾情感領域,從文化與階級之間尚未解決的矛盾中,從心理再現(xiàn)和社會現(xiàn)實的斗爭深處”;因為他的激進思想對傳統(tǒng)的確定結構投下了一道不確定的陰影,在殖民主體的傳統(tǒng)的令人熟悉的并置——黑與白,自我與他者——中,他的聲音打破了白人優(yōu)越論和黑人形象刻板化論調(diào)的傳統(tǒng)根基,從此,主體與客體發(fā)生了移置。在20世紀50、60年代,法農(nóng)對被殖民者主體性的肯定無疑具有先鋒意義,這也確定了他的后殖民主義先聲人物地位。
總體而言,隨著法農(nóng)在后殖民理論中日益突出的位置,其在精神病理學與心理學上的見解,成為后殖民理論建構的重要參照,其對殖民主義雙重主體的剖析以及對殖民者的客體化努力,則成為后殖民理論家用以解構殖民霸權的重要理論資源。直至今日,對于曾經(jīng)經(jīng)歷過殖民主義的民族與國家,當西方的話語霸權仍在產(chǎn)生影響,法農(nóng)的文字與思想,無疑仍舊是幫助探路的明燈。
(胡燕,北京外國語大學文學博士,南昌師范學院文學院講師,《黑皮膚,白面具》中譯者。)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