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視頻|魯迅為什么這么評價吳敬梓的《儒林外史》
南開大學(xué)的寧宗一教授曾在《寂寞的吳敬梓——魯迅“偉大也要有人懂”心解》中說,除了《儒林外史》,“再沒有其他作品能更使魯迅的心和吳敬梓的心相通的了”。為什么這么說?本期的視頻,我們邀請文津出版社總編輯蒙木來談?wù)勽斞负蛥蔷磋鳌?/u>
寧宗一先生的《中國古典小說名作十五講》有三篇論述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其中一篇重點論述《儒林外史》在中國小說史上的地位。(他認(rèn)為)《儒林外史》代表了新的中國古代小說的高峰,就是一種身在其中的敘事,從《儒林外史》里可以看出作者自己的影子,這是中國小說的一個巨大的飛躍,使得我們閱讀小說帶來一個新的巨大的代入感。《儒林外史》講了更多的是平凡的事、我們身邊的事,看起來會更親切一些。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里對《儒林外史》的評價是“戚而能諧,婉而多諷”。戚,其實就是悲戚、凄楚,非常不舒服的一種狀態(tài),它還能夠諧,是一種幽默的態(tài)度;婉,就是我們過去常說的溫柔敦厚,在這當(dāng)中還有諷刺,能夠做到這一點是非常不容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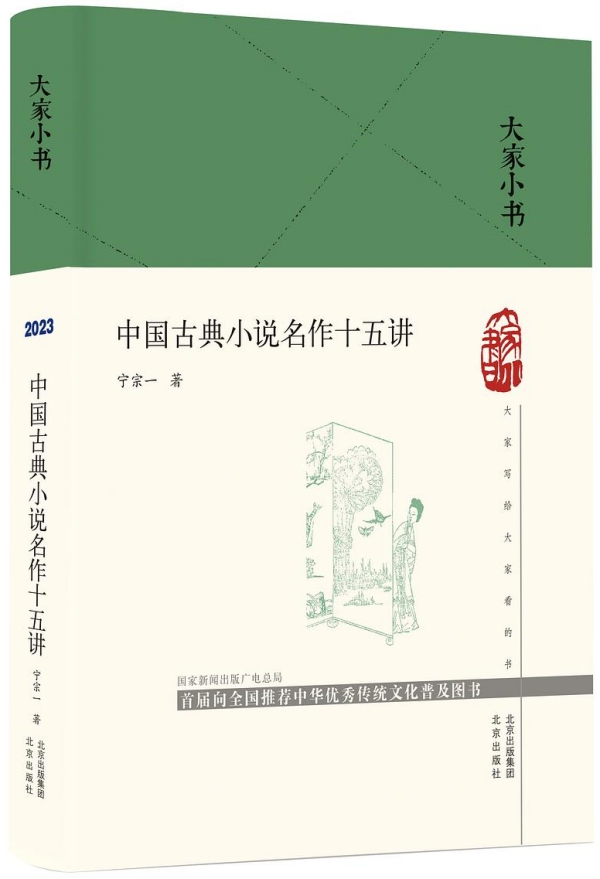
《中國古典小說名作十五講》,寧宗一/著,北京出版社,2023年5月版
吳敬梓的偉大和魯迅的偉大,有何不同?
魯迅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什么是諷刺》,他認(rèn)為諷刺在中國傳統(tǒng)歷史上算不得一種美德。魯迅說諷刺藝術(shù),第一,它要真實,這種事情要么是已經(jīng)發(fā)生,要么是必將要發(fā)生,并且是越普遍存在于我們現(xiàn)實生活當(dāng)中越好;第二,就是要帶著感情,要帶著溫情,而不是一味的批判。不帶感情的諷刺,魯迅用了另一個詞叫做“冷嘲”。我們從《儒林外史》的故事當(dāng)中看到了作者自己的影子,看到作者所追求的那種向上的美的東西和一種靈魂拷問。這種偉大,不是說我們經(jīng)過傳統(tǒng)的、溫柔敦厚的教育的人所能夠隨隨便便理解的。
魯迅的偉大和吳敬梓的偉大,是不是同樣的偉大?如果從對于中國小說的再造,從身在其中的反諷這種敘事方式來說,是一樣的,但如果拓展到更寬的視野,吳敬梓和魯迅的偉大還是有很多區(qū)別的。吳敬梓,是一個傳統(tǒng)的中國知識分子,他接受的是四書五經(jīng)的傳統(tǒng)教育,他有他的叛逆性,有他的理想追求和熱情,但事實上,他不可能找到一個理想的出路,不可能指明一個新的方向出來,所以他的諷刺當(dāng)中調(diào)子比較低沉。魯迅具有更強(qiáng)的戰(zhàn)斗精神,尤其是他的雜文。他的諷刺藝術(shù)不單單是諷刺,也在做大膽的冷嘲,他把諷刺藝術(shù)做得更寬,政治性更強(qiáng)。但是在解析國民的靈魂這方面,兩人是共通的、相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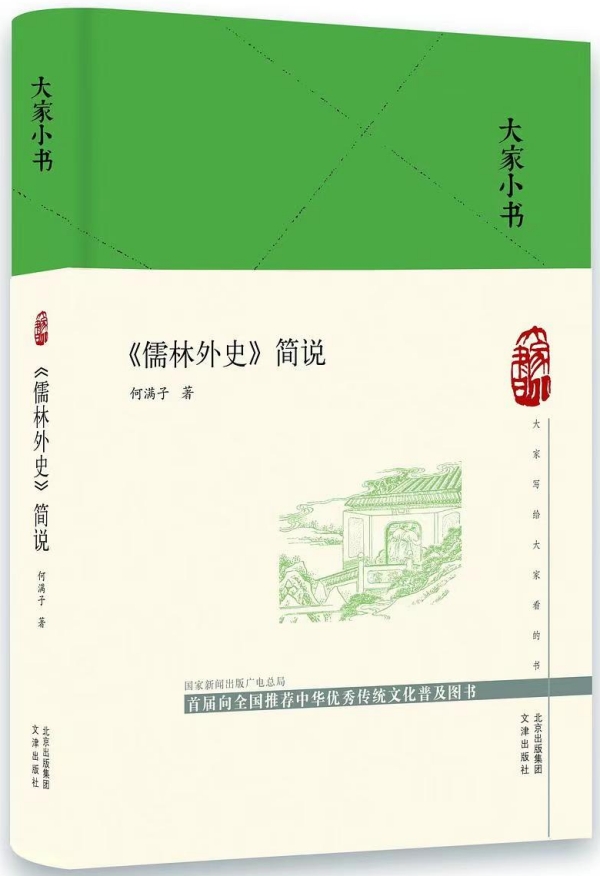
《<儒林外史>簡說》,何滿子/著,文津出版社,2020年9月版
優(yōu)秀文學(xué)作品的寫作都是“解剖我自己、托出真靈魂”嗎?
魯迅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的解剖自己。”每一部偉大作品都是剖析我自己,托出真靈魂,我們理解一部作品,一個正面人物、反面人物的時候,都應(yīng)該抓住這個真靈魂。真靈魂,并不能說是跟作者相近的形象,或者作者所主導(dǎo)的那種正面形象,其實也包括反面形象。弗洛伊德的本我和超我理論,后來廣泛應(yīng)用于文學(xué),本我的東西,其實我們認(rèn)識它很難,說白了就是認(rèn)識一個真實的自己甚于一種生物學(xué)的自己,不是那么容易。超我就是做了一個人設(shè),是我愿意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我們理解的真靈魂,既包括超我,又包括本我。
一部作品,它的偉大就是因為它里面最重要的人已經(jīng)被我們每一個人口耳相傳地符號化了。比如說,你是林黛玉,你是賈寶玉,或者說,你是阿Q,幾乎每一個人在《阿Q正傳》當(dāng)中,都能看到自己的樣子,甚至有人覺得是諷刺他自己。諷刺自身不重要,關(guān)鍵是諷刺能給我們帶來思考,并能夠激發(fā)我們變得更好,能夠更向上。最后我也想沿用魯迅評價吳敬梓的話,“偉大也要有人懂”。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