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訪談︱克洛德·德萊:法軍在一戰(zhàn)中的表現(xiàn)究竟如何
【編者按】
讓-克洛德·德萊(Jean-Claude Delhez),法國(guó)歷史學(xué)家、記者,1967年生于比利時(shí)洛林(Lorraine belge)法語(yǔ)區(qū),1991年畢業(yè)于布魯塞爾自由大學(xué),其后曾從事記者工作,也一直致力于研究洛林地方史與軍事史,代表作為全景記錄邊境會(huì)戰(zhàn)的《法軍的哀悼日》(Le jour de deuil de l'armée fran?aise)一書(shū)。其著作在學(xué)術(shù)界廣受好評(píng),英國(guó)歷史學(xué)家彼得·哈特(Peter Hart)曾在其著作《大戰(zhàn):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作戰(zhàn)史》(The Great War: A Combat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中表示:“我發(fā)覺(jué)讓-克洛德·德萊的作品絕對(duì)是無(wú)價(jià)之寶。英國(guó)的所有一戰(zhàn)史研究者都應(yīng)當(dāng)閱讀他的《邊境會(huì)戰(zhàn):由親歷者講述》(La Bataille des Frontières: racontée par les combattants)和《法軍的哀悼日》。”今年是一戰(zhàn)結(jié)束百年,回首一戰(zhàn),法軍的表現(xiàn)如何?坦克在一戰(zhàn)中究竟發(fā)揮了怎樣的作用?作為一名法語(yǔ)學(xué)者,他對(duì)英語(yǔ)世界的一戰(zhàn)研究,又有何評(píng)價(jià)?帶著這些問(wèn)題,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專訪了讓-克洛德·德萊。

從記者到學(xué)者
澎湃新聞:作為一位來(lái)自比利時(shí)的法國(guó)歷史學(xué)者,是什么激發(fā)了您對(duì)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興趣?作為一位記者,您的職業(yè)是否對(duì)自己所進(jìn)行的歷史研究有所啟發(fā)?
德萊:我居住在凡爾登(Verdun)、色當(dāng)(Sedan)、巴斯托涅(Bastonge)之間的邊境地區(qū),那里僅僅在一個(gè)世紀(jì)里就曾發(fā)生過(guò)諸多戰(zhàn)爭(zhēng)和戰(zhàn)斗。從高盧人到馬奇諾防線,土地上到處都是戰(zhàn)事留下的紀(jì)念物:軍人公墓、各類堡壘。在這樣一種環(huán)境下,軍事史就成了尋常的事情。作為歷史學(xué)家,我對(duì)發(fā)生于1914年8月的邊境會(huì)戰(zhàn)尤為關(guān)注,這場(chǎng)在法德兩軍之間展開(kāi)的會(huì)戰(zhàn)雖然不算赫赫有名,卻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的第一場(chǎng)大戰(zhàn),它讓取得勝利的德軍得以長(zhǎng)時(shí)間地攻入法國(guó)并占據(jù)具備戰(zhàn)略意義的洛林鐵礦,考慮到長(zhǎng)達(dá)四年的塹壕戰(zhàn)所需的龐大鋼鐵總量,德國(guó)的軍事工業(yè)正是依靠邊境會(huì)戰(zhàn)才得以維持下去。此外,1914年8月22日也是法國(guó)歷史上最血腥的一天。過(guò)去的二十年里,我寫了八本書(shū)來(lái)介紹這場(chǎng)會(huì)戰(zhàn)。
不論是作為歷史學(xué)家還是記者,我在所有作品中都非常關(guān)注搜尋信息和核對(duì)數(shù)據(jù)。對(duì)于這類職業(yè)而言,它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是一種尋常舉動(dòng),但它并沒(méi)有我們所認(rèn)為的那么普通。就我而言,對(duì)來(lái)自不同國(guó)家或是不同參與方的信息進(jìn)行比較乃至讓它們針?shù)h相對(duì)是相當(dāng)重要的,這是為了盡可能地趨近事實(shí)、趨近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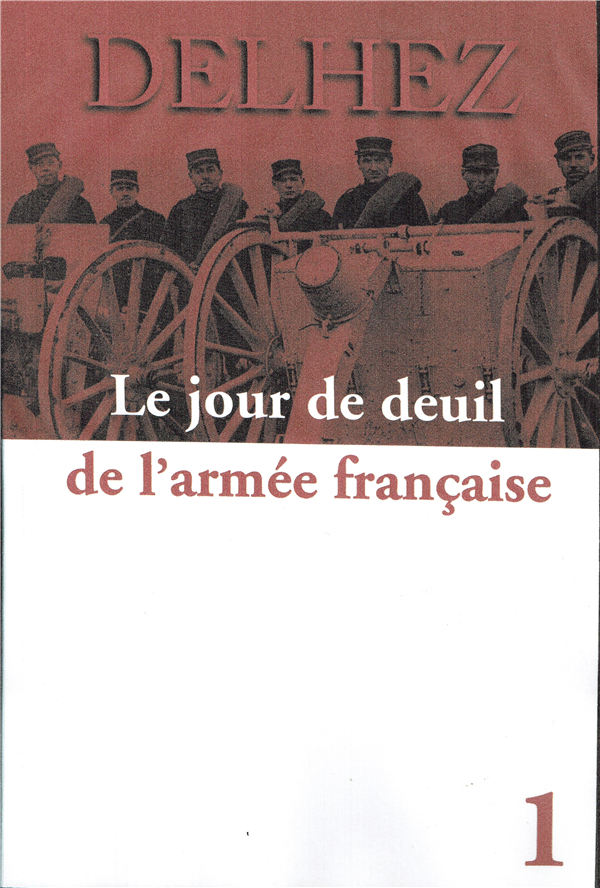
澎湃新聞:出于種種原因,中國(guó)讀者往往通過(guò)英文圖書(shū)了解有關(guān)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歷史,芭芭拉·塔奇曼的《八月炮火》就是其中影響頗大的一本書(shū)。您對(duì)描寫一戰(zhàn)期間法國(guó)、比利時(shí)狀況的英文著作評(píng)價(jià)如何?
德萊:就我的研究而言,我主要運(yùn)用法文、德文的著作和檔案材料。有關(guān)軍事史的英文出版物的確為數(shù)眾多,它們涉及到世界上各個(gè)地區(qū)的各種軍事問(wèn)題,這也包括一戰(zhàn)期間的法國(guó)和比利時(shí)。與一戰(zhàn)題材的法國(guó)、比利時(shí)圖書(shū)的情況相類似,英文圖書(shū)的質(zhì)量也是良莠不齊。例如,美國(guó)人芭芭拉·塔奇曼的《八月炮火》盡管是本暢銷書(shū),在60年代取得過(guò)巨大成功,贏得普利策獎(jiǎng)并受到肯尼迪總統(tǒng)的欣賞,但從學(xué)術(shù)角度來(lái)看,卻很難說(shuō)是好書(shū),其中某些章節(jié)可以說(shuō)近乎小說(shuō),不僅對(duì)法國(guó)的殖民軍(Corps d’armée colonial)人員組成描述有誤,甚至連呂夫(Ruffy)等歷史人物的個(gè)性也自由創(chuàng)作。這可能正是它能夠在出版后頗為流行,甚至直至目前仍然暢銷的緣故。另一方面,我會(huì)推薦美國(guó)人羅伯特·道蒂(Robert Doughty)有關(guān)法國(guó)戰(zhàn)略的著作《皮洛士式的勝利:大戰(zhàn)中的法國(guó)戰(zhàn)略與作戰(zhàn)》(Pyrrhic Victory: French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in the Great War)和英國(guó)人西蒙·豪斯(Simon House)有關(guān)邊境會(huì)戰(zhàn)的著作《失去的機(jī)遇:1914年8月22日阿登會(huì)戰(zhàn)》(Lost Opportunity: The Battle of The Ardennes 22 August 1914)。這兩本著作并沒(méi)有落入傳統(tǒng)英美觀點(diǎn)的窠臼,前者擁有扎實(shí)的法軍檔案文獻(xiàn)基礎(chǔ),后者則充分利用了法文與德文材料。
被德雷福斯事件撕裂的法國(guó)軍隊(duì)與社會(huì)
澎湃新聞:一戰(zhàn)時(shí)期,上海法租界曾用霞飛、福煦、貝當(dāng)這三位法軍統(tǒng)帥來(lái)命名主要道路,或許出于這一緣故,他們也因此成為一戰(zhàn)期間中國(guó)境內(nèi)知名度最高的三位法軍將帥,您對(duì)這三人的戰(zhàn)爭(zhēng)表現(xiàn)有何評(píng)價(jià)?
德萊:霞飛從1911年開(kāi)始執(zhí)掌法軍并一直持續(xù)到1916年為止。這是一段漫長(zhǎng)的任期,當(dāng)你了解到法軍總參謀長(zhǎng)(戰(zhàn)時(shí)自動(dòng)轉(zhuǎn)任為法軍總司令)通常不會(huì)在這個(gè)位子上待很久之后,那就顯得尤為漫長(zhǎng)了。霞飛的繼任者是尼韋勒(Nivelle)將軍,但他在1917年“貴婦小徑”之戰(zhàn)受挫,接著遭到了解職。然后,由于“貴婦小徑”戰(zhàn)后的兵變影響,政府邀請(qǐng)貝當(dāng)出任法軍總司令,要求他重建能夠投入長(zhǎng)期作戰(zhàn)的法國(guó)軍隊(duì)并謹(jǐn)慎地處理士氣問(wèn)題。他在法軍總司令的位子上一直待到戰(zhàn)爭(zhēng)結(jié)束為止。在戰(zhàn)爭(zhēng)的最后階段——其中包括1918年11月的最終勝利——福煦成了協(xié)約國(guó)西線聯(lián)軍的最高統(tǒng)帥。福煦不僅是一位指揮官、一位將領(lǐng),他還是一位戰(zhàn)略家、一位軍事理論家。福煦在當(dāng)時(shí)聲名顯赫,但在此后卻遭到了批評(píng),而且他的思想看起來(lái)并不那么具備原創(chuàng)性。
不過(guò),總司令的舉動(dòng)得與時(shí)代背景聯(lián)系起來(lái)。他是由政府選任的,并非孤身一人,而且必須和陸軍部長(zhǎng)合作——雖然由于克勞塞維茨著作的影響,在法國(guó)和德國(guó),總司令或總參謀長(zhǎng)是惟一負(fù)責(zé)指揮全軍的人物。而且,我們一定不能忘記軍隊(duì)是由成千上萬(wàn)的軍官(他們也需要肩負(fù)自己的職責(zé))和數(shù)以百萬(wàn)計(jì)的士兵組成的。就軍隊(duì)的組織、訓(xùn)練、戰(zhàn)術(shù)、裝備……而言,這些歸根到底都源于數(shù)年前做出的決定。我可以給出一個(gè)案例。在霞飛擔(dān)任法軍總司令期間,法國(guó)于1914年8月輸?shù)袅诉吘硶?huì)戰(zhàn)。許多歷史學(xué)家認(rèn)為霞飛需要為這場(chǎng)災(zāi)難負(fù)責(zé)。可當(dāng)你深入研究這場(chǎng)會(huì)戰(zhàn)的細(xì)節(jié)后,就會(huì)發(fā)現(xiàn)這種看法并不正確。當(dāng)然,這場(chǎng)失敗首先要?dú)w因于德國(guó)軍隊(duì)的作戰(zhàn)技能,在此之后,主要責(zé)任就得落到法軍的中間指揮層身上,我用中間指揮層這個(gè)詞組指代某些指揮集團(tuán)軍、軍、師和旅的將領(lǐng)。此后,法軍不得不進(jìn)行人事迭代,解除了其中許多人的職務(wù)。
澎湃新聞:提到法軍戰(zhàn)前的備戰(zhàn)狀況,許多人認(rèn)為德雷福斯事件對(duì)法國(guó)軍隊(duì)和社會(huì)造成了重大影響。您對(duì)這一事件的看法如何?
德萊:德雷福斯事件始于1894年法軍總參謀部猶太裔上尉德雷福斯被控叛國(guó),進(jìn)而激起了全國(guó)范圍的反猶浪潮,盡管事后調(diào)查證明德雷福斯無(wú)罪,總參謀部卻以維護(hù)軍隊(duì)威信為由拒絕平反,該案內(nèi)幕被公開(kāi)后演化為長(zhǎng)達(dá)十二年的政治危機(jī),對(duì)法國(guó)影響極大,它表明反猶的極端民族主義、天主教教權(quán)主義思潮在當(dāng)時(shí)的法國(guó)具備極大的影響力,也使得溫和共和派威信掃地,激進(jìn)共和派掌握政權(quán)。當(dāng)然,我們也一定不能忘記激進(jìn)共和派掌權(quán)后的另一起事件——“卡片事件”(Affaire des Fiches),它的發(fā)生時(shí)間略晚于德雷福斯事件。當(dāng)時(shí),激進(jìn)派的孔布(Combes)政府利用共濟(jì)會(huì)網(wǎng)絡(luò)秘密建立有關(guān)軍官政治觀點(diǎn)與宗教信仰的檔案,打壓信仰天主教的軍官、偏袒世俗軍官,此事泄露后導(dǎo)致政府垮臺(tái)。之所以會(huì)發(fā)生這些事件,是因?yàn)榉▏?guó)當(dāng)時(shí)的特殊政治背景。盡管共和國(guó)已經(jīng)持續(xù)了三十多年,但軍隊(duì)里依然滿是對(duì)過(guò)去懷有眷戀的軍官,他們寧愿讓法國(guó)成為帝國(guó)或王國(guó),也不愿共和國(guó)繼續(xù)存在下去,這種人里有很多是貴族。也正是在這個(gè)時(shí)期,許多國(guó)家都出現(xiàn)了一種將教權(quán)主義、民族主義、反猶主義等思想融合在一起的反動(dòng)政治思潮。德雷福斯事件表明,這樣的思潮已經(jīng)深深浸潤(rùn)在世紀(jì)之交的法國(guó)軍官群體當(dāng)中。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此時(shí)也正是法國(guó)政府決心政教分離(1905年通過(guò)《政教分離法》(Loi de séparation des églises et de l'état))并確立世俗國(guó)家的時(shí)期,此后,掌權(quán)的共和派對(duì)法軍指揮層進(jìn)行了重組和整肅。這些事件都導(dǎo)致法國(guó)社會(huì)分裂為進(jìn)步派與保守派兩部分,其裂痕直至今日仍未完全彌合。就事件后果而言,1914年的法國(guó)社會(huì)所受影響比軍隊(duì)更為深重。當(dāng)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時(shí),統(tǒng)帥軍隊(duì)的是霞飛,他是一位共和派的將領(lǐng),也曾是共濟(jì)會(huì)員。不過(guò),天主教徒、共濟(jì)會(huì)員、貴族、平民都在軍官團(tuán)體中共存,意識(shí)形態(tài)沖突相對(duì)社會(huì)而言也較為緩和。
一戰(zhàn)史中的神話
澎湃新聞:您在研究中曾發(fā)現(xiàn)關(guān)于一戰(zhàn)的大眾認(rèn)知往往存在謬誤。例如,在《1914年的十二則神話》(Douze mythes de l'année 1914)和《攻擊列日要塞》(L'assaut contre les forts de Liège)中,您指出列日要塞并未如傳統(tǒng)說(shuō)法那樣有效延宕德軍攻勢(shì)、進(jìn)攻至上(l'offensive à outrance)原則并非一戰(zhàn)初期慘重傷亡的原因、巴黎的出租車并未對(duì)馬恩河之戰(zhàn)起到重大影響等,請(qǐng)問(wèn),為何這些與軍事相關(guān)的神話會(huì)在法國(guó)、比利時(shí)乃至各個(gè)參戰(zhàn)國(guó)流傳甚廣?
德萊:我們不僅應(yīng)當(dāng)考慮到一戰(zhàn)歷史本身,也需要理解歷史是如何書(shū)寫的。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也就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人們當(dāng)然對(duì)這場(chǎng)世界大戰(zhàn)興趣極大。許多國(guó)家都出版了為數(shù)眾多的書(shū)籍和文章。在那時(shí),我們實(shí)際上僅僅處于書(shū)寫一戰(zhàn)歷史的初期,可不幸的是,它并沒(méi)有延續(xù)下去。因?yàn)闅W洲在經(jīng)歷了二十年的和平后就迎來(lái)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這場(chǎng)戰(zhàn)爭(zhēng)極為重要,以至于讓有關(guān)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歷史都變得老套了。人們對(duì)一戰(zhàn)興趣不再。直到二十世紀(jì)末,有關(guān)一戰(zhàn)的研究和出版才有所復(fù)興。可是,這時(shí)的研究是從某些特殊角度出發(fā)的,尤其是在法國(guó),對(duì)一戰(zhàn)的研究與社會(huì)學(xué)的發(fā)展存在關(guān)聯(lián)。從那時(shí)起,主要的關(guān)注對(duì)象是士兵的生活條件以及個(gè)人感受。至于有關(guān)一戰(zhàn)的其他視角,此時(shí)仍然保持不變,有時(shí)甚至?xí)霈F(xiàn)一種與西線塹壕戰(zhàn)相關(guān)的諷刺視角。時(shí)至今日,與對(duì)二戰(zhàn)歷史所做的研究和分析相比,一戰(zhàn)所吸引的研究仍不算多。一般而言,純軍事研究已經(jīng)不再是時(shí)興的課題了。因此,就這些軍事問(wèn)題而言,通行的觀點(diǎn)依然是間戰(zhàn)期的看法。這就是某些持續(xù)百年的神話至今仍然存在的緣故。
澎湃新聞:我發(fā)現(xiàn)在您的新書(shū)《坦克:世紀(jì)欺詐》(Chars d'assaut: Un siècle d'imposture)一書(shū)中,您對(duì)一個(gè)世紀(jì)來(lái)的坦克戰(zhàn)及其相關(guān)神話進(jìn)行了精彩分析。請(qǐng)問(wèn)您能否簡(jiǎn)單評(píng)述一戰(zhàn)末期的坦克戰(zhàn)?
德萊:在大戰(zhàn)的最后幾個(gè)月里,貝當(dāng)將軍告訴法軍士兵:“不要放棄,坦克和美國(guó)兵正在趕過(guò)來(lái)!”實(shí)際上,坦克和美軍都不是這場(chǎng)大戰(zhàn)(以及另一場(chǎng)大戰(zhàn))的決定性因素。坦克是由英軍在1916年發(fā)明的,這是因?yàn)楫?dāng)時(shí)所有人都在考慮脫離塹壕戰(zhàn)的方法,作為一種履帶式的裝甲兵器,坦克看上去是個(gè)好主意。可是,從技術(shù)層面而言,坦克并不可靠,甚至直到1940年都不可靠。坦克起初通常會(huì)遭遇的問(wèn)題是機(jī)械故障。而且,雖然坦克起初帶來(lái)了令人驚訝的效果,人們很快就在1916年秋季找到了反坦克手段,比如說(shuō)將原有的火炮改為反坦克炮使用。德軍在1918年第一次非常接近突破西線的塹壕防線,可他們的軍隊(duì)里幾乎沒(méi)有坦克。我在書(shū)中指出這種兵器已經(jīng)被高估了整整一個(gè)世紀(jì)——直至現(xiàn)在仍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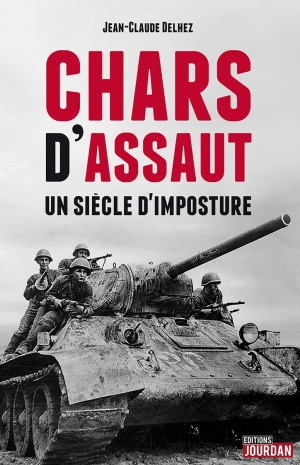
澎湃新聞:法國(guó)在付出了慘重代價(jià)后最終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主要戰(zhàn)勝國(guó)之一。您認(rèn)為法軍在戰(zhàn)爭(zhēng)過(guò)程中的表現(xiàn)究竟如何?
德萊:法軍曾在150年的時(shí)間里先后三次與德軍展開(kāi)大戰(zhàn),當(dāng)時(shí),德軍是世界上最優(yōu)秀的軍隊(duì)之一。法國(guó)在1870-1871年和1940年戰(zhàn)敗,交戰(zhàn)有時(shí)只持續(xù)了幾個(gè)星期。在1914年,法軍開(kāi)局非常不利,可是,由于馬恩河會(huì)戰(zhàn)的勝利,德軍的入侵腳步被擋住了,協(xié)約國(guó)軍隊(duì)得以在接下來(lái)的四年里維持塹壕戰(zhàn)線并最終贏得戰(zhàn)爭(zhēng)。在每一場(chǎng)戰(zhàn)爭(zhēng)當(dāng)中的每一個(gè)時(shí)刻,德軍都能夠憑借其質(zhì)量?jī)?yōu)勢(shì)——特別是其指揮優(yōu)勢(shì)——優(yōu)于法軍,甚至可能優(yōu)于世界上的所有軍隊(duì),1914年的狀況也是如此。所以,法軍最終是如何取得勝利的呢?于我而言,法軍與德軍之間的差別往往就像是國(guó)營(yíng)企業(yè)和私營(yíng)企業(yè)之間的差別。法軍傾向于服從,而德軍傾向于自發(fā)。法國(guó)軍隊(duì)就像是一個(gè)龐大的公共管理部門,非常有組織、非常等級(jí)化,但反應(yīng)非常慢。如果它能夠像1914年那樣成功度過(guò)戰(zhàn)爭(zhēng)的第一波沖擊,它就有時(shí)間去適應(yīng)、去進(jìn)步。此外,一戰(zhàn)并不僅僅是法國(guó)的勝利,其他國(guó)家也參與其中,除去軍事層面外,還需要考慮其他層面的問(wèn)題。1914-1918年的戰(zhàn)爭(zhēng)是一場(chǎng)工業(yè)戰(zhàn)爭(zhēng),經(jīng)濟(j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在這場(chǎng)戰(zhàn)爭(zhēng)中,我們一定不能忘記英國(guó)的海上封鎖給中歐帝國(guó)——德意志和奧匈——最終崩潰帶來(lái)的影響。
中國(guó)與一戰(zhàn)
澎湃新聞: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中國(guó)的北洋政府也曾向德國(guó)宣戰(zhàn),幾乎與此同時(shí),孫中山、唐繼堯、陸榮廷等人在廣州建立軍政府,發(fā)起護(hù)法戰(zhàn)爭(zhēng)。您曾著有《法國(guó)窺探世界(1914-1919)》(La France espionne le Monde (1914-1919))一書(shū),對(duì)法軍在一戰(zhàn)期間的諜報(bào)工作進(jìn)行了出色的研究,書(shū)中也曾引證法國(guó)檔案,表明德國(guó)情報(bào)機(jī)關(guān)與孫中山之間曾存在聯(lián)系。請(qǐng)問(wèn)您當(dāng)時(shí)是如何發(fā)現(xiàn)這份重要的檔案文件?在您看來(lái),這份文件可信度如何?
德萊:有位名叫格爾曼(Gehrmann)的德國(guó)間諜曾于1917年到中國(guó)與孫中山會(huì)面,并聲稱他與孫中山達(dá)成了協(xié)定,打算在中國(guó)發(fā)動(dòng)戰(zhàn)爭(zhēng),切斷云南等省份與北方政府的聯(lián)系。此人的行動(dòng)應(yīng)當(dāng)放在德國(guó)全球政策(Weltpolitik)的背景下理解,該政策目的就在于通過(guò)革命、破壞、生物戰(zhàn)……手段削弱柏林的敵人,其范圍波及墨西哥、英屬印度、中東等地。
這些信息源自德國(guó)情報(bào)人員間的電報(bào)。但法國(guó)軍方破解了德方的密碼,因而能夠閱讀敵人的電報(bào)。這就是一些與格爾曼諜報(bào)活動(dòng)相關(guān)的文件會(huì)出現(xiàn)在法國(guó)檔案里的緣故,這樣的文件或許也會(huì)出現(xiàn)在英國(guó)檔案里,因?yàn)橛?guó)的破譯人員也能夠掌握這種電報(bào)。雖然如此,這份文件仍然不過(guò)是格爾曼的回憶而已。他是否真的曾與孫中山達(dá)成協(xié)定,他是不是一個(gè)夸張自己作為的吹牛者?不幸的是,我在法國(guó)檔案中并沒(méi)有找到與這一事件相關(guān)的更多信息,德國(guó)檔案則有相當(dāng)一部分已在戰(zhàn)時(shí)和戰(zhàn)后被毀。
澎湃新聞:除了一戰(zhàn)、二戰(zhàn)相關(guān)著作外,我注意到您還出版了幾本涉及比利時(shí)洛林地區(qū)的作品,請(qǐng)問(wèn)您對(duì)地方史的興趣緣何而來(lái),日后還會(huì)涉及哪些研究領(lǐng)域?
德萊:我喜歡將歷史與地理聯(lián)系起來(lái)。除了軍事史之外,我還致力于研究鋼鐵的冶金學(xué)和鐵礦。我撰寫了與洛林工業(yè)區(qū)相關(guān)的圖書(shū)和文章。我現(xiàn)在仍然忙于研究這一領(lǐng)域,特別是熱衷于一兩千年前還沒(méi)有鼓風(fēng)爐時(shí)的冶鐵方法。雖然冶鐵鼓風(fēng)爐早已出現(xiàn)在了中國(guó),可當(dāng)時(shí)的歐洲仍然沒(méi)有這種設(shè)備。
當(dāng)然,我仍然在探究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歷史。我的下一本書(shū)將于今年秋季出版,它與一戰(zhàn)期間諜報(bào)活動(dòng)中的女性間諜有關(guān)。幾乎每個(gè)人都知道荷蘭舞女兼德國(guó)間諜瑪塔·哈里(Mata Hari)被法國(guó)當(dāng)局在1917年處以死刑,但在情報(bào)工作的秘密領(lǐng)域,還有許多效率遠(yuǎn)高于她的女性,這也是她們?cè)跉v史上首次扮演此類角色。其后的作品同樣會(huì)涉及情報(bào),甚至可能與生物戰(zhàn)相關(guān)。在一戰(zhàn)期間,我至少可以舉出德軍和法軍運(yùn)用桿菌等細(xì)菌進(jìn)行生物戰(zhàn)的案例,這些病菌感染了歐美諸國(guó)的動(dòng)物,我甚至懷疑這種舉動(dòng)可能與所謂的“西班牙流感”有關(guān)。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yíng)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