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屠格涅夫曾是在歐洲推廣俄國藝術的關鍵角色
【編者按】
鐵路時代帶來了大眾交通與旅行的革命,印刷技術提升了作品量產的市場力量。19世紀的歐洲各國民眾開始將歐洲視為一個整體并共享同一種文化——他們閱讀同樣的書籍、聆聽同樣的音樂、欣賞同樣的繪畫、觀賞同樣的戲劇。最終,他們以“歐洲人”自居,視歐洲為一個不受國界限制的文化交流、翻譯、交換的場域。在《創造歐洲人:現代性的誕生與歐洲文化的形塑》一書中,英國倫敦大學歷史學教授奧蘭多·費吉斯通過俄國作家屠格涅夫、法國女高音保琳娜·維亞爾多和藝術評論家路易·維亞爾多三人的故事,展現了19世紀燦爛輝煌的國際主義文化,以及當時的作家、藝術家、音樂家,如何成為跨國的文化中介者,通過蓬勃發展的文化圈將歐洲各國聯結成一個文化共同體,使歐洲各國人民接受共同的身份標簽——“歐洲人”,進而樹立歐洲文化以及文學藝術在世界文明中的經典地位。本文摘編自該書,澎湃新聞經理想國授權發布。
法國人在19世紀70年代接受了俄國文化。被普魯士擊敗使得法國與俄國走得更近,視其為對抗德國的外交盟友。這種友好關系時斷時續,一直持續到1894年的法俄同盟。法國對俄國經濟進行了大量投資,特別是鐵路,隨著俄國向西方開放,西方對俄國的興趣與日俱增。出現了俄國游記的寫作熱潮,包括戈蒂埃的暢銷書《俄國之旅》。英國作家也爆發出同樣的熱情。劉易斯·卡羅爾(Lewis Carroll)去過莫斯科,在他的旅行日記中將那里描述為仙境(“你看到了扭曲的城市形象,仿佛在穿衣鏡里”),這成為他的《愛麗絲漫游鏡中世界》(1871年)的靈感來源。19世紀70年代,唐納德·麥肯齊·華萊士(Donald Mackenzie Wallace)和阿納托爾·勒魯瓦—博利厄(Anatole Leroy-Beaulieu)這兩位在俄國游歷甚廣的旅行家創作了可能是外國人寫的該國最早的客觀歷史,兩者的銷量都很高。總而言之,俄國不再被視作“亞洲的蠻邦”——作為不同于“歐洲文明”的東方“他者”——就像30年前在居斯蒂納侯爵的時代那樣。它開始被視作歐洲自身的一部分。
歐洲對俄國的興趣隨著那些年里的國際展會而提高——倫敦(1871年至1874年間每年一次)、維也納(1873年)和巴黎(1878年)——俄國的藝術和工藝品在這些展會上吸引了最多的觀眾。在1878年的巴黎世博會上,尼古拉·魯賓斯坦指揮的一系列俄國音樂會也吸引了很多人參加,曲目包括柴可夫斯基、格林卡、安東·賓斯坦和達爾戈梅日斯基的作品,盡管沒有“五人團”的音樂讓許多人感到困惑和失望。巴黎媒體異口同聲地做出了批判性的評價:他們認為這些音樂有趣但缺乏原創性,風格過于德國或意大利化。他們原本希望聽到一些更具異國情調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俄國”音樂。柴可夫斯基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也引起了類似的反響,在大眾音樂會上遭到了噓聲。
西方觀眾對歐洲大陸的“邊緣”文化(俄國、西班牙、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捷克地區和匈牙利等)的接受度越來越高,關鍵原因是他們對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期待。他們希望俄國音樂聽起來像“俄國的”,西班牙音樂聽起來像“西班牙的”,匈牙利音樂聽起來像“匈牙利的”(即使是勃拉姆斯作曲),而不是像德國、意大利甚至法國音樂那樣(后者只需聽起來不像德國音樂就行了)。他們希望這些國家的音樂聽起來具有不同的異國情調,充滿民間主題,帶有吉卜賽和波希米亞舞曲的特色。這種期待鼓勵這些地區推出“專供出口的民族風格”。反過來,民族主義者在他們的藝術和音樂中推廣以民俗作為真實性基礎的神話,不僅是為了他們自己的民族構建,也是為了證明他們的國家在歐洲其他民族中是獨一無二的。這正是斯塔索夫和他的追隨者的計劃。居伊的《俄國音樂》(1880年)一書旨在增進歐洲人對他們的民族主義音樂的認識,它對公眾對于俄國音樂應該是什么樣子的期待產生了持久的影響。
屠格涅夫對俄國文化在西方被視作異國情調感到震驚。他希望俄國藝術家成為歐洲文明的一部分,認為他們的民族性表達應該服從于這一目標——即內化于他們的藝術中,而不是流于表面。這就是為什么他在普希金、托爾斯泰和柴可夫斯基身上看到了偉大的藝術:他們的俄國性并沒有影響他們的歐洲性。
對于在歐洲宣傳俄國藝術家的問題上,屠格涅夫同樣反對斯塔索夫的觀點。巴黎有許多俄國畫家。較年輕的那些大多出身藝術學院,靠獎學金投入知名藝術家(如博納[Bonnat]、熱羅姆或勒費弗爾[Lefebvre])的工作室學習,俄國流亡畫家博戈留博夫被指派監督他們的工作。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受到了法國風俗畫和風景畫的影響,特別是巴比松派畫家,盡管他們也接觸了巴黎范圍更廣的歐洲繪畫潮流:博戈留博夫引導他們了解了西班牙畫家瑪麗亞·福圖尼(Marià Fortuny),以平衡法國人的影響。
屠格涅夫對年輕畫家阿列克謝·哈拉莫夫(Alexei Kharlamov)印象深刻,后者是在巴黎的俄國學生中最西方化的,主要創作風俗畫和肖像畫。他對此人的贊美到了夸張的程度,將其比作倫勃朗(哈拉莫夫曾在艾爾米塔什學習過倫勃朗的技藝)。他委托哈拉莫夫為保琳娜、路易和他自己畫像,從技術角度來看確實非常好。這三幅畫被一起掛在杜埃街的陳列室里,屠格涅夫特意邀請朋友們來賞鑒(就連維克多·雨果也收到邀請)。維亞爾多夫婦的肖像畫在1875年的沙龍上以極好的位置展出(路易是評審團的成員),屠格涅夫的畫像則在次年的沙龍上被掛在顯眼的位置。左拉在年度回顧中特別提到了哈拉莫夫,盡管他認為此人為屠格涅夫畫的肖像讓他的朋友顯出“一種冷酷而悲傷的表情”,“完全不是他平常的樣子”。
通過自己在巴黎的眾多人脈,屠格涅夫在藝術品市場上推銷哈拉莫夫的作品。古皮爾在他最奢華的畫廊——位于巨大的、新開業的巴黎歌劇院(也被稱為加尼耶宮[Palais Garnier])的對面——賣出了他的一些畫作,還把很多畫送到了他的倫敦分店。哈拉莫夫的朋友,對他深表羨慕的愛沙尼亞畫家恩斯特·利普哈特(Ernst Liphart)表示,哈拉莫夫的“漂亮畫作”被英國經銷商搶購一空。利普哈特認為,屠格涅夫對成功的定義讓哈拉莫夫墮落了。利普哈特聽到屠格涅夫說:“當某個畫商來到你的工作室,出高價買下你的一幅畫,相信他可以立即將其轉售給他心目中已經有了人選的某位收藏家,從而賺取巨額利潤時,那就表示成功了。”如果這是真的,這與屠格涅夫早前的觀點相去甚遠;也許這反映了他作為商業出版世界中的一位作家的改變。“可憐的哈拉莫夫,”利普哈特寫道,“他成了他的庇護者的這種理論的受害者。英國經銷商鼓勵他大量創作意大利風格的小尺寸繪畫,對這種作品的狂熱扼殺了那個為維亞爾多夫婦繪制肖像時顯示出大好前途的哈拉莫夫。”
屠格涅夫還在巴黎宣傳其他俄國藝術家。他在報紙上為他們撰文,讓他們接觸經銷商,并幫助他們為自己的作品找到買家。他安排將阿西普·庫因德茲(Arkhip Kuindhzi)的四幅畫作出售給了巴黎的奧地利交易商查爾斯·塞德爾邁耶爾(Charles Sedelmeyer)。1878年的巴黎世博會上展出了馬克·安托科爾斯基(Marc Antokolsky)兩件雕塑,這要得益于路易·維亞爾多的幫助,他在法國和比利時的報紙上稱贊了它們。這兩件作品獲得一枚金牌,為安托科爾斯基贏得了許多國外的委托。
他特別積極地為瓦西里·韋列夏金(Vasily Vereshchagin)宣傳,在1876年的一次莫斯科之行中,他第一次看到了后者的大型戰爭畫和中亞風景畫。兩年后,他造訪了位于巴黎附近的邁松拉菲特(Maisons Laffitte)的藝術家工作室,被韋列夏金的原創性深深打動,想要為他寫一本傳記。屠格涅夫組織了韋列夏金的大型作品展,這是俄國藝術家在巴黎的第一次個展,他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撰寫文章進行宣傳,并邀請了30多位評論家在法國和國際報刊上做了評論,這些評論全都是極其正面的。展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5萬人造訪和排隊參觀了沃爾內街的藝術俱樂部(Cercle artistique de la rue Volney)展出的超大畫布,作品的沖擊力來自其燦爛的光彩和用色,以及不同尋常的中亞草原場景。韋列夏金隨后在維也納也取得了類似的成功,在1881年秋季的短短三周內,估計有13萬人參觀了藝術館(Kunstlerhaus)的展覽,占該市成年人口的六分之一;第二年春天,在柏林,13.4萬名付費參觀者(以及其他許多免費參觀者)觀看了展覽;1882年,漢堡、德累斯頓、布達佩斯和布魯塞爾也舉辦了展覽。
屠格涅夫與畫家伊利亞·列賓(Ilia Repin)就沒有那么親密了,因為后者與斯塔索夫關系密切。這位民族主義評論家將其視為巡回畫派(Peredvizhniki)中最耀眼的明星。巡回畫派是19世紀60年代初脫離藝術學院的一批畫家,就像音樂界的“五人團”一樣,他們致力于創作“俄國風格”的作品。屠格涅夫認識到列賓的才華,不贊成斯塔索夫鼓勵其發展致力于民族主義和政治的藝術。他批評了列賓受莫斯科斯拉夫巴扎酒店的音樂廳委托創作的《斯拉夫作曲家》(1872年),因為他認為在一個場景中同時描繪死去和活著的作曲家是“虛假和不自然的”。他還指責列賓在給斯塔索夫的信中(這位評論家發表了這封信)自稱“拋棄”了拉斐爾。對于崇拜歐洲文明祭壇的屠格涅夫來說,這無異于表示拋棄了基督。
1873年,列賓作為接受美術學院獎學金的學者來到巴黎,在那里待了三年。接觸到西方藝術后,他開始脫離俄國民族畫派,轉而以受印象派影響的方式繪畫。1874年,當印象派舉行第一次展覽時,他正在創作自己最具印象派風格的作品之一——《巴黎咖啡館》(1875年)。列賓受莫斯科紡織品制造商和藝術贊助人帕維爾·特列季亞科夫(Pavel Tretiakov)的委托,在巴黎為屠格涅夫畫像。這幅作品原計劃在特列季亞科夫準備在他的國家藝術博物館中新開設的俄國名人廳展出。畫像的繪制并不順利——維亞爾多夫婦不喜歡它——列賓被迫做出改變,認為這會讓畫像變得更糟。屠格涅夫并不信服列賓作為肖像畫家的才華,他轉而求助于哈拉莫夫,并總是明確表示他更喜歡后者為他畫的像。
哈拉莫夫在沙龍中得到的顯要位置讓列賓惱火,后者的《巴黎咖啡館》被懸掛得如此之高,以至于完全沒有人注意(三周后,當他行使權利,要求將畫作重新掛在較低的位置時,委員會反而將其放得更高)。他在給俄國畫家伊凡·克拉姆斯科伊(Ivan Kramskoi)的信中寫道:“在這里,你需要庇護和人脈。”與哈拉莫夫不同的是,列賓發現他的畫作在歐洲很難賣出去。他向斯塔索夫抱怨說:“俄國人不買,法國人也不買。”屠格涅夫沒有表示鼓勵。他寫信給斯塔索夫,告訴后者最好讓列賓“回到你的羽翼之下,或者最好回到莫斯科。那是他來的地方,是他的天地”。列賓未能打入巴黎藝術市場——藝術世界的首都——讓這位畫家深感失望,他后來將自己的失敗歸咎于屠格涅夫討厭俄國民族主義畫派:“我們都是帶有社會色彩的理想主義者,而屠格涅夫畢竟是個美學家。”他憤憤地承認了這位作家作為俄國藝術家和巴黎藝術機構之間的中間人的關鍵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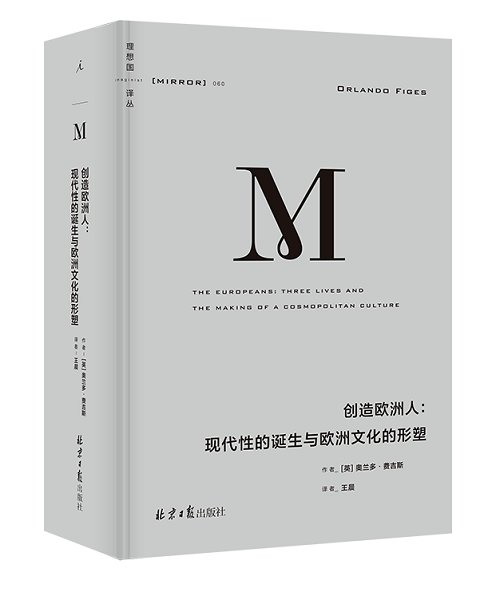
《創造歐洲人:現代性的誕生與歐洲文化的形塑》,[英]奧蘭多·費吉斯著,王晨譯,理想國|北京日報出版社2023年3月。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