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靈工經(jīng)濟(jì):新就業(yè)形態(tài)帶來新問題,解決新問題也需新思路
正如讀者看到,本書將Gig Economy翻譯成“靈工經(jīng)濟(jì)”,而不是“零工經(jīng)濟(jì)”,雖然后者是目前的主流譯法。作出這種改變并非刻意標(biāo)新立異,而是在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tái)上新興的靈工工作(gig jobs),與由來已久的傳統(tǒng)零工工作(casual jobs)有天壤之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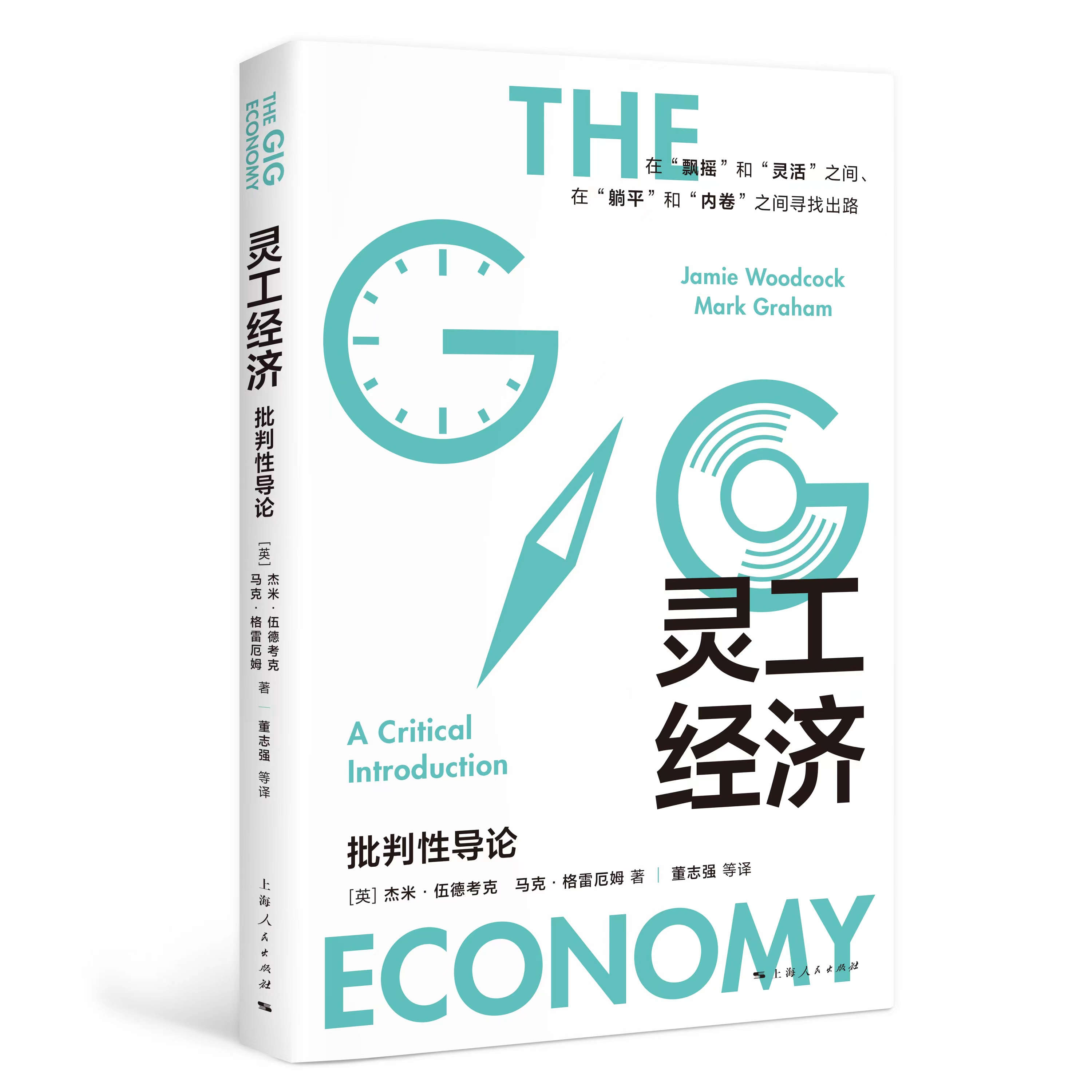
《靈工經(jīng)濟(jì):批判性導(dǎo)論》,杰米·伍德考克、馬克·格雷厄姆 著,董志強(qiáng)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
Gig的本義,是指短暫的音樂演奏會(huì),后來引申為臨時(shí)的前途未卜的工作,也有“小活/小項(xiàng)目”的意思。它是最近十年才迅速流行于媒體的術(shù)語。傳統(tǒng)的“零工”一詞,指的是那種內(nèi)容上零碎、分布上零散、機(jī)會(huì)上偶然、時(shí)間上短期的工作。而“靈工”(Gigs)這種工作,固然也有內(nèi)容零散、機(jī)會(huì)偶然、時(shí)間短暫的特點(diǎn),但它在工作特點(diǎn)和形態(tài)上與傳統(tǒng)零工大不相同——這種不同在文獻(xiàn)中已被定性為“工作性質(zhì)的變革”。
零工與靈工:在市場形態(tài)上,前者存在于傳統(tǒng)市場,后者存在于平臺(tái)市場;在工作性質(zhì)上,前者常具有被動(dòng)的短期性,即勞動(dòng)者不得不接受短期工作,而后者更多或在很大程度上體現(xiàn)了工作的靈活和機(jī)動(dòng)特性,這種靈活性和機(jī)動(dòng)性不僅是雇主的追求,很多時(shí)候也是勞動(dòng)者的追求;在勞動(dòng)力需求性質(zhì)上,前者主要體現(xiàn)為偶然性需求,后者主要體現(xiàn)為即時(shí)性需求;在工作機(jī)會(huì)及分布上,前者是少量工作分散在過于廣闊的空間,后者是大量工作集中于平臺(tái)之上;在交易成本上,前者的主要交易成本是搜索成本,即尋找工作的成本,后者的主要交易成本是信息甄別和選擇成本,即識(shí)別工作的成本,因?yàn)槠脚_(tái)上有太多工作信息需要識(shí)別和選擇。
雖然目前對(duì)Gig工作的討論主要針對(duì)網(wǎng)約車司機(jī)、外賣騎手等群體,在過去也有電召的士、餐飲配送員,但這些人并不是傳統(tǒng)零工的主流,現(xiàn)在卻是Gig工作的主流。而且Gig工作也絕不限于優(yōu)步或滴滴的網(wǎng)約車司機(jī)、戶戶送(Deliveroo)和美團(tuán)的外賣騎手,還包括上工(Upwork)和豬八戒網(wǎng)的遠(yuǎn)程服務(wù)、托客(mTurk)和小蜜蜂等眾包平臺(tái)上的微工作(microjob),以及網(wǎng)絡(luò)創(chuàng)作、直播……從跑腿(TaskRabitt)工人、愛彼迎(Airbnb)房東、在線市場賣家,到各種待命工人(ondemand workers)、斜杠青年、高技能承包人、季節(jié)工、顧問……他們都是靈工經(jīng)濟(jì)的參與者。鑒于這種Gig工作與零工的不同,在一些文獻(xiàn)中也以“新零工”和“舊零工/傳統(tǒng)零工”來區(qū)分。譯者經(jīng)過思慮,認(rèn)為有必要用“靈工”和“零工”來區(qū)分這兩類不同的工作形態(tài)。
術(shù)語和觀念的生命力,要在社會(huì)選擇過程中才能得到檢驗(yàn)。我們對(duì)Gig的翻譯是否更合適也有待檢驗(yàn)。但是,這絕不只是一個(gè)譯法的改變。零工工作,從字面意義上強(qiáng)調(diào)工作的零碎性,它常常與工作的糟糕面孔聯(lián)系在一起。靈工工作,在字面上強(qiáng)調(diào)工作的靈活性,由于雇主和工人都希望更靈活的工作模式,故靈工更加強(qiáng)調(diào)了新就業(yè)形態(tài)的積極面孔(雖然它也有消極面,本書對(duì)此著墨頗多)。從“零工”向“靈工”的名稱轉(zhuǎn)變,實(shí)際上是對(duì)工作未來的積極描繪:工作的未來是更靈活、靈捷、靈便的工作,而不是更零星、零散、零碎的工作。而且,對(duì)靈活性的強(qiáng)調(diào),也有助于我們思考個(gè)體如何適應(yīng)工作性質(zhì)的變革。
以上,就是我們將Gig Economy譯為“靈工經(jīng)濟(jì)”的原因。
靈工經(jīng)濟(jì)作為一種新經(jīng)濟(jì)現(xiàn)象迅速崛起,已經(jīng)不可小覷。據(jù)上工平臺(tái)2020年公布的數(shù)據(jù),美國有36%的勞動(dòng)力從事平臺(tái)靈工。有估計(jì)宣稱,我國靈活就業(yè)人員在2020年突破了2億,其中逾8000萬從事平臺(tái)靈工;靈工經(jīng)濟(jì)對(duì)GDP貢獻(xiàn)達(dá)22%。鑒于平臺(tái)的有效勞動(dòng)者數(shù)量不易精確統(tǒng)計(jì),上述數(shù)據(jù)未必準(zhǔn)確,但平臺(tái)工人數(shù)以千萬計(jì)乃不爭的事實(shí)。
有研究表明,僅抖音短視頻平臺(tái),一年(2019年8月至2020年8月)帶動(dòng)就業(yè)機(jī)會(huì)就高達(dá)3617萬個(gè),相當(dāng)于上海和深圳兩座城市常住人口總和。靈工經(jīng)濟(jì)已有的巨大就業(yè)規(guī)模和未來的巨大就業(yè)潛力,不容忽視。故國家相關(guān)部委將“快遞員”“直播銷售員”等平臺(tái)工作正式納入了職業(yè)分類大典;國務(wù)院《“十四五”就業(yè)促進(jìn)規(guī)劃》充分肯定了平臺(tái)勞動(dòng)新就業(yè)形態(tài),并提出“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yè)和新就業(yè)形態(tài)發(fā)展”。
與平臺(tái)靈工經(jīng)濟(jì)鮮活生動(dòng)的現(xiàn)象相比,對(duì)靈工經(jīng)濟(jì)的研究則相對(duì)黯淡得多。雖然也涌現(xiàn)出了一些優(yōu)秀的研究論文和著作,但總的說來人們對(duì)這一新就業(yè)形態(tài)的認(rèn)識(shí)和理解仍非常有限。倫敦大學(xué)社會(huì)學(xué)博士、牛津大學(xué)互聯(lián)網(wǎng)研究所研究員伍德考克和牛津大學(xué)互聯(lián)網(wǎng)研究所教授格雷厄姆合著的這本《靈工經(jīng)濟(jì)》,對(duì)靈工經(jīng)濟(jì)進(jìn)行了深度考察,兩位作者通過對(duì)英國、加納、南非、印度等國家新就業(yè)形態(tài)的調(diào)查研究,解析了靈工經(jīng)濟(jì)的運(yùn)行方式。書中充滿了對(duì)靈工工人的馬克思式的同情、對(duì)故事的生動(dòng)闡述、對(duì)趨勢的客觀分析、對(duì)爭論的激情面對(duì),不但很好地總結(jié)了現(xiàn)有研究,也提出了未來重塑靈工經(jīng)濟(jì)工作的建議。可以說,這是一本充滿批判觀察和深刻見解的著作。
兩位作者試圖說服人們,盡管平臺(tái)靈工經(jīng)濟(jì)促進(jìn)了服務(wù)創(chuàng)新,為成千上萬的人創(chuàng)造了就業(yè)機(jī)會(huì),但這并非沒有代價(jià);靈工經(jīng)濟(jì)中,平臺(tái)企業(yè)和算法控制隱身于界面之后,很容易將重大風(fēng)險(xiǎn)和責(zé)任轉(zhuǎn)嫁給原子化的靈工工人,由此帶來的社會(huì)問題不容忽視。這些問題具有全球性,不僅僅出現(xiàn)在歐美國家,在我國也初露端倪。比如算法對(duì)勞動(dòng)過程的控制,在當(dāng)下就頗受國內(nèi)學(xué)者的研究關(guān)注。作者的見解,對(duì)于思考我國當(dāng)代靈工經(jīng)濟(jì)發(fā)展,應(yīng)該具有重要的借鑒和啟示意義。
我們對(duì)本書的欣賞并不代表對(duì)作者完全認(rèn)同。兩位作者雖然呼吁重塑更公平的平臺(tái)經(jīng)濟(jì),但對(duì)平臺(tái)和勞動(dòng)者的態(tài)度絕非無所偏倚。他們對(duì)通過立法將靈工工人納作平臺(tái)雇員似乎頗為支持。而我們對(duì)此則有自己的看法。
平臺(tái)有不同角色,既可以是提供界面、撮合交易的中介,也可以是新興的雙邊組織這種新商業(yè)模式中的監(jiān)管者,還可以是市場的參與者。平臺(tái)與其工人的關(guān)系是多元的,不是也不可能整齊劃一規(guī)定為勞動(dòng)關(guān)系。靈工經(jīng)濟(jì)中的高收入勞動(dòng)者,很可能自愿選擇獨(dú)立承包人身份而不是雇員身份,因?yàn)檫@樣可以節(jié)約收入的稅收支出。在許多國家,個(gè)人經(jīng)營比個(gè)人所得的稅率要低很多。實(shí)際上,平臺(tái)用工關(guān)系是不是勞動(dòng)關(guān)系,可能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重要。要加強(qiáng)對(duì)平臺(tái)工人的就業(yè)保障并不一定要仰賴認(rèn)定勞動(dòng)關(guān)系,完全可以有替代的辦法和手段。
比如:將獨(dú)立承包人身份的靈活就業(yè)者也納入社保體系(這是目前廣東省正在探索的創(chuàng)新做法);又或者,讓平臺(tái)為工人提供類似正式員工的一部分待遇(如最低工資),但卻不必將其納作雇員(這是靈工經(jīng)濟(jì)的美國加州模式)。
新就業(yè)形態(tài)的“新”,帶來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問題,解決新問題也需要“新”思路,重要的是不要被“既定”體系所束縛,不要固守在舊的法律和規(guī)定框架下以舊辦法解決新問題,而應(yīng)重新思考與新就業(yè)形態(tài)相適應(yīng)的政策體系創(chuàng)新。
靈工經(jīng)濟(jì)的重要特點(diǎn)是“靈”,即靈活、靈便、靈捷。在工人的雇員身份和獨(dú)立承包人身份之間,在平臺(tái)對(duì)不同組織形式的選擇之間,最佳的監(jiān)管政策應(yīng)該是保持中立,既不偏向雇員式組織形式,也不偏向獨(dú)立承包人組織形式,不必“欽定”某種具體的勞動(dòng)組織形式,而是努力為各種組織形式提供公平的競爭環(huán)境。政府監(jiān)管應(yīng)致力于塑造和維護(hù)公平競爭,既要防范平臺(tái)對(duì)工人的過度剝奪,也要避免過度保護(hù)工人而使得平臺(tái)難以為繼。此外,我個(gè)人還認(rèn)為,本書兩位作者在末章對(duì)未來的建議中,所提出的平等所有權(quán)聽上去很不錯(cuò),但可能只是理想中的烏托邦;對(duì)大家能夠做些什么的建議,似乎也較為激進(jìn)。但作者呼吁關(guān)注底層勞動(dòng)者,這確實(shí)是應(yīng)該的。
另外,本書將目光聚焦在勞動(dòng)者和勞動(dòng)組織過程上,這只是從一個(gè)視角觀察了靈工經(jīng)濟(jì)的一個(gè)側(cè)面。從方法和內(nèi)容上看,它更像一本社會(huì)學(xué)而不是經(jīng)濟(jì)學(xué)的著作。實(shí)際上,靈工經(jīng)濟(jì)是工作性質(zhì)、就業(yè)形態(tài)和經(jīng)濟(jì)形態(tài)的變化,對(duì)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的影響將是全面的、深刻的、深遠(yuǎn)的。
有點(diǎn)令人困惑的是,目前對(duì)靈工經(jīng)濟(jì)討論得更多的是社會(huì)學(xué)、法學(xué)和管理學(xué)領(lǐng)域的學(xué)者,經(jīng)濟(jì)學(xué)者參與相對(duì)較少。但毫無疑問,經(jīng)濟(jì)學(xué)不能忽視靈工經(jīng)濟(jì)的興起,因?yàn)樗鼛砹艘幌盗信c經(jīng)濟(jì)研究相關(guān)的問題,比如對(duì)“就業(yè)”可能需要重新定義、人力資本結(jié)構(gòu)需要適應(yīng)性調(diào)整、工作數(shù)字化很可能加劇不平等和收入極化、需要面向全社會(huì)托底保障改革現(xiàn)有的基于標(biāo)準(zhǔn)就業(yè)的社會(huì)保障體系、稅收政策需要適應(yīng)新就業(yè)形態(tài),乃至宏觀經(jīng)濟(jì)理論和政策也因靈工經(jīng)濟(jì)的興起而需要反思。但目前有關(guān)這些方面的研究仍非常缺乏。
平臺(tái)靈工經(jīng)濟(jì)創(chuàng)造了更多工作機(jī)會(huì),但也放大了工作中種種面目可憎的問題,比如算法控制、勞動(dòng)者缺乏穩(wěn)定和保障等。本書讓人們更加注意到這些問題,并深入分析了勞動(dòng)者的抗?fàn)帲懻摿嗣嫦蚋降鹊墓ぷ魇澜绲奈磥砜梢杂泻胃纳坪徒鉀Q之道。經(jīng)濟(jì)發(fā)展必須關(guān)注“人”的發(fā)展,關(guān)注勞動(dòng)者也就是關(guān)注我們自己,所以關(guān)注這些重要問題是應(yīng)有之義;但我們也應(yīng)明白,手上沾滿污泥時(shí)需要的是洗手,而不是砍掉雙手。
平臺(tái)靈工經(jīng)濟(jì)興起的積極面遠(yuǎn)甚于消極面,它增加了勞動(dòng)者工作選擇的自由,帶來了就業(yè)和收入的增加。在全球遭受疫情的特殊年代,它甚至堪稱民生的重要保障。滴滴司機(jī)、外賣騎手也許算不上好工作,但這些工作畢竟促進(jìn)了市場競爭、提高了經(jīng)濟(jì)效率,更重要的是吸引到眾多工人投身其中(說明它們至少不比這些工人以前干的工作更糟糕)。這是本書中似乎有所回避,但我們也應(yīng)該看到的另一面。
正如本書副標(biāo)題揭示,本書是對(duì)靈工經(jīng)濟(jì)的“批判性導(dǎo)論”,這就不難理解作者對(duì)靈工經(jīng)濟(jì)的批判性立場。在一些人為靈工經(jīng)濟(jì)大唱贊歌的時(shí)候,我們確實(shí)更需要本書這樣的聲音,意識(shí)到潛在降臨的風(fēng)險(xiǎn);同樣,如果本書的觀點(diǎn)成為主流,那我們也要提醒自己看到靈工經(jīng)濟(jì)改善人類經(jīng)濟(jì)生活的積極面。
總之,本書提出的問題具有時(shí)代重要性,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觀察細(xì)致入微、分析思考深刻而有新意(當(dāng)然并非完全沒有偏頗)。其內(nèi)容不一定讓所有人共鳴,觀點(diǎn)不一定被所有人認(rèn)同,但無疑對(duì)我們更深入、更全面地認(rèn)識(shí)和了解靈工經(jīng)濟(jì)這種新就業(yè)形態(tài)和新經(jīng)濟(jì)形態(tài)大有幫助,也一定能促使讀者深思和反思。這是本書的價(jià)值所在。
(本文為《靈工經(jīng)濟(jì):批判性導(dǎo)論》一書序言,作者董志強(qiáng)為該書譯者,華南師范大學(xué)二級(jí)教授,珠江學(xué)者特聘教授,長期從事勞動(dòng)經(jīng)濟(jì)、制度與發(fā)展、博弈論與經(jīng)濟(jì)行為等領(lǐng)域研究。)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