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從家族到個體,一路南下的東北人丨社會觀察
原創(chuàng) 深度營 深度訓練營
深夜一點,文希關上房間門,星星點點的燈光漸次熄滅,下一秒她便癱倒在床上,忙活一整天的疲憊在被窩里被熨帖,昏昏沉沉的睡意正來襲,突然身邊的手機開始震動,文希強迫自己睜開眼接聽電話,得知客戶的狗狗意外去世,她從床上掙扎起來,匆匆找到車鑰匙便往客戶家開去。
“做我們這一行,必須得24小時待命,一接到電話就得開始工作。”這是文希成為寵物入殮師的第二個年頭,清洗毛發(fā)、告別儀式、制作紀念品、安慰寵物主人……文希像對待自己的家人一樣對待每一位來到這里的寵物“寶貝”,從這份職業(yè)里,她學會了如何從容地對待生死。
“走出東北,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這是無數(shù)東北人受到過的期望。他們懷揣著夢想,只身一人,或攜家?guī)Ь欤瑸樽叱鰱|北開始了南遷之路。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shù)據(jù)顯示,東北的人口數(shù)在近10年里減少了1101萬人,相當于哈爾濱整座城市的人口被搬空。2016年,國務院就已部署了新一輪東北振興戰(zhàn)略,發(fā)展新興產業(yè)來應對人口負增長,但目前,東北的外流人口仍在不斷增長。
對于那些已經南遷的東北人,如今的生活如何?離開東北后,他們還留存多少有關東北的印記?未來的歸處又是何方?從一個家族的南遷扎根到一個家庭的往返遷徙,再到一個人的生活選擇,不同的世代的答案不盡相同。這些跨越時間與空間的故事,最遠的距離是4600公里,最長的時間是73年。

圖片來自網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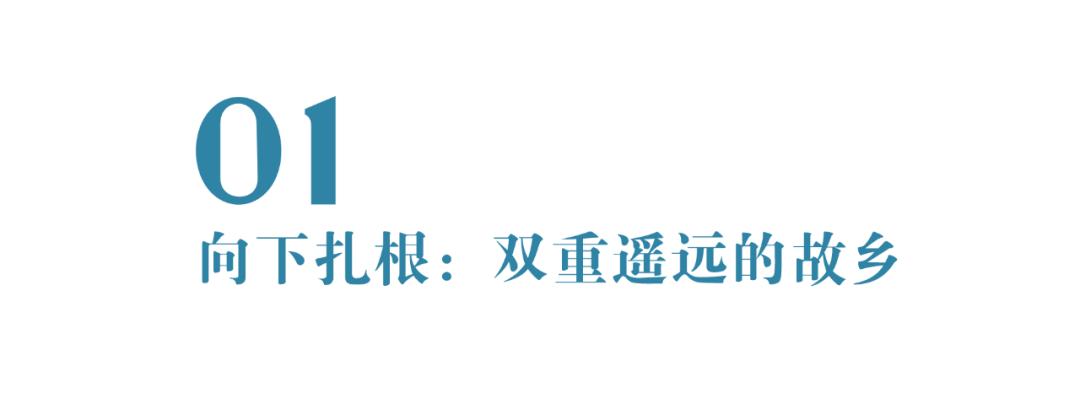
今年是錢芳來到武漢的第73年。如果說廣闊的地域尺度拉遠的尚是人與人的距離,那漫長的時間尺度帶來的則是一個家族的扎根與北方記憶的消磨。
“對于東北,似乎已經沒有多少印象了。”黃小菲借著奶奶的回憶說道。奶奶錢芳今年88歲,出生在黑龍江綏化,一座緊挨著哈爾濱的地級小城。
1950年,15歲的錢芳選擇參軍,隨后隨著軍隊離鄉(xiāng)一路南下至武漢發(fā)展建設。憑借著家里良好的教育底子,錢芳成為了部隊里的一名軍醫(yī)。“奶奶在家里排行老五,是老小,離開家鄉(xiāng)既是時代的需求,也是因為她本身就是比較果敢,是個主意很正的人。”就這樣,十幾歲的錢芳跨越2000公里,在武漢開啟了她的新生活。
1959年,黃剛從中醫(yī)藥大學畢業(yè),來到武漢的一個空軍學院成為軍醫(yī),因為機緣巧合,兩個帶著理想的年輕人在武漢相遇,開始了屬于他們的愛情長跑,一跑就是六十幾年。“奶奶和爺爺相遇后,便有了心意,于是兩個人就決定在武漢結婚定居了。”尚不發(fā)達的交通與通信,讓錢芳與家鄉(xiāng)的距離被拉的更長,結婚生子后,她幾乎沒有再回到綏化,靠著電話偶爾于家里人聯(lián)系。
離開了東北幾十年后,家庭也嵌入了武漢這座城市。“爺爺奶奶后來都住在武漢的休干所,我的姐姐哥哥也都在大院里長大,比起東北我更熟悉武漢。”黃小菲談起往事,大多都已經是和武漢有關的故事,而她作為奶奶最小的孫女,其實連大院里的生活也未曾觸碰。直系親屬一個個的離去,錢芳與東北的故事只能維持在逐漸消散的記憶之中,“奶奶最后一次見的親人,是她的姐姐,在奶奶70多歲的時候從黑龍江來到武漢,兩個人見了一面。”

黃小菲一家的合照,右一為錢芳
時間的跨度里,不變的是對食物的感知。錢芳扎根在武漢多年,口音變了,生活習慣變了,但在她掌握廚房的日子里,東北菜仍然是餐桌上的主角:“小雞燉蘑菇、鍋包肉還有各種面食餃子,是我們家的常客。”錢芳的口味,延續(xù)到了黃小菲的父親身上,身為湖北人的母親也學會了做東北菜。每年春節(jié),他們家會同東北地區(qū)的習俗一樣,炸一些花花綠綠的“蝦片”當做孩子們的零食;外出吃飯時,他們也會更偏愛走進東北菜館,點上一盤醬大骨作為主菜。這份帶著東北記憶的菜單,讓黃小菲時常感嘆自己四分之一的東北血統(tǒng),“這真的很奇妙,地域的血緣讓我對從未觸碰過的遙遠北方有了興趣,東北人身上的直爽我也很喜歡。”
米壽之年的錢芳,對東北的回憶早已模糊不清,但關于在家鄉(xiāng)學習日語俄語的經歷以及人生中的一些重要節(jié)點,她仍時常談起。
黃小菲與錢芳相差了68歲,這個數(shù)字對于南遷這件事上意味著家族三代的完整扎根。對于黃小菲來說,東北是渴望走進的陌生地域,她把東北形容為“遠方親戚”,而對于錢芳來說,東北則是她跨越地域與時間的雙重限制,多年未曾回到過的遙遠故鄉(xiāng)。

不同于錢芳的被動南遷,來自哈爾濱的高倫倫一家的遷徙經歷更像是候鳥南飛選擇溫暖棲居地,他們的目標不是房車,而是0度以上的氣溫。
今年,是高倫倫一家在海南三亞過冬的第十年,從哈爾濱到三亞,他們要坐六個半小時的飛機,“像候鳥一樣去過冬。”高倫倫這樣形容道。
哈爾濱,一座一年有五個月需要供暖的城市。極端的氣候,是高倫倫一家,也是眾多黑龍江人渴望南遷過冬的首要原因,“冬天外面零下三十幾度,很難出門,而且因為燒煤供暖,霧霾很嚴重。”面對嚴寒與低質量的空氣,老人最先敗下陣來,為了頤養(yǎng)天年,他們開始尋找更舒適的養(yǎng)老地,三亞成為了首選之一。相較于哈爾濱,三亞靠海,工廠少,植被覆蓋率更高,空氣質量優(yōu)良率可達到100%,且冬季平均氣溫在15度以上。(數(shù)據(jù)來源于三亞市生態(tài)環(huán)境局《三亞市2020年環(huán)境質量年報》)對于許多老人而言,是再合適不過的天然療養(yǎng)院。就這樣,高倫倫一家為了家里老人的療養(yǎng),也成為了三亞的常駐游客之一。
溫暖與海,令無數(shù)東北人向往。“雖說可以住酒店,但既然每年都要過去待半年,索性想著買個房子更方便一些。”面對旺季高昂的旅游費用,高倫倫一家認為在三亞買房養(yǎng)老更為實際劃算。2018年初,在海南尚未出臺買房限購政策前,高倫倫的姥爺用退休金在三亞買了自己的房子。為了實現(xiàn)徹底的海灘夢,他們避開了市中心,在三亞灣,一個走路十幾分鐘就能到達海邊的地方有了定所。從11月到來年4月,老人們會在三亞居住。因為家人的工作多是遠程可以處理,過年的兩個月,高倫倫也會和父母一起前往三亞。自此,他們正式成為了南飛的候鳥。

高倫倫一家在三亞享受的海邊一角
“因為有很多跟我們家一樣情況的老人,他們甚至有專門的老年遛彎微信群。”高倫倫描述。高倫倫與家人在三亞的生活大多是家海邊菜市場三點一線,早起去買菜,偶爾在海邊曬太陽,父親工作,母親打理家事,高倫倫與弟弟則是放寒假的狀態(tài),生活上雖然愜意但并不像游客更像是居民。而這群來自東北的老人們組織了一個專門的玩樂團,安排了很多行程,他們約定冬天在三亞一起吃喝走步,夏天回哈爾濱接著“溜達”。“這些老人一天都能走上兩三萬步,有一次我看微信步數(shù)發(fā)現(xiàn)今天只走了幾千步,擔心壞了,后來發(fā)現(xiàn)人家?guī)讉€是去打麻將了,沒顧得上鍛煉。”高倫倫笑稱這是東北人的天性,愛玩又自來熟。

一家人冬天在三亞的露天泳池
三亞每年約有30萬東北人前來居住。2017年,這里已經建立了“黑龍江省公安廳駐海南三亞出入境管理服務站”。近年以來,三亞開始向打造自由貿易港而努力,同時建設國家旅游消費中心,過去落腳三亞的人們,正在經歷這座小島的轉型。
“三亞的冬天分三撥人,一撥人是冬天居住的東北人,一撥人是游客,剩下的是三亞的本地人。”東北人體量之大,讓三亞抓住了商機。東北菜館,農家院等等依海而生,宰客現(xiàn)象也就不乏出現(xiàn)。“生活是越來越方便的,但冬天一到,物價就漲得厲害,特別是近幾年,到處都是高消費項目,海鮮每斤可能要漲個20多塊錢,是哈爾濱的好幾倍。”高倫倫覺得這是住在三亞過去沒有體會到的地方,“不過等到夏天,再來三亞,這里又會回歸到一個純粹的小海島,沒有什么人,就像是它最開始的模樣。”東北人們就在三亞這座小島的輪轉中也適應著它的改變。
當越來越多的東北人涌入海南,不斷高升的物價和房價,讓許多追隨“溫暖棲居地”的東北人望而卻步。而在三亞這座小島的西面,云南的西雙版納憑借著同樣的氣溫和更平價的生活成本,正在涌進一批尋找“新家”的東北人,他們活躍在每一個溫暖的地方,開始新的生活。
但對于高倫倫本人來說,三亞已然是另一處故鄉(xiāng)。在哈爾濱的冬天,屋外的世界是難以踏入的,老人也不與他們住在一起,每個人似乎都被封閉在了自己的小房間里,但在三亞的生活,他們可以在尚未立春的日子里久違地一起躺在沙灘上享受陽光,晚上再一起吃一頓海鮮。今年,高倫倫的舅舅也在三亞買了新房,一家人的“候鳥南遷”又多了一處落腳。“我覺得三亞已經不只是作為我們冬天居住的一個城市的屬性,它更像是我們能暫時放下現(xiàn)實生活的一段幸福時光。”一家人聚少離多,在三亞的日子,也許更有家的模樣。

離開東北的群體之中,除了家族的扎根與家庭的遷徙,更多的是像劉亞丹一樣的年輕個體,他們暫且放下了來自家鄉(xiāng)的羈絆,剝離了熟悉的社交場域,走向南方。
2014年,劉亞丹從齊齊哈爾的大學畢業(yè)后只身來到了廣州,對于這個90后東北女孩而言,廣州遙遠,卻充滿著屬于年輕人追夢的氣息。

廣州隨處可見的“橋洞歌手”
劉亞丹大學的專業(yè)是英語,相較于家鄉(xiāng)的外語需求,南方的工作機會顯得更為廣闊。因為親戚在廣州的緣故,劉亞丹一畢業(yè)也南下到廣州,找到了一份對外漢語的工作。
“執(zhí)輸行頭,慘過敗家。”是廣東人常說的一句俚語,意思是慢人一步將失去先手機會,這句話很形象地形容了廣東的工作環(huán)境,無數(shù)年輕人來到這里,為了得到這份“先手機會”而向前奔跑著,劉亞丹就是渴望跑在前頭的那個。
“松弛不符合我的生活狀態(tài),如果閑下來就會覺得自己在浪費時間。”雖然對外漢語的工作大多時候可以在線上完成,但是相較于齊齊哈爾舒適、慢節(jié)奏的生活,劉亞丹更喜歡廣州緊湊的生活環(huán)境,能夠不斷地催促著自己前進。
廣東的快生活節(jié)奏,讓諸多南下廣深的年輕人一直尋找著安穩(wěn)與夢想的平衡點。幾年前,劉亞丹的表哥會經常勸她返回家鄉(xiāng),過更為安穩(wěn)的日子,劉亞丹始終沒有接受,但是這幾年表哥說這些話的頻率低了許多:2021年,劉亞丹靠著自己的努力在廣州買了房子,實現(xiàn)了“粵A房”的目標,“一方面是因為自己已經買了房,有了穩(wěn)定的工作;另一方面表哥也有了新的想法。”劉亞丹的表哥在哈爾濱的一家公司呆了十幾年,已經是那家公司的“元老級”人物,但在想要轉崗的時候,卻發(fā)現(xiàn)哈爾濱的機會過于稀缺,沒有辦法滿足他的轉崗需求。面對這些的時候,原本堅定在家鄉(xiāng)扎根發(fā)展的表哥,此時也改變了自己的心意。
今年是劉亞丹在廣州的第九年,剛開始來到廣州的時候,劉亞丹也會有心理上和文化上的不適應。“下班的時候,同事都會聚在一起用粵語交流,那時我覺得粵語并不好聽,也不愿聽。”劉亞丹回憶起在廣州打拼的這些年,朋友和她聊天時說普通話,但是和其他朋友聊天會轉化為湛江話,這個時間里劉亞丹覺得自己是孤單的、融不進去的,仿佛置身在另一個極度遙遠的地區(qū)。但也因為時間的流逝和與城市的相處,劉亞丹慢慢適應了廣州的生活方式,很少再產生語言導致文化隔閡這樣的想法,“吃喝住行我基本上已經完全適應了,當然聽不懂粵語時偶爾還會覺得是局外人。”
一個人的打拼生活里多少摻雜著孤獨感,但談及情感陪伴,劉亞丹笑稱自己還沒有組建家庭。“我原以為是地域上的性格差異導致的,但時間久了發(fā)現(xiàn)還是找不到,所以慢慢覺得其實是自身的問題更多一些。”以此,劉亞丹分享了和自己同樣南下工作的同學因為在廣州找不到合適的伴侶,最后選擇了返鄉(xiāng)成家立業(yè)的故事。但對于劉亞丹而言,起初認為廣州男生的性格比較含蓄,不像東北人一樣那么“敞亮”,但是相處久了之后發(fā)現(xiàn),從自己的角度出發(fā),南方人里的委婉一面反而相處起來更舒服。“所以我現(xiàn)在覺得愛情這東西并不是地域決定伴侶,也許更多是自己在戀愛方面的選擇所決定的。”

沙面的老年舞團和樂隊,周圍聚集著許多年輕人
關于之后會不會回家鄉(xiāng)發(fā)展,劉亞丹沒有太多猶豫就給了否定的答案,“我應該不會回去了,南遷的生活對我來說已經是一種固定化的生活狀態(tài)。”雖然在廣州生活了九年,但劉亞丹仍然覺得自己的未來還很長,目前還是要“單打獨斗”的階段,并不急于回歸到更為舒適的圈子里。除了自我的選擇,劉亞丹也在考慮當父母退休后把他們接到廣州來照顧的想法,不過在這之前,劉亞丹并沒有決定把自己永遠留在廣州,以“旅居”的狀態(tài)生活,多多體驗各地的風情,才是她更想追求的理想人生。
開年,一部電視劇《人世間》,讓東北這片遠方再一次走向人們的視野,當閃光燈暗下,這片匯聚著三個省區(qū)廣達8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背后,是無數(shù)個出走的個體和家庭。他們因為衰落的經濟和冰冷的冬季一路南下,為了時代,為了生活,為了自己。
(本文除劉亞丹,其余均為化名)
原標題:《從家族到個體,一路南下的東北人丨社會觀察》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fā)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fā)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