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人類語言能力的自然演化:喬姆斯基對陣達爾文
原創 丹尼爾·丹尼特 集智俱樂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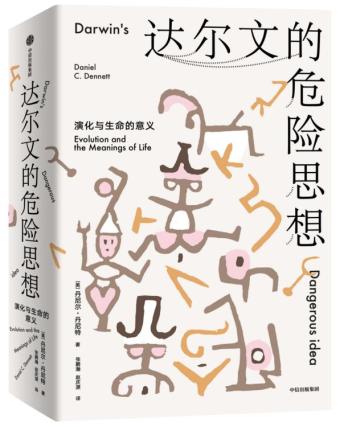
導語
查爾斯·達爾文用他的《物種起源》為生命的多姿多彩提供了一種解釋:是演化和自然選擇造就了這個星球上繽紛的生命。然而自誕生的那一天起,達爾文自然選擇和演化的理論就引發過很多爭議。很多人認為,人類語言能力的演化不能用達爾文式的自然選擇來解釋。諾姆·喬姆斯基,世界上最偉大的語言學家,以及斯蒂芬·杰·古爾德,世界上最著名的演化理論家,就曾一再表示語言可能不是自然選擇的產物。
在《達爾文的危險思想》中,丹尼特基于科學事實和縝密的邏輯論證提出,演化是一個機械的算法過程,這種算法過程不僅決定了羚羊的速度、老鷹的翅膀和蘭花的形狀,也同樣決定了心靈、意義、道德等概念。丹尼特把對演化和自然選擇的論述從生物學領域拓展到了文化、語言、社會等生物學以外的其他領域,把對演化和自然選擇的理解提升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本文節選自《達爾文的危險思想》第十三章。
研究領域:語言演化,自然語言,人工智能,認知心理學,自然選擇
[美] 丹尼爾·丹尼特 | 作者
人們可能會認為,喬姆斯基只要把他那頗具爭議的、關于語言器官的理論建立在演化論的穩固基礎之上,那就萬事大吉了,況且他在自己的一些著作中也暗示過某種這樣的聯系。但他在更多的時候對此持懷疑態度。
——斯蒂芬·平克(Pinker,1994,p.355)
至于語言或翅膀這樣的系統,我們甚至很難想象出可能讓它們得以產生的選擇過程。
——諾姆·喬姆斯基(Chomsky,1988,p.167)
一邊是一批認知科學家,他們有的通過人工智能進入該領域,有的則是通過研究解決問題的行為和形成概念的行為,另一邊是通過關注語言問題進入該領域的人,雙方仍然存在著相當大的隔閡……當語言過程作為一種人類能力的獨特性得到強調的時候—喬姆斯基就是這么做的……,這種隔閡就會加劇。
——赫伯特·西蒙與克雷格·卡普蘭(Simon and Kaplan,1989,p.5)
1956年9月11日,無線電工程師學會(Institute for Radio Engineers)在麻省理工學院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宣讀了三篇論文。
其中一篇是艾倫·紐厄爾和赫伯特·西蒙的《邏輯理論機》(NewellandSimon,1956)。二人在文中首次展示了一臺計算機如何能夠證明重要的邏輯定理。他們談到的這臺“機器”是他們后來的“通用問題解決器”(GeneralProblem Solver)(Newell and Simon,1963)的父親(或祖父),也是計算機語言Lisp(表處理語言)的原型,而Lisp對于人工智能的意義大致就像DNA代碼對于遺傳學的意義。若要角逐“人工智能界亞當”的美名,邏輯理論機足以同阿爾特·塞繆爾的跳棋程序匹敵。
第二篇論文是心理學家喬治·A.米勒的《一個神奇的數字:7±2》,這篇論文后來成為開創了認知心理學領域的經典論文之一(Miller, 1956)。
第三篇論文的作者是一名27歲的哈佛大學初級研究員,名叫諾姆·喬姆斯基,論文的題目是《語言描寫的三種模型》(Chomsky, 1956)。任何回溯性加冕都難免會有些武斷,這已經屢見不鮮,但喬姆斯基在無線電工程師學會的演講作為現代語言的標志性事件,絕對是名副其實。
三大新興科學學科在同一天誕生于同一個房間里——不知道當時的聽眾中有多少人感覺到自己正在親身經歷一個如此有分量的歷史事件。喬治·米勒就感覺到了,他后來對那次會議的描述(Miller,1979)向我們表明了這一點。而赫伯特·西蒙在回顧這場會議的時候,其觀點則隨時間的推移而變化。在1969年出版的書中,他提請人們注意這個非比尋常的時刻,并說道(Simon,1969,p.47):“因而這兩塊理論[語言學和人工智能]在早期就有著親切友好的關系。千真萬確,因為它們都以同一種人類心靈觀作為自己的觀念基礎。”真要是這樣就好了!等到1989年,他就能看到雙方的隔閡已經擴大到了怎樣的地步。
在眾多的科學家中,偉大的科學家少之又少,而在偉大的科學家中,能夠發現一個全新領域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但畢竟還是有幾個。查爾斯·達爾文是一個,諾姆·喬姆斯基又是一個。在達爾文之前就有生物學——博物學、生理學、分類學等等——這些都被達爾文統合成了我們今天所知道的生物學。無獨有偶,在喬姆斯基之前就有語言學。作為當代科學領域的語言學,有語音學、句法學、語義學和語用學等子學科,有交戰不休的學派和自立門戶的分支(比如人工智能中的計算語言學),還有心理語言學和神經語言學這樣的子學科。語言學從各種不同的學術傳統中成長而來,可以追溯到一系列先驅的語言探究者和語言理論家,從格林兄弟到費爾迪南·德·索緒爾和羅曼·雅各布森,可這一切都在一位先驅者——諾姆·喬姆斯基——率先實現的理論進展下,被統合成了一個富含內部聯系的科學探究家族。
在1957年出版的小書《句法結構》中,他把自己之前一項雄心勃勃的理論探究的成果應用到了自然語言(如英語)上,這項理論探究是在設計空間中的另一個片區進行的:該片區是個邏輯空間,其中是能夠生成和辨認所有可能語言之語句的所有可能算法。喬姆斯基的工作嚴格遵循圖靈的探究路徑,圖靈的純邏輯探究關注的是我們現在稱作計算機的這種東西所具有的力量。喬姆斯基最終界定了一個關于語法類型或語言類型的階序——喬姆斯基層級(Chomsky Hierarchy),所有學計算理論的學生至今仍能靠它初窺門徑。他進而展示了這些語法如何能夠同另一個階序相互界定,后者由各種自動機或計算機類型構成——從“有限狀態機”,到“下推自動機”和“線性有界機”,再到“圖靈機”。
幾年后,當喬姆斯基的研究第一次進入我們的視線時,它在哲學界掀起的沖擊波令我記憶猶新。那是1960年,我在哈佛大學讀大二,當時我問奎因教授,在那些批評他觀點的人中,有誰的作品是我應該讀的。(當時我自認為是冷酷無情、信念堅定的反奎因派,并且已經開始在為我的畢業論文擬定論點,而這論文當然是要攻擊奎因的。所以凡是在觀點上反對奎因的人,我都必須了解!)他當即建議我去讀讀諾姆·喬姆斯基的研究。當時哲學界很少有人聽說過這位作者,但他的名氣很快就蓋過了我們所有人。
語言哲學家們對他的研究反應不一。有些人愛,有些人恨。我們中間愛他研究的人,很快就清一色地搞起了轉換、樹狀圖、深層結構以及其他各類可以算作某種新形式主義的神秘玩意兒。在恨他研究的人中,有許多人譴責這是一種庸俗的科學主義,是一群帶著科技范兒的焚琴煮鶴之徒在丁零咣啷地發起攻擊,妄圖破壞語言那優美動人、無法分析、無法形式化的精妙之處。在幾所主要大學的外語系中,這股敵意簡直勢不可當。或許喬姆斯基可以在麻省理工學院當一名語言學教授,或許語言學可以在那里被列入人文學科,但喬姆斯基的研究是科學,而科學就是大寫的敵人——每個實名認證的人文主義者都知道這一點。
自然帶來的知識無不可愛,
我們的智力貿然插手,
扭曲了萬物的美好形態,
——我們殺戮,以解剖
華茲華斯的浪漫主義觀點認為,科學家是美的謀殺者,而這一點似乎完美地體現在了諾姆·喬姆斯基、自動機理論家和無線電工程師身上。但一個天大的諷刺在于,喬姆斯基一直都在捍衛一種對待科學的態度,而這種態度似乎可以給人文主義者帶來救贖。正如我們在上一節所看到的,喬姆斯基認為科學是有限度的,尤其是當它遇到心靈的時候,就像是踢到了鐵板。要把這件怪事辨個分明,一直都挺難的,即便對于那些能夠處理當代語言學中的技術性細節和爭議的人來說也是如此,不過這件怪事也確實令人訝異很久了。喬姆斯基抨擊B.F.斯金納《言語行為》(Skinner, 1957)的那篇評論(Chomsky, 1959)廣為人知,是認知科學的奠基性文獻之一。與此同時,喬姆斯基一直堅定不移地敵視人工智能,并且大膽地將他的一本主要著作命名為《笛卡兒語言學》(Chomsky, 1966)——仿佛是在認為笛卡兒的反唯物主義二元論就要卷土重來了。他到底站在哪一邊呢?反正不是達爾文那邊。如果畏懼達爾文者想找一位本身就頗具科學淵源和科學影響力的勇者,喬姆斯基就是他們的不二之選。
我當然是慢慢才明白這一點的。1978年3月,我在塔夫茨大學操辦了一場引人注目的討論會,而哲學與心理學學會(Society for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順理成章地承擔了主辦方的職責。有一場小組討論名義上是要談人工智能的基礎和前景,結果卻變成了四位重量級理論家之間的口舌之爭,宛如一場雙打摔跤賽。諾姆·喬姆斯基和杰里·福多爾向人工智能發起攻擊,羅杰·尚克(Roger Schank)和特里·威諾格拉德(Terry Winograd)則挺身護之。
尚克當時正在研究用于理解自然語言的程序,兩位批評者的火力集中在他的一個方案上,該方案旨在(在計算機中)對由某些細枝末節組成的雜亂無章的集合加以表征,這些細枝末節盡人皆知,而且也是人人在解碼尋常言語行為時都要依靠的,而尋常語言行為往往是暗示性的、不完整的。喬姆斯基和福多爾對這項事業大為不屑,但他們發動攻擊的根據卻隨著比賽的進行而漸漸起了變化,這是因為尚克在霸凌成風的院系里也是一把好手,他堅定地捍衛著自己的研究項目。他們一開始的攻擊策略,是對準概念上的錯誤進行直截了當、“第一原理”式的譴責——尚克的研究不是竹籃打水,就是水中撈月——可最后喬姆斯基卻做出驚人的讓步:事實可能確如尚克所料,人類理解對話的能力(以及更一般意義上進行思考的能力)可以用成百上千個粗制濫造的小裝置之間的互動來加以解釋——但那就太跌份兒了,因為那會最終證明心理學并不“有趣”。在喬姆斯基的心目中,只有兩種可能性是有趣的:我們最后可能發現心理學“就像物理學一樣”——其規律性可以被解釋為若干深刻、優雅、不可抗拒的法則造成的結果——或者,我們最后可能發現心理學全然沒有法則——在這種情況下,研究或闡明心理學的唯一方法,就會是小說家的方法(假如真是這么回事兒,那么比起羅杰·尚克,喬姆斯基肯定更喜歡簡·奧斯汀)。
隨后,討論組成員和觀眾之間也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喬姆斯基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同事馬文·明斯基的一項觀察將爭論推向高潮。“我想只有麻省理工學院的人文教授才會對第三種‘有趣’的可能性如此習焉不察:我們到頭來可能發現心理學就像工程學一樣。”明斯基一語中的。用工程學方法來考察心靈問題,其前景中的某些東西正是一類特定的人文主義者所深惡痛絕的,而且跟討厭唯物主義或討厭科學無關。喬姆斯基本人就是一個科學家,而且想必也是一個唯物主義者(他的“笛卡兒式”語言學走得并沒有那么遠!),但他不會跟工程學產生任何瓜葛。心靈若只是一個小器具或小器具的集合,總歸有損于其尊嚴。心靈就算最終被證明是一個無法破解的奧秘,一個專供混亂棲身的秘所,也好過成為那種會把自己的秘密拱手交與工程學分析的實體!
雖然明斯基對喬姆斯基的觀察當時打動了我,但我并未領會個中要旨。1980年,喬姆斯基在《行為與腦科學》上發表了作為標靶文章(target article)的《規則與表征》(Chomsky, 1980),而我則是評論者之一。不管當時還是現在,爭議的焦點都在于,喬姆斯基堅持認為,語言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天的,而說孩子會習得語言能力則是不恰當的。按照喬姆斯基的看法,語言結構大體上是以先天指定規則的形式固定下來的,孩子所做的不過是設定一些相對次要的“轉換開關”,這些開關的作用在于把他變成一個講英語而非講漢語的人。
喬姆斯基說,孩子不是一種通用學習者——用紐厄爾和西蒙的說法就是“通用問題解決器”——不是必須弄清楚什么是語言,然后學習如何進行語言活動。與此不同,孩子先天具有說語言、理解語言的設備,他們只需要排除一定的(非常有限的)可能性,并且采納一定的其他可能性。按照喬姆斯基的看法,這就為什么連“慢半拍的”孩子學起說話來也是毫不費力的。他們壓根不是真的在學習,頂多就像鳥類學習振翅那樣。語言,還有翅膀,只在注定會擁有它們的物種身上發育發展,而對于缺少相應的先天設備的物種來說,它們則是無從企及的東西。若干發展誘因會啟動語言習得過程,隨后若干環境條件會進行一些次要的修剪或塑形,孩子遇到的是哪門語言,母語就是什么。
這一主張受到了強烈抵制,但我們現在可以確定的是,真相離喬姆斯基較近,離他的反對者們則較遠。(詳見Jackendof,1993和Pinker,1994中為喬姆斯基立場所做的辯護。)為什么會有人抵制呢?我在網絡論壇上的評論——我在那里提出的是建設性的觀察,而不是反對意見——中指出,有一個抵制理由是完全合理的,即使這個理由只是一個合理的希望。先前,生物學家們抵制過“霍伊爾的瘋吼”,這種假說認為,生命并不始于地球,而是始于別處,然后遷移到了地球;與此相似,面對喬姆斯基的挑戰,參與抵制的心理學家們拿出了一個溫和的解釋:假如喬姆斯基是正確的,那只會讓關于語言和語言習得現象的考察變得難上加難。我們的工作不再是發現近在眼前的、個體兒童的學習過程,這是個我們能夠加以研究和操控的過程;我們將不得不“把擔子甩給生物學”,希望生物學家可以解釋我們這個物種是如何“習得”與生俱來的語言能力的。這是一個更難駕馭的研究項目。依照霍伊爾的假說,人們可以想象:
有些論述會限定變異和選擇的最大速率,進而表明并沒有足夠的時間讓整個過程都發生在地球上。
喬姆斯基的論述與此類似,他的出發點是刺激因素和語言習得速度的不足;他的這些論述旨在表明,嬰兒身上必定有著大量的天賦設計,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這種成熟能力的快速發展。有一種假設可以帶給我們些許安慰,那就是我們有朝一日或許能夠通過對神經系統的直接檢查,來確認這些先天結構的存在(如同發現了我們那些地外祖先的化石)。但這樣我們就必須接受一個令人灰心的結論:學習理論(這里是指它的最一般形式,即嘗試解釋從全然無知到知識的轉變過程)有一個大到出乎我們意料的部分并不屬于心理學的領域,而是最有可能屬于演化生物學的領域。(Dennett,1980)
令我驚訝的是,喬姆斯基沒有看出我這篇評論的用意。雖然他本人已經對什么會讓心理學“有趣”這件事有所反思,但他沒有注意到的是,當心理學家發現自己可能會把擔子甩給生物學的時候,他們可能會因為某件事而“灰心”。多年以后,我終于認識到,他之所以沒明白我的用意,是因為盡管他堅持認為“語言器官”是先天的,但這對他來說并不意味著“語言器官”是自然選擇的產物!或者說,這至少不意味著可以準許生物學家們挑起這個擔子,進而分析我們祖先所處的環境怎樣在無比漫長的時間里使語言器官的設計成形。喬姆斯基認為,語言器官不是一個適應現象,而是……一個奧秘,或者說是一個有前途的怪胎。有朝一日,闡明這樣一個東西的或許會是物理學,但不會是生物學。
在某個久遠的時期可能發生了一次突變,產生出一種離散的無限性,個中原因也許跟細胞生物學有關,能夠對此加以解釋的物理機制屬性我們目前還不知道……它演化發展的其他方面很可能再一次反映了某些物理法則的運作,而這些法則正是適用于有一定復雜性的大腦的那些法則。(Chomsky,1988,p.170)
這怎么可能呢?許多語言學家和生物學家都處理過語言演化的難題,他們所使用的正是在其他演化謎題上行之有效的方法,并且得出了結果,或者至少得出了貌似結果的東西。例如,在光譜上最具經驗性的一端,神經解剖學家和心理語言學家的研究表明,我們大腦的一些特征是我們現存最近親緣動物的大腦所缺乏的,這些特征在語言感知和語言生產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關于在過去600萬年左右的時間里,我們的支系什么時候、按什么順序、出于什么原因獲得了這些特性,人們眾說紛紜;但這些分歧是能在進一步的研究中加以檢驗的,檢驗這些分歧就跟處理——比如說——關于始祖鳥是否會飛的分歧差不多。在純理論的戰線上,要是我們放開眼界,就會看到已經有人推導出了一般交流系統的演化條件(例如,Krebs and Dawkins,1984;Zahavi,1987),人們正在用模擬模型和經驗試驗來探索這些條件所蘊含的意義。
在第7章中,我們看到了一些見解獨到的猜測和模型,它們要處理的難題是生命如何憑借自舉的方式使自己開始存在,而關于語言的產生所必定經歷的過程,也有大量與此類似的機智想法。毫無疑問,語言的起源問題在理論上比生命的起源問題要簡單得多;我們可以用來構建答案的、不那么原始的材料可謂類目繁多。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確認一些相關細節,但要是真能確認,那這就算不得什么奧秘了,充其量只是一點點無可補救的無知而已。某些分外節制的科學家可能舍不得把時間和精力花在這種迂遠的演繹推斷活動上,但這似乎并不是喬姆斯基的作風。他并不是對這項工作成功的可能性持保留意見,而是對這項工作的論點本身持保留意見。
把[先天語言結構的]這種發展歸因于“自然選擇”是萬無一失的,只要我們認識到這句論斷并無根據,認識到它不過是在表達一個信念,即存在某種對這些現象的自然主義解釋。(Chomsky,1972,p.97)
其實早就有跡象表明,喬姆斯基對達爾文主義抱有一種不可知論的——乃至是敵對的——態度,但我們中有許多人發現這些跡象并不容易闡釋清楚。對一些人來說,他看上去就是個“隱蔽的創造論者”,但這似乎不太可信,特別是因為他得到過斯蒂芬·杰·古爾德的認可。還記得語言學家杰·凱澤(第10章第2節)借助古爾德的術語“拱肩”來描述語言是如何形成的嗎?凱澤大概是從他的同事喬姆斯基那里獲得這個術語的,喬姆斯基又是從古爾德那里獲得的;古爾德熱切地贊同喬姆斯基的觀點,即語言其實并非演化而來,而是突然到來的,是一種無法解釋的天賦,頂多是人類大腦增大帶來的副產品。
是的,大腦在自然選擇下變大了。但正是大腦尺寸的增加,以及與之相伴的神經密度和神經連接度,讓人類大腦可以施展一系列跟腦體積增大的初始原因完全無關的、范圍甚廣的功能。不是由于大腦變大了,所以我們才能夠閱讀、書寫、計算,或劃分季節——可我們知道,人類文化有賴于這類技能……語言的普遍特性與自然界中的任何其他事物是如此不同,它們的結構是如此奇特,這似乎表明它們的起源是大腦能力增強的一個順帶結果,而不是跟祖先的嘟囔聲和手勢有著延續關系的一次簡單進步。(這個關于語言的論點絕非我的原創,不過我完全贊同它;以上推論思路直接遵循了諾姆·喬姆斯基的普遍語法理論,是從演化角度對他理論的解讀。)(Gould,1989b,p.14)
古爾德強調,大腦成長的最初原因可能并不是對語言的選擇(甚至不是對更高智能的選擇),人類語言的發生發展可能并不是“跟祖先的嘟囔聲和手勢有著延續關系的一次簡單進步”,但這些猜測(出于論述需要,我們可以姑且承認他的這些猜測)并不能說明語言器官不是一種適應現象。就算我們承認它是一種擴展適應,但擴展適應也是適應。就算人科大腦的顯著成長在古爾德和凱澤所希望的隨便什么意義上是一種“拱肩”,語言器官也仍然會像鳥類的翅膀一樣是一種適應現象!不論在設計空間中把我們的祖先硬生生推向右邊的那次間斷來得有多突然,這仍是自然選擇壓力下一個漸進的設計發展過程——除非這確實是一個奇跡,一個有前途的怪胎。
簡而言之,古爾德把喬姆斯基的普遍語法理論譽為一座堡壘,說它抵御了關于語言的適應論解釋,而喬姆斯基也認可古爾德的反適應論,拿它當作權威借口來拒絕一項明擺著的責任,即為普遍語法的先天存在尋求演化解釋;盡管如此,這兩位權威也只是在一道深淵上彼此支撐罷了。
1989年12月,麻省理工學院的心理語言學家斯蒂芬·平克和他的研究生保羅·布盧姆在麻省理工學院認知科學研討會(the Cognitive Science Colloquium at MIT)上宣讀了一篇題為《自然語言和自然選擇》的論文。這篇后來作為標靶文章刊登在《行為與腦科學》上的論文,是他們下的一封戰書:
很多人認為,人類語言能力的演化不能用達爾文式的自然選擇來解釋。喬姆斯基和古爾德就曾指出,語言的演化可能是一種副產品,產生于對其他能力的選擇,它還可能是迄今未知的成長法則和形式法則的結果……我們的結論是,完全有理由相信,語法的特化演化是按照一種常規的新達爾文式過程進行的。(Pinker and Bloom,1990,p.707)
“在某種意義上,”平克和布盧姆說,“我們的目標無聊透頂。我們只是要論證,語言與回聲定位、立體視覺之類的其他復雜能力沒什么不同,而解釋這樣一類能力之起源的唯一方法,就是自然選擇理論。”(Pinker and Bloom,1990,p.708)他們得出這個“無聊透頂”的結論,靠的是耐心評估針對各方面現象的不同分析,這些分析無可置疑——驚不驚喜?意不意外?——并表明“語言器官”的許多最為有趣的屬性,肯定是由演化產生的適應現象,而這正是新達爾文派所期望的。
不過,麻省理工學院的聽眾反應可一點都不無聊。根據事先安排,喬姆斯基和古爾德要做出回應,所以現場來者甚眾,大家擠得只能站著。名聲在外的認知科學家們,在那個場合沒羞沒臊地表達出對于演化的高度敵意與無知,令我大受震撼。(事實上,正是對那次會議的反思才讓我下定決心:必須馬上寫這本書,不能再拖了。)據我所知,雖然那次會議沒有留下記錄(網絡論壇上的評論涵蓋了這次會議提出的一些主題),但如果你想回味一下當時的情況,可以品一品平克列出的(私下交流)最令人叫絕的十大反對意見,這些反對意見都是自論文草稿開始流傳以來他和布盧姆對付過的。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會議上,這些反對意見大都以不同的版本出現過:
(1)色覺沒有任何功能——我們可以靠強度差異來區分紅蘋果和綠蘋果。
(2)語言根本不是為了交流而設計的:它不像手表,它像一個中間有根棍子的魯布·戈德堡裝置,你可以把它當日晷用。
(3)關于語言具有功能性的任何論證,都可以拿來論證“在沙子上寫字”具有功能性,而且論證的可信度和力度保持不變。
(4)要解釋細胞的結構,就得靠物理學,而不是靠演化論。
(5)擁有眼睛和擁有質量這兩件事都需要同一類型的解釋,因為就像眼睛會讓你看得見一樣,質量會防止你飄浮至太空。
(6)關于昆蟲翅膀的那檔子事兒不是已經把達爾文給駁倒了嗎?
(7)語言不可能有用——它引發過戰爭。
(8)自然選擇是無關緊要的,因為我們現在有混沌理論。
(9)語言不可能是經由對于交流的選擇壓力而演化出來的,因為我們在詢問他人感受的時候,可以并不真的想要知道他們的感受是什么。
(10)大家都同意,自然選擇對心靈的起源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它又無法解釋每個方面——那就沒什么好說的了。
古爾德和喬姆斯基對他們某些支持者的奇怪信念是否負有責任呢?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平克列出的條目多半都可以在古爾德的主張(特別是2號、6號和9號)和喬姆斯基的主張(特別是4號、5號和10號)中明確找到它們的先祖。那些抱有這些主張(還包括清單上的其他主張)的人,在表達它們的時候通常都會借助古爾德和喬姆斯基的權威(例如,參見Otero,1990)。正如平克和布盧姆所說(Pinker and Bloom,1990,p.708),“諾姆·喬姆斯基,世界上最偉大的語言學家,以及斯蒂芬·杰·古爾德,世界上最著名的演化理論家,這二位一再表示語言可能不是自然選擇的產物”。此外——兩條關鍵的狗還未吠出聲呢——我還沒見到古爾德或喬姆斯基去嘗試糾正激戰中冒出來的這些瘋吼。(如我們所見,這是每個人都會有的弱點;令我感到遺憾的是,社會生物學家們的受困心態讓他們忽略了——至少是使得他們疏于去糾正——他們陣營中某些成員那為數不少且糟糕透頂的推論。)
作為達爾文最熱情的支持者之一,赫伯特·斯賓塞是“適者生存”這句話的創造者,是達爾文某些最佳思想的重要澄清者,但同時也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之父。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一種對達爾文式思維的可憎誤用,它捍衛的是從冷酷無情到十惡不赦的一系列政治學說。斯賓塞誤用了達爾文的觀點,達爾文本人對此是否負有責任呢?人們莫衷一是。就我而言,我雖能諒解達爾文沒有像真正的英雄那樣公開責備自己的擁護者,不過還是遺憾于他私下沒能更積極地對其加以勸阻或糾正。
古爾德和喬姆斯基都踴躍支持一個觀點:對于知識分子工作成果的運用和可能的錯誤運用,知識分子本人是負有責任的。所以,當發現自己被這些無稽之談引以為據的時候,可以想見他們至少會有些尷尬,因為他們自己并不抱有這些觀點。(指望他們會感激我替他們做了這些臟活兒,也許是想太多了。)
原標題:《人類語言能力的自然演化:喬姆斯基對陣達爾文|《達爾文的危險思想》》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