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東浩紀:庵野秀明,如何終結了1980年代的日本動畫?
本文經作者授權,選自東浩紀:《郵便的不安β:東浩紀檔案1》,河出書房新社(河出文庫),2011年。文章首刊于《ユリイカ》1996年第9期,青土社。后分別收錄于《郵便的不安》,朝日新聞社,1999年(譯文使用的版本);《郵便的不安#》,朝日新聞社(朝日文庫),2002年。
日本,沒有動畫批評。既不存在動畫批評家,也不存在批評的空間。這一缺失是由于與動畫相關的信息流被分割成了兩部分:一方面,存在著發行量很大的專業動畫雜志。盡管它們作為信息源很有價值,但主要是面向初高中生的以視覺為導向的節目介紹雜志,版面結構也十分明顯地反映著出版社的意圖(例如《Animage》雜志一貫傾向于支持德間書店參與制作的吉卜力工作室的作品)。這類雜志不可能進行與作品保持距離的分析,而且讀者對此也不抱期待。另一方面,還存在通過聲優擔任主持人的廣播節目、電腦通信論壇、同人志、科幻作品與手辦的專門雜志等進行碎片化的信息交換的交流渠道,以及追逐這一渠道的二三十歲的動畫粉絲。這些粉絲具有一定的評估眼力,從他們那里獲得的信息往往很令人感興趣。但是,“內行人都知道”這一渠道既非常封閉(例如,《科幻雜志》1996年5月號的水玉瑩之丞專欄變成了對同年4月13日從林原惠美的廣播節目里傳出的庵野秀明的發言的無聲的反駁,諸如此類……)、同時也不允許對作品進行批評,而且一般大眾往往也并不知道這一渠道的存在。
這一雙重的缺失反映了當下動畫的整體狀況。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日本的動畫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持續地兩極分化,一極是向兒童類的低質量的電視動畫發展,另一極則朝迎合一部分動畫發燒友的高質量的原創光盤動畫(Original Video Animation,OVA)進展。眾所周知,在80年代前半期,還未出現嚴格區分“大眾動畫”與“御宅動畫”的趨勢。例如,當時的《福星小子》(うる星やつら,1981-1986年),這部由押井守擔任首席導演的系列電視動畫的前期(1984年4月以前)內容,與(高橋留美子的)原作漫畫的風格相輔相成,是一部具有濃厚實驗性質與瘋狂吸粉趨勢的特殊的作品。但同時,這部動畫也在大眾層面獲得了廣泛的人氣。可以說該作是一部完美融入了“御宅”要素的大眾作品,并且其高水平的質量也完全得益于其中加入了“御宅”要素。80年代后半期以來,這一狀況急劇改變。此前在動畫文化與鄰近文藝類型(主要是包含科幻在內的文學、漫畫、電影、一部分現代思想……)之間的開放的信息與想象力——例如科幻大會的功能所象征的——通道突然開始閉塞。一方面,引入御宅要素,只能愉悅特定的受眾;另一方面,大眾化的流通渠道也不接受御宅要素了。后面將會談到,《王立宇宙軍:歐尼亞米斯之翼》(オネアミスの翼——王立宇宙軍,1987年)公映失敗就可被視為這一變化的代表。文化狀況的整體變動(新學院派的終焉等)及其連動的結果,就是以1987/1988年為界的電視動畫質量下降(上映量也減少),以及作為這種狀況的補充的原創光盤動畫開始流行。低品質的大眾/高品質的御宅之間的分割在此時出現,日本動畫的發展從此陷入停滯期[*]。具有御宅傾向(無論元虛構的實驗性,還是先鋒想象力)的動畫作品也不再在開放的渠道里流通了。
一般而言,“御宅族”的起源常被追溯至80年代初。不過這種說法其實存在謬誤。例如,這一時期里并不存在御宅族式的自閉(當然也有單純自閉的人)。并且當時的文化狀況成功地將許多在現在看來只能被稱為御宅族的作家暴露在了開放的流通渠道中。代表人物就是吾妻日出夫(吾妻ひでお)。吾妻被認為是“蘿莉控漫畫”“無厘頭漫畫”的開創者,這位在80年代中期幾乎封筆(現在又復出了)的漫畫家,常作為“最御宅族式”人物而成為業界傳奇。但即使是他,也不能被形容為御宅族式的自閉。吾妻在主要雜志上有多部連載作品,并且通過將《妙趣小飛仙》(ななこSOS,1982-1983年)改編為電視動畫而大獲成功,另一方面,他也在小眾雜志上發表《無厘頭日記》(1978-1979年),換言之,吾妻是在極為開放的流通渠道中展開工作的。將他的活動視為自閉的“御宅族式活動”,是80年代后半期以來的意識形態。這屬于事后諸葛亮式地捏造御宅族。[1]同樣的情形,也適用于其他許多的作家?作品,以及所有動畫。例如,80年代前半期的動畫文化常被認為是“御宅族式的事物”的典型起源。這一譜系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當時的動畫文化里的確凝結了后來被稱為御宅族式的要素。然而更重要的是,當時的動畫行業及粉絲群體橫跨了由無數的“間隙商品”(押井守)[2]所形成的交流渠道這一事實。大眾(非御宅族)與御宅族之間的對立只有在這一交流狀況被遺忘后才會出現。

《新世紀福音戰士》劇照。
去年(1995年)登場的動畫作品《新世紀福音戰士》(新世紀エヴァンゲリオン)動搖了大眾與御宅族之間的界限,從內部瓦解了動畫自80年代后半期持續至今的閉塞狀況。這是因為這部作品不是單純的感想或信息,而是旨在喚起人們對動畫這一文藝類型進行批評。
[*]至于宮崎駿。這位動畫作家(現在應稱為動畫導演)在90年代前半期始終是主流,最新的作品無論在票房還是文藝批評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乍眼一看,他好像不符合我們剛才的討論。實際上——即便宮崎確實是離那個閉塞空間最遠的作家——他也無法擺脫這條分界線。例如,1988年在院線上映的《龍貓》(となりのトトロ),被認為是壓抑了之前宮崎作品中的御宅族元素才得以成立的作品。本來支撐《魯邦三世:卡里奧斯特羅之城》(ルパン三世?カリオストロの城,1979年)的重要元素就是女主人公所具有的蘿莉控型的魅力(宮崎在當時對此已有自覺[3]),即使是《風之谷》(風の谷のナウシカ,1984年)與《天空之城》(天空の城ラピュタ,1986年),除了美少女主人公的設定外,還追加了神話-科幻的世界觀,以及獨特的機甲設定等,這些元素都可被認為是喚起御宅族興趣的精心安排。另一方面,《龍貓》里既未出現美少女,也未出現機甲。宮崎在這部作品里的意圖是,將御宅族的想象力從他的物語世界里放逐出去。[4]最后該作品被選為《電影旬報》里的最佳日本電影,從側面反映出動畫與御宅族的社會位置。
1
先介紹一下《新世紀福音戰士》(后文簡稱《福音戰士》)的基本情況吧。這部作品于1995年10月6日至1996年3月27日的每周三18:30-19:00在東京電視臺系(五局網絡)播放。該片是共有26集的系列電視動畫,由“GAINAX”進行企劃、創作、制作,核心成員庵野秀明擔任系列總導演。它沒有所謂的漫畫原著,是由GAINAX內的團體發起企劃、原創的。庵野高度參與了該片所有的故事世界設定、角色設計、腳本制作、演出[5],因此這部作品作為電視動畫具有史無前例的作家性,以及統一的風格。《福音戰士》是一部相當熱門的作品,在動畫雜志的問卷調查中具有超高的人氣,即使是在播放完結后的現在也話題不斷。特別是(正如文末詳述的)由于最后兩集里出現了在通常的電視動畫里無法想象的內容,以大塚英志在《讀賣新聞》上的評論(1996年5月20日)為首,掀起了對該片毀譽參半的論爭。該片的最后兩集將會在明年(1997年)2月預定發售的LD/VT版里被全部重新制作,明年夏天也會制作、發售全新原創故事的電影。總之這是一部至今還未完結的作品。
《Newtype》雜志1996年6月號評價這部作品是繼《機動戰士高達》(1979-1980年)以來的“熱潮”。雖然刊行這部雜志的角川書店參與了《福音戰士》的制作,令人無法不假思索地相信它對《福音戰士》的評價,不過,現在這部作品被80年代中后期以來消失了很久的渠道所接受,這確是事實。《福音戰士》一方面贏得了動畫粉絲之外的人群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成功地吸引了一些非常狂熱的粉絲。從現代思想御宅族、軍事宅到美少女動畫的粉絲,這部作品的粉絲群體的跨度堪稱十分龐大。涵蓋的年齡層也十分廣泛,由于播映時段適當,《福音戰士》也擁有不少小學生觀眾,以及很多被稱為《宇宙戰艦大和號》《機動戰士高達》世代的30歲以上的粉絲。總之,庵野在這部作品里徹底打破了前述大眾與御宅族的界限。可以認為,《福音戰士》出人意料地喚回了最近十年遠離了動畫作品的“曾經的粉絲”。這些粉絲應是從這部作品里感受到了與80年代中前期的作品相同的風格。
下面簡單介紹一下動畫內容吧。故事的基本輪廓就像無厘頭小說一般,總是頻繁出現神秘的敵人,人們必須用神秘的機器將其擊退。只有那些被挑選出的14歲的孩童才能操作這些機器,而且除了他們之外別無選擇。他/她們不容分說地突然卷入了堵上生死的戰斗。盡管動畫在整體上被賦予了“近未來巨大的機器人科幻”這一輪廓,但庵野只是將其當作制作動畫電視的借口。實際上,在播放之初,該作品的推進就具有明確的兩面性。一方面,劇本講述的是賭上人類的存續與入侵的敵人戰斗,另一方面,它又對全都具有“自閉癥氣息”性格設定的主要角色之間的關系及其糾結的心理進行了十分細膩的描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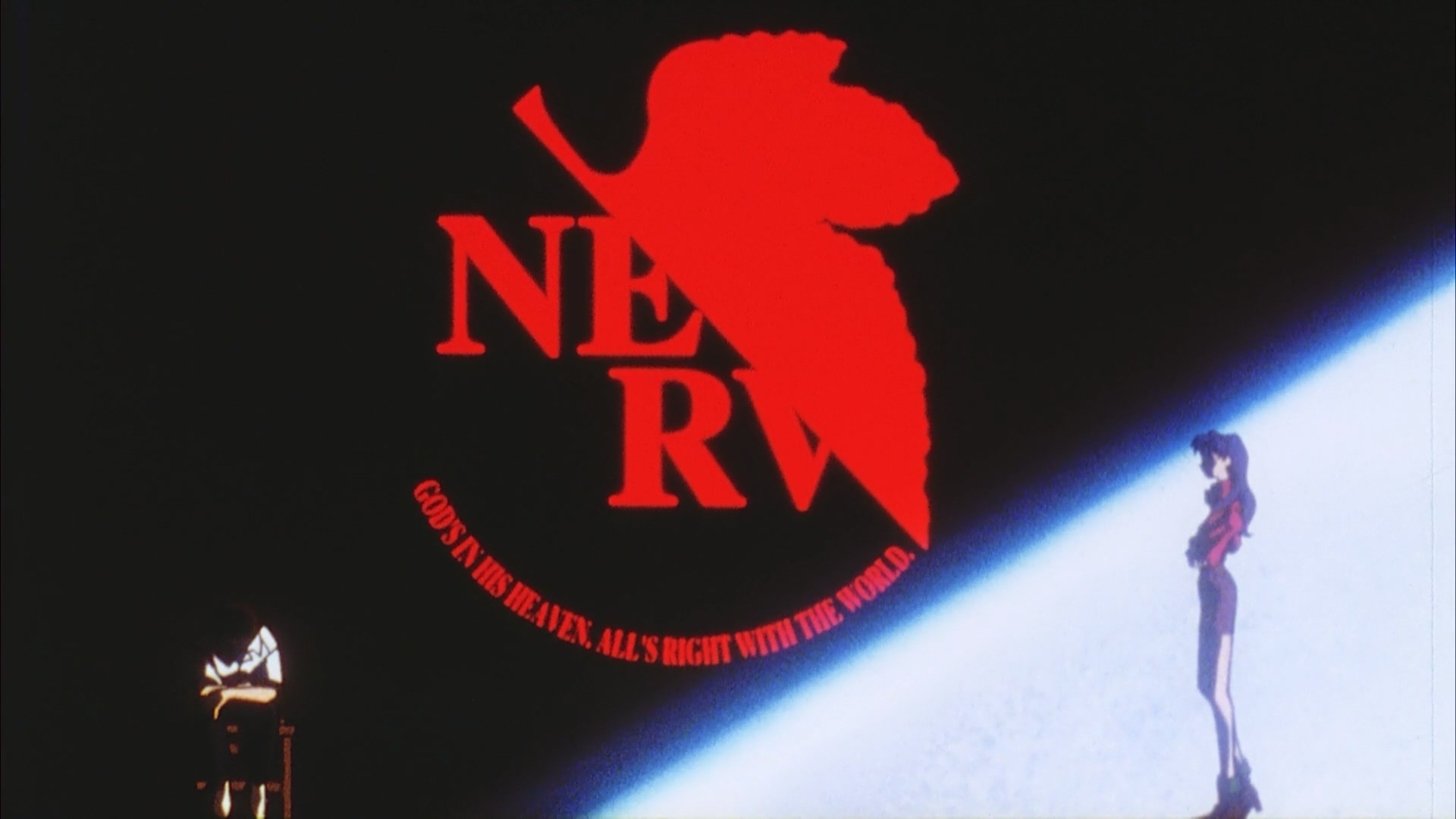
《新世紀福音戰士》劇照。
故事發生在2015年富士山麓的第三東京市。世界設定是,由于人類在2000年遭受了被稱為“第二次沖擊”的災難而失去了一半人口。被稱為“使徒”(英文名是angel,即天使)的存在斷斷續續地對第三東京市發起攻擊。“使徒”中包括巨型生物、浮游的巨大金字塔、電腦病毒以及發光的圓環等存在,但它們的真實身份及攻擊意圖仍然是個謎。已知唯一能對抗使徒攻擊的事物是巨人型生化兵器“福音戰士”(通稱Eva)。福音戰士是超越人類科技的存在,其由來尚無從知曉。一共有三架福音戰士機體,14歲的少男少女(碇真嗣、綾波麗、明日香)分別被選為它們的專屬駕駛員。不過,幾乎直到最后,作品都未交代選擇的標準是什么,因此主人公碇真嗣常對自身的處境產生排斥感。故事以這三個孩子以及碇真嗣的監護人、同時也是戰斗的負責人、29歲的女子葛城美里四人為中心展開。這四人都背負著各自的創傷,不擅于與其他人交流,對于他們而言,“為什么要與使徒戰斗”“為什么要駕駛福音戰士”等疑問,與其說是為了人類,不如說是他們自身內心的問題。
在該系列動畫的前半部分,作品基本上是作為一部制作精良的科幻動畫展開。每一集的結構都很簡單,大致是講述使徒入侵以及在擊退它們的過程中角色之間發生的故事的正統動畫。此時還有許多滑稽的場面以及電視動畫特有的變形表達,也沒有出現“打臉”觀眾的情況。但從“第拾六集”(此處沿用作品的舊字體標識)開始,劇情突然變得慘烈,作品逐漸變成將安逸的退路予以封閉的嚴肅故事。這時的演出效果、作畫、動畫、音響等變得更加細致,動畫的整體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超脫了一般的電視動畫。由于該系列動畫后半部分的情節比較復雜,很難進行簡單的概括,這里只能整理出一些碎片化的情況。首先可以大致明確的是,福音戰士實際上是被投入了每位駕駛員的母親的“靈魂”而制造出來的使徒。碇真嗣們是在母親的胎內進行著戰斗。在“第拾八集”里,碇真嗣的福音戰士背離他的意志,在其眼前將好友弄殘。“第貳拾貳集”里,明日香被使徒“精神污染”,并在被揭出幼年時遭受的創傷后變成了廢人。“第貳拾叁集”里,綾波麗為了保護碇真嗣而自爆,同時我們也知道了她其實是碇真嗣母親的不完美的克隆體。在接下來的“第貳拾四集”里,變得孤獨的碇真嗣與某個少年結成了疑似同性戀的關系,但這位少年被判別出就是使徒,最后也被殺死。——總之,這時的情節里充滿了死亡與性的意味,角色之間的情感關系復雜地交織起來,緊張感十足。福音戰士、使徒的真實身份以及碇真嗣的父親(被設定為對使徒特務機關的最高司令)的過去等故事里的謎題急劇增加,整個作品世界開始急速地顯現出《雙峰鎮》(ツイン?ビークス)一般的迷宮性。每一場景的結構與編導也開始具有魅力(例如,伴隨著穿透烏云的一道光線以及響起的《哈利路亞》的曲子,明日香開始受到精神污染的一系列場景)。正是此時的劇集讓該作品贏得了許多動畫粉絲群體之外的支持者。
從《福音戰士》的故事魅力以及影像的質量的角度來說,人們對這部作品的意見是一致的,即它至少是自大友克洋的《阿基拉》(アキラ,1988年)以來又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未來它應該會被更廣泛地評價為日本動畫里屈指可數的杰作。因此,針對這部作品以及作品本身的世界有很多值得探討的以及有必要討論的地方。但我不想就此展開討論,我想討論的也不是《福音戰士》本身的魅力,而是它之誕生的意義。
2
庵野與GAINAX在創作這部作品時進行了十分嚴謹與細致的設定。他們幾乎將80年代動畫里所有最優秀的元素融入了《福音戰士》。讓我們整理一下這些要素吧。首先,他們在作品中:①采用宮崎駿的世界觀(災難后的世界、沒落的人類、巨神兵、天使)作為作品世界的大致框架。②以神話(圣經舊約、諾斯替主義、卡巴拉)為基礎架構故事,主人公(與福音戰士[母親]聯手)與父親之間俄狄浦斯式的糾葛、類比人類與使徒(即天使)的斗爭并相應地勾勒主線故事。③另一方面,將時代設定在近未來,出現了大友克洋式的機件(用神經系統接口操縱的巨大生化機器人、基因操作、人工智能)。④加入了巨型機器人動畫的戰斗場景,以及對軍事系的機甲的細致描寫。⑤主人公以《機動戰士高達》里的阿姆羅(アムロ)為原型,不過又將其設定為柔弱、內向且自閉的90年代少年。⑥順應了最近的心理學、哲學熱潮,與制作重視內心世界的影像作品的發展方向保持一致。⑦理所當然地設定了各種類型的美少女、美少年角色(特別是在第貳拾四集里出場的美少年,很明顯是沖著某個特定的同人志市場)。⑧一開始不作明確的世界設定,給粉絲帶去了很多推理小說式的樂趣。⑨在引人注目的電視版最后兩集里,庵野甚至在作品中加入了押井守式的元虛構性。⑩除此之外,這部作品的制作還在細節(福音戰士駕駛席的設計、從概念到啤酒商標)上徹底地引用、參照過去的小說、漫畫、動畫、電影、音樂作品群。在其龐大的參考名單上包括了從考德維納·史密斯(Cordwainer Smith)、菲利普·K·迪克(Philip Kindred Dick)、市川崑、詹姆斯·卡梅隆(James Francis Cameron)到村上龍、神林長平、成田美名子、大槻賢二(大槻ケンヂ)等80年代作家的名字。毋庸贅言,大部分20歲以上的粉絲自然十分喜歡這些設計。
總之,《新世紀福音戰士》在某種意義上就是80年代日本動畫的成熟形態。那么,讓我們由此處開始討論吧。
當(1996年2月)《福音戰士》還在日本的電視臺播放時,美國一個在線?動畫雜志(http://www.jurai.net:80/amplus/)就刊載了包含長文介紹與庵野年譜的正式的《福音戰士》專輯。專輯的存在本身不值得驚訝。雖然作品還未在美國公開,但“動畫”(非被稱為日本動畫[Japanimation],而是直接叫做動畫[anime])的全球化進展卻超出了預期。在日本放映的電視動畫通過草根網絡幾乎同時受到了外國粉絲的關注。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該專輯在某些方面的分析已比日本的動畫雜志更優秀。
一般而言,日本對動畫的討論,傾向于只是關心作品世界,而忽視作家性以及作品本身的批評性。總之,只是討論——在某種意義上是否正確地理解了——明日香對碇真嗣“有意思”嗎、福音戰士之謎是什么,等等。盡管作家所傳遞的信息也會受到追問,但那不過是以簡單的形式進行著。例如,《機動警察劇場版2》(機動警察パトレイバー2,1993年)(在內容上)的政治信息雖被觀眾領會,但這部作品的作畫(在形式上)所展現出的對《福星小子》以來押井守所抱有的“動畫性”的訣別,卻未引起關注。這種貧乏是因為,人們沒有批評性地意識到也存在“動畫”這樣的文藝類型。但是在日本之外,70年代以后的動畫在總體上可以說發展成了一種獨立的影像類型。因此,在作家與類型的相互作用方面,國外的文章有時甚至比日語的媒體更加敏感。
這部引起關注的專輯注意到庵野與 GAINAX在過去的作品皆是“終極機器人、美少女動畫”主題,并指出在《福音戰士》里可以發現一種雙重性,即該作品一方面具有超御宅族性(該專輯使用了super otaku這一有趣的詞匯),另一方面,對此又有深刻的自我懷疑。這一分析是正確的。《福音戰士》的確如實地表現了庵野對動畫這一文藝類型的曖昧態度。該作品可謂80年代日本動畫的成熟形態。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實際上正是由于這部作品放棄了80年代動畫所依憑的各種“慣用伎倆”,它才變得圓滿的。
80年代,庵野(在他20歲的時候)作為GAINAX的核心成員,一直涉足于動畫御宅文化味最“濃厚”的領域。他在這方面與之前世代的宮崎駿及押井守有著很大的不同。GAINAX的前身是1981年為了制作大阪科幻大會(通稱DAICON)的開場?動畫而聚集起來的年輕動畫制作人集團(“DAICON FILM”)。當時還是學生的庵野正是這一集團的創立者之一。DAICON FILM制作的雖是業余愛好者的作品,卻贏得了很高的評價(作品在1983年獲得了《Animage》雜志的金獎),這些作品現在仍然作為傳說般的存在被不斷提起。另一方面,由于作品中出現了美少女以及滿是戲仿的手法,上述作品也被視為“‘御宅族’的邪典電影”[6]。總之,庵野是以這樣的經歷為起點才占據了御宅族文化的中心位置。他在之后還參與了《超時空要塞Macross》(超時空要塞マクロス,電視動畫系列,1982-1983年)與《風之谷》(1984年)的制作。
1984年,DAICON FILM與當時DAICON的制片人、后來的御宅族系評論家岡田斗司夫合作,啟動了長篇動畫的企劃。為此設立的機構便是GAINAX。該企劃由萬代(バンダイ)出資完成,于1987年在院線上映了《王立宇宙軍:歐尼亞米斯之翼》(導演?山賀博之)。庵野擔任作畫導演。這部作品擁有高質量的影像、故事,加之排山倒海般的宣傳,卻遭遇了票房失敗。何以如此?如前所述,此時大眾與御宅族之間的分界正急速推進。但這部以異世界為舞臺的科幻動畫里既沒有美少女也沒有機器人,該作品對于大眾與御宅族而言皆是定位不清的,完全被放在了分界線之上。質言之,GAINAX沒能正確認識到欲望回路的時代變遷。
遭遇失敗的GAINAX改變了策略。簡言之,即推行御宅族化(將目標對象限為御宅族)。此時GAINAX也開始布局進軍游戲軟件行業(其成果便是后來的美少女養成游戲《美少女夢工廠》,1991年)。同時,庵野成為了GAINAX動畫制作的核心人物。他導演的第一部作品《飛躍巔峰》(『トップをねらえ!』,OVA,全三卷,1988-1989年)為GAINAX的未來發展確立了方向。總之,在這部讓美少女與機器人同時登場,滿是引用與戲仿過去的動畫、科幻的作品里,幾乎已不存在故事了。這明顯是一部專以御宅族為對象的作品。為了吸引御宅族,GAINAX甚至在作品中創造了全新的色情技法(即“乳搖作畫”)。這部作品不僅取得了商業成功,還被好評為OVA“名作”。然而,此時的庵野對動畫的類型化期待(即只要畫美少女就能賣得好)以及寄托于此的動畫行業抱有強烈的危機感。例如,他早就在《飛躍巔峰》第三卷里嘗試進行巧妙的演出安排。在該作品里,華麗的音樂、大規模的戰斗場景、黑白?畫面縱橫比已與故事無關,它們反而是被用來強調滑稽感的。一面完全以經典的方式展開演出,另一面又對這一切一笑而過,這種諷刺或許就是當時的庵野對自己所置身的閉塞狀況的回應。
庵野導演的第二部作品《藍寶石之謎》(ふしぎの海のナディア,電視動畫系列,全39集,1989-1990年)給他帶來了更大的成功。這部在NHK電視臺放映的電視動畫大量使用了美少女主人公、科幻式的故事裝置以及戲仿手法,不僅深受御宅族喜愛,也是人氣很高的優秀“兒童動畫”(電影版與GAINAX無關)。此時,庵野是為數不多的被動漫粉絲承認為“作家”的人物之一。然而,他在完成《藍寶石之謎》之后離開了動畫制作業。雖然無從知曉詳細的原因,但其根本原因應是對動畫這一文藝類型及其粉絲群體懷有深切的失望吧。事實上,庵野在最近的采訪中也反復地強烈批判了封閉的動畫粉絲們。《藍寶石之謎》的成功似乎絲毫沒有改變動畫的現狀。
庵野在回顧《藍寶石之謎》以后的銷聲匿跡時說,“這四年就這樣處在崩壞狀態什么都沒做”“只是沒有死而已”。[7]《福音戰士》是他在長時間的銷聲匿跡之后的有意識的回歸之作。因此,這部作品在一開始就注定了會是對動畫的批判之作。“想打破那種‘作為文藝類型的’閉塞感[中略]在這種情況下,果然只能是電視動畫吧”[8]
動畫這種文藝類型,其內容(故事)與形式(作畫)是密不可分的。例如,如采用《櫻桃小丸子》(ちびまる子ちゃん)這樣的三等身角色,作品就不可能是美少女或者科幻動作片之類。反過來說,如今的動畫制作者也會根據故事內容反向決定如何作畫。現在只要是有一定閱片量的人,應該都可以從角色設定里想像出大部分作品的內容。眼睛和臉的大小比例、頭發顏色、手腳長短皆對故事有影響。這種必然引起粉絲分化的不自由狀態造成了80年代后半期以來動畫作品在整體上的閉塞狀態,這也是動畫作品朝向精致化發展后的結果。剛才我談到了押井守。他為了在《機動警察2》(バトレイバー2)里展開厚重的故事,不得不放棄由結城正美(ゆうきまさみ)與高田明美創造的支撐起《機動警察》電視動畫與OVA系列的“動畫繪風”式的角色作畫。這一選擇在某種意義上也體現了他的限度。采用連環畫風格的作畫,確實可以展開厚重的故事,但這也肯定只會得到特定的受眾,其結果便是上述的封閉性不會得到改善。
《福音戰士》的出現真正成為事件,就是從這里開始的。庵野干了什么呢?簡單說來,他創作了一部龐雜得驚人的作品,其中充斥著80年代動畫幾乎所有的“慣用伎倆”。在他之前,從未有人同時羅列這些要素。這是因為大家將使用了不同系列的“慣用伎倆”的作品分門別類了(例如,就像宮崎駿的動畫與《美少女戰士》不屬于同一類型),換言之,庵野從根本上缺乏謹慎性。在我看來,這一缺點是80年代前半期間隙產業(すき間産業)所具有的龐雜性的延伸。庵野不承認大眾與御宅族的分界線,故意攪亂了內容與形式的固定組合之間的分別共存。正因如此,《福音戰士》里才會塞滿許多矛盾的設定與要素。

《新世紀福音戰士》劇照。
例如,在《福音戰士》開頭處,沒有觀眾會覺得鈴原東治是重要角色,這是因為他操著一口關西腔,還總是穿著運動服。如此角色,一般是為了緩和故事世界的次要角色。這就是日本動畫的文法。然而庵野毫不留情地破壞了這一規則,鈴原在“第拾八集”里被碇真嗣的福音戰士弄斷了腿,從而成為故事里的關鍵角色。再如在樋口真嗣擔當CG制作的第八集與第九集里,碇真嗣與明日香的滑稽對話在作畫上與該動畫后半部分的氣氛是存在違和感的。而在第九集的最后,則出現了明日香的全息影像打罵碇真嗣的場景,但通常在這種允許變形的作品里并不會展開嚴肅的敘事。這部作品里出現了無數這種同類型的偏差。也就是說,庵野在這部作品里加入了動畫的所有“慣用伎倆”,以便破壞動畫這一類型在總體上的默契。這意味著,正是因為《福音戰士》拋棄了“慣用伎倆”才造成了上述狀況。
3
以執迷于引用、戲仿過往作品為形式的元類型實驗本就在封閉的“動畫界”比比皆是。《福音戰士》之所以出類拔萃,在于這部作品成功地設定了將表達方面的分歧反映在作品內容之上的故事結構。例如,在該系列動畫的前半部分,“學園喜劇”式的鈴原與明日香的存在反而增強了人們對“第拾八集”(福音戰士攻擊鈴原)以及第“貳拾貳集”(使徒侵入明日香)的印象。也就是說,在作品的元層級表達上才應有的分歧,直接支撐著對象層級里的內容。如果采用這種扭曲結構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元虛構,那么《福音戰士》就是非常優秀的元虛構吧。
本來可以直接分析《福音戰士》里的各個場景與情節,但為了接近這部作品所生成的奇妙的“感動”結構,上述迂回的討論是不可或缺的。《福音戰士》的魅力不在于故事本身。其實一切類型的作品里都不存在單純的故事內容,故事內容通常是由所使用媒體的物質性以及作品與所屬文藝類型在整體上的張力決定的。但這不意味著故事是無所謂的。首先須認識到,《福音戰士》故事在1995年以動畫為媒介出現時所具有的意義。其次須注意到,正是上述元層次的意味第一次指明了《福音戰士》作為故事的魅力。而圍繞動畫的諸多討論所欠缺的正是關于作品與文藝類型空間之間相互作用的認識。
——限于篇幅,最后引用一下庵野在《福音戰士》放映結束后接受的采訪吧。他講述了最后一集里(實際上在其他集目里也可看到的)“實驗性”的影像。
實際上,可以這么說。這應該也是可以辦到的,只是沒有被采納。在沒有使用賽璐珞原畫的部分,是故意原封不動地使用CG繪圖的。這不是來不來得及的問題,而是為了從賽璐珞動畫里解放出來。賽璐珞什么的只是符號而已喲。用馬克筆畫出明日香,再從畫里傳來宮村優子的聲音,這就已經夠了吧。拘泥于賽璐珞這件事本身就很討厭。但這不是說要另外走向CG。[中略][要求賽璐珞原畫的動畫粉絲]甚至走到了戀物癖的地步。[9]
那么庵野今后(就像過去的押井守一樣)會去拍真人電影嗎?既然明確表示不會走向CG,事情就不會那么簡單吧。“從賽璐珞動畫里解放出來”是指,把80年代的日本動畫變得精致,一方面,自某時期以來動畫這一文藝類型已從整體上變得閉塞,另一方面又通過這種方式讓它從諸多規范里獲得自由。在《福音戰士》這種故事里使用馬克筆作畫本就構成問題,人們首先必須改變這一狀況。實際上庵野在這方面做得十分出色。他的“自由”不僅在商業上大獲成功,而且影響了許多創作者。陷入精致與閉塞的惡性循環的80年代動畫,終于邁向終結,而且這種終結恐怕不只是動畫的問題。
補論——關于結尾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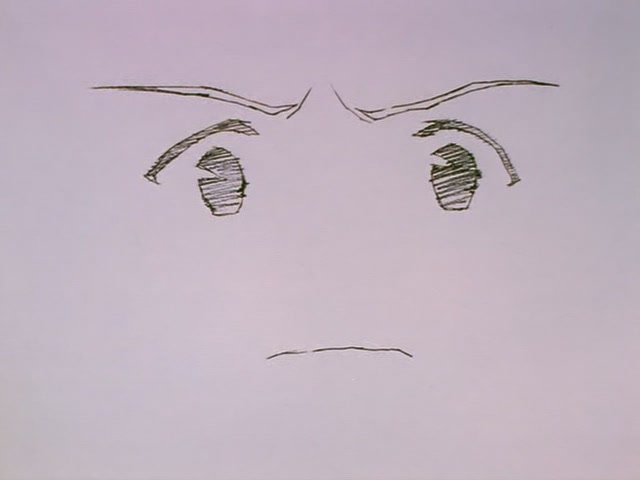
《新世紀福音戰士》劇照。
在最后兩集里,庵野突然放棄了作品里的故事進程,只以碇真嗣的獨白及內心世界描寫結束了《福音戰士》系列電視動畫。直至“第貳拾四集”還一直完美地構筑著的全部鋪墊,在第“貳拾伍集”的開始處就被不加解釋地無視與拋棄了。特別是在最后一集里另外插入的《福音戰士》世界場景——其中不存在福音戰士,碇真嗣們過上了幸福的學園生活——在把作品本身元虛構化的同時,也嘲笑了部分動畫粉絲的的欲望[10],構成了明確的類型批判。這樣的結束方式在動畫粉絲中間引起了相當大的騷動,甚至一段時間內的網絡上還橫行著對庵野的中傷與謾罵。
不過我認為,《福音戰士》的本質不在此處。不知道電視版的最后兩集還剩多少原來的粉絲(有傳聞說電視臺方面也對過于慘烈的初始劇本表達了不滿),加之有報道聲稱故事的結局將在LD/VT版上被重新制作,因此這種赤裸裸的元虛構戰略就不可被簡單地認為是庵野的意圖。的確,電視版的最后兩集直接在內容上反映了庵野的取向。但是我認為,即使沒有這兩集,《福音戰士》的雙重性在形式上也是顯而易見的,其批評性也不會受到絲毫的損傷。其實最后部分的問題,不就在于它反而遮蔽了這部作品本來的激進性嗎?
關于“洗腦”結局的問題(“恭喜天下的孩子們”),就另文再述吧。但有一點須注意,無論肯定還是否定《福音戰士》的結局,在我看來這皆是缺少“作家”觀點的不成熟的感想而已。應予追問的其實是,庵野何以如此作結?[11]其中有何奧妙以及特別的危機意識呢?這才是最后部分震驚我之處,而非結局本身。
注釋:
[1] “御宅族”這一用語并未在80年代的大眾媒體里流通。1980年發生宮崎勤之幼女連環謀殺事件后,它的存在與異常性才被社會認知。詳見《御宅族之書》(『おたくの本』、別冊『寶島』一〇四號、JICC出版、八九年)里收錄的中森明夫的文章。
[2] 押井守在回顧自己全部的電影時使用的語言。『攻殼機動隊/PERSONA——押井守の世界』、アニメージュ編集部?編、徳間書店、九六年、九六頁。
[3] 『魔女の宅急変?ロマンアルバム』、アニメージュ編集部?編、徳間書店、八九年、九〇頁。
[4] 在此意義上,《側耳傾聽》(耳をすませば)播出時,同時上映的時長只有幾分鐘的短篇《ON YOUR MARK》(1995年)的存在意義就可被理解了。即,從《龍貓》到《側耳傾聽》的各個作品所壓抑的前期宮崎元素——盡管在1994年完結的動畫版《風之谷》里繼續存在著——的回歸。然而有意思的是,這一于漢字橫飛的賽博都市里,從國家警察處奪走天使的黑客二人組的短篇,其大致情節及基本設定巧妙地與押井守的《攻殼機動隊》(1995年)保持著平行關系。換言之,宮崎事先不就在這里對押井進行著戲仿嗎?
[5] 例如,副導演鶴卷和哉也承認自己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沒有把握住這一系列動畫的整體方向。參見《新世紀福音戰士//Genesis 0:0 IN THE BEGINNING》視頻、King Record收錄的訪談。
[6] 淺羽通明「高度消費社會に浮遊する天使たち」(『オタクの本』所収)、二六八頁。其中提到的《愛國戰隊大日本》(愛國戦隊ダイニッポン)是DAICON FILM制作的作品。淺羽提到的名為“通用產品”(ゼネラル?プロダクツ)的制作集團,正確說來其實是以岡田斗司夫為首開辦的科幻產品專賣店的名稱。
[7] 漫畫版《新世紀福音戰士》第一卷(貞本義行+GAINAX,角川書店,1995年)庵野的后記,第172-173頁。
[8] 前述視頻『新世紀エヴァンゲリオン\Genesis 0:0 IN THE BEGINNING』里收錄的訪談。
[9] 『ニュータイプ』九六年六月號、角川書店、一四頁。
[10] 借用已有作品的角色來描寫自己的原創世界的短篇小說被稱之為“SS”(可能是sub story或side story的縮寫),有關的學園喜劇風SS在《福音戰士》還放映時就大量上市了。當然,它們都如實地反映著動畫粉絲的欲望。
[11] 本文提到了大塚英志在《讀賣新聞》上的評論,他認為《福音戰士》作為教養小說是失敗的,最后兩集可以被理解為典型的“逃避成熟”的御宅族式的自閉。然而在我看來,這純粹是一種誤讀。正如庵野在很多采訪中反復提及的,以及粉絲們在放映完結后的困惑所明確揭示的那樣,正是封閉的“御宅族”才最熱衷于從教養小說的角度尋求這部作品的結局。完美地描寫碇真嗣的成長故事,其結果就是賦予御宅族一個逃避現實的出口,即一個自律的幻想世界。事實上,這類成長故事在該作品的同人志與短篇故事中大量——實在是自閉性的——出現,這確實證明了此時動畫的扭曲。庵野對這一扭曲十分敏感。動畫粉絲群體所凝鑄的封閉領域已不允許作家進行直接的表達了。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