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晚清重臣翁同龢的人情往來:有些饋贈,堅決不能接受
在溫情脈脈的人情往來中,接受或辭謝他人的饋贈是兩種自然反應,這看似簡單,其實大有文章,其中奧秘處,有時非三言兩語所能概括。筆者選擇晚清重臣、“兩代帝師”(先后擔任同治、光緒的老師)翁同龢作為個案,不僅緣于他有一部記錄詳盡的日記,更主要是他長期位列顯要,是結納酬答的重要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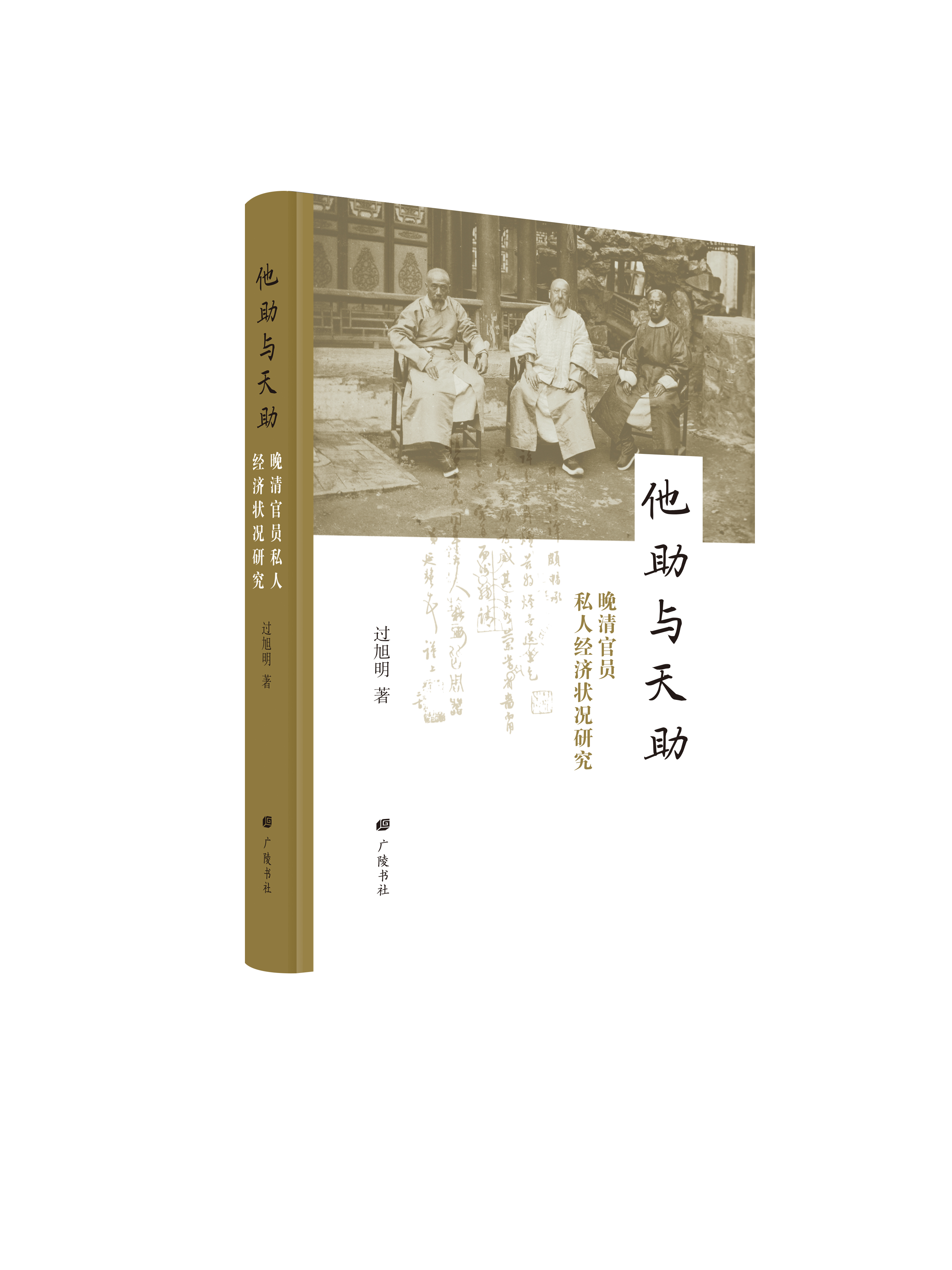
《他助與天助:晚清官員私人經濟狀況研究》,過旭明 著,廣陵書社2022版
翁同龢(1830—1904),應該算是晚清歷史上少年得意的典型。19歲應拔貢試第一,科試正案第一,在京做了小京官,27歲狀元及第,29歲授提督山西學政,30歲因足疾請求開缺得允,幾乎完成了很多讀書人一輩子追求的理想人生。
33歲那年,翁同龢作為山西鄉試正考官差旋回京,受命為詹事府右春坊右贊善,這不算是多大的官位,只有從六品,但這是翰林正途出身必經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開坊。翁同龢的恩遇不謂不重,登科不久外放學政,當時甚至都未散館,直至三年任滿后才回京參加散館考試,現在接著就開坊,要知道當時有的翰林幾十年都開不了坊。
同治元年(1862)七月初二,夏日清早頗為涼爽,雖然天氣陰欲雨下,但翁同龢早上五點多就已出門,六點已到詹事府就任。先補褂朝珠,拜謁文廟,然后正式拜印。時間尚早,翁同龢小坐片刻后又到文公祠拈香禱拜。衙門極小的,人也少,僅有一個書吏和六個皂隸。公事未問,下屬先賀喜老爺,急著討要賞錢,接著告稟日常支出:書吏辦折需要四兩銀子,皂隸等需要二十吊錢。翁同龢不答應,只愿意付二十八吊錢,可下屬也堅決不答應。這讓翁同龢有點難堪。
此前,翁同龢曾在刑部江西司當過小京官,也知道這些規矩,但真正讓自己面對這些開銷時,實在有點局促。由于翁家分家析產時間很晚,前期個人經濟責任和壓力不大,翁同龢第一次赴陜西做鄉試副主考,對地方饋贈的錢物并不在意,大多璧謝了事。當時,他剛剛登第不久,社會經驗不豐富,加上沒有家庭負擔,把潔身自好放在重要位置,辭謝各處的饋贈無疑是自然反應。
作為讀書人,誠心正己是重要的修身功課,《翁同龢日記》對辭謝贈銀、贈物記錄得特別詳細,或許就是出于這個原因。翁同龢在日記中有關私人財務的記錄,目前可以認為是不完整的,這只需將《翁同龢日記》與《那桐日記》對讀就能發現。翁同龢在戶部尚書任上是那桐的上司,同時也是那桐的老師,兩人交集長達十多年時間。兩人日記中關于對方的記錄非常多,那桐每逢端午、中秋都會給翁師送去節敬,但翁的日記中幾乎沒有記錄——這可能是因為類似的小額慣常性禮敬沒必要屑屑記錄。不過,翁同龢罷官離京前和鄉居期間,那桐先后兩次贈送了數額高達千金的現銀,翁同龢都記錄了,而且都沒有收受。
在他個人履歷中,同治五年(1866)是重要的人生節點。這一年,他從低級官員晉升為中級官員。在此之前,他負責全家的整體財務賬目,所以文字中充滿了缺錢的緊張感,
這在日記里體現得十分明顯:
今年歲事較忙,用項亦巨,凡百余金始了私款(同治三年除夕);
此節須用百金,亦靡甚矣(同治四年端午前二日);
此節幾用百金,費極矣(同治四年中秋前二日);
從人假得百金始得料理逋務,此數月來計三百金不敷用也(同治五年端午前日);
節賬粗了,款項益多,所謂由儉入奢易也(同治五年除夕前二日)。
翁同龢擔任底層官員時期,有人敬送贈銀,那是極為令人感動的事情。同治三年二月六日,王榕吉由直隸布政使調山西布政使,離京時送他別敬三十兩。翁感慨地說“蔭堂于余甚厚,亦可感嘆矣”,同時以路菜、京靴回贈,并在三月二十九日一早去送王榕吉啟程,四月十五日專門致信蔭堂函中稱“旄節入都,得近光霽”,可見他真的是內心充滿感激。
這年年底,同鄉繆萼聯送他三十兩炭敬,即使作為非常熟悉的鄉黨,他還以“荷包、補服、帽沿、京靴”回贈在河南當縣令的老鄉。這些贈銀的確幫助底層官員應付“不易居”的京城生活。有時,往往就是這幾十兩銀子會使受贈者終身難忘。六年后,繆萼聯的侄子來京應試,順便又帶來了繆萼聯的一百兩贈銀,但翁同龢沒收。此時,翁同龢的經濟情況已經足以應付生活,認為不該再收同鄉的辛苦錢了。
作為長期浸染于孔孟圣學的知識分子,面對饋贈時始終有著一種緊張感。這種緊張感來源于君子人格的約束,“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然而生活的重壓會讓人不得不妥協,盡管并沒什么惡劣的后果,但那些道德準則會不斷折磨心靈,隱秘而清晰,三省吾身時的些些羞愧足以透出人生的酸楚。
當翁同龢接受了馬新貽(做過安徽布政使、浙江巡撫、兩江總督)的多次贈銀后,他感嘆“可愧也”。這不僅僅是過意不去的愧疚,更是一種無奈的尷尬。事實上,當真缺少這些支持,局面會變得十分尷尬。
同治七年七月末,翁同龢回鄉葬親。這次既是安葬父兄,同時也是葬妻。船到蘇州,江蘇藩臺、臬臺帶領長洲、吳縣縣令前來行禮。翁同龢在蘇州等候岳丈湯修到來。因為這次是葬妻,岳家也要出面,也借此相聚。
出乎意料的是,到了家鄉居然沒有一個地方官員贈送賻金,這大大打亂了翁同龢的計劃。因為在原來的盤算中,在蘇州得到的奠儀不僅能支付一路上的開銷,而且回鄉分贈給親友的薄敬也有了著落,但蘇州地方官員可能認為翁心存是同治元年十一月去世的、翁同書是同治四年十月去世的,現在已無必要再致奠儀。這個意外使得翁同龢只能向久未見面的老丈人開口,先借了一百銀元。仔細算下來,覺得還是不夠,再借了一百元,這樣才得以順利回到常熟。
在人情世界里,炭敬、別敬、年敬、節敬諸如此類,都是表達感情的一種方式,而且是很累人的一種方式。很多外地官員害怕進京陛見,其原因就是太受累了。即使連曾國藩這樣的大員,對同治七年、九年兩次進京的花費,都感到竭盡所能、氣喘吁吁。但在接受方,對一些饋贈接受與辭卻往往也是難題,常出現“受其半”“受其二”的情形,表現了情誼深厚、不在其利的意思。
在這些人情交往中,對有些饋贈是堅決不接受的,這也是翁同龢的原則問題。
首先,是有所請求的饋贈不能接受。同治九年中秋前后,賀澍恩給翁同龢寫信并寄來了節敬四十兩銀子。賀澍恩是江西萍鄉人,道光年間進士,一直在山西地方做知縣、知州這樣的小官。同治元年,翁同龢典試山西,太原縣知縣賀澍恩為第四房同考官,兩人有了交集并在日后互通音問。同治四年,賀澍恩進京時,就曾送給翁同龢二十兩別敬,此次寄來節敬合乎情理,并不突兀。兩天后,賀澍恩的兒子賀培楨登門拜訪。翁同龢在與賀培楨的交流中,覺得他很功利俗氣,存在干請的可能,于是當夜就寫信璧還了節敬,原因就是“恐其有所干請也”。
翁同龢的確十分敏銳。事實上,當時作為拔貢生的賀培楨正在設法謀求地方實職,實現人生自立。同時,他弟弟賀培芬也在京城活動。這些動態,翁同龢完全有可能通過其他途徑了解到。經過與賀培楨的交談,翁同龢更確定了這個判斷,于是謝絕了這樣的饋贈。
不過,翁同龢這次看錯了人,賀培楨日后在任河北省永清知縣時,為官清廉,而且教育兒子賀國昌也很成功。民國期間,賀國昌任江西省省長。1916年袁世凱復辟稱帝,賀國昌堅決反對,被政府重金緝捕,不得不東渡日本。黎元洪再造共和、當選總統后,委任賀國昌擔任福建省省長,但賀國昌堅辭未就,閑居京城,潛心佛學,1919年病逝于北京,安葬在萍鄉三田嶺,也被后人稱為“國公嶺”。
翁同龢的這個原則,對關系親密的友人也同樣如此。張鵬翥是翁同龢的門人,同治四年進士,登科后歷任江西高安、興國、吉水、安福等縣知縣。光緒七年,他被人參劾落職,于是進京活動,送給老師的禮物是一百兩銀子贄敬和二匹葛布。翁同龢早已得知消息,沒有接受他的贄敬。當時,饋贈的重要原則之一是無功利性,雖說完全超越功利的人際關系并不存在,但有著明確目的的饋贈就近乎賄賂了。
其次,在交往中即使是饋銀,也要光明磊落。光緒七年初夏,新任臺灣道臺劉璈前來拜望翁同龢。劉璈(1829-1887)作為左宗棠幕府中極為能干的官員,在當時已經頗有名聲。他是湖南岳州人,字鳳翔,號泳山,別號蘭州,秀才出身,在咸豐初年抵御太平軍入湘時,在家鄉倡辦團練,先是受到湖南巡撫駱秉章的賞識,后來左宗棠在軍中對他倚重尤甚,因軍功授候補道,先后任臺州知府、江蘇候補道、蘭州道員,光緒七年被選調臺灣兵備道。時任山西巡撫的張之洞也曾向朝廷舉薦劉璈,認為他“才力沉雄,素以剿賊治匪得名,至于撫民課吏,尤能慈惠精嚴”。劉璈此次拜會不過是禮節性的拜望,按例贈送別敬,但翁同龢考慮到彼此并不熟識,所以沒有接受。
兩年后,劉璈讓兒子劉浤拜見翁同龢。劉浤當時是秀才,翁同龢稱他長得“美秀”,第一印象應該不錯。交談中,劉浤談到父親在臺灣不甚如意,受到上官的鉗制,并拿出稟稿相商。可年少不更事的劉浤此時拿出一封銀子作為贈禮,這讓翁同龢大為光火,“乃正辭責詰之”,覺得這樣偷偷摸摸的勾當,怎能在我這里出現,并認為“亦妄矣哉”!
但劉璈始終努力想與翁同龢保持良好的關系。一年后,他在中秋節給翁同龢寄贈了四十兩節敬,翁同龢仍然沒有接受。于是,他又讓兒子劉浤再次送去了禮物,不過翁同龢僅接受了三匹臺布、二十支線香和一個茯苓,其余禮物都謝絕了。
出于禮貌,翁同龢也分別給劉璈、劉浤寫信致意,但彼此關系不會太親近了。此后,劉浤還是會去拜見翁同龢,但基本上也是一般的應酬了。后來,劉璈又贈送了銀盒,翁讓人把劉浤叫來把銀盒領回去。
光緒十一年,淮軍將領劉銘傳任臺灣巡撫。由于湘、淮兩軍的門戶之見,劉銘傳一到臺灣便對劉璈進行了彈劾。盡管后人認為劉璈在臺灣頗有建樹,在中法戰爭的臺灣戰役中并無大錯,但此時左宗棠已經去世,朝中無人為他說話。最終,劉璈被革職,籍沒家產,流放黑龍江,很快就病逝了。像劉浤這樣舉止失措的情形,其實并不一定就發生在年輕人身上。李鳳苞從德國大使任上回京,拜見翁同龢。翁同龢對李鳳苞精于西學還是頗為敬重的。臨行,李鳳苞從懷中拿出200兩銀子作為贈禮,翁同龢“力卻之”。李鳳苞只比翁同龢小3歲,當時也是50歲出頭的人了,但這樣的饋贈方式實在讓人難以接受。
再次,位愈高,權愈重,辭卻饋贈更應該是常態。在《翁同龢日記》中,有關前期的受饋情況較為詳細,但越往后,文字記錄也越來越少,其原因有可能是諱言不書。他在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二十日的日記中,寫道:“呂海寰、陳允頤留別,皆卻之,所卻者不可勝記,偶記之耳”。光緒二十三年(1897)七月,已是翁同龢政治生涯的頂峰時期,再過10個月他將被光緒帝開缺回籍。
當時,他的職位是協辦大學士、署戶部尚書、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是真正意義上的政壇核心人物,但此時有關饋贈的記錄越來越少。從上面情形看,可能辭卻得太多,也不愿記了。對于門生故舊贈送的禮物,他也往往“皆受輕者”。從字面來看,翁同龢辭卻的態度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優雅婉轉,對較為熟悉的故舊,往往“固請固卻之”,而對于像馬玉昆、周馥這樣的新進俊才,往往“揮之去”,讓人感覺不佳。
馬玉昆是太原鎮總兵,周馥是北洋派系中的洋務干將。他們出手皆不小,馬玉昆初次見面就送了四百兩銀子,這在翁同龢看來已是巨金。因為不久前翁同龢剛在書估(同“書賈”,即書商)那里見到了宋刻《長短經》,不禁心馳神往,這不但是宋槧中最出色的,而且有乾隆皇帝御題,是《四庫全書》抄錄的底本。書估開價八百兩銀子,他反復討價還價,最后花了三百五十兩銀子得到了這部宋版書。他驚稱是花了巨價才得此瑰寶。現在面對相近數額的饋贈,翁同龢當然覺得不妥當。這種“揮之去”的態度,可能是當時翁同龢的一種做派,這也就是后來他被人攻擊“喜怒見于辭色”“狂悖情態”的具體表現。
當然,翁同龢在晚期并非完全一清如水,就在馬玉昆贈銀不久后,伊犁將軍長庚給翁同龢送了“馬一匹,玉煙壺、翎管各一,虎骨一具,洋蠟一箱,銅盆一,燭臺二,猞猁八只,水獺一”,翁同龢都接受了。他稱萬里遠意,不能卻,并回贈了二套褂袍料。長庚也算是故舊,但更重要的是萬里遠意。這不僅是一個借口,而是真的被感動了。
受與卻,看似不過是受贈方的抉擇,但也存在著潛在的風險。這種明確表示親與疏的行為往往會形成誤解,在政治上造成傷害。張蔭桓曾記得當時恭親王與他聊天,說楊宜治這個人要不得。張蔭桓因為楊是自己的下屬,替他打圓場,說這個人還是非常勤奮的。
甲午年(1894),楊宜治作為隨員出使俄國,臨行向總理衙門大臣張蔭桓贈送了五十兩別敬。張蔭桓認為他是本衙門章京,奉差出京,素來沒有贈送別敬的先例,便非常嚴肅地拒絕了他。這件事在楊宜治內心留下了嫌隙。后來,張蔭桓受到了徐桐、王鵬運等人一系列的彈劾,背后的推動力量都是楊宜治。可見,璧謝饋贈也并不一定會有好的效果。在受與卻之間,往往有著非常復雜的規則在發揮作用,局外人真的難以說明白。當然,當無原則接受成為常態,慶親王的“慶記公司”就出現了,這就成了晚清被人詬病的腐敗亂象。
戊戌變法的前夜,翁同龢被光緒皇帝開缺回籍。他究竟是被慈禧太后還是被光緒皇帝趕出了政壇,史學家有各種不同的說法,或許也有可能是兩者合力的結果。在降旨開缺的第二日,也就是四月二十八日,因為鄰近端午節,太監送來了宮中端午節的例行賞賜——葛紗。翁同龢認為此時不能再接受了,但太監說已請旨,仍賞。翁同龢給了太監二兩銀子的賞錢,把端午節在宮內應發的賞錢也讓他帶回,并結清了自己在國子監、戶部提用的款項,同時通過錢號向在家鄉的外甥俞鐘鑾匯寄了二千兩銀子,交代他妥善保存,因為今后的衣食就靠著這筆錢了。從這一點上看,翁同龢應該算是較為廉儉的官員。十五天后,他黯然出京。
(作者過旭明為文史學者,本文節選自《他助與天助:晚清官員私人經濟狀況研究》一書,廣陵書社2022版,澎湃新聞獲授權刊發。)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