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王家衛(wèi)偏愛自戀、漫無目標(biāo)的角色:折服于岔路前,無意改變
【編者按】
近日,王家衛(wèi)的電影《阿飛正傳》在國內(nèi)公映。據(jù)《亞洲電影》雜志主編加里·貝廷森研究,《阿飛正傳》的人物刻畫以曼努埃爾·普伊格1969年的小說《心碎的探戈》為模板,而《阿飛正傳》和《2046》中潛藏的鳥預(yù)言追溯至威廉斯1950年的小說《羅馬之春》等。
貝廷森認(rèn)為含糊的目標(biāo)推遲了主角的目的行動,因此時間終止和拖延為王家衛(wèi)的敘事定義。或者,表面上主要的目標(biāo)成為泡影,將情節(jié)軸轉(zhuǎn)向預(yù)期之外的路徑。
在《阿飛正傳》中,“旭仔逝去的目標(biāo)所呈現(xiàn)的是人物的自我否決,被生母拋棄的旭仔放棄了追尋個人自尊的重大目標(biāo)。”
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經(jīng)授權(quán)摘選加里·貝廷森《王家衛(wèi)的感官電影:影像詩學(xué)與煩郁之美》部分內(nèi)容。
小說的故事通常包含一個或數(shù)個敘事作用者所扮演或執(zhí)行的一組事件。如梅爾·斯騰伯格(Meir Sternberg)所指出,一個故事能夠構(gòu)建出無數(shù)個不同的情節(jié),每一個皆有自己的時間結(jié)構(gòu)和敘事策略,因此對讀者帶來特有的效果。講述一個已知故事的方式,潛藏著無限的可能。張健德將王家衛(wèi)的故事情節(jié)結(jié)構(gòu)追溯至多元的文學(xué)背景布置。但是,張健德揭示出王家衛(wèi)為情節(jié)素材而探測文學(xué)的典型。舉例而言,《花樣年華》摘選劉以鬯小說《對倒》中的段落,《2046》的敘事和主旨也受到相同作者的小說《酒徒》所影響。《東邪西毒》重新發(fā)掘并改編自金庸長篇舞劍小說的武俠世界。《阿飛正傳》的人物刻畫以曼努埃爾·普伊格(Manuel Puig)1969年的小說《心碎的探戈》(Heartbreak Tango)為模板。還有其他的評論家也進(jìn)一步地探討其文學(xué)的背景。托尼·雷恩(Tony Rayns)認(rèn)為,《春光乍泄》從普伊格的小說中借用了毀滅性同志愛情的創(chuàng)作題材,故事收場于阿根廷的領(lǐng)地中。張健德認(rèn)為普伊格的主角是旭仔的前身,而馬蘭清則將這個角色聯(lián)結(jié)到《2046》里的周慕云。

張健德的研究特別熟練地揭示王家衛(wèi)的文學(xué)挪用和隱喻中的廣博歷史與文化。然而,在這些說明中幾乎完全被忽略的,是田納西·威廉斯對王家衛(wèi)的故事素材所造成的影響,特別是在人物刻畫和環(huán)境氛圍的層次上。例如,我們可以將《阿飛正傳》和《2046》中潛藏的鳥預(yù)言追溯至威廉斯1950年的小說《羅馬之春》(The Roman Spring of Mrs. Stone),以及他于 1955年出版的三幕劇《奧菲斯下凡》(Orpheus Descending)(以及悉尼 ·盧曼特[Sidney Lumet]的改編電影《逃亡者》[The Fugitive Kind,1959])。小說中的男主角保羅(Paolo)這位意大利浪子和旭仔有極為相似之處,威廉斯將他描述為一個有性格缺陷、“急躁狂妄”的舞男,他在精神上的孤獨則展現(xiàn)在他想要“漂泊”的傾向。和旭仔相同,保羅受自身的形象所束縛:在一片段中,他“在(斯通太太) 打斷他自戀的凝視時,在鏡子里露出驚訝的表情”。他和數(shù)個王家衛(wèi)的主角(特別是《東邪西毒》中的那些角色)同樣有種不真實的欲望,想要戰(zhàn)勝痛苦的回憶,并聲稱“不好的回憶是極大的便利”。
這部小說與《阿飛正傳》和《2046》最為顯著的聯(lián)結(jié),即是那任性的鳥寓言,命定永不停歇地飛行。“談及鳥,”保羅被問及,“那只沒有腳的燕子是否真實,而那就是它們總是待在天上的原因嗎?”。威廉斯在《奧菲斯下凡》中重復(fù)使用此一母題,意味著“逃亡者”的“歸屬”之地已被剝奪,此處再一次暗示著旭仔的無根。威廉斯通過他的男性主角瓦爾(Val)闡明鳥的比喻:
你知道嗎,他們是一種沒有腳的鳥,無法停靠在任何地方,因此終其一生必須待在天空中飛翔……這些小鳥,他們完全沒有腳,只能仰賴翅膀度過他們的一生,并休眠在風(fēng)中……他們休眠在風(fēng)中并且……從未曾停靠在地面上,直到他們死去之時。(1961:49—50)
《阿飛正傳》和《2046》同時喚起了這個傳說,而王家衛(wèi)并不僅是挪用這個故事而已。除了描繪人物的特征,無腳鳥的寓言將作者的飛翔母題延伸為一種真實存在的比喻。從此一角度來看,被天束縛的無腳鳥神話與《重慶森林》中的飛機母題有著可共同比擬的功能。如約瑟夫·坎貝爾(Joseph Campbell)所說的:“飛機的航行……是脫離地面的想象。這和鳥所象征的是相同的……鳥象征著脫離束縛落到地面的精神……飛機此刻扮演的正是該角色。 ”阿菲真的飛去了加州,將幻想轉(zhuǎn)變?yōu)檎鎸崳碇鎸嵱苌男袆印H欢谛褡械睦又校瑢⑸ㄙM在“風(fēng)中”,顯然只有象征個人的自由。在針對威廉斯寓言的一篇后記中明白指出,無腳鳥生下來就沒有生命:“那只鳥從未活過。”這正是旭仔的真實處境。不止于衍生的意義,王家衛(wèi)利用威廉斯的寓言推進(jìn)隱晦的人物描寫和作者的主旨。
王家衛(wèi)其他的電影故事題材也令人想起了田納西·威廉斯。王家衛(wèi)證實《藍(lán)莓之夜》是向這位劇作家“致敬”。電影里孟菲斯片段中的溫室氣氛,由蕾切爾·薇茲(Rachel Weisz)所扮演的情欲南方美女和她性無能的伴侶之間的內(nèi)部沖突所引燃,此處高度令人聯(lián)想到威廉斯的情節(jié)劇。此外還有《重慶森林》中林青霞所飾演的毒販。依照王家衛(wèi)的說法,林青霞的角色最初的原型是《欲望號街車》(A Streetcar Named Desire)中費雯麗(Vivien Leigh)所飾演的布蘭奇·杜波依斯(Blanche DuBois)。在最后的分析里,威廉斯對于王家衛(wèi)的影響應(yīng)該不令人感到意外:這位美國劇作家對于這位深深愛好美國電影和文化的導(dǎo)演而言,有著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王家衛(wèi)的所有作品同時擁抱好萊塢電影和美國的圖像研究,他的電影中隨處懸掛著受美國影響的素材。
到目前為止,我已指出王家衛(wèi)偏愛自戀的、漫無目標(biāo)的角色。其他決定故事事件的人物刻畫特征又是什么呢?泛言之,王家衛(wèi)的人物同時拒絕好萊塢英雄明白的目標(biāo)定位,以及藝術(shù)電影主角麻木不仁的被動性。不同于藝術(shù)電影的作用者,王家衛(wèi)的主角構(gòu)思目標(biāo),但是該目標(biāo)的形成包含了矛盾沖突,甚至是負(fù)面的行動計劃。因此,我們發(fā)現(xiàn)遲疑的角色對未來的選擇猶疑不決。的確,劇中主角常常折服于岔路前,無意步入改變。《花樣年華》中那些沒有那么明確定義目標(biāo)的主角即為負(fù)面狀態(tài)的例子。“我們不會像(我們的伴侶) ”,他們?nèi)绱酥鲝垼瑘允匾环蛞黄拗频奈ㄒ话閭H。此處,意志堅定的目標(biāo)定位開展了行動的過程,如此決然的目的是無法求得的。同時,觀影者被提示展開推論一個對照劇中人物所抑制的,更加(真實的)愛情結(jié)合的欲望。因此,電影的敘事未來,取決于劇中人物努力地不行動,此外王家衛(wèi)從觀影者對電影的類型期盼(例如有情人終將結(jié)合),與人物負(fù)面的和矛盾的欲望之間的沖突,進(jìn)而形成引人注目的懸疑。

古典的英雄追求相互和諧的目標(biāo),而王家衛(wèi)的人物所思索的卻是不相容的兩人。周慕云和蘇麗珍兩人相互排斥的欲望,構(gòu)成了情節(jié)劇所需的強烈情緒的要素。在《重慶森林》中,阿菲隱晦地顯露出想要移居美國的目標(biāo),這使得她與663的本土愛情欲望產(chǎn)生混淆。劉德華在《旺角卡門》中飾演身不由己的黑幫,因展現(xiàn)忠誠而身受其擾。特征在于,王家衛(wèi)將故事植入與他們欲望搏斗中的內(nèi)在沖突作用者之中。含糊的目標(biāo)推遲了主角的目的行動,因此時間終止(temps morts)和拖延(longueurt)為王家衛(wèi)的敘事定義。
或者,表面上主要的目標(biāo)成為泡影,將情節(jié)軸轉(zhuǎn)向預(yù)期之外的路徑。在《墮落天使》中,天使 4號(Charlie)瘋狂找尋布蘭蒂(Blondie)卻未曾有個結(jié)果,焦點旋即由無以捉摸的金發(fā)女子轉(zhuǎn)至天使 4號與何志武之間不協(xié)調(diào)的愛情。此外,在《阿飛正傳》中,旭仔和生母和解的目的很快地消散而去,正如波德維爾所指出,這使電影將敘事焦點轉(zhuǎn)移至受旭仔行動所影響的人物命運上。此外,旭仔逝去的目標(biāo)所呈現(xiàn)的是人物的自我否決,被生母拋棄的旭仔放棄了追尋個人自尊的重大目標(biāo)。不變的是,王家衛(wèi)電影中主角是否活躍,在任一時刻皆取決于他們承認(rèn)自我真實欲望的能力。張健德表示這些主角的特征是“病態(tài)的”,但他們或許也可被當(dāng)作是和不真實的存在模式相搏斗的人,關(guān)于這點我將于下一章節(jié)說明。無可避免地,王家衛(wèi)的沖突角色使獨特的行動發(fā)展成為可能。介于古典和藝術(shù)電影的人物刻畫標(biāo)準(zhǔn)之間,王家衛(wèi)的主角皆為目標(biāo)定位的作用者,然而他們的心理復(fù)雜程度引起了麻痹癱瘓的無力感。推論是一種郁積停止的狀態(tài),使故事的“事件變化性”和可預(yù)見性失去活力。
總之,王家衛(wèi)的人物對于真實存在的危急處境存有疑慮,他責(zé)備他的人物落入不真實的樣子。一再發(fā)生的是,這些人物退縮至自我否認(rèn)的狀態(tài),他們可能壓抑真實的欲望和情緒、在社會上自我放逐、否決作為自由個體的人、逃避個人的責(zé)任,并且錯誤地引用“命運”作為行動目的的替代品。舉例而言,在《2046》中,周慕云邀請黑蜘蛛陪同他去新加坡。這名女主角卻通過紙牌游戲做出決定,顯然將她的未來交給了命運。然而,黑蜘蛛抽到 A已是預(yù)料中的結(jié)論,如被打敗的周慕云于旁白中說:“她找到了婉轉(zhuǎn)的方式拒絕我。”如此隱晦和不可捉摸的假托,是王家衛(wèi)的典型主角,他們借由否認(rèn)自身行動的能力而逃避改變。此外,他們退避社會沖突,經(jīng)常導(dǎo)向了其他迂回的社會互動方式,例如《墮落天使》中殺手通過點播機的歌曲遺棄天使。對照那些無可救藥的不真實角色,王家衛(wèi)賦予角色追尋真實改變的潛能。我已說明《重慶森林》中的阿菲和633隨著情節(jié)的推展而活得更加真實,實現(xiàn)了重要的行動和個人的交流。真實性的主旨是王家衛(wèi)故事素材的關(guān)鍵要素。
王家衛(wèi)的主角具現(xiàn)了不同程度的真實性,他們對于愛情也展現(xiàn)出對照的態(tài)度。然而,不論對愛情所抱持的態(tài)度是狂熱的或是無所謂的,王家衛(wèi)的所有角色皆散發(fā)出強烈的情感。王家衛(wèi)偶爾借由他們的感官特征生動地描繪這些人物;他們沉溺于或欠缺了身體上的感受。他們或許被剝奪了視覺(《東邪西毒》中的盲眼劍客)、聲音(《墮落天使》中的何志武),或觸覺(某種程度上《春光乍泄》中的寶榮,及《2046》中具有爭議的黑蜘蛛)。相反地,他們的感覺也可能異常銳利(《春光乍泄》中張宛的播送聲音,及《手》中張震的感觸性)。在每個例子中,這些角色精準(zhǔn)地察覺事物,甚至是表面上堅定不移的角色偶爾也“透漏”出深切的情緒(如《阿飛正傳》里的旭仔或《墮落天使》里的殺手)。若以這種方式去理解,王家衛(wèi)充滿情感的敘事空間,在感官上的制作設(shè)計和音樂的修飾之下,具現(xiàn)化了人物內(nèi)在深沉的情感狀態(tài)。因此,在王家衛(wèi)的電影中,心理上的因果作用不僅開展了行動主線,也支配了情感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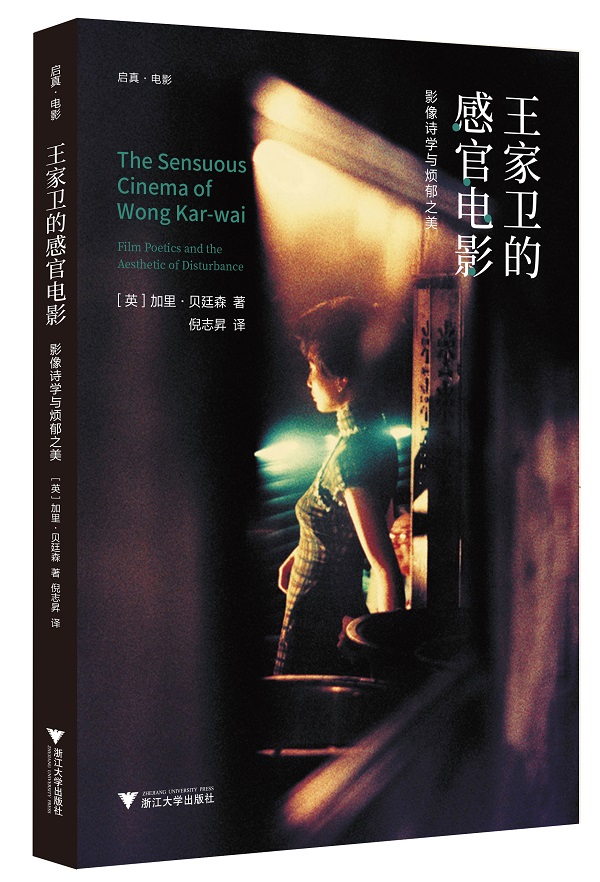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